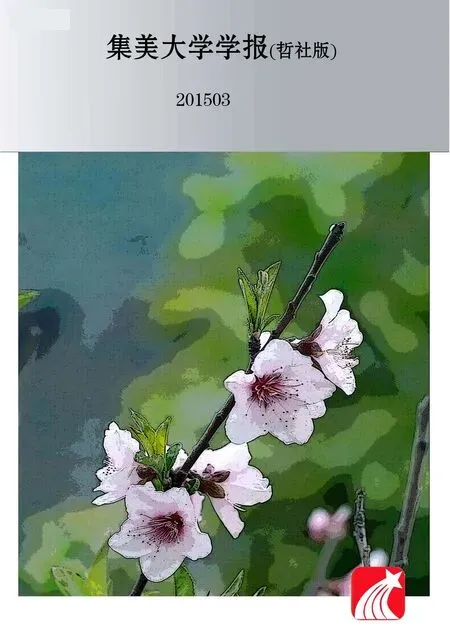李贺与波德莱尔诗歌比较
[摘要]李贺和波德莱尔是生于不同国度且时间跨度近千年的两位诗人,他们在诗歌创作上有着某些共同的趋向,但又同中有异。通过三个方面的比较得出结论,认为:在主题上,李贺表现出苦闷情怀,波德莱尔展示出忧郁主题;在象征手法的运用上,李贺主要是集体式象征,而波德莱尔则单一象征和集体象征并用;在美学风格上,二人都以非美为美,但李贺以诡艳为美,波德莱尔以丑恶为美。这些异同既源于文学观念自身的发生与发展,同时也与诗人独特的气质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有着密切渊源。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9X ( 2015) 03-108-06
[收稿日期]2015-04-27
[修回日期]2015-05-14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研究项目( GD13YZW02)
[作者简介]赵目珍( 1981—),男,山东郓城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汉唐文学和职业人文研究。
李贺( 790—816),我国中唐时期著名诗人,曾因在诗歌中大量表现奇幻怪异之美而被称为“诗鬼”“鬼才”。夏尔·波德莱尔( 1821—1867),法国19世纪中叶著名诗人,1821年生于巴黎,曾因在不朽诗集《恶之花》中大量描写“幽灵”“腐尸”“骸骨”“骷髅”“墓地”而被称为“尸体文学的诗人”和“坟墓诗人”。那么,生于不同国度、时间跨度近千年,并且有着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两位诗人,面对残酷的社会、面对死亡和忧郁的内心,他们在诗歌写作上有什么异同呢?笔者拟从诗歌主题、艺术方法和美学风格三个角度切入探讨二人诗歌的异同点,最后尝试分析造成这种异同的深层原因。
一、苦闷情怀和忧郁主题的抒写
李贺本是唐代宗室后裔。家族早衰和家境贫寒的他常以“皇孙”自居,希冀致身通显。少年之时他便胸怀大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十三首》其五) [1]61 ①当年韩愈和皇甫湜诣门造访,李贺在受命作的《高轩过》中也曾发出“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的高蹈之声。然而自幼体弱多病,壮志难酬的他常因现实的残酷而陷入极端苦闷之中。李贺的忧郁苦闷根源于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给他带来的人生悲剧。李贺因为父亲李晋肃的“晋”与进士的“进”同音而被人议论攻击不得举进士。虽然有韩愈大力为其辩解,但仍然不能摆脱被抛弃的命运。“病骨犹能在,人间底事无?何须问牛马,抛掷在枭庐。”(《示弟》)病骨虽然还在,但是人间什么事没有呢?由于中晚唐的科举腐败,“主司去取,一任其意。”诗人应举失意,“挟策无成,空囊返里”,觉得自己被主司抛弃与牛马被抛掷于枭庐没有分别。(《姚文燮昌谷集注》) [1]208他对未来的仕途充满了担忧并且一直难以释怀。于是,早衰的症状和心态通过沉重的失落感和屈辱感迅速地闪现出来。为此,诗人的壮心时常堕入梦幻当中:“忧眠枕剑匣,客帐梦封侯。”(《崇义里滞雨》)这凝成了他诗歌当中深沉而浓烈的忧郁内涵。
带着沉重的人生关切,李贺短暂的一生其实对命运、生死的理解并不深刻,但是怀才不遇、耽于幻想的他在诗歌中却注入了倍于常人的浓郁色彩。李贺诗中常借助“泣”“啼”“咽”等动词创设出大量的悲感意象,比如“芙蓉泣露香兰笑”“老兔寒蟾泣天色”“孤鸾惊啼商丝发”“衰灯络纬啼寒素”“红弦袅云咽深思”。在颜色词的使用上,李贺也是极尽渲染,他将描写冷色调情态的词语与颜色词搭配起来,将原本单一的色泽硬是推向颓唐境界,像“老红”“衰红”“蛾绿”“颓绿”“碎黄”等呈现的完全是一种病态美。据统计,李贺诗中出现最多的颜色词依次是白、红、青、绿。冷色词系列在简单的修饰中很容易便可渲染出阴沉死寂的境界。但是,在李贺那里,即使比冷色意象占比例多的暖色意象也同样宣示了他内心的苦闷与冷落幽肠,并且与颓废情态词的搭配更加剧了他内心世界的异化程度,使他的诗篇呈现出既艳又郁的美学特质。不过,在这一特质当中, “艳”只是一种表象,“郁”才是它的本质。无情的现实最终还是将李贺的理想击打的粉碎。“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赠陈商》)“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正如姚文燮在《昌谷集注》中所说的“功名成败,颠倒英雄”, [1]208李贺最终还是在悲观绝望中于27岁那年潦倒辞世了。
与李贺一样,波德莱尔也在他传世的200余首诗篇中或隐或显地宣泄了内心的苦闷。不同的是李贺在对忧郁主题的展示中,主要侧重于幻想,而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以抒写现实的成分为多。
《恶之花》诗集共分6组展示。第一组“忧郁和理想”叙述诗人内心的忧郁以及意欲摆脱忧郁的理想,这组诗歌占了诗集全部的2/3,显示出“忧郁”主题在诗集中的分量举足轻重。波德莱尔幼年失怙,母亲改嫁。家庭的变故和环境的改变,给他的心灵带来巨大创伤,这使他养成了忧郁、孤僻的性格。“诗人不被周围一切人理解,而且受到诅咒。他的母亲和妻子也误解他,轻视他”。 [2]11 ①后来,他一度挥霍、放荡以至于靠卖文拮据度日。最后因失语和半身不遂,在46岁时抑郁而死。从《恶之花》中,我们的确可以感受到波德莱尔一以贯之的忧郁主题,在《患病的诗神》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悲惨状态:“我可怜的诗神,今朝你怎么啦? /你深陷的眼睛充满黑夜幻象。/我看你的脸色在交替地变化,/映出冷淡沉默的畏惧与癫狂。/ /是绿色的淫魔和红色的妖魔/用小瓶向你灌过爱情和恐怖? /捏紧专制顽强的拳头的梦魔/曾逼你陷入传说的沼泽深处?”从这一首开始,接下来的10首诗诗人都在描述自己的“阴郁无聊”或者“精神上痛苦的深渊”。在《大敌》中诗人为痛苦的青春寻找希望:“我的青春只是黑暗的暴风雨……谁知道我所梦想的新的花枝,/在被冲洗得像沙滩的土壤里,/能否找到活命的神秘的营养? / /——啊,痛苦!啊,痛苦!时间侵蚀生命,/隐匿的大敌在蚕食我们的心。”然而,由于青春被曝于黑暗的暴风雨中,诗人对梦想和生命充满了莫可名状的痛苦。
诗人的这种痛苦在以“忧郁”为标题的四章诗篇里展示得更加淋漓尽致:第一首写诗人面对阴雨连绵的巴黎冬季,“像怕冷的幽灵似的发出哀号”;在第二首中,诗人将自己比作“连月亮也厌恶的墓地”和“充满枯蔷薇的旧日女客厅”,在多雪之年的沉重的雪花下面,阴郁的冷淡所结的果实——“厌倦”正在扩大成为不朽之果的时光;在第三首中,诗人将自己比作“一个多雨之国的王者”,借未“豪富而且无力,年轻而已衰老”的国王的冷漠和绝望来表达自己对无聊的厌倦;在第四首中,诗人深陷忧郁,仿佛置身牢狱,最后终于在极端的痛苦中得到爆发,然而在诗的末尾诗人又陷入绝望:“‘希望’失败而哭泣,残酷暴虐的‘苦痛’把黑旗插在我低垂的脑壳上。”他像一个被永判失败的勇士,积聚的忧郁在死亡的幻觉中一度沉溺。诗人在《破坏》中还将残忍与快乐结合来发现美,反映出诗人由无聊而产生美的忧郁本质。《不可救药者》在《恶之花》中被看作是“忧郁与理想”的结论,用来阐明“忧郁”的奥义。诗人在诗中叙述自己处于不可救药的状态,把自己形象化地比喻成“堕落的恶天使、不幸者、亡魂、被冰封的航船”,并将自己在灵魂中的恶魔功业和恶中的意识进行了分析,表现出自省的一面。然而对于内心的“忧郁”,诗人却欲罢不能,因为这“恶中的意识”恰恰是“一面意识到恶,一面又作恶”。 [2]177诗人反复地处于矛盾的苦痛当中。诗人本想借对美的追求和爱情的陶醉来排除内心的抑郁,但是未能如愿以偿。为此,诗人摆脱精神压力转向现实世界,结果丑恶、残酷的“巴黎风光”(第二组)却使他转向了“酒”(第三组)与“罪恶”(第四组),诗人叫嚣似地对天主发出“反抗”(第五组),然而最终还是在无济于事的凄凉中倒向了“死亡”(第六组)。
二、象征艺术手法的两个维度
波德莱尔因在十四行诗《感应》中首度引用了瑞典哲学家斯威登堡的术语“感应”和“象征的森林”,由此被认定为象征主义的始祖与先驱,《感应》也因此成为“象征主义的宪章”。受爱伦·坡的影响,他认为象征是一种固有的观念存在,大自然本身就是一座“象征的森林”,它暗示了很多复杂的含义。后来,“象征”成为象征主义流派最基本的创作原则。正如聂珍钊在《外国文学史》所说:“在艺术上,象征主义广泛使用象征、暗示、隐喻等方法,表现自然现象和自我,认为艺术表现只能是象征,诗歌就是暗示,即梦幻,主张用象征性的事物暗示主题和作者微妙的内心。” [3]327值得注意的是,波德莱尔不仅提出了这一概念,而且进行了理论实践。
在《恶之花》中,波德莱尔大量使用象征,简单如“永远的播种者”象征“基督”(《酒魂》),“通往十字架的路”象征“基督受难的路”(《祝福》),“无限碧空”象征“天国”(《忧郁与理想》第25首),“天鹅”象征“流亡者”(《天鹅》),“大蛇”象征“嫉妒”(《献给一位圣母》),这一类象征比较简单。另外,诗人还选择了大量的丑恶、邪恶的意象入诗,并且在诗中反复呈现,有时候虽不是同一事物相反复,但是作为同类事物,它们的繁复也构成象征。比如诗人在《致读者》中提到的“豺狼”“豹子”“猎犬”“猴子”“蝎子”“秃鹫”“毒蛇”,它们合起来就是一种象征,象征着现代人卑劣的罪恶。同一诗篇中,诗人还提到在罪恶污秽的动物园里“有一只更丑、更凶、更脏的野兽! /……这就是‘无聊’!”(《致读者》)“无聊”或者其同义词在诗人诗作中也反复呈现,比如“在无聊之时”(《破钟》),“深沉而荒凉的‘无聊’的狂野”(《破坏》),“烦闷、厌倦、厌腻”(《忧郁》四篇),“空虚的心”(《共感的恐怖》),它们也是一种象征,象征作者那个时代的“世纪病”,包含厌倦、厌恶、萎靡不振、失意、忧郁等。它们与“恶之花”的表达同义。其实“恶之花”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恶之花》的“恶”在法文中即是邪恶、丑恶、罪恶、疾病、痛苦之意,所以“恶之花”也即是那个时代“世纪病”的一个巨大象征。
“‘象征’具有重复和持续的意义。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一个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个部分”。 [4]204从韦勒克和沃伦的这一观点看,隐喻乃是象征的一个低级层次。不过,“意象”却是构成“象征”的不可缺少的因素。象征有时是由单个意象反复出现形成的,笔者将之称为“单一象征”,比如波德莱尔诗歌中所用的“简单象征”。有时是由意象群(即同类意象)反复出现形成的,笔者将之称为“集体象征”,比如波德莱尔诗中所使用的“繁复象征”。它们构成了象征表现的两个维度。李贺与波德莱尔在象征的使用上有着不尽相同的表现方式。与波德莱尔使用象征既有“单一象征”也有“集体象征”不同,李贺诗中的象征主要体现为集体式的。
“象征”与“意象”有着必然的联系。李贺在其诗中反复大量地抒写神仙灵异和妖魅鬼怪,但是他使用的这些意象多是“寄意式”(寄托情感)的,它们本身并不构成单个的象征。据统计,李贺现存的诗歌中以神仙为题材的比以鬼蜮为题材的要多出一倍多,不过李贺大量描绘阴森恐怖的鬼蜮的目的主要在于为苦闷作渲染,而神仙世界则俨然一个象征系统。李贺写神仙世界的意象如“王母”“上帝”“灵书”“凤凰”“仙鹤”“青龙”“瑶草”等奇特而充满幻想,其实李贺更注重的是它们对于神仙世界整体意境的烘托营造,在《天上谣》一诗中,他不吝笔墨地写道:“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珮缨。秦妃卷帘北窗晓,窗前植桐青凤小。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粉霞红绶藕丝裙,青洲步拾兰苕春。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这样如梦如幻的天上仙界无疑是李贺在与人间苦闷的对比之后幻设出来的,它其实就是李贺心目中的“桃花源”,是一个瑰奇而又美丽的象征。鬼蜮世界从整体看,可以看作是李贺“苦闷世界”的象征,但是作为同是由苦闷幻化出的神仙世界,它也是李贺“苦闷世界”的一部分。可以说,鬼蜮世界和神仙世界合起来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集体象征”——那就是李贺的“苦闷情怀”。
三、以丑恶为美和以诡艳为美
通读李贺和波德莱尔二人的诗,我们可以很直观地发现,李贺和波德莱尔的笔下都走动着大量的异感意象,但它们在诗中游移所造成的美学效果却大不相同。从审美上看,他们都以非美为美,但李贺以诡艳为美,而波德莱尔以丑恶为美。
人们从《恶之花》中很容易误解波德莱尔,以为他对丑恶充满了迷恋和喜狂,其实《恶之花》是从反面来表现诗人对美的激赏和追求,而且诗人作诗的态度神圣庄严。诗人曾断言:“绝对不是那种见之于流氓世纪/变质的产品、装饰图案中的美人、/穿高帮鞋的脚、拿响板的手指,/能够满足像我这一种人的心”(《理想》),“我们具有如人所说的颓废之美; /可是,我们这些迟生的缪斯的发明,/永远阻止不了病态的吾民/把我们由衷的崇敬之情献给青春”(第一组第5首)。在《太阳》篇中,他把诗人的使命与太阳的功德等量齐观,而“同美的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的欧洲后世神学的终极根源,就在于《理想国》中那一伟大的譬喻:把太阳和它的光比作是绝对的善及其表现的产物和象征。” [5]39诗人在《恶之花》献词中说:“将这些病态的花呈现给完美的诗人”,诗人原是要从丑恶中来发掘艺术之美,正如《小老太婆》中所说的“连恐怖都变为魅力之处”,这是波德莱尔描写城市风光的独特的表现手法。于是那些邪恶、丑恶、罪恶的意象如“跳舞的蛇”“腐尸”“吸血鬼”“幽灵”“猫头鹰”“墓地”“骷髅”“血泉”“撒旦”便从诗中扑面而来。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些带有异感色彩的意象站立于真善美的对面,然而有时却成了诗人赞美的对象。在“叛逆”中,他以撒旦为“被迫害者、流亡者、失败者”;在“死亡”中,他以死亡为“天使”,显露了诗人的反抗精神。
“诅咒虽然使诗人尝到这样的烦恼,诗人自己却把它当做可贵的考验,当做神圣的灵粮而乐意接受”。 [2]11为此,诗人把美比作“地狱的神圣的眼光”和“巨大、恐怖而又淳朴的妖魔”,认为它“随手撒下欢乐和灾祸的种子,/统治一切,却不负任何责任”。(《美的赞歌》)在《恶之花》中诗人尽力地以丑恶为美,为了达到这一效果,他不惜借助那些最恶俗的事象入诗,比如“在魔女宴会当中被烹煮的胎儿”“堕落天使出没的血湖”“吻你吃你的蛆子”等等,想化腐朽为神奇。他描述“一群恶魔,仿佛数不清的蛔虫,/麇集在我们的脑子里大吃大喝”(《致读者》)描述路旁的死尸:“苍蝇嗡嗡地聚在腐败的肚子上,/黑压压的一大群蛆虫/从肚子里钻出来,沿着臭皮囊,/像粘稠的脓一样流动”,不仅令人骇异,而且达到了令人恶心的地步。尽管与波德莱尔大约同时期的雨果在其《〈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了“丑就在美的身边,……滑稽丑怪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和对照,是大自然所给予艺术的罪丰富的源泉”的观点, [6]493-495“但是,雨果表现的是下层人的穷困,而波德莱尔则着意于穷人和残废者形体的丑,通过这种丑来表现这个社会生长的痈疽现象”。 [7]185像波德莱尔这样恶俗的描写,前所未有。“总的来说,波德莱尔以丑为美,化丑为美,这在美学上是具有创新意义的。以往的作家也有写丑的……然而波德莱尔更进一步,他意识到从丑中可以提炼出美,丑就是美。这种观点是现代文学,尤其是20世纪现代派文学遵循的原则之一”。 [7]188正因为此,我们说波正德莱尔在法国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与波德莱尔相通的是,李贺作为韩孟诗派后期的突起异军,也借奇特的造语和怪异的想象勾勒了一个迥异于常人的独特世界,不过李贺表现出的是另类的凄艳诡激美。这种美,以凄艳和诡激两种美学风格为主体,同时又互相渗透。比如李贺的诗句:“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以“秋坟”和“鬼”的冷色意象融入“碧血”的艳丽,从而产生出怪诞冷艳的特征。对于颜色词的使用,李贺也常将红、绿等原本简单的色泽推向“老红”“愁红”“蛾绿”“颓绿”“碎黄”这样的郁艳,呈现给我们一种病态的特质。“李贺也多用质地锐利、脆硬、狞恶的物象,辅之以剪、斫、古、死、瘦、血、狞等字词,营造一种瘦硬、坚脆、狠透、刺目的意象。……或惊心刺目,或幽凄冷艶,大都是一种怪奇、畸形的审美形态。” [8]268李贺诗歌中时常出现“鬼灯”“老鸮”“鬼雨”“山魅”“萤光”“碧火”“老鱼”“瘦蛟”“猩唇”“啼鸦”“酸风”“铅水”“鬼母”“香魂”“鲸鱼”这样的意象,或写荒山野岭秋坟鬼唱,或写阴森墓地萤火扰扰,或写惨淡黄昏老树滴雨,或写碧火巢中山魅食人。钱钟书先生对李贺此种诗境的独特性曾有揭橥,并且给予他很高的地位:“自楚辞《山鬼》、《招魂》以下,至乾嘉胜流题罗两峰《鬼趣图》之作,或极诡诞,或讬嘲讽,求若长吉之意境阴悽,悚人毛骨者,无闻焉而。” [9]130其实,李贺诗中凡有色调调和的阴凄氛围的描写,并没有达到所谓“悚人毛骨”的程度。后人多以为李贺走的仍是韩愈“以丑为美”的路数,“李贺可以说是以丑为美来写诗的专家。他常常把向来为人们所厌恶的东西写的色彩斑斓”。 [10]200其实李贺并非简单地以丑为美,他与韩愈的以丑为美有着很大的不同,李贺乃是以“诡”来糅合美的。
“象征主义为通感理论提供深奥的理论依据,也宣扬神秘经验里嗅觉能听、触觉能看等等”。 [11]72波德莱尔在《感应》中首度引用“感应”的概念表达了其美学思想。他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之间,外部世界与人的精神世界之间都存在内在的感应关系。这种“感应”在心理学上即被称为“通感”或“感觉移植”。在《感应》中诗人使用了这样的例子:“有些芳香新鲜得像儿童肌肤一样/柔和的像双簧管,绿油油像牧场”,但其表达出来的效果与其以丑恶为美的美学风格却并不相称。其实,在波德莱尔的诗中,通感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表现丑而设的。但在李贺那里,通感的使用却将其诡艳的美学风格更加深了一步,比如其写“酸风”“香雨”,味觉与触觉通感;写“箫声吹日色”,听觉与视觉通感;写“月光刮露寒”,视觉与触觉通感,通过不同感官的转换,将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情态与事物(或事物与事物)联系到一起,产生了复杂的与众不同的美学效果。
四、余论
以上从三个方面对李贺和波德莱尔进行了比较。从对二人的对比研究中,可以发现某些中外文学共生的发展机制,同时也可以透过中西文化来剖析一下二人诗歌产生差异的原因:
在主题上,二人通过对内心和现实的抒写,一个展示出忧郁主题,一个表现出苦闷情怀。忧郁主题和苦闷情怀的抒写,一直是中外文学写作的重要母题,无论时代早晚,还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如何不同,对这一母题的表现始终都是中外文学所共生的。不同的是,波德莱尔通过抒写现实来表达主题的成分较大,而李贺则偏重于以幻想来展示。这与二人的人生经历以及诗人的个性气质密切相关。
象征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也是中西文学所共生的。不过由于中西不同的诗学传统和个人境遇不同,表现出来有些差异。西方的诗学传统是史诗传统,在大量的史诗中本就存在很多单一象征,这在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下很容易显现出来。而作为象征主义文学流派的先驱,波德莱尔在表达个人苦闷的同时,将个人的内心与外在的现实世界建立起联系,发掘出了大量暗示或隐喻的意象群,它们反复地出现便构成巨大的象征。中国的诗学传统是抒情传统,作家常常通过某些特定的具体形象以表现与之共鸣的思想或情感,而很少表现相似的概念。即使借助想象与外在世界建立联系,也常常是作为驰骋感情的手段。加以中国的史诗意识并不强烈,所以诗学中很少单一的象征。李贺本人因受社会现实的打击转而耽于幻想神仙世界,这个由愁思、抑郁的积聚幻化出来的“桃源世界”真正是他个人潜在意识的一种闪现,由此形成他诗中的集体象征。就中西文学的比较看,中国诗学偏于主观,西方诗学偏于客观,所以波德莱尔的象征主要是客观性的,李贺的象征主要是主观性的。
在美学风格上,波德莱尔与李贺共同发展深化了以非美为美的审美机制。波德莱尔发展了爱伦·坡、雨果等人的理论,并进一步将之深化;李贺继承了韩愈、孟郊等人的写作路数而有进一步的拓新。中西文化对比来讲,西方注重分析、综合,加以波德莱尔艺术观中本就有正视现实的一面,所以他能够以现实中的丑恶为美;中国侧重主观上的感官体验,感性意识强烈,加以李贺不敢正视现实,常常因苦闷而耽入幻想,所以李贺注重以色、声、形、味等的结合来虚化诗歌的诡艳美。诗的美学风格总是在嬗变的,这同样符合中外文学共生的发展机制。两人都在诗歌美学的发展道路上起到了里程碑的意义。
结合以上分析来看,李贺与波德莱尔这两位异域异时的天才诗人,在诗歌创作上有着许多共同的趋向,但又同中有异。这些异同既源于文学观念自身的发生发展,同时也与诗人的个性气质以及中西文化差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细节的角度入手,二人之间尚有许多问题可以比较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