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占领初期敦煌部落设置考
陈继宏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元786年,在围城11载之后,吐蕃终于以“勿徙他境”的和平方式入主敦煌。*关于吐蕃占领敦煌的时间,学界有各种说法,参看金滢坤:《敦煌陷蕃年代研究综述》,《丝绸之路》1997年第1期,第47—48页。兹采用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贞元二年(786)说,参看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第1—7页。对吐蕃统治者而言,首当其冲的问题无疑是以何种方式来有效管理当地百姓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虽然吐蕃已有统治吐谷浑等地的经验,但和管理汉地显然不同。吐谷浑与吐蕃一样,皆为游牧民族,“有城郭,不居也,随水草,帐室、肉粮”*《新唐书》卷221《西域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24页。,相同的社会形态和生活、生产方式使得吐蕃在征服吐谷浑后可继续保留其原有部落制甚至扶植傀儡政权来辅助自己进行统治。*邓文科:《试论吐谷浑与吐蕃的关系》,《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第14—21、31页;杨铭:《论吐蕃治下的吐谷浑》,《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106—109页。而敦煌地区则早已进入封建制的农业社会,社会形态、生产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于吐蕃。这种差异反映在行政区划上,就是唐“县—乡—里”制与吐蕃部落制的区别。可以想见,不同于吐蕃部落制的行政建制必然不为吐蕃统治者所容,留守敦煌的吐蕃官员们遂着手推行了从乡里到部落的改制。
如若从部落设置的角度对吐蕃统治敦煌史做一粗略的时段划分,或可将自786年占领至790年正式设置部落视为初期,将790年至820年重新设置军部落视为中期,将820年之后直至848年张议潮起义视为后期。从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相较于中、后两期汗牛充栋的成果,初期的研究由于资料的局限相对较少。但是,初期作为从乡里制向正式部落制的过渡阶段,弄清其间的部落设置至关重要。因此,笔者不揣谫陋,拟立足于敦煌出土文献和前人研究基础,对这一时段敦煌的部落制做一梳理与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已有的学术成果中对吐蕃占领初期的敦煌部落制另分时段专门论述者并不多见,前辈学者们对此时期所设部落的探讨往往夹杂在对整个吐蕃时期敦煌部落制总况或其他相关问题的论述之中,因此较为零散。藤枝晃在《敦煌的僧尼籍》一文中据S.2729《吐蕃辰年(788)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论及吐蕃统治初期敦煌的僧尼部落,*藤枝晃:《敦煌の僧尼籍》,《東方学報》第29册,1950年,第285—338页。后又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一文中探讨了僧尼、擘三等部落的性质,但他并未对文书中出现的诸如悉董萨、阿骨萨、丝绵、行人、僧尼、擘三、上、下等部落做时间先后的区分,视它们为同时并存。*藤枝晃:《吐蕃支配期の敦煌》,《東方学報》第31册,1961年,第199—292页;刘豫川、杨铭译:《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上、中、下),《长江文明》第7辑109—124页,第10辑100—121页,第11辑84—100页。山口瑞凤在《敦煌的历史·吐蕃统治时期》中提出来自吐蕃本土的擘三(phyug mtshams)部落在吐蕃占领初期驻留敦煌一带统治当地百姓,汉人居地被分为左、右二区,称上、下部落。*山口瑞凤:《吐蕃の敦煌支配期间》,《講座敦煌2·敦煌の歴史》,大东出版社,1980年,第197—232页。王尧、陈践《吐蕃占有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探索——敦煌藏文写卷P.T.1083、1085号研究》一文持类似观点,认为敦煌的部落设置一开始是以吐蕃部落(如擘三)为核心将汉户收编管理,社会日趋安定后才编制纯汉户部落。*王尧、陈践:《吐蕃占有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探索——敦煌藏文写卷P.T.1083、1085号研究》,《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第171—178页。姜伯勤《沙州道门亲表部落释证》一文专对“道门亲表部落”进行考证,断之为吐蕃占领初期由敦煌的道士、女官及其内外亲组成的部落。*姜伯勤:《沙州道门亲表部落释证》,《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第1—7页。杨铭《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兼及部落的内部组织》*杨铭:《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兼及部落的内部组织》,《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第34—40页。、金滢坤《吐蕃统治敦煌的社会基层组织》*金滢坤:《吐蕃统治敦煌的社会基层组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27—35页。等文则按时间将敦煌文书中各部落出现的先后次序做了排列,其中涉及落蕃初期的僧尼、道门亲表、擘三等部落,但只划分了790年、820年两次部落设置时间,对初期的情况未能详述。陆离《敦煌的吐蕃时代》将吐蕃时期敦煌的部落设置分初、中、后三期阐述,对落蕃初期敦煌的部落设置情况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陆离:《敦煌的吐蕃时代》,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7—29页。从以上成果可以看出,在前辈学者的努力下,吐蕃占领初期敦煌的部落设置情况日渐清晰,笔者正是在此基础上,拟对该问题做一个更为全面的梳理。
二、敦煌落蕃前的行政建制
唐朝的行政建制沿袭前代郡县制而来,又因“自隋季丧乱,群盗初附,权置州郡,倍于开皇、大业之间”,太宗遂针对这一弊端于“贞观元年,悉令并省” ,*《旧唐书》卷38《地理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84页。并根据山川形势分天下为十道,曰: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景云二年(711)又将山南道分为东、西两道,自陇右道黄河以西分出河西道,分贞观十道为十二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再改十二道为十五道,“分天下为京畿、都畿、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山南东、西道、剑南、淮南、江南东、西道、黔中、岭南,凡十五道”*《资治通鉴》卷213“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二十一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803—6804页。,道下设州(府)—县—乡—里各级行政建制。其中县以下的乡、里处于唐朝行政建制的最末,是直接管理编户齐民的基层组织。其设,据《通典》载:“大唐凡百户为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为一乡,乡置耆老一人,以耆年平谨者县补之,亦曰父老。”*(唐)《通典》卷33《职官十五·乡官》,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2页。
敦煌原属陇右道,景云二年从陇右道分出河西道后又辖于河西道。据《新唐书》载:“沙州敦煌郡,下都督府。本瓜州,武德五年曰西沙州,贞观七年曰沙州。……户四千二百六十五,口万六千二百五十。县二。敦煌、寿昌。”其中寿昌县几置几废,“武德二年析敦煌置,永徽元年省,乾封二年复置,开元二十六年又省”*《新唐书》卷40《地理四》,第1045页。,其地并入敦煌县,为寿昌乡,再加上粟特移民聚居的从化乡,构成了P.2803《唐天宝九载(750)八至九月敦煌郡仓纳谷牒》中记载的十三乡,即敦煌乡、莫高乡、神沙乡、龙勒乡、平康乡、玉关乡、效谷乡、洪池乡、悬泉乡、慈惠乡、洪闰乡、寿昌乡、从化乡。简言之,当时的沙州辖于河西道,州下只有敦煌一县,下辖十三乡,这就是敦煌落蕃以前的行政建制情况。
此处还需谈及吐蕃的行政建制以作参考。吐蕃是居住于青藏高原一带的藏族古代先民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其政权性质是奴隶主军事部落联盟,部落是这一政体的基本细胞。据《贤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时期曾“将吐蕃划作五大茹(ru-chen-lnga),划定十八个地区势力范围(yul-gyi-dbang-ris-rnam-pa-bco-brgyad),划分六十一个‘桂东岱’(rgod-kyi-stong-sde-drug-bcu-rtsa-gcig)。”*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黄颢、周润年译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页。“东岱”即是汉文史料中的部落,相当于唐行政建制中的乡一级。这些部落平日各有驻牧之地,一旦中央政府对外进行军事行动——特别是需要联合作战的重大行动之时便以部落名义参战*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09页。。汉籍中所载的“虏法,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耕牧”*《新唐书》卷216《吐蕃下》,第6108页。,正是这一制度的真实写照。
三、吐蕃占领敦煌初期的部落设置
基于上述唐与吐蕃在行政建制上的不同,吐蕃占领敦煌之后必然会着手进行改制,以更好地管理和组织当地百姓按照自己的统治方式进行生产和生活。但编制部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此时的敦煌刚刚经历过战争的蹂躏,粮械皆竭,民生凋敝,加之战乱导致的人口迁徙和流失、户籍的混乱,这些都增加了实施部落制的难度。显然,在占领之初尽快稳定敦煌社会,安抚当地民众,重新编订户籍,才是为最终的部落改制打好基础的上策。吐蕃统治者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在占领初期一方面采取“只更名、不改制”的保守策略,在敦煌设立蕃名唐制的所谓“乡部落”、僧尼部落和道门亲表部落,依靠原有行政组织进行检阅户口、重新编籍的工作,另一方面又派遣吐蕃官吏担任监部落使对占领区民众加以监管。事实证明吐蕃的这一策略较为成功,经此准备阶段,终于在790年完成真正意义上的部落设置。鉴于吐蕃这一时期在敦煌的部落设置体现出对世俗人口和宗教人口分而治之的特点,以下笔者将从这两个方面入手进行论述。
(一)世俗人口
1.“乡部落”
有关“乡部落”的记载出现在敦煌文书P.2259V《龙勒乡部落管见在及向东人户田亩历》中:
龙勒乡部落,合当部落管见在及向东人户总二百十(?)五户。九十二全家向东,□廿八有田。*《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15页。
虽然乡名后加“部落”的例子笔者目前仅见到此例,但可以据此推断吐蕃占领敦煌初期对当地民众的管理政策,即:保持敦煌原有乡的建制、规模甚至名称,只在乡名后缀以“部落”二字区别于唐朝以宣示主权。如此,则吐蕃占领初期在敦煌设置的此类“乡部落”应同原来的乡建制一样有13个。另一件吐蕃时期的文书S.11344Av·Bv《官人封户名簿(?)》中记载的乡部落官吏数量正好可以印证这一推测,兹录文如下:
S.11344Av:
(前缺)


(后缺)
S.11344Bv:
(前缺)


(后缺)*[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英藏敦煌文献》第13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1页。
陆离指出,文书中的“效”指效谷乡,“沙”指神沙乡,“部落使”“副部〔落使〕”即吐蕃占领初期所设乡部落官员。*陆离:《敦煌的吐蕃时代》,第28页。从S.11344Bv的记载可知当时敦煌的部落使及副部落使有36人之多,按吐蕃于790年设置真正意义上的部落时只有行人、丝绵等为数不多的几个部落,不会有如此之多的官吏配置,则这36人当为吐蕃统治初期保留原有十三乡基础上所设官吏无疑。鉴于吐蕃进入敦煌后对率众抗蕃达十一载之久的领袖人物阎朝都授予“大蕃部落使、河西节度”*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一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0页。以继续维持其在敦煌的地位,笔者以为这些人当为敦煌陷蕃前的原各乡乡官。
吐蕃在新进入敦煌时实行这样的政策的原因在于:一来吐蕃与敦煌订立城下之盟的条件是“勿徙他境”,如此,则保持原有乡的建制规模不变,甚至保持原有管理者的地位不变,有利于尽快地安定民心。二来敦煌久罹战争,户籍早已混乱,且民众仍处于流动状态,如上引P.2259V中就记有“向东人户”,这类东奔人户在其他文书中亦有记载。再如S.5812号《丑年八月女妇令狐大娘牒》亦记载了敦煌百姓东行的情况,文书曰:“尊严舍总是东行人舍收得者为主居住,两家总无凭据,后阎开府上尊严有文判……论悉诺息来日,百姓论宅舍不定,遂留方印,已后现住为主,不许再论者。又论莽罗新将方印来,于亭子处分,百姓田园宅舍依旧,亦不许侵夺论理”,此外文书还记载了打官司一方张鸾的女婿“吴诠向东”之事。*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87页。据此可知,吐蕃占领敦煌初期由于部分百姓东向逃走,房屋为留守百姓收为己用,因而一度引发归属权之争。
在这种尚未安定的情况下,吐蕃统治者很难着手进行部落改制,因此就像龙勒乡的情况一样,他们只将乡名更为部落,实际上仍保持原有建制和官吏,逐步对现有民众进行户籍、田产登记。据P.3774号《丑年(821)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记载:“一大兄初番和之日,齐周阝(附)父脚下,附作奴。后至佥牟使上析出出(衍)为户,便有差税身役,直至于今。”*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284页。佥牟使即是负责户口清查的官员,吐蕃通过户口清查,将未入征税户籍的人口析出(如文书中“附作奴”的民户),以便对更多民户征税课役。至于佥牟使清查人口的时间,从该文书的记载中也可知一二,“□□□至阎开府上,大番兵马下,身被捉将。经三个月,却走来,在家中潜藏六个月。齐周咨上下,始得散行。至佥牟使算会之日,出钿贝镜一面与梁舍人,附在僧尼脚下”*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283页。。齐周自“大番兵马下”身被捉将后,先“经三个月”逃走,后又“在家中潜藏六个月”,此已有九月,“始得散行”之后至佥牟使“算会之日”应该又有一段时日,则可推断佥牟使清查户口至少在吐蕃占领敦煌一年左右以后。另一件文书S.2729《吐蕃辰年(788)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更明确记载“辰年三月五日,算使论悉诺罗接谟勘牌子历”*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 1990年,第194页。唐耕耦、陆宏基录为“算使论悉诺罗按谟勘牌子历”,此“按谟”当为“接谟”误,“接谟”即“佥牟”,二者发音相近。,此辰年据藤枝晃、陈国灿皆考证为788年,距离敦煌陷蕃正好一年有余。从这条记载还可以看出,负责清查户口的佥牟使(算使)论悉诺罗为吐蕃人,结合P.3774号文书中“出钿贝镜一面与梁舍人”始得“附在僧尼脚下”的记载可推断,吐蕃人论悉诺罗只是总管户口清查工作,进行具体工作的仍是当地汉人小吏如梁舍人之流。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吐蕃在占领敦煌初期未正式设置部落前仍保留原有乡的规模和沿用当地乡官来管理民户的事实。辰年的户口清查为吐蕃在敦煌的首次户籍检阅,为正式设置部落奠定了基础。之后户籍制度不断完善并最终确立,P.3432《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依蕃籍所附佛像供养具并经目录等数点检历》载“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依蕃籍所附佛像供养”*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 1990年,第2页。,此“蕃籍”说明吐蕃时期的户籍制度此时已完全确立。
另一方面吐蕃政府直接委派官员对敦煌的事务进行监管,除了尚绮心儿这样身居相位的要员坐镇敦煌总管各项事务外,吐蕃还派遣了中、底层官吏来处理具体事宜,如前引S.5812号文书中记载的论悉诺息、论莽罗新等就持方印评断百姓田园宅舍争端。另一类基层官吏应该就是吐蕃占领初期的文书中出现的“监使”“监部落使”,如P.2763号V1《巳年(789)沙州仓曹会计牒》记载:“贰硕麦十月廿三日牒贷吐蕃监使软勃匐强。捌硕肆斗麦,十一月七日贷监部落使名悉思恭。”*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第486页。P.2654号《巳年?(789?)沙州仓曹会计牒》记载:“贰硕麦,十月廿三日牒贷吐蕃监使软勃匐强。……十一月七日,贷监部落使名悉思恭肆硕。”*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第492页。“监使”应是“监部落使”的简称,这两件文书的年代均为789年,在790年正式分部落之前,则所载的监部落使软勃匐强、名悉思恭应该就是对敦煌乡部落进行监管的吐蕃官吏。
2.擘三部落
“擘三部落”一语出自吐蕃时期的敦煌汉文文书,显然这并非一个汉语词而是音译的藏语词,其藏文对音藤枝晃考订为phyug mtshams gyi sde,为一来自吐蕃本土中部的中翼伍茹(dbu ru)的部落。*王尧将phyugs mtshams音译为“球村”,系按现代藏语音译。陆离指出,在吐蕃时期藏语声母中辅音和后辅音还未融合成一个音素,则phyugs读音近似“破”,与宋代“擘”的读音“补革切”非常接近甚至相同。参看《吐蕃金石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8页;《王尧藏学文集》卷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183页表二;陆离《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行人”、“行人部落”》,《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第85—94页。杨际平对S.3287V《子年(公元九世纪前期)五月左二将百姓氾履倩等户口状》中的“擘三部落”有不同解读,认为其并非部落名称,而应与前缀“午年”合起来理解为午年分三部落之意,表示的是一个时间概念,*杨际平:《吐蕃子年左二将户状与所谓“擘三部落”》,《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第19—23页。山口瑞凤、岩尾一史亦同意此说。陆离通过对phyug mtshams在古代藏文中的读音的考察,指出“擘三”正是其音译。笔者以为藤枝氏与陆氏的说法更为合理。且前文已经述及吐蕃本土部落在中央政府对外作战时要联合出征,因而在敦煌、新疆出土的文书中就出现了吐蕃本土的部落名称随战争的进展而移动的现象,如原驻地为那曲地区的那雪部落、原驻地为后藏的管仓部落均见载于安西四镇地区出土的木简,*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第209页。其他如宗木、倭措巴、墀邦木、郎迷、洛扎、芒噶、喀尔萨、聂巴、畿堆、那赤、叶若布等名称在西域出土的木简中亦均有载。擘三部落的情况应当与上述部落相同,其名称随着战争推进而移动的情形在文书中亦有反映,如麻札塔克出土的一份借契0509+ 0510号文书中就记载了三名来自擘三部落的见证人:“见证人如下:擘三(Phyug-mtshams)的茹波,达·吉玛,杰札·拉贡。”*F.W.托马斯:《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兰州:刘忠、杨铭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8页。另一份文书P.T.1287X,Pl.570—571为吐蕃在安史乱后攻占河陇地区的过程中,墀松德赞奖赏臣下的记载,藏文转写如下:
vbangs kyi nang na/dor te pyugs tshams ste vdzom(vjom)dpav ba vi mtshan mar/stagi thog bu stsal to/黄布凡、马德译为“臣属中凡英勇参与征服多尔部和擘三部者均赐以虎皮制品作标志”*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2、294页。,陈践、陆离认为此句也可译为“多尔部和擘三部之臣属中凡英勇参与征服(河陇地区)者均赐以虎皮制品作标志。”*陆离:《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行人”、“行人部落”》,《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第88页。P.T.997号《瓜州榆林寺之寺户、奴仆、牲畜、公产物品之清册》更明确记载了擘三部落在瓜沙一带驻扎并对当地事务进行管理的情况,文书曰:
瓜州地面寺庙产业大岸本(总管)古日赉卜登与谢卜悉斯之书办王悉诺椤*王尧、陈践认为此王悉诺椤为吐蕃人,因受汉人影响遂采用汉姓。笔者以为其时吐蕃为统治民族,吐蕃人反采用被统治民族的姓氏似为不妥,则此王悉诺椤更有可能是蕃化的汉人,原本姓王,吐蕃统治瓜沙之后又起了藏文名字。在敦煌文书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与榆林寺寺内岸本(总管)擘三[部落]赞拉囊长官及其麾下之榆林寺顺缘寺户、信财、牲畜、粮食、青稞、大米、物品等登记簿本清册……
……所收布施上交,依册清点,更改清册后,于沙门住持和军官、悉编观察使驾前点交,然后交与大岸本总管古日赉卜登与谢卜悉斯之书办王悉诺椤和榆林寺之总管擘三[部落]赞拉囊长官及其麾下诸人。*《榆林寺庙产牒译释——P.T.997号吐蕃文书写卷研究》,原载《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后收入《王尧藏学文集》卷四,第59—66页。
从记录中可以看出瓜州地区榆林寺寺内岸本即为来自擘三部落的吐蕃官吏,他管理着榆林寺的寺户和财产。可见吐蕃本土的擘三部落在对外军事扩张中曾开赴河陇地区,则它出现在敦煌地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山口瑞凤推测,擘三部落军队驻留沙州后,将汉人居地分左右二区,称上、下部落,纳入擘三部落的统治之下。王尧、陈践持同样观点,认为吐蕃部落在开赴瓜、沙、甘、凉等地后,“以这些吐蕃部落为核心,再把若干汉户收编在部落之中,便于管理约束。后来,形势有了变化,社会日趋安定,才逐渐重新编组为以行业(丝绵)或居住地(上、下)等为主的纯汉户部落”*王尧、陈践:《吐蕃占有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敦煌藏文写卷P.T.1083、1085号研究》,第175页。。笔者以为这种推测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吐蕃在占领区派驻军队以监管征服地区民众在文书中屡有记载,如米兰,XXiv,0031号木简记载:“分派阿柴农夫进行耕作时,要派出一定数量的军队进行监视。”*F.W.托马斯:《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第22页。如此,驻留敦煌一带的擘三部落也担负着监督这一带民户生活、生产的责任。
再观S.3287V《子年(公元九世纪前期)五月左二将百姓氾履倩等户口状》中记载的“午年擘三部落依牌子口户”“午年擘三部落口”*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379页。,此午年即790年吐蕃在敦煌设置部落之年,午年时擘三部落的民户已经存在且编制了户籍,或可推测擘三部落在790年之前已经存在,早于午年后出现的行人、丝绵等部落,这正与王尧、陈践的观点相合。但是擘三部落收编的是全部敦煌民户还是部分敦煌民户,以及其与乡部落之间有何关系,笔者目前尚不得而知,有待于更多文献资料的发掘。
二、宗教人口
相较于世俗人口来说,宗教人口因其集中性更易于统计和管理,因此吐蕃占领敦煌后很快设置了管理佛教人口的“僧尼部落”和管理道教人口的“道门亲表部落”。
1.僧尼部落
有关僧尼部落的文书笔者目前仅见S.2729《吐蕃辰年(788)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一件,为辰年(788)吐蕃佥牟使论悉诺罗对敦煌僧尼进行清查后所造牌子历。这件文书记录了龙兴寺、大云寺、莲台寺、灵图寺、金光明寺、永安寺、乾元寺、开元寺、报恩寺等9所僧寺所属僧139人,灵修寺、普光寺、大乘寺、潘原堡等4所尼寺所属尼171人,总计310人,此当为僧尼部落的全员。这份牌子历不仅记载了所有僧尼的姓名,还注出了已逝之人,甚至在造牌子之后去世之人亦登记在案,如文书第59—68行所记:
59 造牌子后死:辰年三月十日龙兴寺僧张净深死。吐蕃赞息检。三月十三日石法阇梨死 赞息检。
60 四月一日乾元寺僧法达死。赞息检。四月廿日大云寺僧刘金云死。赞息检。四月廿六日乾元
61 寺僧刘像真死。赞息检。六月十九日龙兴寺僧氾惠朗死。赞息检。八月四日大乘寺尼
62 阎真心死。赞息检。八月廿四日普光寺尼阎普明死。赞息检。巳年三月卅日龙兴寺僧
63 李志真死。赞息检。七月十一日云僧吕惟寂死。赞息检。七月廿一日永安寺僧贺常觉死。萨董罗检。八月十四日乾元寺僧
64 王像空死。萨董罗检。午年正月六日灵修寺尼安净法死。杨舍人检。午年七月廿五日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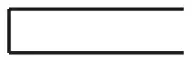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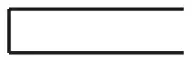
68 七月廿二日大乘尼阴净相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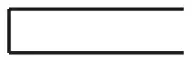
笔者还注意到第63行载有“云僧吕惟寂死”一语。云僧即云游僧、行脚僧,则此吕惟寂并非敦煌本地僧人,游历经过敦煌卒于斯,其名亦出现在吐蕃所勘僧尼籍中,足见吐蕃对僧尼部落的户口清查之彻底、严格。
僧尼部落的设置是吐蕃统治敦煌初期的权宜之计,这一部落很快随着行人、丝绵两大部落的设置而消失。藏文文书千佛洞,75,iii号为一份比丘尼名录,托马斯转写的藏文转写节选如下:
[1] dge slong ma Kvang vgam ‖sha cu [pha] Rgod …… bang Shang za Dzav ch-‖dge slong ma L[a]ng c[a]vu Sha cu pha Dar phavi sde Beg za Hye wi[vu?]︱[dge] slo[ng] ma……
[a] sha cu pha Rgod gyi sde Leng za Sevu sevu‖dge slong ma Thevi cin‖[b] Sha cu pha Rgod gyi sde Then za Beng ’ em‖dge slong ma Vbyevu vdzi‖Sha cu pha dge slong ma Kvag za Ji lim gyi bran mo Kvag za Tam tam dge slong ma Thong cevu.*F.W.托马斯:《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第421页。
刘忠、杨铭的中译本译释为:
比丘尼光康;沙州阿骨萨(部落);……邦,项氏才……比丘尼朗雪;沙州丝绵部落;白氏海卫;比丘尼……
沙州阿骨萨部落;梁氏苏苏;比丘尼泰坚。
沙州阿骨萨部落,藤氏本恩;比丘尼吉子;沙州比丘尼瓜氏吉玲之女奴瓜氏丹丹;比丘尼通吉。*F.W.托马斯:《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第63—64页。
通过对照藏文转写,此处“阿骨萨”部落对应的藏文是Rgod gyi sde,岩尾一史、陆离认为此正是“行人部落”的藏文对音,*岩尾一史:《吐蕃支配下敦煌の漢人部落——行人部落中心に——》,《史林》2003年第4期;陆离:《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行人”、“行人部落”》,《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第85—94页。此说不差。再考虑到文书中与之并存的“丝绵部落”,则此“阿骨萨”实为“行人部落”无疑,这就说明在790年吐蕃正式设置部落之后,僧尼部落被取消,僧尼户编入世俗人口一并管理。僧俗混编的情况在其他吐蕃占领区同样存在,如米兰,ⅸ,15号木简记载:“在小罗布,有寺庙菜园子地八畦。这些地由僧人(ban-de)姜求宁波耕种。僧人现已死亡,因为他与贱民属同一千户(部落)的尚论官邸之下,此……(或由于他与贱民我同在一个千户之尚论官邸管辖下,此……)。”*F.W.托马斯:《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第309—310页。这是小罗部地区僧俗户归同一部落管理的例子。
2.道门亲表部落
道教在唐代地位颇高,有很大发展。于此全国崇道的大背景之下,敦煌陷蕃前道教亦较发达,有灵图观、开元观、神泉观、白鹤观、冲虚观等数座道观,道士、女冠自然不少。关于吐蕃占领敦煌以后如何管理这些道教人口的问题,现有文书并无太多记载,但据P.4640号《阴处士碑》、P.4638号《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等文书可知,吐蕃占领初期曾于敦煌设立过一个“道门亲表部落”,阴嘉政的父亲阴伯伦曾任这一部落的部落大使。P.4638记曰:
皇考,讳伯伦,唐朝游击将军,丹州长松府左果毅都尉、赐绯〔鱼〕袋、上柱国、开国男,……自赞普启关之后,左衽迁阶;及宰辅给印之初,垂祛补职。蕃朝改授,得前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39页。
藤枝晃最早注意到了“沙州道门亲表部落”,指出此名称并非藏文音译,但其具体含义不甚明了。*藤枝晃:《吐蕃支配期の敦煌》,《敦煌千佛洞的中兴》,《東方学報》第35册,1964年。姜伯勤研究指出,“亲”者内亲,“表”者外亲,所谓“道门亲表”者,即道徒及其内亲外戚。道教中的三张一派可以迎娶妻妾并与家属在道观中同居,早期天师道张道陵一系道官亦可婚配,则道观中的出家道士有妻室家眷并不奇怪。此外,唐代还有“在家道士”,这些在家道士必然是与亲表一起生活的。如此,吐蕃统治者为了便于管理这一人群,便把有家室、与世俗亲表杂居的道士女冠编为“道门亲表部落”。*《沙州道门亲表部落释证》,第3—7页。
与僧尼部落一样,道门亲表部落仅见于上述文书,为吐蕃占领敦煌初期的权宜之计,其具体废止时间无从考略。按道教受李唐皇室崇奉,且为汉族本土宗教,是汉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和载体,必然会受到吐蕃的排斥和打压,整个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道教几无发展,由道门众人组成的“道门亲表部落”很快被废除也就不足为奇了。
综上所述,吐蕃占领敦煌初期,虽然名义上不采唐朝的乡里制度,但由于敦煌久罹战患,民生凋敝,百姓流离迁徙者众,户籍混乱不可用,为稳定社会民心计,吐蕃统治者采取了“蕃名唐制”的权宜之计,对世俗人口和宗教人口分而治之。对世俗人口,吐蕃统治者一方面只在原有乡的名称后缀以“部落”二字以宣示主权,实际上基本保留了原有乡的建制甚至官吏,并以此为单位进行户口、土地登记,为下一步正式设置部落做准备。另一方面派驻了来自吐蕃的“监部落使”等官吏对敦煌民众进行监管。而来自吐蕃本土的“擘三部落”随着对外战争一路开赴瓜沙地区,对当地各项事务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管,并有可能在吐蕃占领初期收编了部分或全部汉户置于其管辖之下。对宗教人口,因其较为集中更易统计管理,吐蕃统治者占领敦煌不久即在当地设置了管理佛教人口的“僧尼部落”和管理道教人口的“道门亲表部落”,二者为占领初期吐蕃采取的权宜之计,很快便随着行人、丝绵等正式部落的设置而消失,僧尼户被混编入世俗人口一并管辖,道士女冠则在吐蕃时期的敦煌文书中消失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