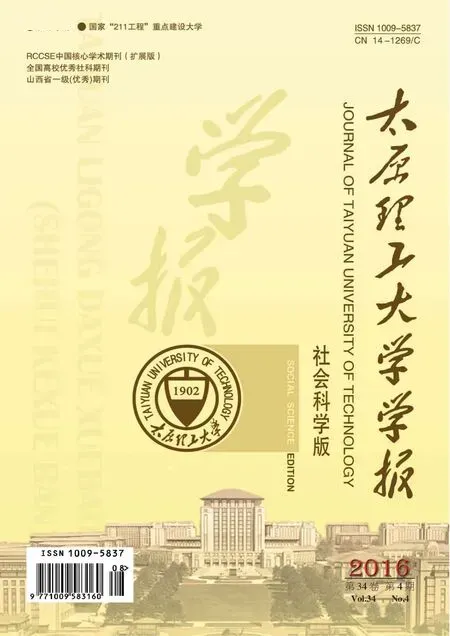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探析
凌洪斌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探析
凌洪斌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是商标侵权抗辩的重要事由,但由于其内涵和外延比较模糊,判断标准也不够具体和明确,因此造成司法适用上的困难,这不仅给利害关系人陡增困扰,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因此亟须厘清商标指示性使用的概念,明确符合“必要”“善意”和“合理”等主客观条件的商标指示性使用是侵权豁免的行为,同时,我国立法也应当完善和构建科学、合理的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制度,以期更好地指导和服务商标法律实践。
指示性使用;商标;善意;合理
当下商事活动蓬勃开展,商标权益纠纷日渐增多,这固然是私权意识高涨的大环境驱动使然,但也与权利主体自身缺乏对商标所承载的一定公共利益属性的认识紧密相关。商标使用是实现商标价值的必要手段,也是商标维系的生命之源,简言之,商标的价值和生命均在于使用,但商标本身又蕴涵较多的公共利益元素,因此商标权人的权利及其使用也应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正如我国司法政策所指出:“正确把握商标权的专用权属性,合理界定权利范围,既确保合理利用商标资源,又维护公平竞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9]23号)。因此,对商标权利限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的缘起及其定义
(一)缘起
学界认为,美国1946年《兰哈姆法》第33条(b)款(4)的规定只适用于商标叙述性合理使用的情形。叙述性合理使用原则仅适用于被告使用原告的商标来描述被告的产品或服务这一情形,而当被告使用原告的商标来描述原告的产品或服务时,该原则就无法适用。因此,商标叙述性使用的适用范围有其先天的局限性。为弥补这一不足,美国在遵循先例法律传统的情况下,于1992年通过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审理的“New Kids ”商标案*New kids On The Block v. News America Publishing,Inc.971F.2d302(9th cir.1992).创设了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原则。在本案中,原告“New Kids on the Block”是美国一个摇滚乐队,其拥有“New Kids”的注册商标,而两位被告“News America Publishing”和“Gannett Satellite Information Network”则是美国的两家报社,被告在其刊发的报纸广告中刊登了一张“New Kids on the Block”的照片,并且要求读者评选出其中“最喜爱的New Kids”。原告认为被告已侵犯自己的商标权,遂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如果不提及原告的商标,就无法完成该项评选活动,因此认为被告不构成侵权,最后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案判决的出炉亦被学界认为是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司法裁判的开山之作。
(二)定义
我国学界对商标合理使用的称谓较为多元,将叙述性合理使用称之为描述性使用或说明性使用,又称之为传统合理使用或法定合理使用等,将指示性合理使用称为被提及的合理使用等。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是商标合理使用的一个下位概念,因此探讨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的概念需要追根溯源,先从商标合理使用概念入手。我国商标立法并没有“合理使用”字样的明确表述,因而学界对合理使用的定义理解不一。有学者认为,“商标的合理使用,简言之,是指在一定条件下非商标权人可以使用他人的商标,但不构成侵权”[1];也有学者将商标合理使用定义为“商标权人以外的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以叙述性使用、指示性使用、说明性使用或平行使用的方式善意使用商标权人的商标而不构成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2]。总之,以上概念都是着眼于“使用而不构成侵权”这一点,即商标合理使用是基于侵权抗辩角度而言的,这也是合理使用制度的真谛。诚然,商标合理使用制度并不囊括所有的商标使用侵权抗辩,即并非所有的“商标不侵权”使用都可以用“合理使用”的理由来抗辩。
笔者认为,所谓商标合理使用制度,是指在特定条件下,商标使用人可以无须经过商标权利人的许可,也不必向其支付相关报酬或费用,而不构成侵权的商标使用行为。而商标指示性使用的具体做法,则是市场主体在商业活动中,善意而又合理地使用他人所有的商标,客观地说明自己的商品用途、服务范围及其他特性,在该使用过程中,虽然使用了他人的商标,但终极目的还是为了说明或宣扬该市场主体自身的商品或服务。换言之,商标指示性使用是指他人使用商标权人的商标来描述自己的商品或服务,以此来说明自己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能够与使用该商标的商品或服务配套。综上所述,商标的指示性合理使用是指使用人使用他人所有的商标用来说明自身产品或服务,而不构成商标侵权的一种商标使用行为。
二、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
古语云:“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的成立,也应当符合一定的构成要件,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为商标性使用,其二为正当性使用。商标性使用为前提要件,而正当性使用则为免责或侵权豁免要件。
(一)商标性使用的解读
从使用所指向的对象来看,指示性使用与描述性使用不同,描述性使用的商标指向的是使用人自己的商品或服务,而指示性使用商标指向的是被使用的商标权利人的商品或服务。但不管是何种性质的合理使用,均应符合商标性使用这一基本前提。所谓商标性使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48条*本法所称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的相关规定,是指市场主体在商业活动中所使用的商标能够发挥区分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作用的使用。换言之,商标性使用需满足两个基本要件:(1)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2)商标发挥区分识别的基本功能。总体而言,商标的指示性使用在日常生活中亦较为常见,例如,在某品牌的笔记本电脑键盘下方粘贴有其他商品商标,如“DELL”(戴尔)公司所销售的笔记本电脑,在其键盘下方通常都粘贴有“Intel”(英特尔)和“Windows”(微软)商标的图标,以表明其内置的微处理器和操作系统的来源。此处“Intel”或“Windows”商标的使用符合“商标意义上的使用”的上述两个构成要件。原因如下,首先该笔记本电脑是用于销售的商品,显然贴附的商标是“商业活动中”的使用行为;其次,贴附的“Intel”或“Windows”商标可以明确而有效地将其与相关商品联系起来,能够将符号与商品进行对应连接,虽然使用者使用该商标最终的目的是指代自己的商品或服务,而不是指代“Intel”或“Windows”产品本身,但不容否认,在这指示性使用过程中,消费者看到“Intel”或“Windows”标识,客观上确实容易“条件反射式”地联想到“Intel”的处理器或“Windows”的操作系统等商品,从而将该商标与商品进行有效关联和对应。仅就“Intel”或“Windows”商标本身而言,的确发挥了商标区分识别的基本功能,而并没有损害商标的识别功能,因而使用人客观上也对“Intel”或“Windows”进行了“商标意义上的使用”。综上所述,商标指示性使用是“商标意义上的使用”,即属于商标性使用。以上分析仅解答了第一个设问,即指示性使用是否是“商标意义上的使用”这一问题。而指示性使用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还需进一步地对其是否侵权做出判断。若不构成侵权,则可认定为合理使用。
(二)正当性使用的考察
商标指示性使用语境下的正当性是指商标的指示使用不构成侵权的理由及其构成要素。在“New Kids”案中,主审法官考辛斯基曾经提出了指示性使用是否“正当”的三个判断因素:(1)被告若不使用该商标将无法表示;(2)被告的使用在合理、必要的限度内;(3)该使用不得暗示其与原告存在赞助或者许可关系。因此根据该判决,笔者认为,指示性商标合理使用的“正当性”判断标准应当包含以下三个要素。
1.必要性。“必要性”条件是指示性合理使用的基本前提,是指使用人若不使用该商标将无法呈现其自身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使用该商标是重要甚至唯一途径,其他产品很难将之替代或根本无法将之替代。例如上述“Dell”一例中,戴尔公司若不使用“Intel”和“Windows”商标,将无法有效地向其用户表明该笔记本电脑使用英特尔微处理器和微软操作系统的客观事实,因而也无法呈现其产品的本来面目。美国大法官霍姆斯也说:“商标权只是用于阻止他人将其商品当作权利人的商品出售,如果商标使用时只是为告知真相而并不是要欺骗公众,我们看不出为何要加以禁止。商标不是禁忌。”[3]总而言之,必要性是指商标的指示性使用不可替代,这是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的根本前提。
2.善意且合理。此处“善意”(good faith)与民法上之“善意”,即所谓“不知情或不应当知情”含义不同。商标合理使用语境下的“善意”是以使用人主观上不具有损害商标权人利益的故意为衡量标准。这既是一般道德正当性的要求,也是商业道德的体现。具言之,“善意”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也是衡量是否合理使用的主观要件,至于客观上是否造成损害的实际后果即不再考虑。判定是否善意,在具体操作上,还需借助外化的证据材料来证明。此外,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在“片仔癀”商标侵权案*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1310号民事判决书。中指出:当某个注册商标具有描述性时,其他生产者出于说明或客观描述商品特点的目的,以善意方式在必要的范围内予以标注,不会导致相关公众将其视为商标而发生来源混淆的,构成正当使用;判断是否属于善意和必要,可以参考商业惯例等因素。即判断“善意”与否可以以外在的商业惯例为衡量标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26条中提到“正当使用商标标识行为的构成要件”问题时,也开宗明义地列出善意要件。可见,在我国相关司法活动中,对行为人的主观善意均有所着墨。
所谓“合理”,是指商标使用人应当采取合乎常理的方法使用,即要求使用的方式、手段和效果不能超过所能容忍的限度。简言之,是适度而不是过度地使用。我国有些法院在审判中认定是否合理使用时也纳入了“合理性”这一要素。例如,在沃尔沃商标控股有限公司起诉瑞安滤清器有限公司商标侵权纠纷一案*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06)浦民三(知)初字第122号民事判决书。中,本案被告主张,标示“FOR VOLVO”是为了说明该滤清器适用于“VOLVO”汽车,这种行为属于商标的指示性合理使用,不构成侵权。而原告认为,被告虽然在“VOLVO”前加注了英文“FOR”,但是这几个英文字母被刻意地放大并放在了显著位置,成为该产品上唯一标示产品来源的符号,使消费者产生了混淆而误以为被告与原告有某种特定的许可关系。上海浦东新区法院最终支持了原告的主张,判令侵权成立。显然,被告败诉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对商标做了“突出”的使用,而致明显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同样在“联想”商标纠纷案*江苏泰州中级人民法院(2013)泰中知民初字第243号民事判决书;江苏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知民终字第 0142 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亦秉持了适度使用的观点。在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顾某在其经营场所全面使用涉案商标,并在店铺门头、店内装饰、名片、销售清单等处突出使用“Lenovo联想”“Lenovo”等标识,从而推断其具有试图使消费者误认为其与联想公司存在特许经营、加盟、专卖等特定商业关系的故意,而在客观上也确实形成或达到了上述效果,显然被告的行为属于对合理指示商品来源的权利的不当扩张,已经超出了商标指示性使用的合理范畴。综上,“合理”强调商标使用的“适度性”问题,指示性合理使用必须坚守合理适度使用的底线,一旦逾越了合理的界限即构成商标侵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然而,“合理”一词的词义较为抽象,在司法实践中也留给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案情基本相同的情形下,有可能会造成裁判尺度不一,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裁判结果。在实践中,各国或地区也都在对“合理”这一抽象的法律概念寻求明确和细化的方法。例如,我国台湾地区2011年修正了“商标法”第36条,用“以符合商业交易习惯之诚实信用方法”取代了2003年“商标法”第30条“以善意且合理使用之方法”的表述,该条款重点仍然在强调使用的“方法”,同时又突出强调“商业交易习惯”,对其使用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限定。
3.非混淆性。是否应将商标的“混淆可能性”作为合理使用的衡量因素,学界和实务界的分歧均较大,在指示性合理使用制度较为完备的美国,其判例对此也发生过较大的反复和转变。以2004年KP案*KP Permanent Make-up,Inc.v.Lasting Impression I,Inc.,543 U.S.111(2004).为分水岭,在KP案之前,各巡回上诉法院对叙述性合理使用是否应纳入混淆可能性要件的看法各异,美国最高法院在2004年KP案中全面阐述叙述性合理使用原则并指出:在商标侵权案件中,即使混淆可能存在的情况下,叙述性合理使用之抗辩也能成立,被告在提出叙述性合理使用之抗辩时,并没有义务否定诉争商标和引证商标之间的“混淆可能”,此判决很快消弭了各巡回法院在该问题上的长期分歧,各法院最终倾向于弱化混淆可能性在指示性合理使用构成要件上的作用。虽然该判决是用在叙述性商标使用案件中,但同是作为商标侵权抗辩的重要事由,该案的判决对指示性合理使用亦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
我国司法实践也曾面临是否应当将非混淆性因素纳入指示性合理使用的判断因素之列的困惑,也曾出现态度的反复。譬如,北京市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颁布的《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9条中明确规定:“使用不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但其随后在2006年重新颁布的解释中则认为要构成描述性使用或指示性使用等正当使用行为,不需要“相关公众不会造成混淆误认”的条件,显然是对原先的看法予以了否定。
笔者认为,在商标指示性使用场合,行为人主观上可能并不具有混淆的故意,但在客观上仍有可能形成消费者对两种商品存在某种程度关联的错误认知。例如,在上述所举的“DELL”电脑一例中,虽然“Intel”和“Windows”都是国际知名一线品牌,但“DELL”自身也是国际知名一线品牌,所以其主观上想通过“搭”知名品牌的“便车”而企图混淆商品的可能性较小。如果行为人主观上确实具有傍品牌、搭便车的攀附他人商誉的故意,实际上也违背前述行为人主观“善意”的前提。同时,在客观效果上是否会造成消费者的混淆误认,这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来判断,而消费者最终会做出何种联想,商标指示性使用人实际上很难予以掌控。即使使用人本身并没有暗示商品之间存在赞助或许可关系,消费者实际上也可能会认为它们为实行达到互利双赢而存在某种合作或达成某种默契。此外,从民事诉讼举证分配的角度而言,如果坚持混淆可能性要件,可能会对主张权利的一方造成举证上的极大困难,不合理地加重权利人的举证责任。综上所述,不论是从主观方面还是客观方面,抑或诉讼证明等角度来看,均不适宜将“非混淆性”因素认作指示性合理使用的考量标准。
三、我国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制度的体系构建
在我国商标立法中并没有“指示性合理使用”的相关表述,但在商标侵权案件中,被告方通常以包括指示性使用在内的合理使用作为侵权抗辩的“护身符”,而且我国法院做出以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为诉争焦点的司法判决越来越多,典型的就有“维多利亚的秘密”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 104 号民事判决书。和“米其林”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三终字第 239 号民事判决书。等。鉴于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在商标侵权抗辩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我国有必要在立法中构建完整的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制度。笔者建议具体制度可以做以下设计或安排:(1)在未来修法中将“合理使用”一词明确写入相关条文中,确立“商标合理使用”的法律地位;(2)明确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商标使用人对某商标的使用首先应当是“商标性使用”,且必须符合“必要”“善意”和“合理”等基本因素;(3)明确指示性合理使用的基本类型。从实践上看,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主要包括基于产品修护、零配件制造、产品销售、产品组装和产品兼容等各类型的指示性使用。另外,从学理层面考察,比较广告也属于指示性合理使用的一种。但从实践和操作层面看,比较广告在我国受广告法律制度和竞争法律制度的规制比较严格,一般认为我国立法对比较广告持否定态度,为避免立法上的冲突和适用上的困惑,因此在商标合理使用制度的构建上也不宜将比较广告纳入其中;(4)明确非商业性使用不属于商标合理使用范畴。在具体诉讼实践中,也经常有当事人误认为商业性使用不构成商标合理使用,而非商业性使用才能构成商标合理使用。如在江苏高院审理的一起上诉案件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的行为不属于我国商标法规定的商标合理使用,而是一种商业性使用行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知民终字第0297号民事判决书。。在本案中,上诉方认为商业性使用不能构成商标合理使用。笔者对此主张不予认同,原因在于非商业性使用不是商标意义上的使用。比如前述的新闻报道、评论和词典编撰中“使用”是一种表达自由和文化传播层面上的使用,不属于商标性使用,而是属于著作权意义上的使用,因此也不应当纳入商标合理使用的范畴。
四、结语
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是被控侵权人重要的侵权抗辩事由,也是商标权利限制的一种重要形式和实现途径,在司法实践中,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成立与否是商标侵权与否判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开展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的研究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通过考察商标的本质以及对“商标性使用”的法律定义,揭示指示性商标合理使用的真谛。厘清指示性商标合理使用的内涵,首先应当明确“商标性使用”这一法律概念,而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的判定则需建立在“商标性使用”的基础之上,再具体结合“必要”“善意”和“合理”等主客观因素予以综合考察。此外,鉴于包含指示性使用在内的商标合理使用制度在我国的立法缺位,亟须予以科学合理地构建和完善。
[1] 杜颖.社会进步与商标观念:商标法律制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85.
[2] 冯晓青.商标权的限制研究[J].学海,2006(4):137-146.
[3] 黄晖.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的法律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93.
(编辑:张文渲)
Research on the Indicative Reasonable Use of Trademarks
LING Hong-bin
(SchoolofLaw,Wu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China)
The indicative reasonable use of trademarks is the important reason for trademark infringement defense, but its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are relatively vague and judgment standards are not specific and clear either, which results in difficulties in judicial application. It not only perplexes the interested persons, but also greatly damages the authority of the law.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concept of the indicative use of trademarks and to define that the indicative use of trademarks which conforms with such subjective or objective conditions as “necessity”, “goodwill” and “rationality” is immune to infringement. Meanwhile th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system of the indicative reasonable use of trademarks should also be constructed and perfected by China’s legislation so as to better guide and serve the legal practice of trademarks.
indicative use; trademarks; goodwill; rationality
2016-04-2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谐世界’理念下国际知识产权制度重构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08BFX08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项目“二十一世纪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发展中的若干重大法律问题研究”(07JJD820163)
凌洪斌(1982- ),男,江西赣州人,武汉大学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民商法、知识产权法研究。
D923.43
A
1009-5837(2016)04-00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