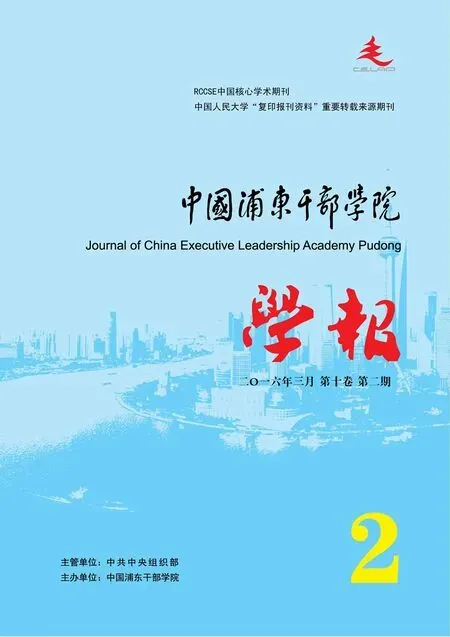从传统性到现代性:世界观的颠覆与重构
王喜国,刘 芳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上海200433)
从传统性到现代性:世界观的颠覆与重构
王喜国,刘芳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上海200433)
摘要:自从进入现代性社会以来,整个人类社会的价值出现了错乱,这个错乱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它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将来会是怎样的?要真正理解现代性,不仅要观其“流”,更要溯其“源”。为此,本文沿着“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这一思路,从传统性世界观入手,梳理了从“神学主导的时代”到“神人并立的时代”,再到“人的时代”这一世界观变化,这一变化使传统性价值观遭到颠覆,从而使整个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发生转向,这便发生了诸如欲望凌驾理性、功利高于道德、个体高于群体等现象。因此,现代性的重建必须从世界观的重构开始,在“存在观”上需要“再启蒙”,在“发展观”上需要学会“限制”,在“实践论”中需要在社会充分分化的基础上,走向并实现更高层次的“融合”。
关键词:现代性;世界观;重构
在现有对现代性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注重从“什么是现代性”的角度出发,并从概念的解释延伸出相应的现代性构建模式(对现代性的定义就多达数百种,建构模式更是花样繁多)。这种思考模式奉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圭臬,把假说当成真相,忽视了支配现代性思维、行为、心理的世界观研究,结果导致莫衷一是的理论纷争与实践模糊。马克思强调,认识世界才能改造世界。如果认识世界的问题解决不好,改造世界的问题就必然混乱。格里芬也认为“我们面临的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现代世界观”。[1](P22)有鉴于此,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考察与分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人们世界观变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其他一系列变化,在与传统性的对比中把握现代性,建构现代性,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
一、传统性世界观的转向
从传统性转到现代性,最突出的事件是“主体性转向”,这一转向的实质是世界观的革命,并由世界观革命而引发人们自我观的变化和人我观的变化。世界观之于人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种普遍认可的世界观总能在我们身上唤起神圣的意识和宗教般的反应,主导人们遵守、践行,并焕发出巨大的能量,正如格里芬所说:“一种世界观所显示的我们经验中的要素,是作为整体的实在中最重要的要素:这些东西是永恒的和持久的,而不是转瞬即逝的;它们是原初的动力因,而不是次要的和派生的。我们的世界观通过说明在事物的本性中最为重要的是什么而告诉我们,对我们来说什么才是终极关怀。”[1](P23)当然,这里所说的世界观,指的是普遍的、事关终极意义的最高价值,而非权力或金钱、享乐等形而下的东西。
现代性发端于西方,其酝酿、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决不是后世研究者认为的某个理论的提出或某一事件的发生就标志着现代性的诞生。“后来的历史学家用来称呼之前历史阶段的所有名称,都是用来秩序化具体化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在那段历史本身里,并不具有此种自觉的身份认同。”[2](P190)将漫长的历史进程概括为孤立的一句话,或者想用几句话来概括现代性,必然会犯形而上学的绝对化错误。不管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或启蒙运动,都不足以概括得尽现代性。正因为单纯的定义或单一的时间节点并不能把握现代性,特别是不能把握它是怎样萌芽、怎样产生和怎样发展的,所以这里将梳理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世界观变化,在渐进式的变化中了解社会发展是怎样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从而描述出现代性萌发、产生及其演变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神学主导的时代
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其传统社会对于宇宙世界的认识、亦即世界观都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而是以上帝、宗教或自然神为中心,并由此发展出一套宗教、神学以及道德本位的学问和理论体系。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在这一世界观的主导和支配下,形成了传统社会中重道德、讲秩序、崇信义、尚服从、睦他人、爱集体等价值观念。当然,这也是从总体上而言的,真实的情况是,长期稳定的社会内部,其实也一直在悄悄酝酿着突破传统的因素。
西方社会发生世界观革命,首先是从古希腊哲学开始的。公元前5世纪前后,也就是雅斯贝尔所说的“轴心时期”,古希腊产生了以“三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被称为“智慧的爱好者”“爱智”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试图不借助宗教来理解世界,把理性视为绝对忠诚的对象和真假对错的终极标准,认为只有理性才是智慧的开端,才是“世界观革命”的源头所在,也是与传统社会决裂的开始。然而,人们能够提出理性的概念,却并不代表人们就真的拥有了理性的能力。因为理性不仅要建立起一个完美的现实秩序和民主社会的依靠原则,还要填补宗教隐退带来的空白,即使是思想家本人,当其把所谓的理性加诸本质上非理性的世界之时,他们也让自己承担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的计划就是把自主的理性加给一个非理性的世界。正如我们所见,这个事业是大胆的甚至革命性的,但它并无成功的指望。”[2](P32)即使是后来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也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中说:“只有很少数的人能够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并且从而迈出切实的步伐来。”尽管如此,“理性人”的提出给后世带来的影响和震撼也是革命性的,但最初古希腊哲学中的这一思想只限于希腊半岛一隅,对外界的影响还很小、甚至没有。此时,仍然是神学世界观主导世界。
(二)神人并立的时代
第一位使神学发生转向的是托马斯·阿奎那,他经常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哲学来解释事物,阿奎那把实在分为两层,居上层的是恩典(包括的概念有上帝、天堂、不可见存在、灵魂等),居下层的是自然(被造物、地界、可见存在、人的身体等)。尽管没有哪个中世纪的神学家会让神学服从哲学,但是通过这种方法,阿奎那在实现了神学信仰与亚里士多德哲学之间调和的同时,无意之中却埋下了哲学与神学分开的种子,不仅破坏了基督教世界观的统一性,更为学术、哲学、政治、经济等“世俗”领域开启了大门。
哲学与神学出现了初步的“分工”后,彼此开始争夺统治权,由此延伸出了教权与皇权的争执。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与亨利四世的争执过程中,实现了教皇对皇帝的胜利,即无论在观念上、事实上,还是在制度层面,格列高利的改革都导致了统一的社会分成了两个社会:一边是教会,一边是“国家”或社会,这便造成了中世纪早期社会里居于主导性的两极之间的分裂。
在此基础上,另一位思想家彼得·阿伯拉尔正式开启了理性探寻动力之源。以往的神学家们不称自己为“神学家”而称自己是“掌握圣书的人”,是人与“神”之间沟通的纽带,其诠释学不被当做“专业”和其他专业并列,而是高于其他学科。但是阿伯拉尔在释经的过程中却经常采用提问式的方法,这样疑问的产生就不可避免、势所必然,阿伯拉尔更试图给出“理由”来满足人们的理智,“‘提问题'的方法游离了‘阅读'背景,以致神学和释经分离,最终理性和信仰分离,哲学和神学分离”。[2](P159)哲学与神学分离后,神学逐渐地由世界的本体变成了世界观,也就是认识世界的方法之一。人与神的并立也就自然而然地结束了。
另一位思想家奥卡姆走得更远,他以“马”的共相和马的具体实在之间的完全不同和千差万别来举例,反对阿奎那式的综合,消除共相和抽象,注重经验和具体,这与中国古代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唯名论”认识论常被看成现代科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并与现代“科学方法”非常相似,为认识个体事物提供了哲学基础。但总体上说,这一时期上述观念的传播及影响并不是主流,中世纪仍然是信仰的时代,是以宗教和神学认识论为主的时代。
(三)人的时代
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的思想酝酿,理性的种子终于破土而出,这就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
随着印刷术在欧洲的广泛应用,文化传播的速度加快,文本研究和语言研究的兴起,人文主义者开始具备了绕过中世纪积累的注释,直接进入原始文本的研究能力。这一方法以及文化的转变对基督教而言是非常具有震撼性的,后来宗教改革“因信称义”的方法都能从中找到影子。此时更有一个核心的内容要素出现,那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译成拉丁文,给西欧提供了一个无论是爱丁堡还是罗马都能方便使用的哲学资源,亚里士多德著述最终成为西欧哲学讨论的核心,[2](P199)几乎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都以亚里士多德文本为哲学反思与探索的基本出发点,并大规模进入了大学课程。有人甚至把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概括为“亚里士多德主义”。这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至关重要。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极大地影响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探求,从而产生了包括哥白尼和伽利略等人在内的一批有影响的科学家。哥白尼“日心说”的创立,不仅仅是对天文学和自然科学的一次革命,也是一种思考范式的转换、一次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革命,更是世界观的革命。它从根本上撼动了神学的根基,直接宣告了科学时代和人的时代的到来。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流行,不仅意味着人学理念的潜滋暗长和神学的逐步消解,更加快了神学世界观向人学世界观的位移,也就是神圣的“祛魅”,这种“主体性转向”在世界观上是个决定性的转移:从上帝中心论转向不同程度的人类中心论。[2](P258)人们突然发现,千年以来,在神的影子下生活的人们是那样“没有自主”,而今终于要走出“蒙昧”了,这种“人的发现”让世人欢欣鼓舞。在此影响之下,到了15世纪晚期,神学世界观和圣经都已经失去了独有的权威地位。为维护宗教神学的应有地位,宗教改革势在必行。
路德和加尔文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虽然坚持以上帝为中心,抨击亚里士多德,反对把人类理性放在太高的位置;但路德坚持“因信称义”,张贴了教皇95条罪状,大大反对赎罪票;认为人性的基本问题就是原罪,所以基督徒应当顺从统治者,这是上帝命定了的。可能路德本人也没意识到,他的做法在实际上也是把全面性的圣经世界观对生活的全部方面所能有的影响缩减到了最小范围。加尔文并不追问或证明上帝的存在,而是考察我们如何能认识上帝,认识我们自身,进而认识我们周围的世界,而就是这些“认识”,构成了真智慧。不管路德和加尔文领导的宗教改革其出发点是什么,其实质却都是“妥协了的上帝中心论,倾向于比较人类中心论式地理解世界”。[2](P221)因此,这场宗教改革导致了宗教的剧变,因而也是一场世界观的革命。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冲破旧思想束缚的观念蔚然成风,继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发出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横扫宗教神学的宣言,开辟了英国的启蒙运动之后,法国的笛卡尔更是预设了人的大脑和心灵的优越性,以系统性的怀疑为思想基础,开始对一切问题展开怀疑,进而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笛卡尔的“我思”开创了现代性的整体进程。自我确证、理性化的自足,成为笛卡尔基础主义的立足点。不管接下来的17、18世纪认识论采取什么形式,它们都采纳了笛卡尔的预设,使笛卡尔与过去的决裂深化。笛卡尔的全新方法——怀疑;我思想,所以我存在——给出了主体性的、理性的起点,一个人类赖以自主的理智性的阿基米德点,它为以后的所有哲学探讨定下了基调。[2](P268)
此后,德国的康德重塑了认识论、伦理学和神学,提出“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到社会科学范畴,这成为世界观历史中的又一个“哥白尼革命”;弗洛伊德以集体性的“俄狄浦斯情结”为基础来解释宗教,把宗教描述为人类常见的心理失常,这种处理将世俗先知对基督教进行批判的思想路线带到了进攻的高潮。至此,启蒙思想家在理论上完成了颠覆传统世界观的工作,人、神之间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传统人的理念被根本动摇,传统人的形而上学本质遭到解体,革命者更是用这种先验理论来改造世界,促成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这场世界观的革命到美国的建立达到了顶峰,它代表着传统社会君权神授的法理基础和秩序根源被世俗社会主权在民所取代,实现了彻底的政教分离。此时,英、美、法等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人的力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也就是说,西方思想家完成了现代性世界观的改造与革命,而革命者又促成了现代性从“世界观”向“历史观”的转变,赋予了现代性的正当性、合理性与合法性。然而,这种奠基于进步——进化的价值观念以及它所衍生出来的历史主义叙事,正如章太炎所揭示的那样,本质上是“以力代神,以论理代实在”。[3](P445)“它把人类活动引入到先进——落后或者文野之辩的逻辑中,一方面它鼓吹征伐——扩张——战争——竞争的现代性态度,另一方面它又通过逻辑的法则替代起初的历史过程,这两点都成为遮蔽存在者自性的方式……使得存在的自性无所容身。在这种情况下,虚无主义成为现代性及其进步逻辑与历史主义态度中难以摆脱的梦魇。”[4](P3)
由上可见,所谓现代性,它是与传统性相对比而言的,从狭义上看,它主要是一种世界观,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对世界所做的、趋于一致的、比较普遍性的认识。从广义上看,现代性作为现代世界体系中发生的以西方世界观为中心、向周边不断扩散并走向全球化的过程。它不仅指新的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也指新的世界体系的生成过程。所以当代研究的现代性一般是指现代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层面的基本精神特质与制度架构,它既是世界观的充分展示,也是在世界观支配下改造社会的必然结果。对“传统性”的理解也应作如是观。
那么,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从传统世界观变为现代世界观,以神为本位的世界观消解了,以人为本位的世界观确立了。从实质上来说,神、上帝、宗教等是道德、正义、真理和至善至美的载体和化身,西方传统文化中以宗教神学为本位的学问,实则是以道德为本位的学问;东方以中国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以伦理为本位的学问。这样看来,上帝的退隐和传统的消解,实际上就是伦理道德的消解,人除了无止无休地“工作”、生产和“改造世界”外,已不知生活的真正意义为何,牟宗三认为这是“时代精神的堕落”。[5](P241)特别是启蒙运动的发生,引起了人类整体心态和生存模式的根本变革。当然,时代精神的危机也意味着时代精神的转化,它预示着一种新的精神面貌即将出现。舍勒指出:“心态(体验结构)的现代转型比历史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更为根本。”[6](P17)生命模式的历史性变迁,造成了人类发展历程的“传统”与“现代”的区分。那么,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时候,会出现些什么问题呢?
二、传统性价值观的颠覆
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和总的态度。它决定着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和人生价值。而价值的变化又决定了其他的社会变化。从世界观的转变到价值观的颠覆,存在着历史逻辑上的不可避免的关联。也就是说,只要人们的世界观是从神转移到人身上,只要走出这一步,那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一切——不管是成就还是弊端——都是必然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不一定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而是某一理论学说发展的必然。所以,我们研究现代性时,绝不能从设定的概念入手来研究,而应把它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宏阔视野下进行研究与考量。这正如当代美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家、《单一的现代性》的作者詹姆逊所说的:“如果我们要执着地从概念入手研究现代性话语,那么我们毫无疑问会陷入同一性的陷阱。因为如果我们将现代性视为一个概念,我们就会将其视为绝对的和普遍的,并且在研究现代性问题的过程中看不到事物的差异,就会把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和现代性话语当作一种普遍性的东西去接受,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7](P前言20-21)
(一)欲望凌驾理性
传统世界观被颠覆、瓦解后,西方社会所理解的世界本体转移到人自身上来,对人的理解、对人性的理解也发生了彻底转变,从而也诞生了“新人”“新人性”。现代性是人的现代性,要把握现代性,就要研究人性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批判边沁时所说的,不仅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更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8](P704)
尽管东西方对人性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其中也有交集。如中国古代有“性善、性恶”“性三品”,以及“天理”与“人欲”的冲突;而西方从柏拉图分析人性的时候开始,就认为人性是由理性、意志、欲望三个部分组成。同时,东西方的传统社会中对于人性结构的分析也都是立体的,有层级等差之别的。中国古代把“至善”置于最高层;而柏拉图也认为理性、意志、欲望这三个部分中,理性最高,意志次之,欲望最低。托马斯·阿奎那也持类似看法,只是稍有不同:人性中信仰最高,理性次之,欲望最低。也就是说,在这个立体结构中,欲望在人性中一直都是最低的,上不得大雅之堂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欲望在人性结构中是最普遍的,任何人都有欲望,这是人性中最低的价值,因为动物也都有欲望。但理性却不是人人具备,或者说,从柏拉图的分析来看,理性应属于人性中的“神性”结构,只有具备相当高修养之人才能具备。所以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西方传统社会认为代表理性的哲学家最高(柏拉图甚至认为国王应该是哲学家),代表意志的军人次之,最低的也是工商。这些都是用最高的人性来管制约束最低的人性——欲望。
经过“现代性的洗礼”,新的世界观必然产生新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新的人性观,传统社会中立体性的人性观遭到瓦解,思想界开始从平面化的角度认识和分析人性,人性结构中的欲望、意志和理性、信仰等再无价值高下的等差之分。在这个背景下,不受约束的人性开始张扬,“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9](P275)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9](P277)由此带来了现代社会前所未有的物质丰富、经济繁荣和社会便利。据统计,到今天为止,人类社会97%的财富是在近250年里创造的,也就是在人类诞生以来的0.01%的时间里创造的。这正是“现代人”力量的充分展示。这是不容否定和抹杀的,也是人们引以自豪的。
然而,辩证法告诉我们,物极必反,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走向它的反面,这就是“自反性”,现代性的自反性也使人的欲望和物的发展走向了反面。马克思通过研究发现了现代社会发展中蕴藏的秘密:在现代社会中,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亦即资本必然天然的增殖逻辑,在这一逻辑的牵引下,必然引发商品拜物教或资本拜物教。马克思发现这一链条发展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的“自私自利”,一切价值的“为我性”,而资本主义突出利己性的原因,正是现代人的狂妄和人性中欲望的贪得无厌。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9](P277)吉登斯也曾明确地把驯服资本称为“驯服野兽”。我国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资本及资本之链带来的种种后果,如何驯服资本问题也非常严峻。正确认识和利用资本、限制资本、超越资本,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现实的课题。
但是,欲望与理性并列,并没有结束这场世界观的革命以及全社会的革命,资本之链背后,是价值取向的重大变化。曲高和寡的理性、信仰被拉下神坛后,像“落架凤凰”般地开始受到原本属于最低层次的欲望的无情嘲笑,价值判断的终极标准被彻底颠覆,欲望凌驾于理性和信仰之上,正如舍勒所说:“现代性——一言以蔽之曰:本能冲动造反逻各斯。”[10](P23)欲望、利益、自我就成了人性中的最高价值,笑贫不笑娼,金钱、美色等传统之“恶”步入道德殿堂的金色大厅,也走向每个人价值判断的最高位,用鞭子抽打着已经蜷缩一角的、可怜的理性与信仰。这就是现代性世界观支配下诞生的“新人性”,人变成了受欲望支配的动物。马克斯·韦伯指出:“当竭尽天职已不再与精神的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或者说,当这种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就不再被感受到了的时候,一般地讲,个人也就根本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在其获得最高发展的地方——美国,对财富的追求已丧失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转而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11](P126)大陆新儒家蒋庆先生这样评价现代性:“人欲跑到天理的位置上自称自己就是天理,而把真正的天理——‘魅'——扫除在地,极尽妖魔化丑化之能事,最后使人们厌恶天理,使天理最终在人类记忆中消失。这就是我对‘现代性'的总评价。”[12](P112)
(二)功利高于道德
在西方传统社会政教合一的体制下,主流的政治学说都承认政治的最高目的是道德。比如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的开篇就开宗明义指出:“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13](P3)中国的传统社会作为“伦理型社会”或“道德型社会”就更是如此。《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也就是说,政治要为道德服务,治国是为了明德于天下,政治必须具备实现道德目的的崇高功能,而不能脱离道德。社会评价体系也都是道德考虑高于功利考虑。正如《大学》中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吕氏春秋·长利》中记载:“天下之士也者,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若也;利虽倍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安虽长久,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汉书·董仲舒传》也指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句话,传统社会中,“形上”是高于“形下”的。
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现代性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图式。现代性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分化”,宗教改革的结果就是政教分离,这一分离的直接结果就是在西方的基本政治架构与制度安排中政治彻底脱离了道德,在制度架构上再也不受道德规范约束。其他各个领域也都从普遍的道德约束之下“解放”与“独立”出来,并宣称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自己成了自己的主人。政治宣称“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把实力最大化作为自己领域的“道德”。经济领域把实现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领域的“道德”,其他如文学、艺术、法律等领域都有了自己独立的价值。以往普遍的道德退守到伦理学和神学的小领域,基督教所体现的道德价值也只是诸多价值中的一种价值,只适用于宗教而不适用于其他领域。信不信宗教,坚不坚持内心道德,只是“个人的事”。道德再也不能统摄规范各个领域,因而各个领域开始可以不讲道德了,这种“价值中立”也是所谓的现代性。
政教分离之后,整个社会从宗教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促进了各领域、各行业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从国家层面来看,各民族国家在竞争中合作,在竞争中发展,国家利益被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也成了判断国家实力的标准。即使今天处于“第三世界”多数落后国家,除极少数部落制和非洲一些国家之外,其发展程度与该国纵向发展相比,也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都是社会现代性带来的巨大成就。中国由于到了清朝后期,闭关自守,与整个世界发展脱节,所以“落伍”了,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下一败涂地,“弱肉强食”的动物界法则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彻底让中国人警醒,在这种西方功利主义评价体系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道德评价体系土崩瓦解。自此以后,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基本上都是从功利角度来解释一切,一切向功利看齐了。正如蒋庆对现代性评价所说:“由于近代对人性有了新的看法,那些所谓启蒙了的人,突然发现,原来自己过去竟完全生活在黑暗中,原来一直受到道德宗教的压迫,现在终于启蒙了,眼前一片光明;现在终于解放了,除我自己外没有什么东西能约束我。用中国以前流行的话说,原来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我终于知道我以前全都错了,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人生来就是要享受,满足欲望天经地义,以前什么道德,什么宗教,全都是虚幻的,骗人的。”[12](P115)今天我们为什么在鞭笞、抨击功利主义,却又走不出这个功利主义、唯利是图的怪圈,就是现代性的世界观在暗中作祟、甚至主导和支配的结果。
(三)个体高于群体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其传统社会的基本特质和核心精神都是以群体本位来做价值判断标准的。《荀子·王制篇》认为:“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人善”如果缺少“城邦善”的支持就无法实现,人也就无法成为其所是。他认为人在本性上是社会性的,与社会群体相隔离就如同禽兽一般。“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就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以身体为例,如全身毁伤,则手足也就不成其为手足,脱离了身体的手足同石制的手足无异,这些手足无从发挥其手足的实用,只在含糊的名义上大家仍旧称之为手足而已。我们确认自然生成的城邦先于个人,就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才能让大家满足其需要]。”[13](P8-9)群体本位思想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林语堂先生说“血缘是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基础之上,它强调以群体利益为核心利益,个人只是群体的组成部分,强调个人对家族、社会等群体的责任、义务和贡献。东西方传统中的这种群体本位价值观对于促进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会造成社会绝大多数个人沦为极少数人统治的工具,个人的正当利益、权益得不到尊重等问题。
世界观发生转向之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也发生了转向,由被支配和从属的地位变成了支配和主人的地位。笛卡尔的“我思”与康德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使得具有“自我意识”的人逐渐成为征服世界的自足主体。因为人类的“我思”“理性”,打破了权威,但也打乱了最高信仰,只承认“我”是实在的,其他都是可质疑的。所以格里芬认为:“无论如何解释,现代性总是意味着对自我的理解由群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一个重大转变。现代性不是把社会或共同体看成首要的东西……作为一种理想,人们一直强调的是个人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14](P5)也就是说,现代哲学集中关注的是个体,个体的生成方可视为现代性的标志。在这一转向的过程中,主体已不单单是个实体范畴,更是一个价值范畴,是对人所具有的地位和意义的一种价值评价,体现的是一种能动的价值关系,只有处在这种关系中的人才是主体。正如马克思所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15](P34)这就形成了人从自身出发、以人类中心论的视角看世界的思维模式。个体主体性激发了蕴藏在人体中的潜能,调动了人们内在的积极性。
个体本位发展的典范就是美国。美国现代性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竞争主义与征服主义的混合体,它把“欲望满足”理念、“自由实现”理念、“经济人”理念和“以‘人'为本”理念与享乐主义人生观奇特组合,把欲望人本化,把“人本”自然主义化,号称实现个人自由最大化、个人利益最大化、个人才能最大限度地施展,编织起了如巨型气球般的美国梦,创造了资本主义的繁荣。这种极端个体本位相信人为宇宙之主,正如唐君毅所说:“近代之西洋文化……要想建立人国于地上与天国比美,而显出一与上帝竞赛伟大的雄心,成所谓浮士德精神。”[16](P272)然而,詹姆逊就提醒人们不要被现代性话语的美丽面纱所蒙蔽。在詹姆逊看来,不管现代性话语如何宣扬自由、平等与解放,它们都有意无意间体现了现代化的资本逻辑,最终都没有逃脱资本逻辑的吸纳。
个体高于群体的直接结果就是,个体私利成了人人都认可的“社会公利”和“善”。在此价值观支配之下,冲破群体利益约束的个体利益必然要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允许在市场上不受道德约束地追求自我利益的做法,其合理性也得到了“理性经济人”为之辩护的道德证明。这种发展模式扩展开来,进入了生活中的许多领域,紧接着便是为了实现自我利益,便可不再顾及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了满足当下的利益,便不可再顾及长远发展的利益。也就是说,注重个体,必然淡化集体和他人利益;注重当下,必然诋毁传统,沉醉于对新颖性的追求之中,把现代性说成是“启蒙”,把过去则说成是“黑暗的时代”。忽视将来,只会在当下的及时行乐中寻找意义。自我膨胀必然导致自我迷失和人的异化,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从何处出发,更不知道要去往何方,虚无主义便降临了。美国的乔·霍兰德指出:“在接近20世纪末的时候,我们以一种破坏性方式达到了现代想象的极限。现代性以试图解放人类的美好愿望开始,却以对人类造成毁灭性威胁的结局而告终。今天,我们不仅面临着生态遭受缓慢毒害的威胁,而且还面临着突然爆发核灾难的威胁。与此同时,人类进行剥削、压迫和异化的巨大能量正如洪水猛兽一样在‘三个世界'中到处肆虐横行。”[14](P64)
现代性既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利益,也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使现代社会成了名副其实的“风险社会”。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形容的正是现代性图景:“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格里芬认为:“人们不再把现代性看作是所有历史一直苦苦寻求以及所有社会都应遵守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而越来越视之为一种畸变。我们认识到,传统社会已持续几千年,而现代社会能否存在100年还是个问题,因而人们开始对传统社会的智慧予以新的关注。同样,现代主义这种世界观越来越不被人们看作是‘终极真理'。”[14](P235)以上这些其实是在告诉我们,现代性经过上千年的酝酿和数百年的发展,已是不可避免的当下实存。应当看到,尽管现代性带来了诸多问题,但也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带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当然不能逆时代而行,但我们应当也必须理性审视现代性,辩证地否定,科学地扬弃,使之为社会造福。因此如何科学构建现代性,取长避短,就成了近代以来思想家和政治家一直不懈的努力和追求。
三、现代性世界观的重构
中国的现代性是后发现代性,其构建过程与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密切相关,是伴随着西方的武力入侵与“科学运动”进入中国的。一方面是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图景,另一方面掺杂于其中的危机、焦虑和困境意识也一直萦绕在中国人的心头。在追求和引进现代性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与现代性相伴而生的种种弊端,力图重新认识现代性、深入批判现代性、全面超越现代性。现在世界比较流行的超越现代化模式是“后现代性”构建模式。但是,后现代性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建设性的后现代性,另一是解构性的或消除性的后现代主义。后者以一种反世界观的方法,消解了世界观中不可或缺的自我、意义、真理等成分,导致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不仅如此,纯粹名词术语的转换,对于解决现实问题并起不到什么作用,毕竟我们不能在下一个时代,或更远的未来,再创造出“后后现代性”或“后后后现代性”来解决问题。现代性的构建是个系统工程,单纯依靠传统、当下或未来都不能解决问题,而是要在传统、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历史链条上寻找一个平衡点。应当清醒看到,尽管各国国情不同,现代性在不同国家的构建图式也必然不同。但是,要构建现代性,有一个根源性的东西是相同的,那就是只有发展出一种新的世界观,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自我在宇宙中的定位,重新发现能够给人类存在与发展赋予意义的合理的精神支撑,重新调整与校正人的生存根基与精神气质。在此基础上,再综合调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才能使这种被颠覆的价值观得到改变与重构。这种认识与重建,绝不是简单地回复到过去,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提升过程。
(一)存在观——再启蒙
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们来理解和证明自己与世界的联系。传统社会是靠宗教、道德来确定自己与世界的联系的。经过现代性的启蒙,人类整体性地失去了身份认同、遭遇了无家可归的茫然感和生活无意义的空虚感,这就必须要求我们来一次“启蒙之启蒙”,在重新认识世界中重新认识自我。因为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就对自我如何进行定位;我们如何认识自我,我们就如何存在;我们心中最服从什么,我们就会如何行事。决定我们生活意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会由此重新确立。
在对世界与自然的认识上,既非世界凌驾人类,也不是人类征服世界,应该说,自然界是人类的家园,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呵护的大花园。这一点,中国古代“和”的哲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理念仍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由于人生命的有限性和宇宙的无限性,人永远不可能摆脱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制约。尊重自然规律,顺应世界潮流,对于人类更长久的存在,更健康的发展,永远具有第一位的意义。离开这一前提,把人视为自然的主宰和霸主,其最终结果就是加速人“类”的自我毁灭。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定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17](P519)
为此,我们还需要在重新认识世界的基础上认识自我。现代性社会由于颠覆一切、怀疑一切,导致了相当程度的自我身份定位系统紊乱。社会秩序有序的前提是界定身份认同,即确定“我(们)是谁”。如果我是丈夫,就应该爱妻子;如果我是中国人,就不应该崇洋媚外;如果不知道我是谁,就不知道我应如何。如果界定我是赚钱机器,那一切道德准则都是浮云。界定了社会身份,价值观就比较稳固。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身份界定方面的“个人主义已成为现代社会中各种问题的根源”。[18]人既是自然的存在物,又是社会的存在物,应该在自然与社会中谦逊地存在、有限地认知,自觉做自然与社会的维护者。人既要对他所认识到的保持理性,又要对他长时间尚未认识和认识不到的保持敬畏。不管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中心主义”,都不是冷静而客观的态度。从长久来看,不仅妨碍着人们客观地认识世界,也妨碍人们正确地认识自身,还妨碍人们理性地认识他人,人类社会的诸多争斗、战争都由此缘起,这必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这种对“自我”的过度认同和过度膨胀,往往是以歪曲、蔑视、贬低他人为条件的,其结果是导致人与自然对立,人与社会对立,人与他人对立,导致多重的不和谐。
重新认识了自我,才能重新界定人我关系。一些思想家主张摒弃现代激进的个人主义,倡导主体间性来消除人我之间的对立,这应该说是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属性在于他的社会性,人不可能脱离他人而独立存在,人必须在与他人的协作与交往中才能体现自我价值,实现自我价值。人作为自然生命,与自然界是一致的,有限的自然生命对于无限自然的认识本应是谦逊而有限的认知,而不是膨胀的、狂妄的认知,对于自然界的改造是友善的利用,持续的有节制的开发,而不是破坏性的宰制。只有这样,才能在机械的传统有序与激进的现代失序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找到和谐的生活秩序。明白了这些,我们才能在纷乱的社会中不迷茫,懂得如何存在,懂得如何去生活。
(二)发展观——限制
在科技高度发展、改造和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人对自我定位越来越自信的今天,我们需要的可能不是如何加速度向前,而是在哲学认识上学会“节制”“限制”或“克制”。
人性的克制。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这里无意重新构建一个体系。既然现代性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不加限制的自我主体性膨胀引起,在重新认识世界与自我的基础上,我们必须要学会的则是“节制”“限制”或“克制”。这正如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的“利用、限制与改造”,又如埃利亚斯所说的“克制”之意。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洞察非常深刻,见地入木三分,但我们搞建设又离不开资本。我们倒是想利用资本的优点并克服它的缺点,但多数时候在资本的逻辑面前却无能为力。资本对利润的无限制追求,其实质是人心对利润的无限制追求,因此我们必须要回归于对人性贪婪的限制。尊重人的合理需求,限制人的无度欲求。埃利亚斯认为“文明的大厦建立在克制本能冲动的原则之上”。[19](P194)如果我们想超越现代性,却不从人的角度入手,不去遏制人性的贪婪无度,只不过是用更大的物质、更多的错误来掩盖当前的失误,无异于扬汤止沸,负薪救火。
发展的限制。当前的现代性社会走入了为了发展而发展的怪圈,为了追求所谓的发展,人们对自己给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视而不见,心安理得,并认为贫穷、失业、债务、通货膨胀、赤字、污染、犯罪等诸多问题都可在所谓的“发展”中得到解决。霍伊将这种寄希望于未来的思想称之为“乌托邦式思维”,他认为把经济增长视为至高至善的灵丹妙药,耗尽自然资源以支持人类挥霍,这就陷入了一种追求经济增长的“增长癖”。它本质上是西方线性进步观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丝毫无助于我们了解我们在过去哪儿做错了,有哪些错误我们其实是能够避免的。[14](P代序13-14)所以,尽管后发展国家力图避免现代性的弊端,却根本无济于事,不知不觉中仍然是步入了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老路和陷阱。
这种不加限制的社会发展模式,吉登斯称之为“失控的世界”,并引用沃尔夫斯坦大主教于1014年说的话:“这个世界正急匆匆地走向它的尽头。”[20](P1)丹尼尔·贝尔也认为,文明的衰落是由于不加控制的人性欲望所致,“各种文明的兴衰史上都出现过这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在崩溃之前,社会总要经历一个个标志着衰落的特定阶段——此乃天才的阿拉伯思想家伊本·赫勒敦的历史哲学基础。这些递变的顺序是从朴素到奢侈(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二卷里称之为“从健康城市到高烧城市”),从禁欲到享乐。”[21](P130)所以,他认为:“我们正在摸索一种语言,它的关键词汇看来是“限制”: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开发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生物界横加干预的限制。”我们国家秉持的理念是可持续发展,避免“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度统一起来,这些都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这就必须要让人们相信单纯经济增长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无序和乱象,只有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稳态经济”才是人类社会的唯一出路。
可是,如果想让高速发展的经济降温、自限,绝非易事,许多人会立刻想到“生活水平下降”,立刻想到曾经受苦受难的岁月而心有余悸。丹尼尔·贝尔认为:“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发展中工业化社会的世俗宗教:个人动机的源泉,政治团结的基础,动员社会以实现一个共同目标的根据。”[21](P295-296)格里芬也认为,我们这个时代被实利主义所驱动,追求无限增长。他希望经济能返回它的正常位置,亦即用来满足人的需求、但不是为了人的无限欲求而无节制地发展。他把经济无限增长视为“一种除了在我们这个反常的社会之外的所有社会中都应有的地位,而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经济却成了关注的中心,它事实上成了一种宗教”。[14](P代序31)因此,当经济增长成为“世俗宗教”、且被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的时候,除非人们集体性地遭遇重大挫折,否则很难说服世人接受这一认知。
(三)实践论——融合
如果说“分化”是现代性的最大特点、并把一切都导向碎片化的话,要超越现代性就要在社会充分分化的基础上,走向并实现更高层次的“融合”,包括传统与现代融合,物质与精神融合,理性制度与精神信仰融合等。
传统是我们的根,它蕴含着一个民族的基因、血脉、集体经验和整体记忆,现代人精神迷失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割断了传统。但我们构建现代性不是纯粹的昔日回归,不是要那种一神论或存天理、灭人欲式的生活,也不是只活在当下、注重眼前利益的破坏式存在,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美好社会的无限遐想,而是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合适的结合点,使之保持必要的张力,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进而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性生长的同频共振。尤其要把传统中对于道德的坚守,对于人性的冷峻认知,对不可知力量的畏惧,以及对现代人无限扩张和实现自我所持的怀疑和克制态度结合起来,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价值资源,寻找身份认同,构建意义世界。
物质繁荣的丰裕社会,人们的精神迷失在物欲之中,用贝尔的话说就是经济冲动力战胜了宗教冲动力,韦伯说它是工具理性战胜了价值理性所致。面对现时代的精神混乱,需要重新而彻底地审视人类社会的理念形态,这种理念和精神要立足于本民族的实际,而不是外在和脱离本民族的抽象理论。我们必须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寻找结合点,构建一种成熟的、稳定的精神文化或价值观念,甚至可以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出现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形成一套适应新时代发展的伦理道德规范,用以协调日益巨大的物质力量,而不至于被物所牵所役,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本和共同坚守的精神家园。
另外,当今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仅有精神文化建构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合理的制度安排。“文化是制度之母”,在一定意义上说,制度是文化的固化。一种价值理念(如法治理念)要深植入每一个公民的内心,使其坚定不移地按此行事,这一政治安排或制度架构必须适合本国国情,并体现时代性、正义性、平等性、包容性、开放性和价值引领性。这一制度安排要兼顾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现代个体的主体性、个性、自由等精神特质;另一方面要保证具有这种精神特质的个体如何形成一个合理合法合情的共同体;同时实现传统与现代、个体与集体、国家与社会、制度架构与精神文化等的有机结合。以道德和精神信仰来为制度建设提供合法性依据,以制度建设来保护道德和精神信仰,使其在多元社会中为人的存在的发展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宗教[M].孙慕天,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2][美]安德鲁·霍菲克.世界观的革命:理解西方思想流变[M].余亮,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章太炎全集:第4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4]陈赟.困境中的中国现代性意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卷[M].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
[6][德]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A].刘小枫,主编.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7][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单一的现代性[M].王逢振,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1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雷震,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
[12]蒋庆,盛洪.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M].福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1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4][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6]唐君毅.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A].张祥浩编.文化宇宙意识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8][韩]金泰昌.世纪大转换时期与政治哲学有关联的神学、哲学体系的转变[J].国外社会科学,1996(5).
[19][法]达尼洛·马尔图切利.现代性社会学[M].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20][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责任编辑沈斐]
The Subvers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World Outlook:from the Traditional to a Modernist View
WANG Xi-guo;LIU Fang
(PLA Nanjing Political College at Shanghai,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The modern society has witnessed a confusion in the value of human society. What is the origin and future direction of this confusion?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bout modernity relies on a full knowledge both of its origin and future direction. Taking“world outlook,values and methodology”as the main clue,the paper studies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world outlook from the era in which God played the leading role in spiritual world,to the age when human and God stand side be side and finally become the master of their own life. The subversion of traditional world outlook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new values in human society,such as giving priorities to personal desires rather than rational appeals,the collapse of morality driven by utilitarianism and individualism's overriding on collectivism. Thus new modernist value relies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world outlook with re-enlightenment of“the true value of life”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guidance of philosophy on practice,we can achieve a higher level of“integration”of new world outlook.
Key words:modernity;world outlook;re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6)02-0052-11
收稿日期:2015-11-26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现代性视阈中人的精神家园建设”(项目编号2011BKS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喜国(1973-),男,辽宁建昌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讲师,军事学博士,军队政治工作学博士后;刘芳(1953-),男,山东招远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