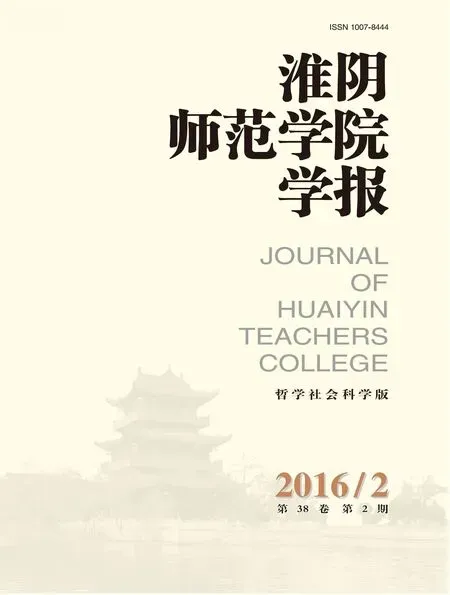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考据
谢保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考据
谢保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显微镜下解剖琐事”作为一种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以严谨的风格、缜密的方法创立了他们的学说,成为重视考据和善于考据的典范。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深刻的理论论证和丰富的历史实例紧密结合的经验总结,是不断得到验证的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必须具备深邃的理论素养、厚重的历史知识,并善于历史考据,才能不断抵制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充实、完善和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理论素养;显微镜下解剖琐事;历史考据
历史考据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通过对掺杂了不同时代主观意识、碎片化了的各种历史记载的系统整理、综合考察,而后“寻其伪之所自出,通其类例之所在”的一种辨别伪史、探寻历史真实的科学方法。长期以来,对历史考据的认识被人为地搞得很混乱,似乎马克思主义从来就反对历史考据。近日养疴在家,对近年有关这个话题的讲学记录稿略作整理,形成这篇文字寄《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多少表示一点对学报长期赐刊而无回应的歉疚之意。
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重视考据和善于考据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考据作为一种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以风格的严谨、方法的缜密,创立了他们的学说,成为重视考据和善于考据的典范。
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主义历史观——都是在从“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来说明历史的过程中发现的。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集中在《资本论》全书中,反映马克思对于考据的高度重视和娴熟运用,第一版序言明确地写着:“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1]8把从事研究比喻为“显微镜下的解剖琐事”,形象而深刻地道出考据的基本特征。《资本论》通过“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看穿整个商品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的演进,正可谓“以小见大”的最经典的典范!从后面第二三部分的引文,同样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实际的细节”“单独的实例”等的强调和重视。自1844年到1883年逝世,马克思“把从事实际革命斗争和‘为了挣钱’的工作以外的全部时间”,都用在了这一巨著的写作上,40年间研读过的相关著作都是写有提要或摘要的。由于马克思认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的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23-24,所以《资本论》“在形式上”不像我国近现代考据家的著作那样,在书后列有引用书目。但从《资本论》编辑者在每卷书后编辑的“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来进行统计,则有1 500种以上的著作。从马克思本人所作注,更可以看清其引书的做法,如第一卷第一篇第二章交换过程,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作为价值只是耗费在它上面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注(47)引述福尔邦奈、孟德斯鸠、列特隆、黑格尔、帕尼尼等人著作中的不同说法。[1]109这正是对当时关于货币是否“商品符号”所“展开了论战”的一个简要考证,完全可以与司马光《通鉴考异》的做法相媲美。再从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最基本方法看,“为了掌握材料,为整理材料作好准备”阅读相关书籍,然后“把材料整理出来”,1854年12月—1855年1月以《货币,信贷,危机》为纲目,在每一目之后标出摘自不同作者(吉尔巴特、桑顿、图克、哈伯德、约·斯·穆勒、富拉顿等)的笔记,注明作者、书名和自己笔记本的页码,后来在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第三卷相关章节时,采用的就是这份材料[2]。事先做《货币,信贷,危机》的纲目,与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之前做“丛目”“事目”不也很相似吗?
再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从未涉及领域的考察和研究。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数十年间,欧美学者围绕人类原始历史和文明起源出现研讨热,引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极大关注,认为这预示着“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及进一步窥探人类史前史的可能”[3]12。马克思1881年5月至1882年11月,围绕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结合亨·梅恩、鲁·佐姆、爱·泰罗、约·拉伯克等多人关于史前文化研究的著作,认真阅读、详细摘要、撰写批语,这就是今天见到的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单行本,共270页)。恩格斯根据这些基本素材完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撰写,因此说“执行”马克思的“遗嘱”。如果用传统的考据学术语来做比喻,说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是恩格斯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史料长编”,是不是也不为过?而且,恩格斯对摩尔根的取材情况可谓做到了如指掌的程度,一面肯定《古代社会》“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劳动。他研究自己所得的材料,到完全掌握为止,前后大约有四十年”,才使这本书成为“划时代的少数著作之一”,一面指出关于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摩尔根所掌握的差不多只是第二手的材料,而关于德意志人的章节——除了塔西佗以外——还只是弗里曼先生的不高明的自由主义的赝品”,同时表示:关于希腊、罗马历史的章节“补充了我所掌握的材料。关于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章节,基本是属于我的”,经济方面的论证“我把它全部重新改写过了”[3]3。
19世纪初,特别是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中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以及生物学领域都获得一系列卓越的发现和成就。恩格斯在与马克思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同时明确表示:“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4]为此,他于1873—1886年间完成了《自然辩证法》中的10篇论文、169个札记和片断,引用当时著名科学家的著作总数有百余种,并充分利用期刊《自然界》发表的各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从现存的169个札记和片断,可以清楚地知道恩格斯的研究线索或思路。其中部分材料直接运用到论战著作《反杜林论》中,同样展现着他那严谨、缜密的科学风范。《反杜林论》第一编《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驳论杜林的“定数律”,在引述了杜林三段文字(约1 000字)之后,首先清楚地指明:“这些命题是逐字逐句从一本书上抄下来的,这本书在1871年第一次出版,书名是《纯粹理性批判》,伊曼努尔·康德著。这些命题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第二编第二卷第二章第二节纯粹理性的第一个二律背反中读到。”然后讽刺说:“杜林先生的光荣只在于他给康德所表述的思想按上了一个名称——‘定数律’,在于发现有一个时候世界虽然已经存在,但是还没有时间。至于其余的一切,即在杜林先生的分析中还有些意思的一切,那就是‘我们’——伊曼努尔·康德,而‘现代’只不过是九十五年以前。”原来,杜林的几段文字都是沿引的康德的观点,只不过按上了一个“定数律”的新名词,其余的一切,所说“我们”实即康德,所说“现代”实即95年前。随后,一针见血地揭出:“康德根本没有说上述命题已经通过他的证明得到解决了。相反地,在同页的对照栏内,他叙述并证明了相反的命题: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在空间上没有终点;康德正是在第一个命题像第二个命题一样可以得到证明这一点上,看出了二律背反,即不能解决的矛盾”,而杜林却“孜孜不倦地从康德的二律背反中抄下对他有用的东西,而把其余的东西抛在一边”[5]87-89。考察如此细致,揭露必然彻底!
至于《德国农民战争》,则提供了一个完全借用“唯心主义”史料进行唯物主义历史研究的范例。恩格斯首先表明自己“并不奢望提供独立研究过的材料”,而是“借用的”威·戚美尔曼的《德国农民战争》(1—3部),认为它“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著作中值得嘉许的一个例外,就当时来说,它还是写得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然后指出其主要问题是论述“缺乏内在联系”,而这正是其书“问世的那个时代特有的错误”[6]287-288。
上述实例足以显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如何在“显微镜下解剖琐事”的,这需要我们切实继承、不断弘扬。时下有些论著也罗列一串相关的“参考书目”,其实作者并没有看过其中的几种,甚至不知所列书中有诸多与其本人观点完全相左之处。这种罗列“参考书目”与马克思不列书目却在注文中详注读书摘要、评语,实有天壤之别!
如果读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著能够有在“显微镜下解剖琐事”的耐心,不仅不会有所偏见,还会以严谨、缜密赞赏他们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具体方法的。
二、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在理论论证和历史研究结合中不断得到证明的唯一历史观
唯物主义历史观有一个形成、完善、发展的过程,是迄今所知形形色色历史观中唯一经过理论论证与历史研究结合、不断得到证明的历史观。
1845年以前的几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独立地形成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念。1845—1846年在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对这一历史观作了初步概括,但所用术语尚未确定。一年以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明确了“生产关系”这一概念,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一方面继续经济学理论研究,一方面分析当时的政治事变,研究各相关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两个方面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不断证明唯物主义历史观。而这后一个方面,大都以时事评论的形式发表,对于当时发生的重大事变以及与事变相关的各国历史进行考察和研究,作出带有预见性的评述,大都带有“以小见大”的显著特点。这一部分论著对于完善、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具有重要意义。限于学识,在此仅作一点提示。
马克思、恩格斯评述当时事变,差不多囊括了整个欧洲所有的国家,涉及各主要国家的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外交和对外政策。对欧洲以外国家的关注,主要在与欧洲事变有相互依赖关系的土耳其、中国、印度和北美。
考察法国事变与历史。如果说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7],那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则是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一段历史的杰出代表,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透彻的洞察”,使唯物主义历史观得到具体阐述和历史验证。
考察德国历史与事变,恩格斯有两部名著,上面提到的《德国农民战争》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并获得理论建树的一个范例,《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围绕德国1848—1849年错综复杂的历史,“根据确凿的事实找出合理的原因来说明运动的主要事件和主要转折”[8],使唯物主义历史观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并提出和阐述了起义是“一种艺术”的原理,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起义学说的基础。
考察英国方面,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后,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二人在《纽约每日论坛报》《新奥德报》上发表的关于英国问题的评论,特别是1855—1856年发表的与英国有关的评论。通过诸多实例考察当时工商业周期的各个阶段,将早在40年代就已提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有周期性的原理具体化,发表了一连串以“危机”命名的评论,如《工商业危机》(经济周期又到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投机为危机代替”的阶段)、《论内阁危机》《两种危机》《论新的内阁危机》《英国的危机》《金融市场》(引用英国金融危机加深的材料)、《欧洲的金融危机》等,预见到1857年将爆发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恩格斯1855年9月26日即告知马克思,“推测危机将在1857年夏天爆发”。这一系列的评论,都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现实、预见未来的范例。
考察亚洲事变。1853年3—5月间,马克思阅读有关中国与印度历史和经济方面的著作并作摘录,5—7月写成《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评论,分析英国对亚洲的掠夺给欧洲带来的深刻影响:“在最惊人的繁荣当中,就已不难看出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的明显征兆……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末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按:太平天国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不列颠的工商业又已经经历了通常的一个经济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从印度这方面来看还必须指出,在印度的不列颠当局收入当中,整整有七分之一是来自向中国人出售鸦片,而印度对不列颠工业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决于印度的鸦片生产……中国的新皇帝颇有意在本国种植罂粟和提炼鸦片,显然,这将使印度的鸦片生产、印度的收入以及印度斯坦的商业资源立刻受到致命的打击。虽然有关的各方或许不会马上感觉到这种打击,但终有一天,这种打击的影响会充分地显示出来,并且使普遍的财政危机尖锐化和长期化,这种危机我们在前面已经预测过了”[6]4、6-8。理论分析与历史事实的紧密结合,既为如何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做出范例,又表明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空泛的理论,而是经过历史和现实不断验证的历史观。1857年6月,恩格斯发表《波斯与中国》,不仅预见到“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还告诫英国那些“向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我们不能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任何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6]20-22。这篇评论告诉人们:在认识国际争端问题上,只有坚持以史实为基点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能避免历史虚无主义和采取“双重标准”。
考察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是马克思、恩格斯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原理并使之具体化的又一范例。在《北美内战》《美国内战》《北美事件》《美国战场的形势》等评论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具体材料说明18世纪末的北美独立战争揭开了美国资产阶级统治的纪元,南北战争“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的活动必将与华盛顿齐名”[9]。在这些评论中,还揭示出战争性质影响作战方法这一军事科学的重要原理,并提出相应的军事战略计划。战争的进程证明了他们预见的正确,唯物主义历史观再一次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重大历史事变中得到验证。
以上所举马克思、恩格斯推动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断丰富和逐步完善的历史实例,就是马克思1859年1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6]84-85而获取的,最终对这一历史观作出了经典的表述,为人们经常引用。1863年8月以后,马克思决定用更加系统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理论学说,至1865年12月完成《资本论》的新手稿(共3卷),1867年9月第1卷出版。列宁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没有另一种想科学地说明某种社会形态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在没有另一种想象唯物主义一样把‘有关事实’排列得秩序井然,把某种社会形态生动地描绘出来并给以极科学的解释的尝试之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别名……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10]
1870—1871年,“两场大战——普法战争和法兰西内战——改变着欧洲的面貌”,唯物主义历史观得到进一步验证。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两篇同为马克思所写的《宣言》,再次“显露出惊人天才,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6]324。恩格斯的《战争短评》(包括59篇评论)则为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军事事变的典范,将先前提出的关于一个国家的军队状况和战斗素质取决于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原理更加具体化和深刻化,从普法战争以前的战争经验中援引实例进行广泛的历史对比,以惊人的洞察力精确地预测军队的运动方向、正在展开的战斗进程以及对战争进程的影响,最经典的例证就是提前五天预见到法国麦克马洪军团将在色当惨败而降的战争走向。[11]
在看到“两场大战改变欧洲面貌”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看到“仍在继续进行”的第三场战争,即“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战争”。马克思在继续完成《资本论》的同时,以《哥达纲领批判》发展自己的学说,回击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恩格斯以《反杜林论》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和统一性,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丰富了唯物主义历史观。1880年3—5月,恩格斯发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第一次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名词。虽然指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成为科学,但仍然强调“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要精准”地描绘“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3]424、420。换句话说,仍然坚持继续对这一原理的“一切细节和联系”进行科学的、辩证的论证和验证。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结尾处追述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时,恩格斯只提到中世纪社会、资本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三个阶段,尚未涉及人类起源、原始社会。随后,“执行”马克思“遗嘱”,1884年3月—5月完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系统阐述原始社会演变的过程,把家庭作为一个历史范畴进行考察,分析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通过对古代雅典、罗马国家以及克尔特人、德意志人氏族和国家的演变考察国家的本质及特征,使此前唯物主义历史观没有解决的问题得到新的科学的论证。
纵观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完善、发展过程,列宁作出又一科学的论述:“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12]
相比而言,历来形形色色的历史观,有哪一种是经过如此深邃的理论论证和丰富的历史知识相结合而总结出来并得到验证的呢?对于那些缺乏“丰富历史知识”的形形色色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均目之为“虚构体系”,如马克思称赞黑格尔是“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但同时指出他“爱好虚构思辨体系”[6]1,而恩格斯批判“创造体系的”杜林是“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5]46-47。20世纪20—40年代国内不同意甚或反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学者也多有相似的认识,如王国维经历了从研究哲学到研究历史的转变,深有体会地说:“哲学之历史,空想居其半焉。”[13]常燕生(乃德)在其代表作《生物史观与社会》中用一节篇幅评述“历史科学上的几种观点”,批评历来的历史家和哲学家努力想拿出一种或数种原则来说明历史的现象,但他们的说明“多数不根据于事实的归纳,仅凭一己冥想独断而成,所以不免陷于玄学的窠臼”,自斯宾诺莎至黑格尔“所有历史哲学的解构都是玄学的,而非科学的”[14]。
三、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必须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并善于历史考据*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需要深刻的哲学理论和丰富的历史知识的紧密结合,本文只谈如何结合“历史实例”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方面,不涉及如何加强理论修养的方面。
唯物主义历史观被发现以前,从事历史考据卓有成就者不乏其人。唯物主义历史观被发现之后,既有摩尔根那样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并“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者,也有“不以史观为急图”或“不甚同意”唯物主义历史观而取得巨大成就者,他们关于历史考据的成就和方法至今仍然为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人所推崇和遵循,推动着中国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这种情况表明,历史考据追求的“实录”原则或“求实”态度是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但这种“实录”或“求是”,仅仅“求其是”而未必能够“求其所以是”,仅仅“知其然”而未必能够“知其所以然”,仅仅是进行研究必须经过的一步,而不应该是局限研究的一步。“述往”为着“思来”,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用新的“历史实例”完善、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断证明它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仍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
唯物主义历史观被发现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在运用这一历史观方面有着不成熟的地方。恩格斯1895年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导言坦白地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以及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7]597另一种情况是,在分析刚刚发生的事变时“没有时间和可能去核对”消息来源,如1853年所写《俄军在土耳其》《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土耳其战争的进程》,1855年所写《俄国军队》等评论,都影响到对事变的某些估计和预测。[15][16]这两个方面的情况告诉人们,即便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运用这一历史观分析问题时,未能精准地审核材料,也会出现偏差,经不住历史的验证。由此,恩格斯在1859年提出了一条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原则:“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6]118说得多么清楚、明白!要用“历史实例”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哪怕“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都必须进行“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即经过缜密的考据,才能够完成。任何脱离“历史实例”的史学理论研究,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总结的这一基本原则的。
前面谈到唯物主义历史观发展,直至恩格斯逝世,已经论证了的人类“发展进程”主要是用欧洲的“历史实例”论证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中世纪社会以及资本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等不同的历史阶段,而用中国的“历史实例”论证和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尚有大量研究工作需要去做,况且中国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中国的“封建社会”更具“中国特色”,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用中国古代的“历史实例”论证和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做出大量成绩。随着近几十年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实例”的大量材料的涌现,形成又一轮的中国史研究新潮。中华文明起源,夏商周考古,甲骨、简牍、敦煌、西夏研究的逐渐成“学”,明清档案的系统整理和利用,地方志的系统整理和利用,各少数民族史料的整理和利用,等等,展现中华民族发展全貌的研究正在“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艰辛地进行着,这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为用中国的“历史实例”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提供了绝好的机遇和再充实不过的基础资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应当牢记马克思、恩格斯的教导,像马克思写《资本论》、恩格斯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那样,在“显微镜下解剖琐事”,“对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探讨”,把“深刻的哲学理论与丰富的历史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够切实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才能够不断用中国的“历史实例”充实和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
近代以来,中国从被动到主动,逐渐融入世界,记述和反映中国的社会、中国的事变、中国的历史者不再局限于国人。大量不同肤色、不同观念、不同利益的政治家、学人,从不同视角观察、了解、认识中国,评论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出现的重要历史人物,用各种文字留下极为丰富的档案材料和记述资料。经历近代事变的各类人物,更留下关于当时时事的诸多文字,包括记事、书奏、信函、日记,等等。这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开放程度扩大而逐渐呈现出来,视野不断拓展,认识程度渐次深化。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关于东方主战场的全面认识和史料发掘,可谓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典型范例。当人们把视野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争,拓展到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再放眼为20世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抗日战争,历史资料的发掘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盛况,“禁区”解禁,档案解密,海内外各种形式的人证、物证,包括声像、多种文字记录大量涌现,最终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20世纪的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中国开始,在中国结束”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最新科学论断,正是通过正确的历史观与验证的历史资料紧密结合总结得出的!这再一次提醒人们: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必须以科学的历史观与缜密的历史考据紧密结合,“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
重温恩格斯晚年批评“青年派”歪曲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系列论述,对于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历史考据紧密结合,有效地抵制各种“主义”或史观,防止史学研究碎片化倾向,仍然具有重要意义。1890年8月5日恩格斯写信给康·施密特强调:“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地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3]475
就所见的某些历史研究、特别是某些史学理论研究,或因为时风急功近利而好讲“原理”、喜说“大话”,大都缺乏马克思在“显微镜下解剖琐事”的理念和定力,不想进行“多年冷静钻研”,不愿对“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探讨”,只求“尽速构成体系”或连篇累牍的数量,缺乏实实在在的、经过缜密考证的历史实例,发表的成果论说空泛、历史知识贫乏,既使历史虚无主义有了某种展示的机会,又给碎片化研究的浮现留出了空间。如果这些历史研究,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能够像恩格斯所要求的那样,把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充分掌握大量经过审查的历史资料,不给历史虚无主义留下丝毫的史料空白,它还怎么去“虚无”历史!同样,让碎片化研究在大量经过考证的历史资料面前相形见绌,它还会有市场吗?恩格斯写给保·恩斯特的信指明,当你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让人家认为“抓住”了你的“错误”,而且还显得“他是有一点道理的”[3]472。全视角地审视历史虚无主义,不能只强调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个方面,还必须强调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善于缜密的历史考据这一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特别是在当今的大气候下谈论国际领域的历史问题,面对的是诸多持不同历史观念的人群,更要记住恩格斯的告诫,“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唯有靠大量经过缜密考据的历史资料、实践验证的历史事实才有说服力,才有可能使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要像马克思主义那样赢得世界,必须做到深刻的哲学理论与丰富的历史知识紧密结合!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14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91.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0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86.
[10]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75.
[12]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4.
[13]王国维遗书:第4册[M]//观堂别集:卷4国学丛刊序.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8上.
[14]常乃德.生物史观与社会[M].上海:大陆书局,1933:1-2.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说明.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说明.
责任编辑:仇海燕
Marxism and Textual Criticism of History
XIE Bao-cheng
(Institute of Histor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
Abstract:1.The founders of Marxism took "dissecting trivial matters under the microscope" as a methodology of researching. They established their theory with precise style and deliberate means, which has become an example in the field of textual criticism. 2.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an experiential summary of close integration of the profound theoretical demonstration and abundant historical instances. It is also an exclusive scientific conception of history which has been continuously verified. 3. In order to resist varied conceptions which do not belong to historical conceptions of Marxism,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theory of Marxism should possess profound theoretical qualities, a rich fund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be good at textual criticism of history. Only in this wa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n be enriched and be better improved.
Key words: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oretical Quality; "Dissecting Trivial Matters under the Microscope"; Textual Criticism of History
作者简介:谢保成(1943-),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隋唐五代史、20世纪学术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6)02-0142-07
收稿日期:2015-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