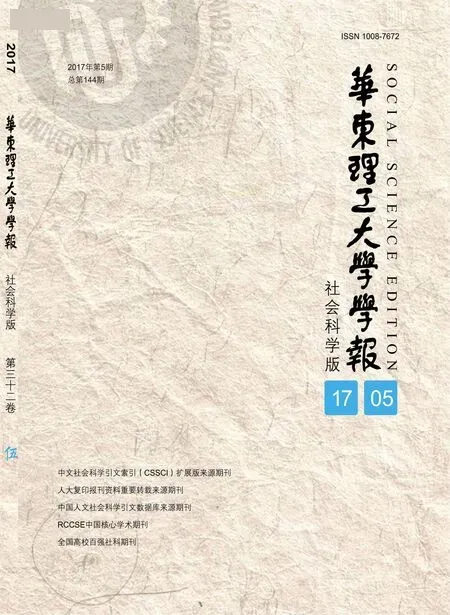历史与使命:从郡县国家到超级郡县国家*
刘炳辉
历史与使命:从郡县国家到超级郡县国家*
刘炳辉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讲师)
历史无法割裂,传统深植人心,治理体系尤其如此,因为人的社会行为主要依赖传统,而非创新。以郡县国家为核心特征的传统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与生命力,在近代以来百余年的内外冲击挑战下,浴火重生,全面升级,而并未如一些人所期待的那样全盘西化,拆了故宫建白宫。沧海横流,时代剧变,全球市场化带来全球大流动,中西方应对这一巨变时代时各自走上了不同的治理探索之路。中国对自身的传统有沿有革、大沿小革、支柱沿技术革,成绩斐然全球共睹。这其中的道理何在?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征程意味着什么?对人类在新时代寻求秩序的意义何在?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重新审视的重大命题。
一、历史并未远去:围绕郡县国家的三个问题
在《郡县国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传统与当代挑战》①曹锦清、刘炳辉:《郡县国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传统与当代挑战》,《东南学术》2016年第6期。(以下简称《郡县国家》)一文中,笔者从结构与制度的角度初步概括了中国在农业时代的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和特征,后蒙各方师友拨冗斧正,建议和意见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文中提出的郡县国家四大支柱(中央集权为核心导向、文官制度为中层支撑、乡土自治为基层设计、行政区划为技术保障)的依据和遴选标准是什么?为什么不是别的选项?二是当代中国是否还算是郡县国家治理体系?三是郡县国家的治理体系虽然在农业时代是有效的,在当代和未来是否依然有效,即具有合理性?
三个问题均十分中肯也很重要,是《郡县国家》一文中囿于篇幅并未展开的内容,这里略作回应和进一步阐释。
首先,四大支柱的选择视角是源于构成国家的四大要素。我们探讨的是国家治理体系,而非公司治理体系、全球治理体系等领域,所以必然紧紧围绕“国家”的核心要素来选取,而构成国家的四大基本要素一般认为至少是领土、人口、政府和文化。是否有领土构成了国家治理和公司治理等领域的重要区别,所以在四大支柱中特别强调了行政区划问题,即是这一视角的凸显,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巨型国家尤其如此。人口方面是从农业时代的静态社会结构治理方面提炼了乡土自治的特征。中国在传统社会中的政府组建与运行,以其先进的科举取士制度领先世界,是较为早熟的文官制度。而文化方面,中国历史上是内儒外法,核心取向在于维护大一统的家国天下结构,故而用中央集权的导向来概括,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一个提炼,也包含在政府特征中,当然这样的概括属于治理视角,纯从文化视角看有其局限,但并无根本的偏差。
其二,当代中国的治理体系和传统治理体系的关系。如果说两者完全一致,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但如果我们将这种纵向的历史比较转向横向的世界范围内的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的这套治理体系与欧洲、美国、印度、非洲和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差异更加巨大,而且彼此之间还非“量”的或多或少的区别,而是“质”上的根本思路的差别。中外的治理体系的差异显然远远大于中国纵向的自我对比的差异,如此我们会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当代治理体系与传统治理体系的关系。我们并未远离传统,郡县国家的治理体系基本结构得到了延续,尤其是在中央集权这一核心导向上尤为明显,但这套治理体系的能力与技术得到了全面的升级与强化。对于这套新体系,笔者从学术视角概括为超级郡县国家。超级郡县国家治理体系渊源有自,其核心特征与功能在于始终努力维持一个整合和团结的国家与社会结构状态。这种整合的状态对于绝大多数百姓从根本上和长远上而言是更有利的。而西方是一种高度分化分权的状态,这当然也是他们的地理历史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而成的,这种区别是两套治理体系的最核心差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版图广袤、人口繁多、内部差异巨大的历史古国而言,维持整合与团结是压倒一切的最高标准,否则动荡不止,或许对极个别人有利,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注定是悲剧。
其三,历史上有效的治理体系,是否今天和未来依然有效?这种提问背后其实往往还包含着一种价值判断,即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特征的传统治理体系是否还有其合理性?除非心存偏见,否则对于中国历史上郡县国家治理体系的成效一般不会有太大争议。但近代以来我们波折起伏的国家命运和奋斗史,让不少人困惑于何种治理体系更为“现代”?效法西方分权分化的治理体系是否更为“先进”?历史在行进中时,我们往往会当局者迷,蓦然回首才发现已经变了人间。超级郡县国家不是无本之木,我们在核心支柱并未改弦更张的情况下,已经离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在于近代百年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三大核心任务和挑战均从根本上支持了以中央集权为导向的超级郡县国家体系的建构。这三大核心任务和挑战分别是军事战争、工业革命和全球市场化。否则,将超级郡县国家体系的构建仅仅归结为个别人物的偶然选择和偏好,则是视野狭窄而肤浅无知的。中国共产党恰恰是自觉承担了改造升级传统治理体系,使之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不断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才取得和不断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并长期获得人民的认可和支持。这套治理体系的成效已经毋庸置疑,只是不同于西方的路径而长期被轻视和批判,我们过去经常显得理屈词穷在根本上是源于“四个自信”不足,而并非实际治理绩效低劣,这种理论上被动的局面正在迅速改观。
二、分化中的整合:超级郡县国家的使命
超级郡县国家相对于传统郡县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变化在于“政治科层化”,即将传统“君主官僚制”①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中只有“皇帝”一个人“讲政治”(相对于文官集团的“讲行政”)转变升级为一个庞大强有力的政党在科层化“讲政治”,进而实现了超级动员能力和效率,并且不断抑制和改造“理性化”的文官队伍成为讲政治的“干部队伍”。“讲政治”指的是自觉维护整体利益的高尚觉悟,“讲行政”指的是照章办事拘泥于局部事务的规则意识,当前中国共产党对其党员“讲政治”的最新全面表述就是“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市场化大潮中社会日益走向“分工”、“分化”(同时也意味着日益解体),一个历史悠久、版图广袤、区域差异巨大的大国如何保持团结和整合,并实现工业革命和民生富足?“超级郡县国家”治理体系是一种值得重视的选择和路径,其理论意义需要更多深入探讨。
在当代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以执政党的方式传承着传统郡县制“中央集权”这一灵魂,并据此呵护版图统一、抑制分裂势力,紧密联系群众维护社会团结,改造文官队伍的所谓“理性化”弊病。对现代和当代中国治理体系的分析观察,只有立足于以中国共产党这一政党组织为核心、以“党军关系”、“党政关系”和“党群关系”三大立柱为基本结构,才是一个基本全面的视角。考虑到和平年代“党军关系”一般是处于“隐态”并不显著,“党政关系”和“党群关系”就处于治理体系结构的核心位置。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党群关系”属于“纵向”(上下)上的问题,“党政关系”是如何更好地“以党领政”的“横向”(左右)上的问题,两者并行不悖,并不冲突。中国共产党必须同时处理好“党政关系”和“党群关系”两大任务,才能长期优良执政。而并非说强调处理“党群关系”时需要的“群众路线”,就可以取消或者直接解决了“党政关系”中的如何“以党领政”的难题。如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党群关系一直很好,但毛泽东却一直被“官僚问题”(走资派、“新阶级”等概念实质都是担心中共官僚群体异化)所困扰,就证明“组织领导干部”是独立于“组织领导群众”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演变(笔者这里没有使用“转型”,以避免线性发展观的局限)首先是渊源于其传统“郡县国家”体系,而且这种传承上千年的“超稳定”现象之核心内容是“先进”的,至少是有较大积极意义的,并非如一些人认为的带有“停滞”、“落后”等色彩。争议的焦点无非在于“集权”问题,如果我们撇开西方近代在此问题上刻意的意识形态化的贬损和污蔑,将集权与分权作为具体治理方式看待,会发现更多有益的内容,或者将其更换为“整合”与“分化”也具有同样的理论启发意义。
中共在现代中国治理体系中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就在于其“整合性”,抑制和克服各种内外部和主客观因素带来的“分化”和“解体”风险。其具体意义有三个层面:第一是处理地理空间上各个部分(军区、行政区、市场区域)的分权化,使其适度;第二是处理不同专业化部门之间的分权关系,使其适度;第三是处理科层组织的工具理性和政治要求的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使其适度。
在党军关系中(主要在战争年代)主要是第一方面,这是最为传统的。因此,也构成了当今“超级郡县国家”的母体。当然同时也有第二方面,尤其是随着军队系统的规模扩大、复杂化和专业化发展,会更加凸显。党指挥枪,在和平年代依然有价值。在党政关系中(主要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三方面功能都有。在党与经济的关系中(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主要是前两个方面。
进一步地总结,这也是现代世界中控制已经中央集权化的官僚体系的一种经验,甚至于可能具有普遍类型学的价值,而学术界却长期陷入“民主/专制”的西方意识形态二分法中无法自拔,遮蔽了我们的更客观清醒地认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意义的可能性。如何在一个“大分化”和“大流动”的时代保持“整合”(团结),依然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研究:聚焦人口流入型地区”(15ZDC02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