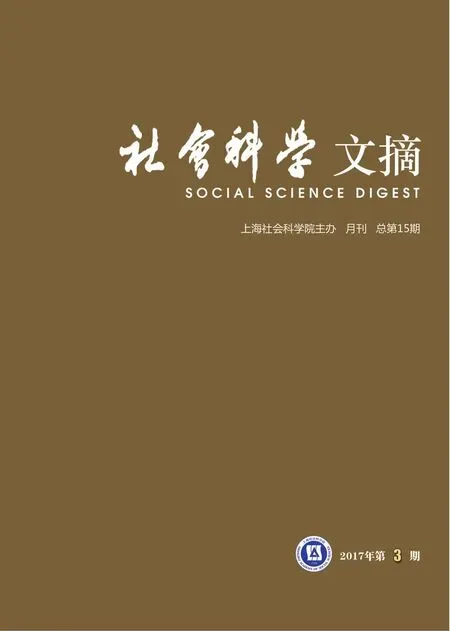文化心理结构、伦理变迁与乡村政治
——陈忠实笔下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秘史”
文/张勇
文化心理结构、伦理变迁与乡村政治
——陈忠实笔下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秘史”
文/张勇
陈忠实的小说创作,从《白鹿原》所展现的20世纪上半叶的乡村变迁,到21世纪初期几篇短篇小说中所揭示的农村现实,几乎完整记录了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秘史”。20世纪中国经历了帝制的崩溃、现代的创生、战争、革命以及此起彼伏的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个世纪。如何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事件和关系去把握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是极具挑战性的。《白鹿原》这部著作不仅具备了卢卡奇所说的“史诗的本质标志”——对“共同体的命运”而非“个人的命运”的关注,还运用了正确的历史方法,即在主要社会力量的关系之中考察历史的走向和共同体的命运,而非在这些关系之外建构另一种历史图景。
《白鹿原》展现了某种“民间历史”,但这种“民间历史”是被置于政治、社会的变迁之中呈现的,而非孤立甚至对立于政治、社会变迁的。因此,《白鹿原》更像是在“革命现实主义”延长线上所产生的杰作,它非但没有以“民间历史”置换“革命史”“政治史”,而且将“革命史”“政治史”当作了重要的表现内容。在陈忠实的其他小说中,乡村政治也是作家始终重点关注的对象。这在新时期以来浓厚的消解政治、拒斥政治的文学氛围中,是难能可贵的。布罗代尔曾引用埃德蒙·法拉尔的话说,“正是对大历史的恐惧扼杀了历史”。 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大概也存在着类似的“恐惧”,而《白鹿原》和陈忠实其他一些创作的价值正在于将“大历史”重新带回到文学的视野之中。
“文化心理结构”及其“剥离”
“文化心理结构”是陈忠实谈创作时最常提及的概念。这个概念最初由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它的内涵与之前更为常用的“民族性”“国民性”有较大重叠,不过,“文化心理结构”呈现为中性色彩,不像“民族性”尤其是“国民性”那样,在中国近代以来语境中被赋予了明显的贬义。以“文化心理结构”取代“国民性”,不仅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价值评判上的变化,同时也关涉到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的重新评价。
“文化心理结构”学说并未让陈忠实否定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它的启示性在于为作家提供了一个透视历史变迁的视角。“文化心理结构”的承载者通常是作为群体的“民族”,它与其说来自对于民族共性的实际观察,不如说源于某种理论预设,反过来又限制了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丰富性、复杂性的认知。陈忠实以“文化心理结构”来解释作为个体的人物及其差异是一种误用,却恰恰弥补了该学说可能带来的武断。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陈忠实没有循着“文化心理结构”走向“寻根文学”,他对个体“差异”的兴趣决定了他的落脚点在于“演变”——“民族的精神和心灵演变的秘史”。
首先,陈忠实关注的是人的多样性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作家甚至在一些短篇小说中,也试图勾勒人物的转变,如《失重》《轱辘子客》《两个朋友》等。其中有的篇目由于未能运用恰当的叙述结构或技巧,仍然按照时间顺序平铺直叙,不免给人以仓促之感,艺术上也算不上成功。陈忠实常常是以长篇小说的思维方式和结构形式来创作中短篇小说的。其次,陈忠实虽然像大多数作家一样,在批判现实的基础上构筑起自己的文学,但是未从根本上动摇过对于美好未来的信念。现实的问题不会上升到对于现代化途径优劣、对错的思考;对于历史,陈忠实的兴趣在于历史的具体形态,特别是能够与自身相联系的、具体化为先辈生活和心路历程的历史形态。在陈忠实看来,历史的实然便是历史的必然,历史上的错误不过是通向必然王国道路上的小波折,因此,历史的应然几乎不会作为问题进入作家的视野中。当作家系统地审视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道路时,他对历史必然性的认知更加被强化了。
陈忠实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以及当代现实的认识算不上深刻,反而显得有些正统甚至于“过时”。这类似于作家所坚持的现实主义、一定程度上还带有“革命现实主义”印记的创作方法,在新潮更迭、叙事技巧日新月异的80年代文坛所表现出的姿态。陈忠实绝非思想型的作家,也非先锋实验型的作家。他的作品不易被归入到某个具体的流派或创作类型之中,然而,悖论的是,当文学新潮声势浩大时,“保守”或“落伍”反而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
陈忠实自觉地“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去写人物”,最早可以追溯至中篇小说《蓝袍先生》。作家此时对“文化心理结构”的观察主要是负面的,接近于金观涛所说的“宗法一体化结构”。作家是从传统/现代的二元结构来审视“传统”的,当现代被赋予了正面价值时,“传统”便不可避免地带有了负面的品质。稍晚创作的《四妹子》基本上延续了这种思考。
“文化心理结构”常常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决定了农民在思想观念、情感上与旧事物之间的分离过程是漫长的。陈忠实从自己的经验中也领悟到这一过程的缓慢与痛苦,他称之为“剥离”。陈忠实详细记述了自己“剥离”对农村集体化的信仰的过程:1982年,当陈忠实作为农村干部指导农民落实中央的“分田到户”政策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的工作“正好和30年前柳青在终南山下的长安乡村所做的事构成一个反动”。直到这一年的秋天,当陈忠实亲身享受到“责任制”所带来的农业大丰收时,他才真正开始了对集体化的“剥离”。在此期间,陈忠实创作了短篇小说《霞光灿烂的早晨》,其中透露了作家对于“包产到户”政策的隐忧。一方面,作家看到了“单干”所激发出的潜在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作家也洞察到了“包产到户”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单干”的逻辑已经开始动摇农村的互助伦理。农村中新的现实问题迫使他从另一个维度上思考“文化心理结构”的嬗变,“剥离”因而演变成了“疏离”的问题。
“离乡”母题与乡村伦理的衰微
陈忠实几乎从不在城/乡二元对照的结构中观照乡村,从而也避免了在文明/野蛮或异化/自然的对立视野中将乡村简化为某种符号。他笔下的乡村既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也非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长期在乡村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使得作家很少在类型化的意义上去书写乡村。这决定了他笔下的乡村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尤其是知青文学中常见的农村形象的差别。如果说陈忠实笔下的乡村也体现为某种类型的话,那便是“根”或“本”。这里的“根”不同于“寻根文学”中的“根”,它是无需寻找的,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在陈忠实8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创作中,存在着一个与知青文学、“寻根文学”迥然不同的“离乡”母题:对精神上离“根”、忘“本”的批判或忏悔。如果把“根”“本”理解为乡村伦理、生活和做人准则的话,那么陈忠实大部分的作品都可以纳入到该母题之中。“离乡”母题显现了一种农民式的价值、道德观念。
“离乡”母题可以看作是对赵树理、柳青、王汶石等作家所开创的农村小说叙述模式的一种反题叙述。陈忠实延续了赵树理、柳青等作家对农村“新”“变”的关注,但是“新”“变”却不再是“好”的同义词。《康家小院》的前半部分很像是一个赵树理式的妇女翻身的故事,玉贤参加村里的冬学识字班,从杨老师那里了解了外面的世界;但是后半部分却演变为妇女翻身故事的反题,玉贤发现杨老师只是玩弄了自己,她带着忏悔重新回到了丈夫身边。“离乡—返乡”的情节模式取代了“传统—现代”的进步叙述模式。
从《蓝袍先生》到《白鹿原》,作家对“传统”的态度悄然发生了变化,呈现为更为客观和正面的评价。这种变化源于作家对乡村现实问题的观察。80年代中期以后,乡村社会在经历了最初的欣欣向荣之后,开始暴露出一些问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投机倒把、价格双轨制、脑体倒挂等中国社会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也在乡村表现出来。作家对这些问题都有所关注,创作了诸如《旅伴》《灯笼》《失重》《轱辘子客》等作品。即使是在这些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中,陈忠实也往往侧重于从心理或精神的层面去进行把握,作家最为关注的是乡村伦理及价值观念的变化。
正是道德丧失的现实,使得作家重新评估“传统”的价值。此时,即使是《蓝袍先生》中反复出现的“慎独”,也具有了积极意义。对乡村伦理的关注,让作家走向了“传统”并发现了其复杂性。《白鹿原》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其中尤以作为“仁义”化身的白嘉轩、朱先生等形象最为动人。在历史的洪流中,白嘉轩的“恒”与鹿子霖的“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朱先生也有着明确的充当人间“砥柱”的自我期许。这种对做人原则的坚守之所以赢得了读者的普遍共鸣,也需要置于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道德缺失的语境中来理解:通过这些人物,人们重温了某种已经变得久远和模糊的道德信念。作家对白嘉轩这个人物的偏爱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陈忠实在面对“传统”时又是足够清醒的,他没有单纯跌倒在“传统”这个怀抱中,同时从被压迫者、被侮辱者特别是女性的角度,看到了“传统”压抑性的一面。《白鹿原》道德态度的含蓄,也正是作家此时对“传统”的复杂态度的写照。
《白鹿原》之后,陈忠实很少再创作小说。进入21世纪之后,作家零星发表的几篇短篇小说仍然是在80年代中后期的框架中书写乡村。不过,乡村伦理每况愈下,形同消亡。这可能也是陈忠实很少再写小说(乡村)的一个原因。乡村伦理是乡村区别于都市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曾是陈忠实“离乡”母题创作的根基,作家确信这种伦理的存在及其优越性。中国的乡村社会的变迁,完成了从互惠、合作的道义伦理到理性的个人经济伦理的转变。随着乡村伦理的衰微,乡村伦理逐渐与都市伦理趋同,价值意义上的乡村实际上也就终结了。毫不奇怪的是,作家与此同时对故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令他“肃然敬仰”的人物发生了兴趣,写下了“三秦人物摹写”系列短篇《娃的心娃的胆》《一个人的生命体验》《李十三推磨》。然而,无论是中条山战役中的孙蔚如、作家柳青,还是嘉庆年间的剧作家李十三,都已成为历史,他们恰恰映照出了现实的匮乏与苍白。
乡村政治: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与出路
陈忠实对于乡村伦理的关注,使得他一直对乡村政治和乡村社会机制的变迁保持着敏感。与新时期许多作家着力于反思“文革”不同,陈忠实更为关注的是“四清运动”。相比于“文革”,“四清”运动对农村社会的冲击更深入、剧烈。就此而言,陈忠实准确地抓住了乡村政治悲剧的关键。在陈忠实的前期创作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塑造了一批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尤代表轶事》中的老安和尤志茂代表了陈忠实笔下农村基层干部的两种类型,前一类型还有如《猪的喜剧》中的韩主任、《乡村》中的葛队长等,都是不了解农村现实、上级政策教条式的执行者。后一类型则是从农村生活和劳动实践中自发产生的领袖,如《信任》中的罗坤、《乡村》中的泰来、《梆子老太》中的胡长海和胡振武等。乡村政治的悲剧源于前者对后者的粗暴打击,培植出了像“梆子老太”这样的政治怪胎,造成了国家权力与群众之间的裂隙。
在新的历史时期,“好干部”的界定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好干部”体现为对自己历史错误的正确认知和忏悔意识。《土地诗篇》《土地——母亲》都是写地方干部对土地、母亲、人民忏悔并得到宽恕的故事,寄寓了作家对于新的干群关系的期盼。其次,“好干部”应该有勇气通过自己的努力修正历史错误,继续带领群众生产、致富。在《反省篇》中,作家深入思考了“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地方干部职能转变的问题:干部可能会从“瞎指挥”的极端走向“不指挥”的极端,或者忙于自己致富,造成农村一盘散沙的局面,如小说中河东公社的情形那样。不幸的是,作家笔下的河东公社后来成为了中国乡村更为普遍的形态。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孤立、无序地劳动和竞争;基层干部对这种经济生产基本采取不作为甚至是为己谋利的态度。
《白鹿原》中忠实地记录了中国当代乡村的前史。白鹿原乡村的结构性变化始于“乡约”成了“官名”,官僚机构的膨胀不仅带来了赋税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它破坏了旧的乡村结构。随着国家权力向乡村的逐步渗透,原先由“乡约”和族长维续的乡村秩序让位于“乡约”“甲长”所代表的国家权力,乡村由德治、自治转向政治统治。在《白鹿原》中,“交农事件”是国家权力与乡土社会相遇的一个象征性时刻。“交农事件”之后,白鹿原上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乡约’的条文松驰了,村里竟然出现了赌窝”,二是保障所新组建了配备枪支的“民团”。二者之间并非没有关联,国家权力的强化与乡村社会自治力量的衰弱总是同时发生的。
杜赞奇曾借用吉尔茨的“内卷化”概念,以“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来描述“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及其现代化过程”。及至20世纪后半期,国家权力的扩张也未停止。集体化时代,“国家史无前例地渗透到农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地方制度和农民价值观失去了根基”,“村社准则、乡规、共享的观念,退出了公共话语空间,甚或不复存在”。 新时期以来,国家权力虽然不像之前那样将乡村社会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但是农村干部却迅速转向杜赞奇所说的“赢利性经纪”,成为乡村社会发展的新的阻碍因素。
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来看中国20世纪的变迁无疑是一个颇富启发性的视角,然而,它也潜存着将国家与社会对立看待的危险。最为极端的情形便是:否定国家所有的社会计划包括社会解放与革新的努力;以“传统”“自治”等名义,遮蔽或美化社会既有的问题。黄宗智认为,基于现代西方经验的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模式并不适合于考察中国的情形,中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而国家与社会又都参与其中”。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如帝国晚期、民国时期和当代,都曾发展出一些不同形式的“第三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协商性而非命令性的”。“第三领域”的历史经验也可以为解决当代中国农村社会问题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需要重视和发挥乡村社会中自发形成的地方精英的结构性作用。村庄作为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直接相遇的接触点,村庄干部应该是村庄中的精英,而非国家政权内卷化中最低的一个层级。各级地方干部也需要从官僚尤其是“赢利型经纪”的角色中转换过来,成为农民共同富裕道路上的带头人。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摘自《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