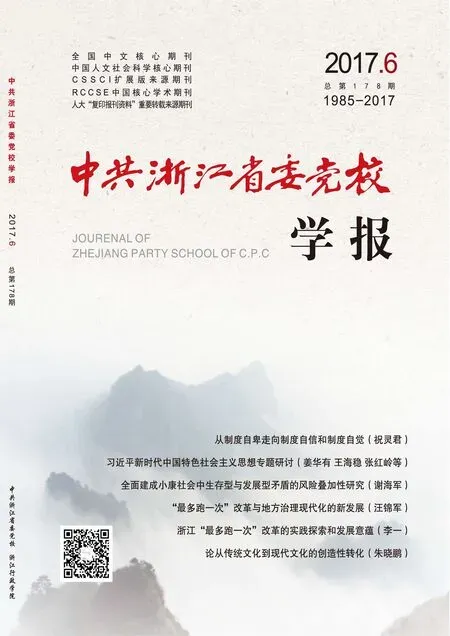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下的社会管理研究:一个反思
□ 肖扬东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下的社会管理研究:一个反思
□ 肖扬东
学界有关社会管理和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解大多采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依据“国家——社会”关系的侧重与偏爱,“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又可划分为国家中心视角、社会中心视角以及国家社会互动的视角。“国家——社会”分析框架虽略显宏大,但颇有可取之处。问题在于,上述研究通常都把“国家”和“社会”视作静止的单面体,这使得“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解释力受到影响;相反,把国家和社会当作变化的多面体来理解,“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社会管理研究中的解释力将大大增强。
国家;社会;社会管理;反思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管理”概念,把社会管理与经济调节、市场监督、公共服务等并列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第六部分以“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为题,专门论述社会管理问题,并提出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内涵丰富,涵括了教育和医疗的投入,环境保护,加强公共参与和公共服务,建立对灾害、事故、公共安全事件、社会矛盾冲突的快速反应机制等,被认为是“新社会主义社会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①Pieke,F.N.2012.“The Communist Party and Social Management in China.”China Information 26(2)(June 17):149-165.毫无疑问,“社会管理”的出现,既有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考量,更是新时期执政党的宏观布局和谋划,其目的旨在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新挑战,通过协调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关系,进而走向繁荣的新长征。②保罗·乌里奥:《走向繁荣的新长征》,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也因此,社会管理很快成为各级政府施政重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日益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能,社会发展支出在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也逐步增大。与此同时,围绕“社会管理”的讨论和研究也方兴未艾。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社会管理”被“社会治理”取代,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新词。“社会治理”被誉为“社会管理”的升级版,意味着一种新治理理念的登场,此后,“社会治理”迎来新的研究热潮。
在笔者看来,深入理解“社会治理”的内涵,不是放弃“社会管理”的研讨,恰恰是建立在对“社会管理”深入检视的基础之上。本文旨在对此前的“社会管理”研究进行一个大致梳理。本文认为,学界有关社会管理的研究大多采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这种研究视域虽略显宏大,但颇有可取之处。问题在于,就社会管理研究而言,无论是国家中心视角,还是社会中心视角,抑或是国家社会互动视角,它们通常都把“国家”和“社会”视作一成不变的固定“实体”,认为“国家”和“社会”是既定的,有着固定的边界,是一个统一的行动者。本文认为,“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依然是“社会管理”研究中极为便捷和有效的研究路径,但要彰显并增强其解释力,就必须把“国家”和“社会”当作变化的多面体来理解。
一、社会管理研究:国家中心/社会中心视角
近现代以来,国家一直是人类寻求安全,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的重要社会建制。巨兽“利维坦”尽管不免祸及人类,但也好过重陷无政府式的自然状态。一旦如此,人们复将彼此为敌,“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5页。。因此,管控和规训社会历来是国家的重要职能,这一点,即便是所谓“最小”国家或“守夜人”国家也不例外。根据米格达尔的看法,国家职能可划分为决定性的渗透社会、管制社会关系、汲取资源以及分配处置资源。*米格达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认为国家权力包含专制权力与基础权力。专制权力是一种专断式力量,指国家执政者可不经由社会同意而遂行其意志,基础权力指的是国家贯穿渗透社会的力量,其透过组织的建构与政策制定去协调人民的生活。*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传统上,中国一直是家长式社会,崇尚民本主义,强调国家统一和秩序。与西方相比,除了偶尔来自游牧民族和半游牧民族的挑战,中华帝国面临的主要是内部挑战,即内部瓦解的危险。因此,维持和重建王朝秩序,加强对地方豪强和农民的控制成为了中华帝国的首要任务。*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但中国的王朝秩序或社会秩序往往是至上而下施加的,这种传统不仅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改变,反而经常得到进一步强化。*郑永年:《危机或重生——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命运》,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页。
“社会管理”问题的提出原本为应对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和紧张关系。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社会结构失衡,社会冲突加剧,群体性事件频发。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93年到2009年,全国的社会群体突发事件从每年的8709宗增加到接近9万宗,涉及人数也从70万人增加到300多万人。*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泱泱中国某种意义上正端坐于一个火山口上,随时面临火山喷发的威胁。2002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最早提出“社会管理”问题。报告强调指出,为改进社会管理,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应“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显而易见,“社会管理”的提出明显有“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是一种“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范式”。作为社会控制的社会管理,政府对社会矛盾进行打压,崇尚“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社会管理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维稳”的代名词。*岳经纶、邓智平:《论理解社会管理的五种路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不少人注意到,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以“维稳”的名义把某些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固定化、模式化,严重制约了社会力量积极性的发挥。事实上,尽管目前我国在形式上已基本建立起了从调解、仲裁、复议、诉讼到信访、上访等一整套的纠纷解决渠道和社会管理模式,但一些地方政府依旧存在对自身定位不准,对社会主体作用认识不足的弊病,进而在实行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上存在许多误区。一些地方在社会管理中仍然存在简单、粗暴管理的现象,社会管理主要采取单一行政干预手段,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的方法。*龚维斌:《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的社会管理新格局》,《行政管理改革》,2010年第4期。由此可见,在当下中国,“社会管理”一词与社会独立领域的出现与演进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而是社会结构失衡社会矛盾激增的产物。也因此,社会管理体系的创新必然缩小为甚至降格为以强制性权力积极地干预具有独立性的社会领域,“社会管理体系的创新只不过是政治体系维护社会稳定意图和行动的另一表达。”*孔繁斌:《中国社会管理模式重构的批判性诠释——以服务行政理论为视角》,《行政论坛》,2012年第1期。社会管理也许会形成多元主体共治的格局,但最终依然是一个国家统合主义体制。*Litao Zhao,“From Community Management to Social Management: China’s New Approaches to Managing social Complexity”,Conference Paper,October 25,2012,Institute for East Asia,Singapore.转引自岳经纶、邓智平:《论理解社会管理的五种路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社会管理和社会管理创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是社会中心视角,社会中心视角强调并凸显社会和社会力量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值得指出的是,社会中心视角受公民社会理论的影响极深。在一些学者的笔下,公民社会几乎就是社会的化身。众所周知,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有过一场公民社会*90年代的公民社会大讨论中,学者对英文civil society的翻译并不统一,为方便起见,本文统一采用“公民社会”的译名。的大讨论,在这次大讨论中,尽管有学者如邓正来曾经提出过公民社会和国家的良性互动说,但在大多数学者笔下,这一时期的公民社会论述多体现出明显的社会中心主义倾向,侧重强调理想中的公民社会的特征、地位和作用,并从公民社会角度研究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应然关系。*何增科:“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话语体系变迁与政策调整”,俞可平、[德]托马斯·海贝勒、[德]安晓波主编:《中共的治理与适应》,中共中央编译局2015年版,第247-248页。诚如何包钢所言,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公民社会研究最重要的目的就在于寻找一个规范的民主理论和国家理论*Baogang He,The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ST. MARTIN’S PRESS, INC., p57.,作为国家的对立面,公民社会被认为是对抗和制衡国家的重要力量。
如果说国家中心强调的是国家(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规管作用,那么社会中心则认为社会管理的目标和出发点在于“社会的自主管理”*郭苏建:《社会管理的根本目标和出发点》,《浙江日报》,2011年1月17日,第014版。,期待“社会管理回归社会”*蒋德海:《政府退出让社会管理回归社会》,《人民政协报》,2012年11月26日,第B01版。,鼓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应由“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逐步培育社会的自立、自主和自治*周红云:《社会管理创新实质上是一场政府改革》,《理论参考》,2012年第1期。,转变社会管理理念,培育各类公民社会组织,提高社会管理的公众参与*周红云:《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现状、原因与方向》,《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指出,当下中国的社会重建和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尊重社会自组织、实现社会自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尊重社会自组织,实现社会自治》,《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28日,第003版。。周雪光坦言,中国的治理机制需要随着社会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政府的当务之急是“适应”而非“统领”社会发展,为此应鼓励并推动新的组织形式的发展*周雪光:《社会建设之我见:趋势、挑战与契机》,《社会》,2013年第3期。。孙立平认为,从传统的消极社会管理走向积极社会管理,其目标是建设一个好的社会,为此,需要健全社会机制,推动社会组织系统的发育,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孙立平:《走向积极的社会管理》,《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总之,社会管理的最终目的在于服务社会,而非压制社会、压制人民。因此,社会管理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国家(执政党和政府)管理社会,更不能理解为国家单向控制、统制社会。“社会管理的主体首要的应当是社会自己,社会应当享有充分的社会自治权力和民主参与和监督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权利。”*郭道晖:《我看社会管理的创新方向》,《炎黄春秋》,2012年第1期。
二、社会管理研究:国家—社会互动的视角
从上可见,在社会管理研究中,无论国家中心视角,还是社会中心视角,他们通常秉持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或强调国家(政府)对社会的单向规管,淡化甚至忽视社会组织或社会力量的作用;或强调社会的自主或社会本位,降低或者忽视国家(政府)的作用。应该说,在社会管理研究中,国家中心视角和社会中心视角皆有可取之处,不足的是,这两个研究视角忽视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为此,一些学者提出应从国家社会互动的视角来看待社会管理和社会管理创新。
国家社会互动的构想并非新创,而是受到西方理论如治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等理论的影响。“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作为传统的由政府对社会公共事物实行单一向度统治和管理的修正和补充,“治理”理论主张“多元共治”,推崇基于合作网络权威的管理机制,“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俞可平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席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则提出“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主张政府转换其在公共管理和服务中的角色——由“划桨”变为“掌舵”,倡导“公私合作”。*戴维·奥斯本、彼得·普拉斯特里克:《再造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版;(美)珍妮·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超越国家—社会二分的视角,西方学者纷纷致力于探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并创设了一系列概念来描述国家—社会互动的重要形态,比如“法团主义”(Corporatism)、“社会中的国家”(State in Society),“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以及“国家与社会共治”(State-Society Synergy)等概念。西方概念的引入为中国学者思考国家—社会关系提供了重要工具,也激发了他们的灵感,促使他们根据中国更为复杂的国家—社会关系现状,提出一些新的概念来描述中国国家—社会的互动关系,比如“与国家协商”(negotiating the state)、“分类控制”、“利益契合”*郁建兴、观爽:《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进展》,《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2期。以及从“双向嵌入”到“双向赋权”等*纪莺莺:《从“双向嵌入”到“双向赋权”:以N市社区社会组织为例——兼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浙江学刊》,2017年第1期。。
就社会管理研究而言,虽然学者们并未直接援引上述概念和话语,但仔细检视他们繁复多样的表述可知,其基本内涵和上述理论如出一辙。比如,唐文玉指出,当前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管理创新绝不是要挑战和质疑国家的主导作用,其要点在于使社会管理更具“柔性”。国家应通过进一步诉诸合法性的方式来管理社会,加强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协商与沟通,建构一种国家主导的、规范有序的“双轨政治”。“双轨政治”旨在“强调国家和社会之间建设性关系的可能,主张国家与社会协同发展、相互增权和互相促进,以形成一个国家能力强大、社会富有活力的新格局。”*唐文玉:《当前中国社会管理向何处去——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思想战线》,2012年第1期。陶建钟提出一种“国家主导社会自主”的复合治理模式,该模式承认国家在社会管理中的主导作用的同时,强调社会自主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一方面国家或政府仍保持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制度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社会作为一种相对自主力量的存在,承担(国家)政府退场后形成的职能空缺,国家和社会在职能上有所偏差并相互依赖。*陶建钟:《复合治理下的国家主导与社会自主——社会管理及其制度创新》,《浙江学刊》,2014年第1期。周红云认为我国社会管理的基本理念应该是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治理。社会管理既包括“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所展开的社会管理,也包括“作为非国家政府机构”的社会管理。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1)在政府逐渐退出的前提下,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确立政府在推进社会事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2)在引导公民社会独立自主的过程中,政府为公民社会的独立自主发展提供制度环境,为公民参政和实现权利创造条件,积极引导、组织和支持公民参政和公民社会的自治。在上述前提下,社会管理由“政府本位”逐渐走向“社会本位”,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让位于调控、引导和服务于社会,政府对社会的统治让位于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治理。*周红云:《理解社会管理与社会管理体制:一个角度和框架》,《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3期。吕志奎也认为社会管理应该是一种协作性社会管理,指出“协作性社会管理主张共享权力结构——社会管理秩序是‘合作生产’,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公众共同努力,发挥比较优势,促进资源整合”*吕志奎:《中国社会管理创兴的战略思考》,《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6期。。杨华锋则认为协同治理理论可以消除政府主导和社会自治的两极对立,其优势在于“行政者系统的开放性、行动策略组合多样性、文化制度结构的适应性、网络化组织的创新性以及社会协同机制的有效性”*杨华锋:《协同治理: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策略的比较优势》,《领导科学》,2012年第6期。。
“双轨政治”、“国家主导社会自主”的复合治理模式、国家和社会的协作性社会管理或协同治理等,这些研究不再一味强调国家或社会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而是认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演进,中国的社会管理需要国家和社会的沟通协作,需要国家社会携手共进。不过,由于缺少相应的案例分析与验证,上述论文多停留于理论作业,略显空泛。值得注意的是,郁建兴、关爽2014年发表《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进展》,基于中国“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整体态势的辨认,他们提出“国家主导下的社会治理”概念,以广州、深圳社会组织的制度改革,上海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为例,深入阐述了当前我国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实际内涵:在走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国家仍然是主导者,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并因此奠定了社会发展的制度基础;但社会治理的动力机制来源于社会自身,社会建设的推进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绩效。*郁建兴、观爽:《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进展》,《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2期。
三、旧瓶装新酒:重思社会管理研究中的“国家”与“社会”
国家中心/社会中心也好,国家社会互动也罢,概括起来,中国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管理创新实际上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因应当前社会分化的客观现实,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横向秩序协调机制;其次是如何在纵向秩序占据优势地位的当下中国建立一种纵横结合的秩序整合新框架。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在于寻求横向秩序和纵向秩序的有效连接方式,在激发社会内在活力的同时强化纵向秩序的合法性,实现有效的社会整合。*李友梅:《中国社会管理新格局下遭遇的问题——一种基于中观机制分析的视角》,《学术月刊》,2012年第7期。不过,笔者注意到,在社会管理和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中,无论是国家中心/社会中心视角,还是国家社会互动的视角,它们通常都把“国家”和“社会”视作一个静止的单面体,这使得在运用“国家——社会”框架研究社会管理时产生了不少问题。因此,如果我们依然坚持运用“国家——社会”框架来研究社会管理,我们首先必须重新思考和审视“国家”“社会”这两个范畴。换句话说,在社会管理研究中,我们所使用的思考框架也许是旧的,但是我们必须在其中注入新的内容。
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国家一度威力无边,挤压甚至吞噬社会,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惧怕这个巨灵式的“利维坦”,嫌恶“一元层级式”的政治组织形式;加上中西学人对“国家”的左右夹攻,“国家”神话遭到消解,“国家”在中文学界经常成为指责和批判的对象。于国家力量膨胀、国家主义盛行的当下中国而言*许纪霖:《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批判》,《天益学术》许纪霖专栏,2014年3月4日。,对“国家”印象不佳乃至激烈讨伐自然有其必要,不过,在我们以“国家”作为标靶之前,我们或许有必要反思一下:我们批判的是哪一个“国家”,或者说我们批判的是国家的哪个面向?
通常,批判者大多把国家视为整体,当成一个统一的行动者,很少有人注意到,国家其实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不同的组成部分,有不同的面向,以不同的方式与社会展开互动。诚如米格达尔所指出的,“现代国家由大量的部门和机构组成,这些部门和机构具有不同的职能和利益,从不同的方向牵引他们的力量——地方的利益诉求、利益集团的杠杆作用、国际上的压力——十分巨大”*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相互构成》,李杨、郭一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页。。在一篇关于中国农村的政治信任的论文中,李连江发现,单纯如农民也知道中国国家*对于很多普通人而言,政府就是他们眼中的国家。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把国家分解为值得信任的中央和不值得信任的基层政府,或更笼统地区分为值得信任的“上级”或“上面”和不值得信任的“下级”或“下面”。*李连江:“中国农村的政治信任”,熊景明、关信基编:《中外学者论21世纪初的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央/基层政府,上级/上面、下级/下面的划分固然失之简单,但朴素地传达出有区别地认识和对待中国“国家”的必要。华裔学者高柏别出心裁地指出,在过去30年面对全球化挑战的过程中,中国国家已经演变为一个具有六面特征的魔方国家:即权威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国家、发展型国家、掠夺型国家、改进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统合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国家告诉我们为什么过去30年中国经济比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更具发展动力;发展型国家揭示了中国在争取外国直接投资以及经济结构升级上优势的来源;改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国家拥有更多资源支持其政策目标的理解;权威主义国家、掠夺型国家以及统合主义国家则使我们明白,为何中国在经济高歌猛进的同时,没有跟随第三波民主化的政治潮流,很好地保持了政权的稳固,确保了社会的稳定,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高柏:《魔方国家:当代中国政治变迁的重新思考》,共识网,2014年3月4日。可以说,魔方国家颠覆了传统的把中国国家作为一个单一的内部一致的行动者的认知,清晰地呈现出一个混合及多面体的国家形象。
社会的孱弱和先天不足在中国由来已久,保卫社会因此成为迫切的历史任务*郑永年:《保卫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弱小者历来是同情的对象,与国家遭遇的敌视相比,处于夹缝中和边缘化的社会自然成为了关爱和呵护的对象。再加上公民社会理论、治理理论、新公共管理运动等西方话语的连番冲击,我们已经习惯于把社会视为“好的”、“善的”,是需要珍惜和培育的事物。赞扬者似乎很少追问:社会有没有可能也包含“不好的”、“坏的”东西;在对“社会”一片褒扬叫好的情形下,是否有必要对“社会”本身进行去魅和反思?
传统中国,“社会”为“社”“会”之合称,通常指祭祀土地神为中心的地区性团体。*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明代以降,“社会”一词具有志趣相同者结合而成组织的意思,其意义与西方大致接近。新文化运动前,“社会”包含三重含义:一是泛指人类生活其中的一般组织;二是按照某种目的结成联盟(自行组织起来),有时也指公共空间(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必定是个人和国家之外的领域);三是社会分层。新文化运动后,绅士阶层逐渐退出中国政治舞台,最初以他们为主体的政治社团也日趋萎缩,随着公共空间的消失,“社会”含义逐渐窄化,日趋抽象和空洞。由于公共空间和人自行组织过程从“社会”的抽离,“社会”作为人类组织的总称成为了一种空洞抽象的存在。*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影响所及,此后学者笔下的“社会”逐渐失却其丰富性,成了空洞无物的存在,社会也俨然成为一个整体,有共同的意志、共同的愿望,是可以理性控制的人格化整体。他们忘记了,“真正有助益于社会概念的东西,并不是经由强行设定绝对的权威或领导而达致的,甚至也不是由趋向于一种共同目标的共同努力构成的,而毋宁是由我们所有的人对这样一个过程所做的贡献总和构成的——这个过程要比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伟大,因为经由这个过程,一些新鲜事物和一些无法预见的事物会不断涌现。”*“什么是社会的?——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冯·哈耶克:《民主向何处去?——哈耶克政治学、法学论文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2页。在哈耶克看来,与国家的刻意组织不同,社会是一种自生自发的东西,它缓慢自由地成长,因而无法理性地加以建构。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把整体式的社会当作同等逻辑加以批判,倡导一种差异逻辑,“同等的逻辑是把政治空间简单化的一种逻辑,而差异的逻辑则是把它扩充和增加它的复杂性的一种逻辑”*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的战略》,陈璋津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74页。拉克劳和墨菲指出,由于统筹社会差异的原则与客观性并不存在,社会无法成为一个完满/客观的社会,社会型构与认同无法以任何超验性或化约性的范畴作为其源头。因此,社会必然是一个多重决定的空间,而非一个客观的存在。*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的战略》,陈璋津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珊坦·慕孚(Chantal Mouffe):《民主的吊诡》,林淑芬译,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5版。显然,无论是哈耶克的自生自发说,还是拉克劳和墨菲*本文采借大陆学者的译名,未采用台湾学者的译名。所说的社会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们都意在表明社会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多面体,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单面体。
以图示的方式,我们可以简单地作如下总结:社会管理研究诉诸的“国家——社会”框架,国家/社会被视作一个光滑的、没有裂缝的圆体,是一个单一的行动者,各自以一体化的方式与对方进行互动(图1)。相反,本文认为国家和社会应该是一个多面体,它们各自都布满裂缝,并以多样化的方式展开互动(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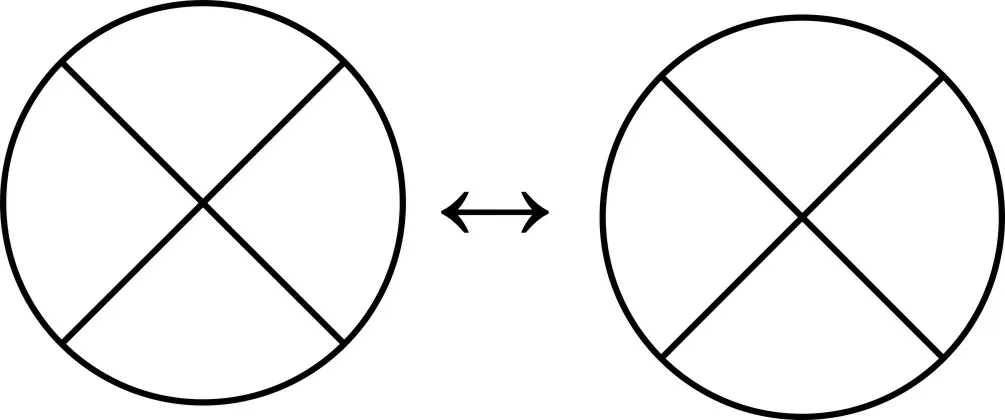
图1 国家/社会是一个单面体,以统一的行动者与对方进行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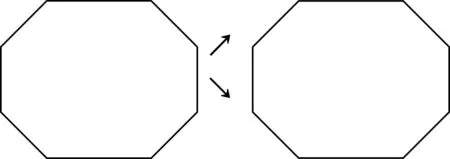
图2 国家/社会是一个多面体,以多样化的方式进行互动
结 语
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建国初期中国一度被视为全能主义国家,中国社会也被认为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国家/社会俨然是不可分割的总体,具有统一的意志。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家结构日趋复杂,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国家转型和重建的过程,国家力量的退出、加强和重构交织在一起,图景纷繁芜杂*刘鹏:《三十年来海外学者视野下的当代中国国家性及其争论述评》,《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国家结构充满了冲突和矛盾,中国国家成为了一个多面体国家*Yanfei Sun and Dingxin Zhao,‘Multifaceted State and Fragmented Society:Dynamics of Enviromental Movement in China’.Edited by Dali Yang,Discontented Miracle:Growth,Conflict,and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s in China,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Pte.Ltd, 2007,P115。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逐渐由总体性社会演变为一个分化性社会。改革开放前,国家社会处于同构状态,资源和权力高度集中,国家具有很强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但国家结构僵硬,反应迟钝;社会的组织类型和方式简单划一,几乎都以相同的模式建构按统一的方式运行。改革开放后,社会逐渐挣脱国家的束缚,有了更多的流动资源,多种利益主体和权力主体得到发育,各种社团组织开始出现,一个充满活力的独立的社会空间开始逐步浮出水面。*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出现新的变化,由分化性社会演变为“断裂社会”。断裂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在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社会旧秩序面临解体,社会信任缺失,社会矛盾和对抗激增,新的社会和秩序很大程度上以强力和不公正为特征。*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概念原本抽象,“所指”与“能指”之间总是充满张力。更何况,一段时间以来,在有关国家和社会的认知上,国内学界受“全能国家”和“总体社会”的支配,因而不免把“国家”和“社会”当成一个单一的行动者。在这种政治想象的支配下,“国家”和“社会”所指变得单薄,失去了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次,“国家——社会”框架所涉理论多为西方舶来品,简单地运用于中国的社会管理研究不免“淮橘为枳”,造成洋理论的“水土不服”。因此,“国家——社会”框架下的社会管理研究,无论国家中心/社会中心,还是国家社会互动意义上的论述大多为一种理论演绎,侧重“应然”和价值层面,与当下中国实践联系甚少,无法厘清现实困境背后的复杂机理*李友梅:《中国社会管理新格局下遭遇的问题——一种基于中观机制分析的视角》,《学术月刊》2012年第7期。。某种意义上,这些表述并没有超出官方有关社会管理模式“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论述,更多地只是其进一步展开和引申而已。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就社会管理研究而言,社会管理包含社会的“被”管理,也即被政府管理,同时也包含社会的自我管理,也即社会自己管理自己,无论就主体还是客体而言,国家和社会都是其中的要角,需要注意的是,在运用“国家——社会”的理论框架展开社会管理分析和研究时,我们必须把“国家”和“社会”看成动态的多面体,立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丰富充实对中国“国家”和“社会”的理解。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停留于纯理论层次上反复申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此抽象地演绎社会管理研究,还不如通过扎实的调研,基于具体的个案研究来推进和充实当下中国的社会管理研究。*学界有关社会管理创新的典型案例研究,参阅周红云主编:《社会管理创新》,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
(责任编辑:徐东涛)
C916
A
1007-9092(2017)06-0044-008
2017-08-07
肖扬东,肇庆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制度化研究”(项目号:138ZD040)、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进展”(项目号:GD15CZX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