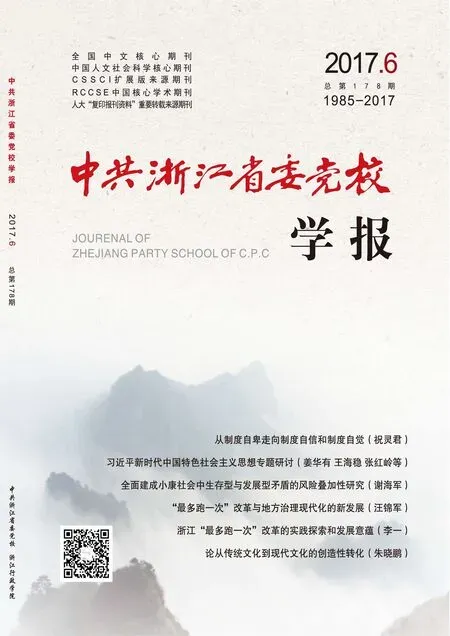代表制与民主:理论逻辑与历史实践的优先序之争
□ 冉 昊
代表制与民主:理论逻辑与历史实践的优先序之争
□ 冉 昊
基于对代表制和民主关系的最新理解,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挖掘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通过考察代表制的起源问题,并明确界定代表制、代议制政府和民主等几个易混淆的概念,我们发现在代议制民主过程中,“民主”不应当放在优先的位置,因为民主是否能够充分发展往往要受到代表制的局限;相反,“代表制”应当优先于“民主”——这不仅仅是因为代表制左右了民主发展的进程,还因为从内在逻辑上说代表制可能是包含了民主这个特殊矛盾的普遍性矛盾。基于此,我们进一步考察民主和代表制在我国的实践形式。民主在我国的实践体现为组织方式上的民主集中制,和实现形式上的基层民主、协商民主和党内民主。代表制在我国的实践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党代表大会制度。通过梳理各自脉络我们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中国特色代表制之间,各有逻辑线索,并且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太能对中国特色代表制产生影响;相反,中国特色代表制却能影响、规约甚至某种程度上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这种逻辑关系,与西方代表制和民主之间的逻辑关系的相似之处,对于如何通过排列代表制和民主的改革顺序,以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代表制;民主;代议制民主
围绕代表制和民主之间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不少。但是关于代表和民主之间的争论,却并未随着研究的深入获得更为一致的意见。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厘清代表和民主关系的本源。虽然这个做法的初衷是为了探究二者的本质关系,但我们却不经意从中获得了新的发现。
一、关 系
人们往往认为代表制和民主是一回事,于是才会有“代议制民主”一说。但实际上,代表制和民主,无论是从起源、发展过程还是表现形式,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通过对近四十年来关于代表理论的文献的整理和分析,以及对规范性研究、经验模型研究和经验研究的三个新发展进行的归纳,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呈现出代表和民主之间的关系(见表1)。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Manin,B.,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1997.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②Pitkin,Hanna Fenichel,1972.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③Voegelin,Eric,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Vol. 5,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0.
④关于古希腊时期就存在代表制之说,亦有国内学者认为,认为在古希腊时期代表制和民主就有关联,不过其分析并不同于曼宁,因为曼宁所强调的只是古希腊时期有代表制,但和古典民主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参见蔡定剑: 《中国人大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年版,第154 页。
⑤Miller,Warren E.,and Stokes,Donald E.,Constituency Influence in Congres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7 ( March 1963) : 45-46.
⑥Achen,Christopher H.,Measuring Representation: Perils of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21,No. 4.( Nov.,1977) ,pp.805-815.
⑦Andewed,Rudy B.,Beyond Representativeness? Trends in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European Review,Vol.11,No.2,147-161( 2003) .
⑧Mansbridge,Jane J.,Living with Conflict: Representation in the Theory of Adversary Democracy Ethics,Vol.91,No.3,Special Issue: Symposium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presentation ( Apr.,1981) ,pp.466-476.
⑨Rehfeld,Andrew,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Journal of Politics,68,no.1,2006,February: 1-21.
可见,代表制和民主是两个概念,或者说是两个脉络。弄清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这是研究代表和民主之关系的前定条件。对一个事物的结构性研究,与对不同事物的关联性研究,在研究思路上会大相径庭。因而,明确了这个前定条件,即对代表制和民主之关系的研究属于对不同事物的关联性研究,对深化研究的径路选择非常重要。
进一步,我们要搞清代表制和民主发生关联的时间。通过表1我们可以发现,代表制和民主之关联在时间上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曼宁(Mannin)援引麦迪逊的观点,认为代表制是古典民主时期就有的形态,并且是一种不同于民主的更高级的政治系统。但他并未明确指出代表制和民主在哪个时期发生了关联。他认为,代议制政府不是作为一种间接民主的形式,而是一种建立在不同于民主形式的政治系统。也就是说,代表制有自己的脉络,和民主不是一个脉络,所以更不是间接民主的表现形式;相反,民主倒是构成代议制政府特征的一个方面。比如麦迪逊(Madison)和西士哀(Sieyes)就持有这样的观点。
而国内相关研究认为,在古希腊时期,代表制就和民主有关联,原因在于“二十岁以上的男子是每个妇女、小孩和奴隶的代表”。*蔡定剑:《中国人大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页。
然而,并不是说甲代表乙就是代表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县太爷和天子就构成代表制关系,律师和原被告就构成代表制关系了。这显然十分荒谬。那到底何谓代表制?
政治学意义上的代表制,应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代表至少在名义上是代表其所在地域的公共利益的。之所以是“名义上”,在于在代表制发展史上本来就存在“委任与独立”之争,即代表的角色到底是其所在地域的“传话筒”还是能发出独立且公正的声音。二是代表的职责是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这里指的是参与决策,大家共同商议,而非一个人拍板,否则,秦时的县令和汉时的刺史也可以称作代表了。据此,所谓古希腊时期代表制和民主就有关联的说法并不能成立,因为二十岁以上的男子只是其家庭的代表,而且代表的更多的是私人利益。这里应当注意的是,代表制并不意味着选举——代表本来就有“委任代表”和“选举代表”之分。*伯奇:《代表——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朱坚章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出版公司,“民国”六十七年版,第131页。皮特金(Pitkin)之说更接近于此,即古希腊只有民主而无代表制。
一般认为代表制起源于英格兰,具体说是起源于中世纪的教会和国王召集的议事会。*参见王绍光:《民主四讲》,三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但按照以上关于代表制的表述,具有代表制特点的代表形式在此之前已经形成。故而,代表制之起源似乎可以前推。
早在公元五世纪的罗马帝国时期,陆续有一些城镇被并入罗马。这些城镇,“其政治合并是完全的;它们的居民和罗马人一样享有在罗马的投票权”,*基佐:《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张清津、袁淑娟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页。这些城镇的公民可以“赶赴罗马去到大会投票,既可能因为法律,也可能因为行政长官的职位”。*基佐:《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张清津、袁淑娟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页。这些被兼并的城镇的公民,由于其特殊身份或法律赋予,可以代表该城镇到罗马投票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这大概可以作为代表制的起源了。
此后,代表制在欧洲进一步萌芽。13-16世纪,代表制的形成促进了国家统一,促成了统治权集中的君主制度进一步完善和流行,但反过来,君主又不容许代表制造成权力的分散。于是代表制形式的尝试在专制君主的压制下逐渐式微。只有英格兰的萌芽保存下来。即便是关于英格兰代表制的发展,也存争议。
有学者认为英国代表制起源于1264年,彼时英国议会首次召开。“大封建主西门·孟福伯爵战胜了国王,上台摄政。他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征收赋税,召开了一次由贵族、僧侣、骑士和市民代表参加的会议。”*王沪宁:《国家主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然而,我们可以在更早的时代发现英国的代表制形成:
1214年,当心怀不满的贵族准备革命时,约翰*“无地王”约翰,英格兰国王,1199年到1216年在位。亨利二世和阿基坦的埃莉诺的第四个儿子。由于疆土大部分被分配给其兄,自己几乎没有获得什么,因此被称为“无地王”。参见基佐:《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张清津、袁淑娟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页。在牛津召开了一个全体大会。国王下发文书命令郡长为大会提供一定数量的武装骑士;而另一份文书则命令贵族的随从出席牛津大会时不能带武器,此外还命令郡长从每个郡派遣四个优秀的骑士到牛津,“以与我们一起研究国家事务”。
这是第一次看到骑士被选为议会议员,也就是说,承认某些个人可以代表大家出席大会。*基佐:《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张清津、袁淑娟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7页。
可见,上述到此为止关于代表制的叙述中,民主并没有与之关联。如皮特金所言,随着近代民主因对神权假设的挑战而兴起,代表制本身也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逐步制度化,为了适应近代社会人口多国土广的要求,代表制就成为了实践近代民主的一种工具。这也是民主和代表关联的开始。因此,代表制和民主的关联形成了代议制政府,换言之,代议制政府正是代表制和民主发生关联的表现形式,而间接民主其实是代议制政府的最显著特征,而间接民主和代表制本身并无直接关系(见图1)。

图1 代表制、代议制政府和民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以上厘清了代表制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代表制的起源问题,并就代表制、代议制政府,以及间接民主几个关键性概念的逻辑关系进行了辨析。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面对代表制和民主这两个原本毫无关联的东西,我们应如何进行偏好排序?
二、为什么不是民主优先
自从汉密尔顿第一次把“代议”和“民主”合并使用之后,*据有学者研究,汉密尔顿大概在1773年首先使用“代议民主”一词。参见王绍光:《民主四讲》,三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代议制民主”这个概念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而变得越来越流行。这一用法的弊病有二:一是阴差阳错地把代表制和民主联系起来,让人们误以为代表制就是民主的一种形式。然而,就连汉密尔顿自己都从来没有认为民主和代表制构成属种关系。他把“代议民主的体制称作共和政体,两者都与原来意义上的民主没有多大关系”。*王绍光:《民主四讲》,三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二是不自觉地将代表制纳入民主的脉络中进行思考,以致一提及代表制,人们就会从民主发展史的角度来思考代表制,这样便局限了代表制的理论发展。
既然代表制和民主本不同源,则代表制既可以发展民主,也可以取代民主。最直接的例证是两院制的形成和发展。目前所知最早的两院形式始于英国,具体时间仍有争议,但大致时间范围是可以确定的,即十四世纪中期。
十四世纪中期之后,议会才完全和明确地分成了两院——一个由单独召集的领主或大贵族组成,另一个则由所有当选的郡和自治市的代表组成;这两个议院对所有事物都进行共同协商和投票。*基佐:《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张清津、袁淑娟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2页。
还有一种对两院制起始年代更确切的说法。
1343年,议会开始分为两院:上院由大贵族和大僧侣组成,下院由骑士和市民代表组成,也称众议院。下院实际上代表了城市市民阶级的利益。*王沪宁:《国家主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由此亦可表明,代表制本身的发展和民主也没什么关系,这恰可以作为代表制对民主施予独立影响的明证。
而到了美国建国时,建国者们对立法机构的精心设计,则充分表明了他们意欲限制民主的决心。他们不仅设置了在当时还不是由民选的具有贵族色彩的参议院来分割众议院的立法权力,还设置了众所周知的三权分立体制。因而,人们所熟知的三权分立体制,其实并不是民主的象征,恰恰相反,其设计的初衷,正是用来限制民主。
此外,卢梭的观点也可作为“民主不优先”之佐证。很多人会认为,卢梭作为古典民主的鼓吹者,对代表制应该十分痛恨。凡持此观点者,其实混淆了代表制和代议制的区别。如按照我们前面关于代议制和代表制的分析,则卢梭不屑的是代议制而非代表制。同时,卢梭的观点从反面证明了代表制与民主之间的无关联性。卢梭认为,“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能代表的;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决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因此人民的议员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20页。换言之,主权不能被代表,而主权在民,因此人民不可以被代表,由此推论,代表和民主也就没有必然关联了。
看来,在代表制和民主的关系上,民主的发展与否都是受到代表制的制约,那么,对于两者的排序,代表制无疑比民主具有先天优势。虽说代表制和民主都是独立变量,且代表制的发展与否也会或多或少受到民主的影响,但由于代表制的形成和发展晚于民主,则很有可能意味着代表制较民主而言更具活力和可塑性。此外,以往已有大量论著从民主的角度来研究代表制,而代表制在新兴民主理论中的贡献却甚少。或许,民主视角下代表制对民主理论的发展推动力已陷入瓶颈,其原因正是民主思维局限了我们对代表制的理解。
以上从理论渊源层面论述了代表制之于民主的重要性,从而从反面论证了相对于代表制而言民主为什么不优先。
“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其发展演变主要发生在欧美地区。因此,典型意义的民主,就是指在欧美发生流变的民主。民主大致有古典民主和近代民主之分。古典民主是指古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近代民主,即间接民主,主要表现为代议制的特征。
对于近代民主,按熊彼特的说法,本质是选举程序,即人民通过投票选举出代表来代之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程序。除此,典型意义上的近代民主有一个显著特征是,其所选代表要么是立法席位(或议员席位),要么是政府行政分支的重要职位即政府的一把手位置。而那些官僚体系中的公务员职位和技术职位,是由通过选举而获得那些重要职位的代表者们任命的,这些职位本身是无须通过选举程序获取的。
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对此有经典表述。他把这个问题划为代议政府中的行政问题,并阐述了三点意见。其一,行政职务首长负责,“必须有一个人承担全部的毁誉褒贬”。*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91页。其二,“任何行政官员都不应根据人民的选举来任命,即既不根据人民的投票也不根据他们的代表的投票来任命”,*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95页。但其中有一项例外,是“共和政府的行政首脑”可以由人民普选或议会多数政党任命产生,虽然密尔对人民普选的方式持保留意见。“各大臣,除为首的大臣外,自然均由为首的大臣选任”。*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95页。其三,职业公务员应通过考试选拔并保持稳定,“构成公共服务常备力量的那一大部分重要人员,那些不随政治的变动而变动的人员,则留下来用他们的经验和传统来协助每一任部长,向他提供他们的业务知识,并在他的一般监督下从事具体业务”。*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00-201页。概言之,密尔认为,行政一把手应间接选举而非普选产生,并承担全部责任;其他行政官员应由一把手任命;一般公务员和技术官僚通过考试选拔,并且不随部门首长的更替而变化。可见,即使在西方经典的代议制政府蓝图设计里,民主的办法都从未获得过特别青睐,而只是作为一种替代性办法加以考虑。由是观之,要说民主天然具有制度优先的排序,恐怕稍显牵强。
三、为什么是代表制优先
在厘清了“为什么不是民主优先”这一重要论题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代表制优先?
事实上,由“民主”向“代表制”的转变,不仅仅是研究焦点的转移,而是一种结合了可操作性的更深层的思维方式的转换。正如近代哲学史上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变,其要义不在于研究的关注对象,也不在于语言的表达方式,而在于整个认知方式的改变。“民主”向“代表制”的转变,其可操作性体现在,它既不会逾越党治容忍限度,也可以满足无论是由于利益受损还是怀有变革理想的一批人对体制松动的一种憧憬,而不是纯粹铁屋式的呐喊;其智识的转换体现在,它是在逻辑与历史、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分析中所整合出的一种思维认知方式的转变。
本文开头部分对于代表制的基本特征作过分析,但它只阐明了什么构成代表制,而并未论证什么是代表制。如果我们把代表制放在一个更为宽阔的视阈中理解,或许会有不识庐山之慨叹。那么,什么是代表制?
德裔学者沃格林是西方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他对代表制有着极为精到的理解。沃格林认为,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代表制,*李强、叶颖:《在多元存在中寻求秩序——沃格林论代表制》,未公开发表文章。代表制是政治社会出现的关键。“一个政治社会出现的前提是它‘形塑’(articulates)自身,并产生一个代表。”*Voegelin,Eric,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Vol.5,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0.在沃格林看来,传统对于代表制的理解实在过于狭隘,远远不能反映全部政治理论的要核。他把代表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基本的代表制”,他将之描述为“基本类型的代表制涵盖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形塑(articulation)与代表制的外在表现。”*Voegelin,Eric,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Vol.5,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000.——意即代议制政府。二是“存在意义上的”代表制,是人对社会的形塑出于高尚的道义和为社会谋福祉而非私利的动机从而代表了社会,因而,这种代表类型体现了代表制的本质特征。可以说,第一种类型是第二种类型的特殊表现形式。三是“政治社会对先验真理的代表”,它是基于前两种代表类型的基础之上的一种理想型的代表,维持这种真理代表性意味着维护它业已在原则上寻求到的秩序;正是在寻求和建立秩序的这个意义上,政治社会对先验真理的代表对自身存在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李强、叶颖:《在多元存在中寻求秩序——沃格林论代表制》,未公开发表文章。
可见,沃格林把代议制政府仅仅视作普遍性代表制下的特殊性代表方式,这一观点和本文关于代表制与代议制政府之间关系的论断是不谋而合的。
然而,采用一家之言来理解代表制的概念,是否会有以点盖面的偏颇之嫌?须说明的是,沃格林乃德裔学者,在德国完成学业。而德国思想史上的国家观和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更为接近,其思维方式,更天然亲近于东方世界。这样一来,优先“代表”而非“民主”,或许就显得更为顺理成章了。
四、对我国民主和代表制的启示
(一)民主的实践分析
民主在我国可以从组织方式与实现形式两个层面来分析。
从“民主”的组织方式看,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行动揭示的严峻情况表明,党的民主集中制呈现民主不足而集中有余的态势。近年来腐败蔓延的根源在于权力过于集中在少数人,尤其是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一把手手上,而缺乏对其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从而导致腐败频发。如果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一面,则情况会有所不同。
从“民主”的实现形式看,主要有如下几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基层民主。基层民主集中体现为村一级的村民自治制度、村支书的公推直选等。现在在少数乡镇党委和基层的机关党委也试行公推直选。虽然其选举程序是民主的,可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基层民主的主要实施场所是村一级,而村委会并不属于我国行政建制的一级,只是我国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因而其所蕴含的民主光芒有限,难以扩展其辐射范围。另一方面,虽然部分村支部实行公推直选,但总体而言,村党支部特别是党支部书记依然在事实上由乡镇政府任命,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行政逻辑,这与村委会选举的“自下而上”的行政逻辑,存在着结构上的冲突。于是才会出现农村“两委一肩挑”的模式。但同一人身兼书记和村长两职有可能造成村中“一言堂”的局面。
第二种形式是协商民主。可以说,协商民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载体。然而,目前我国的协商民主仍面临一些问题。一是形式较为单一。我国的协商民主主要是通过各级政治协商会议的平台来实现。政协会议无疑是实现协商民主的好平台。但新时期实现全民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从根本上要求我们实现治理主体的多样化。因此,丰富协商民主的实现方式,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协商会议到调动市场、社会和公民等不同主体的积极性以实现协商民主形式的多元化,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二是基层协商民主发育仍然不足。近年来,基层协商民主在各地有一些创新。如浙江温岭的预算式协商民主,浙江余姚的村民“道德厅”协商民主,吉林安图的“民意裁决团”协商民主等。但总体而言,基层协商民主的创新仍然比较匮乏。有的地方甚至把基层协商民主视为走过场、搞形式。
第三种形式是党内民主。就其核心内容而言,如关于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涉及的是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提名方式,不断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和幅度,等等,虽有关选举程序,但并不涉及投票,更未涉及重要职务的选举,这些都和典型意义上的民主意涵相去甚远。同时,“党内民主”的优良传统在当前并未得到有效弘扬,这从近年来的官场腐败频发就可以看出。此外,有学者认为“党内民主”暗含了一个逻辑预设,即由党内民主逐步过渡到国家民主。然而,这样的逻辑链条是否成立?既然是逻辑推导,自然无法用经验验证之。然则不可证实之物却未必不能证伪。若对于古今中外的政党史进行观察,则很难发现一例组织松散和程序民主的政党是能够壮大发展的。
无论从民主的组织方式还是实现形式来看,我国的民主既不是西方典型意义上的民主,也与民主中国化的自身逻辑演变目标相距甚远,那么我们何不遵从现实的考量,甩掉“民主”的包袱,轻装上阵呢?
更为关键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国现实政治运行中的民主,没有一个与代表制有任何直接的关联:基层民主在本质上是直接民主,它意味着所有人的参与——例如村委会主任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协商民主是通过众人商议获得一种意见进而反馈给执政者——其实质在于协商的方式,而不在于是否被代表;党内民主更强调的是用民主决议来取代个人专断,也就更无涉代表制了。
这实际上佐证了西方民主发展脉络的独立性,及其与代表制发展脉络的无关联性。在这个民主脉络里,民主不仅不能制约代表制的发展,反倒要受到代表制的规约;民主不仅不能取代代表制,反倒可能为代表制所取代。这和西方民主发展不优先的逻辑是一致的。
(二)代表制的实践分析
代表制在我国的具体实现方式主要体现为如下两种。
第一种实现方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方面,人大制度与我国政治传统切合。西方民主国家是先有代议制后有政党,而政党是通过代议制来获取执政权。议会选举作为西方典型意义上的民主的一种重要体现方式衔接了代议制和西方的政治传统。而在我国,从时间顺序上看是先有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统率代表制,则成为必然,获得了先验的合法性,并且在政治逻辑上获得认可。钱穆认为,老子对政治认识最深微透彻之语是“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钱穆:《老庄通辨》,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30页。这个“神器”,在当下中国,就是党。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暗含的党统率代表制的特征,符合中国传统政治的逻辑。另一方面,人大制度与我国的政治权力运行结构切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特点是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最早提出了人大制度,“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转引自蔡定剑:《中国人大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因而有学者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一个重要特点,是植根于公有制经济基础的“高度的集权和权力一元化”。*蔡定剑:《中国人大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这与我国政治的权力运行结构相吻合。
第二种实现方式是党代表大会制度。与党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的相关研究不少,其中有三种观点涉及代表制与民主的优先顺序问题。
一是党代会常任制的民主论。党代会的常任制常被视作改进党内民主的重要议题。*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9/09-18/1874805.shtml事实上,党代会常任制涉及的是一个开会频率问题,这是一个标准的代表制问题,而不是什么民主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共八大初期实行过党代会常任制。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总结讲话时提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一样”*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页。。由于决定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所以,八大就取消了原有的党的各级代表会议制度。*陈丽凤:《党代会制度的发展历程与改革走向》,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5期。
但是到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党代会的常任制就由于种种原因取消了。可见,党代会常任制的民主论曲解了党代会常任制的本质,它实质上涉及到代表制的规则问题。
二是党代会改革的分权论。“在地方党委会、执委会(党的常委会成为党的执行机关并更名为执委会)和纪委会之间实行权力制衡,成员互不兼职,三个委员会均对地方党代会负责,在党代会闭会期间,由党委会领导执委会和纪委会。党委会负责决策,以集体领导为原则;执委会负责执行,以首长负责制为原则;纪委会成员可以参加执委会会议,发表意见,阅读执委会发布的文件,监督其在政策执行方面的情况,纪委会成员实行垂直任命,以免于受到同级常委会和执委会的控制”。*李永忠:《关于改革党委“议行合一”领导体制的思考》,载《体制改革》2002年第4期。转引自胡伟:《民主政治发展的中国道路:党内民主模式的选择》,载《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1期,第20页。这种欲将三权分立和中国的党国体制相嫁接的僵硬思维方式,历史经验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种嫁接式改革的荒谬。加之如前文所述,政党的内在属性决定了其集权性特征,如果在党内搞分权,不仅会使权力斗争扩大化和公开化,更会使组织系统变得散漫与失序。
三是党代会功能的完善论。关于完善选举功能的观点,包括推进常委会和党委会的票决制和党代会的差额选举。*胡伟:《民主政治发展的中国道路:党内民主模式的选择》,载《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1期,第22页。它虽具有可操作性,但其思维涉及民主方式(选举),其内容却不涉及民主实质(无重要职务选举),加之党代会制度本身也不是民主脉络的产物,因而没有把握党代会制度作为代表制的一种实现方式的实质。
由上可知,涉及民主的代表制无论哪种观点成立的一个先置条件是,剔除其中的民主或伪民主因素。换言之,只有廓清了代表制中看似关涉却实际无关的民主论调,如上这些代表制才可实施或更好执行。
在这里我们发现,在我国的现实政治运行中,民主不仅不能对代表制的发展产生丝毫影响,相反,代表制却在很大程度上规约了民主的空间,使得民主要么无法发挥应有作用,要么彻底丧失功能。至此,代表制和民主孰先孰后,也就一目了然了。
无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官方意识形态追求的发展目标。然而无论从组织方式还是实现形式上看,恰恰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一套自洽的逻辑线索、与体现“中国特色代表制”的人大制度和党代会制度有着不同的脉络,因而现实政治距离这个目标仍有相当的距离。同时,反倒是人大制度和党代会制度在不断地成熟和完善过程中不断剔除了所谓“民主”的要素,变得更加纯粹,却证明了代表制是如何影响、规约甚至取代民主的。到这里,我们蓦然回首,发现中国特色代表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竟然与我们所要借鉴的最本源的那个代表制和民主的关系殊途同归了——于是先代表制而后民主,无论从逻辑上还是现实上,都成为可能,并且有可能成为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条捷径。
五、小 结
概言之,代表制和民主是在近代民主时期才真正意义上发生了关联,形成了对近当代人类政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代议制民主制度。虽然在自此之后的很多时候,代表制和民主相辅相成,但也有一些时候,代表制本身会限制民主的发展。无论是托马斯·杰弗逊等对美国三权分立制度设计的初衷,还是卢梭对代议制的疑惧,抑或是密尔认识到民主在代议制政府过程中只是起到有限的作用——民主都不具备优先于代表制的资质。相反,代表制优先于民主。其关键原因在于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民主——即代议制政府,只是代表制这个普遍矛盾之中包含的特殊矛盾。
进一步认识代表制和民主的关系,并且深刻把握两者之间内在的逻辑矛盾关联,对于如何从政治制度上理解当前诸多民主国家深陷经济和福利双重危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它对于理解在我国应用和实践代表制和民主及其关系,以及如何通过代表制和民主来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责任编辑:林赛燕)
D08
A
1007-9092(2017)06-0100-009
2017-05-08
冉昊,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副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和社会治理。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危机与民主调适机制研究”(编号:17CZZ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