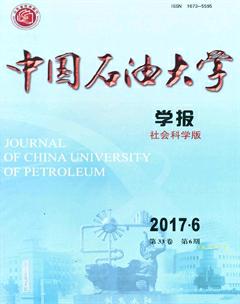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再审视
Dec.2017Vol.33No.6
DOI:10.13216/j.cnki.upcjess.2017.06.0009
摘要:未成年人犯罪在总体趋势上呈现由“冲动犯罪型”向“蓄意犯罪型”转变。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理解和适用存在偏差,“宽严相济”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片面从宽”。认识上的“片面从宽”导致对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无法进行准确评估。因此,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司法中适用应以人身危险性评估为核心。在相较成年人从宽的基本框架之内,未成年人的刑罚适用应以从轻为基点,并在此基础上适用人身危险性的评估结果。
关键词:宽严相济;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
中图分类号:D9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7)06005205
近年来,数起恶性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引起社会高度关注。2015年10月18日,湖南省邵東县一位小学女教师被三名不满13周岁的未成年人抢劫杀害;①2015年10月5日,初中生潘某、曹某、谢某经过长期预谋后,至其同学邓某家中实施强奸,并趁邓某的父亲熟睡将其杀死。②这些案例虽不具有大数据的样本意义,但所反映的个别未成年人犯罪之凶残性、预谋性仍令人震惊。长期以来,未成年人被认为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未成年人犯罪后相较成年人往往获得更多的谅解和宽容,这一点主要表现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适用。但在未成年人犯罪宏观态势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片面理解和评估方式的不科学,将导致未成年人司法出现“宽严失衡”的局面。
2012年修法之后,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制度除保障人权之外,还具有教育未成年人、矫治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1]有鉴于此,为正确理解和适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而有效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本文将反思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适用,并探讨构建以人身危险性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以期有益于未成年人司法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
一、转变:从“冲动犯罪型”向“蓄意犯罪型”
就宏观态势而言,未成年人犯罪在总体趋势上呈现由“冲动犯罪型”向“蓄意犯罪型”转变。
在传统研究中,未成年人犯罪的直接原因多被归纳为青春期的生理躁动以及心理的不稳定,特别是未成年人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尚不稳定的变动期,多因琐事一时冲动而犯罪,甚至有部分未成年人由于缺乏法律知识而在无意中犯罪。基于实践经验总结的这一认识基本反映了以往未成年人犯罪的整体犯罪概貌,对此可以归纳为“冲动犯罪型”。在“冲动犯罪型”中,由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基础是生理变化,因而其犯罪行为的危害性较小,在行为人认识到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后往往能主动配合矫治,积极接受司法机关的教育。也正是在这一认识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理论和实践均强调对未成年人要从宽处理,以使未成年人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避免其因一时冲动而受到过度严厉的处罚。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未成年人的“早熟”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相当一部分未成年人犯罪的直接动因不再是青春期的生理变化与心理冲动,而是未成年人对实施犯罪行为的积极追求。对未成年人的这一整体犯罪概貌可以归纳为“蓄意犯罪型”,即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多是未成年人自身主观追求的产物,未成年人在明知犯罪危害后果的情况下仍蓄意实施犯罪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只是使用“冲动犯罪型”与“蓄意犯罪型”两个概念总结和概括未成年人犯罪的整体转向,以更好地揭示未成年人犯罪的整体趋势,而不意味着“冲动”和“蓄意”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特征。“冲动犯罪型”与“蓄意犯罪型”只是从现实经验中抽象出来用以解释和预测未成年人犯罪的一组理论模型。限于篇幅和主旨,本文主要就当前未成年人“蓄意犯罪型”的特征加以分析。
根据相关实证数据,“冲动犯罪型”向“蓄意犯罪型”的转变大致以2000年为转折点,2000年以后的未成年人犯罪主要呈现重复犯罪增多、有预谋犯罪增多、暴力型犯罪增多、有组织犯罪增多等特点。
根据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年司法》的统计数据,在全国范围内,2009—2014年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按照从宽处理的整体思路,非监禁刑的适用率表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由3223%上升到4176%。但与此同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严重暴力犯罪激增,抢劫、强奸等严重犯罪在2009年呈现猛增态势。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12月
第33卷第6期马康: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再审视
局部地区的调查研究也基本符合“蓄意犯罪型”的总体特征。“天津市犯罪调查科研数据库”对 1990—2005 年重新犯罪人员的调查统计结果说明短刑犯重新犯罪的比率升高:原判3年以下的短刑犯出狱后再犯罪的,2005年比1990年上升了286%;原判5年以下的重新犯罪人从1990年的635% 上升到2005年的855%,上升了22%。[2]辽宁省在1980年后的10年内,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由7%上升至17%,并在2004年达到了2214%,之后仍以每年768%~1594%的速度激增。[3]某课题组的相关调研显示,截至2009年,京、鄂、贵三地未成年犯管教所中未成年犯的重复犯罪率达到了惊人的569%。[4]
重复犯罪率的提高,表明未成年人犯罪不再停留在冲动犯罪、法盲犯罪等传统认识层面。而且,未成年人重复犯罪凸显了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习惯化,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在犯罪预谋的调查中,京、鄂、贵三地未成年犯管教所中几乎40%的未成年人在犯罪前进行了准备,而且有106%的未成年人曾经制定周密的犯罪计划。[5]95这一调查结果也颠覆了未成年人多为青春期偶然犯罪的传统认识。这意味着部分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欲望更为强烈,社会危害性更大,其潜在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也更强。endprint
在未成年人犯罪预谋性、再犯性增强的同时,恶性犯罪也达到了较高的比例。在京、鄂、贵三地未成年犯管教所中,有776%的未成年人为了压制被害人反抗而使用暴力手段,甚至有61%的未成年选择故意杀人。[5]94在以往的研究中,以获取物质利益为主的侵犯财产型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类型,其暴力性和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而在京、鄂、贵三地的调查中,抢劫犯罪、强奸犯罪占到65%,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占到164%,合计达到了834%的高比例。[5]95
与暴力型未成年人犯罪相伴随的是有组织犯罪。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的偶发性和冲动性决定了其犯罪往往是个别人的临时起意,少有出现纠合多人共同犯罪的情况。而“蓄意犯罪型”未成年人有预谋地从事暴力性犯罪的伴生后果就是以增强犯罪能力为目的的有组织犯罪。2005年北京市的调查表明,部分未成年人组成的犯罪组织已经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6]在京、鄂、贵三地的调查中,有427%的未成年犯认为在其犯罪组织中存在明确的支配关系。[5]9394在2011年粤、苏、豫、鄂、川五个省的调查中,超过80%的未成年人犯罪属于有组织犯罪。[7]
上述数据表明,伴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未成年人犯罪在近20年来已经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在此态势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指导未成年人司法的基本纲领,应当得到重新审视。
二、审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中国刑事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指导功能。但作为一项纲领性、指导性的刑事政策,其具体内涵和理解仍存在一定的争议。有学者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是区别对待具体情况,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中有严,严中有宽。[8]也有学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一面是指从宽处理,包括了当宽则宽与严中从宽两个含义;另一方面是指从严处理,包括了严格和严厉两个含义,严格是指要将符合条件的严重违法行为视为犯罪对待,不应一味姑息,严厉是指具体刑罚一定要依法适用,当严则严。[9]
具体到未成年人司法中,理论界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解多集中于对“宽”的解读,并以之作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的主要方面。比如,有学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主要表现为惩罚从宽,预防从严。[10]还有学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体现不应当强调“严”,甚至指出“严”不适用于未成年人。[11]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片面理解和适用导致理论界的研究不断向论证未成年人进一步轻缓处理的方向发展,司法实务部门对于刑事政策的贯彻也演变为扩大未成年人的外延、减轻甚至免除未成年人的刑罚。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也被解读为“能宽则宽”,其中的极端做法是将“未成年人”的外延扩展至在校学生,而不以年龄为准。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5条规定:“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犯罪情节轻微,或者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实施的较轻犯罪,或者被告人具有犯罪预备、犯罪中止、从犯、胁从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情节,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对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做好善后、帮教工作或者交由有关部门进行处理,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该条明确将犯罪情节轻微、犯罪预备、防衛过当、避险过当等可以免除刑罚的情节与行为人是未成年人、在校学生情节等同视之。《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等也沿袭这一思路,将在校学生等同于未成年人。
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等同为“宽”是过于片面的,忽视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严”。在一定意义上,“片面从宽”的认识和做法忽视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相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着眼点不应是“宽”和“严”孰重孰轻的问题,而是“宽”和“严”如何“相济”的问题。换言之,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如何通过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落实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帮助未成年人重新生活应当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因此,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与“严”需要在人身危险性视角下重新理解和适用。
三、方法:人身危险性的科学评估
未成年人司法中的“宽严相济”之所以演化为“片面从宽”,除了政策引导与不当理解之外,实践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无法针对涉案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行准确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将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从轻”“减轻”处罚的应当情节,在于该因素必然反映人身危险性,并直接影响量刑根据。[12]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无法准确评价涉案未成年人的行为与心理,宽缓处理的政策指导导致了一律从宽的处理方式。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现有评估方式或流于形式或不具有可操作性,无法为公安司法机关提供必要的办案参考。而理论界对人身危险性的研究仍有待深入,对未成年人犯罪中人身危险性的应用的研究更是少之甚少。因此,有必要重新梳理人身危险性理论,以此为工具审视现有评估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科学的人身危险性评估方法。
(一)前提:人身危险性概论
人身危险性作为刑法理论中的特有概念,起源于近代刑法学理论。以龙勃罗梭和加罗法洛为代表的刑事人类学派与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刑事社会学派虽然存在诸多分歧,但其共同点是均极为强调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李斯特提出了“应受惩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这一著名论断,其认为刑罚适用的对象不是受先天因素和后天环境影响所导致的犯罪行为,而是基于人身危险性的犯罪人。总的来说,刑事人类学派对人身危险性的考察侧重生理基础,而刑事社会学派更多地关注社会环境等整体影响。[13]77
人身危险性概念在刑法理论中主要有三种观点:广义说认为人身危险性包括了初犯可能性与再犯可能性;狭义说认为人身危险性仅仅指再犯可能性,而不包括初犯可能性;混合说认为人身危险性是初犯可能性与再犯可能性的统一,再犯可能性的主体必须是犯罪人,而初犯可能性的主体则可能是犯罪人以外的任何人。[13]78笔者认为,人身危险性的广义说较为适当。从人身危险性的起源来看,龙勃罗梭关于犯罪人的生理研究和李斯特关于犯罪人的社会环境研究均指向犯罪倾向,并以此作为人身危险性的基础。endprint
因此,人身危险性是由特定行为人的犯罪倾向所显现的初犯可能性或再犯可能性。由于人身危险性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强烈影响,变化性是其较为重要的特点之一。比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小偷小摸为主的未成年人犯罪显著下降,而受拜金主义、奢侈享乐主义的不良影响,未成年人犯罪中为获取较大物质利益而进行暴力犯罪的趋势已经开始显现。
前文已述,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若仍以以往的实践经验作为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基础,其科学性将不得不令人质疑,具体表现为未成年人犯罪评估方法的不足。
(二)障碍:现有评估方法的缺陷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重要部分,其所具有的证据属性对于未成年人的具体量刑具有重要意义。[14]但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的考察表明,调查方式主观性和调查方法的不科学导致大部分社会调查报告流于形式。社会调查报告的制度性缺陷导致难以准确评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15]
从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主体来看,实践中的做法并无统一标准,呈现两极化趋势:一是完全以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为主;二是以聘请社会工作者为主。这两种方式都存在不可避免的弊端:长期从事刑事法律工作的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容易形成追诉思维和被追诉人一般有罪的潜意识,而且他们也缺乏相应的社会学、心理学等知识,很难对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作出科学评估。社会工作者存在的问题则是另一个极端,一般而言,社会工作师是目前中国较受认可的社会工作主体。社会工作师的资质考试对于社会调查报告主体具有指引性的意义,但相关资质的考察主要集中于社会服务等领域,犯罪心理学等相关知识则毫无涉及,对人身危险性等相关知识的忽视将对未成年人犯罪倾向的预测和犯罪行为的预防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在资质认定以外,社会调查报告制作主体的培养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目前开设与社会调查报告相关的专业的学校较少,而且这些学校的相关课程也并不包括与人身危险性有关的内容。
部分研究已经发现这些缺陷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在以地级市和省为样本进行的调查中,均发现目前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不够科学,其内容与结论之间很难认为存在逻辑联系,而且社会调查报告的结论也一般倾向于幅度较大的从宽处理。[1617]有学者在更为细致的量化研究中发现,“犯罪年龄”以外的其他社会调查报告内容均已沦为裁判文书的装饰,而未曾对裁判者的心证真正发挥影响。[18]
上述研究成果也验证了本文之前所提出的假设:由于人身危险性科学认定方法的缺失,在将未成年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解读为“片面从宽”的语境下,未成年人犯罪的评估和处理已经“失之过宽”。
四、改进:科学评估方法的引入
前文已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所以失之过宽,不仅在于理解存在偏差的认识原因,更在于无法准确评估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的实践原因。在保护和教育未成年人的宏观语境和以宽缓为主的现实评价下,由于难以具体量化和把握“宽”“严”,所谓的“宽严相济”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未成年人犯罪处罚“能宽则宽”。因此,在反思理论误区的同时,更具有现实紧迫性的问题是,如何寻找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中具体适用的“抓手”。在世界范围内,评估和考察人身危险性的“抓手”主要包括投射技术、主体测量、自陈量表、行为观察四种。其中,自陈量表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较为成熟,而且客观性和操作性较好,已经得到了较多国家和地区司法机关的应用。就实践运用来看,自陈量表的具体问卷形式主要包括明尼苏达大学教授S.R.Hathaway和J.C.Mckinley制作的人格测试及伊利诺伊大学Cartel教授的16PF分析等。
中国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在近年来已经卓有起色。比如,针对未成年人的恶性犯罪行为编制的《反社会人格倾向评估问卷》对9718名青少年和1347名未成年犯进行了测试,对具有反社会倾向的未成年人具有良好的区分度。[19]司法实践的需求则更早地催生了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的评估测试,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早在2006年就引入了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测试,并将其作为评估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倾向的重要依据。该“人身危险性”测试重在结合刑事法、社会工作等相关专业知识,通过对未成年人自身特质進行分析和赋值,以量化打分的方式计算其“人身危险性”分数,并以此作为裁判时量刑的考虑因素。[20]
如果将借鉴的范围适度扩大至未成年人犯罪之外,则中国人身危险性评估在刑事领域的研究和应用更早。基于自陈量表的基本模式,中国研究组织在2006年成功制作COPA-PI评估量表,该评估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和实用效果,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比较普遍的应用,并作为监狱系统刑罚减免的重要考量因素,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各地刑罚执行部门也在探索中逐渐形成多套行之有效的科学评估体系。比如,浙江省
已经研制出 RRPI(罪犯教育改造质量综合评价系统),用于对“再犯可能性”进行测量; 江苏省监狱局开发了“罪犯心理、认知和行为量表”“人身危险性简评表(RW)”“刑罚体验简评表(XT)”、“再犯风险简评表(CX)”等一系列量表;北京市教育矫治局基于综合因素开发了“教育矫治质量评估量表”等。这些量表和相关经验对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评估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意义。
因此,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中的适用应当以人身危险性的评估为核心。未成年人的刑罚适用建立在相较成年人从宽的基本框架之内,即定罪量刑时以“从轻”为基点,并在此基础上适用人身危险性的评估结果。具体而言,在建立人身危险性的评测系统后,对于《刑法》规定的“从轻”“减轻”处罚,应当在法定从轻、减轻的基础上具体考虑量刑情节。比如,对体现不同人身危险性的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的量刑赋值应当有所区别;因不满14周岁而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再次犯罪的,其较大的人身危险性也应当在“从轻”“减轻”后的量刑幅度内有所体现。endprint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并非重刑主义者,也并非要求未成年人应该适用与成年人完全相同的刑罚,笔者所试图探讨的是未成年人司法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具体实现。易言之,未成年人犯罪时得到一定程度的宽缓不仅是中国的刑事司法传统,也是世界各国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但在宽缓处罚的基本线上,其应“宽”到何种程度、其“严”又在何时适用,均是不得不慎重考虑的现实问题。否则,一味从宽不仅不能教育和挽救未成年人,甚至会在客观上造成其继续犯罪的悲剧。
注釋:
① 参见http://news.youth.cn/sh/201510/t20151021_7226720.htm。
② 参见http://www.youth.cn/preview/news.youth.cn/jy/201602/t20160201_7594648.htm。
参考文献:
[1] 付奇艺.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理论反思与体系重构——以《刑事诉讼的目的》为参照[J].犯罪研究,2016(3):7.
[2] 丛梅.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青少年犯罪防控研究[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2):51.
[3] 李秋月.浅析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现状及原因[J].学术探索,2011(9):88.
[4] 张远煌,姚兵.从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全面贯彻[J].法学杂志,2009(11):1820.
[5] 张远煌,姚兵.中国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的新趋势——以三省市未成年犯问卷调查为基础[J].法学论坛,2010(1).
[6] 席小华,金花.北京市未成年人犯罪实证研究[J].法学杂志,2005(5):124.
[7] 郭开元.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25.
[8] 高铭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J].法学杂志,2007(1):3.
[9] 陈兴良.宽严相济政策与刑罚规制[J].法学杂志,2007(1):8.
[10] 何显兵.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诠释[J].江西社会科学,2013(4):156.
[11] 马克昌.中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演进[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163224.
[12] 涂欣筠.我国刑法从宽处罚规范化研究[J].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4(6):69.
[13] 赵永红.人身危险性概念新论[J].法律科学,2000(4).
[14] 马康.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若干问题研究[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4):18.
[15] 马康.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冷思考[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6(3):6668.
[16] 蒋雪琴.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实践考察[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130.
[17]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中社会调查制度的实际运用与分析[J].法律适用,2014(6):119.
[18] 莫然.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距离:未成年人量刑实证研究[J].政法论坛,2015(4):144.
[19] 贺超,罗宏,杨业兵,等.反社会人格倾向评估问卷[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9):1131.
[20] 殷文静.南京中院首创“危险性”预研[EB/OL].(20060713) [20170115].http://news.sohu.com/20060713/n244230766.shtml.
责任编辑:袁付娜
Research on the Criminal Policy of Temper Justice with Mercy in Juvenile Jus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sonal Dangerousness
MA Kang
(Institute of Evidence Law and Forensic Scienc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2249, China)
Abstract:The general trend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present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accidental crime type" to "premeditated crime type". There is a deviation in the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riminal policy of temper justice with mercy in the juvenile delinquency. To some extent,the "tempering justice with mercy" has been "too wide". The "one-sidedness" in the understanding results in the failure to assess accurately the minors personal danger. Therefore, the criminal policy of temper justice with mercy should be applied in the minors, and the evaluation of personal dangerousness should be the c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inor penalty is based on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leniency of adults,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evaluation of personal dangerousness.
Key words:temper justice with mercy; juvenile; personal dangerousness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