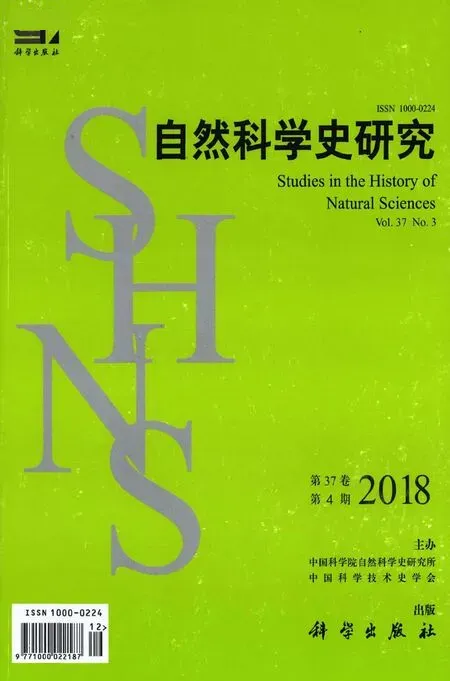中国天文大地测量的历史演变
关增建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0 引言
天文学本质上是一门测量科学,古今中外,于此皆然。但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天文学测量,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欧洲,天文学对测量的需求可以用1563年17岁的第谷(Tycho Brahe,1546~1601)的一段话为代表 :
我研究过所有现有星表,但它们中没有一个和另一个相同。用来测量天体的方法好比天文家一般多,而且那些天文家都一一反对。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长期的、从一个地点来测量的计划,来测量整个天球。[1]
这段话的重点是“一个长期的、从一个地点来测量”。第谷在天文学上能够彪炳史册,与他坚持进行长期的、在一个地点进行天文观测,是分不开的。
相比之下,在中国天文学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天文学测量是所谓的“天文大地测量”,这种测量的本质是在多个地点、约定时间的同时测量,有时还要对这些地点间的距离进行测量。测量的目的,与第谷所思也大不一样。
为什么中国古代天文学会形成这种独特的测量,它是如何发生和演变的?学界就中国古代天文大地测量的研究已有丰硕成果,但就此视角展开论述者,则尚属鲜见。本文不揣浅陋,试图对此有所回答。
1 呼吁已久的测量——僧一行的天文大地测量
中国古代独特的天文大地测量的形成,与古人对大地形状的认识密不可分。
在中国古代的宇宙结构学说中,不管是盖天说,还是浑天说,在对大地形状的认识上,占主流地位的观点都认为地是平的,大小有限。由这两个前提,很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 :地面有个中心。古人称这个中心为“地中”。[2]
显然,地中概念的存在,为古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天文观测地点。地中,就是古人心目中进行天文观测的坐标原点。所以,《隋书·天文志》才郑重指出 :
《周礼·大司徒职》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此则浑天之正说,立仪象之大本。([3],522页)
那么,这样的“地中”具体在哪里呢?《周礼·大司徒职》对地中概念给出了具有天文意义的定义 :
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4]
根据《周礼》的定义,在夏至的时候,立8尺之表,测量正中午时表影长度,如果影长正好1尺5寸,则立表之处即为地中。古人用这种方法进行测量,认定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市下属的告成镇)为地中之所在。现在该地还保留有元代郭守敬(1231~1316)在那里建高台测影的遗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现代天文学告诉我们,按照《周礼》的定义,是不可能测出这个点来的。满足“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这一条件的,是一条纬度线。也就是说,古人如果坚持进行这样的测量,应该会发现他们所确定的地中是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不确定性的。在这里,古代宇宙模型下的定义的完备性与实际操作中的不确定性产生了矛盾。
正是由于实际操作中具有不确定性,古人想方设法试图在《周礼》之外找到新的测定地中的方法。南北朝时的祖暅就提出过一种可称之为“五表法”的解决方案([3],522~523页),试图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祖暅的方案,就当时的地平观念来说,在理论上可谓是完美的,但若付诸实施,则不难发现,按他的方法进行测量,将会发现处处都是地中。
如果连祖暅的方案也不能解决问题,那么,是不是地中概念本身出了问题了呢?《周礼》为何要以夏至之日影长1尺5寸去定义地中呢?现实迫使古人去思考这一问题。他们知道,这个定义本身隐含了所谓“千里差一寸”的假说,那么,是否该前提出现问题了呢?自汉至隋,人们的测量实践表明,“千里差一寸”之说未必成立。《隋书·天文志》对此总结道 :
又《考灵曜》、《周髀》、张衡《灵宪》及郑玄注《周官》,并云 :“日影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案宋元嘉十九年壬午,使使往交州测影,夏至之日,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遥取阳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计阳城去交州,路当万里,而影实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又梁大同中,二至所测,以八尺表率取之,夏至当一尺一寸七分强。后魏信都芳注《周髀四术》,称永平元年戊子,当梁天监之七年,见洛阳测影,又见公孙崇集诸朝士,共观秘书影,同是夏至日,其中影皆长一尺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洛,南北略当千里,而影差四寸。则二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也。况人路迂回,山川登降,方于鸟道,所校弥多,则千里之言,未足依也。([3],525~526页)
把前人在各地分别进行的测影数据加以汇总,就会发现“千里差一寸”之说不符合实际。对此,隋朝刘焯(544~610)提出了一个切实的解决办法——进行天文大地测量,用实际测量来检验该说是否成立 :
仁寿四年,河间刘焯造《皇极历》,上启于东宫。论浑天云 :“……《周官》夏至日影,尺有五寸。张衡、郑玄、王蕃、陆绩先儒等,皆以为影千里差一寸。言南戴日下万五千里,表影正同,天高乃异。考之算法,必为不可。寸差千里,亦无典说,明为意断,事不可依。今交、爱之州,表北无影,计无万里,南过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实差。焯今说浑,以道为率,道里不定,得差乃审。既大圣之年,升平之日,厘改群谬,斯正其时。请一水工,并解算术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数百里,南北使正。审时以漏,平地以绳,随气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则天地无所匿其形,辰象无所逃其数,超前显圣,效象除疑。请勿以人废言。”不用。至大业三年,敕诸郡测影,而焯寻卒,事遂寝废。([3],520~522页)
显然,刘焯认为,地中说是建立在千里差一寸学说之上的,而千里差一寸学说是否正确,则可以通过实测来判定。这是他提出要进行天文大地测量的根本原因。由于各种缘故,刘焯的提议,一开始并未被采纳,等到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开始要实行的时候,刘焯又因病去世,事情就拖了下来。
到了唐朝,开元九年(721),天文官几次预测日食不准,玄宗下诏让僧一行(673~727)制订新的历法。一行提出要改进仪器,进行测度,获得玄宗认可。玄宗又进一步下诏,要求一行首先测定地中位置。《新唐书·天文志》记载 :
初,淳风造历,定二十四气中晷,与祖冲之短长颇异,然未知其孰是。及一行作《大衍历》,诏太史测天下之晷,求其土中,以为定数。([5],812页)
由此,僧一行的天文大地测量正式登场。显然,他的这次测量,除了满足历法制订的需求外,本质上是对刘焯倡议的实施,直接目的则是要满足唐玄宗关于测定地中的要求,以此作为今后天文学发展的基础。
根据唐玄宗的指令,从开元十二年(724)开始,一行组织了全国13个点的天文大地测量。这次测量到开元十三年(725)结束,其中以天文学家南宫说等人在河南的工作最为重要。南宫说等在黄河南北选择了几乎位于同一经线的白马(今河南滑县)、浚仪(今河南开封)、扶沟和上蔡这四个地点,分别测量了其北极出地高度和夏至日影长度。此外,他们还测量了这四个地点之间的距离,得到了一些新的认识。《新唐书·天文志》对此记载道 :
太史监南宫说择河南平地,设水准绳墨植表而以引度之,自滑台始白马,夏至之晷,尺五寸七分。又南百九十八里百七十九步,得浚仪岳台,晷尺五寸三分。又南百六十七里二百八十一步,得扶沟,晷尺四寸四分。又南百六十里百一十步,至上蔡武津,晷尺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晷差二寸余。而旧说王畿千里,影差一寸,妄矣。([5],813页)
南宫说的测量,就是刘焯建议的实施,目的在于验证千里差一寸学说是否成立。比较这些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到,该学说与实际情况完全不合,故《新唐书·天文志》明确指出,“旧说王畿千里,影差一寸,妄矣”。从此,“千里差一寸”的说法,作为天文学理论,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一行天文大地测量的过程及其取得的丰硕成果,已有的天文学史研究已经做了详尽揭示[注]例如,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天文史整理研究小组在《天文学报》1976年第2期发表的论文《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天文大地测量及其意义》,揭示了僧一行天文大地测量的方法和经过,并讨论了测量的意义;向华荣、钮仲勋、厉国青、丁延暻在《陕西天文台台刊》1982年第1期发表的文章《我国地理经纬度和子午线实测的沿革》,对我国历史上唐、元、清几次大规模天文大地测量的情况及意义做了梳理,对学术界了解这些测量的具体情形及意义颇有裨益。,这里不再赘述。
2 五代至宋——以岳台为地中?
“千里差一寸”学说被否定了,那么,地中概念呢?换言之,唐玄宗让一行“求其土中”,这个任务他完成了吗?对此,一行未做明确回答。实际情况也不允许他明确做答,因为开元九年他受诏进行天文大地测量,要确定地中之所在,但在开元十一年(723),测量还未正式开始,唐玄宗就先确认了地中的具体位置。《新唐书·地理志二》记载 :
阳城,……有测景台,开元十一年,诏太史监南宫说刻石表焉。([5],983页)
阳城就是传统上所认为的地中所在地。唐玄宗在天文大地测量正式开始之前,派遣南宫说到那里树立石表以作纪念,其意图显然是要让一行通过测量来证实他的判断。南宫说树立的石表留存至今,成为登封观星台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奉诏树立石表的举措,却置一行于尴尬地位,因为一行让南宫说进行的测量,实际上否定了传统的地中学说,亦即否定了玄宗的判断。这促使他不得不为二者间的矛盾寻找自己的说辞 :
古人所以恃句股术,谓其有证于近事。顾未知目视不能及远,远则微差,其差不已,遂与术错。譬游于太湖,广袤不盈百里,见日月朝夕出入湖中;及其浮于巨海,不知几千万里,犹见日月朝夕出入其中矣。若于朝夕之际,俱设重差而望之,必将大小之同术,无以分矣。横既有之,纵亦宜然。
又若树两表,南北相距十里,其崇皆数十里,置大炬于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于其下,则当无影。试从南表之下,仰望北表之端,必将积微分之差,渐与南表参合。表首参合,则置炬于其上,亦当无影矣。又置大炬于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于其下,则当无影。试从北表之下,仰望南表之端,又将积微分之差,渐与北表参合。表首参合,则置炬于其上,亦当无影矣。复于二表间更植八尺之木,仰而望之,则表首环屈相合。若置火炬于两表之端,皆当无影矣。夫数十里之高与十里之广,然犹斜射之影与仰望不殊。今欲凭晷差以推远近高下,尚不可知,而况稽周天里步于不测之中,又可必乎?([5],815~816页)
这一说辞的核心内容,是说用立表测影的方法,不能解决此类问题。他给出的理由是,“目视不能及远,远则微差,其差不已,遂与术错”。为此,他还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设想在南北相距10里的地方树两个高几十里的巨表,人站在南表的下面,仰视北表的表首,因为距离遥远,将会发现两个表的表首会连合在一起。如果在北表的表首放置一个火炬,在南表的下面立一个8尺之表,那么这个8尺之表也不会有影子。因为两表表首会合,火炬就相当于放在南表的表首上了,这样在南表下面进行立表测影,就测不到影子。之所以如此,一行认为,人眼在观测远距离的光线传播时,会产生视觉错觉,光线本身也未必按直线传播,这些都会影响到观测结果的可靠性。距离越远,误差越大,错误越甚,最终导致所采用的观测方法不能成立。由此,像立表测影,作为测定天高日远、地中所在之术,因其所涉范围巨大,凭人的视线进行观测,结果是不可靠的,“欲凭晷差以推远近高下,尚不可知,而况稽周天里步于不测之中,又可必乎?”
一行不愿明目张胆否定唐玄宗要求测定地中的指令,于是做了模糊其辞的说明,说依靠立表测影,很难定出地中。到了五代时期,后周天文学家王朴(906~959)没有了这样的忌讳,他对一行的测量结果做出了全新的解释 :
古者植圭于阳城,以其近洛也。盖尚慊其中,乃在洛之东偏。开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横野,中得浚仪之岳台,应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国,定都于汴,树圭置箭,测岳台晷漏,以为中数。晷漏正,则日之所至,气之所应,得之矣。[6]
王朴是后周大臣,他把地中的位置解释成位于浚仪。浚仪是古县名,西汉时置,治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北朝、隋、唐时期先后为陈留郡、梁州、汴州治所;五代、宋朝时则与开封县同为开封府治所。也就是说,王朴把地中与后周的都城所在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一行天文大地测量的结果。
王朴把地中放在都城,在那里建台立表,测影制历。这一方面,使地中概念更为神圣;另一方面,也为天文官员进行实地观测提供了极大方便。正因为如此,他的做法,为多数北宋学者所喜见。北宋学者进行天文观测,相当一部分是在浚仪的天文台也就是岳台进行的。
王朴借用了一行天文大地测量的结果,确立了新的地中,但他的说明并未获得天文家的一致认可,仍有一些北宋学者坚持阳城的地中地位。在北宋的历法中,虽然大部分以岳台为地中,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用阳城测影所得数据编制的。
既然地中具体位置存在争议,一行的天文大地测量也明确肯定用立表测影的方法不能确定地中,宋人干脆放弃了对地中的寻找,把天文观测的注意力完全放到了直接影响历法精度的天文仪器制作和恒星观测上了。宋朝对天文仪器制作和天文观测格外重视,据天文学史专家潘鼐的统计 :
自北宋至道元年到南宋绍兴三十二年,赵氏皇朝共铸造了约十座大浑仪用于天文观测。另外还有两座浑象与机械时钟,即太平兴国浑仪与元祐的水运浑象。
同仪器的频繁制作相呼应,就史所录存,恒星的实测也有七次之多,有如下述 :
(1)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曾测定二十八宿距度。
(2)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曾测定外官星的位置。
(3)景祐年间(1034~1038年),曾测定二十八宿距度及周天恒星。
(4)皇祐年间(1049~1054年),曾测定二十八宿距度及周天恒星。
(5)元丰年间(1078~1085年),曾测定二十八宿距度,亦测全天恒星。
(6)绍圣二年(1095年),曾复测二十八宿距度。
因此,在我们乡下,我的三爹和母亲深受乡亲们的爱戴,而我在遥远的北大,则当更加勤奋地工作,用出色的成绩回报他们。
(7)崇宁年间(1102~1106年),又测定二十八宿距度。[7]
这么多次测量,没有一次跟一行那样的天文大地测量类似。原因很明显 :没有像一行那样检验“千里差一寸”理论是否成立,并进而确定地中具体位置的要求。
3 一行模式的卷土重来——郭守敬的天文大地测量
元朝郭守敬的“四海测验”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天文大地测量。郭守敬的测量方式,与僧一行所为,几乎完全一样,都是在全国范围内选定若干分离地点,派人分别测量观测地点的北极出地高度、夏至影长、昼夜时刻等。只不过,与一行的测量相比,郭守敬的测量范围更大,精度更高。《元史·郭守敬传》记载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
十六年,改局为太史院,以恂为太史令,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给印章,立官府。及奏进仪表式,守敬当帝前指陈理致,至于日晏,帝不为倦。守敬因奏 :“唐一行开元间令南宫说天下测景,书中见者凡十三处。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远方测验,日月交食分数时刻不同,昼夜长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测验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测景。”帝可其奏。遂设监候官一十四员,分道而出,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硃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凡二十七所。([8],3848页)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至元十六年(1279),郭守敬担任了太史院的实际领导人,他向元世祖忽必烈讲授天文,趁机向忽必烈提出,为了编制历法,应以唐朝开元年间天文学家僧一行的天文大地测量为榜样,派人在全国范围进行大规模的天文测量。他的建议,获得忽必烈认可,得以实施。
一行组织的天文大地测量的范围很广,北到北纬51 度左右的铁勒回纥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南到约北纬18 度的林邑(今越南的中部)。在这样广大的范围内,一行一共选择了13处测点,对其夏至日影长度和北极出地高度做了测量,规模是空前的。
相比之下,郭守敬主持的“四海测验”,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7个观测点,数量上是一行观测点的二倍还多。观测点的分布东起朝鲜半岛,西至川滇和河西走廊,南到纬度只有15°的南海,北到纬度高达64.1°的北海(今俄罗斯西伯利亚中部通古斯卡河一带),比一行的测量区域更大。“四海测验”的内容之多、地域之广、精度之高、参加人员之众,在我国乃至世界天文学史上都是空前的。
一行的测量有两个目的,一是验证“地隔千里,影差一寸”这一天文学理论是否正确,并进一步考校地中的正确位置,这是继承了刘焯提议的结果;二是测量各测点的夏至影长、北极出地高度等天文学要素,以之编制新的历法。一行之前的历法修订,虽然也重视测量,但那些都是第谷式的测量,是在同一个观测地反复进行的测量,目的是提升测量精度,而一行的跨地区测量,除了刘焯的提议之外,也与一些新的天文发现有关。据《旧唐书·天文志上》记载 :
贞观中,史官所载铁勒、回纥部在薛延陁之北,去京师六千九百里。又有骨利干居回纥北方瀚海之北,草多百药,地出名马,骏者行数百里。北又距大海,昼长而夕短,既日没后,天色正曛,煮一羊胛才熟,而东方已曙。盖近日出入之所云。[9]
在郭守敬的时代,“地隔千里,影差一寸”学说被天文界弃置已久,一行的天文大地测量的第一个动机对郭守敬而言不复存在,能拿到桌面上的理由,只剩下修订历法这一条了。但是,仅仅为了修订历法,哪怕是为了编制“九服晷影”,需要搞这么大规模的“四海测验”吗?27个观测点,有些位于人烟稀少之处,编制好的历法,能颁行到那里吗?
特别是,27个观测点被分成了两类 :南海、衡岳、岳台、和林、铁勒和北海六处,再加上元朝首都大都,这7个观测点是一类,它们的观测项目为“北极出地”、夏至“晷景长”“昼夜长短”三项;其余的20个观测点是另一类,仅“北极出地”一项。对此,厉国青等认为,“当时正是制订授时历的紧张阶段,急需测量一些与制历有关的数据,所以先在有代表性的六个点上测完了上述三项数据。”[10]由厉先生的说法来看,其余20个观测点的观测,对《授时历》的编制没什么用处。确实,单一的“北极出地”数据,对编制和验证历法,能发挥什么作用?
既然大部分观测点的观测都与历法编制无关,郭守敬为什么要组织这么大规模的“四海测验”?其潜在动机究竟是什么?要探究这一问题,需要回顾当时天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在郭守敬之前,元代天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成就是“时差”现象的发现。事情源起于成吉思汗西征时,著名天文学家、政治家耶律楚材随行,按照当时金朝使用的《大明历》的推算,庚辰年(1220)五月要发生月食,于是,耶律楚材等人进行了观测 :
庚辰岁,公在寻斯干城,当五月望,以《大明历》考之,太阴当亏二分,食甚子正,时在宵中。是夜候之,未尽初更而月已蚀矣。盖《大明》之子正,中国之子正也;西域之初更,西域之初更也 :西域之初更未尽时,焉知不为中国之子正乎?隔以万里之远,递迟一时,复何疑哉![11]
寻斯干城即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城。这年五月发生月食,根据《大明历》的推算,月食应发生在半夜,而耶律楚材等在寻斯干城观测的结果,天刚黑不久就月食了。耶律楚材经过分析,认识到《大明历》的推算没有错误,他们在寻斯干城的观测当然也是准确的,这表明寻斯干城的天黑时分跟开封的夜半是同一时刻,由此认识到了时差现象(他称其为“里差”)的存在。
时差现象的存在,是大地为圆球形状的有力证据。虽然耶律楚材接下去并没有提出地球学说,但元代人知道源自西方的地球学说,则是无疑的。《元史·天文志》记载了西域人士扎马鲁丁为元世祖忽必烈所造的西域天文仪器,其中就有一台地球仪 :
世祖至元四年,扎马鲁丁造西域仪象,……苦来亦阿儿子,汉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8],998~999页)
如果说耶律楚材对时差现象的认定,是对地球说的隐晦表达,那么,“苦来亦阿儿子”亦即地球仪的存在,就是元代地球说的实物见证了。郭守敬提出要进行天文大地测量,是至元十六年(1279),而扎马鲁丁造地球仪,则是至元四年(1267),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发现时差现象,更早在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由此,郭守敬对这些天文学成果当有所知。更重要的是,耶律楚材在发现里差现象后,将其引入到他所制定的历法《西征庚午元历》中[12],并将这部历法进献给了成吉思汗;而扎马鲁丁则在至元四年,依据伊斯兰教历法编著《万年历》,由忽必烈颁行天下。郭守敬进行天文大地测量,目的是为了编制新的历法,不可能对上述两部历法视若无睹。实际上,此后郭守敬编制的《授时历》,确实受到了回回天文学的一些影响[13]。综合这些因素来看,郭守敬设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天文大地测量时,一定知道地球观念的存在。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利用这次测量的机会,去检验一下地球说的真伪呢(昼夜长短随地理纬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现象,就是地球学说的旁证之一;北极出地高度与地理距离的线性关系,也是西方地球说的特征之一)?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因为中国人对地平说的笃信是由来已久的,扎马鲁丁虽然造了地球仪,但元代学者中,并未见有中国人肯定地球学说。甚至300多年后,当传教士再度告诉中国人大地是个圆球时,中国学者对之仍然表现了高度的怀疑。由此,当郭守敬得知这样一个完全有悖于传统认识的地球学说时,心生好奇,有意把测量范围尽可能扩大,在满足编制历法的需求的同时,顺便对地球学说做个验证,也不无可能。遗憾的是,验证结果如何,他是否由此确信了地球学说,史料无载,我们不能妄猜。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在其遗留至今的关于天文学的论述中,他从未提及过地球学说。毕竟,这种测量方式的验证,只是一种间接验证,其说服力尚未达到让人闻知即信的程度。
4 从天到地——康熙时期的地图测绘
明朝在天文大地测量方面未有大的举动,但其后期,却发生了一件导致天文大地测量转向的事情——西方传教士来华。
明末传教士来华,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传教士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天主教,也带来了西方科技,其中与天文大地测量有关的有两部分内容 :一是西方几何天文学的传入,包括地球观念的传入;另一是西方地图的引进。
元代人们虽然已经接触到了地球观念,但从元到明,地球观念并未在中国人心目中扎下根来。这种状况,一直到明末清初,传教士把科学的地球观念引入我国,才有了根本的改观。《明史·天文志一》详细介绍了利玛窦引进的地球说的内容 :
其言地圆也,曰地居天中,其体浑圆,与天度相应。中国当赤道之北,故北极常现,南极常隐。南行二百五十里则北极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则北极高一度。东西亦然,亦二百五十里差一度也。以周天度计之,知地之全周为九万里也。[14]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接受地球学说,首先是接受了西方学者对地球说的论证,所谓“南行二百五十里则北极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则北极高一度”,就是地球说的直接证据。正是因为传教士不但引进了地球观念,而且介绍了支持地球说的证据,这才使得一部分中国学者开始承认地球学说,使地球学说得以逐渐在中国立足。
西方地图及其测绘方法的传入,首先表现在世界地图的绘制上。利玛窦于万历十一年(1583)进入肇庆后,发现中国虽然重要地区都有地图,但那些地图都是关于中国本土的,人们更感兴趣的是他携来的世界地图。在肇庆知府王泮的要求下,利玛窦重新绘制了自己带来的世界地图,但对其内容做了改动,把中国的位置移到了靠近中央的位置,同时把有关说明文字改成了中文。出乎他的意料的是,王泮对该地图非常重视,很快就将其翻印多幅,以馈赠高官和友人。这使利玛窦受到启发,意识到向官绅赠送世界地图和其他科技仪器如日晷、地球仪、自鸣钟等,是减少当权者对其传教事业的猜疑的有效手段。
此后利玛窦便不断绘制和改进他的世界地图,并将其进献给有关人士。他摹绘印制的世界地图有十几种之多,名称也多有更改。他最初绘制的地图叫《山海舆地全图》;万历二十九年(1601),他给明神宗进献了一幅绘制在木板上的世界地图,题作《万国图志》;次年,李之藻在北京根据利玛窦的增订重新印制了该图,题名为《坤舆万国全图》;再次年,李应试时又据之刻印了《两仪玄览图》。以世界地图作为礼品敬献当权者,以之打开传教之门,亦成为传教士通行的做法,例如南怀仁亦曾刻印《坤舆全图》献给朝廷。
世界地图的传入,对中国文明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并不等于“天下”,中国人的心扉被一幅世界地图打开了。除了地理知识的增加和眼界的开阔之外,中国人还认识到天文学对地图测绘的重要性,正如南怀仁所言 :
近今二百年来,大西洋诸国名士航海通游天下,周围无所不到,凡各地依历学诸法测天,以定本地经纬度,是以万国地名舆图大备。[15]
南怀仁活跃的时代,是清朝康熙皇帝执政时期。康熙帝在治理国家和抵御外国侵略的过程中,对当时的地图测绘粗略、精度不高、内容不详等状况甚感不满,于是他同意了一些外国传教士的奏请,决定进行全国性的大地测量。
康熙朝的这次大地测量最大特点是采用了西方经纬度法测绘全国地图。测绘工作经历了十余年的准备,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开始,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完成了全国性的大规模地图测绘,其结果即《皇舆全览图》的绘制。《皇舆全览图》采用桑逊投影法绘制[注]本文原写成“梯形”投影。汪前进《康熙铜版《皇舆全览图》投影种类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已经指出该图采用的是“桑逊投影”。感谢审稿人在此问题上的提醒。,描绘范围东北至库页岛,东南至台湾,西南至列城以西,西北至伊犁河,北至北海(贝加尔湖),南至崖州(今海南岛)。测绘人士有耶稣会士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1663~1738)、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杜德美(Pierre Jartoux,1668~1720)及中国学者何国栋、索柱、白映棠、贡额、明安图以及钦天监、理藩院的相关人士等。就其测绘范围、测绘精度等多种因素而言,《皇舆全览图》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一份地图。
就测绘史而言,《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充分利用了传教士传来的西方天文学相关知识,开辟了中国测绘史的新纪元。其最大特点是地球观念引入导致的地理经纬度概念的采用,整个测绘过程中所有方法上的创新,都是围绕着如何精准测定待测地点的地理经纬度这一问题展开的,测量思想的核心是以天体作为测定地理经纬度的依据。《历象考成》曾揭示过这一思想 :
欲明天道之流行,先达地球之圆体。日月星辰,每日出入地平一次,而天下大地,必非同时出入,居东方者先见,居西方者后见,东西相去万八千里,则东方人见日为午正者,西方人见日为卯正也。周天三百六十度,每度当地上二百里,是故推验大地经纬度分,皆与天应。([16],上编卷1,“历理总论·地体”)
这是当时测绘思想的具体表现。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是次测绘在方法上表现了诸多创新,要而言之,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
(1)根据地球地理经度一度弧长来规定测绘用尺的标准
进行地理测绘,首先需要确定测绘用尺,这是不言而喻的。当时清朝立国不久,全国范围内尺度尚未统一,这导致了地图测绘的不准确。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月,康熙皇帝曾针对测绘用尺问题,明确指出 :
上谕大学士等曰,天之一度即地之二百里,但各省地里有以大尺者,有以八寸小尺量者。画地理图稍有不合者,职此故也。([17],卷217,“康熙四十三年八月至十月”)
对此,康熙的解决办法是,规定以地球经度一度弧长为200里的标准来制订测绘用尺。为此,在大规模测绘开始之前数年,他就已经派人预先做了测量。他曾在朝堂上对大臣们明确宣示道 :
天上度数,俱与地之宽大吻合。以周时之尺算之,天上一度即有地下二百五十里;以今时之尺算之,天上一度即有地下二百里。自古以来,绘舆图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数以推算地里之远近,故差误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视之。([17],卷246,“康熙五十年四月至六月”)
所谓“前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视之”,指的是此前康熙已经派人用这种方法,进行了地图测绘的实践。实际上,早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他就已派皇子胤祉率人沿过北京的子午线,测定了霸州(今河北省霸县)至交河之间的每度弧长。在这次测量中,耶稣会士安多发挥了重要作用。[18]正是这次测量,为后来的地图测绘用尺标准的制订提供了基础。
关于康熙以地球经线1度弧长为则制订测绘用尺基准之事,前贤已有论述[注]例如,早在1930年,翁文灏《清初测绘地图考》(《地学杂志》,第18卷第3期)即曾专节论述此事。,这里不再赘叙。但需要指出的是,按照清代长度单位进位关系,1里等于180丈,据此可以推出康熙制订的测绘用尺与现在的长度单位换算关系是1尺等于30.9厘米,但现存清代营造尺的标准长度是32厘米[19]。作为国家标准来说,这样的差距不可谓不大。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个中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2)采用天文观测法测定待测地点的地理纬度
制订了测绘用尺标准之后,接下去就要进行各地的地理经纬度的测量了。在纬度测量方面,情形稍微简单一些,直接观测即可,即观测天北极与地平线之间的夹角,所得即为观测地的纬度。当时人们已经知道北极星与真正的北天极并不重合,《清史稿·时宪三》记载了这种情况下的测量方法 :
测天极高度以定天体。于冬至前后,用仪器测勾陈大星出地之度,酉时此星在北极之上,候其渐转而高,至不复高而止。卯时此星在北极之下,候其渐转而低,至不复低而止。以最高最低之度折中取之,为北极高度。[20]
引文中的“勾陈大星”,即当时的北极星。用这种方法测量,可以保证测得的纬度值达到一定的精度。
除了用天北极高度测定地理纬度之外, 还可利用恒星中天高度测定纬度。具体方法是 :
取恒星之大者,测其最高为若干度。若此星为赤道以南之星,则以其距赤道之纬,与其高相加,得若干,即赤道之高。若此星为赤道以北之星,则以其距赤道之纬,与其高相减,得若干,即赤道之高度。既得赤道之高,与一象限九十度相减,余若干,即北极出地之度也。此法较之前法为少烦,盖因赤道南北之星距赤道之纬,俱系测得北极之高度而后可得,而恒星有岁差,其纬度亦有増损,然存此法,与前法参互考验可也。([16],上编卷4,“日躔历理·北极高度”)
这种方法并不简便,但它可以作为一种备用方法,与前一种方法相互校验,最大程度地减少观测误差。
(3)采用月食经度测量法测定特定待测地点的地理经度
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下,经度的测量相应复杂一些。测绘人员采用的办法是,首先以通过北京的经线作为中央经线,再使用月食经度测量方法测定一些重要地点的经度。《历象考成》论述道 :
测经度,则必于月食取之。盖月食与日食异。日之食限分数,随地不同,月之食限分数,天下皆同,但入限有昼夜,人有见不见耳。此处食甚于子者,处其东三十度,必食甚于丑;处其西三十度,必食甚于亥。是故相去九十度,则此见食于子而彼见食于酉;相去百八十度,则此见食于子而彼当食于午,虽食而不可见矣。([16],上编卷1,“历理总论·地体”)
因为月食发生,天下共睹,但不同地点其当地地方时不同,两地之时差直接决定于其经度差,故可由观测月食直接推算出待测点的经度来。这一方法的理论依据是地球学说。在西方古典天文学中,月食经度测量法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中国人一旦接受了地球学说,在经度测量中使用这种测量方法也就水到渠成,成为理所当然之事。
(4)采用三角测量法测定一般地点的地理经度
由于月食的发生和观测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全国性的地图测绘中,绝大部分测点都难以采用月食经度测量法测定其经度。对此,该次测绘采用的解决办法是,以利用月食经度测量法测定的若干地点为基点,运用三角测量法测算出所有需测地点的经纬度。
所谓三角测量法,基本方法是以已经测定经纬度的若干地点为基点,选择若干可以直接观测的地点构成系列的三角形,用直接测量方法测量其中一条边的长度,然后根据三边之间的夹角及所测得的一边长度,用三角函数方法推算出其余两边的长度。嗣后,再以此为基础,推算出所有三角形各边长度,然后,再根据边长及方位角,推算出各点的经纬度数。
使用三角测量法的必要性及优点,当时参与测量的雷孝思神父曾有详细论述 :
受命作图者皆努力从事。各省重要地方,务必设法亲到,各府州县志书皆加查阅,各处官吏皆经询问,而尤要者在实地测量,用三角法测定地点。盖应测区域,幅员广大,欲从速成图,实以三角测量为最易。若纯用天文测量,则或以时计之错误,或以木星卫星出现观察之错误,即能使经度数目大受影响。例如时间错误一分,则经度即差至十五分,距离即差至四至五“刘”(lieue,法国古里,每度二十刘),视所处纬度而异。
如用三角法,则错误决不至四刘之多。实地测量,距离及角度,均为相当准确。而时计一经远道输送,易有一分之差,如欲更正,非有数日观察不可,必致耽误时日。卫星之观察,不但需时较久,而且须有两处同一远镜,同一观察者,方能比较。如观察者所见先后稍有不同,则所得经度,即不能确定短距离之数目。倘欲确定,仍须用几何学方法,即三角测量是已。
又一方法,可以试验测量之是否准确,即由不同路线回至初测之点,如能相会,即足证明所测无误。如不能回至原点,则另由已经测定之处,遥望测定该地附近之塔顶,或显著之山峰,更不时实测其间之距离。[21]
雷孝思比较了三角法和天文测量方法的优劣,肯定了采用这种方法,测量结果准确,不易有误差,测量过程也快捷。而且,他还提出了检验测量结果准确与否的方法。这些,无疑是富有科学价值的。
康熙时代的地图测绘最大成果是成功编绘了世界测绘史上著名的《皇舆全览图》,此外,它还有一些别的收获。例如,传教士在实测一些经度弧长的时候,意外发现地球经度一度的弧长并不相等,在世界上首次通过实地测量获得地球为椭圆体的实际证据,为牛顿的“地球扁圆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明。[22]
需要指出的是,康熙时期的这次测绘,与一行、郭守敬等的天文大地测量本质上是不同的。唐代和元代的那两次测量,目的是为了天文学的发展,而康熙时代的测量,则是为了绘制地图。在方法上,它标志着传统测绘的现代化,是天文学发展的受惠者。
在康熙时代,也存在为了满足制订历法的需要而进行的测绘,那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的事情 :
辛亥,和硕诚亲王允祉等奏,昔郭守敬修授时历,遣人各省实测日景,故得密合。今修历书,除畅春园及观象台逐日测验外,亦不必各省尽测。惟于里差之尤较著者,如广东、云南、四川、陕西、河南、江南、浙江七省,遣人测量北极高度及日景,则东西南北里差及日天半径,皆有实据。得旨,广东,着何国栋去;云南,着索柱去;四川,着白映棠去;陕西,着贡额去;河南,着那海去;江南,着李英去;浙江,着照海去。([17],卷261,“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
与传教士参与的地图测绘一道进行的这次测量,就其本质而言,也是天文学知识的应用,并非为了天文学本身的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即是说,由于天文学的发展,传统的天文大地测量,至清代已近尾声。此外,乾隆时期也组织了大规模的地图测绘。该次测绘比康熙时期的测绘范围更大,其最终绘制的《乾隆内府舆图》范围比《皇舆全览图》也几乎扩大了一倍,但在测量方法上,基本还是沿用康熙时期的那一套,故此本文不再专门讨论。
中国传统天文大地测量,是古人在其宇宙结构观念驱使下的一种大规模科学实践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古人证伪了传统天文学中的一些错误理论,如“千里差一寸”学说、地中观念等。传统天文大地测量因为有其能够满足历法编纂需求的功能,因此在其最初动机(寻找地中位置)被一行的测量所否证后,仍然能够被元代郭守敬发扬光大。郭守敬的测量在其表面动机和测量行为之间还存在不自洽之处,这意味着他的测量除了具有服务于编制历法这一实用功能之外,还像一行的测量一样,具有某种科学探索的意涵。随着明末清初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天文学被中国天文学家们普遍接受,传统天文大地测量所蕴含的科学探索功能不复存在,这种测量本身也走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古人转而把他们掌握的天文学知识用于地图测绘,使天文学知识在服务社会方面揭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