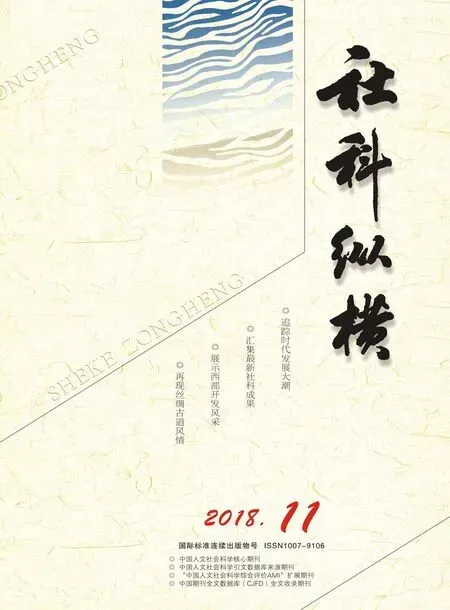为吾有身
——中国传统身体观的基本相态解读
张永飞
(大理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云南 大理 671003)
人人都拥有自己的身体,身体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都可以说“我熟悉自己的身体”。《道德经》记载“为吾有身”,以现象学的立场来看,意味着“我不仅是拥有一个身体,而且我就是我的身体”,也就是将身体还原到了存在本体论的层面——身体是我们生存于世的根本。看似简单的身体现象,无论在西方哲学还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都承载着深刻的哲学命题:古希腊以“认识你自己”作为警世箴言,“身体”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对象;儒家以“修身”作为“积极入世”的起点,“身体”既是实践活动的发起者,又是实践活动的承受者。因此,中国古人所思考的哲学问题,无不与身体相关。以《孝经》为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终于立身”。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传统的价值观里把“身体”视为我们立命处世的根基。在《道德经》中也有“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的论断。“身”,归根结底是我们产生悲喜忧患情感体验的泉源。儒家以“修身”为出发点,齐家治国而达天下治;道家以“养生”为着眼点,寻道悟道而达“天人合一”。儒家和道教看似形态有很大的差异,但“儒道互补”却是中国传统文化既存的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是儒家的“修身”还是道家的“养生”,其终极问题都是对“身”的关注与思考。身体观在一定意义上也就代表了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和宇宙观。对中国传统身体观基本相态的阐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身体主体性
“主体性”是哲学讨论的重要内容,西方哲学深受主客二元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理性至上”和“重客体性”的特征。与此不同,“中国思想的三大主流,即儒释道三教,都重主体性”。[1](P4)刘宗周认为“人合天地万物以为人”。人以身体的形式生存于世,但生命的自然存在尚不能彰显人主体性的全部价值。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界定为“社会性”,儒家哲学从开始也赋予了“身体”以社会的意义。君子奋发有为应对入世,必先“修身”,然后才能逐步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在这里,人主体价值的实现源发自“身体”。反过来,“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主体性的最终实现还是要依赖于反观自身。以儒家思想来看,“身体”是人主体性价值实现的根本载体。儒家主张的修身之“身”,不是仅局限于人的肉身,更是集“形—气—心—性—天”于一体的“身体”。传统儒家理想的身体观应该具备:意识的身体、形躯的身体、自然气化的身体与社会的身体四义……任何一体皆有主体义。[2](P9)当代西方现象学从社会、政治、文化、技术、知觉等维度重构了“身体主体性”,这与中国传统思想所主张的“身体主体性”有殊途同归的微妙。
如何处理“身体主体—身在世界”的关系?与西方思想所主张的“主—客对立”、“主体以客体为对象”不同,中国传统哲学始终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易》的三才思想把人置于天地之中、放在自然之间。人是自由的,但主体的活动以及主体价值的实现,必须要法天敬天、尊重自然。以孔子为例,他曾说“五十而知天命……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所指的“从心欲”并非是毫无约束的放纵,而是始终在“天命”和“天道”所规定“矩”范围内的自由。只有顺应天命,人的自由和实践才不会出错,最终也才能达到“天合地合道和”、“身合己合人和”的和谐状态。因此,古人曰“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身体”已经超越了身心合一的自然主体,被赋予了以生活化、世俗化、社会化乃至宇宙化的意义,这是传统哲学中身体主体所蕴含的丰富内涵。
二、身体整全观
传统的身体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人一种整全的世界观。这种“整全观”与西方的“还原论”不同,后者试图把人主体的活动还原为“物理-化学运动”。整全的身体观不孤立的看待身体问题,它始终把身体放到社会、宇宙的系统中来理解,始终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时刻把人与宇宙相联系。
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人理解人体、社会、自然、宇宙及万物相互关系的基本术语。《易》及其阴阳五行学说反映了中国哲学朴素的整体和合思想,传统身体观受其影响颇深。阴阳互根学说可以用来阐释身与心的关系——身与心互为存在的前提与条件。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中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古人认为宇宙大身体,身体小宇宙。人身不是自然的身躯,而是与天地宇宙互蕴的身体,人身上体现着宇宙的精神——“即身而道在”。“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哲人也运用五行学说来认识和描述身体构成及身体与世界关系。五腑、五脏、五官为身体的五行;五味、五色、五情为身体主体对世界的感知及其结果;五服、五伦、五德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日常规范。正因为身体与宇宙互通,人才能够做到天人感应、天人合一。这样,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身心交融的身体,成就生命的自然美善;安身立命的身体,成就生命的社会价值,天人合一的身体,成就生命的至高境界。传统的伦理道德、建筑审美、书画艺术、中医文化等无不受这种整全观念的影响。
三、身心一如论
身心二元论在西方文化中带有普遍性,自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就认为“理性灵魂独立于肉体”,且在身体和心灵的二元中,价值的天平明显的倾向于“心灵”一端。“身体”被定义为肉体与躯壳、它是“灵魂的坟墓”和“原罪”的根源。被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引导,社会发展往往容易走向极端:中世纪“禁欲主义”和现代社会“身体消费主义”。
与西方身体观不同,中国传统思想主张身与心的“浑然一体性”,即“身是心之身,心乃身之心”。传统典籍中有较多从“修身论”或“心性论”等不同角度阐述生命本意与价值的论著,但它们总是有共同的特点——论身必论心,言心必言身。中国古人怎样看待身与心的关系?王阳明认为“何谓身?心之形体运用之谓也。何谓心?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也就是说,身与心是人生命的一体二面,它们相为依存,且身与心之间,不存在着孰轻孰重的问题。在身心关系的认识上,中国传统哲学更倾向于身心一如的一元论。
同时,先哲亦承认身与心是有分别的,但这种分别不是二元对立,而是生命主体的“一体两面”。《易》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可以为“一体二面论”提供解释的依据。“道”分阴阳,阴阳有别,但两极共生,阴与阳互为必要条件以维系两极的存在。阴阳互根学说可以进一步用来解释身与心的关系,“儒家的心性论与身体观乃是一体的两面……身体体现了心性,心性形著了身体”[2](P1)。在儒学经典中,可以较容易找到诸多关于“身”的论述,如:“吾日三省吾身”、“一朝之忿,忘其身”、“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等等。传统哲学用“身”表达了人身心一体的整全生命状态,“修身”是立命处世之根本,“身心合一”为修身之要义。
三、身体认知论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古人对自身及对世界的认识,首先是从对身体的认识与表达开始的。“体知”是直觉之知。象形文字的发明与使用能够说明这一特点。以“立”字为例,甲骨文写为“”,小篆写为“”。可以看出,早期象形文字既是文字符号,也是图形图像。它们具有直观、形象、写实的特征,望文不一定知读音,但望文可推知其义。人类知识最原初的感知与表达,必然是一种基于身体性的直觉感知与表达。不仅如此,古人也使用身体隐喻对社会关系进行阐述。如“一国之君,其犹一体之心也……任群臣无所亲,若四肢之各有职也;内有四辅,若心之有肝肺脾肾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体孔窍也”。董仲舒用身体各部分密不可分的关系来隐喻君、臣、辅、官之间同生共存、相互依赖的紧密关系。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身体”是中国古人概念系统的核心。
“体知”是悟性之知。身体具备悟道参禅的能力,身体同时又是悟道参禅的对象。先贤哲人通过身体的参悟,可以参透自然之道。老子“涤除玄览”、王阳明“龙场悟道”、黄帝内经“慧然独悟”、禅宗“静心悟道”等,无一不是强调通过“以身悟道”而达“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自然自在境界。
“体知”是实践之知。“体”除了做名词特指“身体”外,也可作动词理解,意为“亲身经历”。以“庖丁解牛”为例,他能够做到“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经过了反反复复的亲身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身体经验,然后才逐渐参悟了“道”,进而做事出神入化。《卖油翁》典故中“无他,惟手熟尔”一语中的:只有身体的感知、亲身的练习和实践,才能够让人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因此,体知不是仅凭借着直觉和悟性在意识层面实现的,它更要需要人在社会实践来完成。
对传统身体观基本相态的分析与讨论,有助于进一步挖掘和发现“身体”所蕴涵的丰富而又独特的哲学思想,其价值在于:其一,重拾了身体的生命本体和主体意识,以关照身体性来关照生命的整全性意义;其二,在身体研究中,寻找相关研究的中国文化根源,避免唯西方意识。将传统精神与现代文化精神相融通,在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中,增强我们文化自信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