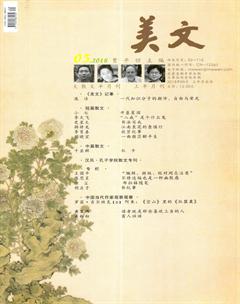布拉格随笔
洁尘 作家。现居成都。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先后供职于媒体和出版社。已出版有《华丽转身》《提笔就老》《生活就是秘密》《一朵深渊色》《啤酒和鲈鱼》《酒红冰蓝》《中毒》《锦瑟无端》等随笔和小说三十余部作品。
查理大桥上的赫拉巴尔
到布拉格,对于我来说,最关键的那个人名不是哈谢克,不是哈维尔,不是塞弗尔特,也不是米兰·昆德拉,甚至不是卡夫卡。是赫拉巴尔。
好几年前,读过苗炜的一篇文章,说他在布拉格的一家书店,站着把赫拉巴尔书中的黄段子翻了一个遍(这些黄段子在中文版里被删了),然后,跟着书店大妈去一个烟熏火燎的酒馆,见到了赫拉巴尔和哈谢克,跟他们聊了聊足球;后来在桥边(应该是查理大桥吧)还看到了卡夫卡的背影,差点上去打招呼,却被90公斤重的书店大妈死死抱住不得动弹,桥边,乌鸦嘎嘎嘎地飞起来。这篇文章写得有趣,有苗炜一贯地那股邪劲。作家通过想象,虚构一下与自己心仪已久的作家见面的场景,这是真爱。
我没想象过与赫拉巴尔相遇。我的想法比较文艺婉约——带上一本赫拉巴尔的书,让书跟布拉格合影。
那是中文版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底层的珍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我有赫拉巴尔好些书的中文版,带上这本,是因为它最小最薄。旅途中,能轻便则轻便,这本书我还要带回家的。
把这本书跟布拉格的什么景色合影呢。赫拉巴尔生前常去的金虎酒吧吗?最合适的地点应该是那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找去。这是我第一次到布拉格,完全不辨東南西北,何况,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看过龙冬写给赫拉巴尔的那篇长文,知道金虎酒吧应该就在查理大桥附近。好吧,那就查理大桥吧。桥边还有卡夫卡博物馆。我也爱卡夫卡呢。
在欧洲最古老最长的查理大桥上,我把带去的这本赫拉巴尔中文版小说摆在了桥栏上,对着伏尔塔瓦河水,拍下了照片,向赫拉巴尔致敬。那天是2014年10月12日,早起,查理大桥上笼罩着一层薄雾,十点左右,薄雾散开,阳光通过两端的桥塔。哗啦一下穿刺下来,整个查理大桥上下一片金黄。我一下子就蒙了,金黄色!是啊,黄金之城布拉格,这就是一座金黄色的城市!就是老黄金的颜色!金得无比沉着。怎么能就这样跟想象完全吻合了呢?!想象和现实怎么能够这样毫无分别?!我实在是恍惚,一瞬间心乱如麻。晕晕乎乎,跟喝高了似的。怪不得到了布拉格的人,说起这座城市都那么痴狂。
我拍的那幅照片凝固了这样的景象:
石桥栏很厚,中间凸起。这种灰色的石头就是传说中加了鸡蛋清的波希米亚砂岩吧!它们让查理大桥坚不可摧。查理大桥的奠基时间是1357年9月7日5点31分,按当地的书写习惯,写成135797531:这串数字成了一个回文,正念反念都一样,包含着人们对查理大桥不朽的祈福。查理大桥也的确回应了人们的心愿,六百多年来安然无恙。
《过于喧嚣的孤独》摆在桥栏上面,向着湛蓝的天空,向着灰绿的河水,向着远处红顶黄墙的布拉格的老房子,有尖顶和穹顶时不时地冒出来,建筑轮廓线十分优美;伏尔塔瓦河上,两艘绿白相间的游轮成掎角之势远远驶过来,正准备穿桥而过,涟漪荡漾,绿绸起皱……封面上,黑白的赫拉巴尔用手支着脑袋,正严肃地看着前方,谢顶的大脑门上沟壑丛生,鬓角斑白。不知道这张照片的他是多少岁?
对于一个习惯于从书本上抬起头再去观望世界的人,曾经热爱过的作家已然进入了血液之中,一旦身临其境,昔日被滋养过的那种感恩之念,就会像味觉记忆一样的清晰且顽固。这种感觉,在国内有过很多体验,在国外,也许是因为千山万水的距离给发了酵,体验似乎更为强烈。内罗毕与卡伦·布里克森,伊斯坦布尔与帕慕克,巴黎和杜拉斯,京都与三岛由纪夫。奈良与松尾芭蕉……现在,在布拉格,是赫拉巴尔。我的眼睛和嘴里都有酸涩的味道,岁月跌宕中内心艰难成长时的那种酸涩。人是怎么长大的啊?多辛苦,多努力,多幸运啊!
看着桥栏上的赫拉巴尔,我想,他给了我什么?是捷克文学传统核心的波西米亚气质,是生命的粗粝、忧惧、绝望和狂欢,是不被理解的骄傲,是琐碎的尊严和阴影中的层次与质感。我读赫拉巴尔的时候。84岁的他早在1997年2月3日从医院五楼坠落离世。
阳光中,查理大桥上的赫拉巴尔肖像成了黄金,那一刻,我在心里对他说,先生,我来到了您的城市!谢谢您!
布拉格广场的“国王”和鹦鹉
布拉格最热闹的地方是旧城广场,也叫老城广场,外人喜欢叫布拉格广场。我是外人,也喜欢布拉格广场这个说法。
广场上,有各种堪称绚丽的广场艺人。也许是波西米亚根据地的原因,这里的广场艺人有一种特别的鲜艳和古怪。在波西米亚服装的样式元素中,刺绣、流苏、褶皱、大摆裙、平底软皮靴等等,跟这里的气氛特别搭,而在波西米亚风格的基本颜色中,暗灰、深蓝、黑色、橘色、正红、玫瑰红,还有著名的“玫瑰灰”等等,混杂在周围的哥特建筑和巴洛克建筑以及奇妙的金色光线中,隐没又显眼,芜杂且抽象,既像油画一样厚重,又如天空一般单纯。
各种广场艺人中,我首先盯住了那个“国王”和他的鹦鹉们。
在横杆上一排金刚大鹦鹉的陪伴下,“国王”着白色长袍,束金色腰带,系曳地的金色披风,箍金色头冠,戴着白色手套的左手上站着一只白色鹦鹉,他面对我,右手抬起,面带微笑,背后是双塔耸立的汰翁教堂……我的镜头定格了这个画面。作为一个广场艺人,他的那身行头其实相当简陋和廉价,但在照片中。简陋和廉价的因素全然被过滤了,呈现了颇具古风的某种华贵和神秘。
当天,我把这张照片发到了微信朋友圈,命名为“布拉格广场,鹦鹉王子”。有朋友在下面留言,此人怎么那么像丹尼尔·戴·刘易斯呢。仔细一看一想,真是耶。再看再想,可以说酷似。这么像刘易斯,那“王子”的称谓就轻了,叫他“国王”吧。
说起来有一种牵强的缘分。我对布拉格较为具象的了解是通过书——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和影像——该小说改编电影《布拉格之恋》。《布拉格之恋》的男主角就是丹尼尔·戴·刘易斯。刘易斯是作为布拉格这个城市的某种形象进入我的阅读记忆中,居然,在我第一次来到布拉格的时候。迎面“遇到”刘易斯。
说是应该早些年到布拉格。但能有多早呢?作为中欧的中心城市。它历来就是焦点城市之一。尼采曾说,说到音乐,他想到维也纳,说到神秘,他想到布拉格。
现在的布拉格,已经是全球旅游热点城市了,人流量可能比不上巴黎,但据说跟西欧和南欧主要旅游城市相比也差不多了。吸引全世界游人的关键因素除了布拉格这个城市特有的美貌之外。漫长的历史、曾经的世界中心地位、波西米亚风味、神秘感觉、两种意识形态的占据和由此造成的对峙和变革……使得布拉格拥有一种特别的丰厚滋味。
之前看过很多布拉格的照片,雾气和阳光锻造出一个金色的城市。待我实际来到布拉格时,我发现,从色彩感觉来说,如果说布拉格是黄铜色,似乎更合适。不过,金子和布拉格的分量更为匹配,蒙了些微銹迹的金子,就是布拉格。
布拉格广场那个区域,包括查理大桥,人真是多啊。我们的导游罗先生说,东欧其他国家的旅游有旺季和淡季之分,比如我们已经离开的波兰,很快就会入冬,游客就相当少了;但布拉格没有旺季和淡季的区别,一年四季每一天。布拉格的这个区域都是这么多人。
布拉格广场上人最多的地方是天文钟的下面,人们簇拥在那里,等着报时的钟声。天文钟十分精美,但背后的故事十分悲惨。1410年,当天文钟完工后,执政者为了不让设计师造出比这更好的钟,派人弄瞎了他的眼睛,悲愤的设计师跳进了自己设计的天文钟里,以身殉钟。我也目睹了天文钟的一次整点报时,钟面下面的十二门徒木偶轮流出来转一圈,同时,旁边的死神牵动铜铃,最后以雄鸡呜叫结束报时。在钟下刚一转身,遇到了一个贩卖劣质手镯的老头儿,他说他是塞尔维亚人,嬉皮笑脸缠着我买,说他很穷,我说我也很穷,他笑得更开心了,还嘟起嘴想在我脸上亲一口,我赶紧把他推开。
从早晨到近晚,我们一直在布拉格广场和查理大桥两边来回穿梭游逛。一会儿,身背一个同等身量的木头偶人的餐馆招领人走过来塞一张广告单,一会儿遇到正在闭目悬浮的杂耍艺人横在路中间,静静看一会儿,在小盒里扔下两个小钱绕道而过……此刻,查理大桥青蓝色的雾气已经完全散去,金色阳光笼罩着一切,桥上很多摆摊的艺术家,画肖像或者卖手工制品,都在逆光中成了虚蒙蒙的人影。那支塞尔维亚四人铜管乐队继续在演奏着,乐声让人想起库斯图里卡的电影配乐。穿梭累了,干脆在桥上那个小提琴手的身边坐下,我摘下帽子,放在面前,对同行闺蜜、艺术家苗苗说,你觉得有没有人把钱放到里面?小提琴手朝我们做鬼脸,又拉起了《YOU RAISE ME UP》,拉着拉着,突然停下,朝着他的CD摊位一扭屁股。嘴里配合一声“噗”,然后在周围人的笑声中十分得意地抽抽鼻子。我对苗苗说,这家伙长得好像憨豆,我要买他一张CD。我买了,十欧。他搂着我照了一张相,又翻开CD封面,给我讲他灌的这张CD里面还有哪些名曲,说,你看你看,有《YOU RAISE ME UP》哦。
查理大桥和布拉格广场都太迷幻了,两边由几个曲折穿梭的小巷连成一片,中间有一个著名的12秒绿灯街口。绿灯亮起,只有12秒,行人必须快速通过,否则可能被开得飞快地布拉格的汽车给撞到。为什么只有12秒?也不知道。
记不得来回了几次12秒路口。每次回到广场,“国王”还是那样,跟他的鹦鹉们站在一起,不知道表演什么。也许他的表演就是这样站着,在阳光下炫目。日光开始倾斜,我们等不到“国王”取下头冠。在我的想象中,“国王”会在火烧云的夕照中,取下他的头冠,让长长的头发披散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