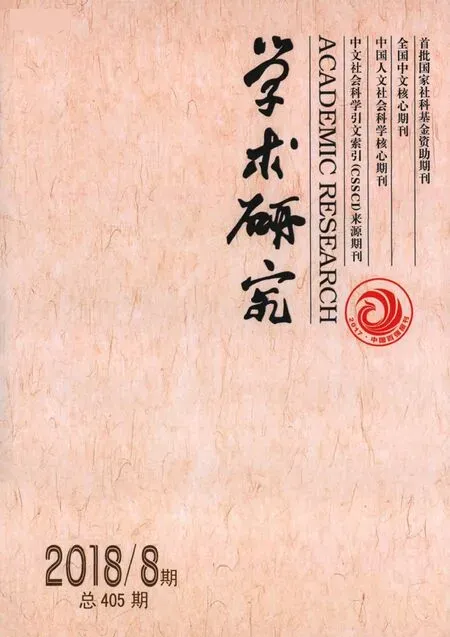疆界·意境·境外之境
——王国维境界说访谈录
宋湘绮 施议对
一、 问题的提出:理论的误判及误区的困惑
宋湘绮(以下简称宋):一直以来,您对于当代诗词创作及理论研究都比较关注,也曾指出过存在的问题。在一篇文章中,您曾说:“有关理论上的失误,则须从王国维说起。王国维发表《人间词话》,倡导境界说,开创新词学,功不可没。但所立论,于意与境之间较偏重于意,已经向左倾斜。其后,胡适、胡云翼进一步加码,促使其左转,并将其推演为风格论。”这里所说理论失误,既包括后来者的失误,也包括王国维自身的失误。今天的访谈,首先想请您说说这一失误的表现及根源。
施议对(以下简称施):我的这篇文章,题称:《立足文本,走出误区——新世纪词学研究之我见》。a施议对:《立足文本,走出误区──新世纪词学研究之我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论说误区问题,谓重思想、轻艺术,重艳科、轻声学,包括重豪放、轻婉约,诸多偏向,造成许多论述只是在词体的外部做文章,只是赞赏其美与不美,而忽略其怎么样才能达至于美。至于误区之所以误者,后来者的失误,诸如胡适、胡云翼的推演,将境界说演变为风格论,即将“词以境界为最上”,演变为“词以豪放为最上”。此外,王国维自身之所立论,也有其偏颇之处,他有关意和境的论述,大多偏重于意。这就是一种左的倾向。
宋:重思想、轻艺术,重艳科、轻声学,包括重豪放、轻婉约,诸多偏向,表明王国维境界说研究已陷入误区。这一问题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施:有关重豪放、轻婉约的偏向问题,子臧先生(吴世昌)在世之时曾为文进行批判,先生身后我也曾将这一偏向当作词学误区出现的原因之一而提出讨论。2003 年9月21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所作题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关于二十一世纪中国词学学的建造问题》的演讲,再次提出这一问题。讲演的文字稿后来发表在《新文学》第4辑。2005年《叶嘉莹教授八十华诞暨国际词学研讨会纪念文集》出版,也收入这篇文章。这次演讲,提出两个问题。其一云:“相对于本色论,境界说之作为现代化的一种批评模式,已经有了更大的可操作性。这是境界说优胜于本色论的地方。但是,由于王国维学说自身所产生的误导以及读者理解上的问题,在很短时间内,境界说即被异化。先由境界异化为意境,再异化为风格论。这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一方面,王所说意境,在三个步骤,三个层面之间,原来就是一种过渡,其与此前之疆界以及此后之境界,并无明确分野,易于给人造成误会;另一方面,由于大家的理解,只到第一、第二两个层面,未到第三层面,只是将境界二字当名词看待,就概念及其内涵大做文章,亦即只是停留于境内,而未能到达境外。两个方面,双向进行;先天与后天,都大大加速其异化。”其二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适、胡云翼相继推演,从意境之有意与境之区别,说到男性、女性以及豪放与婉约,将境界说异化为风格论。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其间,前苏联的反映论,作为马列经典传播中华,亦进一步为境界说的异化提供理论依据。尤其是五十年代之后,反映论占据主导地位,境界说则遭到误判,被当做推广工具。论者说境界,多将物与我阐释为主客观关系。物为客体,我为主体。主观与客观,情与景,二者互不相容。词界讲风格,不讲境界,风格论被推向绝顶。以豪放、婉约‘二分法’,替代三个层面的境界分析,半个世纪以来,境界说基本上都跑到哲学、美学那里去了。”a施议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关于二十一世纪中国词学学的建造问题》,《新文学》第4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宋:境界说讨论陷入误区数十年,与中国当代认识论美学的误判应有一定关系。20世纪50—60年代和70年代末,两次美学问题的讨论,都在认识论的框架里。80年代之后,反思中国当代美学的困境,暴露了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局限:一是把人与世界分成两块,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二是把人与世界从生生不息的“生成之流”中抽离出来,把人与世界看成各自“现成”的主体和客体,忽视了人与世界在关系中“互相生成”的过程。所以,王国维所拈出境界二字一直被当作概念、范畴,作为认识的对象被研究,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没有与诗词创作实践和人的生存发展挂起钩来,即“只是赞赏其美与不美,而忽略其怎么样才能达至于美”这一问题。
施:境界说讨论中的误区和当代认识论美学所曾出现的误判,二者之误究竟有何牵连,这一问题尚须作专门研究。如只就词的一方考虑,我以为境界说误区之误,包括境界说自身所产生的误导以及读者理解上的失误,既是个认识问题,也是个学风问题。认识上的问题,是将意和境的关系简单化,以主客观的对立与协调,替代对于艺术创作中言与意以及意与境之间所呈现内外、远近的分析与综合;学风问题,主要体现是趋易避难,只是在表层意义上作感发与联想,而不愿意就文体自身作深入的探讨。例如词学史上有关词与乐问题的探讨,一千年当中,以沈括、朱熹为代表的和声说或泛声说,令一代代倚声家忙个不亦乐乎;但一百年来,王国维的境界说一出,直是说词,乐就被抛置一旁。
从大的范围看,千年词学代表中国倚声填词之正,百年词学代表中国倚声填词之变。倚声填词之正,声学与艳科,虽有所偏重,却无所偏废;倚声填词之变,只重艳科,废弃声学。1908年,王国维发表《人间词话》,提出境界说,开辟中国今词学。此后将近一百年,历经开拓期(1908—1918)、创造期(1919—1948)、蜕变期(1949—1995)三个发展演变时期,境界说的遭遇并不顺当。
在世纪词学的开拓期,境界说的出现尽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尚未引起学界注视,不曾展开讨论。世纪词学进入创造期,词界左、中、右三翼,对于境界说,各自持以不同的立场与态度。胡适、胡云翼,站在左的立场上,将境界说推演为风格论;唐圭璋、吴征铸,或谓其未能会通,或谓其自相矛盾,乃从右的立场,提出批评意见。左和右两翼,对于王国维境界说都并非积极的推动。此外,顾随另行提出高致一说,作为境界的补充,缪钺从词体特性以及文体的嬗变角度阐释境界说,属于一种改造与充实。从总的趋势看,世纪词学创造期的三十年,胡适、胡云翼的推演,为境界说异化的开始;顾随、缪钺的阐释,为境界说的再造作准备;实际上,词界所通行,仍然是传统本色论。
20世纪后半叶,世纪词学进入蜕变期,大致经历三个阶段:批判继承阶段(1949—1965)、再评价阶段(1976—1984)、反思探索阶段(1985—1995)。第一个阶段,秉承批判地继承及古为今用原则,重豪放、轻婉约进一步发展为以政治批判替代艺术研究,由境界说推演而成的风格论成为唯一的批评模式;第二个阶段,将上一个阶段的褒扬与贬斥掉转过来,为原来被轻视的婉约派翻案,但换汤不换药,其所用批评模式仍旧是自己所否定的豪放、婉约“二分法”,风格论仍然一统天下;第三个阶段,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一方面是经过美学阐释、文化阐释,由境界说推演而成的风格论被推向顶峰,一方面是经过推本溯源、要终原始,被风格论推演而异化的境界说,得以回归与再造。
以上是世纪词学所经历的三个时期——开拓期、创造期、蜕变期以及第三个时期的三个阶段——批判继承阶段、再评价阶段、反思探索阶段。三个时期,自1908年到1995年,中国今词学经历了生、住、易、灭的全过程。1995年,蜕变期结束,所谓在烈火中重生,中国今词学进入新的开拓期。此时,王国维境界说之被异化、被再造,又回归王国维。不过,此时的境界说,是否仍然是王国维的境界说,王国维的后来者是否已经从误区中走了出来,仍须仔细加以检讨。
二、 论题的确立:疆界、意境、境外之境三层意涵的辩证
宋:您以疆界、意境、境外之境三层意涵论境界,由形下层面上升至形上层面,在哲学高度上,认识境界说,运用境界说。境外之境的提出,已到达创造论、存在论的层面,而并非停留在认识论的层面。但有关讨论,大多只是将境界当作一个词语,只是留意其作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非作批评模式看,是不是缺乏在形上部分的开拓?缺乏对人的理想生存状态的关照?
施:作为词语的境界与作为名词的境界,二者并不相同。作为词语的境界,是一个概念,有一定的内涵与外延,属于语文范畴问题;作为名词的境界,是一个模式,有一定时空范围及容量,属于韵文范畴问题。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境界,是作为批评模式而拈出的境界。其谓:“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这则词话在《人间词话》手稿列居第四十一,于初刊本所发表六十四则中居第一。从排列位置上看,王国维应是有意识这么做的。但是,后来的研究者大多只是将境界当一般词语看,如将其与佛经中的境界相比对,不知什么时候令其成为一种批评模式,即于境界二字加上个说字成为境界说?我觉得,将境界说当作批评模式看待,是认识上的一种飞跃。因为有了境界说,以王国维为界限,其前其后,泾渭分明,词学研究整个方面的问题似乎都解决了。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我带着这一观念前赴北美参加词学讨论会,我说“境界是一个容器”,其大小深浅皆可丈量,与其前本色论大为不同。与会者听了大吃一惊,但都表示赞同。
宋:叶嘉莹先生也曾多次谈到境界和境界说问题,她说:“我以为王氏在《人间词话》中所标举的‘境界’之说,其义界之所指盖可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范畴。其一是作为泛指诗词之内容意境而言之辞,如《词话·附录》第十六则所提出的‘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及《词话·删稿》第十四则所提出的‘“西风吹渭水,落日满长安”,美成以之入词,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者也。’若此之类,便都是对内容意境的一般泛指之辞,此其一;其二是作为兼指诗与词的一般衡量准则而言之辞,如《词话》第八则所提出的‘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他所举引的前二则例证是杜甫的诗句,而后二则例证则是秦观的词句,可见他提出的境界之大小优劣之说,自然应该乃兼指诗词之衡量准则而言的,此其二;其三则是将‘境界’二字作为专指评词之一种特殊标准而言之辞,即如他在自己亲手编订的发表于《国粹学报》的第六十四则《人间词话》中,所首先提出的第一则词话,就是‘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从这段话来看,其‘境界’一词自然应该乃是专指他自己所体认的词的一种特质而言,此其三。”a叶嘉莹:《清词丛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9-300页。叶嘉莹先生认为,王国维境界说重视诗歌的兴发感动之作用,就内容意境而言,偏重在所引发之感受在作品中的具体呈现,认为境界说是一种评价标准?
施:叶嘉莹先生阐释王国维的境界说,谓“其义界之所指盖可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范畴”,即:其一是作为泛指诗词之内容意境而言之辞;其二是作为兼指诗与词的一般衡量准则而言之辞;其三则是将“境界”二字作为专指评词之一种特殊标准而言之辞。泛指、兼指、专指,修饰词以外,三个不同层次的中心词都是“而言之辞”。三个层次从横的方向展开,着重说其运用,亦即结果,条理清晰,但对于境界自身究竟为何物,除“而言之辞”外,应尚未可得知。
宋:对于王国维所标举“境界”之说,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演讲中曾说:叶嘉莹先生的探测,颇有创意。但以为叶嘉莹先生着重说结果,未及过程。您另从纵的方向说境界,以为王国维“境界”之说的理论创造,亦可以下列三个层面加以表述:
一、拈出疆界,以借壳上市,为新说立本;
二、引进改造,将意境并列,使之中国化;
三、联想贯通,于境外造境,为新说示范。
您以疆界、意境、境外之境三种意涵解读王国维的境界说,精辟独到,希望有机会再听听您的演说。
施:境界说的三层意涵,既表示王国维所拈出境界二字究竟为何物,亦包涵王国维境界之说到底是怎么创造出来的。依据三层意涵的推进,我以为,王国维创造境界之说大致依以下三步进行。第一步,拈出以立本。先说一个境字,将境界解释为疆界,再将其引申为容器,为载体,谓其有长、宽、高,可以测量,可以用现代语言加以表述。第二步,引进与改造。主要说意和境的创造。意即欲,境即时间和空间加上时空里面的人和事。但是,王国维所讲的欲是叔本华所讲的欲。叔本华所讲的欲和中国人的欲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欲是七情六欲的欲,是欲壑难填的欲,叔本华的欲是一种意志,代表社会发展的动力。王国维将叔本华的欲中国化,将其放入境这一载体就变成意境。第三步,联想与贯通。通过此物与彼物,将境内与境外连接在一起。例如,雕栏玉砌,在境之内,都看得到;春花秋月,在境之外,不一定都看得到。这就是存在于境之内与境之外的二物。所谓联想与贯通,用王国维的话讲就是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其时,其另构新境,就是境外之境。这应当就是王国维立论的原意。
宋:您以疆界、意境、境外之境三种意涵解读王国维的境界说,三种意涵的描述,对于认识论到实践存在论的理论提升很有启发。第一,说境界是一个疆界,是可以测量的,即指可以用文学批评的标准,用科学的现代话语对作品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做出客观的评价。第二,说境界是意境,是时间和空间加上时空里面的人和事,以实践存在论的生成观看,人生境界永无止境,诗词创作一步一步走在人生境界的攀登之路上。第三,说境界是境外之境,王国维所说境界,在境之外,而非在境之内。历时百年,数千篇论文的研讨中,将意境、境界混为一谈,这是诗词认识论研究本身跨越不了的方法局限。您境外之境的解读,不仅把王国维吸收叔本华的意即欲理解透彻,反思到欲是个人成长、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且吸纳了马克思的现实观和实践论,以及海德格尔的“在时间中存在”的精髓,不仅回答了“美还是不美”、“有多美”,而且解决了“怎么样才能达至于美”,说清了创造境界的过程,这个批评模式无法回避的问题。
施:由疆界、意境,到境外之境,既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就王国维的立论原意看,诗歌创作的四个可以,其所谓兴、观、群、怨,四个方面之是否能够达至境外之境这一目标,主要看其如何处理物与我的关系以及古与今的关系。用太史公的话讲,就是能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此,考虑境外之境的理论创造问题,亦当立足于此。
三 、境外之境:从认识论到实践存在论的提升
宋:实践存在论美学认为,人生在世是一个生成的过程;人性也是一步一步生成的。抒情、言志,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生产。境界与人的实践存在相关联。在您看来,从认识论误区走向实践存在论的境界说,在理论创造及方法运用上有何特别之处?
施:王国维境界说之所谓境界,无论将其看作疆界,看作意境,还是将其看作境外之境,其中都有个空间范围在。这一空间范围,由一定的长、宽、高的限度,可以测量,并可以用现代的语言,用现代的方法加以表述。这既是境界说之作为一种批评模式所具备的特征,也是境界说可操作性的体现。比如,意境的创造问题,多年前我所撰《论“意+境=意境”》a施议对:《论“意+境=意境”》,《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一文,就以“意+境=意境”这一算术公式展开话题。1+1=2。固然为着向某些满纸空话的高头讲章挑战,而意境的创造本身,其具体过程,实际上亦可以通过算术的方法加以推进。这一问题说明,所谓理论创造,除了原理的标榜,还须提供方法及其运用。
宋:当代诗词审美学将诗词之美置于现实关系之中,主客一体。境外之境的标举,从文本研究提升到文化诗学、乃至哲学诗学的研究,打开文学—文化阐释的空间,或将开辟新世纪诗学研究的新视野。
施:境外之境,相对于境内之境,由于层面不同,创造方法亦有所区别。只就上与下的关系看,其区别在其所指是个别行为还是一般现象,是属于形下层面还是形上层面。而就古与今的关系看,其区别则在于用政治家之眼观物还是用诗人之眼观物,是域于一人一事还是通古今而观之。但二者的关键,仍看其能不能将界限打通。例如李白与杜甫,一个是天上谪仙人,在天上;一个是乾坤一腐儒,在地上。一个在庙堂思考问题,不在庙堂也思考问题;一个在庙堂不思考问题,不在庙堂才思考问题。其层面分别,十分明显。苏轼与辛弃疾亦然。苏轼《永遇乐》夜宿燕子楼,梦盼盼。给一片树叶惊醒。醒了以后,小园行遍,开始思考问题。首先想到张建封和关盼盼,为其浩叹;然后想到自己,想到眼下许多人;最后,想到大家为他浩叹。表层意思是“燕子楼空,佳人何在”。深层意思是“古今如梦,何曾梦觉”。至于作者自己,显然已抽离于梦境之外。这就是苏轼。而辛弃疾《永遇乐》,于京口北固亭怀古,回顾四十三年事,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却仍然是,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始终抽离不了梦境。所谓天上、人间,同样有着明显的区别。
宋:目前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缺乏能够一语道破的文章。抒情言志,是笼统之说。追根究底,情志之根在人性。如果把情感表现理解为传统诗词创造理想人性的方式的话,诗词艺术发展到今天,应该有更高级的理性和感性认识的结合,即创造。人性,是生成的,不是现成的。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原稿中所说:“自然中之物,相互关系,相互限制,故不能有完全之美。然其写之于文学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b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页。遗其关系、限制处就是一种“境外之境”的创造方法,“材料必求之于自然”、构造“必从自然之法则”,都是言说“创造境界”的材料、原则。从境内材料、法则出发,虚构出境外的“理想”,则是境界说作为批评模式的关键:不仅给出了目标,还给出了实现目标的方法。使得“境界”说从认识对象,变成与人的实践存在相关的创造目标和方法。艺术的时代性就体现在创造出“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中,或者说通过作品中艺术形象的实践存在状态(意境),写出该时代的理想人性——“合乎自然,邻于理想”。作者有什么样的人生境界,就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意境;作者每一部作品中的意境是其一生境界成长的“足迹”。这种开放的、动态的、生成的境界观,与马克思开放的、动态的、生成的现实观,以及海德格尔所说的“在起来”,有深刻的一致性。您揭示出“境外之境”,不仅是理论上的突破,而且对当代诗词创作和理论研究,乃至文化创新和当代文论中国式话语体系的建构,都有一定的影响,有效实现了传统文论与西方哲学实践论、存在论,以及当代美学实践存在论的融通。就“境外之境”的创造问题,怎样才能达到极简的表述?能否归纳出一个公式?希望您能有好的建议。
施:境外之境的创造,其方法与途径,如用中国式的表述,就是太史公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句话,既表示一种追求目标,亦揭示实现目标的方法与门径。目标一个,在于成一家之言;方法与门径有二:一为打通天人界限,二为打通古今界限。
例如,李煜《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首词究竟如何解读?上世纪出版两种词总集,一曰《婉约词》,一曰《豪放词》。编者不同,但都收录这首词。主婉约者,谓其凄婉感怆;主豪放者,谓其悲壮刚健。以风格论说词,没有明确的标准,说了等于没说。可见,豪放、婉约“二分法”,无助于学词与词学。以下,试以太史公语,略作分析,看看李煜这首词所造境外之境究竟为何?讲堂上,我曾多次解读这首词。我问学生: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往事者为何?答曰:故国。曰:非也。曰:雕栏玉砌。曰:亦非也。那么,往事究竟为何?曰:春花秋月。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曾特地画了个图,加以展示。图中将雕阑玉砌与春花秋月对举,一个在地,一个在天,构成一组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的二元对立单位;再将小楼和风月,用作二者之间之中介。表示:藉此中介,将人间与天上,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且因为这一联系,进而推知:所谓往事,并非不堪回首之故国,亦非依然存在的雕阑玉砌;而乃春花秋月,亦即有如春花秋月一般美好的事物。理解得到这一层意思,方才到达王国维所造境外之境。这是借用太史语,以打通天人界限的方法对境外之境的解读。有同好者,不妨一试。详情请参阅下图:

——评陈水云教授新著《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