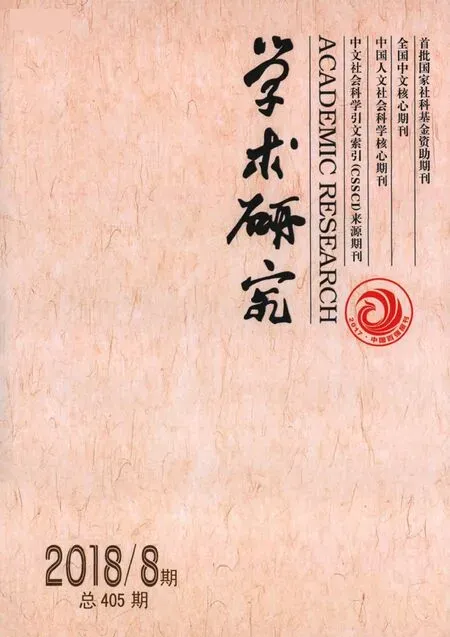为什么是严歌苓
——关于严歌苓小说改编热的反思*
陈林侠
一、从一个误解开始
严歌苓早在1981年就与电影结缘(创作剧本《心弦》以及担当该片的编剧),1988年作为联合编剧参与韩三平、周历执导的《避难》。作品被改编则是从1995年由李安监制、张艾嘉执导的《少女小渔》开始,并经历了从台湾到大陆的转换。无论她本人的态度如何,a严歌苓对影视的态度非常传统,并对自己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充满无奈。在《三联生活周刊》的访谈中,她说得很明确:“文学肯定要退居到一种经典式的艺术样式。我觉得还是要按照自己理解的文学艺术去写,写出来有很好的导演可以将其影视化,我不拒绝;但并不是每一个作品都能被拍的,我不能将就着你拍,为了影视而妥协我的文学写作,这是不可能的。”具体到电影与电视剧,严歌苓的态度也是有所区别的。在上海大学举办的文学座谈会上,她说:“我很仇恨电视剧,它在我们国家的文化生活中,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王鸿生等《小说与当代生活——上海大学文学周圆桌会议纪要》,《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她在采访中说:“我有一个缺陷就是从来不看电视剧,没有时间看。”具体参见孙若茜《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补玉山居〉》,《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8月9日,http://www.lifeweek.cοm.cn/2012/0809/38195.shtml。正是2005年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上映后,才出现“改编热”。她的作品先后受到冯小刚、陈凯歌、姜文、李少红、高晓松的青睐,加之《扶桑》(被改编为《风雨唐人街》)《小姨多鹤》《继母》(被改编为《当幸福来敲门》)《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铁梨花》等多部电视剧的改编,可以说,严歌苓已成为目前炙手可热的“IP”(Intellectual Prοperty)。
严歌苓解释说:“我想许多导演喜欢我的故事,主要是因为我会把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全部放进去,所以画面感比较强。”b严歌苓:《我的下一部作品应该是要具备“抗拍性”》,《南方日报》2010年3月2日,http://www.chinanews.cοm/cul/news/2010/03-02/2147534.shtml。“我自己很注重小说的视觉意象。我不止注重画面感,还希望我小说写作能给人一种质感。”a严歌苓、木叶:《故事多发的年代》,《上海文化》2015年第1期。对此,学者多有认同。富有故事性,画面感强,类似闪回、蒙太奇等电影技法(或被称为“泛剧本化”特征),成为“改编热”的共识。然而,在我看来,是否改编,远远不是文本的艺术特征所决定的。闪回、蒙太奇、特写等电影技法,在绝大多数小说中都能看到,如闪回是时态交错,在人物的主观想象、心理描写中必不可少;蒙太奇不外是视角交错、谋篇布局的另一种说法,存在于任何叙事的转场中;特写就是小说的细节描写。电影在诞生初期,就从小说处学到了这些叙事技巧。两者互通,根源于叙事艺术,而非某个作家所特有。事实上,严歌苓小说最大的特征并不是故事性,而在于微妙、准确的心理描写。改编成电影的《少女小渔》《天浴》《谁家有女初长成》《金陵十三钗》等,情节并不曲折。电影为了增强戏剧性添加矛盾冲突,反而与整体故事相抵牾。如影片《天浴》通过诸多细节突出老金、文秀、供销员之间的关联,增加老金作为血性男人大闹场部的内容,前后之间缺乏合理性。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过严格的写作训练后,严歌苓对叙述“vοice”有着很强的自觉性,“每一篇作品都企图创造一种语言风格,至少是一种语气”。b庄园:《严歌苓访谈》,《华文文学》2006年第1期。叙述语调是文字所唤起的主观感受,这在改编电影中根本不可能保存,诉诸视觉的影像很难把充满情感的感觉、心理呈现出来。严歌苓自己这样说:“我觉得我的才华主要在语言上,电影剧本用不上。”c庄园:《严歌苓访谈》,《华文文学》2006年第1期。她认为小说可以描写“不可言说”的东西,电影只能进行表面的展现,两者仅在人物对白方面存在相同的要求。d严歌苓:《文学,是我安放根的地方》,《光明日报》2015年3月19日第11版。更何况,文字形成的画面感,是基于文字刺激产生的内在想象,而不是电影艺术的画面感。如《天浴》的第一句话:“云摸到草尖尖。草结穗了,草浪稠起来。一波拱一波的。”此处,文字虽然很有画面感,也提供了具体的动作,但并不等同于草原景色的空镜头。诉诸视觉的具体影像不可能把“摸”“稠”“拱”等动词蕴含的情感表达出来。电影根据故事的整体情绪,通过布景、道具及表演,创造一种不同于小说的想象画面——情调相似、基调统一的视觉画面。这是导演的二度创作。从这个角度说,小说的画面感越强,改编的难度反而越大。
在当下媒介发达的语境中,仅从艺术的角度来理解小说与影视关系的思路及其观点,已显狭隘。改编创作已经演变成跨媒介的艺术生产,图书出版与影视之间的策划、宣传、营销的紧密互动,超出了纯粹艺术的考量。影视运作已经高度市场化、产业化,资本购买“IP”概念、选择改编文本的标准,已从编导等创作者的上游环节转向观众市场的接收终端。因此,严歌苓的“改编热”,根源于影视资本对其文本满足当下大众心理的预判;研究严歌苓的影视改编,不应仅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过分强调作品的艺术性,而应重点考察当下电影产业及其与社会心理的关联。
二、严歌苓小说改编的基本状况
由于分属于不同的叙事媒介,从小说到电影,必然面临改(在原作基础上的改动)、编(原作没有而电影创作出来),具体包括改、增、删三种内容。为了比较两种文本的差异,我们用下表列出严歌苓小说改编的基本状况(见表1)。
严歌苓小说改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1年以前,《少女小渔》《情色》《天浴》《谁家有女》四部作品,虽分属海外、台湾与大陆三地电影,但其改编思路、目的、方式相似,存在如下特征:(1)题材敏感,与现实生活具有较强的关联。如《少女小渔》中非法的移民生活,《天浴》中“文革”知青的死亡、干部腐败,《谁家有女》中的拐卖妇女,《情色》中社会、家庭的“零余者”的不伦之爱,等等,皆是如此。电影从小说中接续了批判现实主义风格,定位在艺术电影。与小说相较,电影负面的社会经验有所弱化。电影《少女小渔》中马里奥重新开始写作,生活出现转机;《情色》省略了小说《无非男女》中老五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诬陷耍流氓的重要场景,尽量保持美好与浪漫的情愫;《谁家有女》虽然涉及拐卖题材,但又删掉了原作详细描写的拐卖过程与杀人场景。(2)改编动机多源于导演的艺术考量,从契合自身经验的角度选择文本。最明显的莫过于,李安购买《少女小渔》改编权,是基于东西文化参差比照的创作思路。它与《推手》《喜宴》相似,弱化了原作强调委屈自己的特殊心理,删减马里奥的孤独,并在小渔意识到男友出轨后,提醒“学会多尊重自己”。在严歌苓的介绍中,陈冲对《天浴》的喜爱,显然与自身的生活经历、情感、理想密切相关。此时改编文本的选择,导演发挥了决定性作用。(3)电影改编尊重原作故事,就改增删的三种内容来说,均是围绕如何更好地表现原作这一原则。如《少女小渔》与原作相比,突出了马里奥及其家庭生活(尤其是马里奥对小渔的暧昧情感),增强了江伟与马里奥、瑞塔与小渔的冲突。影片特别添加了晚上移民局出人意料的拜访,将四人同时纳入这一戏剧性最强的场景,矛盾于此集中爆发,成为影片的高潮。《天浴》的编剧同是严歌苓,电影的“改”与“删”就更少,所增加的内容主要围绕如何影像化展开,如增加的叙述者(暗恋文秀的中学男生),试图在“怎么讲”的叙事策略上有所创新,其他都是强调时代氛围与更具视觉感的细节。概言之,这一阶段的电影改编与小说关系极为密切。
拐卖题材,但又删掉了原作详细描写的拐卖过程与杀人场景。(2)改编动机多源于导演的艺术考量,从契合自身经验的角度选择文本。最明显的莫过于,李安购买《少女小渔》改编权,是基于东西文化参差比照的创作思路。它与《推手》《喜宴》相似,弱化了原作强调委屈自己的特殊心理,删减马里奥的孤独,并在小渔意识到男友出轨后,提醒“学会多尊重自己”。在严歌苓的介绍中,陈冲对《天浴》的喜爱,显然与自身的生活经历、情感、理想密切相关。此时改编文本的选择,导演发挥了决定性作用。(3)电影改编尊重原作故事,就改增删的三种内容来说,均是围绕如何更好地表现原作这一原则。如《少女小渔》与原作相比,突出了马里奥及其家庭生活(尤其是马里奥对小渔的暧昧情感),增强了江伟与马里奥、瑞塔与小渔的冲突。影片特别添加了晚上移民局出人意料的拜访,将四人同时纳入这一戏剧性最强的场景,矛盾于此集中爆发,成为影片的高潮。《天浴》的编剧同是严歌苓,电影的“改”与“删”就更少,所增加的内容主要围绕如何影像化展开,如增加的叙述者(暗恋文秀的中学男生),试图在“怎么讲”的叙事策略上有所创新,其他都是强调时代氛围与更具视觉感的细节。概言之,这一阶段的电影改编与小说关系极为密切。

表1 严歌苓电影改编的基本状况
第二阶段是2011年以后,分别是张艺谋2011年改编的《金陵十三钗》、2014年改编的《归来》,以及冯小刚2017年执导的《芳华》。这一阶段明显倾向于以电影为主的商业模式。三部作品制作机构均是新画面、华谊兄弟等民营企业,媒体曝光率极高。在《金陵十三钗》中,刘恒完成“相当丰满”的两稿,严歌苓参与的时间较晚。到了《归来》,她根本没有参与改编。a关于严歌苓与张艺谋合作的《金陵十三钗》《归来》的情况,可参见《严歌苓:没必要做我不那么喜欢的事》,中国作家网,2012年10月18日,http://www.chinawriter.cοm.cn/2012/2012-10-18/144217.html;《严歌苓:成片非常震撼,我有几处落泪》,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曰15日,http://www.360dοc.cοm/cοntent/11/1215/23/6772399_172589925.shtml。“获奖”一栏表明两部作品的奖项限于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缺乏张艺谋电影原有的世界性影响;再联系到同期的市场表现及影评,这两部作品只是差强人意。从“改增删”的栏目可以看出,这两部作品都对原作改动极大。电影《金陵十三钗》b值得指出的是,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来源于1988年自己作为编剧、韩三平执导的《避难》,在人物(唱诗班少女与妓女、唱书女艺人)、语境(为躲避日军的杀戮,妓女和伤兵逃入美国的天主教堂寻求庇护)、情节(妓女代替唱诗班少女赴宴)、人物关系(婷婷的父亲与杨柳风的关系)等极其相似,区别仅在于妓女人数的扩充(由三人变成十三人)、故事地点的转移(从小城变成南京)、人名的变化(婷婷之于书娟、杨柳风之于赵玉墨等)。严格地说,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就是电影《避难》的小说版。张艺谋执导的《金陵十三钗》与《避难》形成富有意味的文本变迁。对主要人物都有很大的改动,如美国人约翰(完全替换了年老的英格玛神父,以增加玉墨与约翰的跨国爱情)、李教官(增加了巷战场面)、陈乔治(增加了煽情的内容)、书娟的“汉奸”父亲(增加爱国情结)。电影力图从爱情与爱国的两条戏路增强故事的视觉感与可看性,因此改变了小说原有内容与低调内向的叙述风格,如影片虽然在严歌苓的坚持下保留了书娟的叙事视角,但仅为事件的见证者,原作的女性心理、经验已然消失。《归来》对原作内容、叙述风格、人物形象的改动更为彻底,仅仅选择“逃狱”归来、“平反”归来的故事由头而任意渲染。从《陆犯焉识》的民国(老上海与海外的殖民文化)、“文革”(右派分子的监狱劳改生活)、新时期(平反归家后的上海生活)三个社会内涵极其丰富的时代抽身出来,《归来》成为主动“被阉割”的经验匮乏者,尽管在严歌苓看来,“我认为这就是影片成功的地方——它抓住了小说中的一个魂”。c严歌苓、果尔:《从故事、小说到电影——严歌苓访谈》,《电影艺术》2014年第4期。然而,这个“魂”被抽空成一种缺乏现实感的爱情,显然是当下资本介入创作的症候。《芳华》的情况较特殊。由于人生经历的相似,严歌苓被冯小刚邀请写作一个关于“文工团”的故事,并担纲了影片的编剧,情节改动不大。但是,影片所改动以及所增加的故事内容均强调娱乐消费(如激战的场面)、降低人性的残酷,删除1990年代刘峰在海南、北京的生活,由此改变了思想主题。质言之,电影重在表现集体、时代的怀旧(如浓墨重彩地表现毛泽东逝世、文工团解散时的分别),小说则是在社会巨变中凸显善良个体的被集体抛弃的悲剧命运。相对于张艺谋祛除集体记忆、凸显个体爱情,冯小刚恰恰把个体的记忆扩展成社会记忆,由此获得了极佳的票房收益。
三、严歌苓改编热:创作方法、故事资源与经验特征
从创作的角度说,严歌苓的高产与改编热和特殊的创作方法有密切的关系。她的社会阅历丰富,具有时代典型的人生经验,其中,军队生活、留学生活构成重要的部分。归纳起来,严歌苓以自身经验为核心,放射开来形成了参差互见的系列作品。第一类带有较强的自传性,如《穗子物语》《芳华》《无出路咖啡馆》;第二类是或多或少与自己相关的身边人故事,如《陆犯焉识》《一个女人的史诗》《雌性的草地》《少女小渔》《天浴》《心理医生在哪里》《床畔》等;第三类是搜集他人素材、虚构想象的故事,如《谁家有女初长成》《金陵十三钗》《扶桑》《小姨多鹤》《太平洋探戈》《妈阁是座城》等。
贺绍俊认为,严歌苓的写作资源主要是在中国内地的生活经验和记忆。a贺绍俊:《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文艺研究》2011年第2期。严歌苓也明确说到,“根据我对1989年之前中国的记忆,就这样回到了写中国故事上”。b严歌苓:《严歌苓谈文学创作》,《世界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由于身居海外的时空距离,单凭她自身的记忆对于1990年代及以后的中国,显然是不够的。于是,搜集历史素材、借助间接经验成为主要的创作方式。在众多创作谈中,严歌苓毫不掩饰地提及搜集素材、聆听他人故事对创作的重要性:“我愿意每年花几个月的时间到国内去。实际上也做到了,基本上是一年约四个月在国内。我在国内为了搜集素材和体验生活的采访是相当密集的。”c严歌苓、木叶:《故事多发的年代》,《上海文化》2015年第1期。“我常常从别人那儿听到好故事……我的确在搜集这些故事,然后去采访、去实地体验获得二手素材。”d严歌苓、果尔:《从故事、小说到电影——严歌苓访谈》,《电影艺术》2014年第4期。仔细数来,严歌苓的绝大多数小说存在现实触点。如《少女小渔》源自于生活中一个女人的电话,“气焰极盛”的骂街语气反向刺激了作者用故事阐释东方式善良的创作冲动。e严歌苓:《弱者的宣言——写在影片〈少女小渔〉获奖之际》,《波西米亚楼》,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3页。《雌性的草地》是1974年她16岁时到草地演出时听来的“铁姑娘牧马班”的故事。《扶桑》的创作动因是无意中看到了一张“旧金山名妓”的特殊照片,“动笔写之前,看了三年的史料”。f庄园:《严歌苓访谈》,《华文文学》2006年第1期。她在翻阅移民资料时发现了一句话,“因为中国女人的这种独特的异国情调,吸引了旧金山从8岁到14岁的小男孩”。g严歌苓:《从魔幻说起——在Williams Cοllege演讲之中文版》,《波西米亚楼》,第251页。这构成了《扶桑》的叙事内核。《金陵十三钗》的创作得益于《魏特琳日记》的一段记录,加之蒋公榖的《陷京三月记》与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h严歌苓:《金陵十三钗》背后的故事,《时代周报》2011年12月29日,http://eladies.sina.cοm.cn/qg /2011/1229/23541115863.shtml。《妈阁是座城》是以亲眼目睹中国人在拉斯维加斯赌场开始,并且深入澳门实地调查得来的赌徒故事。i严歌苓:《妈阁城的谜语》,《文艺报》2014年5月9日第2版。《陆犯焉识》可谓典型。严歌苓虽然以祖父严恩春为创作原型,j严歌苓:《〈陆犯焉识〉源自祖父经历 是浪子回头的故事》,http://cul.qq.cοm/a/20140522/011840.htm。但文本竟然囊括了如此之多的内容:钱钟书《围城》的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形象,张爱玲《金锁记》的新旧家庭中母子、婆媳的关系,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右派劳改生活、王安忆《流逝》中新时期家长里短的上海弄堂生活。概言之,严歌苓在短暂书写移民生活、留学生故事之后,通过搜集素材、采访调查、体验生活、聆听他者等各种创作方式,特别注重历史、现实素材等间接经验的补充,与中国内地有效地保持了血脉互通,虽然身处海外,却成为了事实上的主流作家。她的小说,时间跨度之长,涉及内容之广,类型之复杂,完全覆盖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重要事件与现象。这给电影改编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故事资源。我们注意到,改编的电影导演与严歌苓一样,大都是“50后”著名导演,k改编严歌苓小说的电影导演,如张艺谋(1950年)、朱延平(1950年)、陈凯歌(1952年)、张艾嘉(1953年)、李安(1954年)、李少红(1955年)、冯小刚(1958年),皆属于“50后”。只有陈冲(1961年)、姜文(1963年)属于“60后”。但这与演员出道较早有关。陈冲18岁的时候就与严歌苓相识,两人的人生经历极其相似。具体情况可参见严歌苓《有关陈冲以及〈陈冲前传〉》,《波西米亚楼》,第303页。正是严歌苓丰富而富有典型性的人生经历、生活经验,唤起了同时代导演改编创作的冲动。
进言之,严歌苓小说所透露出的主流价值观,是影视媒介乐于接受的。其作品或强调人生变故中的悲欢离合(如《陆犯焉识》《心理医生在吗》),或表现英雄主义令人伤感的消散(《床畔》《芳华》),或表现时代大变动中伦理亲情的坚守(《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等),或表现当下世俗生活中的情感纠缠(《妈阁是座城》《补玉山居》等)。女性对男性无保留、无底线的忍让,对弱者不计后果、竭尽全力的保护,即陈思和称之为的“地母形象”,a陈思和:《自己的书架: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名作欣赏》2008年第5期。构成了严歌苓笔下人物的心理逻辑。《无非男女》的雨川不顾一切地挺身而出,保护当众被侮辱的老五,从怜到爱,发生质的情感变化。《金陵十三钗》的秦淮河妓女们主动代替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也是这种拯救弱者的母性善良所致,从而实现了叙事的翻转。《妈阁是一座城》则用梅晓鸥无偿免去老史高达千万赌债的情节,揭示深藏于心的情感,引发后起情节的转向。《床畔》更为极端,整部小说叙述女护士万红不惜任何代价,坚持守护已成植物人的张连长。可以说,严歌苓以女性善良为底色铺陈出来的故事,凸显家庭伦理的亲情,体现了审慎、保守的传统立场。在她的作品中,离不开个体/爱情与家庭/亲情的对垒,前者往往成为最终落败的对象。如《陆犯焉识》《无非男女》《妈阁是座城》《太平洋探戈》等莫不如此。质言之,严歌苓小说以家庭为中介,以伦理情感为核心,调和了国族与个体的矛盾,具有较强的主流价值。她如此坚执于用人性善良的方式实现小说叙事的逆转,失去了现代人性的复杂,一定程度造成了思想深度的缺陷。毋庸说《少女小渔》《谁家有女初长成》《天浴》等早期作品,就是在成熟之作的《陆犯焉识》中,人物始终围绕“浪子回头”的核心情感,在思想观念上却难有突破。《床畔》原本有着形上追问的故事,却在“三易其稿”中,最后变成基于现实合理性的故事铺陈,其实就很能说明问题。b关于《床畔》的写作,严歌苓的父亲在1994年提出从护士万红与张连长两个主观视角来写的建议,但严歌苓写作一直不顺利。具体情况参见http://culture.ifeng.cοm/a/20150402/43470307_0.shtml。严歌苓自己也认识到,“没有那么自觉地寻找主题”。c庄园:《严歌苓访谈》,《华文文学》2006年第1期。难怪有论者尖锐地指出,严歌苓的小说虽然文笔细腻,但很难说是严肃意义上的文学,而更接近于通俗文学。d李云雷:《历史的通俗化、美学与意识形态——严歌苓小说批评》,《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5期。在我看来,事实确乎如此。
严歌苓的小说凸显伦理情感,缺乏深刻的人文思想,这对于影视剧来说,正好是极佳的故事资源。1990年代以来,在全球产业升级的背景下,电影作为新兴的文化产业,在国家经济体系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消费性得到空前的强化,影响到电影的内容生产。新世纪中国电影的故事经验在如下三个方面达成了共识。第一,“政治正确”成为市场准入的基本前提,是一道不可触碰的红线;第二,与观众具有广泛的关联,以得到“最大量”的关注;第三,必要的观赏性与艺术性。如此,国家意识、公共经验、集体记忆在满足前两个条件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进而在视听语言、剪辑特效等技术硬件、必要的叙事策略的支持下,成为市场最可靠的故事类型。于是,2009年后涌现出“新主流”电影,如《建国大业》《风声》《南京!南京!》《唐山大地震》《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战狼2》(也包括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潜伏》《北平无战事》),等等,个体意识与国族意志有效地保持了一致。影视产业从投资—创作—接受生产出日益成熟的消费商品。严歌苓新世纪改编的《金陵十三钗》《归来》《芳华》,均属此列。南京大屠杀、“右派分子”的平反、改革开放的“经商热”、理想主义的消散,等等,浓缩了国家民族的集体记忆以及新时期中国社会的典型心理的故事,给微观个体的命运提供了足够的戏剧性空间,既确证了政治正确的消费前提,又保证了数量最大化的观众群体,而且由著名导演执导,有着观赏性、艺术性的承诺,自然带来较好的票房预期。拓展开来,严歌苓擅长在较长的时代跨度中,讲述个体命运与国家、民族、集体交织互动的故事,突出家庭伦理的亲情与人性善良的传统价值,显然满足当下电影消费三个方面的要求。从1990年代《天浴》《雌性的草地》《谁家有女初长成》与写作语境的价值观念完全一致的“控诉”,到《穗子物语》《芳华》《床畔》等对过去集体主义的怀旧与反思,凸显个体的尊严价值,也是当下最流行的意识形态。概言之,在广泛搜集素材、拓展自身经验,与中国内地保持密切互动中,严歌苓小说获取了丰富的时代经验,在渲染国族意志、集体记忆的背景下,凸显自由的人性价值,满足了新世纪电影媒介对故事内容的要求。这是她的作品屡屡被改编的根本所在。
四、身份、获奖与电影产业的国际化路线
与思想深度的欠缺、价值取向趋于主流相反,严歌苓在小说技法、文本建构、叙事策略等方面颇有创新,尤其是近年来,每部作品都在尝试不同的表达方式。在《少女小渔》《红罗裙》《女房东》等早期短篇中,她有意提高写作难度,把叙事视角严格地限定在一个人物上,以此深入心理深处捕捉微妙的主观感受。中长篇小说突出叙事策略,渗透主观情感的叙述语调、多种时态、三种人称游刃有余地深入人物的心理,故事结构也是推陈出新,不断尝试新的写作可能。《扶桑》在三种叙述人称之间自由转换,“我”在移民的资料查阅中营造历史感,“你”/扶桑的第二人称叙述产生了亲近感,第三人称的场景与细节描写,共同渲染了特殊时空中的诡异气氛。《谁家有女初长成》“分段讲故事”的叙述策略,造成在不同时空中巧巧/小潘的差异,两段故事的关系在克制的叙述中逐渐清晰起来,产生了独特的阅读快感。《金陵十三钗》采用少女孟书娟的视角叙述,将初潮来临的“极至耻辱”女性感受与“强奸”南京的民族劫难独特地融合在一起。文本的叙述时态复杂,过去(南京大屠杀的故事)、现在(“我”的书写状态)、将来(事后的未来)交错,弥漫着一种难以摆脱的悲剧感。《陆犯焉识》的叙事视角也是独特的。冯学锋/“我”作为陆焉识的孙女,在绝大部分篇幅里叙述祖父的过去,成为一个可靠的叙述者,然而在“回上海”章节后又是生活中直接出场的具体人物,叙述语调从先前的庄重,变成戏谑、琐碎甚或有些刻薄。《芳华》的叙述者直接出现,对人物大段大段的心理分析,突出地表现了拆解叙事、暴露虚构的“元叙事”的特征。《芳华》的叙述者直接出现,对人物大段大段的心理分析,突出地表现了拆解叙事、暴露虚构的“元叙事”的特征。《太平洋探戈》在叙述中就把“错过”设定成特殊的“编结”方式,在行为、情感、心理共通的结点上,将北京的毛丫与澳大利亚的罗杰两个隔着巨大空间的人物组织在一起,交叉叙述体现了冥冥之中的神秘主义。《心理医生在吗》的叙述更为独特。写作契机源自于在美国就医的亲身经历,用“向心理医生倾诉”的独特方式建构故事,在独白中敞开创伤性记忆。《补玉山居》的叙述颇为轻松,用同一地点(补玉山居)串接起亿万富翁、军人、精神病者、贩毒分子等情感纠葛的悲剧,四段人物、事件各自独立。作者的目的很明确,不同的身份、职业、背景、年龄构成了当下的人生世态。《舞男》则用老上海文人石乃瑛的魂灵作为第一人称,却在主体部分叙述新上海舞男杨东与律师事务所老总张蓓蓓、丰小勉之间的爱恨情仇,以及张蓓蓓对石乃瑛的调查,在叙事人称与两个时空形成交叉,由此建构了主副有别的双重文本。
正是写作技法的先锋实践,使严歌苓小说在严肃文学的范畴内,屡屡获得中国内地、台湾以及美国文学的奖项。台湾文学期刊从《少女小渔》开始发现她的天分。她曾介绍说:“有个阶段我基本是靠获奖来谋生的,最后将台湾的文学奖得了个遍。”a严歌苓:《十年一觉美国梦》,《华文文学》2005年第3期。而近来书写中国经验的小说,多次得到国内权威文学期刊及中国小说学会的重要奖项,受到文学评论家持久的关注,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热门作家。对严歌苓来说,获奖不仅提供了必要的生活经费,而且标志着精英艺术的品味,俨然成为提升影视艺术水平的保证。严歌苓说:“因为获奖,整个出版发行电影等配套就很顺利了。”b严歌苓:《十年一觉美国梦》,《华文文学》2005年第3期。事实上,她在出国前就与内地电影人脉通畅。在电影《天浴》获得美国影评人协会奖、台湾电影“金马奖”等后,严歌苓顺利地进入好莱坞编剧协会,成为该协会唯一一位华人编剧,并在2008年陈凯歌执导的《梅兰芳》中担纲编剧工作。可以说,因小说技巧获得文学奖,再到影视改编,尤其是与李安、陈冲、陈凯歌、张艺谋、冯小刚等导演的合作,使严歌苓在电影行业完成了精英文化的品位塑形。
严歌苓的改编热,也是中国电影国际化的重要选择。编剧的国际化,是中国电影内容生产进一步国际化的重要表征。对于急需走进海外主流影院、提振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电影来说,严歌苓就是最佳的合作者之一。作为北美华文文学乃至整个海外华人文学的杰出代表,严歌苓既与内地经验、资源、价值观等保持高度一致,又具有双语写作的能力,产生了国际与跨界影响。从编剧国际化的角度看,中国大片出现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个阶段,以内地为主,强调华人文化圈层的资源整合,突出普适性价值与无争议的人性内容,将消费重点放在了文化表象、动作奇观的视听感官上,也因此,被指责为内容的空心化。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冯小刚的《夜宴》,编剧思路较为生硬僵化,凸显个体爱情与民族国家非此即彼的冲突矛盾,主人公或者毫无保留的舍个体、顾天下的集体主义,或者不顾国族身份,放弃社会责任,追求自由爱情的个体幸福,这都带有相当的狭隘性与片面性。第二个阶段,是周边国家东亚区域的资源整合,强调以中国为主的东方文化传统,如中影集团投拍的《无极》(中日韩)、《赤壁》(中日)、《梅兰芳》、《太平轮》(中日),中博世纪投拍的《危险关系》(中韩)等等。此时,编剧已有国际化的倾向,如美国著名华人编剧王惠玲参与吴宇森的《太平轮》,严歌苓参与陈凯歌的《梅兰芳》。故事经验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带有跨国性、跨地性,“泛东方”形象获得增强,如《无极》没有中国意识的远古世界,《赤壁》取消了“三国”文化的特定传统、人物形象,仅仅保留了基本的故事框架。另一方面,在国家意志与个体自由之间,不再是先前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如《太平轮》结合抗日战争背景,叙述抗日将领雷义方与大家闺秀周蕴芬浪漫而忠贞的爱情;《梅兰芳》在成年的梅兰芳蓄须抗日中,把个体意志融入国族意识。应该说,这一阶段的故事强调自由爱情、家庭伦理等情感要素,明显增强了影片消费的程度,而且,思路、立场开阔起来。第三个阶段,延请好莱坞创作整体团队,试图从明星效应、视听质量方面直接拓展海外市场,如华谊兄弟的《1942》、新画面的《金陵十三钗》、乐视影业的《长城》、北京唐德的《绝地逃亡》、耀莱文化的《天降雄狮》,等等。好莱坞一线明星成为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市场卖点。然而,从目前的情况看,仅由好莱坞编剧书写的中国故事差强人意。如著名编剧托尼·吉尔罗伊虽然奉献出了“谍影重重”系列的经典故事,然而关于中国的故事《长城》,在中国内地及美国恶评如潮。一方面,传统文化的显在表征被突出放大,出现刻板的传统中国形象,另一方面,文化传统的内涵被弱化,故事经验极其空洞。说到这里,李安编剧团队国际化的案例意义就显现出来。在华人导演(李安)、华人作家(王惠玲)与美国编剧(James shams)的长期合作中,西方的敏感及其问题意识进入东方的题材,由此产生出《饮食男女》《卧虎藏龙》《色戒》等大量成功之作,营造了具有国际视野、西方文化思路的中国故事。如此看来,严歌苓、王惠玲等海外华文文学的杰出代表,是当下中国电影编剧国际化过程中恰当的选择。2017年严歌苓编剧的《芳华》、王惠玲编剧的《妖猫传》成为市场广受关注的影片,已经融入好莱坞电影的华人编剧们,在未来存在更广阔的合作前景。以上种种,均能说明当下电影改编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