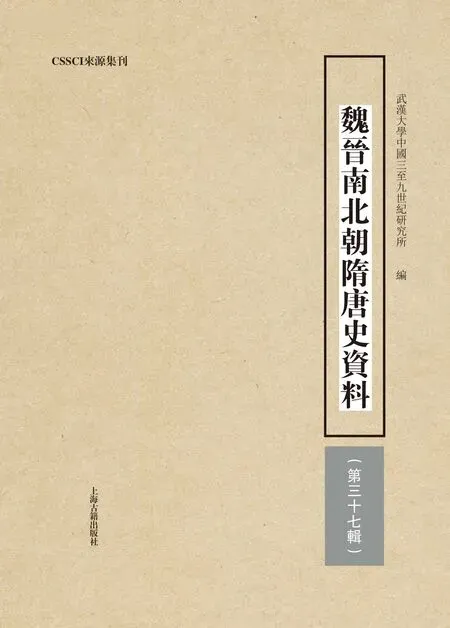五代張全義家族與政權更替
——以張氏家族墓誌爲中心的考察
羅 亮
衆所周知,五代諸政權大都國祚短促,這使得朝中名臣大都有着曆事多朝的經歷。張全義及其家族便是其中的代表,從唐末到北宋,纓冕不絶,是五代史上的重要家族。那麽他們是如何面對更迭頻繁的政權,在動蕩時代中又做出了何種策略以保全家族,便成爲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其中關於張全義的材料,除新舊《五代史》本傳之外,尚有宋人張齊賢所作的《齊王張令公外傳》。然而張氏一族在五代中期逐漸衰弱,子孫中除張繼祚在《舊五代史》中有簡要傳記外,其餘人都近乎湮没無聞。前人研究也就大多圍繞張全義而展開。[注]如諸葛計: 《張全義略論》,《史學月刊》1983年第6期,第39—43頁;劉連香: 《張全義與五代洛陽城》,《洛陽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2期,第9—12頁;胡安徽: 《張全義農業思想初探》,《農業考古》2013年第1期,第113—115頁;山根植生: 《五代洛陽の張全義について:“沙陀系王朝”論への応答として》,中國文史哲研究會: 《集刊東洋學》第114期,2016年,第48—66頁。本文定稿後,又發現北京大學閆建飛博士論文《唐末五代宋初北方藩鎮州郡化研究(874—997)》(2017年)第四章第一節亦對張全義家族墓誌進行了考釋。本文雖與之難免有重合之處,但主題亦頗有不同。特此説明。幸運的是,近年陸續出土了多方張氏家族的墓誌,使我們進一步研究成爲了可能。故筆者擬以其爲中心展開探討,不當之處,還請方家指正。
一、 張全義家族出土墓誌概況
由於相關傳世文獻主要集中在張全義個人之上,對其家族子弟介紹頗少,近年在河南省陸續出土的六方張氏家族墓誌也就彌顯珍貴。故在對相關問題展開討論之前,有必要對這六方墓誌做一簡要介紹:
(一) 張繼業墓誌,題爲《唐故河陽留後檢校太保清河張公墓誌銘并序》。1991年出土於河南省孟津縣朝陽鄉崔溝村東南,現藏於河南省孟津縣文管會。誌並蓋青石質,長寬均71.5釐米,蓋篆文,志文楷書,47行,滿行49字,唐鴻撰,王鬱篆蓋,趙榮書,後唐同光三年(925)二月二十一日葬。拓片見《洛陽新獲墓誌》;録文見《全唐文補遺》第六輯、《洛陽新獲墓誌》《五代墓誌匯考》。[注]李獻奇、郭引强編: 《洛陽新獲墓誌》,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32頁。吴鋼: 《全唐文補遺》第六輯,西安: 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209—211頁。周阿根: 《五代墓誌匯考》,合肥: 黄山書社,2012年,第157—161頁。誌主爲張全義嫡長子。李獻奇、張欽波對此墓誌及張季澄墓誌有所考釋。[注]李獻奇、張欽波: 《五代後唐張繼業、季澄父子墓誌淺考》,載《河洛文明論集》,鄭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30—453頁。
(二) 蘇氏墓誌,題爲《唐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清河張公故夫人武功蘇氏墓誌銘并序》。王禹撰,後唐同光三年九月十三日葬。録文見《全唐文補遺·千唐志齋新藏專輯》《五代墓誌匯考》。[注]吴鋼: 《全唐文補遺·千唐志齋新藏專輯》,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22—423頁。《五代墓誌匯考》,第162—163頁。誌主爲張全義之弟張全恩之兒媳。
(三) 王禹墓誌,題爲《唐故朝議郎尚書屯田員外郎前河南府長水縣令賜緋魚帶琅琊王君墓誌銘并序》。誌石與誌蓋長寛均爲55釐米,蓋篆文,李鸞撰並正書,29行。拓片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三六册、《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洛陽卷》第一五册、《洛陽出土歷代墓誌輯繩》;録文見《全唐文補遺》第五輯、《全唐文補編》卷九七、《五代墓誌匯考》。[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36册,鄭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5頁。陳長安主編: 《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洛陽卷》第15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43頁。《洛陽出土歷代墓誌輯繩》,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723頁。吴鋼: 《全唐文補遺》第五輯,西安: 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70—71頁。陳尚君: 《全唐文補編》卷一,北京: 中華書局,2005年,第1209—1210頁。《五代墓誌匯考》,第242—244頁。誌主爲張全恩之婿。
(四) 張季澄墓誌,題爲《唐故金紫光禄大夫檢校户部尚書前守右威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清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張公墓誌銘并序》。1991年與張繼業墓誌同時出土於河南省孟津縣朝陽鄉崔溝村東南,現藏於河南省孟津縣文管會。誌石長寬均爲72.5釐米。楊凝式撰,張季鸞篆蓋,郭興書。拓片見《洛陽新獲墓誌》,録文見《全唐文補遺》第六輯、《洛陽新獲墓誌》《五代墓誌匯考》。[注]《洛陽新獲墓誌》,第135頁。《全唐文補遺》第六輯,第214—216頁。《五代墓誌匯考》,第272—276頁。誌主爲張繼業之子、張全義之孫。
(五) 張繼昇墓誌,題爲《晉故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張公墓誌銘并序》。河南省洛陽市出土,現藏河南省洛陽古代藝術館。誌石長66釐米,寛65釐米。楊凝式撰,劉珙正書。拓片見《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洛陽卷》第一五册、《洛陽出土歷代墓誌輯繩》,録文見《全唐文補遺》第五輯、《五代墓誌匯考》。[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洛陽卷》第15册,第150頁。《洛陽出土歷代墓誌輯繩》,第726頁。《全唐文補遺》第五輯,第68頁。《五代墓誌匯考》,第309—311頁。誌主爲張全恩之子,張全義之侄。
(六) 李氏墓誌,題爲《大晉故隴西李氏夫人墓誌銘》。胡熙載撰。録文見《芒洛塚墓遺文》卷下、《隋唐五代石刻文獻全編》第二册、《全唐文補編》卷一、《五代墓誌匯考》。[注]羅振玉: 《芒洛塚墓遺文》卷下,收入《歷代碑誌叢書》第14册,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12—413頁。《隋唐五代石刻文獻全編》第2册,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237—238頁。陳尚君: 《全唐文補編》卷一,北京: 中華書局,2005年,第1249—1250頁。《五代墓誌匯考》,第326—328頁。誌主爲張全義之孫、張繼業之子張季宣之妻。劉連香對此墓誌有所考釋。[注]劉連香: 《後晉張繼昇墓誌考》,《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第25—28頁。
除以上六方出土墓誌之外,《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還存有一篇北宋名臣富弼撰寫的《張樞密墓誌銘》。誌主張奎是張全義的七世孫,該墓誌銘記載了不少張氏譜系、遷徙的信息,亦是考證張氏籍貫及支脉流傳的重要材料。[注]按除此之外,閆建飛博士論文中還收有《張繼美墓誌》《張繼達墓誌》及諸幕僚墓誌等,亦十分重要,但今暫不涉及。參閆建飛: 《唐末五代宋初北方藩鎮州郡化研究(874—997)》,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17年,第183—185頁。
二、 張氏家族的籍貫與譜系
關於張氏家族籍貫,存在濮州與清河兩説。《舊五代史·張全義傳》敍張全義家世稱:“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祖璉,父誠,世爲田農”,[注]《舊五代史》卷六三《張全義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837頁。視其爲濮州人。而張繼業、繼昇墓誌則均稱其爲清河人,《王禹墓誌》亦云:“府君夫人清河張氏,及故齊王親弟諱全恩之女也,故齊王之親猶女也”。[注]《王禹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243頁。故李獻奇認爲當據此將正史中張氏籍貫改爲清河,然考慮到墓誌書寫中攀附著姓的傳統,清河一説未必確鑿,此説難免有失武斷。
雖然,張氏墓誌和其他中古墓誌一樣,在開篇列舉了許多張氏先賢,但其中卻並無一人出於清河張氏。如《張季澄墓誌》中稱“良推漢傑,耳號趙王”,指張良、張耳;“廷尉治獄”“御史埋輪”,指張釋之、張綱;[注]《後漢書》卷五六《張綱傳》云:“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北京: 中華書局,1965年,第1817頁。“博物丞相平吴”“持麾將軍破虜”,指張華、張遼;[注]《三國志》卷一七《張遼傳》云:“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北京: 中華書局,1964年,第518頁。“尚書令以專對而命秩”“博望候因承傳而開封”,指張安世、[注]《漢書》卷五九《張安世傳》云:“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遷光禄大夫。”北京: 中華書局,1964年,第2647頁。張騫。[注]《史記》卷一一一《衛將軍驃騎列傳》云:“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絶國功,封騫博望侯。”北京: 1963年,第2929頁。又如《張繼昇墓誌》中稱“儀良以籌策匡邦”,指張儀、張良;“飛耳以干戈衛社”,指張飛、張耳;“鑄銅渾而衡僅通獲”,指張衡;“神笻杖而騫稱奉使”,指張騫。以上種種名臣良將,籍貫各不相同,但無一出於清河張氏。只能認爲墓誌作者意在誇炫,而非據實記録氏族源流。仇鹿鳴在考訂張氏郡望時也指出“在郡望虚化之後,墓誌的撰者不再注意辨别世襲源流,誌文中關於家族源流的敍事逐漸變爲了虚應故事的程式。”[注]仇鹿鳴: 《製作郡望: 中古南陽張氏的形成》,《歷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33頁。
更有力的證據是《宋史·張亢傳》,其辭云:“張亢字公壽,自言後唐河南尹全義七世孫。家於臨濮。”[注]《宋史》卷二三四《張亢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7年,第10428頁。張亢是張全義七世孫,卻仍稱家於臨濮,可見其確實爲其籍貫祖宅所在。清河一望,當屬攀附。
然而這種攀附風氣並未隨着五代時士族的衰弱而消亡,反倒兩種籍貫的記載有着融合的趨勢。北宋名臣富弼爲張亢之兄張奎所作墓誌銘中篇首即稱:“清河張公,皇祐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以疾終於天平之郡”,是以清河爲望。而在文末又云:“公之先,累世居濮州晉城。七代祖全義,封齊王,唐五代間,有大功於洛,没謚忠肅”,[注](宋) 富弼: 《張樞密墓誌銘》,(宋) 杜大珪: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之卷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50册,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290—291頁。則又承認其累居濮州的事實,與《宋史·張亢傳》的記載相符。
由上可知,張氏籍貫最可能是如史傳記載的濮州臨濮,而非墓誌中所見的清河。在明確其籍貫之後,我們可結合墓誌與傳世史籍對張氏家族的譜系做進一步的梳理。
據《舊五代史·張全義傳》和張繼業、季澄、繼昇墓誌,張全義祖父爲張璉,累贈太保、尚書左僕射,妻沛郡朱氏,累封趙國太夫人;[注]《張繼昇墓誌》作“楚國太夫人”,《五代墓誌匯考》,第309頁。父誠,累贈太師、尚書令,妻樂安郡任氏,追封秦國太夫人。
張全義兄弟可考者有張全恩、張全武二人。李綽《昇仙廟興功記》云:“今河陽行軍懷州刺史僕射清河張公,即留守太保相君之令弟……時乾寧四年正月三日記。”[注]李綽: 《昇仙廟興功記》,(清) 董誥編: 《全唐文》卷八二一,北京: 中華書局,1982年,第8650頁。所謂“留守太保”,即張全義,參劉連香: 《後晉張繼昇墓誌考》,《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第25頁。《張繼昇墓誌》云“先考諱全恩,累贈檢校太保,守懷州刺史……公即懷州使君之第三子也。”[注]《張繼昇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309—310頁。《蘇氏墓誌》云“公即故懷州刺史太保公之塚子也。太保公,齊王令公親仲弟也。”[注]《蘇氏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162—163頁。《王禹墓誌》云“府君夫人清河張氏,即故齊王親弟諱全恩之女也,故齊王之親猶女也。”[注]《王禹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243頁。據此可知,張全義有弟名全恩,爲懷州刺史、僕射,累贈檢校太保。而全恩妻始平郡馮氏,封太君。
張全義另一弟見於《新五代史·張全義傳》,傳稱“初,全義爲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爲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人通問於太原”,[注]《新五代史》卷四五《張全義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491頁。則其名全武。遺憾的是,目前尚未見到更多的材料。
張全義有兩任妻子,一任爲姜氏,累贈天水郡夫人,見於張繼業、張季澄墓誌,爲繼業之母;一任爲儲氏,被封以“懿賢”“莊惠”之號。[注]參劉連香: 《後晉張繼昇墓誌考》,《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第26—27頁。其子至少有三,分别爲繼業、繼祚、繼孫。關於此三人事迹,下文還要詳細談及。女兒亦至少有三,一女嫁與梁太祖朱全忠之子福王友璋,[注](宋) 張齊賢撰,俞鋼校點: 《洛陽縉紳舊聞記》卷二“齊王張令公外傳”條云:“梁祖遂以子福王納齊王之女爲親”,傅璇琮編: 《五代史書彙編》,杭州出版社,2005年,第2400頁。二女嫁與李肅。[注]《洛陽縉紳舊聞記》卷二“李少師賢妻”條云:“李公自雍之梁,齊王見之,愛其俊異,以女妻之,即賢懿夫人所生,王之適也。數嵗而亡,又以他姬所生之女妻之。”第2401—2402頁。除此之外,還有兩處記載張全義子嗣有張衍、張從賓二人,然考諸他籍,恐爲誤載。下面對此略作考證:
首先是張衍。《册府元龜》卷八五三《總録部·姻好》云:
後唐鄭珏,昭宗朝宰臣鄭啓之侄孫。父徽,光啓初爲河南尹張全義判官。全義子衍婚徽女,珏以家世依張氏,家於洛陽。[注]《册府元龜》卷八五三《總録部·姻好》,北京: 中華書局,1960年,第10142頁。
張衍,字玄用,河南尹魏王宗奭之猶子也,其父死於兵間。衍讀書爲儒,始以經學就舉,不中選。時諫議大夫鄭徽退居洛陽,以女妻之,令應詞科,不數上登第。[注]《册府元龜》卷六五《貢舉部·應舉》,第7798頁。
按“魏王宗奭”即張全義,兩條史料同出《册府》,又都提及張衍與鄭徽之女結合一事,只是在“子”與“猶子”之間存在差異。其實第二條材料出於《舊五代史·張衍傳》,[注]《舊五代史》卷二四《張衍傳》,第325頁。按此條下注“《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即證明是《舊五代史》原文,而非後人補入。文字全同,在史源上要早於第一條。[注]按鄭珏在新舊《五代史》中皆有傳記,並未提及與張衍姻戚關係,可知此條史源不出自二書。而“後唐鄭珏”之謂,後人裁剪痕迹明顯,亦非實録、國史口吻。故此條史源最可能源自某種文人筆記。《資治通鑑》卷二六八亦載:
(乾化二年二月)是日,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於路。左散騎常侍孫騭、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最後至,帝(梁太祖)命撲殺之。衍,宗奭之侄也。[注]《資治通鑑》卷二六八,後梁太祖乾化二年二月條,北京: 中華書局,1956年,第8751頁。
則亦云張衍爲張全義之侄,並非親子,可爲旁證。而且以張全義當時之權勢地位,梁太祖再是盛怒之下,恐怕也不會輕易處死其子。這也從側面證明了張衍的身份當是張全義之疏親。《册府元龜》卷八五三所載恐在“全義”下漏一“猶”字。
晉張從賓,父全義,爲河南尹四十年,積而能散,以至令終。及從賓、繼祚,好治生,商賈盈門,多藏而致禍也。[注]《册府元龜》卷九四《總録部·不嗣》,第11068頁。
然張從賓在《舊五代史》中有傳,稱:
張從賓,未詳何許人也。始事唐莊宗爲小校,從戰有功。[注]《舊五代史》卷九七《張從賓傳》,第1288頁。
則張從賓早年一直追隨唐莊宗征戰,是後唐元老,而張全義“爲河南尹四十年”,爲後梁重臣,其子嗣也均居於洛陽,不容别有一子活動於河東河北,兩人並非父子,明矣。但《册府元龜》言之鑿鑿,稱二人爲父子,未必無因。之所以出現這種誤會,可能源於張從賓、張繼祚的關係。《舊五代史·張繼祚傳》云:
張繼祚,故齊王全義之子也。……天福初,喪制未闋,會張從賓作亂,發兵迫脅,取赴河陽,令知留守事。[注]《舊五代史》卷九六《張繼祚傳》,第1274頁。
張繼祚本人才具平平,張從賓似無“發兵脅迫”,特意將其從洛陽“取付河陽”之必要,甚至還要“令知留守事”。這顯然是要利用張全義父子在河陽的政治影響力以及張繼祚“好治生”所積累的財富。在此過程中,或許張從賓對張氏聯宗攀附,以擺脱自己“未詳何許人”的卑微家世,爲自己的叛變樹立威望。其後遂有張從賓乃全義之子的記載流傳下來。
綜上所述,張全義可考之子只有繼業、繼孫、繼祚三人,張衍、張從賓二人並非全義親子。
再看張氏子孫。張繼業妻解氏,封雁門郡夫人。有子六人: 季澄、季榮、季昇、季荀、季鸞、季宣。季澄妻高氏,子元吉。季宣妻李氏。又張繼業墓誌蓋爲“外甥女婿左藏庫副使朝散大夫守太府少卿柱國賜紫金魚袋王鬱”篆筆所書,可知其尚有一外甥女,也即尚有一姊妹,然是否爲嫁與朱友璋或李肅者,尚難判斷。
張全恩一支,至少有三男一女。長子名字不詳,妻蘇氏,子鐵哥、劉奴、嬌兒。三子繼昇,妻儲氏、葛氏,子歲哥。另有一女嫁與王禹,而王禹正是蘇氏墓誌的撰寫者。此外,《張繼昇墓誌》云“親侄季弘,諸堂侄皆孝敬承家”,[注]《張繼業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310頁。則知“親侄”季弘必屬全恩一支孫輩,而與張全義、全武之孫即所謂“諸堂侄”相别。只是季弘是全恩長子、次子抑或其他子嗣之子,暫時還無法判斷。同墓誌又云“侄女二人,一人出適牛氏”,[注]《張繼業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310頁。亦可資補充。
根據以上考訂,繪成張氏譜系如下圖。在了解了張氏家族成員的基本情況之後,我們將於後文對其在五代亂世中的浮沉及其時代背景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圖一 張氏譜系圖
三、 張全義改名之背景
張氏家族的核心人物無疑是張全義,有關他的研究,前人已有不少成果,多集中於張全義的施政方略上,[注]如諸葛計: 《張全義略論》,《史學月刊》,1983年第6期,第39—43頁;劉連香: 《張全義與五代洛陽城》,《洛陽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2期,第9—12頁;胡安徽: 《張全義農業思想初探》,《農業考古》,2013年第1期,第113—115頁。然略顯粗疏,在其個人命運及其反映的時代背景問題上仍有探討的空間。如其屢次改名一事,雖有人撰有《張全義: 三改其名的亂世名臣》一文,[注]沈淦: 《張全義: 三改其名的亂世名臣》,《文史天地》,2013年第7期,第46—49頁。但對改名時間的考訂、改名的範圍乃至改名的意義都未能詳細述及,對張全義本人的評價則多是輕率批判,少了一份對歷史人物的“同情之理解”,也就很難從中窺見唐—後梁—後唐間易代的複雜性。故本節以傳統史料記載結合墓誌對其改名問題作進一步的考證,以期能做出更多的詮釋。
《舊五代史·張全義傳》敍張全義改名一事較詳:“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初名居言,賜名全義,梁祖改爲宗奭,莊宗定河南,復名全義。”[注]《舊五代史》卷六三《張全義傳》,第837頁。然仍有不確之處。如其他史籍中多以“張言”爲名,而非“張居言”。又如“賜名全義”一語,主語不明,不知何人賜名。其姓名變動雖看似小節,卻是唐、梁、後唐三朝易代的絶佳反映。故需不憚繁複,對此加以考訂。
《五代史闕文》“張全義”條稱“唐昭宗賜梁祖名全忠,賜張言名全義,入梁改名宗奭”,[注](宋) 王禹偁: 《五代史闕文》“張全義”條,傅璇琮編: 《五代史書彙編》,杭州出版社,2005年,第2453頁。似乎張全義和朱温一起被昭宗賜名。然此條記載存在錯誤,因爲朱温在中和二年(882)背叛黄巢,改投唐庭,被僖宗賜名。而文德元年(888)三月時,張全義仍以“張言”的名字被記入史籍之中,[注]《舊五代史》卷一五《李罕之傳》載:“(文德元年)三月,克用遣其將李存孝率師三萬助之,來攻懷、孟。城中食盡,備禦皆竭,張言遣其孥入質,且求救於太祖(朱全忠)。”第208頁。當時唐昭宗已經即位,只是尚未改元。又《册府元龜》《新五代史》皆稱:“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注]《册府元龜》卷八二五《總録部·名字二》,第9798頁。《新五代史》卷四五《張全義傳》,第490頁。則昭宗賜名張全義一事,當無疑義。
但若我們繼續追問張全義具體是在何時被唐昭宗賜名?問題則變得複雜,除史籍上並無明確記載之外,由於改名帶來的書寫體例的混亂亦加大了我們考訂的難度。如前所言《舊五代史·李罕之傳》在文德元年是尚稱其爲“張言”,似乎就可斷言賜名在此之後。然而同樣是《舊五代史》,其《梁太祖紀》記載同樣事件云“是月,河南尹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克之。罕之單騎出奔,因乞師於太原,李克用爲發萬騎以援之。罕之遂收其衆,偕晉軍合勢,急攻河陽。全義危急,遣使求救於汴”,[注]《舊五代史》卷一《梁太祖紀一》,第10頁。則又稱其爲“張全義”。兩條材料在可靠性上難分軒輊,我們還需更多的綫索。
《資治通鑑考異》引《編遺録》云:“八月,遣從周入上黨。九月,壬寅,上往河陽,令李讜救應朱崇節,又命朱友裕、張全義簡精鋭過山,於澤州北應接,取崇節、從周以歸”,[注]《資治通鑑》卷二五八,唐昭宗大順元年七月條,第8401頁。事在大順元年(890)。這條材料的關鍵之處在於其史源,所謂《編遺録》,全名爲《大梁編遺録》,在梁末帝貞明中時由宰相敬翔編纂而成,與實録偕行,是研究後梁歷史的寶貴資料。可惜現已散佚,只在《通鑑考異》中保留了零星的數條。尤爲重要的是,該條材料其實是傳世文獻中關於張全義的最早記載。其餘史籍無論是正史的新舊《唐書》《五代史》還是《資治通鑑》、唐五代《會要》《册府元龜》等重要典籍,甚至包括同樣保存於《通鑑考異》中涉及張全義的各種《實録》,[注]如《資治通鑑》卷二五七,唐僖宗光啓三年六月條《考異》云:“《太祖紀年録》:‘七月,癸巳,澤州刺史張全義棄城而遁,太祖以安金俊爲澤州刺史。’……按《實録》,六月,全義已除河南尹。”第8358—8359頁。其中所引《太祖紀年録》,爲後唐宰相趙鳳於長興四年修成(參《五代會要》卷一八《修史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00—301頁)。所引《實録》,當爲《僖宗實録》,唐光化年間,裴摯嘗撰,但五代時已經散佚。司馬光所見《僖宗實録》爲宋人宋敏求所撰。(參《宋史》卷二三《藝文志二》云:“《唐僖宗實録》三十卷……並宋敏求撰。”第5089頁。)在編纂時間上都要晚於《大梁編遺録》。
由於張全義曾反復改名,那麽相關材料的形成時間就變得更爲關鍵。如是後唐之後的材料,我們就無法判斷其中所稱的“張全義”究竟是一種歷史事實,還是後世爲方便起見的追述。换言之,我們無法區别到底記載的是第一次還是第三次改名。而《大梁編遺録》妙在成書的時間節點上,張全義只進行了兩次改名,最終名爲張宗奭。後梁史籍上記載他也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嚴格按照歷史事實,以其所處年代的名字來稱呼他,那麽記載中可能出現張言、張全義、張宗奭等多種稱謂;一種是以其最終的名字張宗奭代替此前的名字,那麽記載中應當統一爲張宗奭。但無論如何不會出現以張全義指代張言、張宗奭的情況出現。反言之,材料中出現的“張全義”,便是歷史事實,也即賜名不晚於大順元年九月。
將以上結論綜合起來,張全義賜名當發生在文德元年(888)三月至大順元年(890)九月這一年半間。但我們知道,賜名行爲往往不會獨立發生,而需依附於其他政治事件。在大順元年之前,張全義與中央的交集主要有三: 其一是他在黄巢敗後依附諸葛爽,被表爲澤州刺史。具體時間雖不明確,但至少在諸葛爽去世的中和二年(882)之前。其二是諸葛爽死後,張全義在李克用的支持下,與李罕之一起驅逐了爽子仲方,李克用表李罕之爲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爲河南尹,事在光啓三年(887)六月。其三則在文德元年四月,因李罕之需求無度,張全義偷襲河陽,旋即爲李克用所敗,退出河陽,只得轉投朱全忠,並在其幫助下擊退李克用,朱全忠以丁會爲河陽節度使,張全義仍爲河南尹。由此可知,唯有第三次在我們考證的時間段内,也即張全義改名最可能發生在文德元年四月。
雖然張全義是在投靠朱全忠後才獲得賜名的,但當時後者的實力尚未如全盛時那麽强大,張全義還保有較强的獨立性,這一點在其名字中也有所反應。和“全忠”一樣,“全義”也藴含唐室希望他們牢記朝廷恩義,忠於國家的意味。但皆以“全”字爲行輩,則暗示了張全義地位與朱全忠相當,可與之抗衡,這是昭宗慣用的“縱横術”。[注]王賡武著,胡耀飛、尹承譯: 《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上海: 中西書局,2014年,第25頁。事實上,直到後梁建國之後,這種獨立性仍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如洛陽出土的《張濛墓誌》云:
今居守魏王(即張全義),昔在懷覃,將建勛業而切於求士,乃早知其名,即招居麾下,乃授以右職,掌其要司。……以開平四年九月十三日,自檢校兵部尚書轉右僕射,授柳州刺史。(梁)太祖因召對便殿,頒賜獎諭,至於再三。府君(張濛)始以盡節許主,不貪其榮,固請不之所任。[注]《張濛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59頁。
張濛早年被張全義招致麾下,成爲幕僚。後梁太祖將其提拔爲柳州刺史,他卻要“盡節許主”,顯然將張全義視爲自己唯一的君主,而不爲梁太祖高官所動,而梁祖也對其無可奈何。這亦是張全義勢力入梁後仍保有獨立性之一證。
張全義本人也深知此點,故而在後梁建國之時,爲避嫌疑,主動要求改名。《新五代史·張全義傳》云:“唐亡,全義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奭。太祖猜忌,晚年尤甚,全義奉事益謹,卒以自免。”[注]《新五代史》卷四五《張全義傳》,第490頁。胡三省更直言“帝舊名全忠,故更全義名宗奭”。[注]《資治通鑑》卷二六六,後梁太祖開平元年七月條,第8684頁。朱全忠在登基後,已改名朱晃,“全義”二字並不犯諱。張全義仍要改名“宗奭”,只能理解成是“奉事益謹”的表現,同時也説明了朱全忠對曾與自己並駕齊驅的張全義,確實存在着“猜忌”。
唐莊宗滅梁興唐之後,張全義馬上“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名”。[注]《新五代史》卷四五《張全義傳》,第491頁。這裏的“故名”當然不是其本名“張言”,而是唐昭宗所賜的“全義”。唐莊宗一直以中興大唐爲口號,這樣一位重臣改回舊名,代表着唐室權威的恢復,正是投其所好。
張氏家族中被賜名的不止張全義一人。上文已經指出,張全義有弟全恩、全武,又考慮到其原本名爲張言或張居言,兄弟不當以“全”字爲行輩,於是我們有理由推定張全武、張全恩二人亦屬賜名,賜名時間應當與張全義同時。然而在張全義被賜名之前,張全武已被晉軍俘虜。很難想像,身在囹圄的張全武能够順利改名,故“全武”一名,當是張全義投降後唐,復名“全義”之後的産物。而在此之前出現的記載,則是史書采用統一姓名的書寫模式的體現。
其實,不僅是張全義及其兄弟的名字屢次變動,他的子侄可能也同時受到了影響。上節我們考訂了張氏譜系,張全義有子繼業、繼祚,還有一名養子名繼孫;張全恩有子名繼昇,是張氏第二代皆以“繼”字爲行輩。《張繼業墓誌》載繼業六子,名爲季澄、季榮、季昇、季荀、季鸞、季宣,[注]《張繼業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160頁。《張繼昇墓誌》云:“親侄季弘”,[注]《張繼昇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310頁。則是張氏第三代皆以“季”字爲行輩。
但在後梁之時,張氏家族還未有如此齊整的字輩排行。雖然《新五代史·張全義傳》中載“(梁)太祖兵敗蓨縣,道病,還洛,幸全義會節園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繼祚憤恥不自勝,欲剚刃太祖”。[注]《新五代史》卷四五《張全義傳》,第490頁。看似在後梁之時,張全義之子已名“繼祚”,然而這個名字很可能和“全義”一樣屬於後人的改寫。《資治通鑑》記載此事,把“全義”换成了梁名“宗奭”,[注]《資治通鑑》卷二六八,後梁太祖乾化元年七月,第8744頁。更符合歷史事實,只是“繼祚”一名,仍非舊文。此條最爲原始的記載出自王禹偁的《五代史闕文》,其辭云:
梁乾化元年七月辛丑,梁祖幸全義私第。甲辰,歸大内。《梁史》稱:“上不豫,厭秋暑,幸宗奭私第數日,宰臣視事於仁政亭,崇政諸司並止於河南府廨署。”世傳梁祖亂全義之家,婦女悉皆進御,其子繼祚不勝憤耻,欲剚刃於梁祖。[注]《五代史闕文》,第2453頁。
其中“《梁史》”,指的是後梁實録(最可能爲《梁太祖實録》),而非《舊五代史》中的《梁書》部分。[注]關於《五代史闕文》史源的討論,參見拙作《五代正統性與司空圖形象的重塑 ——〈舊五代史〉原文有無〈司空圖傳〉問題再探討》,《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2輯,2015年,第165—186頁。而《梁史》所云的内容也即此事的最早史源,其中並無張繼祚的身影。换言之,歐陽修、司馬光所載,只是“世傳”的内容,名字自然也是以最終流傳的名字爲準,並不能證明其在後梁時的實際情況。
更爲直接的證據是上節提及的張衍,他在後梁乾化二年時被梁太祖處死,名字自然也不會再産生變動。他是張全義的侄子,與張全恩之子張繼昇具有同樣的身份,卻並不以“繼”字爲行輩。這也證明了張氏家族的行輩産生於後唐之時,最可能是隨着張全義第三次改名而整齊化的[注]閆建飛文引《張繼達墓誌》叙繼達改名一事云:“公諱繼達,字正臣。入仕之始,梁季帝賜名昌遠。後莊宗皇帝即位,公以名與廟諱同,遂改斯名耳。”可見張氏第二代最初被梁末帝賜聯“昌”字,“繼”字確系後唐莊宗所賜。參閆建飛: 《唐末五代宋初北方藩鎮州郡化研究(874—997)》,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17年,第183—185頁。。
最後,還要對張氏第二代爲何要以“繼”字行輩略作推測。該字來源很可能與唐莊宗有關。我們知道,唐莊宗滅梁之後,對張全義甚爲重視,多次對其施以家人之禮。如初見之時,便“詔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注]《舊五代史》卷六三《張全義傳》,第841頁。其後莊宗妻劉后又“欲拜全義爲義父”,莊宗許之,甚至對張全義“敦逼再三”,最終全義“不獲已,乃受劉后之拜”。[注]《舊五代史》卷六三《張全義傳》,第842—843頁。此舉招來了後世史家的强烈批判,胡三省云:“繼岌,皇嗣也,豈可兄事梁之舊臣!存紀,皇弟也,既使其子以兄事全義,又使其弟以兄事全義,唐之家人長幼之序且不明矣;是後中宫又從而父事之,嘻,甚矣夷狄之俗好貨而已,豈知有綱常哉!”[注]《資治通鑑》卷二七二,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月,第8902頁。
確實,施禮者的區别導致了張全義同時成爲了莊宗的長輩(以劉后論)、平輩(以李存紀論)、晚輩(以李繼岌論),而這種倫序上的混亂恰恰反映出唐莊宗還未思考清楚應該如何與這位後梁重臣相處。如在同光元年十一月,對張全義的處理是“以洛京留守、判六軍諸衛事、守太尉、兼中書令、河南尹、魏王張全義爲檢校太師、守中書令,餘如故”,[注]《舊五代史》卷三《唐莊宗紀四》,第420頁。只是在加官上進行了變更,其本職工作並没有改動。次年二月,“以檢校太師、守尚書令、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魏王張全義爲守太尉、兼中書令、河陽節度使、河南尹,改封齊王”,[注]《舊五代史》卷三一《唐莊宗紀五》,第429頁。加官又變回了“守太尉”,王爵由魏而齊,又加兼河陽節度使。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張全義仍保有“判六軍諸衛事”的權力,也即禁軍仍在其掌握之下。直到一個月後,才由“皇子繼岌代張全義判六軍諸衛事”。[注]《資治通鑑》卷二七三,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三月,第8918頁。這再次説明了,唐莊宗對後梁重臣的安排是在不斷調整之中的,需要雙方不斷的磨合博弈。
最終唐莊宗采用了賜姓名的辦法來安撫後梁降將,其中大多被賜予了疏支的“紹”字爲行輩,而對於地位特别崇高的人物,則被賜予了莊宗嫡系的“繼”字作爲行輩。[注]關於唐莊宗賜予姓名一事,可參拙作《姓甚名誰: 後唐“同姓集團”考論》,西北大學: 《“區域視野下的中古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五届中國中古史前沿論壇會議論文集》,2017年。其中代表的是後梁重臣朱友謙,入唐後,莊宗“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命繼岌兄事之”,[注]《資治通鑑》卷二七二,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一月,第8905頁。這和張全義的待遇如出一轍。然除地位之外,與莊宗劉后關係親密者,也會被賜以“繼”字。如李繼宣,《北夢瑣言》載:“李繼宣,汴將孟審澄之子,亡命歸莊宗,劉皇后蓄爲子。”[注](五代)孫光憲著,賈二强點校: 《北夢瑣言》卷一八“明宗誅諸凶”條,北京: 中華書局,2002年,第334頁。又如李繼陶,爲莊宗徇地河北(天祐八年,911)時所得小兒,後收養宫中,故名之爲“得得”,及長,賜名繼陶。[注]《舊五代史》卷五四《李繼陶傳》,第733頁。繼宣、繼陶身份都相當一般,更談不上有功於國,只是因受寵而被賜以姓名。張全義父子一則地位崇高,二則被待以家人之禮,如此視之,莊宗選擇將兒子的“繼”字作爲張氏二代子弟的行輩,以示親近拉攏之義,是完全有可能的。
以上討論了張全義家族改名的時間、經過以及其時代背景。他的改名不僅是出於個人安危的變通之舉,其中更參雜了唐昭宗借助張全義平衡朱全忠勢力、梁太祖樹立自身權威、唐莊宗强調恢復唐室、安撫後梁降將等多重政治意圖,是五代政權更迭頻繁的時代特徵最爲直接的體現。而其子孫的仕宦履歷,則更是這種時代潮流衝擊下的産物,也是我們下節討論的重點。
四、 張氏子弟仕宦及其衰弱
以張全義功業之盛大,位望之顯赫,尚且連姓名都無法做主,其子孫的仕宦自然也常爲時勢所左右,折射出動蕩的光影。我們可以通過對其家族的興衰沉浮,窺見時局之變動。
首先張全恩,《蘇氏墓誌》稱“當齊王節制洛師之始,太保公分總兵戎,控臨河上。時密邑大夫爲孟州糾,以是得議姻好”。[注]《蘇氏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163頁。其中齊王爲張全義,太保公即張全恩,密邑大夫是誌主的父親蘇濬卿,因其曾任河南府密縣令而得名。所謂的“得議姻好”,即指誌主蘇氏嫁給了張全恩的塚子“僕射清河公”,惜乎其名字不存。
這條材料中提到張全義“節制洛師之始”,也即第一次爲河南尹,時在光啓三年六月。從張全恩與“孟州糾”蘇濬卿結親來看,所謂的“控臨河上”,也必與孟州相臨近。而當時孟州正是河陽節度的治所,在李罕之的控制之下。張、蘇的姻好,一方面代表了張全義與李罕之在蜜月期的結合,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張全義勢力在河陽的滲透。這也是爲何張全義後來能輕易的攻佔河陽的重要因素。
李罕之被逐之後,引晉軍南下,張全義亦依附朱温,請梁兵救援。梁晉大戰,最終以朱全忠一方的勝利而告終,朱全忠乘勢控制了河陽、懷州,其間雖也多次指派麾下名將出任河陽節度使,但最終還是於景福元年(892)二月“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河陽節度使”。[注]《資治通鑑》卷二五九,唐昭宗景福元年二月條,第8246頁。《舊唐書》卷二上《昭宗紀上》云:“五月甲辰,制以河南尹張全義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兼孟州刺史,充河陽三城節度、孟懷澤觀察等使。”第748頁。其中二月到五月的差别,當是朱全忠上表與昭宗正式下制的區别。《張繼業墓誌》中稱“齊王令公已三鎮懷孟矣”,[注]《張繼業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159頁。這便是第一次。
再看懷州刺史。懷州本是河陽節度的治所,至會昌四年(844)河陽才移鎮孟州。而此時懷州處於梁晉交界的最前綫,是河陽乃至洛陽、開封的門户,位置亦十分重要。故朱全忠先後令得力幹將丁會(文德中,888)、葛從周(乾寧二年,895)出任懷州太守。[注]參郁賢皓: 《唐刺史考全編》,合肥: 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83頁。然據上文引李綽《昇仙廟興功記》云:“今河陽行軍懷州刺史僕射清河張公,即留守太保相君之令弟……時乾寧四年正月三日記。”[注]《昇仙廟興功記》,《全唐文》卷八二一,第8650頁。則在乾寧四年時,懷州刺史换成了張全恩。也即是説,張全義兄弟在此時控制了洛陽、河陽、懷州等黄河兩岸地區,勢力到達了一個高峰。
張氏家族的第三位核心人物當屬張全義長子張繼業。他在新舊《五代史》中無傳,幸運的是卻有墓誌留存,爲我們了解其生平乃至當時的政治環境提供了新的資料。據其墓誌云他“享年五十三”“即以同光三年(925)二月二十一日歸葬於河南縣徐婁村先郡夫人塋之南隅”,[注]《張繼業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160頁。知其當生於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然墓誌中敍其官位,卻是從昭宗遷洛的天祐元年(904)開始。誌文云:
年號天祐,歲當甲子,昭宗皇帝遷市朝文物,宅於東周,時公始妙齡,抑有休問,既彰官業,仍振軍聲,累遷環衛將軍、六宅使,相繼兼左右僕射。[注]《張繼業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158頁。
而這時張繼業已經三十有餘,張全義也早已控制洛陽、河陽達十餘年。按照當時習慣,張繼業應該早已出仕乃父幕下,獲取一官半職,但這些在墓誌中卻絲毫没有提及,只是隱晦的稱“即彰官業,仍振軍聲”。之所以要隱去此前歷官,而從昭宗遷洛之後開始計算,是爲了强調張繼業的環衛將軍、六宅使、左右僕射等官職,得到了唐室的正式承認,而非張全義、朱全忠等私相授受。而這種書寫模式的背後,是當時(後唐同光三年)强調唐室正統的政治環境。這一點在墓誌中還有更爲直接的體現:
堯水忽降,禹功未宣,天厄漢圖,運僭新室。公以爲無砥礪則匪石之心莫展,避羅網則長纓之志不申,默藴沉機,何妨立事。授鄭州防禦使……爰自檢校司徒,領鄆宋兩鎮留務……奪情授六軍副使,出爲淄沂二州牧……改亳州團練使……由是擢拜河陽留後。[注]《張繼業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158—159頁。
志文中備述張繼業在後梁任官,這其實在當時政局中頗爲敏感。後唐李琪在爲霍彦威撰寫神道碑時,“敍彦威仕梁歷任,不言其僞”,最終“望令改撰”。[注]《舊五代史》卷五八《李琪傳》,第786頁。可見是否僞梁,仍是當時朝堂關注的焦點。《張繼業墓誌》的作者唐鴻在此點上就較爲謹慎,稱“天厄漢圖,運僭新室”,點出後梁屬於僭僞。同時爲張繼業的經歷做出辯解,認爲其出仕僞朝,是在“砥礪匪石之心”,是在“默藴沉機”,等待時機,故而不妨立事。
實際上,張繼業在僞梁之功業,對其意義頗爲重大。誌文在其任河陽留後時,仍忍不住稱“加以詳鄭亳之政績,聽淄沂之詠歌”,指的便是其出任鄭州防禦使、淄沂二州刺史、亳州團練使的經歷,並對其政績加以了充分肯定。甚至到了天福五年時胡熙載所作的《李氏墓誌》仍稱“爰自牧民淄沂,去虎鄭亳,皆敷美政,盡布化條”,[注]《李氏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327頁。李氏是張繼業兒媳,墓誌中還要對其功業如此渲染,一方面説明了這段經歷確實是張繼業仕宦生涯中的亮點;另一方面也説明了在後晉之時,是否以梁爲僞已變得不再那麽重要,無需在誇耀之前加上限定解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張繼業墓誌》中對唐莊宗保留了張繼業河陽留後一事描繪得頗爲詳盡,多有頌德謝恩之意,其詞云:
上(莊宗)嘉是懿績,首議明恩。尋拜(張全義)守太尉、中書令,復兼河陽節制。仍自大魏,改封全齊,異姓之褒,當代稱美。不易(張繼業)專留之務,俾分共理之權,地則三牆,境才兩舍,雞犬之聲相接,山河之勢不遥。欲使榮家,勵其報國,豈待祁奚之舉,雅知羊祜之清,識魚水之諧和,見君臣之際會。[注]《張繼業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159頁。
這裏雖然提到張全義復兼河陽節制,但其實張全義實際職務仍是河南尹,其人在洛陽。而河陽政務,仍由張繼業處理。父子治所相接,也即所謂“不易專留之務,俾分共理之權,地則三牆,境才兩舍,雞犬之聲相接,山河之勢不遥”。而在《李氏墓誌》中則稱“其後曆汶上睢陽,主留懷孟,偶未正節鉞,俄歎壞梁”,[注]《李氏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327頁。則深以未能從河陽留後升任節度使爲憾,全未顧忌河陽節度使實爲張全義。
之所以産生這種差異,除《張繼業墓誌》是“奉命書”,[注]《張繼業墓誌》末尾云:“河南府隨使押衙兼表奏孔目官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趙榮奉命書”,《五代墓誌匯考》,第161頁。本就要更多的體現唐莊宗的恩德之外,更是因爲張氏家族在後晉之時已頗爲衰弱,故而對張繼業未能更進一步便英年早逝抱有强烈的遺憾之情。如李氏是張繼業第六子張季宣之妻,在墓誌中敍張全義、張繼業事迹頗詳,對季宣的官位卻隻字不提,只是稱“青史尤新,必復公侯之位;令名積善,克承基構之功。”[注]《李氏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327頁。從“必復”一語中,一方面可以窺見張氏家族企圖振作的決心,另一方面更説明張季宣不僅早已喪失了公侯的地位,甚至連在墓誌中值得一提的官位也不存在,只得寄希望於未來。
稍早一些的《張繼昇墓誌》中也有類似的表述:
上古之秩,司空以平秩爲重;西京之謀,亞相已弄印爲尊。雖異於真銜,亦非輕受。公侯未復,方慊於下僚;陵穀遽遷,俄悲於逝水。[注]《張繼昇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310頁。
張繼昇是張全恩三子,張繼業之堂弟。此條材料的前兩句指張繼昇曾任檢校司空、檢校左僕射,然而這些都“異於真銜”,只是加官而已。而他的職事官只是左領衛將軍、左神武將軍,也早已成爲了虚銜,没有實際權力,故誌文中才稱其“慊於下僚”。他和張季宣一樣,都被家族寄予了復公侯之位的期望,但最終仍以失敗而告終。
那麽,顯赫一時的張氏家族何以會迅速衰弱呢?王禹偁在評價張全義時,展開了激烈的批評,並云“斯蓋亂世之賊臣耳,得保首領,爲幸則多。晉天福中,其子繼祚謀反伏誅,識者知餘殃在其子孫也。”[注]《五代史闕文》“張全義條”,第2454頁。將其餘殃歸結在子孫上。除提到張繼祚謀反一事外,還有一條與“子孫”有關。那便是張繼業告發全義養子繼孫,導致後者被殺一事。《册府元龜》卷九三四《總録部·告奸》云:
後唐張繼業爲河陽兩使留後。莊宗同光三年六月,繼業上疏,稱:“弟繼孫,本姓郝,有母尚在。父全義養爲假子,令官衙内兵士。自皇帝到京,繼孫私藏兵甲,招置部曲,欲圖不軌,兼私家淫縱,無别無義。臣若不自陳,恐累家族。”敕:“有善必賞,所以勸忠孝之方;有惡必誅,所以絶姦邪之迹。其或罪狀騰於衆口,醜行布於近親,須舉朝章,冀明國法。汝州防禦使張繼孫,本非張氏子孫,自小丐養,以至成立,備極顯榮,而不能酬撫育之恩,履謙恭之道。擅行威福,嘗恣姦凶,侵奪父權,惑亂家事,從鳥獸之行,畜梟獍之心,有識者所不忍言,無賴者實爲其黨。而又横徵暴斂,虐法峻刑,藏兵器於私家,殺平人於廣陌。罔思悛改,難議矜容,宜竄逐於遐方,仍歸還於姓氏,俾我勛賢之族,永除污穢之風。凡百臣僚,宜體朕命,可貶房州司户參軍同正,兼勒復本姓。”尋賜自盡,仍籍没資産。[注]《册府元龜》卷九三四《總録部·告奸》,第11015頁。
首先需要説明的是,《舊五代史·唐莊宗紀六》將此事繫於同光二年六月條下,影庫本粘簽引上述《册府》材料,亦作“同光二年六月”,與今明本《册府》做“同光三年六月”不同。現存宋本《册府》中此卷恰好缺失,邵晉涵所見或即本此。現據《張繼業墓誌》,張繼業卒於同光三年二月,不容於六月告發繼孫,可知《舊五代史》爲是,明本《册府》有誤。
張繼孫的罪行歸納有三: 一,侵奪父權,惑亂家事;二,横徵暴斂,虐法峻刑;三,私藏甲兵,招置部曲。然揆諸史籍,有些罪行恐是子虚烏有。首先侵奪父權一條,即不可能成立。據《舊五代史·莊宗紀五》云“(同光二年)二月以楚州防禦使張繼孫爲汝州防禦使”,[注]《舊五代史》卷三一《唐莊宗紀五》,第430頁。張繼孫一直在楚州、汝州任官,如何能侵奪身在洛陽的張全義之權力?同樣的道理,“惑亂家事”“私家淫縱,無别無義”一事亦難以成行。若是張繼孫外放之前所爲,那麽張繼祚當在彼時已知此事。需知當年梁太祖淫亂張家,張繼祚尚且“欲剚刃於梁祖”,[注]《五代史闕文》“張全義”條,第2453頁。若繼孫果有是行,即使不爲其“剚刃”,恐也早已被告發,又如何能爲楚州、汝州防禦使?
再看第二項罪名,這種酷戾之風,在五代頗爲盛行。張全義號稱“朴厚大度,敦本務實,起戰士而忘功名,尊儒業而樂善道”,[注]《舊五代史》卷六三《張全義傳》,第842頁。然亦不乏“虐法峻刑”之事。《五代史闕文》載“河南令羅貫,方正文章之士,事全義稍慢,全義怒告劉皇后,斃貫於枯木之下,朝野冤之。洛陽監軍使常收得李太尉平泉醒酒石,全義求之,監軍不與,全義立殺之,其附勢作威也又如此”。[注]《五代史闕文》“張全義”條,第2454頁。可見横徵暴斂、嚴刑酷法實爲當時之常態,不足爲奇。而且舉報繼孫此事,對張氏家族而言得不償失,恐怕並非繼業本意所在。
真正致命的是第三項内容,也即“私藏兵甲,招置部曲,欲圖不軌”。按五代積習,節帥刺史往往蓄有私兵部曲。如《玉堂閒話》載“梁朝將戴思逺任浮陽日,有部曲毛璋,爲性輕悍,常與數十卒追捕盜賊。”[注](五代)王仁裕: 《玉堂閒話》卷一“戴思遠”條,傅璇琮: 《五代史書彙編》,杭州出版社,2005年,第1839頁。又如楊光遠“私養部曲千餘人,撓法犯禁,河、洛之人,恒如備盜。”[注]《舊五代史》卷九七《楊光遠傳》,第1291頁。風氣如此,張繼孫招所爲本屬尋常,但壞在時機之上。上文已經提及,張全義在同光二年三月,“判六軍諸衛事”之職被李繼笈所取代,交出了禁軍軍權。莊宗正欲藉此樹立皇子權威,繼孫在此時招置部曲,仿佛正在暗示張全義對此有所不滿。張繼業身爲後梁降將,在此敏感之時,不得不選擇告發義弟,以打消莊宗疑慮,也即所謂“若不自陳,恐累家族”。莊宗明曉其心意,故在詔中添加了張繼業並未舉報的“侵奪父權”之罪名,並强調“仍歸還於姓氏,俾我勛賢之族,永除污穢之風”,將繼孫改還郝姓,以示其罪行與張氏家族無關。
張繼業通過舉報義弟的方式使得張家避開一劫,可惜的是,這位張氏二代中的核心人物卻在八個月後去世,死在了張全義之前。繼業終年五十三歲,雖不能稱之爲早夭,但未能與乃父完成交接,將其政治資本繼承下來,恐怕才是張氏家族面臨的最大挑戰。
在此情況下,延續家業的重任便落到張季澄的頭上。他是張繼業的嫡長子,三代子弟中的頭面人物。據《張季澄墓誌》,他卒於清泰二年(935)七月二十日,終年三十八歲,也即生於光化元年(898),在張繼業去世時年僅29歲。而當時其官位爲“紫金光禄大夫、右威衛大將軍”,[注]《張季澄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274頁。與其叔父繼祚的“左武衛大將軍”同級,[注]《張繼業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160頁。更遠在諸弟之上。這説明當時張季澄已經被當作家族的核心人物培養,晉升速度遠超其他二代子弟。更爲關鍵的是,在張繼業死後,季澄卻並未守喪。《張季澄墓誌》云:
屬先太保即世,難抑因心,幾至滅性,如荼之痛何極,絲綸之命旋臨。遽奪苴麻,俾從金革,爰授起復雲麾將軍,餘如故。[注]《張季澄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274頁。
張季澄的奪情起復,一方面固然是唐莊宗的恩典,旨在安撫拉攏張全義;另一方面,張氏家族接受此安排,並不堅持服喪禮制,也可窺見其急於推出繼任者的迫切心情。而且張季澄此前階官爲正三品的文散官“紫金光禄大夫”,而在奪情之後變爲了從三品的武散官的“雲麾將軍”,品階雖然有所下降,卻由文轉武,也即所謂的“俾從金革”,開始接觸軍權。
然而朝局再起波瀾,李嗣源在同光四年三月借討伐趙在禮之機,於鄴都發動兵變,率兵南下。而舉薦李嗣源北討平亂的正是張全義,全義也因此“憂懼不食”,馬上“卒於洛陽”。[注]《資治通鑑》卷二七四,唐明宗天成元年三月,第8968頁。此後李嗣源大軍逼近洛陽,莊宗帥諸軍出逃,卻爲左右所殺。而張季澄正在諸衛之中,墓誌中所云“遇莊宗晏駕,公恭陳警衛,禮畢橋山”是也。[注]《張季澄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274頁。
由於張季澄曾是莊宗宿衛,等於站在了新君唐明宗的對立面。雖然明宗在登基之初並未針對季澄,相反還將其“進封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卻並没有如莊宗一樣奪情,而是任由季澄守喪,其實即是默認免官。也即是説,張季澄在還未充分成長的時候,張全義這顆參天大樹便已倒下。此時季澄的去官守喪,不僅使得張氏在朝堂上出現了權力真空,更再次喪失了交接政治資源的機會。這也使得張氏家族的衰弱瞬間突顯出來。
這種情況在季澄守喪完成之後也並未得到好轉。雖然墓誌中稱“服闕,落起復階,官勛封並如故”“明宗睠注彌深,嘉稱每切”,但這或許只是掩飾明宗打擊身爲莊宗衛宿虚詞,也可能是季澄確實在莊明政變之中受到打擊,對仕途心灰意冷,故而選擇了“堅辭貴位,唯事燕居”,[注]《張季澄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274頁。最終再也没有出仕。
《張季澄墓誌》中還稱“而又昆弟間各揚名稱,悉務矜持”,[注]《張季澄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274頁。則在暗示他們雖是名家子弟,仕途上卻並不順利。如在墓誌末尾對“公仲弟前度支巡官季鸞”多有誇炫,甚至到了“朝野所欽,公卿共仰”的地步,仕途上也“爰奉相筵,嘗修邦計”,[注]《張季澄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275頁。似乎成爲季澄之後的另一政治新星。但張季鸞的官位只是“前度支巡官”,説明此時並無官銜。而這個“前”字,還要追溯到同光三年(925)張繼業去世之時。《張繼業墓誌》敍諸子仕宦云:
長子曰季澄,今任右威衛大將軍。第二子曰季榮,太子舍人。第三子曰季昇,國子大學博士。並銀印朱紱,皆先公而逝。第四子季荀,著作佐郎。第五子曰季鸞,度支巡官、大理評事。第六子曰季宣,千牛備身。[注]《張繼業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160頁。
《張季澄墓誌》撰於清泰三年(936),居然還要追敍季鸞十年前的官職,可見在這十餘年間,張季鸞可能也並未出仕。而其他子弟中,季榮、季昇二人已先於張繼業去世,無需再言。《張季澄墓誌》稱季鸞爲“仲弟”,並未提及四弟季荀,可能在清泰三年之時,季荀也已去世。季宣在上文中已經提及,他妻子李氏的墓誌之中,亦未曾記載其官職,可能也和季鸞一樣,因對此守喪,失去了千牛備身的身份。張繼業一支在張季澄不肯出仕之後,可以説已經徹底衰弱。
而張全義另一個兒子張繼祚的境遇要稍好一些。《舊五代史·張繼祚傳》云“始爲河南府衙内指揮使,全義卒,除金吾將軍,旋授蔡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明宗郊天,充供頓使,復除西衛上將軍。唐清泰末,丁母憂。”[注]《舊五代史》卷九六《張繼祚傳》,第1274頁。而據《張繼業墓誌》可補其在同光三年時官銜爲“左武衛大將軍”,[注]《張繼業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160頁。據《張季澄墓誌》可知其在清泰三年爲“檢校太保、右驍衛上將軍”。[注]《張季澄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274頁。繼祚曾外放蔡州刺史,又回京爲從二品的右驍衛上將軍,較之季澄,已頗有起色,若潛心經營,未必不能復振家聲。然其在丁憂之時,卻捲入了張從賓之叛亂。史稱:
天福初,喪制未闋,會張從賓作亂,發兵迫脅,取赴河陽,令知留守事。從賓敗,與二子詔戮於市。[注]《舊五代史》卷九六《張繼祚傳》,第1274頁。
有關張從賓與張繼祚之關係,第二節中已有所考證,此處不再贅言。總之,最終結果以張繼祚一支斷絶而告終。這徹底宣告了張氏家族復興的失敗,由王侯之後成爲了叛臣之族。這在張全恩之子張繼昇的墓誌中表現得尤爲明顯。
需要指出的是,《張季澄墓誌》與《張繼昇墓誌》的作者是同一人,即五代著名文士楊凝式。他在後梁曾任洛陽留守巡官,是張全義的幕僚,對張氏一族頗爲熟悉。但這同一作者爲同一家族所作的兩方墓誌,卻有着天壤之别。不僅在篇幅上前者多達兩千餘字,敍季澄仕宦經歷頗詳,甚至還精心解釋其在明宗朝隱世不出的原因。而後者不足千字,只是單調的羅列了繼昇所曆官職,文詞單調,絲毫看不出作者“大手筆”的風采。其間的區别不僅是楊凝式個人態度的轉折,同樣也是張氏政治境遇下降的反映。
更爲重要的是,在《張季澄墓誌》中,楊凝式花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誇耀張全義、張繼業父子(當然也包括他們的妻子)的德行功業。但在《張繼昇墓誌》中,卻對家族中最爲重要的人物——張全義——隻字不提,敍及張全恩之時,也只簡單的稱“先考諱全恩,累贈檢校太保,守懷州刺史”。[注]《張繼昇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309頁。這又與其他墓誌形成了差異,如同爲張全恩兒媳蘇氏墓誌稱“公即故懷州刺史太保公之塚子也。太保公,齊王令公親仲弟也。”[注]《蘇氏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162—163頁。女婿王禹墓誌稱“府君夫人清河張氏,即故齊王親弟諱全恩之女也,故齊王之親猶女也。”[注]《王禹墓誌》,《五代墓誌匯考》,第243頁。蘇氏和王禹都是張全恩一支的親屬,但他們的墓誌之中都將全恩依附於全義之下,仿佛非如此則不足光耀家聲一般,這當然是與張全義的崇高地位是相匹配的。而基於同樣的道理,當張全義一支或隱或誅之後,張繼昇家人便不希望再與其發生交集,在墓誌中將其伯父事迹全然抹去,與亂臣賊子做了徹底的割裂。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喪失了繼承張繼業政治資本的可能,再也没有活躍的表現。
與之對應的,張全義一支雖屢遭打擊,然亦受其遺澤甚深,直到北宋仍有全義七世孫張奎、張亢兄弟仕宦顯達。而他們的父祖,亦有官位在身。富弼《張樞密墓誌銘》云:
以皇祐五年閏七月十六日葬於南京某縣某鄉某里……皇曾祖裕,好學,避周漢亂,不仕。皇祖居實,終鄂州嘉魚令。考餘慶,官贊善大夫,贈兵部尚書。妣宋氏,贈廣平郡君。自皇祖之前皆葬魯城,公用吉蔔,獨舉考妣二喪葬於宋。故公之喪亦從而歸之,今遂爲宋人。[注]《張樞密墓誌銘》,《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之卷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50册,第291頁。
這段材料除了記載張居實、張餘慶官位之外,透露了兩點重要信息。其一,從張氏出土的多方墓誌來看,張全義子孫也即張奎之六、五世祖皆葬於洛陽。而張奎祖父以前皆葬魯城,説明張氏中的一支曾有過遷徙,從洛陽移居到了魯城,而遷徙時間,至遲不晚於曾祖張裕活動的周漢之時。其二,張奎父子葬於南京應天府(唐代宋州),故其“遂爲宋人”,説明在張餘慶之時,張氏一族又已遷到了宋州。
值得注意的是張裕所謂的“避周漢亂”。從漢隱帝於乾祐三年(950)十一月丙子誅殺楊邠、史弘肇、王章引發政變開始,到乙酉郭威入開封,隱帝被弑,不過半月有餘,其間亦無大戰,似乎無需也無法搬遷避亂。而在稍後,兗州節度使慕容彦超據州叛亂,旋即被曹英、史彦韜等平定。魯城距兗州極近,正是慕容彦超控制的核心區域。很難想像張氏會爲了避禍,從較爲安定的洛陽遷徙至戰亂中心的魯城。故我們有理由推測,張氏的遷徙更在周漢易代之前。那麽,所謂的“避周漢亂,不仕”可能就有兩種解讀。一是張裕知道慕容彦超必敗,没有出仕彦超幕下;二是張裕曾依附慕容彦超,在戰敗後被剥奪了官身,“不仕”只是較爲委婉的説法。但無論如何,張氏一族再次因朝代更迭受到了嚴重打擊,跌至了谷底,直到宋朝建立之後,才逐漸復興起來。
小 結
本文利用近年洛陽出土的多方張全義家族墓誌,結合傳統史籍,對張氏家族的籍貫、譜系做出了梳理,使得我們對其基本構成有了更爲清晰的了解。而在此基礎上,詳細地討論了張氏家族的興衰成敗與當時政治環境變動之間的關係。張全義能從一介農夫,成長爲洛陽河陽兩岸的控制者,得益於唐末動蕩分裂的大環境。而當軍閥兼并逐漸完成之時,張全義閃轉騰挪的餘地也就愈發狹小。在唐昭宗入洛之前,還能與朱全忠相抗衡的“全義”,在入梁之後也只能改爲“宗奭”。而在後唐建立之時,又在中興唐室的旗號下,改還成了全義。這看似細微的名字改動,背後反映的是藩鎮不斷衰弱,權力由分散轉爲集中的歷史重大轉折。
以張全義的權勢聲望,名字尚且不能自主。其子孫的仕途命運就更易受到政局變動的影響。從張繼業舉報義弟繼孫的主動避禍,再到張季澄在莊明易代之際的消極應對,再到後晉初年張繼祚被迫卷入叛亂的無奈,直至周漢易代時張裕的避亂不仕,每一次政權更迭,往往都對張氏家族産生了重大打擊。這其中既有命運不幸的偶然成分,也是晚唐藩鎮軍閥逐漸退場的必然發展。在五代亂世以軍功、門蔭走入仕途的張氏家族,隨着時代的發展,在北宋已經成爲兄弟父子相繼進士及第的詩書之家。[注]張奎之子張燾亦舉進士,後爲龍圖閣直學士。通過張氏家族發展變遷的細緻考察,對我們深入體會唐末五代乃至北宋的時局變動有着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