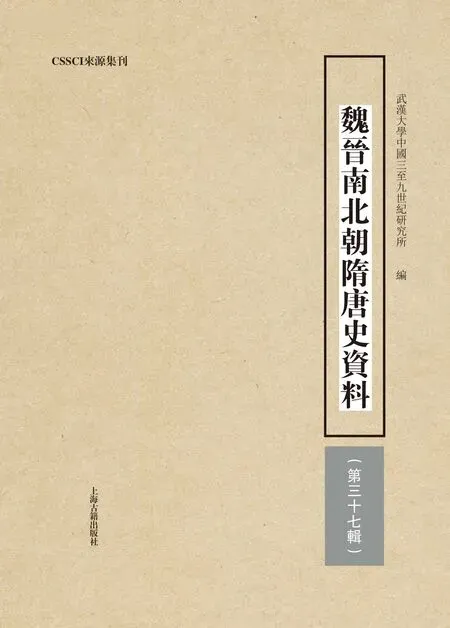唐長孺讀《流沙墜簡》筆記校證*
王 素
唐長孺師在20世紀80年代中葉,曾撰七律憶舊,其頷聯云:“平生不負雕蟲手,垂老猶詮發冢書。”[注]王素箋注: 《唐長孺詩詞集》丁卯(1987)條,北京: 中華書局,2016年,第104頁。“發冢書”指《吐魯番出土文書》。可知唐師是將整理《吐魯番出土文書》視爲自己“垂老”最重要的事業的。唐師爲整理《吐魯番出土文書》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在唐師故宅保存的尚待整理的衆多遺稿中,僅讀《吐魯番出土文書》筆記就有三册,近四百頁。此外,還有不少讀散見吐魯番文書卡片,讀《吐魯番出土文書》出版物批注,以及《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組成員陳國燦、朱雷、吴震、李徵、程喜霖、王素等談整理工作來信等。談到《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整理,大家都只知道出版物的成品樣式,不知道這個成品樣式的形成過程。因此,我們準備以《唐長孺讀吐魯番文書筆記》爲名,將前揭相關遺稿皆整理出版。本文揭載之讀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筆記,亦爲整理《吐魯番出土文書》準備工作之一,且時間較早,故先行整理校證,以饗讀者。
説 明
一、 筆記寫於“文物出版社稿紙”正面,凡四頁,十六條。背面爲唐師讀《南齊書》札記,凡四十六頁。筆記時間應該在前,札記時間應該在後。
二、 筆記所據《流沙墜簡》是何版本不詳,爲便於讀者核對,整理者根據中華書局1993年影印1934年修訂版《流沙墜簡》,在原文後括注影印版頁碼。
三、 筆記整理分“原文”與“校證”二項,“原文”爲唐師夾敍夾議文字,“校證”爲整理者解説。“原文”中的《王釋》爲王國維《流沙墜簡考釋》略稱,《文書》爲《吐魯番出土文書》略稱,顯示筆記係爲整理《文書》而作。
四、 筆記係唐師寫給自己看的文字,較爲隨意,故體例並不統一。譬如俗字與正字混用,“缺”與“闕”不分,漢字數字與阿拉伯數字錯出,引文或加引號或不加引號,“上缺”“下缺”或加括號或不加括號。其他標點亦有不太規範之處。整理者迻録時,在不影響原意的情況下,稍稍做了一些統一工作。
筆 記 整 理
1.高昌土兵
原文: 《流沙墜簡》卷二稟給類四十六簡記稟兵食斛斗,有“□ 栿 五斛四斗稟高昌土兵梁秋等三人,日食六升,起九月一日,盡卅日”。(第169頁)而三十二簡記“出 栿 二斛四斗稟兵鄧□(下缺)兵梁秋等四人,々日食六升(下缺)”,下署“領功曹掾梁鸞”。(第166頁)梁鸞又見第二十八簡及雜事類六十七簡,(第164、205頁)此二簡一爲泰始四年物,一爲泰始五年物,故《王釋》以爲梁鸞、梁秋皆泰始時人。(第170頁)
“高昌土兵”按此簡記稟食共七條,都只記稟兵某人等若干人,獨此稱“高昌土兵”,表明梁秋等四人是由高昌來戍守海頭,不是戊己校尉營兵,而稱高昌,可知當時雖未置郡,實際上已把戊己校尉所管地區稱爲高昌。其稱爲“土兵”不可解,或是征自土人,别於校尉營兵而言。
烽燧類第七簡記“宜禾郡蠭第”,(第129頁)宜禾並非郡,《王釋》以爲殆指宜禾都尉所轄全境。(第131頁)則高昌未置郡前,也可能有高昌郡之稱。
校證: 第三十二簡釋文,原文係按《流沙墜簡》格式照録,即以“出”字頂格,以下爲雙行,分别以“ 栿 二斛”“兵梁秋”開頭,故在下面括有两个“下缺”。此處爲製版方便,改爲單行。此條“高昌土兵”材料,唐師曾在《魏晉時期有關高昌的一些資料》一文中引用。[注]唐長孺: 《魏晉時期有關高昌的一些資料》,原載《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1期,收入《唐長孺文集: 山居存稿》,北京: 中華書局,2011年,第345—355頁。當然,该文根據的羅布泊簡牘材料,並不限於《流沙墜簡》。因爲《流沙墜簡》所收主要是斯坦因在樓蘭等地掘獲的簡牘,而该文還引用了孔好德(Conrady)《斯文赫定在樓蘭所獲的中國文書和零星文物》所收晉代木簡。[注]按: 孔好德,或譯孔好古、康拉迪、康拉德。此書名稱亦有不同譯法,原名與出版信息爲: 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tfen 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 in Lou-lan,Stockholm,1920.因而该文的一些結論,與筆記不盡相同。譬如: 關於“高昌土兵”的含義,该文云:“值得注意的是‘高昌土兵’的稱謂。土兵這一名稱,在當時是不經見的,顧名思義,應該即以高昌土人充當的兵。如果這個推測不誤,那就表明這個自漢以來的屯戍區已存在着一定數量的土生土長的定居人户,也表明戊己校尉所領兵除了來自别地(包括來自海頭和内地州郡)的屯戍兵以外,還有在高昌居民中組成的隊伍。”[注]唐師重視十六國時期高昌郡的兵制,在稍後發表的《新出吐魯番文書簡介》中也説:“從文書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兵士出自兩個來源,一是徵發或稱爲‘入幕’,見哈九一號墓所出《下二部督郵、縣主者符》和阿二二號墓所出《翟蔥等應幕入幢名籍》。符下給主管地方的二部督郵及縣主者,這些兵士稱爲‘見入軍之人’,可知徵自民間。當時南朝是沿襲魏晉相承的世襲兵制,北魏當時基本上以鮮卑和其他少數族人當兵,行之於高昌郡的徵發制度應該也繼承戊己校尉時代遺制。”该文原名《新出吐魯番文書發掘整理經過及文書簡介》,載日本《東方學報》第54册,1982年,收入《唐長孺文集: 山居存稿》,第323頁。關於“高昌”當時是否稱郡問題,该文云:“總之,在(高昌)置郡前,高昌已具有郡的規模以及作爲郡的一切軍、政制度。”均較筆記更加嚴謹。這反映了唐師對這兩個問題前後思想上的變化。
2.器物簿

校證: “折傷弊絶簿”之“弊”,《流沙墜簡》原文作“敝”。“鎧曹請條所領器仗及亡矢簿”“完堅折傷簿”原補寫於“兵四時簿”四字上方,“兵四時簿”右邊有插入符號,遂插補於此。唐師關注此類“器物簿”材料,是因爲《文書》同類材料不少。如闞爽政權有《器物帳》《器物帳殘片》,麴氏王國有《張相受等器物殘帳》《蔡禪師等器物殘帳》。[注]唐長孺主編: 《吐魯番出土文書》,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78、82、369頁。另參王素: 《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第225、226號,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第126頁;王素: 《〈吐魯番出土文書〉附録殘片考釋》,《出土文獻研究》第3輯,北京: 中華書局,1998年,第151頁。不同之處是《文書》稱“帳”,不隨《流沙墜簡》稱“簿”。這反映了唐師對於《文書》的定名,有着自己的思考。
3.襲、褶
原文: 器物類第三十七簡“練復襲一領”,《王釋》:“衣之有著者必具表裏,其無著者則有複有單,複者謂之襲,謂之褶。”(第182頁)又六十三簡有“故黄旃褶一領。賈綵三匹。”(第189頁)
校證: “三十七簡”之“七”,據《流沙墜簡》原文,應爲“八”之筆誤。唐師關注“襲”“褶”,是因爲《文書》“襲”雖未聞,其另名“褶”卻屢見。如闞爽政權《缺名隨葬衣物疏》有“褶一枚”、《苻長資父母墟墓隨葬衣物疏》有“故褶一枚”,麴氏王國《某家失火燒損財物帳》有“綞褶一領”、《章和五年(535年)令狐孝忠妻隨葬衣物疏》有“褶裬三具”、《章和十三年(543年)孝姿隨葬衣物疏》有“故錦褶一枚”、《章和十八年(548年)光妃隨葬衣物疏》有“紫綾褶一枚”,[注]唐長孺主編: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55、91、98、130、143、144頁。另參王素: 《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第233、209、437、300、311、315號,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第127—128、122、186、148、151—153頁。等等,不贅舉。又,“綵”,《文書》所收隨葬衣物疏亦常見,因未入條目,此處不贅證。
4.條
原文: 器物類第五十七簡:“兵曹謹條所領器仗及亡矢簿。”(第187頁)按條,條别也。《文書》有條呈,即條記事項之呈。
校證: “兵曹”之“兵”,據《流沙墜簡》原文,應爲“鎧”之筆誤。另參前揭第2條“器物簿”。唐師關注“條”,如筆記所説,是因爲《文書》有“條呈”類文書。如西涼有《某人條呈爲取 栿 及買毯事》《劉普條呈爲得麥事》《劉普條呈爲綿絲事》,沮渠氏北涼有《玄始十一年(422年)馬受條呈爲出酒事》。[注]唐長孺主編: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6—7、61頁。另參王素: 《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第33、29、30、57號,第77—78、85頁。此外,《文書》屬於“條”文書者,還有“條知”“條次”類文書。如沮渠氏北涼有《義和三年(433年)兵曹條知治幢墼文書》,闞爽政權有《兵曹條次往守白艻人名文書》(二件)、《兵曹條次往守海人名文書》。[注]唐長孺主編: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63、72—73頁。另參王素: 《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第94、141、142、172號,第95、105—106、113頁。按: 《兵曹條次往守白艻人名文書》二件原定名均脱“次”字,此據第二件内稱“謹條次往白艻守人名在右”補。
5.
原文: 器物類第五十九簡有“ 棖 鍪”。《王釋》:“《説文》兜:‘兜鍪,首鎧也,從從皃省,皃象人頭也。’今變皃作兒,變作白,像人戴冑之形。”(第187—188頁)
校證: “像人”之“像”,《流沙墜簡》原文作“象”。唐師關注“ 棖 ”,推測應是因爲《文書》“斛斗”二字寫法缺乏規範,“斛”多寫作“ 毐s”,“斗”多寫作“ 棖 ”。如麴氏王國《和婆居羅等田租簿》(二)記“毛師奴一畝六十步,十二月廿日,三 毐s(斛)柒 棖 (斗)”,又“□孝敍一半,七月廿三日,肆 毐s(斛)五 棖 (斗)”。[注]唐長孺主編: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276頁。整理時在“ 棖 ”後括注“斗”,需要有文獻根據。
6.沽酒二斗
原文: 雜事類第六簡賣布袍券有“時在候史張子卿、戍卒杜忠知察,□各□二斗”。所謂“時在旁”即《文書》之“時見”,“沽酒二斗”即漢孫成買地券之“沽酒各半”。(第193—194頁)《文書》有“沽各半”,省“酒”字。
校證: “布袍”之“袍”,《流沙墜簡》原文作“”。“知察”之“察”,《流沙墜簡》原文作“卷約”。標題“沽酒二斗”之“斗”與“□各□二斗”之“斗”,原均寫作“升”,後改爲“斗”,《流沙墜簡》原文作“□沽□二升”。“所謂”以下“時在旁”“沽酒二斗”云云,釋文與原引文不同,係據《王釋》,而漏寫“《王釋》”二字。唐師關注此條,如筆記所説,是因爲《文書》有“時見”和“沽各半”。如麴氏王國《承平五年道人法安弟阿奴舉錦券》記“倩書道人知駿,時見道智惠”,又《義熙五年道人弘度舉錦券》記“民有私要,々行二主,各自署名爲信,沽各半,倩書道護”。[注]唐長孺主編: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88—89、94—95頁。另參王素: 《高昌史稿·統治編》,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84—285、327—329頁。
7.索盧靈
原文: 雜事類第五十六簡“景元四年八月八日,幕下史索盧靈□兼將張禄(正)録事掾關”。(第202頁)按魏時海頭有姓索盧之史。
校證: “(正)”,《流沙墜簡》原文作“簡面”。“録事”前,《流沙墜簡》原文有“上缺”二字。按《漢書》卷九九下《王莽傳下》地皇三年冬條“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師古注曰:“索盧,姓也。”可知此姓見於史籍甚早。唐師關注“索盧”之姓,是因爲《文書》有此姓。如西涼《劉普條呈爲綿絲事》有“索盧來”,闞爽政權《翟蔥等應募入幢名籍》有“索盧早”。[注]唐長孺主編: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7、102頁。另參王素: 《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第30、152號,第78、108頁。
8.起
原文: 雜事類第五十七簡:“(上缺)元五年八月癸卯起(下缺)。”(第203頁)按年月日起乃魏晉以來文書形式。見《宋書·禮志》。
校證: 唐師關注官文書“年月日起”,是因爲《文書》有此形式。如段氏北涼《神璽三年(399年)倉曹貸糧文書》有“神璽三年五月七日起倉曹”,沮渠氏北涼《義和三年(433年)兵曹李禄白草》有“義和三年六月五日起兵曹”,麴氏王國《義和二年(615年)都官下始昌縣司馬主者符爲遣弓師侯尾相等諸府事》有“義和二年乙亥歲十月 日起工相兒侯阿伯”。[注]唐長孺主編: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12、62頁;同書,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98頁。



10.統軍
原文: 雜事類第八十八簡:“(上缺)統軍君□(下缺)。”(第208頁)
校證: 唐師關注“統軍”,是因爲《文書》有此官。如前秦《倉曹屬爲買八緵布事》有“統軍玢”。[注]唐長孺主編: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4頁。另參王素: 《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第16號,第73頁。
11.會
原文: 《流沙墜簡》簿書類第七簡:“賓籍,吏出入關人畜車馬器物如官書會,正月三日須集,移書各三通,毋忽,如律令。”(第107頁)
第八簡:“出入關人畜車馬器物如關書移官會。正月三日,毋忽,如律令。”(第107頁)
第十簡:“以小面一言已也,未□會五月朔以爲(下略)。”(第107頁)
《王釋》:“七、八、九三簡則督促期會者也。《續漢書·百官志》:‘主記室史,主録記書,催期會。’賈誼云:‘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則漢人之視期會重矣。”(第108頁)按《文書》有買八縱布賈會事,當即期會之會。察簡文“如官書會”“如關書移官會”,皆指出入關人畜車馬器物須記上簿籍,於正月三日移主管官會集。期會即如期會集。
校證: 唐師關注“會”亦即“期會”,如筆記所説,是因爲“《文書》有買八縱布賈會事,當即期會之會”。此“買八縱布賈會事”,即前揭前秦《倉曹屬爲買八緵布事》,其正文爲:“倉曹樊霸、梁斌前屬催奸吏買八縱(緵)布四匹,竟未得。今日盡,急須。屬至,亟催買,會廿六日。屬官付。”可以看出,筆記的撰寫時間,應遠早於《文書》所收最早的十六國文書(即高昌郡文書)的定稿時間,因爲筆記所記“八縱布”“賈會”,正式出版的《文書》已改作“八縱(緵)布”“買,會”了。[注]按原所以誤“買”爲“賈”,蓋因“買八縱布賈會事”之“布賈”亦爲一詞。長沙三國吴簡常見,如《竹簡》有“ 五年田畝布賈準入米 ”(666號),《竹簡》有“入嘉禾二年所貸食新吏田畝布賈米四斛”(1913號),但意義不詳。明温純《温恭毅集》卷一一《明壽官峩東王君(一鴻)墓誌銘》謂誌主:“早年家徒四壁立,意氣軒軒,若纏十萬緍,常佐長君化居吴越間,爲布賈,已稍贏,則又轉而鬻販江淮間,爲鹽賈,家遂大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8册,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1986年,第644頁。)此處之“布賈”則指販賣布匹的商人。
12.守堤兵
原文: 簿書類三十一簡:“帳下將薛明言: 謹案文書,前至樓蘭□還守堤兵廉(下缺)。”(第115頁)按樓蘭有屯田,故有守堤兵。《文書》言守水,也是屯田。又三十九簡:“得勑: □□兵張遠、馬始今當上堤,勑得具糧食伯物詣部會□動時,不得稽留設解。”(第117頁)亦守堤兵。
校證: “得勑”之“得”,《流沙墜簡》原文作“將”。“勑得”之“得”,《流沙墜簡》原文作“到”。第三十九簡釋文,原文按《流沙墜簡》格式照録,即以“得(將)勑”字頂格,以下爲雙行,分别以“□□兵”“詣部會”開頭,此處爲製版方便,改爲單行。唐師關注“守堤兵”,如筆記所説,是因爲“樓蘭有屯田,故有守堤兵。《文書》言守水,也是屯田”。筆記所謂“《文書》言守水,也是屯田”,指沮渠氏北涼《兵曹下八幢符爲屯兵值夜守水事》。[注]唐長孺主編: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70頁。另參王素: 《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第104號,第97—98頁。唐師《新出吐魯番文書簡介》也談到:“由於這一地區開渠灌溉的重要性,在放水時要屯兵守水,這當是漢代以來的傳統。”[注]唐長孺: 《新出吐魯番文書簡介》,《唐長孺文集: 山居存稿》,第323頁。所謂“漢代以來的傳統”,應是根據《流沙墜簡》的記載往前逆推的。
13.刾
原文: 簿書類三十七簡:“將尹宜部 溉北河田一頃 六月廿六日刾。”《王釋》:“右簡亦下白上之書,簡所謂刺者是也。”並引《漢書·外戚傳》“條刺”顔注及《釋名》,以爲“刺本謂書寫,後遂以所書寫之物爲刺”,最後且謂公文之名。又引《唐六典》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職,“諸司自相質問,其義有三,曰關刺移”。(第116—117頁)按此簡云刺,如據唐制,則平行之文書,非必下達上。

14.隧
原文: 烽燧類三十四簡下《王釋》:“簡文, 檹或作隧,或作隊,他書則多作燧,皆别構之字,非有他義也。”(第137—138頁)按隊、燧、 檹一字,則隤、 檼亦一字。
校證: 此烽燧類三十四簡正文與《王釋》均只提到隊、燧、 檹,並未涉及隤、 檼,僅《文書》中有隤、 檼。唐師是想據《王釋》認定隊、燧、 檹爲一字,説明《文書》中的隤、 檼亦爲一字。如沮渠氏北涼《玄始十二年(423年)兵曹牒》中的“大塢隤”、《玄始十一年(422年)馬受條呈爲出酒事》中的“隤騎”,原件均寫作“隤”;[注]唐長孺主編: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31、61頁。而《兵曹張預班示爲謫所部隤事》中的“部隤”之“隤”,原件寫作“ 檼”。[注]唐長孺主編: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73頁。按: 其中“部隤”之“隤”,雖因塗有墨迹不太清楚,但看得出來“隤”下是有“辵”的。按《龍龕手鑑》:“ 檼,同隤。”唐師所言甚是。
15.作墼
原文: 戍役類十四簡,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皆記戍卒作墼積々。《説文》:“墼,瓴適也,一曰未燒磚也。”顔師古注《急就篇》云:“墼者,抑泥土爲之。令其堅激。”(第147—149頁)
校證: “十九”後似脱“簡”字。“々”,據《流沙墜簡》原文,應爲“積”前“墼”之重文符號,此處正確釋文應作“作墼、積墼”。“《説文》”前,據《流沙墜簡》原文,應脱“《王釋》引”三字。“墼者”之“墼”,《流沙墜簡》原文作“毄”。唐師關注“作墼”,是因爲《文書》所收沮渠氏北涼《義和三年(433年)兵曹條知治幢墼文書》中亦有“作墼”。[注]唐長孺主編: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63頁。此外,唐王朝《寶應元年(762年)六月康失芬行車傷人案卷》中還有“般(搬)墼”。[注]唐長孺主編: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331頁。
16.屯田
原文: 戍役類三十一、三十二簡,並稱大麥若干頃或畝,已截若干畝,小畝若干畝,已截或溉若干畝,禾若干頃畝,莇溉若干畝,下 栿 若干畝,溉若干畝。(第152—153頁)《文書》91: 33有“選兵十五人夜往守水”及“引水溉两部”語,皆屯田也。
校證: 本條未涉及第“三十二”簡内容,此“三十二”應爲衍文。“小畝”之“畝”,據《流沙墜簡》原文,應爲“麥”之筆誤。唐師關注“屯田”,如筆記所説,是因爲“《文書》91: 33有‘選兵十五人夜往守水’及‘引水溉两部’語,皆屯田也”。此處引《文書》云云,爲沮渠氏北涼《兵曹下八幢符爲屯兵值夜守水事》語。[注]唐長孺主編: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70頁。另參王素: 《吐魯番出土高昌文獻編年》第104號,第97—98頁。但亦可看出,筆記的撰寫時間,應遠早於《文書》所收最早的十六國文書(即高昌郡文書)的定稿時間,因爲筆記所記“91: 33”“夜往”,正式出版的《文書》已改作“75TKM91: 33(a),34(a)”“夜住”了。
結 論
唐師讀《流沙墜簡》筆記,通過前揭校證,可以推知,具體應寫於1975年左右。其時《文書》整理組剛剛成立,很多工作都還處在準備階段。唐師作爲《文書》整理組組長,[注]按: 1974年10月,經周恩來批准,王冶秋主持,在北京相繼成立了《銀雀山漢墓竹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吐魯番出土文書》三個整理組,工作地點在沙灘文物出版社。這三個整理組,僅《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組設有組長,由唐師擔任。另两个整理組最初合稱“竹簡帛書整理組”,不設組長,大致實行聘用制,即根據學人專長,聘請從事某一類别文獻的整理,故先後聘用的唐蘭、商承祚、羅福頤、顧鐵符、張政烺、朱德熙、史樹青、于豪亮、馬雍、李學勤、裘錫圭、曾憲通等一大批老中青學人,均各有專攻,譬如唐蘭主要承擔馬王堆竹簡遣册和帛書古佚書整理,羅福頤、顧鐵符主要承擔銀雀山《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整理,張政烺主要承擔馬王堆帛書《老子》整理,等等。當然,也有交叉整理和综合討論會。後來,也僅《吐魯番出土文書》釋文本全10册、圖文本全4卷,於1981至1996年全部整理出版。這應該與《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組設有組長,有唐師直接領導負責,存在一定的關係。肩負的責任更加重大,不僅需要做資料方面的準備,還需要做研究方面的準備。本文揭載的讀《流沙墜簡》筆記屬於資料方面的準備。關於《文書》所收十六國文書(即高昌郡文書),唐師撰寫過五篇研究文章,除了前揭《魏晉時期有關高昌的一些資料》《新出吐魯番文書簡介》二文外,還有《吐魯番文書中所見高昌郡縣行政制度》《吐魯番文書中所見高昌郡軍事制度》《吐魯番文書中所見絲織手工業技術在西域各地的傳播》三文,[注]唐長孺: 《吐魯番文書中所見高昌郡縣行政制度》,原載《文物》1978年第6期;《吐魯番文書中所見高昌郡軍事制度》,原載《社會科學戰綫》1982年第3期;《吐魯番文書中所見絲織手工業技術在西域各地的傳播》,原載《出土文獻研究》創刊號,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5年。現均收入《唐長孺文集: 山居存稿》,第356—373、374—400、401—412頁。按: 唐師還有《高昌郡紀年》,原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期,1981年,收入《唐長孺文集: 山居存稿三編》,北京: 中華書局,2011年,第39—70頁。但该文主要是用傳世文獻寫成,很少涉及吐魯番文書,據前言所説:“幾年前,我參加整理吐魯番所出文書,其中一部分即是高昌郡時代文書。爲了便於考查當時發生的與高昌郡直接或間接有關的史實,初步搜輯諸書所見,按年序列。”知實際亦屬唐師爲整理《文書》做的準備工作之一,故不統計在内。則都屬於研究方面的準備(前揭十六條筆記内容,此三文亦頗多涉及,本文限於篇幅,未能一一校證,讀者有興趣可自行比對)。因而可以認爲,《文書》的整理,所以能够成爲出土文獻整理的典範,不僅是唐師個人的知識學養所致,也與唐師個人的勤職敬業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