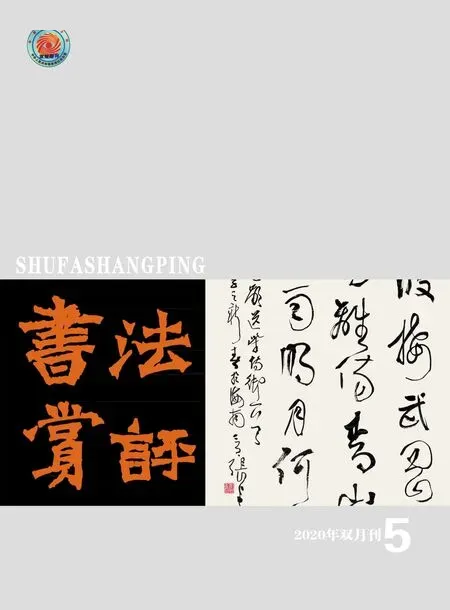北魏平城碑额书法艺术试论
杜 浩
一千多年来,北魏书法一直处于尘封状态。人们对北魏书法的重视,从清朝乾嘉时期金石考据学的兴起开始。最先肯定北魏书法的学者当是阮元和康有为,由于刊行的北魏书迹多是北魏后期之作,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北魏书法,可谓是知“洛阳”而不知“平城”。要了解北魏书法历史的全貌,平城时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殷宪先生对北魏平城书迹的研究,平城魏碑开始走进书家的视线,越来越多的书家学者对“平城体”及魏碑体源流关系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而忽略了这一时期篆书的发展。北魏平城时期篆书主要表现在碑额上,是篆书发展进程中重要的一环,具有很高的审美性和装饰性,并对当下书法篆刻的学习与创作具有启迪意义。
一、平城时期篆书碑额概况
“碑,竖石也。从石卑声。”[1]碑是指刻着文字或图画,竖立起来作为纪念物或标记的石头,其碑身的正面称为碑正或碑阳,碑身后面称为碑阴,两个侧面为碑侧,碑阳的正上方题写标题的区域为碑额。碑刻书法通常镌刻在碑额或碑身,内容主要为标识、纪功、颂德等,因此,碑刻书法既包括碑文书法,亦包括碑额书法。叶圣陶先生在其《登雁塔》中有言:“向来玩碑的无非揣摩书法,考证故实,注意到碑额、碑趺和碑旁的装饰雕刻是比较后起的事情。”[2]即通常情况下关注碑文书法者甚多,而关注碑额书法者鲜少矣,碑额书法也是碑刻书法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碑额者,秦汉碑版刻石顶端题刻碑名者之谓也。碑额乃一碑之名目,位尊、字大、醒目、突出,亦是立碑、书碑者着意经营处。”[3]无论秦汉,北魏平城时期亦如此。
在至今为止的很长一段历史进程中,北魏平城书法在书法史的大网中,一直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地位,它总是被人们忽视,谈到魏碑,只知“洛阳体”,而不知“平城体”,提起碑额书法,只知两汉碑额,而少闻平城碑额。公元398 年,道武帝拓跋氏贵族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定都,由此开启了近一个世纪的北魏平城历史。建都平城后,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加上佛教的传入,对书法文化的创新与发展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以碑刻、砖石、瓦当、漆画等为载体,其中又以碑刻书法为主,碑文书法整体为隶楷书,方严、厚重、古朴,是魏碑体书法的早期阶段,而碑额书法则基本选用篆书。要客观地对北魏平城时期的篆书有所了解,就必须对平城碑额书法艺术加以分析,首先需要对平城时期含碑额碑刻的分布情况及大致数量有所了解。

图一:《皇帝南巡之颂》碑额
放眼篆书的发展史,篆书在汉字的发展中居于首要的位置,秦代李斯对文字的规范使篆书的发展达到兴盛。发展到汉代,篆书逐渐由实用性变为非实用性的字体,其载体丰富,主要表现在碑刻、碑额、砖、瓦当、铜器、陶、印章及简书、帛书等墨迹上。到了北魏平城时期,篆书的发展较为低落,这一时期是魏碑体书法形成的重要阶段,而篆书面貌仅见于碑额之上,富有装饰意味。而现存北魏平城时期篆书碑额的大体数量有多少呢?笔者通过对殷宪先生的《北魏平城书迹研究》阅读以及查找统计,北魏平城时期(公元398—494 年)所控制的中国北方地区包括现今的山西、内蒙古、新疆、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吉林、辽宁、甘肃等地,而平城(今山西大同)作为政治、文化及军事中心,其出土资料数量为最,亦最具有代表性。现如今发掘可考北魏平城时期的书迹有60 余处,具有代表性的石碑近20 件,而有碑额者,约10 余件,且碑额书体都为篆书,其中大多出土于大同地区。
北魏平城篆书碑额,是北魏平城历史文化的见证,同时也是篆书在当时的发展形态,是篆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4]同样,碑额书法除了其装饰性和审美性,也具有其文化反映。从大的社会背景来看,平城的建都是拓跋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在完成汉化之后,以求帝位永传,如云冈石窟出土的“传祚无穷”瓦当,便为此愿。碑额书法则线条宽厚,布局茂密,当为巩固统治,以显示其庄严气象。从社会阶级来看,立碑者多为宫廷贵族,如《皇帝南巡之颂》,为表现其华贵,故笔画收尾处多有尖锋饰笔挑出。
二、与汉篆书碑额的比较
汉代蔡邕在《篆势》中有言,“体有六篆,要妙入神。或像龟文,或比龙鳞,纡体效尾,长翅短身。”[5]蔡邕对篆书的描述可以看作是汉代篆书的风格特征。汉代厚葬及竖碑之风盛行,上自帝后,下至民庶,莫不竖碑,碑刻字体多为当时流行的隶书,碑额则用篆书书刻,篆书在碑额中表现的非常丰富,其打破了碑身文字的刻板,使得活泼大方而又庄重古朴。两汉的篆书碑额与秦小篆的典雅匀称相比,更加雄强朴厚,隶意浓厚,并在造型基础上追求夸张和变形而增加装饰意味。北魏平城时期的篆书碑额中,有对两汉篆书碑额继承与发展者,亦为历代碑额书法具审美价值者。
北魏平城时期的篆书碑额与汉碑额在章法布局上是有区别的。首先从位置上来看,汉碑额大多处于居中的位置,除此外,还有居左的,亦有居右的,碑额居左的,如《张迁碑》等,碑额居右的,如东汉的《仙人唐公房碑》《汉豫州从事尹君之铭》等。汉代以后,到北魏平城时期的碑额,则基本全是居中的位置。其次从碑额的行数排布来看,汉碑额内容较为简单,排布为竖式,有一行、两行、三行者,其中,两行者最多,如《张迁碑》《汉循吏故闻熹长韩仁铭》等,一行者如《白石神君碑》等,而三行者极少。北魏平城时期的篆书碑额则多为三行及四行竖式排布,三行排布者如《皇帝南巡之颂》等,四行者如《中岳嵩高灵庙碑》等。从碑额的界格来看,汉代碑额基本无界格,有界格者甚少,而平城时期的碑额常有界格,基本上一字一格,三行及四行排布者最多,有三行排布者并用“井”字界格隔开似九宫格者,如《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四行排布者,如《城阳宣王(拓跋忠)墓志》的篆额,另有四行排布特殊者,每行界格内两个字,行行分开,如《司马金龙墓表》。从碑额的块面轮廓来看,两者也有差异,若把碑额文字看成一件单独的作品,观其块面轮廓,汉代的碑额基本上总体呈长方形,像一件条幅作品,而到了北魏平城时期,碑额的块面轮廓则由纵向变为横向,或正方形,或横势扁状,像一件斗方或者一幅长卷。
除了在章法布局方面的差异外,北魏平城篆书碑额与汉代篆书碑额二者在字形与线条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在字形结构处理方面,汉代篆书碑额文字大小有别,参差不齐,字形长短方扁亦不同,线条穿插挪让,变化多端,而平城时期的篆书碑额线条布白则更加均匀,不同于汉碑额的奇绝,而变得整饬。在线条方面,汉代篆书碑额文字线条整体松动而又瘦硬,线条转折处有方有圆,而北魏平城时期的篆书碑额文字线条宽厚,点画饱满,笔画起收笔处常呈截状或尖状。
三、平城时期篆书碑额的造型特征及分类
唐代著名书学理论家孙过庭在其书论著作《书谱》中论述书法四体特征时有言:“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简而便,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性情,形其哀乐。”[6]孙氏认为婉转、通畅是篆书书体的通髓。纵观北魏平城时期的篆书碑额,在继承秦小篆的基础上,又有鲜明的特色,它不同于粗细一致、有转无折的“玉箸篆”,亦不同于汉篆额的跌宕起伏、变化多端。北魏平城时期的篆书碑额厚重古朴,提按有别,转折处虽有方有圆,仍体现了“婉”“通”的篆势原理。
元代吾丘衍在其《学古编·三十五举》中有云:“凡写碑匾,字画宜肥,体宜方圆,碑额同此。但以小篆为正,不可用杂体。”[7]在秦小篆的基础上,笔画更加宽肥厚重,起笔、收笔作截状,或盘绕出锋尖锐,对称的纵向及横向笔画均向外侧弯挑,这就是北魏平城篆书碑额的整体造型特征。
就目前所出土北魏平城时期的碑刻,具有代表性的篆书碑额,根据其造型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A:方劲“楷篆”类
此类碑额数量多,最具有平城时期篆书碑额的特点。字形面貌相近,横画与竖画呈方状,笔画的起笔与收笔有明显的特征,呈平截状,或斜截状,亦有圆状,且有意识出尖峰上挑,转折有方有圆,妙趣横生。(表一)

表一
《皇帝南巡之颂》碑额,有篆书“皇帝南巡之颂”六字,竖式三行排布,于界格中,每字一格,疏朗飘逸而又肃穆精劲,线条流畅。《皇帝东巡之碑》,有篆书“皇帝东巡之碑”六字,碑额文字以竖式两行分开排布,而更多一些苍厚之感。《司马金龙墓表》有篆额“司空琅邪康王墓表”八字,按四行分开排布,每行两字为一个界格整体,篆额流美,有委婉华美之姿。《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碑额为“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九字,三行排布,被九宫界格分割,呈方正状,字形亦方,每个字都尽力撑满于各自的方格中,笔画媚丽,于方正中见婀娜。《城阳宣王(拓跋忠)墓志》有“魏故城阳宣王墓志”八字篆额,分竖式四行排布,字字分开,分列于独自的界格,线条凝练厚重,起收笔呈方截状或随势出尖峰。《元淑墓志》的碑额为“魏元公之墓志”六字,以方折居多,字势方扁,沉厚敦稳,别具一番滋味。
B:圆厚肥重类。
如《中岳嵩高灵庙碑》,碑额为“中岳嵩高灵庙之碑”八个篆书大字(图二),与方劲“楷篆”类篆额不同,其笔画更加厚重,并且以圆为主,起收笔有呈斜截状,但大多起收笔表现为圆厚中挑出尖锋,尤其是横画的收笔,与隶书的波折有相通之处,其意趣可谓在篆隶之间,大有庙堂之气。

图二
C:形态草率类。
此类碑刻面目较少,有代表性的如:《平国侯韩弩真妻碑》。其碑额为“平国侯韩弩真妻碑”八个篆书大字(图三),碑额没有明显的界格,分竖式四行排布,其形制较小,字态则显草率自然,字形及笔画圆转,圆多于方,起收笔处亦有尖锋表现。

图三
四、北魏平城篆书碑额的艺术价值
艺术创作具有参照性,书法与篆刻艺术的创作亦如此,前人的艺术成果会成为后人学习与创作的参照本。北魏平城篆书碑额的厚重古朴与截状尖锋的用笔,是平城书法重要的一笔,对现如今书法艺术与篆刻艺术的创作有很大的参照与启示意义。
清代,金石学兴起,残存于各地的金石碑文受到书家学者的重视,受到大规模的发掘,其中碑额书法就是书家们创作的灵感之一。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陈鸿寿、赵之琛、莫友芝、吴昌硕等,他们当中大多既是优秀的篆书家,也是篆刻家,在学书渊源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汲取了篆额的养分,并且能够使各自的篆书与篆刻艺术互相渗透,在书坛上掀起浪潮,其中以邓石如最具有代表性,沈增植在《海日楼书论》中提道:“完白以篆体不备,而博诸碑额瓦当,以尽笔势,此即香光、天瓶、石庵以行作楷之术也。碑额瓦当,可用以为笔法法式,则印篆又何不可用乎?”[8]可见碑额书法之影响。清代篆书家借鉴并取法汉碑额的大胆尝试,皆为其艺术创作打开了广阔的思路而成功。
北魏平城篆书碑额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独特的艺术性,也是我们临习与创作的极佳资源。当代中国书坛已经进入展厅时代,由此,书法作品更趋于视觉冲击的效果,于书法创作而言,平城篆额的厚重宽博是很好的取法对象。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九十二件篆书入展作品中,以二李、清篆及《毛公鼎》等风格为主,创作取向雷同,戴文先生认为当今篆书资源还需要进一步发掘和整理,他说:“古人所留下来的传统的东西,都可以作为经典或取法对象去进行学习,我们不能总认为就那么几种书风或几个人物代表了经典。”[9]北魏平城篆书碑额则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与重视。于篆刻创作而言,平城篆额则是“印外求印”创作的新源,其方正圆厚的结构适于入印排布,尽显金石意味,同时,北魏平城篆额的章法可以为篆刻边款的创作所借鉴,无论纵向横向、界格的划割与分列的排布,都是极好的章法。另外,在篆刻印屏的制作中,北魏平城篆额也可以用来题签,于肃穆精劲中含婀娜流美之姿。随着北魏平城书迹的重现以及书家的重视,平城碑额书法也必将引起关注。
结语
北魏平城时期是魏碑书法的早期发展与嬗变时代,然而北魏平城碑额书法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中也是不容小觑的,在那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相互碰撞的时代中,它与“平城体”一起,是构筑中国艺术神话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信这个民族融合、多姿多彩的近百年时代,北魏平城篆书碑额,一定会令艺术家们引起重视,为篆书的再次复兴发挥其布帛菽粟似的作用。
注释
[1]许 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
[2]叶圣陶.没有秋虫的地方 大家散文文存精编版[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8:188
[3]马博.书法大百科 第8 册 图文珍藏版[M].北京:线装书局,2016:377
[4](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0:42
[5]傅如明.中国古代书论选读[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09:21
[6]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7]王国平.杭州文献集成 第15 册 武林往哲遗著 2[M].杭州:杭州出版社,2014.05:614
[8]宋民著.书法美的探索[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7.11:120
[9]戴文.篆书现状与反思[J].中国书法,2019(21):94
——以平城宫遗址百年保护史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