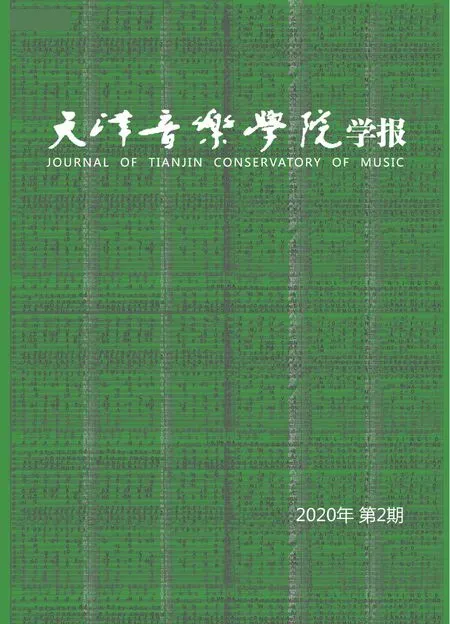寻找内心的声音
——陈其钢《抒情诗Ⅱ》的个性表达与创作探析
张一
1988年,在相继获得巴黎大学硕士学位和巴黎音乐师范学院高级作曲文凭之后,陈其钢开始了职业创作的道路。在笔者眼中,陈其钢是一位专注自我表达的作曲家,他不合流俗、追求心灵的自由,真诚的情感表达是其创作的出发点,多年来,他始终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研究和创作,不刻意追求形式或观念的新颖,始终保留音乐的自然性与艺术本质。
男中音与器乐合奏《抒情诗Ⅱ》①由阿姆斯特丹新音乐团委托创作,作品曾以其立意和独特的音乐表现力给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关于作品,初版《抒情诗》的乐曲说明曾写道:作曲者是希望藉由其个人所构思的诗词、人声、器乐的“三位一体”——宋朝的古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发展自清代中叶的京剧唱腔,以及西洋室内乐团与现代乐队写作技术的丰富表现力,来表达作曲者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下所感受的孤独感。
可见“孤独”是作品表达的中心,而且这种孤独感更多来自作曲家在异文化环境中“寻找自己”时的感受,是彼时心境和思考的记录。关于这一点,可参见陈其钢于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撰写的文章及其接受采访时的表述,可以想见,这一阶段他处在对现代音乐、中国文化以及音乐创作的思考当中,他在厘清观念,一方面要走出现代音乐,特别是走出“西方人心目中的‘现代音乐’”,另一方面是重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再一方面是对个人风格的坚定追求。这些思考不仅体现在《抒情诗Ⅱ》里,还体现在《道情》(1995年)、《逝去的时光》(1995—1996年)、《五行》(1998—1999)、《蝶恋花》(2002年)等一系列作品中,应该说,每一部作品都记录着作曲家当时的创作态度和对生活、情感的体悟,这正如毕加索(Pablo Picasso)在一次采访中所言:“这(指艺术作品,笔者注)是我们自己书写的记忆,像日记一样”。
众所周知,《抒情诗Ⅱ》的唱词取自苏轼的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如果将原词比作一幅画,那么《抒情诗Ⅱ》的表达方式就如同装裱这幅画的相框或张挂画作的场所,它们关乎作品的风格和接受者的体验,亦体现了作曲家的观念与审美。在笔者看来,陈其钢对于“相框”和“场所”的选择既恰当,又充满个性,表现出非常个人化的艺术表达。同时,在构成相框、场所的诸多要素中,受启于戏曲唱腔的人声表现占据着首要位置,既奠定了作品的风格基调,也决定着其他音乐要素的选择与呈现。有学者认为:“苏轼很善于处理抒情的节奏,从‘无言问月’的迷惘到希望‘乘风归去’的向往;从‘又恐琼楼玉宇’的犹疑到‘不应有恨’的自我解脱;从‘此事古难全’的体认到‘千里共婵娟’的祝福,情感在回环往复中向前发展……。”②笔者认为,《抒情诗Ⅱ》的人声表现虽不符合历史真实,却高度契合艺术真实,正是这样的表达方式,才使这首千年以前的宋词所蕴含的情感与深刻哲理得以淋漓地、鲜活地表现出来。与此同时,以字行腔、以腔为调的人声(唱词)也极大地拓展了作品的时空尺度,使听者的感官体验游走在传统与当代、想象与现实之间,当然,这种体验同样与作品的构思、创作技术密不可分,这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从整体布局来看,原词结构分为上阙、下阙,作曲家依据音乐发展的逻辑将作品的结构扩展为四个部分,同时对唱词进行相应的调整和细节处理,以适应创作需要。第一部分为引子,唱词内容分布在后三个部分,总体呈现出起、承、转、合的功能布局,但若依据织体和音响结构的逻辑关系看,也可将前两部分合并,形成起、开、合的三部性结构。(图表1)

图表1.《抒情诗Ⅱ》整体结构布局
一、 审美理想的听觉呈现:音高、音色的建构
综观陈其钢的作品,不难发现其中或显著或微妙的延续性,这与作曲家有意识地建立自我音乐语言风格的观念密切相关⑤。1992年,陈其钢在《从梅西安先生去世想到的》文章中说道:“音乐创作并非纯理论,在理论、知识和技术上有所感受还远远不够,要想建立自我只能逐步在自己的作品中提炼出那些真正属于自己的音响和语言结构方式,并逐步形成体系。”作为早期的代表作,《抒情诗Ⅱ》中诸多素材和技术的选择为作曲家音乐语言风格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譬如音高与音色,这也是作曲家较早就关注的技术问题。
(一) 凝练的音高材料
参照谱例1和图表2可以看出,五声性音高材料在作品中发挥着主体作用,其构成形态有三种:音程、和弦、音列,它们既是全曲的核心音高材料,又作为主导性因素影响着结构的建立。在这里,音程,主要指纯五度音程和小二度音程;和弦,是指音响柔和的小七和弦(羽和弦)。音列,主要是指五个非同宫系统的五声调式和有限移位调式的运用,纯五度音程与小七和弦均脱胎于五声调式音列。
谱例1.《抒情诗Ⅱ》核心音高材料


图表2.《抒情诗Ⅱ》音高布局图
参考图表2,从核心材料的分布来看:纯五度遥相呼应于首尾两部分,小二度关系主要体现在五声音列的宫调关系、调布局以及音高组织方面,既满足音响紧张度的需要,也具有一定的结构意义;小七和弦的音响结构主要分布在第一和第二部分;有限移位调式主要集中在第三部分第三阶段,五声调式音列主要以纵合化和声音响呈现。

谱例2.第一部分1—34(+2)小节和声音响设计(不含装饰因素)



第三次点状音响(16—18小节)由竖琴拨奏G小七和弦开始,弦乐声部和颤音琴作长音延音,颤音琴音高为C-#F,兼顾装饰功能。17小节继续叠加装饰因素,即木管组和弦乐组分别持续移位的纯五度(A-E),在两组色彩音持续的过程中,长笛音高横向运动(E→#C),当#C音进入18小节后,纵向音响再次错落出现装饰因素(其音高来自第四次和声音响#G小七和弦)。需要特别说明的是,#C音对于G小七和弦和#G小七和弦来说均属装饰因素,但它却是随后即将出现的B宫五声音列的组成音,音响的不协和感略有降低,故笔者未将其列入装饰因素。由此可见,作曲家细腻的音响感觉。
第四次点状音响(19小节)改由吉他拨奏#G小七和弦开始,依然由木管+低音提琴作长音延留。进入第一部分的黄金分割区域,亦是持续时间最长、音响(织体)最丰富的段落。值得注意的是,19—20小节双簧管和单簧管的横向大二度反向进行具有鲜明的再现意味,但仅短暂闪现即开启新的变化(谱例3):由弦乐组滑奏(除低音提琴外)和音群织体引出两个单音持续(23小节小提琴和短笛声部,E和A),进而继续引出短笛独奏旋律(23—32小节)。从音高观察,作曲家依据音响紧张度的不同设计了三个音群织体(曼陀林、竖琴、颤音琴,具有五声性十二音特征),此时核心材料不再成为听觉的主导,取而代之的是刚刚提及的两个持续音E和A,它们属于装饰因素(见下文详述)。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作曲家有意保持三种核心材料的可辨性,以突显其主导地位,同时通过核心材料的叠加、或通过装饰因素(见下文详述)来控制整个和声音响的起伏与色彩变化,最终呈现出迂回、渐变发展的音响特征。这也是全曲和声音响组织的基本思路。
(二) 和声音响构成的主要方式
谈论陈其钢的音乐风格不可不提到和声和音色,《抒情诗Ⅱ》中,这两个要素的写法并不复杂,既给个性化的人声表现留出必要的空间,也给听者留有想象的空间。同时,作曲家的音响追求是圆润、透明和色彩感,也对应着他对于词、词作者的理解与感受。即使是在富有动感的第三部分,也可见这种审美偏好。
谱例3.第四次点状音响20—23小节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兴德米特的和声理论对陈其钢的音响观念颇有影响,从此角度观察,全曲的音响设计严谨、考究,与五声性音响风格的融合非常自然。创作中,在明确的音响要求下,作曲家严格控制着纵横音高关系、音区、音色以及每件乐器的起奏状态⑥,同时,音响的纵横结合以五声性音程关系为主(音程数为2/3/4/5),适时叠加不协和音程(音程数1/6)。笔者认为,尽管和声音响的结构不具有明显的规律性,但通过对音程数容量、比例、排列方式的观察,和声音响发展的逻辑(包括和声起伏、音响紧张度等)总体上具有渐进的特征。
1. 五声性音高材料的运用
就音高材料而言,作品音乐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同宫系统五声性音高材料的交替变化与叠置,在音响偏于疏淡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可捕捉具有五声性内涵的单纯音响。从整体布局来看,全曲唯一一次单纯地使用C宫五声音列是第三部分第二阶段(对应唱词“不应有”的地方),作曲家通过其前后略显复杂的和声音响突显此处音响的纯度,使人印象深刻。有趣的是,相似的布局构想在室内乐《三笑》(排练号13处)也有所呈现,虽然两部作品的表现内容完全不同,但单纯地将C宫调式置于高潮部位的做法是有关联的。

谱例4.第一部分21—23小节 曼陀林声部


谱例5.第四部分218—219小节 颤音琴声部


谱例6.第三部分133—137小节

2. 装饰因素的使用

从用法来看,装饰因素常位于显著的高音区,或被置于人声声部,借助音长、音色、织体、演奏法凸显其存在,甚至有时在装饰因素中施加力度的渐变还会形成音差和色差。此外,装饰因素也常被隐藏起来作为背景声部出现在各种形态的音群织体中。从效果来看,装饰因素与总体呈渐进起伏的和声音响构成一种调节和平衡的关系,特别是在力度和速度的严密控制下,使整体音响的建构更加精致细腻,应该说,独具匠心的装饰因素是陈其钢音乐创作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在《五行》《蝶恋花》等作品中亦可见装饰因素的运用和探索。
3. 有意味的布局逻辑


谱例7.第二部调布局方式,55—56小节、72—73小节

谱例8分别是作品的开始和结尾部分,作曲家显然是希望通过材料的两种呈现方式使纯五度音程形成首尾呼应。同时通过结尾处涵括的直音⑦、颤音、滑音,以及线性织体表现一定的回顾意味,特别是其利落的上行大三度的收束方式再次使人联想到戏曲声腔。
谱例8.核心音程的开始(第1小节)和结束(235—237小节)

(三) 细腻的音色感觉
在陈其钢的作品中,音色无疑是表现个性、表达情感的重要元素,无论何种身份的接受者,都能通过作曲家对声音的细腻的处理感知其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抒情诗Ⅱ》的声音塑造给笔者最直观的感受是,不同音色(包括人声)的细腻糅合与顺畅、自然的转接,声音中既有统一又有精妙的色差(层次感),给人带来诗意的感受,从创作的角度看,还有缜密的逻辑在里面。

谱例9.第一部分1—4小节


第四部分中,作曲家结合原词赋予的意境与个人构想,营造出一种幽深清远、释然超脱的意境,特别是从最后一句唱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开始(217—239小节),音乐进一步升华,音响愈发空灵、富有空间感,极轻的力度(pppp—pp)使整个音响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轻盈、飘逸的感觉。从创作角度看,从217小节至乐曲结束共有三个陈述阶段,结构间的音响转接简洁有效,弦乐声部自始至终以长音(伴有滑音)持续为背景:(1)216小节,竖琴刮奏引出唱词“但愿人长久”,瞬间营造了豁然开朗的感觉,同时,高音区双簧管的加入使音响的明亮度和空间感随即显现,紧接着218小节稍作提速(≈56),随即引出吉他⑧和颤音琴的音群化织体以及竖琴的点缀,进而更明确地指向乐曲结束。(2)222小节,加入了双簧管和单簧管的点缀,形成看似随意的节奏张弛,进而与竖琴和颤音琴构成三个不同节奏密度的装饰音层。此外,颤音琴与提升音区之后(222小节)的人声音色更自然地糅合在一起,声音更为纯净。(3)231小节之后,配器再作减法(见谱例10)。在颤音琴和弦乐的背景下,吉他借助滑棒(Bottle-Neck)一高一低地拨奏出轻柔的上滑音,其细腻圆润的音色与竖琴互映,也自然地呼应→承接人声的颤吟;同时,短笛在高音区缓慢地以直音→颤音→小二度上滑音→扬起小三度收束的方式奏出f3→b3的旋律。随着织体的渐退,乐曲最终在吉他颤动的余韵中结束。如此细腻的处理使看似平淡的音响富有特殊的意象内涵。
谱例10.第四部分230—234小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在作品结尾处所营造的空灵、静谧的意象在陈其钢日后的创作中也有所呈现,譬如在《五行》第四乐章《土》,作曲家意图营造的是大地和宇宙的感觉,空灵而宽广,有母性的色彩在里面⑨。相似的构想还可参见2003年为弦乐团而作的室内乐《走西口》的结尾处(404—416小节)。

谱例11.第206—207小节

除上述内容外,就音响的逻辑建构而言,作曲家非常重视音乐材料(包括旋律、音色、织体)的“转接”,笔者总能看到出于唱词结构或音乐逻辑发展需要所进行的各种转接。譬如,笔者认为前文所谈的“先现音”亦是一种转接的方式,此外还可见带有变奏、渐变思维的织体的先现。又如,在多声部线性织体中,通过复调手法在声部间形成音色与旋律片段的转接、呼应,以此增加旋律的纵深感和线条运动的层次感,进而塑造形象意境(见乐谱26和31小节的大提琴声部,64—72小节的人声、木管和弦乐声部)。再如,在和弦音响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进行同质或异质音色的转接,并有意弱化转换的痕迹,造成一种不动声色的音色微差。(见乐谱220—221小节,225—226小节)。
总之,《抒情诗Ⅱ》的乐队音响并未有新奇的演奏法或夸张的音色,一切技术的精细处理和对声音的想象都指向陈其钢对音响的透明度和色彩的追求,不仅避免产生所谓现代音乐的冷漠音响,也体现出他对于美感和情感表达的追求。在技术方面,作曲家试图寻找不同音色之间的相似性,特别是那些由少数几件乐器(两件或三件乐器,包括人声)构成的细腻糅合的混合音色是最精妙的创造,这些具有独特质感的声音,既承载着作曲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亦唤起了听者对于音响色彩的感知,同时引发内心的联想与情感共鸣。在作曲家随后的创作中(譬如在《逝去的时光》《五行》《蝶恋花》中,均可见对这些音色的探索),这些别致的音响色彩逐渐成为陈其钢音乐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文化与心灵的融通
在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中,戏曲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象征,它既体现着创作者的文化身份,也记录着他(她)们与众不同的人生际遇。戏曲在陈其钢的音乐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更值得注意的是,陈其钢与戏曲的渊源来自家庭,他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是在生活、生长的自然环境中逐渐形成的,这样的教育显然是启蒙式的,这些文化内容也自然地成为音乐创作的灵感源泉。笔者以为,戏曲与陈其钢的关系,如同川蜀文化与郭文景的关系,巫文化、傩文化与谭盾的关系、草原文化与秦文琛的关系,是作曲家的人文底色,这些元素不仅融化在血液里,更带有鲜明的性格标签,与其心灵相融通。在陈其钢看来,所有的教育、环境、素养、技巧、才能、心性应该与文化一道,全部融化在音乐中,融化在由衷的表达里,只有这样才是创作。
作为早期作品,《抒情诗Ⅱ》能使人强烈感知作曲家的文化身份,这样的创作追求一方面受到彼时所思所想以及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艺术家常会在创作早期从自己熟悉的文化语言出发创作,进而建立个性。还需要关注的是,《抒情诗Ⅱ》所涵括的文化元素是多样的,更重要的是,文化元素的运用一直与作曲家的心灵世界、自我心性保持关联,这是陈其钢始终坚持的创作观念。
(一) 滑音、颤音的艺术表现与文化隐喻
在多数与戏曲内容相关的中国当代音乐作品中都可见滑音的使用。总的来说,不同的滑音形态与效果在陈其钢的作品中具有风格标识的重要意义。同时,滑音既可以表达情感,又可塑造音响,更唤起了听者的文化想象,这一点,与滑音的轻、重、疾、徐密切相关。此外,细腻的滑音和颤音表现亦是作曲家对圆润音响追求的投射。
作品中,滑音的塑造方式主要有三种,按出场顺序来看,一是滑音的局部“染色”(见乐谱2—4小节,弦乐和长笛声部);二是滑音与作曲家所偏爱的“永不间断的线条”的融合;三是人声吟诵、模仿念白、塑造意象时,自然流露的各种滑音效果(相关研究可参考已有成果,本文不再赘述)。不难看出,作曲家有意识地在人声出现之前铺垫滑奏,使不同形态面貌的滑音衔接自然。
以第二种滑音为例。作曲家将滑音置于延绵不断的线性织体,使其与直音、颤音自然衔接。此外,滑奏的形态多种多样,譬如同向异步、反向同步、同向同幅度异步、异向异步异幅度等等,通过对滑奏的幅度、速度、力度、时长、起滑的位置、方向等多方面的精细控制,满足创作的不同需要。从文化角度看,细细品味,滑音的声响形态是有文化隐喻性的,特别是当轻柔的滑音表现出柔曼婉转的姿态时,如谱例12所示,起伏的音高变化、考究的声部对位、自下而上的整体音势,以及力度的渐变张弛,都使人联想到圆润柔美的声腔韵味。这样富有表情的滑音效果与人声的表现互映生趣,自然形成逻辑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抒情诗Ⅱ》之后,滑音也用来表现特定的音乐形象或音响氛围,譬如《五行》第四乐章《土》和室内乐《走西口》(2000年)的结尾部分。
谱例12.第一部分20—23小节弦乐声部

在作品中,颤音也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在中国传统音乐中,颤音与直音相对应,归属于单个音的表现形态⑩。在《抒情诗Ⅱ》中,颤音的使用更易引发对戏曲声腔的联想。此外,声音颤动的方式有很多种,除乐曲说明中提到的三种颤音效果之外,作曲家还通过精确记谱限定颤音的音高幅度(如微分音、大小二度或小三度)、速度、长度和节奏形态,通过声音颤音的不同效果,形成或细微或显著的音响对比。
谱例13选自第一部分15—19小节弦乐声部,除低音提琴外,其他三个声部呈现为“直音→上滑音→颤音/震音→颤音”的声音过程。显然,只有17小节小提琴声部的揉颤音效果具有文化隐喻性,其他两声部为震音式和长音式的和声背景,并且它们的力度也作了精细区分,从而使小提琴与其他声部形成了音色微差。
谱例13.第一部分15—19小节弦乐声部

(二) 休止符的情感表达
在《抒情诗Ⅱ》中,休止符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不仅在宏观结构的布局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影响着唱词句法、呼吸,控制节奏的缓急,有益于表现语气、情绪,使音乐形象更加生动鲜活,富有诗意的氛围。在之后的创作中,休止符从人声移至乐器,譬如在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中(谱例14),休止符的使用极大地拓展了独奏乐器的表情能力,在与其他元素(装饰音、滑音、音色、音区)的合力作用下,若断若连的主题似人声的娓娓道来,深沉含蓄地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留恋”。总体而言,休止符的使用既源自作曲家细腻的情感体验,也体现了戏曲艺术追求意象生动和意境表现的审美理想。
谱例14.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138—147小节

限于篇幅,笔者仅从前述两点阐述观点。毋庸置疑,戏曲因素是理解陈其钢音乐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实际上,《抒情诗Ⅱ》中细密铺陈的橄榄型力度、独特的旋律轮廓、缓慢、稳健且富有表情的速度和节拍、乐器起奏的状态等都与戏曲艺术的表现有一定的关联。更为重要的是,作曲家对于文化元素的理解和选择,与其自我心性、心灵世界密不可分,因此我们从对文化内容的体验中还感受到了作曲家细腻的内心世界和他的审美趣味,这也是中国传统音乐元素能够自然地融于创作的关键所在。
此外,还想提及一点,《抒情诗Ⅱ》体现了作曲家极好的内心听觉、音色感觉,以及基于不同阶段文化熏陶的直觉表达,但“逻辑与控制”使他能够更好地兼顾形式的完整和内容表现,应该说,从整体结构布局,到内部音乐进程的层次安排,特别是和声、音色、声部关系的细微变化与走向都富有逻辑性。这样的理性思考既有性格因素,也与陈其钢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影响相关。
结 语
我国著名音乐理论家于润洋教授曾说:“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在寻找他自己的‘语言’,不为历史的规范所束缚,他们是自由的。这倒并不是简单地为了追求新奇,而是因为真正的艺术家只能是他自身。”陈其钢也说过:“没有心灵的自由,就没有艺术”。在笔者看来,艺术家心灵的状态,亦是其艺术的状态。每一位从中国文化走来的作曲家都通过对音响的塑造展现其心灵的状态、表达其艺术主张,尽管创作语汇的来源、音色感觉、审美观各不相同,但他(她)们都在寻找自己内心的声音。
作为早期的代表作品,《抒情诗Ⅱ》体现了陈其钢深厚的文化素养、调性意识,记录着他当时的内心世界、他的音响观念,以及精细的创作过程,同时也涵括其音乐创作语汇的部分技巧……这些都是作曲家音乐风格与审美理想的原初状态,更重要的是,如果把《抒情诗Ⅱ》放回彼时的文化环境里,还可以看到作曲家的“独立”,正如他所说,既不顺从过去,也不附和现在,只跟随你自己的意志。
作为一位专注自我表达的作曲家,陈其钢将音乐创作与对生活、人生的感悟和思考紧密关联,作品细腻、深刻、具有不可抗拒的感人力量和灵动的生命力。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他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研究、寻求自我突破,在2017年创作的三部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更为丰富的情感层次和人性层面的深度表达。聆听陈其钢的音乐总使笔者想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的一段话:“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娇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
① 《抒情诗Ⅱ》作品编制:男中音、长笛(兼短笛)、双簧管(兼英国管)、A调单簧管、曼陀林、吉他、竖琴、颤音琴、吊钹、大锣、中国锣、三角铁、砂槌、通通鼓、盒梆、大鼓、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与初版相比,编制中以两件非延音类乐器:曼陀林和吉他,替换了初版《抒情诗》的延音类乐器:小提琴和圆号。
② 仲红卫:《从寂寞到寂寞的解脱——细读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3页。
③ 本文所使用的音频资料来自陈其钢个人网站:www.chenqigang.com.乐谱版本:Gérard Billaudotditeur.
④ 在音乐发展的进程中,还包含局部速度的弹性变化,以体现情感表现的张力。
⑤ 参见陈其钢于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撰写和接受采访的文章。
⑥ 参见《陈其钢访谈》,连载于《爱乐》2002年6至9月号。
⑦ 完整的旋律从231小节开始至237小节结束。
⑧ 吉他先于颤音琴在217小节进入。
⑨ 参见金晶:《陈其钢寻找中国“五行”》,《上海青年报》2004年2月21日。转引自http://ent.sina.com.cn/2004-02-21/0836309115.html,查询时间2020年2月19日。
⑩ 参见赵冬梅:《中国传统音乐中的音高元素在现代音乐创作中的继承与创新》,中国音乐学院博士论文2012年,第9页。






——贝多芬晚期钢琴奏鸣曲颤音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