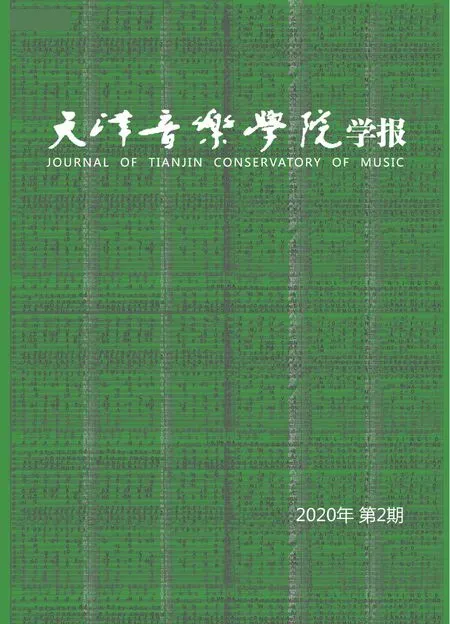“多重矛盾”与“人性和解”的咏叹
——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的立意及其实现
邹威特
“一部艺术作品整体上成功与否、价值高下主要取决于艺术家在该作品中的立意,即艺术家对作品所持的憧憬、观念或构思,以及取决于立意是否被实现。”①在科尔曼眼中,似乎只有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和《魔笛》符合其严苛的立意标准。《费加罗的婚礼》确实是一部立意深远的好戏:“这是一部讲和解的歌剧——费加罗与马尔切琳娜的和解,伯爵与伯爵夫人的和解,最后,还有整个这一小群住在城堡里的人,他们彼此之间的和解。这就是该作品的主题。”②“和解”在《费加罗的婚礼》中至关重要,但该剧的立意也绝不能忽略“矛盾”,正是缘于费加罗、苏珊娜、伯爵夫人、伯爵等人物的情感纠葛及阶层分歧,才使得“和解”有因可循并充满戏剧张力。此外,还必须提及伯爵夫人感染并升华众人的剧终场景,正是伯爵夫人的宽宏与仁慈才使最终的和解得以实现,这是本剧立意的核心。如何实现中心立意呢?莫扎特在音乐戏剧结构上进行了有效的创新与整合,咏叹调、重唱、终场等多种音乐组织形式被组合运用,其中,咏叹调仍担负着剧作构思的核心使命(在28首分曲中,包括14首咏叹调,13首咏叹调涉及了“矛盾”或“和解”立意)。毕竟,“在十八世纪,咏叹调是意大利喜歌剧最主要的独立分曲形式,表现意大利喜歌剧风格必需考虑咏叹调,因为咏叹调也是该风格剧作法的根基。”③
一、性别关系和社会阶层:“多重矛盾”立意的两大原点
两性矛盾、同性矛盾、阶层矛盾,《费加罗的婚礼》中的“多重矛盾”交织出一幅复杂而生动的众生相,而引发“多重矛盾”的两大原点是性别关系和社会阶层。众所周知,《费加罗的婚礼》的文学渊源是博马舍的同名话剧,博马舍的原作具有强烈的阶级色彩:“费加罗是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人民的典型代表。他和伯爵之间的矛盾斗争,不能光看成是个人之间的恩冤斗争,而是第三等级和贵族特权之间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④在我国,博马舍的戏剧文学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人们对于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立意的理解,受到了博马舍话剧剧本的影响——强调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抨击和反抗,忽视了人性和解的维度。实质上,莫扎特有意弱化了阶级属性,转而强化了角色间因性别关系引发的情欲纠葛,可以说“《费加罗的婚礼》是一部以情欲为中心并充满情欲特征的歌剧。”⑤作为该剧主要的导火索,绝大部分的矛盾都根源于角色间性别关系的冲突与不满足,阶级因素已然退居次席。
1.“矛盾”的集中呈现:咏叹调和重唱的协作
《费加罗的婚礼》的第一幕完全是矛盾的集中呈现:首先是费加罗与苏珊娜的疏离,然后依次呈现的是费加罗意欲挑战伯爵(分曲3)、巴尔托洛誓言复仇费加罗(分曲4)、苏珊娜与马尔切琳娜的相互嘲讽(分曲5)、伯爵对凯鲁比诺的不信任(分曲7)、费加罗对凯鲁比诺的调侃(分曲9)。显然,费加罗与第一幕登场的主要人物都存在矛盾:费加罗和伯爵既是情敌,又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第三等级和贵族),两人间的矛盾关系是该剧的主要矛盾;费加罗与凯鲁比诺则是主要矛盾的代际延续(凯鲁比诺对苏珊娜也有觊觎之心),“许多评论家认为,凯鲁比诺是少年时代的伯爵”⑥;费加罗与巴尔托洛的恩怨则可追溯到《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正是费加罗帮伯爵从巴尔托洛那里追到了罗西娜(后来成为伯爵夫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费加罗和苏珊娜的矛盾体现了性别间的对抗,这是最终实现“两性和解”的一条重要线索。
咏叹调与重唱在第一幕的分曲数量上平分秋色(各有四首),两种剧作形式各擅所长,协同推动着各种矛盾的集中呈现:费加罗与苏珊娜的二重唱(分曲2)初步显现了两人之间的一些疏离,这也是“两性矛盾”的首次呈现;苏珊娜与马尔切琳娜的二重唱是情敌间的战斗,矛盾不再局限于两性之间;苏珊娜、伯爵、巴西里奥的三重唱将情节变得更加复杂,越来越多的人物卷入“情欲纠葛”与“阶层分歧”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当中。四首咏叹调不仅在剧作结构上起到了连接和收束的作用,还直接呈现了所涉及角色的情感状态及心理进展:凯鲁比诺的咏叹调《我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分曲6)保持了前后重唱的快速步履,着力刻画了凯鲁比诺因无法满足情欲而万分焦灼的心理状态。费加罗的《伯爵,如果你也想跳舞》点明了本剧的核心矛盾——费加罗与伯爵的对立,这是“矛盾”呈现的一个关键之处,莫扎特为此调节了戏剧节奏,让其暂时脱离了前面重唱快速步履的控制。《再不要去做情郎》的主要作用是对第一幕做一个辉煌的收束,坚定的C大调对应着费加罗攻击凯鲁比诺的自信,铜管乐制造的军乐效果则为第二幕开场的幽怨情调做了艺术所需的对比性铺垫。

表1 《费加罗的婚礼》第一幕的动作或情节进展
2.“矛盾”的深入和爆发:咏叹调与终场的协作
第二幕会继续第一幕的喜剧气氛吗?如果第二幕完全继承第一幕的戏剧节奏与基调,《费加罗的婚礼》将毫无疑问地沦为平庸之作,但莫扎特适时地以咏叹调形式展现了伯爵夫人的悲剧性(分曲10),将两性关系“矛盾”导向深入,进而建立起一个完全不同于第一幕的戏剧世界。伯爵夫人的悲情符合弗莱塔克定义悲剧的三个标准:“对于主人公是至关紧要的;必须出人意料、突然出现;必须引起观众一系列的联想,使人清楚地感到它和前面的情节有合情合理的联系。”⑦伯爵在第一幕对苏珊娜的垂涎让伯爵夫人难堪,这也增加了观众对这位悲情弃妇的关注。音乐上的显著特征是速度的骤降,小广板的速度同第一幕惯常的快板速度形成了强烈对比,这对应着伯爵夫人的内心苦楚。更为重要的是,这首《求爱神给我安慰》(分曲10)同《美好时光哪里去了》(分曲19)及剧终原谅伯爵的宽恕场景共同实现了中心立意、协同达成了最终的戏剧高潮。因此,《求爱神给我安慰》是剧作构思的核心分曲,这种重要性无法在凯鲁比诺的咏叹调《你们可知道》(分曲11)和苏珊娜的咏叹调《你过来跪下》(分曲12)中实现;通过控制戏剧节奏,上述三首咏叹调共同建构了一个以表述人物内心情感为中心的戏剧世界,这与第一幕以展现人物矛盾关系的戏剧世界截然不同。莫扎特通过咏叹调的连续呈现,突出了“情欲纠葛”在《费加罗的婚礼》中的地位,阶级问题则进一步被削弱。莫扎特和达·蓬特把伯爵夫人的登场位置安排在了第二幕的开场,这样伯爵夫人就成为了唯一没在第一幕露面的主要人物,观众一定对此满怀好奇(这制造了戏剧悬念)。在长达17个小节的利都奈罗前奏之后,伯爵夫人的悲切咏叹映射出她和伯爵间的深刻矛盾及其对爱情的绝望,两性关系矛盾这一立意由此导向深入。
苏珊娜的《你过来跪下》是一首为凯鲁比诺换装的动作咏叹调,但歌词与音乐说明“换装”只是幌子,这首分曲主要用于营造轻佻的情色氛围:跳跃性的音符显露出苏珊娜的激荡心情和对凯鲁比诺的由衷喜爱,这一点也与费加罗威胁凯鲁比诺的咏叹调取得了逻辑联系;但这种角色定位和戏谑性的音乐风格从整体上弱化了苏珊娜的人物形象,也与本剧赞美女性的主题意念相悖,苏珊娜的咏叹调更应该用于表现她被伯爵引诱后的反思。莫扎特如此设置咏叹调结构,只能是为了强调歌剧的“情欲色彩”。随着“矛盾”的不断积累与深入,莫扎特需要以一个长时段的终场(实际演出中,这个终场大约持续20分钟)来持续不断地呈现“矛盾”:从开始的二重唱逐步发展到八重唱,随着各个角色的不断卷入,前两幕积累的“多重矛盾”开始激化并最终爆发——马尔切琳娜、伯爵、巴尔托洛要求费加罗按照契约完婚;伯爵夫人、苏珊娜、费加罗则结成联盟反对此事,终场在咏叹调的深入铺垫下完美地呈现了“矛盾”的爆发场景。

表2 《费加罗的婚礼》第二幕的动作或情节进展
二、平等和宽恕:“人性和解”立意的实现
《费加罗的婚礼》中的“多重矛盾”是欧洲大革命时代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但莫扎特和达·蓬特不满足于仅仅描绘人类历史中经常出现的种种“矛盾”,而是在《费加罗的婚礼》中提出了一种解决“矛盾”的方案,实现“和解”的核心力量是“人性”。人性是人本质的心理属性,包含真假、善恶、美丑等对立因素,莫扎特相信人性中“真、善、美”的力量,将平等意识和宽恕精神注入了《费加罗的婚礼》的立意当中,从而重塑了剧中人物因性别关系和社会阶层造成的“多重矛盾”,实现了全面而深入的“人性和解”。
1.“和解”初现:伯爵夫人咏叹调的核心作用
第三幕的终场重要吗?如果只考虑戏剧情节因素,这个终场表现的确实是本幕最重要的戏剧场景——费加罗与苏珊娜的结婚仪式。但莫扎特的音乐说明“认亲”六重唱(分曲18)和伯爵夫人的咏叹调(分曲19)比它更重要。第三幕的结构存在问题:为了让同时饰演巴尔托洛与安东尼奥的首演演员弗朗切斯科·布萨尼能有时间更换服装⑧,“莫扎特将本幕唯一可以移动的分曲(因为没有话剧原作的对应部分)——《美好时光哪里去了》及其宣叙调的位置后移了。”⑨在莫扎特原来的剧作构思中,“认亲”六重唱与伯爵夫人咏叹调的次序是倒置的,这显然是更合理的次序。在大多数实际演出版本中,也都采用了先咏叹调后六重唱的合理顺序⑩。这样处理也有益于进一步突出伯爵夫人在莫扎特构思中的卓越地位。伯爵夫人这首咏叹调的结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它是全剧的转折点,也是第三幕剧作结构的核心。“像格鲁克和珀塞尔一样,莫扎特和谐歌剧的其他作曲家独具慧眼,他们知道少量的咏叹调如果安排得当,在整体形式中会具有何等力量。”在此之前,没有实质性的“和解”场景出现,伯爵夫人的自我拯救带动了整个戏剧的反转:马尔切琳娜与巴尔托洛认出了他们被偷的儿子费加罗,一家人达成了和解,这也为第四幕的剧终大和解埋下了伏笔;这首咏叹调还真正转变了伯爵夫人的行为方式,在随后出现的她和苏珊娜的写信二重唱中(分曲20),伯爵夫人首次展现出与女仆一样的音乐风格(莫扎特在此有意混淆了主仆的界限),这说明伯爵夫人平等地进入了苏珊娜的生命内里,她愿意真正地理解苏珊娜,并和这个对自己构成间接伤害的女仆达成深度和解,这段写信二重唱也是本剧最终由女性角色实现中心立意的一种铺垫。伯爵夫人咏叹调前置的另一个优点是两首咏叹调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咏叹调集合单位:伯爵咏叹调所表现的狭隘、自私、占有犹在耳前,伯爵夫人醍醐灌顶般的正直誓言就紧随而来,两位主要人物精神世界的高下立即清晰可辨,这也进一步验证了莫扎特在本剧中所持的性别观念——女性比男性更优秀。

表3 《费加罗的婚礼》第三幕的动作或情节进展
2.“和解”的最终达成:咏叹调与终场的协作
第四幕的剧作结构(五首咏叹调加一个终场)非常特殊且耐人寻味!莫扎特为什么要设置如此多的咏叹调呢?五首咏叹调密集并置导致了组织形式比例上的严重失衡(同前三幕的结构形式反差巨大),这招致了一些批评:“《费加罗的婚礼》的最大问题发生在歌剧的最后一幕。很明显,马尔切琳娜和巴西里奥的咏叹调是多余的,对于戏剧进展没有贡献。”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在第四幕开场,三首咏叹调形成的链条展现了莫扎特希望创作一个与话剧《费加罗的婚礼》不一样的结局。”可以肯定的是,莫扎特塞入过量的咏叹调绝不仅仅是为了迎合歌手和观众的愿望,这些所谓多余的咏叹调大多有其自身的戏剧意图:马尔切琳娜咏叹调的戏剧中心是“性别平等”、巴西里奥的咏叹调(《在那样的年纪》,分曲25)则运用反讽的手法指涉了“阶级平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马尔切琳娜和巴西里奥的咏叹调都采用了通常代表贵族阶层的小步舞曲模式,“在上流社会,学习小步舞曲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费加罗和苏珊娜的咏叹调(分曲26、27)也都前置了通常贵族角色咏叹调才采用的宣叙调,颠覆性的音乐戏剧构思由此得以逐渐清晰——莫扎特刻意混淆了阶级、性别的差异,平等意识被集中地予以强调。
马尔切琳娜的女性宣言(《公羊和母羊》,分曲24)绝不能删除。“从费加罗和苏珊娜的死敌,转变为他们的朋友和同盟军——这一至关重要的效忠对象的变更,需要得到强调,莫扎特就是这么做的。这首咏叹调表达的观点——女人被男人非法压迫——为尾声里由女性扮演主导角色埋下了伏笔。它对结局起到了十足的推动作用:解决问题、修正错误的都将是女人。”随后,这一主题在费加罗与苏珊娜的咏叹调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强调:费加罗的《睁开你的眼睛》宣示了费加罗对形势的误判及莽撞,这对解决问题于事无补;紧随其后的《美妙时刻将来临》在结构地位上非常重要。显然,莫扎特安排了苏珊娜来做总结陈词,苏珊娜的咏叹调不仅仅以仁慈和宽容之心原谅了费加罗的狭隘,更上升到喜乐和澄明的新境界,一个优秀的新女性已然成长起来,并预示了另一个更为出色的成熟女性将引发最终的和解。最终的“和解”发生在最后的终场,莫扎特早已对此缜密安排:“在大范围的结构层面,此剧的整体趋势是朝向结尾处,在这里,伯爵夫人的宽恕带来人性的顿悟。”全剧结构的缜密构思就是为了最后终场的戏剧凸显——蒙羞后的伯爵真心祈求原谅,伯爵夫人则回应以仁慈的宽恕,这段不足10小节的乐段可以看作是嵌入终场的一段“微型咏叹”,这种人性力量感动并升华着世俗世界的众生,“和解”由此真正达成并令人信服。“如果没有先前的准备和清晰展现,在剧终时唐突引入这种崇高格调,《费加罗的婚姻》的质量便会大打折扣。导向最终和解的线索其实贯穿全剧”。显然,伯爵夫人的两首咏叹调是剧终崇高立意得以实现的重要铺垫,马尔切琳娜、苏珊娜、费加罗等角色的咏叹调分曲也与中心立意紧密相关。

表4 《费加罗的婚礼》第四幕的动作或情节进展
结 语
《费加罗的婚礼》远远超越了十八世纪作曲家对于意大利喜歌剧的认知,这部传世经典混合着咏叹调、重唱、终场等多种结构形式的力量,莫扎特小心翼翼地平衡着这些结构形式的位置与比例,复杂的剧作法技巧保证了“多重矛盾”与“人性和解”这种复杂立意,获得了有效且有时间延展的呈现;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咏叹调是莫扎特唯一贯穿全剧的结构形式,如果没有这些咏叹调,或者只是删去部分咏叹调,中心立意都将无法实现。与咏叹调引领剧作形式这样的“技术因素”相比,《费加罗的婚礼》的戏剧立意更具当代价值:无论在剧作首演的十八世纪下半叶,还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性别关系和社会阶层都是导致“矛盾”的重要诱因,“矛盾”映射着人与社会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暴露出人性的弱点与社会发展模式的不完美;正因如此,平等意识和宽恕精神所带来的“人性和解”才更显得弥足珍贵。更不可思议的是,《费加罗的婚礼》预示了女性在此后历史进程中的成长和在争取平等权利方面获得的胜利,戏剧立意的非凡价值由此获得了历史发展维度上的实证。在社会价值趋向多元的今天,艺术的社会功能也趋向于多元化:艺术不仅引领人类思维的提升,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滋养和教化人性(正如《费加罗的婚礼》的立意所示),人本质属性层面的进化才是推动人类与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动力,这也应是文艺创作予以关注的重要命题。
① 杨燕迪:《歌剧的真谛:以音乐承载戏剧——评克尔曼的<作为戏剧的歌剧>》,《音乐艺术》2000年第1期,第65—68页。
② 大卫·凯恩斯:《莫扎特和他的歌剧》,谢瑛华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119页。
③ Mary Hunter:ThecultureofoperabuffainMozart’sVienna:Apoeticsofentertain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p.95.
④ 任明耀:《博马舍和他的费加罗三部曲》,《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第90页。
⑤ Brigid Brophy: ‘Figaro’andtheLimitationsofMusic. Music & Letters, Vol. 51, No. 1 (Jan., 1970), pp. 26-36.
⑥ 保罗·罗宾逊:《歌剧与观念》,刘彬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⑦ 余秋雨:《舞台哲理》,中国盲文出版社2007年,第196页。
⑧ Moberly, Robert, and C. Raeburn.Mozart’s‘Figaro’:ThePlanofActIII. Music & Letters 46.2(1965),pp.134-136.
⑨ Moberly, Robert, and C. Raeburn.Mozart’s‘Figaro’:ThePlanofActIII. Music & Letters 46.2(1965),pp.134-136.
⑩ 例如2006年萨尔茨堡音乐节版、2006年伦敦皇家歌剧院版、2014年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