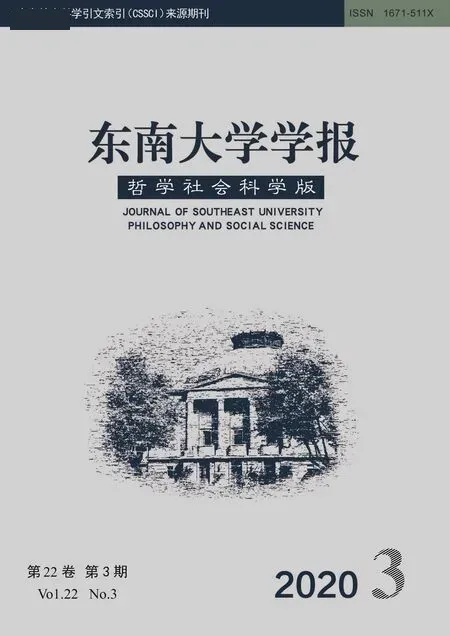忧患意识与君子的责任
何善蒙
(浙江大学 哲学系,浙江 杭州 310028)
一、什么是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中国思想史中所凝练出来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人文精神,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活的源泉,正是在忧患意识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从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文化也由此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形态而影响深远。
作为一种学理的概括,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是徐复观先生首先使用“忧患意识”一词来概括中国早期的思想传统。徐复观在研究西周文明的精神时,提出了“忧患意识”说。根据徐先生的概括,“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地自觉的表现”(1)徐复观: 《中国人性论史 (先秦篇)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9页。,忧患意识是人的精神自觉、成熟的直接表现,是指由殷周变革而来的中国早期思想的特质(2)关于殷周变革,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是这个方面研究的典范,后来此说法也成为了中国早期思想研究的一个共识。,从而在中国思想传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徐复观先生在考察西周文明的时候,认为与殷商相比,西周人的精神发生了重要转变: “在以信仰为中心的宗教气氛之下,人感到由信仰而得救; 把一切问题的责任交给于神,此时不会发生忧患意识; 而此时的信心,乃是对神的信心。只有自己担当起问题的责任时,才有忧患意识”, “在忧患意识跃动之下,人的信心的根据,渐由神而转移向自己本身行为的谨慎与努力。这种谨慎与努力,在周初是表现在 ‘敬’‘敬德’‘明德’等观念里面”(3)徐复观: 《中国人性论史 (先秦篇) 》,第20页。。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精神价值,从殷周变革以来,忧患意识在西周的文化传统中得到了非常直接的表达,也由此成为西周人文精神的重要方面。由此,如果我们说后来中国文化的传统是继承周代而来的话,那么,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最为核心的精神价值,在中国文化中也得到了普遍的延续。
虽然忧患意识作为一个观念的使用是从徐复观先生的作品开始,但是,事实上,忧患意识广泛存在于中国传统经典中。在中国传统经典中,最早将“忧患”两字连用的,出现在《周易》中。《易传·系辞下》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下》又云: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王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始终,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系辞传下》的这两段描述,很明显的是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忧患意识是《周易》的一种核心精神,《周易》之创作就是基于这种忧患意识的;其次,忧患意识的萌发是在殷周变革之际。这种忧患意识对于殷商之际的变革有非常重要的、直接的作用,所以,孔颖达在疏解《周易》的时候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者,若无忧患,何思何虑,不须营作。今既作《易》,故知有忧患也。身既患忧,须垂法以示于后,以防忧患之事,故系之以文辞,明其失得与吉凶也。”(《周易正义》卷八)从这个角度来说,殷周制度变革,小邦周之所以灭掉大邑商,其中一个直接起作用的因素,就是“忧患意识”。正是因为如此,在《周易》一书中,这种忧患意识实际上无所不在。如果说《周易》是一种变化之书,其所讨论的核心议题就是“变”的话,那么世界中一切现象无不处于变化之中,为了更好地应对这种永恒的变化,随时保持警惕,以忧患意识来应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可知的变化,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正因为如此,《周易》对于人的现实行为具有更为直接和永恒的指导意义,作为“大道之源”“群经之首”,《周易》也是当之无愧了,因为它是对于人的现实行为的最直接的关注。
如果说殷周变革是一个契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时代开始的很多经典都对忧患意识有了比较明显的表达,或者说,忧患意识成了文本的一个核心内容。比如在《尚书·周书》部分,忧患作为一个中心的观念,经常被周武王、周公、召公等人提及,这也是对殷周变革的直接回应,比如“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尚书·无逸》),很明显,在这里,忧患意识是被当作君子的重要德性而表达出来的,也是君子人格和治理行为的依据所在。又比如在《诗经》中,这种忧患意识同样是非常明显的,如《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而到了《论语》《孟子》的时代,这种忧患意识已经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文化心理和精神价值,比如在在《论语·卫灵公》中,“君子忧道不忧贫”以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提法,很直接地把忧患意识作为人(尤其是君子)的基本精神价值确立了起来。《孟子·告子下》中“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说法,更是耳熟能详。
凡此种种都表明,忧患意识作为中国古人对于现实的深刻反思而来的经验总结,成为其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二、为什么需要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为什么会成为中华早期思想传统中的一种重要价值?大概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于天命的敬畏、对于未知的恐惧以及对于时变的重视。这三个因素在忧患意识的产生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对于天命的敬畏,这是忧患意识的价值根源;对于未知的恐惧,是忧患意识的心理基础;而对于时变的重视,是忧患意识的现实导向。
如前文所言,殷周制度变革是忧患意识产生的基础,那么,小邦周取代大邑商实际上就是一个天命转移的行为。而对此天命转移的反思,在周人的观念中形成的就是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周人对于天命转移的反思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构成了这种反思的结论,即敬、谦与德,这三者也可以说是构成忧患意识的基本内核。敬在这里是最为根本的,它表达的是对于天命的敬畏,按照徐复观先生的说法,这是周人哲学的核心,“周初所强调的敬的观念,与宗教的虔敬,近似而实不同。宗教的虔敬,是人把自己的主体性消解掉,将自己投掷于神的面前而彻底皈依于神的心理状态”,“周初所提出的敬的观念,则是主动的,反省的,因而是内发的心理状态。这正是自觉的心理状态,与被动的警戒心理有很大的分别。……因此,周人的哲学,可以用一个‘敬’字作代表。”(4)徐复观: 《中国人性论史 (先秦篇)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0-21页。徐复观先生区分了周之前和周初的敬的观念,认为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主要是一种宗教性的虔诚(在这种虔诚之下,个体的选择和判断是不存在的,即所谓“人把自己的主体性消解掉”),而后者则是人的一种主动的、自觉的行为(即人通过对于现实的反省而主动接受的一种状态,这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彰显,而非宗教的表达)。在徐复观先生看来,这种对于天命的敬,是周人忧患意识的重要来源。其实,如果我们去看《尚书》《诗经》等文献,这种“敬”的表达比比皆是,由此,“敬”也构成了周人哲学、思维的重要向度。对于天命的敬,实际上是对于天命转移的一种积极回应,这是在殷周变革背景下非常自然的选择。这种对于天命的敬,在现实中直接可以转化为对行为的“谦”的强调,我们通常都说谦逊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如果我们把谦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考察,就更容易理解谦的由来及其意义了。《周易》中有“谦卦”即是对此的最好描述,谦卦的卦辞曰“谦:亨。君子有终”,孔颖达对此疏解为:“谦者,屈躬下物,先人后己,以此待物,则所在皆通,故曰亨。而小人行谦则不能长久,惟君有终也。然案谦卦之象,‘谦’为诸行之善,是善之最极,而不言元与利贞及吉者,元是物首也,利、贞是幹正也。於人既为谦退,何可为之首也?以谦下人,何以幹正於物?故不云元与利、贞也。谦必获吉,其吉可知,故不言之。况《易经》之体有吉理可知而不言吉者,即此《谦卦》之繇及《乾》之九五‘利见大人’,是吉理分明,故不云‘吉’也。”(《周易正义》卷二)谦成为了人类行为的基本要求,也是君子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确保其行为善始善终的基本保证。在周人那里,这种谦是直接源于对天命的敬,因为天命对现实生活有着根本的决定意义,人不能不敬天,由此,对于个体行为的谦逊以及谨慎的强调也是自然而然的,正所谓“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旻》)。在这种谦的行为要求基础上,实际上强调的是以德行来承接天命的一种基本的行为方式。“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这是周人对于天命转移的一种解释,也是对自身行为的一种基本要求,我们在后来中国传统中看到道德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跟周人的这种反省有关系的,周人在反省的基础上,围绕着德行进行了系统的制度设计,“故知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而制度典礼之专及大夫士以上者,亦未始不为民而设也”(5)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王国维集》(第4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 135 页。。
对未知的恐惧是忧患意识产生的心理基础。人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对安全感的追求是最为基础的。人对未知的恐惧程度是和人对于现实的掌握程度密切相关的,这也就是说,越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活贫乏的时代,这种恐惧感会越强烈,这大概是人类的共同心理,所以,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诸如宗教、鬼神等等的信仰是非常普遍的。在中国古代,生活水平的低下是极其自然和明显的一个事实,“当尧之时,水逆行,氾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着为巢,上着为营窟”(《孟子·滕文公下》),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下,人的生活自然是面对种种的不可知,恐惧也是在所难免的。这种情形应该怎么来面对?按照《孟子》的说法,“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滕文公下》),尧舜派鲧禹治水,这是对于人类巨大的福利,也是人在应对自然界种种未知状况(尤其是生存威胁)面前,所采取的积极努力,按照孟子的解释,这就是圣人之道。从这样的解释方式来看,在中国的传统中,我们应对未知恐惧的方式,主要不是一种宗教化的形式,而是强调个人的行为努力(尤其是道德行为),这也就是后来强调最多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而这种行为方式,也是忧患意识的一种直接表现,“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成为人们最为清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对于时变的重视,这是忧患意识在现实维度的具体展开。中国人对于“时”的重视,应该来说是极其明显的一个事实,这与早期农耕生活的基本特点是密切相关的。由于农耕生活的需要,导致中国人对于“时”特别敏感。而对“时”的强调,就意味着行为的具体性和针对性,中国传统重视的是人的实践,这种实践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跟时间有着紧密关联的行为方式。在《周易》中有非常丰富的“时”的观念,也可以说,“时”是《周易》最为核心的、基础的观念。《周易》对于“时”的描述可以分为两种类型:首先是对自然时间的描述,如“观天地之神道,而四时不忒”(《观卦·彖传》),“变通莫大乎四时”(《系辞上传·第十一章》)等;其次是侧重对人事活动的概括,如“君子藏器於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系辞下传》),“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卦·彖传》)等,这种“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时务、时势等含义。不管何种意义的“时”,其所强调的都是两个方面的意思,首先是具体性,也就是任何行为都是针对具体的时间、时势而展开的,是应对具体情境的需要;其次是变化性,时的不同就意味着变化的存在(普遍的变化)。那么,人应该以何种方式来应对这种现实的“时”“变”呢?忧患意识成为一种直接的选择,在这个情况下,忧患意识意味着对具体的、现实的变化保持一种警惕,由此可以很好地达到应对时势的目的,所以,《周易》中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周易·乾·文言》)
三、责任与担当:君子忧患意识的内核
虽然在传统中关于忧患意识的表述是多维度的、多层面的,在现代人关于传统忧患意识的研究中,所涉及的内涵也是极为丰富的,但是,在我看来,传统对于君子忧患意识的强调,实际上重视的就是君子的社会责任和道义担当。作为一个君子,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要有忧患意识,我们在前文已经做了初步的讨论,对于天命的敬畏、对于未知的恐惧以及对于时变的应对,这些都可以对君子忧患意识之产生做一个比较清晰的梳理。而在这个梳理的背后,所呈现出来的无非是责任与担当。所谓责任,是君子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格形象,对于社会所应当具有的责任感;所谓担当,是在这种责任感的背景下,君子对于道德行为的自觉履行。由此,责任感是基础,因为有这种社会责任感,君子才会有对于现实社会、人生的种种未雨绸缪的忧患;担当是现实表达,正是因为有对于现实的忧患,君子的行为方式就是积极承担道义,这种道义是指对于学术(道与学)的承担,也是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对于家国天下的责任),由此,忧患意识在现实表达上可以有忧道、忧君、忧天下等不同的形式,但是无论哪一种形式,都是其担当精神的一种表达。
在《论语》的尧曰篇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
“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寿。”答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在《尚书·商书·汤诰》中也有类似的说法:
嗟!尔万方有众,明听予一人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并告无辜于上下神祗。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聿求元圣,与之戮力,以与尔有众请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贲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辑宁尔邦家,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凡我造邦,无从匪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呜呼!尚克时忱,乃亦有终。
“天下有罪,罪在朕躬”,这样的表述,无论是在舜的话语中,还是在商汤的话语中,都很清楚地表达出一种对于天下的责任意识。这在古代传统对于王的德性的设定中是非常基本的一种品性,也就是说,作为王者必须要具有责任感(6)《道德经》 第三十九章“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第四十二章“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实际上表达的也是君王的这种责任。。如果说在君王这里,这种责任是源于天命和政权的话,那么,在后来对于道德行为加以强调的背景之下,对于君子的这种责任意识的重视,也是自然而然的后果,同时,也是基于君子的道德义务而来的。在《论语》泰伯篇中有一段论述,可以直接说明这一点。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里,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很明显是对于君子责任的一种强调,对于道德的承担,这就是君子的责任。也正是因为有这种责任的存在,君子必须是要有忧患意识的。只有忧患意识,才能强化君子的这种责任感;而君子的这种责任感,同样可以更好地维系君子的这种忧患意识。因此,责任感毫无疑问是君子忧患意识的一个基本内核。
君子必须要有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直接表现为对于道义的担当。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君子,是有承担天下道义的责任的,这也就是孔子一直以道德来作为对于君子人格要求的意旨所在。为天下,行仁义,这就是君子的担当。在《论语》微子篇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在这段描述中,作为隐士的长沮、桀溺对孔子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因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那样的社会现实,又有谁能够改变么?孔子汲汲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游说诸侯,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行为方式,除了彰显出个体道德的崇高之外,对于改变现实有什么作用呢?对于这样的批评,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在这段自白中,孔子表达出来的就是对于世界的一种义无反顾的担当精神,世界的混乱,对于君子来说,毫无疑义要承担拯救、改变世界的责任,这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孔子就是以这样的担当精神来成就自己的人格形象的,无论是在何种困境之下,这种担当精神让孔子具有了面对现实的强大武器,成就了一个崇高的道德人格形象。
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如予何!”孔子使从者为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史记·孔子世家》)
困于匡,厄于陈蔡,这是在孔子生命中非常困顿的时刻,但是,因为孔子有着这样积极担当的精神,才会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如予何”的自信,才会有面对困境而保持一种积极乐观态度的可能。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责任感和担当精神是构成忧患意识的重要内核。因为有责任感,所以君子时刻保持着忧患意识。君子的这种忧患意识并不是指向个体的生活事实的,正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也正是因为这种担当的精神,我们在中国传统中才深刻地感受到了一种基于文化内核的精神价值。
四、家国与天下:君子忧患意识的价值指向
如前所言,君子的这种忧患意识指向的不是个人的生存事实状况(富贵或者贫穷),而是对于理想价值的实现,对于社会责任的担当。正是在家、国、天下的关注中,尤其是在天下的意义上,君子的忧患意识才得以超越自我的有限性而具有更高的升华。在前文,我们曾对君子忧患意识的层次作了简单的区分,即忧患意识可以涵盖忧道、忧君以及忧天下等不同层次。这些不同层次,是忧患意识在君子日常生活经验中的现实展开,体现的是忧患意识的丰富性和具体性。
忧道,是对于道义(道德)的忧患,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忧患意识,忧道关注的更多的是精神价值,或者说是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对于个体来说,关注什么内容,是有着很多选择的可能性的。当然,最基本的形式是选择物质生活还是选择精神价值。通常来说,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是个体存在的基本保证,是维系个体存在的重要手段,但是,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大体对于执着于个体物质生活选择(以物质生活选择为优先)的方式,给予的评价并不特别高,而对于超越物质生活指向精神价值的选择,都给予了相当高的重视,认为这样的方式,是人之为人的意义所在。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对于忧道还是忧贫、谋道还是谋食问题的选择,就是对于个体存在的精神价值的一种探讨。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论语·卫灵公》)
孔子在这里的讨论,就是围绕道和食的问题展开的。道和食可以说是人所追求的两种基本形式,孔子开宗明义地提出,一个君子必须考虑道义的问题,而不是纠结于衣食的问题,这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基本立场。当然,这并不是反对君子对于衣食的追求,而是说在衣食和道义的比较之中,道义具有更高的精神价值,道义才是君子成为君子的标志。君子和小人有着行为方式上的根本差异,董仲舒曾说:“遑遑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君子之事。遑遑求财利,常恐匾乏者,小人之事”(《汉书·董仲舒传》),简而言之,君子关注的重点在于仁义,在于百姓;小人关注的重点在于钱财,在于自己。这样的价值立场,在中国传统中,可以说是一贯的。孔子紧接着的讨论非常有趣,“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以衣食为重点,注重的是物质生活的满足,在这样目标的指引下,你去参加耕种,可是也难免会被饥饿所困扰;如果你以学道也己任,注重的是对于道义的担当,这样的学习,也不会妨碍你获得物质利益,因为禄也会自然而然地到来。简而言之,注重物质生活,反倒不一定会实现自己的目标;关注道义,也可以满足物质生活。这样一来,对于君子来说,其行为的要求就非常明确了,那就是“忧道不忧贫”,作为一个君子,就必须以道义作为其行为的基础。
由此,对于道义(道德)的忧惧成为君子人格的根本标志,这是君子忧患意识的基本内涵,是对于一个人是否是君子的判断标准,“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这样对于道义(道德)的推崇,也就成为中国思想传统中最为基本的向度。所以,如果说君子的忧患意识是具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涵,那么,不管我们怎么去表述这个忧患意识,忧道是最为根本的,它奠定了君子的基本色调,渲染了整个中国传统的基本精神向度。
忧君,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对于君主的担忧(忧君之事)。当然,如果从中国传统社会来看,三纲之中是以君臣为主(7)这说明君臣大义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在社会层面来说,儒家作为一种面向社会生活的理论形态,其对于社会治理的意义,最终是落实在君臣关系上来展开的。,君臣关系是以“忠”(8)当然,作为一种伦理形式的“忠”在中国传统中是存在变化的,不同时代的具体内涵和要求并不一样,尤其是先秦和秦汉以后,作为一种伦理标准的要求产生了较大的改变,但是作为一种基本伦理精神,是依旧存在的。为基本要求。如果说君代表的是国的话,其实在君臣关系中,呈现的是对家国一体(9)家国一体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逻辑,这无论是在儒家的思想传统中,还是在道家的思想脉络中,都是被认可的。这与中国传统社会的血缘宗法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在儒家的文献,无论是《大学》还是《孝经》中都有明显地表达。考虑到《大学》和《孝经》产生的年代下限是汉代,我们可以说,至迟在汉代的时候,这种基本的思想脉络已经确立起来。的行为方式的基本描述。这样一来,忧君不仅仅是士人对于君主本人的一种责任关系,也是对于家和国的责任关系的具体化表达,在忧君上,表达的是士人对于家和国的责任和义务。
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今年以来,不雨者百有馀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奸宿赃,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从事于文学,见有忠于君、孝于亲者,虽在千百年之前,犹敬而慕之;况亲逢阁下,得不候于左右以求效其恳恳?(韩愈《上李尚书书》)
在韩愈的这篇著名的文字中,“赤心事上,忧国如家”是最为核心的内容,这也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对于君主忠心耿耿,忧虑国事如同忧虑家事一样。这种情怀在古代知识分子(君子)那里是一种基本的价值立场,对这样的价值立场,最为著名的描述,是范仲淹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从这个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忧君并不是狭义地围绕君主来展开的,而是跟忧家、忧国和忧民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士人所关注的重心所在,也是其精神价值的直接表达,对此在理论上作了重要、直接的阐释的是张载: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西铭》)
“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在张载看来,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由此,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这样,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因此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有所不同。但所有的人都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对于君子来说,更是应该承担起自己对于家、君、国的责任。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忧道到忧君的内在理路。忧道是君子行为方式的基础,忧君是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表达(或者说正是在忧君的基础上,君子忧道的这种精神价值找到了具体化的表达)。忧君就其内涵来说,包含着忧家、忧国以及忧民的不同层面,这是一个圆融无碍的整体,贯穿于其中的就是君子的道德立场。
最后是忧天下,以天下为忧,这是君子忧患意识的境界所在,就像范仲淹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这种忧乐的观念也是在君子文化传统中有着深刻认同和广泛影响的观念。立足于天下,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分子(君子)的一种非常崇高的价值立场,虽然人的现实存在形式总是有限制性,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天下关怀,“心忧天下”就是这种情怀最为直接的表达。从先秦时代开始,君子的这种天下观念是非常普遍的,无论是在儒家的文献中,还是在道家的文献中,都有非常深厚的基础和普遍的表达,这是君子的价值立场和理想境界。王阳明有一段论述,可以很直接地说明这一点,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大学问》)
其实这样的想法在中国古代传统中是非常普遍的,立足天下而非一国一家一姓,这无论是从理论的高度来说,还是从思想的境界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黄宗羲曾指出:
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况于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许也,况于杀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见,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君为己死而为己亡,吾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匿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
立足于天下,心系万民,这才是真正的君臣关系。在黄宗羲这里,一姓并不具有最终的价值,只有天下才是,天下是士人精神价值的归依。这也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贯的价值立场。正是在对于这种立场有深刻领会的基础上,黄宗羲才会强调“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跟黄宗羲同时代的顾炎武才会直接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10)这段话后来被梁启超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聊消遣》),从而影响深远。(《日知录·正始》)。
由此,从忧道到忧君再到忧天下,实际上是君子之忧患意识的不断具体化和提升的过程。忧道是一种道德责任的基础,是君子对于自我责任的一种认同,这是君子忧患意识的起点。这样的忧患意识必须在现实层面具体展开,才能使得忧患意识作为一种事实的形态,由此,忧家、忧国、忧君、忧民,就构成了君子之忧患意识的现实展开路径。但是,君子的这种忧并不是限制于一家一姓、一国一君的狭隘观念,而是具有着超越性意义的,这就是忧天下。忧天下,是君子忧患意识精神境界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