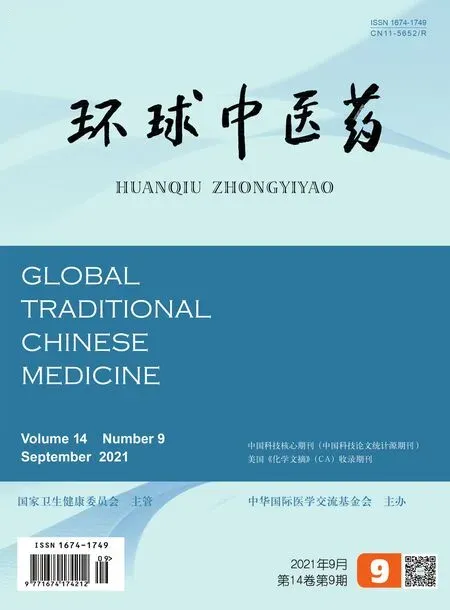杨素清教授运用角药治疗掌跖脓疱病经验
张艳红 安月鹏 石光煜
掌跖脓疱病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疾病,局限于掌跖部,在红斑的基础上出现深在无菌性小脓疱,呈周期性反复发作,伴有角化鳞屑[1]。其病因病机复杂,病情缠绵难愈。在掌跖脓疱病的治疗过程中,中医治法体现了其特有的优势。临床治疗掌跖脓疱病,中医方剂配伍形式常有单行、对药、角药、方药等,旨在通过配伍减毒增效。将三种中药组合在一起,配伍应用,为角药[2]。其形成基于中医基础理论、辨证论治和配伍原则,而后产生三足鼎立、互为犄角的协同叠加效果,三药常体现相须相使和相反相成的关系,从而加强药物性能,增加药物作用,扩大治疗范围,组方意义也更为广泛深邃。杨素清教授结合多年临床经验,运用茯苓、猪苓、泽泻,白术、苍术、薏苡仁,蜈蚣、紫草、鬼箭羽,土茯苓、菝葜、乌梅,茯苓皮、陈皮、桑白皮五组角药,分别从六淫之“湿”、脏腑之“脾”、传承经验之“毒、瘀”、中药研究之“现代药理”、取类比象之“以皮达皮”角度论治掌跖脓疱病,以期为临床治疗掌跖脓疱病提供新的思路。杨素清现为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专科带头人,师从中医皮肤科名家王玉玺教授,并在继承王老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出治疗掌跖脓疱病的特色辨治诊疗体系。笔者有幸跟师左右,亲聆教诲,收获颇多,现将杨素清教授应用角药治疗掌跖脓疱病的经验总结如下。
1 茯苓、猪苓、泽泻
1.1 从六淫之“湿”论治掌跖脓疱病
掌跖脓疱病中医属“瘑疮”范畴,《医宗金鉴》有:“形如茱萸,生于指掌,两手相对而生,亦有成攒者,起黄色白脓疱,痒痛无时,破津黄汁水,时好时发,极其疲顽,由风湿客于肤腠而成”[3],指出其病机是风湿客于肤腠所致,其症状主要体现在湿邪的致病特点,如破津流水脓疱,极其疲顽等。故湿邪是掌跖脓疱病重要的致病因素。湿有内、外之分,外湿多源于久居湿地冒雨涉水等,内湿多因脾失健运,水湿内停,且内外之湿互相引动诱发。中医认为湿久滞于体内,可蕴阻化热成毒发于皮肤[4]。杨教授认为掌跖脓疱病的发病多因禀赋不足,外感湿邪,客于肌腠,湿蕴日久,化热成毒,搏结气血,流溢四肢,起疱生脓,指出湿邪是其主要致病外邪,是其发生的关键致病因素,宜以利湿为基本治则。
掌跖脓疱病的发病局限于掌跖部,且跖部多于掌部。《素问》载:“伤于湿者,下先受之。”湿为阴邪,其性类水,湿性趋下,易袭阴位,故湿邪为病,常伤及人体的下部。湿性重浊黏滞,临床表现可有沉重之感和分泌物及排泄物秽浊不清之状,其与主要的皮损特点“红斑上有水疱、脓疱、糜烂面、渗液、脓液色黄、粘稠液体”等相符;黏滞指湿邪为病多缠绵难愈,病程较长或反复发作,与其慢性复发性周期性发作相符,皮损特点亦相似。湿邪为病,阻遏气机,损伤阳气,气不行则湿不化,与皮肤胶着难解,皮肤出现肥厚、粗糙、脱屑、干裂与本病伴有片状鳞屑、角化脱皮、皲裂干燥等表现相符[5]。杨教授认为湿邪的致病特点结合掌跖脓疱病的疾病特点,主要体现在发病部位、皮损特点、病程变化、伴随症状等方面。
1.2 除湿角药茯苓、猪苓、泽泻
基于审因论治,杨教授常言外湿以利为宜,故治疗时,善将茯苓、猪苓、泽泻相伍为用。茯苓,味甘而淡,甘能补,淡能渗,性平和,既祛邪,又扶正,利中有补,健脾宁心,不伤正气,为利水之要药;猪苓,甘淡渗湿,虽仅利水渗湿之功,但利水之功强于茯苓,经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二者相须,一走气分,一走血分,前入脾肺而渗湿,后入小肠膀胱而泻湿,合而为用,气血兼行,淡渗利水。泽泻,甘淡利水渗湿,苦以泻热,与茯苓相伍,既泻又补,泻则利水渗湿,补则健脾治湿;与猪苓相伍,利湿泻热之性相同,一则入肾和膀胱,一则入小肠和膀胱,二者合用,使肾和膀胱脏腑相通,泄利下焦湿热。三药相合,同类相须,取猪苓汤之意,淡渗利水而不伤阴,气血兼行而不耗气,补泻同用而不伤肾,达利水渗湿兼顾中焦之功。
1.3 除湿角药在掌跖脓疱病中的应用
杨教授在治疗湿邪为主的掌跖脓疱病时,以茯苓、猪苓、泽泻作为角药,常辨证配伍他药而用。湿热者加清热燥湿之黄连、黄柏,寒湿者加散寒祛湿之蚕砂、木瓜,风湿者加祛风胜湿之白鲜皮、地肤子,与三药相合、相须为用而疗湿之相兼之证,体现了从六淫之“湿”论治掌跖脓疱病的理论思想。
2 白术、苍术、薏苡仁
2.1 从脏腑之“脾”论治掌跖脓疱病
《诸病源候论》有:“瘑疮者,由肤腠虚,风湿折于血气,结聚所生”,指出掌跖脓疱病的发生内因,以肤腠虚为主,亦强调外因合而为病[6]。《杂病源流犀烛》有:“湿之为病,内外因固俱有之。其由内因者,则本脾土所化之湿,火盛化为湿热,水盛化为湿邪。”内湿之证,多与脾脏的盛衰有关[7]。杨教授认为掌跖脓疱病的发病源于湿责于脾。湿邪为病,可从外袭,可自内生,皆归于脾[8]。《素问》有“诸湿肿满,皆属于脾”,二者相互影响,湿能伤脾,脾失健运,湿从内生,水湿内困,日久化热成毒,流溢四肢而发。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运化水谷水液,输布精微,灌注经络,荣养肌肉四肢,濡润皮肤。四肢肌肉功能,有赖于脾的运化。脾失健运,生湿化热,酿毒成脓,流窜四末,故掌跖反复出现红斑、丘疹、水疱、脓疱,伴有脱屑、痒痛等临床表现;若运化正常,气血旺盛,充养肌肉,脓消肤华[9]。
2.2 健脾角药白术、苍术、薏苡仁
基于《内经》《难经》的理论基础,张仲景提出了“脾旺不受邪”观点,强调了脾胃在防治疾病中的重要作用。是谓:“水惟畏土,故其制在脾。”[10]杨教授认为掌跖脓疱病虽病在掌跖,但病在内必形于外,脾脏是发病之根,以健脾除湿为法,将白术、苍术、薏苡仁相伍为用。白术,甘温补虚,苦温燥湿,既补气健脾,又燥湿利尿,为健脾补气之要药;苍术,苦温燥湿以祛湿浊,辛香健脾以和脾胃,直达中州,燥湿强脾,用于湿阻中焦,湿邪泛滥之证,尤偏除皮肤腠理之湿;二药相伍,同类相须,白术补中焦而除湿,苍术运脾,除上焦湿而发汗,使脾气健而水湿化。薏苡仁,淡渗甘补,利水消肿,与白术相伍,可渗除脾湿,取参苓白术散之意健脾止泻,与苍术相伍,渗湿健脾,似四妙丸之意祛湿热利筋骨,其性偏凉,又可清热排脓,解毒散结。三药合用,异类相使,除湿宜生用,健脾宜炒用,主入脾胃之经,益气健脾,补中渗利,共疗脾虚湿蕴之疾,以达追本溯源之效。
2.3 健脾角药在掌跖脓疱病中的应用
杨教授常以三药作为角药,审因论治,力求其本。配以厚朴、陈皮,以燥湿运脾,取平胃散之意;伍以茯苓、猪苓,以健脾利水,取五苓散之意;佐以荆芥、防风,以散风舒脾,取风能胜湿之效;辅以通草、滑石以清热利湿,取湿祛热孤之功。故清流者必洁其源,治病者必求其本,体现了从脏腑之“脾”论治掌跖脓疱病的理论思想。
3 蜈蚣、紫草、鬼箭羽
3.1 从传承经验之“毒、瘀”论治掌跖脓疱病
王玉玺教授基于“毒”“瘀”中医理论背景,总结出银屑病的发病与转归,主要体现在“病由毒生”“久病必瘀”,认为“毒”是其发生的先决因素,“瘀”是疾病转归的必然结果,提出了银屑病“毒蕴瘀结”的发病机制,以解毒消源,祛瘀截末为原则,自拟经验方“蜈蚣败毒饮”,广泛用于治疗寻常型银屑病,取得了满意疗效[11]。杨教授在继承王老的学术思想的基础上,不断的发扬与创新,认为本病的发病特点与毒、瘀的致病特点相似,毒邪顽固,反复发作,迁延难愈;怪病多瘀,病久皮损鳞屑肥厚,反复难治。在本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毒瘀是重要的致病因素和病理产物,毒瘀积聚于掌跖,使其深蕴肌腠,胶着难散,蕴久成顽。
3.2 解毒散瘀角药蜈蚣、紫草、鬼箭羽
基于“毒、瘀”理论,将蜈蚣、紫草、鬼箭羽相伍而用,以达解毒散瘀之效。首先善用虫类药物蜈蚣,取其散行走窜入络搜邪之性。蜈蚣,辛温有毒,以毒性之偏,以毒攻毒,性善走窜,行表达里,无所不至,散结通络,《医学衷中参西录》言:“凡气血凝聚之处皆能开之散之。”紫草,甘咸性寒,清热解毒透疹,凉血活血,《药性论》有:“治恶疮、瘑癣。”鬼箭羽,辛苦性寒,主入血分,善破瘀活血,通经解毒消肿。三药相合,异类相使,伍以土茯苓,取蜈蚣败毒饮之意,一则治风毒、散血毒、化瘀毒、除湿毒,体现从毒论治掌跖脓疱病;一则攻毒逐瘀、凉血散瘀、破血化瘀、祛湿通瘀,体现从瘀论治掌跖脓疱病,共达解毒散瘀之功。
3.3 解毒散瘀角药在掌跖脓疱病中的应用
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善用虫类之品,所谓“辄仗蠕动之物,以松动病根”,取其走窜通络之性,引药直捣病所,用其攻毒散结之功,祛除皮肤顽疾[12]。临证多伍以乌梢蛇、全蝎、地龙、蝉衣、僵蚕等入络搜邪之物,用以掌跖脓疱病的治疗。若毒偏重,伍以全蝎,互为对药,攻毒通络散结;若瘀偏重,佐以土鳖虫、水蛭,同为血肉有情之品,活血化瘀通络;若风毒瘀明显,用以蝉蜕、僵蚕、乌梢蛇以祛内外之风,而通络散瘀,解毒止痒;若湿毒瘀明显,投以全蝎、水蛭以祛湿解毒通络散瘀,既体现从毒、瘀论治掌跖脓疱病,又体悟到善用虫类药,其力相得益彰,每每获得奇效。
4 土茯苓、菝葜、乌梅
4.1 从中药研究之现代药理论治掌跖脓疱病
掌跖脓疱病亦称为掌跖脓疱型银屑病,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现普遍认为与细胞免疫关系密切,其发病的主要环节可能与细胞免疫紊乱有关[13]。近年来中医药治疗掌跖脓疱病取得了很大进展,杨教授认为在审因辨治的基础上,可借鉴现代中药药理研究的结果,方可收到更好的临床疗效。
4.2 现代药理角药土茯苓、菝葜、乌梅
土茯苓、菝葜、乌梅三药相伍。土茯苓,甘淡渗利,解毒利湿,使湿从尿出水化,湿祛则热无所依,达湿热分消之效,为化湿利湿之要药,《本草纲目》言:“健脾胃,强筋骨,祛风湿,利关节”,指出其在解毒除湿同时亦可健脾胃,壮中焦之脾土。《本草正》言:“疗痈肿,除周身寒湿、恶疮”,可用于反复发作的疮疡、湿疹等。菝葜,味甘微苦,利湿去浊,祛风除痹,解毒散瘀,《中草药学》言:“解毒祛风,治牛皮癣。”乌梅,味酸而涩,可滋阴解毒生津,《本草求真》言:“入于死肌、恶肉、恶痔则除。”故本品单用可治疗牛皮癣,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有抑菌脱敏,增强免疫的作用,可刺激非特异性游离抗体,中和入侵体内变应原[14]。土茯苓与菝葜皆属百合科植物,土茯苓可选择性地抑制炎症过程,即抑制致敏T淋巴细胞释放淋巴因子以后的炎症过程,因含黄酮类化合物成分,可选择性抑制活化T细胞,形成独特的抑制细胞免疫模式[15];菝葜具有抗炎镇痛,免疫抑制和抗肿瘤的作用[16]。
4.3 现代药理角药在掌跖脓疱病中的应用
在治疗掌跖脓疱病时,强调健脾除湿。土茯苓常作为治疗本病的首选药物,长期服用无明显的不良反应,对胃肠刺激也较小,临证常重用,剂量一般为20~60 g,常与槐花相伍,取土槐饮之意,可清热解毒利湿,又在蜈蚣败毒饮治疗银屑病中起祛湿毒之功,亦有《当代名医临证精华》菝土乌梅汤治疗脓疱性银屑病。其中,土茯苓、菝葜、乌梅作为角药,既注重现代药理,又强调辨证论治,遣方配伍用药,收效颇佳。常配伍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中药如白英、半枝莲、紫草、鬼箭羽、全蝎、蜈蚣等,发挥良好的免疫调节功效,在治疗掌跖脓疱病时,每每用之,收获良效。
5 茯苓皮、陈皮、桑白皮
5.1 从取类比象之“以皮达皮”论治掌跖脓疱病
杨教授在治疗掌跖脓疱病时,重视湿邪致病,强调审因论治,根据“取类比象”之法,巧妙选药配伍应用。《本草求真》有:“为皮者达皮肤。”皮类药物,犹如人体的皮肤,保护卫外[17]。遵“取类比象”之义,多选用皮类药物治疗本病,基于治病求本,选择既针对病机又是皮类的中药用于本病的治疗。
5.2 以皮达皮角药茯苓皮、陈皮、桑白皮
选取茯苓皮、陈皮、桑白皮作为角药。茯苓皮,甘淡性平,专行皮肤水湿,健脾渗湿,利水消肿;陈皮,辛苦性温,辛行苦降,既行气,又燥湿,理气运脾;二药合用增强健脾利湿之功。桑白皮,味甘性寒,肃降肺气,通调水道,《成方便读》言:“肺气清肃,则水自下趋。”三药相伍,异类相使,皆用皮者,因病在皮,故参佐五皮散之治疗思路,首具以皮达皮之意,治疗水湿聚于皮表。脾肺为母子之脏,茯苓皮、陈皮为脾药,可醒脾化湿,达脾旺方能制水,桑白皮为肺药,清降肺气,通调水道,欲取五皮散之意,上下互调,内外同治,一则达降肺气通水道之功,二则能疗肌表皮肤之疾,三则能健脾祛湿以求本。将其作为角药,宜常配伍白鲜皮、牡丹皮既可以皮达皮,又有清热燥湿止痒,凉血不留瘀之功,体现从取类比象之以皮达皮论治掌跖脓疱病。
5.3 以皮达皮角药在掌跖脓疱病中的应用
杨教授在治疗掌跖脓疱病从以皮达皮思想论治的基础上,常选枝条藤蔓类药物,用于引经与通络,以达事半功倍之效。《本草求真》有:“为枝者达四末。”植物的枝条,如同人体的四肢,向外舒展,故选桂枝、桑枝能引药达臂至上肢;《本草便读》有:“凡藤蔓之属,皆可通经入络。”藤类药蔓延缠绕,似人体的经络,纵横交错,故选忍冬藤、夜交藤能疏通经络,通达四肢;又因湿邪在上宜微汗之,桂枝辛温可开腠理宣阳气以发汗解肌,甘温可扶脾阳以助运水;桑枝则性平,善达四肢经络祛风湿;忍冬藤性寒味甘,可清热解毒、通络止痛,善治湿热壅滞下部;夜交藤味甘性平,能补阴养心安神,祛风通络止痒,善于祛风通络;四药常伍而用,一则引经使药直达病所,二则能疗风湿热所致之病。故巧用皮类、枝类、藤类药物,既体现了以皮达皮的理论思想,又注重取类比象的广泛应用。
6 病案举例
患者,女,35岁,2019年9月13日初诊,病史:患者1年前无明显诱因,手足部出现片状红斑,成批出现针尖或针头大的深在水疱,疱液呈脓性,水疱干瘪后有片状鳞屑,病情时轻时重,呈周期性反复发作。伴微痒,脘闷纳呆,大便不成形,小便正常,舌质淡,苔白腻,脉沉涩。西医诊断:掌跖脓疱病。中医诊断:白疕。治法:健脾除湿解毒。处方:炒白术20 g、茯苓20 g、泽泻10 g、猪苓10 g、陈皮15 g、厚朴15 g、苍术15 g、通草10 g、车前子包煎10 g、白英15 g、菝葜15 g、蜈蚣2 条、紫草15 g、鬼箭羽15 g、土茯苓20 g、桂枝15 g,14剂,水煎服,每日1剂,早晚饭后30分钟温服。二诊:患者服药后皮疹有所消退,然手部仍有少量新发脓疱,察其舌脉,舌淡,苔白,脉沉涩。苔腻已化,湿邪有消退之兆,伴有瘙痒,大便成形,饮食尚可,上方增土茯苓至40 g、薏苡仁30 g、忍冬藤30 g,14剂,煎服同前。三诊:患者皮疹大部分消退,无新发脓疱,皮疹不红,皮肤干燥,微痒,舌暗,苔白,脉沉涩。去通草、车前子,加茯苓皮15 g、夜交藤30 g、乌梅15 g,14剂,煎服同前。四诊:仍以此方加减化裁治疗,2月余皮疹完全消退。
按 本例掌跖脓疱患者,脾虚生湿,湿邪内阻,阻滞气机,气血搏结、湿毒凝聚所致,遂以健脾除湿解毒为法,随证加减论治。其辨证要点为掌跖部出现红斑基础上,反复性、周期性发作深在性的水疱、脓疱,伴脘闷纳呆,大便不成形,舌质淡,苔白腻,脉沉涩。方药中体现了五种角药不同的治疗思路:一是茯苓、猪苓、泽泻合用,利水渗湿,兼顾中下焦而不伤正气,体现了从六淫之“湿”论治掌跖脓疱病的思想;二是炒白术、苍术、薏苡仁同用,主入脾胃之品,补脾、运脾、健脾,以达除湿之效,体现了从脏腑之“脾”论治掌跖脓疱病的思路;三是选用蜈蚣、紫草、鬼箭羽联用,解毒散瘀,达蜈蚣败毒饮之功,体现了从“毒、瘀”论治掌跖脓疱病的理念;四是结合现代药理选用土茯苓、菝葜、乌梅;五是注重以皮达皮,选用茯苓皮、陈皮论治掌跖脓疱病的独特想法。考虑病因病机,注重遣方配伍,随证加减,用通草、车前子以助利湿,使湿退而有路;伍以厚朴以理气健脾和胃,配以白英与菝葜合为对药,既具有免疫抑制作用,又可清热解毒利湿,佐以桂枝、忍冬藤、夜交藤,既可引药直达病所,又可通络祛风止痒,诸药相伍,外治湿邪,内疗脾脏,辅以解毒祛瘀之法,达脾健湿祛之功,畅瘀散毒解之效,使脓消疱愈掌跖重复光亮。从治疗过程中,可以体会到应用角药治疗掌跖脓疱病的临床辨治思路,获得良好疗效。
7 结语
掌跖脓疱病形成原因复杂,故在治疗上需要重视其发病因素,从而确定治法。杨素清教授结合多年临床经验,重视病因病机,强调辨证论治,将相关药物配伍应用于掌跖脓疱病的治疗,形成独特的用药特点与配伍风格,所列五组角药均可辨证治疗本病。临床上杨教授常以六淫之“湿”为切入点,将治湿贯穿始终,祛外湿、化内湿以疗其标本;以治脏腑之脾为出发点,以健脾强调治湿,达知外揣内,治病求本之效;基于传承之“毒、瘀”经验,完善其理论;同时结合现代药理,依据取类比象等思想,遣方用药,精准配伍,抓住主证,随证加减,增加疗效。亦可同一处方,多组角药共用,扩大治疗范围,配伍巧妙,治法独到,效如桴鼓。为临床中医药治疗皮肤疾病提供了新的用药理念和配伍形式,而进一步探索角药治疗疾病合理伍用和减毒增效作用值得深入挖掘,以期提高角药在临床应用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