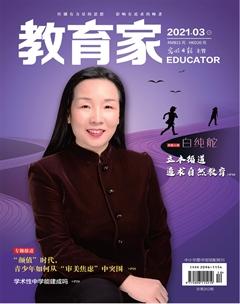互联网如何重塑青少年的审美想象
曹华威
在医美整形方兴未艾的21世纪初,大众媒体便已左右中国人的审美想象。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博士文华在对整容医院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坐在医院等候整容的女性常常翻看《ELLE》《VOGUE》等时尚杂志。杂志上白皙、苗条的明星照片无疑保留着对于“何为美”的解释权。
在这种将自己与明星对照而产生的审美焦虑之下,人们不可避免地通过杂志上的医美整形广告来获得宣泄与救赎。彼时,通过医美整形改造身体尽管并不被大众广泛接受,但在媒体中仍然被诠释为一种自由意志指导下的对于身体的积极改造,即使这种美丽的标准是被高度规训的。
2018年10月5日,“高中某班32人几乎都接受过整形手术”的新闻经由央视财经《第一时间》栏目报道后引发了社会对于青少年审美焦虑的关注。人们曾寄希望于互联网的出现能打破媒体机构的垄断,从而带来更为多元和平等的观念市场。然而如今看来,资本只是进一步放大和极化了审美焦虑。
A4腰、锁骨放硬币、反手摸肚脐……近些年层出不穷的审美新标准显然比从前更为苛刻,从女性到男性,从网红到普通人,从成年人到青少年,借由互联网,这种单向度的审美想象如病毒一般在人群中传递。青少年仍处在价值观不断变化的人生阶段,这既意味着他们更容易受到影响,也意味着他们存在改变的可能。青少年的审美焦虑并不能简单归因为涉世未深,而是一种互联网加速下的时代症候。
作为仪式的自拍
在所有表露青少年审美焦虑的行为中,自拍是最为明显且频繁出现的。自2013年11月18日“自拍”(selfie)被英国牛津大学评为年度热词,到今日,自拍已经从小众的亚文化变为流行的大众文化。但严格来说,自拍技术只是人类自我凝视历史的延续,而非突破。从顾镜自盼到自画像,人们从未放弃通过各种与自我对话的仪式来审视身体,并借此宣示对于身体的自主权。
从 1839 年化学家罗伯特·科尼利厄斯拍出人类第一张自拍开始,自拍便成为摄影技术中极为特殊的存在。不同于传统的摄影,自拍过程中拍摄的主体和客体均为摄影器材的使用者。自拍的出现使得人们可以更为方便地进行自我观看。在此后的一百年里,自拍技术仍然仅仅停留于艺术家进行自我表达的小众亚文化中。然而,随着互联网移动通信设备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被赋予了自拍的权利。
“自拍”(selfie)具有鲜明的社交属性,它最初指向的便是用户通过摄像头拍摄照片并上传到社交博客的行为,无论自拍者承认与否,今天流行的自拍游戏都有着潜在的公共性。换言之,观看自拍照不再是私密的个人行为,而越来越成為公共空间中的展演。根据极光数据研究院的统计,青少年是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自拍的主要群体。除此之外,在修图软件的使用上,55.6% 的用户不到 30 岁。由于“自拍”所附带的社交属性,青少年希冀从自拍中得到的并非真实的自我,而是一个更为美好的形象,或者可以说是更符合他人期待的自我。
如果说早期的自拍技术仍符合福柯对于“自我技术”的定义,即个体可以借由这种技术来构成主体,确认自我的主体性。那么今天流行的自拍技术无疑已经演化为一种新的规训,在这一反复声张自我的仪式中,自我却被远远地驱逐出去,成为被他人凝视的客体,继而引发广泛的焦虑情绪。
在一项针对四所瑞典学校的13岁学生的自拍现象的研究中,学者迈克尔·福斯曼发现:青少年群体的自拍行为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一种自恋行为,而是充满互动性的社交行为。为了获得更多的点赞和更积极的评价,青少年们会让自己更符合主流审美的要求。自拍不再是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反而是审美刻板印象的庸俗回声。
网红的阶层符码
网红,一度被认为是青少年审美焦虑的始作俑者。2017年,新华网一项针对青少年的调查显示,54%的受访者将网红、主播等职业选为理想职业。在整容医美手术和修图技术的合力下,千人一面的网红被大量炮制出来。这一群体的出现既迎合又引导着青少年的审美想象。在传统媒体时代,普通人的生活往往以底层群像的方式出现。随着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形态的涌现,媒体赋权让介于社会名流和普罗大众之间的网红群体,获得了自我展示的空间。
网红群体的出现带给青少年的,不只是单纯局限于外貌和身材的审美焦虑,而是更为广泛的阶层审美焦虑。重要的不是网红,而是网红讲述的故事,是和这些精致面孔出现在同一取景框中的其他景观。青少年与其说是在模仿网红,不如说是试图模仿网红所代表的中产阶层审美。
网红起初作为一个名词出现,而后衍生出形容词词性。网红脸、网红穿搭、网红店、网红景点,通过与其他词汇的联结,“网红”迅速构建出一个指涉庞大而复杂的能指集合,日常生活用语被大量“网红化”。它们共同的所指,则是21世纪以来,在中国一线城市新兴的中产阶层生活方式。
1999年,一本名叫《格调》的译作风靡中国大城市的图书市场。尽管其初衷在于讽刺,却也为中产阶层确认自我身份提供了有效的指南。有趣的是,这本书的英文原名是Class,即阶层。如今的网红群体,是互联网时代无处不在的“格调”。他们将中产阶层审美,简化为一套物质符号和外在编码。
当个人的审美风格和生活趣味成为划分阶层的标尺,网红符号的出现提供了一条捷径——只需要通过对符号的消费及对编码的模仿,就可以扮演一种中产阶层的生活。这对于尚没有工作收入的青少年群体来说,显然具有更为切实可行的吸引力。更为关键的是,当这样的中产阶层审美被资本指认为是有品位、有追求的美好生活范式时,也意味着另类想象的可能性被消除了。当网红审美被追捧为唯一值得践行的审美,青少年便因此不能甚至不敢去想象更为多元的审美。
颜值经济,景观的拜物教
青少年对于自拍和网红的热衷催生了颜值经济,在这种高度依赖互联网的虚拟经济中,“美”被异化为一种标签、一种符号。颜值经济的兴起反映出当代消费文化审美语境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拜物教,正如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所阐释的“偏爱图像而不信实物,偏爱复制本而忽视原稿,偏爱表现而不顾现实,喜欢表象甚于存在”。
根据2017年1月QQ社交指数发布的《年轻洞察白皮书》,“颜值”名列当下年轻人媒介使用习惯的首位。当颜值成为“正义”,个体价值的评价维度就会变得单一。青少年群体正处于最渴望得到承认和肯定的生命阶段,单一的评价体系让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个体不可避免地陷入焦虑。这时,一个声称可以让人变美的行业,一个由品牌和医美技术构成的消费主义符号系统就成了帮助青少年缓解、消除焦虑的新宗教。
然而这种焦虑是无止境的,消费主义的特征就是以提供个性的名义抹除个性。在颜值经济中,更多的欲望被发明,更少的审美被肯定。青少年一旦放弃了对于自我身体和审美的主体性,而甘愿将自己放置在消费主义的评价体系中进行改造,那么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在未来越来越苛刻的审美标准中迷失自我。
青少年的审美焦虑,是互联网时代下的结构性困境,无法寄希望于个体成长后的自然觉醒和突破。因此,在资本轮盘高速运转的今天,教育不能再局限于对于课内知识的学习和运用,更不能为审美设立标准答案。教育工作者除了要发挥好自己守望者的功能,关注消费主义对青少年造成的审美焦虑,更应该扮演好引导者的角色,帮助青少年树立多元审美观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颜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