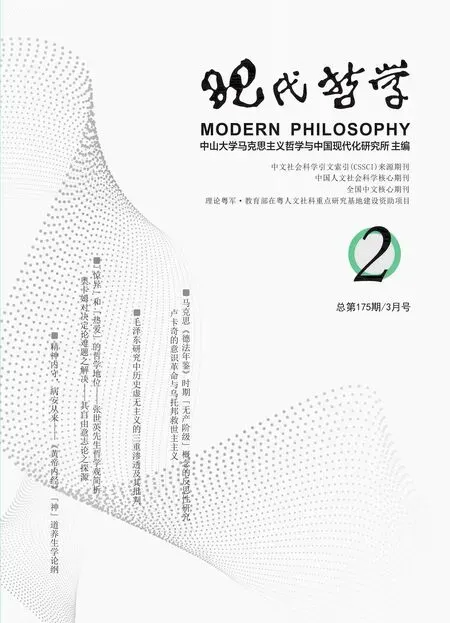汉娜·阿伦特思想的“决断主义批评”之反思
肖 蓉
阿伦特(Hannah Arendt)素来以对纳粹主义的批评而著称。但思想界却存在一种对阿伦特思想极为特别的批评,即“决断主义之批评”(Decisionism Critique)。其特别之处在于,决断主义往往被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阿伦特等人用来批评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等赞许纳粹统治的思想家。然而,乔治·凯特布(George Kateb)、马丁·杰(Martin Jay)、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等人却将“决断主义”的帽子扣向阿伦特。他们突出强调阿伦特思想中行动的绝对开端性,以及对“积极生活”(vita activa)与“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的严格区分。因而,阿伦特思想看上去像是一种生存主义的、审美主义的政治哲学,藐视规范与伦理,强调多元开端的无序与无限制的创造,充满了意志主义的色彩,潜在地蕴含了不受控制的暴力倾向。这种“规范性之缺乏”,正是决断主义思想的典型特征。针对上述批评,玛格丽特·卡诺凡(Margaret Canovan)、达纳·维拉(Dana Villa)等阿伦特思想的支持者则明确拒斥了上述指责,转而强调阿伦特思想中的公共性,包括阿伦特对康德之“反思性判断力”的居有、对“共同行动”的强调以及阿伦特晚年在《精神生活》三部曲中对“意志”的重新理解。
两种解读针锋相对,孰是孰非,莫衷一是。鉴于此,我们认为,阿伦特对于人之行动的捍卫实际上蕴含决断与反-决断主义的双重向度:一方面,批评者们正确地看到了阿伦特强调的多元行动者之意志力量、开端性、自主性,蕴含了强烈的反规范主义、非道德主义色彩,但其理论意图恰恰在于对纳粹极权主义统治下的顺从主义(conformism)的克服,因而是极有必要的;另一方面,阿伦特的前述反规范主义、非道德主义的主张并非(施米特式的)决断主义,这是因为她同时强调多元之行动者是在政治的公共空间中,施展着自身判断力(以及相应的共通感)的共同行动者,因而是一个具备“扩展了的心灵、思维”的行动者。
一、决断主义之批评
(一)决断主义及决断主义之批评
决断主义(Decisionism, Dezisionismus)是一个来自施米特的术语。与规范主义相对立,决断主义认为一切法的终极基础在一个意志过程、一个决断中,而非基于规范。决断创造了法,是处理危急、混乱的紧急状态之时的终止现有秩序的能力,它不受任何规范的束缚,并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绝对的东西(1)参见[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神学》,刘宗坤、吴增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9页。。这意味着就决断之实施而言,“为恢复秩序与和平,主权者在宣布例外状态后,可以违反现行的宪法体系和普通的法律体系”(2)[美]乔治·施瓦布:《例外的挑战:卡尔·施米特的政治思想导论(1921-1936年)》,李培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9页。。
然而这里隐含了巨大的危险,因为决断之为决断,就在于它是绝对的开端,它瓦解庸常的规范与秩序,是对任何形式的公共审议、意见辩论的超越,是一种建基于虚无之上的以自身为根据的奠基行为,因而是主权者绝对权威的体现。在批评者看来,决断主义思想内在地通往专制、独裁统治,恰恰是对个体行动自主性的瓦解。因此,在施米特之后,决断主义一词在洛维特对海德格尔、施米特等人的著名批评中拥有一种贬义色彩,并与纳粹意识形态联系密切。
基于决断主义之批评的立场来看,决断主义者摒弃规范,倡导一种初始的、无根据的、彻底的意志,渴望一个彻底的建基之奇迹般的瞬间时刻,只是纯粹地为了决断而决断,“至于为了什么东西都差不多,因为在他们那里,决断就是政治的特殊本质”(3)[德]卡尔·洛维特:《海德格尔——贫困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在20世纪的地位》,彭超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9页。。这意味着人类行动唯一的根据就是自身的决定、决心,并以这一决定为自身行动之——无根据的——根据。剥离了一切规范性内容之后,无根基的专制决断全无凭依,其“内容只是从当时已有的政治局势的偶然的时运中取得的”(4)同上,第55页。。而缺乏规范的任意决断必然滑向偶然,在向被抛处境的回退中,这种对规范、准则的纯粹蔑视恰恰沦为对既有现实世界的接纳和承认。这样一种偶然的决断主义导向一种对既有传统、历史事实的一味顺从,表面上独断专横的意志沦为可鄙的懦弱。这也解释了那些口口声声要决断的思想家,为何如此快地匍匐于希特勒身前。
(二)对阿伦特思想的决断主义之批评
就决断主义与纳粹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来说,决断主义之批评被翻转为对阿伦特本人思想的批评是令人惊讶的。然而,在批评者看来,阿伦特思想虽不能等同于海德格尔等人,但仍然拥有明显的决断主义倾向。这首先缘于她在哲学方面对海德格尔这样的生存主义者的暗中依赖。马丁·杰认为,尽管阿伦特对海德格尔、施米特、荣格尔等人都有过激烈的批评,但“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恰恰就置身于1920年代的政治生存主义传统中,尽管它是‘柔性的’而非‘强硬的’变体之一”(5)Martin Jay, Permanent Ex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40.。
在批评者看来,阿伦特思想的决断主义色彩,首先便缘于她“试图将政治行动从其他的积极生活的方式中解放出来,并急于确保行动最大的自主权”(6)Ibid., pp. 241-242.。这导致其对自由的强调超出应有的界限,她的自由概念与其说是康德式的“对法则的遵从”,倒不如说是海德格尔式的“自由就是对法则的创造”:行动是出于自我内在的因素,阻断了外在的干扰,因而这种决断不受外在事物的束缚。“就像生存主义者一样,她倾向于相信无限的人类可塑性,很少考虑到历史的限制,即使她有时分享了生存主义者对‘情境’力量的勉强的认同,以确定自由。”(7)Martin Jay, Permanent Ex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 p. 244.阿伦特基于生存主义传统,视历史为对自由限制的非法来源。只有突破传统、历史的权威,才能使行动不被过去所束缚,行动的开放性是政治的生命力所在。因此,“阿伦特虽然远不及决断主义者肯定意志作为政治行动的动力,却分享了决断主义的观念,即摆脱一切外在的考虑来使行动自由”(8)Ibid., p. 242.。这种界限的逾越,最终导致阿伦特思想呈现出反规范主义的色彩,而这也是决断主义——作为规范主义之对立面——的核心特征。阿伦特对行动开端启新的强调,使得其批评者认为如果行动不再运作于一个既有的规范性空间中,它的成败便只能系于自身的“量”之强度,而不再具有“质”的区分(9)参见[美]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周宪等、王志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四章。。
此外,批评者还认为,阿伦特的思想充满盲目的、非理性的意志主义色彩。通过对多元、无端、创造的强调,阿伦特思想蕴含了一种冲破任何束缚的暴力倾向。马丁·杰就直截了当地认为,阿伦特“厌恶整个理性主义传统,她强调无中生有的全新开端的重要性,她信赖那对立于纯粹沉思的行动”(10)Martin Jay, Permanent Ex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 p. 240.。在沃林看来,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一样陷入一种规范之缺失状态,因而通往一种意志主义的主张,“现存的道德定向的唯一根据就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决断,一种对意志的偏激肯定……所以,决断主义就是一种意志主义,它和尼采的‘强力意志’理想如出一辙”(11)[美]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第55页,译文有改动。。
这种批评凸显了阿伦特行动概念所具有的内在张力,一方面阿伦特严格区分行动与暴力,另一方面阿伦特又强调行动的开端特征。“为了给自己的行动以空间,它必须排除或毁灭已经存在的事物,必须改变事物固有的样子。”(12)[美]汉娜·阿伦特:《共和国的危机》,郑辟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4页。马丁·杰据此批评道:“这种亲和力使得她对暴力和政治之间的区分浑浑噩噩。”(13)Martin Jay, Permanent Ex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 p. 249.阿伦特对于行动的开端能力的强调以及对于生存主义的颂扬,有可能导致其理论也滑向暴力。
基于批评者的视角,如果阿伦特思想确实蕴含决断主义倾向,虚无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的色彩将使阿伦特思想的反极权主义力量大打折扣。在无规范的行动中,多元行动者在释放自身的独特差异性之际将陷入无穷无尽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
二、对规范的反思性态度
鉴于前述批评,我们首先要承认的是阿伦特思想确实彰显了行动的决断性,但其思想中的这种决断性因素对于她的使命——把人从纳粹极权主义式的全面统治中拯救出来——而言是必要的。阿伦特的行动伴随着多元个体之间的权力以及人们相互之间承诺所具有的约束性(14)参见肖蓉:《论阿伦特的“多元性”之思及其困境的克服》,《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因而与决断主义所具有的任意性、专断性不同。一个真正的多元行动者,既不是一个完全拒斥所有规范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彻底谨守各种既有规范的顺从主义者,而是一个有所反思的思想者。
(一)齐一性的克服
卡尔维瓦(Andreas Kalyvas)说:“施米特的决断概念与阿伦特的行动概念是一种主题的两种变体。”(15)Andreas Kalyvas, “From the Act to the Decision: Hannah Arendt and the Question of Decisionism”, Political Theory, 32(3), 2004, p. 322.施米特式的主权决断是一种绝对的开始,它既包含了创造的意义,又隐含着不稳定、任意性和不确定性的危险(16)See ibid., p. 323.。而在阿伦特这里,“去行动,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意味着去创新、去开始……某个新的东西出现了,它完全不能从以前发生的事情中预测出来,这就是开端的本质”(17)[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因此,对阿伦特思想的决断主义之解读,以一种近乎“夸张”的方式凸显了人之行动所具备的开端启新之维度。如果我们想要理解阿伦特思想中的这种夸张的“决断”色彩何以是必要的,就必须理解阿伦特行动之思所针对的是什么。
首先,阿伦特的思想旨在克服以纳粹统治为代表的极权主义对多元行动者的绞杀。其次,阿伦特之思所针对的绝不仅仅是那样一个已然覆灭的纳粹政权,而是更广泛地涉及现代文明中的资本化、技术化统治所蕴含的“全面统治”因素。维拉生动地刻画了阿伦特眼中的人之境况:“随着社会存在的越来越多的领域臣服于工具理性的支配和理性监管的特权,留给行使公民权的空间逐渐消失。自由、自主的启蒙理想,以及理性的民主政治秩序……实际上已经消失。”(18)Dana R. Villa, Arendt and Heidegger: The Fate of the Politic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顺从主义的个体在一种来路不明的规范性——世界——中生存,依据一些固有的判断执行机械的计算,在其中奔忙着的个体都在一种经济学式的算计下沦为只有效益性的、可替代的、匿名的人力资源,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无人统治”(no-man rule)的状态。
在阿伦特看来,顺从主义蕴含了社会性的削平一切的要求,也就是说,“社会总是要求它的成员像一个大家庭内的成员一样行动,只有一种意见、一种利益”(19)[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第25页。。在现代社会中,传统专制社会由君主、氏族首领一人自上而下的统治模式被转换为一种“无人统治”,这种无人统治就像海德格尔所刻画的“常人”之专制一样,将其治下的每个独一个体都磨平为匿名的螺丝钉,成为整个巨大无人统治的、仿佛自动运行的机器中的一个环节。这种“无人统治并不必然意味着无统治,在某些情形下,它甚至会演变为最残酷最专制的形式之一”(20)同上,第26页。。所有个体——包括统治者自己——从出生伊始,便被纳入整个社会的规训、塑造与监控的体系之中,不断地成长为合格的、正常的“社会人”。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塑造机器面前,任何逾制者都成为反常者。阿伦特认为这种无人统治的现状植根于人的本性:人都倾向于抹平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异性,而使自己尽可能地以符合物种本身的特征来生活,但这种物种性的发展,却是对人的尊严的扼杀。
鉴于上述全面统治对行动者的压制,阿伦特的政治之思显现出与规范主义明显的紧张。这首先便体现在她对行动之意志力量的褒扬:真正的多元行动者是依靠其意志力量克服自身向齐一的全面统治的沉陷。卡尔维瓦认为,其行动的自发性首先是与意志联系在一起的,意志作为一种由内而外的力量,从自我出发来对外在的世界发生作用,它能够超越当下的限制,具备塑造未来的能力;就意志自身的特性来看,一方面是任意的选择,另一方面却是新的开始,它既是个性化的力量(意志使得个体区别于其它人,它创造了自我的特征),又是个性行动表现美德的能力,决定了他们想要成为谁以及怎样揭示自己(21)See Andreas Kalyvas, “From the Act to the Decision: Hannah Arendt and the Question of Decisionism”, Political Theory, pp. 334-336.。
因而,阿伦特思想中的决断色彩主要来自对规范的反思,她反对公民成为政治共同体的盲目顺从主义者。对全面统治的既有规范的遵奉,是摒弃个体思想能力的表现,是造成政治上灾难的重要原因,也是缺乏政治判断能力的表现。据此,阿伦特对于规范的消极结果的反思,最终诉诸于人的行动能力以及人所具有的意志。行动的生产性能力以及它的无限性才能为真正的政治生活留下空间(22)参见[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第150页。。阿伦特思想的决断因素,实际上是强调人之行动的开端性与创造新事物的潜能。
(二)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反思
对齐一性统治的反思通往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反思,似乎使得阿伦特沦为一个“道德虚无主义者”。批评者认为,阿伦特思想中的决断因素挑战着现有的规范秩序。但一个共同体的优越性只能体现在遵从规范吗?阿伦特说:“希特勒政权时代受尊敬阶层的那种全面道德崩溃也许会使我们明白,在这种境况下,那些珍惜价值并坚持道德规范和标准的人们是不可靠的。”(23)[美]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陈联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9页。沉陷极权统治中的个体,将对外在社会规范的遵奉视为自身良知的使命,其所遭遇的各种突发境况都不通过内在的审查来加以检验,并运用社会既有规范来事先指导个体行动,在整个过程中,个体不需要真实的思考,其对外在规范的遵奉也是完全无疑问、非反思的。就像处在一场全民性的群体性运动中,对某些特定群体的加害,恰恰是社会规范所认可甚至提倡的,而置身其间的加害者在实施加害活动过程中,也不是反思性地、主动地接纳这种社会规范,而恰恰就是“不知不觉”地裹挟其中。因此,一旦整个社会规范由于外在事件而发生急转弯的时候,先前的那些疯狂的加害者也能毫不困难地接受一种新的社会规范,而展开对之前所信赖的规范的“批判”和“反思”。这种形式的“忏悔”之便捷,正是真正令阿伦特感到震撼和恐怖的事实。无论是加害者被裹挟的加害,还是事后的忏悔,都只不过是一种顺从主义的实行,传统上的“良知”观念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个不光彩的角色(24)阿伦特的这一思想与海德格尔关系密切,参见汪隐峰:《“见证”的双重意义——论海德格尔的“见证”之思》,《现代哲学》2018年第2期。。
彼得布里奇(Danielle Petherbridge)认为:“阿伦特旨在捍卫一个沉思或批判性反思的空间,在其中,主体能够从‘黑暗时代’的公众意见和判断的不可靠性中批判性地分离出来。”(25)Danielle Petherbridge, “Between Thinking and Action: Arendt on Conscience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42(10), 2016, p. 975.人需要这种自我质询、自我对话的能力。在道德全面崩溃的纳粹时代,那些所谓的顺从的、有道德、有教养的阶层是靠不住的。“在这种境况下,可靠得多的则是那些怀疑者……因为他们习惯检审事物并且自己作出决定。”(26)[美]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第69页。与那些“正派体面”的纳粹合作者相反,“那些不参与者的判断标准与此不同:他们自问,在已犯下某种罪行之后,在何种程度上仍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他们拒绝杀人,并不因为他们仍坚持‘你不得杀人’这一戒条,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与一个杀人犯——他们自己——共存”(27)同上,第69页。。这要求一个人应该具备沉思内省的能力来应对外界的事务。在阿伦特这里,“思想——因而孤独——的重要性在于中断了使意识形态得以压倒思想的齐一性、确定性与信心”(28)Roger Berkowitz, “Solitude and the Activity of Thinking”, ed. by Roger Berkowitz, Jeffrey Katz, and Thomas Keenan, Thinking in Dark Times: Hannah Arendt on Ethics and Politic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41.。与之相反,艾希曼等人的危险之处在于“他未经思考地径直冲入政治或行动中”(29)Danielle Petherbridge, “Between Thinking and Action: Arendt on Conscience and Civil Disobedience”,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p. 974.。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阿伦特误解为一个道德虚无主义者,在她的视域中,道德主义意味着对道德的遵从,亦即共同体中的成员随波逐流地遵循既定的规范,而不去思考在此规范下的行动之合理性。她对道德的批判实际上是呼唤每一个个体去思考自身的行为,从那些不合理的规范中逾越出来,并希望人们尝试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修正彼此的意见。
三、决断主义的克服
正如上节所说,阿伦特思想确有强烈的决断之主张,但这绝不意味着她就是一个典型的决断主义者。在阿伦特看来,行动者的行动并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全然无规范的,而是行动者与共同行动的他人一道表达着自身的判断;在共同体中扩展着自身的多元个体所构建起的世界是一个共同显现的政治空间。阿伦特正是通过诉诸人的共同行动与人的判断力,来应对决断主义的危险。
(一)共同行动
决断主义批评片面地强调了阿伦特行动概念的“无端”“无根据”的特征,并试图将其阐释为对某种神秘的、封闭的自我的表达。然而,这种“表现主义”式的解读是错误的。阿伦特认为,行动除了是行动者自身的表达之外,更重要是交流能力(30)Maurizio Passerin d’entrèves, “Freedom, Plurality, Solidarity: Hannah Arendt’s Theory of Action”,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15(4), 1989, p. 330.:多元的行动者不仅在行动中展现出自身异于他人的“什么”,而且在其行动中蕴含了交流、沟通的维度。
这首先表现在阿伦特行动概念所蕴含的言说式的交往维度。哈贝马斯认为,阿伦特的行动概念是一种典型的交往行为。他首先区分了两种行为模式:一种是马克斯·韦伯的目的论行动模式,以个体的目的作为自己的出发点,通过合适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最终达到对于他人意志的左右以及对于他人行动的支配;另一种就是阿伦特式的交往行为模式,行动的目的不在于支配他人的意志,而是在交往过程中与他人达成协议以形成一个共同的意志(31)参见江天骥主编:《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5—156页。。在此交往行动中,每个个体都可以表达自身的诉求,所达成的共识包含着每个个体的利益。并且,在平等沟通与意见交换中,我们能够通过公共审议以及自身判断来发现某种主张的合理性,这种共识不以个体成功或目的为转移,因而这种主体间关系的建立并不具有强制性,共识的达成是对于自由的一种相互的应允。诚如维拉所说:“阿伦特的理论不是将自由等同于个体生活方式的选择,而是视为为了共同体而‘共同行动’。”(32)Dana R. Villa, Arendt and Heidegger: The Fate of the Political, p. 7.
与阿伦特的这种注重交往、言说、公共维度的行动概念相比,那些典型的决断主义者近乎夸张地强调行动的独断专行的本质,为了表明主权者绝对的权威,它无需公共审议与对话,也无需任何外在的根据,因而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萧高彦认为,“同样在生存主义的脉络中,阿伦特透过他者、世界性、协同一致的开端启新等,尝试克服决断论所带来的任意专断色彩”;所以就阿伦特的立场来看,“她和施米特的隐蔽对话,终极地看来,乃是尝试以共和式的多元主义来对抗民族主义以及主权国家单一性的政治权力观”(33)萧高彦:《西方共和主义思想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21页。。
(二)从意志到判断
在决断主义批评者看来,阿伦特主张行动者不需要依赖任何规范,完全依从自身的原则来意求某物或者做出选择,并由此堕入无可救药的任意性之中。然而,阿伦特自己清楚地看到个体意志能力中所蕴含的悖谬之处:如果说意志是绝对的开端能力,那么它究竟开启哪一个全新筹划似乎是完全任意的,也就是说它最终选择了A而非B完全是无理由的。如果有理由,就又受制于其他能力(例如理性能力);若是那样,意志就不再能够成为一种单独的能力,所谓意志自由也是可疑的。为了克服这种悖谬,我们就必须从全新的视角重新理解意志观念。诚如扬-布鲁尔所说,“当阿伦特开始写《心灵生活》的‘意志’部分时,她想在众多文献中寻找一个将意志构想为非独断、非指挥式能力的典范”(34)[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陈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88页。,这最终构成了从意志到判断的道路。
阿伦特对判断力的重视,与其对康德《判断力批判》的疏解无法分开。判断力所处理的是具有差异性的特殊对象,因而不能把判断的对象划归到一般性范畴之下(35)参见[美]汉娜·阿伦特:《康德政治哲学讲稿》,罗纳德·贝纳尔编,曹明、苏婉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5页。。在康德那里,从自然经验的特殊对象之所以能够反思到某种普遍性,乃是源于主体自身的“共通感”(36)参见[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14、74—77页。。在阿伦特看来,“‘判断’是心灵生活真正的政治活动”(37)[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第502页。,其原因可以从下述三个层面来刻画。
首先,类似于康德的反思性判断力,政治行动不应该预设某种僵硬的、普遍适用的原理或法则,行动者需在行动的过程中向着判断的形成开放自身。阿伦特认为,我们在判断中超出纯粹的特殊之物,将其视为某一普遍者——如公正、善、美——的例示,藉此超出纯粹的主观品味。这是一种“范例的有效性”(exemplary validity)。在反思判断的过程中,我们既保留了具体对象的特殊性,又使得这种特殊性在交流之中得到审视,从而可以逐步上升为普遍,因而反思判断仍然有通往正义的可能。行动并不是凭借自身意志的任意妄为,而是在与他人的交往活动中慎思谨行,行动之前的判断对于政治生活的意义不言而喻。判断中所蕴含的公共审议维度,使得公共决策中包含了不同人之立场。可以说,判断力与思想、意志都不同,它缺乏后两者的绝对性,而总是向着共同体和未来的修正开放自身。正是因为阿伦特思想体系中对于判断思想的引入,从而避免其滑入决断主义。
其次,判断与共通感(sensus communis)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判断虽然是处理特殊性的问题,但其并不是纯粹主观的,因为判断是可以与他人交流的。判断绝不是个体的孤芳自赏,而是诉诸于共通感,这避免了判断陷于一种虚无主义式的相对主义。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提出三条思维的准则:“1. 自己思维;2. 在每个别人的地位上思维;3. 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地思维。”(38)[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36页。其中第二条即用以刻画行动者所具备的共通感。阿伦特认为,共通感指的是“一种附加的感觉,这种附加的感觉把我们置于并让我们适于某个共同体”(39)[美]汉娜·阿伦特:《康德政治哲学讲稿》,第106页。。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次来理解:(1)藉共通感,行动者走出封闭的自身而与他人相关,能够站在他人的位置上来思考;(2)共通感不仅达及他人,而且还在诸多行动者中具有一种主体间的普遍性维度。
最后,共通感要素的引入,使得行动者具备一种“扩展的(erweitert)思维”(40)[德]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37页。。在阿伦特这里,判断中的多元行动者通过“站在他人的立场”来思考,而使自己超出狭隘的个体之唯我论,成为一个可与他人交换意见的扩展的心灵。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阿伦特思想因其对齐一性的全面统治之拒斥,而确有决断性的色彩,但又因其强调行动概念所具有的交往-言说性以及行动者的判断能力,而不至于彻底滑向决断主义。对阿伦特思想的决断主义之批评的澄清,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阿伦特思想中所蕴含的“行动、意志、差异、私人性……”与“言说、判断、平等、公共性……”之间的张力,在阿伦特思想中,这组对子中的每一对都不是(如决断主义之批评者所想象得那样)完全对立的,而恰恰是在一个共同显现的政治空间里相互奠基的。进而言之,对阿伦特思想与决断主义之绞缠的考察,使我们有可能越出阿伦特思想本身的畿域,去思考自由与规范、个体与共同体、多元性与整体性、私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对立”,从而为我们的实践哲学之思考提供一个独特的窗口:在一个日趋强调个体自由、私人空间、本真主张的时代里,我们还能否合理地在普遍性、规范性的维度上思考人类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