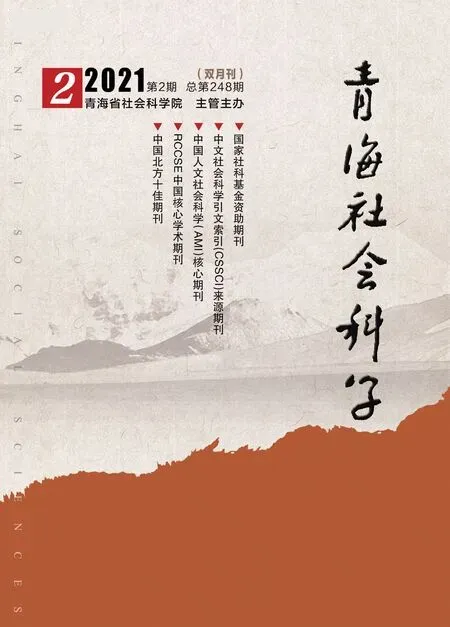乡村振兴背景下高原农业转型与小农户发展研究
◇王希隆 明占秀
由于历史文化和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乡村发展更是“短板中的短板”。而农业的转型发展对于西北民族地区来说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意义,农业转型构成了乡村发展最核心的线索,也是西北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根基与先导。由是观之,对我国西北民族地区乡村发展特点与规律展开基于农业转型的深入科学研究应成为新时期乡村研究的重点。
小农户是小规模经营群体[1],是“在特定资源禀赋下以家庭为单位、集生产与消费于一体的农业微观主体”[2]。结合恩格斯对“小农”定义的分析,“小农户”的上限是由家庭劳动力利用的最大化程度所决定,下限是由维持家庭基本生存需要所决定[3],体现出“小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属性。根据政府部门测算,土地在50亩以下的弹性区间内均可被称为“小农户”,而“我国目前有2.6亿农户,6亿多人生活在农村,其中2.3亿户是承包农户”[4]。尽管这一数字在不断减少,但各地农业资源禀赋条件差异很大,尤其是高原地区山地陡且零散,短时间内难以实行规模化经营。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仍将是我国乡村振兴进程中农业生产经营的重要发展方式。
由此,本文结合笔者近期在西北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选取T藏族自治县(以下简称T县)作为高原农业发展的典型地区,通过不同的农业发展案例来呈现西北民族地区的农业形态变迁,认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转型发展并不仅仅要按照发展主义或现代化预设的发展模式进行,而应以中国传统农业发展中沉淀的小农户自身的乡土逻辑为基础,打破传统模式与现代路径的二元对立,逐步推进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发展,才能够真正实现以农民为主体的内源式的乡村发展,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
一、变迁中的高原农业形态:基于T县的田野调查
在西北民族地区除了传统的小农农业之外,可以看到一些发展变迁中的农业形态。按照范德普勒格对世界农业趋势与模式的分类,[5]这些农业形态既包含了工业化的企业农业,也包含了“再小农化”的产业趋势,更有面向“农村发展”的多元化产业。这些农业形态既根植于“小农户”发展,又在市场经济中充满现代性特点,同时也在塑造着新型的小农户发展模式。西北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也正是在这多样的农业转型推动下展现出丰富的未来发展空间。T县位于河西走廊东端,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在2040~4874米之间,以山地为主;气候以乌鞘岭为界,岭南属大陆性高原季风气候,岭北属温带大陆性半干旱气候,年均气温-8~4℃,气温垂直分布明显,小区域气候复杂多变,常有干旱、冰雹、洪涝、霜冻、风雪等自然灾害发生。T县农村历来以种植、养殖和务工作为家庭生计的主要来源,而高海拔和复杂多变的气候使得种养业具有较高的不可控性,“靠天吃饭”是当地农村的常态。近年来随着国家扶贫开发和农业现代化项目的普及,T县种养为主的传统农业依托高原生态特质逐渐转型,形成了以小农户主导的高原果蔬特色产业、企业主导的食用菌产业和乡村多种要素聚合的发展型农业等形态。
(一)高原特色产业:政府扶持与小农户主导
T县的冬季温室果蔬产业可谓是西北民族地区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化的代表。该地虽然海拔高、温差大、无霜期短、降水量少,但充足的灌溉水源为发展反季节温室果蔬产业创造了条件。近十多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T县建起了高原反季节果蔬温室9000多座300多万平方米,总产值1.5亿多元。日光温室反季节果蔬已成为该县农业发展的支柱产业。仅西葫芦种植就达到3500多座温室大棚,面积超过2100亩,严冬季节日产量最低也在140吨以上,随着气温升高和日照延长,产量会不断上升,最高时日产量将接近300吨。回顾十多年来T县反季节温室西葫芦产业的发展历程,发现其是以小农户家庭经营为主导的,在多年的产业发展中,小农经营根基性作用的坚守、对菜农利益的保护都构成了T县蔬菜产业健康良性发展的基础,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动力和活力。
案例1:
A村是T县较早种植反季温室西葫芦的地区。可以说,该地西葫芦产业发展与脱贫致富密切联系在一起。2006年前后,长期贫困的A村人在政府的带动和扶持下,选取较平坦的耕地建造了第一批温棚,共60多座。每座棚占地约0.6亩,引水入棚灌溉。带头种植西葫芦的家庭棚均收入在初期便达到1万元以上。之后,政府继续投资建起300多座温棚扩大种植面积。良种的培育优选与滴灌技术的引进不仅使温棚收入持续增加,而且使劳动力投入越来越少。户均2座温棚,从当年9月种植至次年5月结束,投入两个劳动力便可以挣4万多元。西葫芦性耐寒,5~25℃之间可正常生长,因T县气候寒冷,冬季最低温常常在零下20℃以下。严冬来临时,温棚仅用塑料膜覆盖是无法御寒的,而使用草帘子人工覆盖费时又费力,因此2017年A村在政府的补贴下引进了卷帘机,利用机械化完成温室覆盖工作。一座60米长的温棚卷帘机政府补贴5000元,其余2000元左右由农户自己担负。种植至今,因可观的利润,菜农便利用自家所有的平地和坡度较小的山地建起温棚,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以前举家外出打工的刘某也回来利用自家耕地建起了3座温室蔬菜棚,年收入在六七万元左右,用他的话来说,“背井离乡出去打工,一年下来,挣的几个钱全部耗在生活上了,现在政策这么好,还不如回来种棚。”①2020年8月28日访谈资料。
2016年,T县S镇实行棚户区改造,仅X村和Y村在城镇化建设的支持下统筹各项资金改造民居160余院。此地棚户区改造采取货币化安置与房屋安置两种模式。货币化安置是将农村房屋估价以货币方式给农户给予补偿后拆除原住房。住房安置则采取农户平房与政府新建楼房置换的方式,按砖混结构1:0.8、砖木结构1:0.7、土木结构1:0.6来兑换楼房,面积不足者由农户按2200元/平方米补齐,多余者则可卖给不足者。在原Y村宅基地建起6栋楼房,可容纳160余户。自2019年8月交房至今,已有80%的农户入住。A村棚户区与S镇街道相连,水、电、暖、路、学校、卫生等基础设施一应俱有。为了农户种植需求,政府允许在自家大棚附近可修建15平方米的房子,用来置放农具等,满足了乡村城镇化的过渡性需求。X村村民杨某说:“以前我们种那么多地,累死累活一年下来就只能维持生计。现在好了,种了蔬菜大棚,钱袋子鼓了,谁能想到我们这辈子还能住上楼房,这都是政策的好处啊。我装修都花了十多万元,要不是蔬菜大棚的收入,连房子都装修不起来。我给娃娃们经常说呢,这么好的社会主要还是要靠劳动,靠双手去挣钱。以前一到冬天,大家围着火炉烤呢,一个冬天就闲闲待在家里。现在无论有多冷,村民们都冒着严寒在大棚干活,虽然辛苦但心里开心呀。”①2020年8月30日访谈资料。
从种植反季节温室蔬菜的案例可以看出,T县突破粗放型的以扩展土地外在规模增加收入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利用冬季温室大棚种植反季节蔬菜,改变了片山片洼种植庄稼还难以维持生计的现状,增加了家庭经济收入,降低了小农户生存风险,实现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有效保护了草原,体现了就地脱贫致富的内生过程,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农业转型的重要模式。
(二)企业农业:资本下乡与“小农化”趋势
在西北民族地区开展乡村调查,也存在这样的事实:一个位于高原地区乡村的某农业企业经营的农作物基地生产的是专门供给外地的蔬菜,而该农作物基地的投资者则包括了来自浙江、福建、广东等东部地区的企业家,蔬菜基地的工人有当地的各民族农民也有来自外地的农民工。产业园基地管理工作通常由来自贵州等地的农民工担任,而短期临时的加工包装等工作则多由本地人担任。这是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农业的常态,它是由政府、企业和小农户共同运作的跨地区的农业形态。T县依托高寒冷凉山区优势资源禀赋,积极培育食用菌产业,建成了滑子菇、香菇、海鲜菇、羊肚菌、秀珍菇、金针菇等众多食用菌类产业园,被誉为“中国高原食用菌之乡”。
案例2:
在S镇D村坐落着由T县N农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优质香菇栽培科技示范基地,主要种植和销售以香菇为主的赤松茸、金耳、滑子菇、羊肚菌等食用菌类。目前香菇种植技术十分成熟且已大面积种植。据统计,仅D村种植香菇的温室大棚就有400多座。S镇地处三大高原交界处,年均气温在3.5℃左右,4—9月自然平均温度在12℃左右,此阶段的冷凉气候非常适宜香菇等中低温型食用菌的生长,使香菇具有极好的饱满度,生产期从4月至11月,病虫害很少。有专家评价:T县是我国发展中低温型食用菌品种的适宜气候区,品质非常好。这些香菇主要运往兰州、西安、成都、新疆、广东等市场,年产达到1000吨左右。
这片食用菌种植基地的诞生是资本下乡的产物,也是国家扶贫开发和农业现代化项目规划的产物。N农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其老板早在2000年就开始在青海、甘肃等地探索食用菌的种植方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本,现今在S镇形成香菇的规模化种植。2014年,S镇作为T县生态移民的安置区,建立了近800多户的移民村。在生态移民安置项目中,来自T县8个乡镇的生态移民搬入了政府统一规划建设的移民村,并给予移民每家两个温室大棚的生计安置。N农业公司即通过当地政府的招商引资流转农户土地建立产业园来培育食用菌菌棒,依托小农户一家一户单独经营来发展订单农业。每户经营1~2个菌棚,管理出菇和采摘工作,采摘后送到指定地点,由企业统一收购,高峰期每天采摘100公斤左右,收购价格一般在4~8元/公斤。一年出菇时间约为7个月,棚均收入在2.5万元以上,政府再补贴1000元。企业投资引进了食用菌类烘干技术,建设了1200平方米的冷库。香菇采摘后按需求一部分进入冷库并全程冷链销售,另一部分即时烘干并进行简单包装。产业园区每天需要30人左右的临时工,全部来自附近的移民村。香菇简单加工并加以包装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烘干之前的剪脚工作需要大量人工。剪脚劳工领取计件制工资,每筐框40斤左右的香菇计价5元,手脚麻利的工人半天可挣80元左右,手脚稍慢的老年人或残疾人可挣40元左右。
在香菇的案例中,看到的是一个由资本投入、种子技术、出菇管理、冷链物流(或烘干技术)、租赁土地、政府补贴所构成的以小农户家庭经营为主导的农业企业典范。农业企业面向市场、依赖市场,按照订单+保单模式,把移民村“嵌入”产业链,就企业来说,借用移民村的地理和劳动力之便解决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难的问题;就小农户来说,家庭经营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还学会了种植技术,忙碌之余可在产业园区赚取工资,体现了现代化农业中的“小农化”趋势,真正实现了资本下乡带动老乡的发展。
农业的多功能化是农业发展的新趋势。在传统的生产性种植业和养殖业之外,一些“非生产性”农业活动也发展起来,比如景观管理、能源生产、农业旅游等,这些是农业生产的附产品。农业是以一个多元农村发展活动有机构成的“共存体系”,与企业农业高度的专门化不同,这样的“农村发展型”农业更为多元化、地方化,将农业中的自然、社会和作为生产者和行动者的人的利益与愿景连接在一起[5]。通过藜麦产业的发展,扶持开办农家乐、藏家乐、牧家乐及农家客栈,推进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有机结合,积极发展景观农业,建成观光、体验、餐饮、住宿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在保障小农户利益的情况下,提升了在地生活的品质,推动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道义与理性并存:小农户发展的乡土逻辑
现代化浪潮推动下市场经济有偿服务的渗入和资本力量在农村的显现,促使资本、市场与村民生活之间发生越来越紧密的关系,旧有的人情味浓厚的社会交往关系逐渐被资本和商品的理性逻辑所代替。在西北民族地区,虽然资本与商品的逻辑也冲击着乡村社会的传统互助及其形式,使得小农户家庭向经济理性化发展,但传统逻辑并没有完全消失,也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形成了道义与理性并存的小农户发展逻辑。
(一)变工与帮工
基于过去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农民自身随时都可能面临着的生存风险,小农户之间常常以人力、畜力、农具等变工和帮工,这是农民相互调剂劳动力的方法,一种集体主义的互助行为。相互变工的互助方式最近可以追溯到农业变工组,起初是几家在一起变工种地,后来衍生到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互助行为也体现在西北民族地区的乡村现代生活中。如以小农户家庭种植高原夏菜为例,种植和收购采摘环节需要集中人力去完成。通常这个时候,农民很少去雇工,而是与村上其他村民进行变工来完成,一是村里种植蔬菜的农户都比较熟悉这些流程,干活效率高;二是雇工需要花钱,而变工就用自己的劳动力去还,节省了雇工钱,降低了成本。较之于变工,帮工既暗含了潜在的变工之意,是出于小农户自身随时都可能面临着的生存危险而提前投入的劳动力储蓄,期望在自己需要时能够换回别人的劳动力;也指对有困难的人的无偿和自愿的劳动帮忙。
案例3:
2019年8月,王某因出车祸腰椎断裂,原本依靠种植蔬菜大棚获得收入来供两个子女上大学的夫妻,因妻子需要照顾丈夫王某而无法种棚,这样一来几乎断绝了整个家庭的生计和孩子的学费来源。9月正值大棚种植时期,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村民马某等人一面种植自己的大棚,一面不请自来为王家种植。马某等人是自愿义务来做的,他们知道王家没钱付给他们,但他们认为邻里乡亲应该这样做。他们认为乡亲有重大困难,自己应当出手相助,这就是一种“道义”。
无论是变工还是帮工,事实上就是将自身劳动力投资或潜在地转换成内含情感的“雇工”价值。变工有时候是不对等的,比如张家10亩地的娃娃菜收购需要两天,而李家5亩地只需要一天,就等于“一天变了两天的工”,小农户之间是不会收取多出来这一天的工钱的。因此小农户之间的变工与帮工逻辑是基于互惠和道义的原则。即使农业转型能够降低这种风险,然而传统的生计惯性已深深根植于小农户的观念中,他们追求避免风险和安全第一的基本生存目标。正如斯科特所说,小农就像相互之间牵着手过河的人,相互依靠,互惠互助,为生存而共同抵御风险。这种互助行为亦被置于家庭伦理责任基础上,属于良心、责任的范畴。
(二)家庭生计结构的自觉强化
与传统农业不同的是,以种植果蔬为主的转型农业不仅具有较强的季节性,而且在劳动力和时间的需求上具有很强的聚合性,相应地就会有间歇性的分散时间,这成为小农户家庭生计结构强化的前提。如以移民村D村的生计方式来看,小农户家庭每天只需要1个人两小时的时间便可完成当日的香菇采摘工作,待交购以后便有闲置时间在产业园区做活。园区在时间上管理松散,农户只要闲着便可以做工。笔者调研正值暑假,许多爷爷奶奶就带着孙子过来挣钱,大人们忙忙碌碌,小孩们开开心心,真是一番热闹的景象。宋爷爷说:“假期么,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就带着孙子过来,赚一点是一点,一天能赚个自己的生活费或家里的水电费也是可以的。”又如以种植冬季日光温室蔬菜为家庭主要产业的小农户,除个别工作需要多人合作完成以外,由一个劳动力负责一个温室大棚的采果、施肥、浇水、卷帘等主要工作即可。有些家户一个人管理2~3个大棚,在时间安排上就显得比较紧密,早上5~9点采果、9~10点卷帘,不到12点可完成所有工作,回家后还可以做家务、照顾孩子,直到下午四五点盖上大棚即可。而家中其他人则可以通过做小工来增加家庭收入,如到了夏季,正值工程开工,可以去工厂或工地上班。家庭生计结构得以强化,保证了家庭经济的连续性。
转型农业生产因较强聚合劳动时间的特征和小农户家庭经营具有高度责任感、自觉性、主动性和灵活性的特质而自觉强化了家庭生计结构。正如舒尔茨所说,小农是一个在权衡长短期利益之后,会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合理抉择生产的理性经济人,能够在自身特定约束条件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6]正是这种理性选择,小农户能够在家庭内部实现时间的最优化安排和劳动力的最大化使用。因此在对家庭劳动力的合理权衡之上会决定以何种生计方式为主导,并根据家庭人口和劳动力的变化随时调整。这种灵活的小农户理性发展模式强化着整个农户家庭生计的可持续性,保障了农户家庭职能的正常运作。也因此,很多家庭都形成了以某种产业为主导的复合型产业发展模式,主要有种植-务工、养殖-务工、种植-养殖等模式,也形成了不计价自身劳动力无限制投入劳作的生计习惯。如此,家庭主业和副业之间便相互支撑,主导产业维持着整个家庭的运转,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副业作为家庭经济的补充,能在一定程度上辅助家庭发展。
案例4:
李女士,今年55岁,小学文化,家里现有5人(她和丈夫、儿子、儿媳、孙子,孙子已上幼儿园)。她家有两个日光温室蔬菜大棚,主要由老两口经营。儿子在县域附近跑运输,一般过完年出工,11月底返回,家里有特别忙的事情还可以回来帮忙。儿媳在家做家务、照顾孩子。她说:“以前家里种地,一年四季耗在庄稼上,也就是个吃饱肚子。现在不用花那么多时间了,冬季种大棚,收入在4万元左右。儿子一年跑七八个月运输,也能赚取六七万元,冬天回来后还可以帮忙干大棚的活。到了四五月份,大棚种菜结束了,我照看家里,儿媳妇就去附近街上饭馆里做短期工。丈夫也会在附近找临工做。”她还说:“现在年龄都大了,丈夫打工也打不动了,准备买上几头牛来养,每年生个小牛犊,比打临工强,还比较轻松一些”。①2020年8月18日访谈资料。
归根结底,小农户所做出的这一举动的真实面目,其实是乡土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受小农的道义逻辑与市场的理性逻辑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复杂的形塑结果,即小农户内生发展的乡土逻辑。正是这种一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和一边兼顾着互惠互助的道义行为的发展逻辑致使小农户在农业转型发展中作出合理选择。在长久的农村发展中留存了深厚的乡土观念,包含了村民自己的记忆,还讲述了村落发展的故事。正因如此,普适的发展主义或现代化的路径往往在乡村发展中显得“水土不服”。而遵从乡土逻辑、基于村民熟悉的模式去实现与现代农业的衔接,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农户发展的主要路径。
三、地方实践:几种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发展的有效模式
从小农户的现代发展趋势来看,小农户不再是过去自给自足的个体单位,也不可能自给自足地生存和发展。事实证明,现代小农户已经不是传统自给自足的兼业小农,而是专业化的商品生产者。[7]随着西部民族地区高原农业的转型发展,以小规模家庭经营为主的小农户已被越来越深地卷入到现代化社会体系之中,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是乡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由“乡村中国”转型到“城市中国”的需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农户实现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重点在于突破小农户的生产弱势、组织弱势和市场弱势,以土地规模化、组织规模化和服务规模化的方式将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的轨道。T县高原农业发展形态已经涌现出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多元实践。
(一)农业社会化服务
农业规模存在内在规模与外在规模,农业主体规模扩张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另一种形式就是通过社会化服务得到规模化的效益。[8]打破封闭的小农户家庭社会单元模式,利用社会化服务实现农业发展的规模化和效益化,是西北民族地区小农户向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路径。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小农户通过购买社会化服务,把自己的某些部分劳务委托给社会化服务的提供者,双方之间形成一种委托-代理关系。[8]小农户则利用社会化服务主体提供的规模化服务使得自身实现了规模化,提高了劳动效率,享受到集聚化大规模的红利,从而小农户不再小,更加显示出小农户自身的优势。
案例5:
小农户杨某是个养殖大户,每年需要种植20亩地的青草。他自己没有播种机,就将20亩地的种植工作承包给李某。李某在前年购买了播种机,10万元左右,仅种植自家的地是不划算的,因此他便专门给别人种地,一亩地50元,这种大型播种机一天就能翻20亩地,开春种植季节便能播种几百亩地。这样一来,小农户杨某和其他农户则通过购买李某的社会化服务融入了规模化经营而享受到规模化的种植效益,摆脱了规模小的弱势,从而对接了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生产。类似地,小农户也通过购买社会化服务完成秋收工作。杨某说,“以前村里没有大型收割机的时候,全靠人力完成收割,20亩地的青草收割工作如果依靠家庭劳动力来完成那么至少需要20天左右,费时又费力,而变工又来不及,只能雇人。记得2017年时,雇佣五个人整整割了7天才割完,还非常辛苦,仅工钱就付了2000元。这两年来,附近村里好几户人家都买了专门的收割机,收割工作就委托给有机械的农户完成。就拿去年来说,20多亩地的青草收割只花了两天时间,费用仅需1000元。”①2020年9月27日调研资料。
这样一来,小农户通过与社会化服务的自动衔接,降低了自己的生产成本,节约了社会资源,提高了效率。杨某如果自己花钱买播种机、收割机肯定不划算,因为成本太高,农具闲置没有效益,且还得专门学习机械操作技术。小农户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衔接是出于小农户自身发展的需求。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衔接发展的有效手段,是乡村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小农户与市场对接型
西部民族地区高原农业的转型发展已使小农户成为专业化的面向市场的农产品生产者,小农户与市场的对接成为必然。调研中得知,蔬菜小农户通常与批发市场的对接较多。但分散且偏僻的村庄分布与较高的农村物流成本与人力成本制约了小农户以个体形式直接与市场对接的可能。因此,小农户与批发市场的对接主要依托中间商发挥上门收购、数量集聚、冷链服务的中介功能来克服小农户分散生产和流通分离且难以冷藏的难题,从而实现小生产对接大流通和大市场,如T县的西葫芦多与兰州、青海、新疆等批发市场对接。
案例6:
小农户张某每年都将自家两座温室用来种植西葫芦。自西葫芦11月底挂果至次年四五月间,日产量大约在300斤左右。附近乡村都是西葫芦种植区,无销路,独自卖到县城或者兰州的批发市场成本太高。因此,只能将西葫芦卖给上门收购的中间商。权某是附近许多收购西葫芦的中间商之一,每年到11月底,便开始向农户收购西葫芦。权某每天可以收购5000斤左右的西葫芦,两天便可拉上一车送到兰州西固区蔬菜批发市场。供大于求时,便可先放进冷库。这样一来,小农户与批发市场之间通过中间商实现对接,小农户只负责生产,而销售由中间商与批发市场对接,降低了小农户的销售风险。
小农户依托中间商有效解决了蔬菜销售问题。对于小农户来说,只负责保质生产,没有单独议价的权利,价格多由中间商说了算。但是,随着中间商竞争主体的增多,单个中间商无法“跑马圈地”,为了获取更多更持久的货源渠道,也无法恶意压价。在长久的合作关系中,按时收购成为买卖双方约定俗成的内在条约,如果卖方不按时收购,蔬菜变质损失由中间商承担,即使收购后需要倒掉,也要按市场价格付款。有些商贩为了竞争货源渠道,有时会恶意抬价,而大多数小农户为保持正常的交货渠道,则会选择长期收购值得信任的中间商,因此避免了由不法中间商哄抬价格而导致的合作不稳定性。而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也成为农户监督价格的机制。在调研中发现,许多农户都加入相关微信群。如笔者在西葫芦种植小农户索某的微信上看到,他加入了“A村西葫芦种植群”“农资化肥销售群”“西葫芦议价群”等,这些群里包括T县各个地方种植西葫芦的农户、卖化肥的商户以及小商贩等各种人。由此可知,在小农户与批发市场的对接中,小商贩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上门收购节省了小农户的时间成本,解决了销售渠道;而发达的信息有效监督了市场价格。因此,笔者认为,小农户与批发市场之间的间接对接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发展的有效模式。
(三)小农户与公司联合型
公司+农户型发展模式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利益为纽带,以农副产品加工销售等企业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来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模式。[9]订单农业是目前较为普遍的有效发展模式,公司与农户建立合同契约关系,公司向农户收购农产品,而农户有向公司出售农产品的合同义务。[9]如D村移民搬迁户林某与T县N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将政府搭建的两个温室大棚种植了香菇,由公司发放菌棒进行技术指导并统一收购。林某说:“我是从2017年开始种香菇的,前三年菌棒由公司免费给我们,由产业园的人进行技术指导,由他们负责收购。今年开始菌棒由公司和小农户分担,即每个菌棒按3.7元计算:公司承担2元,我们自己则承担1.7元。每天采摘完便用电动车拉到附近的产业园区。种了三年,平均每年两个大棚能收入5万元左右,政府又补贴1000元,算起来收入还可以。”①2020年9月20日访谈资料。
这种公司带动小农户发展的订单农业模式,公司和农户的关系仍受制于市场化,且农产品价格的多变性以及合同约束的脆弱性非常容易导致公司的机会主义倾向,[10]即收购价格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公司可调整,而农户销售渠道的唯一性则限制了他们议价的权利,使得公司和农户的衔接仍然处于不稳定状态。但是,经济利益是纽带,公司和农户为了追求长久和稳定的利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达成默契。由于公司与农户之间较为松散的契约形式,如果收购价格太低,农户便会弃种,公司也就没有了效益;而为了提高收益,农户也会用心经营,因此农户与公司之间又相互制约。在未来的发展中,公司应思考采取农户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和“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主体共同参与的运行模式。
结 语
相比之前西北民族地区靠不断开荒扩大耕地的外在规模也难以维持生计以至于劳动力不得不大批涌进城市务工的现象,高原农业由传统农作物种植向经济作物种植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离农化”“去农化”趋势。T县农村高原农业转型的案例,事实上提供了在西北民族地区探讨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转型由小农户主导的发展框架。一方面,小农户在千年的传统农业发展中形成了一套自身的乡土逻辑,即植根于家庭伦理道德的道义责任和致力于家庭发展的生存理性,因此必然要遵循源于农民自身动力的内源式发展逻辑,有内在发展动力的乡村才是振兴的根基。另一方面,“小农”本身是多元性社会生产关系集合的范畴,小农与自然生产、家庭关系、传统文化和社区生活方式始终处于动态共构的状态。小农本身蕴含着向多维社会生产关系转化的特性。因此,要充分认识并挖掘小农户自身所蕴藏的丰富的自然社会关系,将小农户发展和现代农业发展相衔接。但乡村振兴背后隐藏的逻辑很多时候是发展主义或者现代化预设的范式,往往与乡土发展逻辑背道而驰。将农业产业的现代发展融入本土建构,乡土逻辑与现代路径相辅相成,是小农户发展之路。小农户自身发展逻辑给生存上了安全阀;与现代农业衔接背后的制度保障与保险则降低了小农户发展风险。从产业到村民,应该建设的是一种有人情味的乡村,而转型农业在空间上的“在地化”为人情味乡村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小农户经营仍然可以在资本和政策规划的干预下保持充分的活力。在多元资本和多元主体融入乡村发展的大潮之下,乡村振兴不是“现代逻辑”对传统乡村的强势解构,而是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实现以小农户为发展主体的乡村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