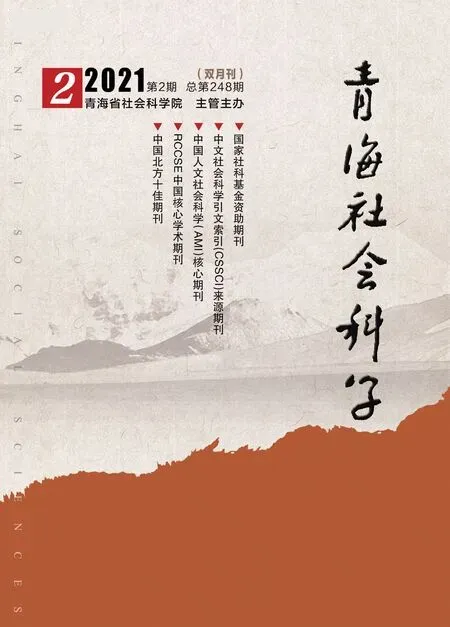文化认同视域下青海三大民俗文化圈的交融与共享
◇胡 芳
青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交融地之一,早在元明时期就已逐渐形成了汉、藏、回、土、蒙古、撒拉六大世居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以及儒释道、藏传佛教和伊斯兰三大民俗文化圈交流交融、互动共享、和谐发展的多元一体民俗文化格局,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进而在与现代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互动,尤其是在与新时期政府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互动中得到了挖掘弘扬和创新发展,迸发出了勃勃生机。从青海多元民俗文化圈的历史发展看,虽然由于文化和民族差异,三大民俗文化圈之间曾有过排斥和隔阂,但其主流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吸收,尤其是在宗教信仰、节日文化、生活习俗、人生礼仪、口头文学和民间文艺等方面存在相互交融、互动共享、和美共荣的现象,而三大民俗文化圈以多元一体、互动共享为基本特征的文化结构的构建过程,也是青海六大世居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认同过程。
一、宗教信仰与节日文化的交融共享
信仰是民俗文化中最具有统领功能的核心要素,渗透于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青海儒释道、藏传佛教和伊斯兰三大文化圈分别是在儒释道信仰、藏传佛教信仰和伊斯兰教信仰基础上形成和演化的,青海儒释道民俗文化圈主要涵盖青海境内的汉族,但对土族和青海东部的藏族、蒙古族等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也有深刻影响;藏传佛教民俗文化圈涵盖青海境内的藏族、土族、蒙古族及部分汉族;伊斯兰民俗文化圈涵盖青海境内的回族、撒拉族、保安族等。从区域分布来说,儒释道民俗文化圈和伊斯兰民俗文化圈所涵盖的区域是以西宁为中心的河湟流域,藏传佛教民俗文化圈则涵盖整个青海地区,而河湟地区是三大民俗文化圈的汇聚地、交融地和共享地。由于在历史发展中都受过儒家和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有着共同的信仰基础,儒释道和藏传佛教民俗文化圈互动较为密切,文化交融和文化共享现象较为普遍,其中,以多元杂糅为特质的宗教信仰和多民族共享的节日文化是两大民俗文化圈交融共享的文化表征。
青海儒释道民俗文化圈的信仰特征是儒释道并重,以“敬天法祖”为核心信仰,以天地人神共存、祖先崇拜、圣人崇拜为基本内容,而藏传佛教民俗文化圈的信仰特征是以释迦牟尼为主神信仰,显密兼容,其基本教义大多来自佛教,以“四谛”“六道轮回”等为基本内容。这两大民俗文化圈均以“万物有灵”为其宗教信仰的心理基础,以多元杂糅的多神信仰和崇拜为其宗教信仰的基本特征,它们在长期的并存共生中相互交流、相互吸收、交汇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享现象。如儒释道民俗文化圈中的二郎神、文昌帝君、关公,藏传佛教民俗文化圈中的吉祥天女、大威德金刚等都是青海河湟地区汉、藏、土等民族共同供奉的神祇。据《贵德县志》记载:贵德河阴镇的文昌庙“汉番信仰,士民供奉。每逢朔望,香烟甚盛,有事祈祷,灵应显著,久为汉番信仰祈福消灾之所。”①王昱主编:《青海方志资料类编》(下),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8页。该庙的文昌宫建于明代,从这段记载看,从明代到民国时期,文昌帝君一直被附近的汉、藏、土等多民族信仰。除了文昌帝君外,青海的土、藏、蒙古族还信奉关公和二郎神,如土族十分尊崇关公,在土族纳顿节的“三国戏”傩戏表演中,被尊称为“老爷”的关羽是中心和主角。海西都兰寺也设有关帝庙,周围赛什克乡、铜普乡及茶卡乡部分蒙古族每逢年节要到关老爷像前烧香磕头、求签问卦。吉祥天女是藏传佛教神祇,不仅在各大藏传佛教寺院中被广为供奉,还被青海汉、藏、土和蒙古等民族群众作为家神、村落保护神或地方保护神而虔诚供奉。此外,青海藏、土、蒙古、汉民族都有山神崇拜,遍布各地路口、山口或山顶上的“拉什则”“峨博”等都是各民族山神信仰的外化形式。
除了供奉共同信仰的神祇外,青海的汉、藏、土、蒙古等民族群众还有在家中供佛堂、拨念珠、诵六字真言、转嘛呢经轮、煨桑、挂经幡、斋戒、布施与朝拜等共同的信仰民俗。如:青海的汉、藏、土和蒙古族群众都有供佛龛的习俗,汉族群众主要供释迦牟尼、菩萨、弥勒佛等,藏族、蒙古族供释迦牟尼、莲花生、宗喀巴大师以及班禅等有名望的活佛;藏族每逢娘乃节、东巴节等宗教节日时有斋戒习俗,土族则在每年六月期间有集中到寺庙封斋的习俗;藏、土、蒙古族和部分汉族群众有每逢初一、十五及重大节日煨桑、点灯习俗;等等。这些共享的信仰神祇、仪式与习俗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增强了两大民俗文化圈内各民族对彼此的文化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间的隔阂,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
青海多元民俗文化圈的节日文化绚丽多彩,六大世居民族既有自己特有的民族传统节日,也有共享的全国性或区域性节日。如民和三川土族的纳顿节、贵德藏族的“拉伊”节、海西州蒙古族的那达慕、玉树曲麻莱的赛牦牛节、互助土族口邦口邦会、同仁藏族和土族的“六月会”、塔尔寺的酥油灯会、乐都七里店的九曲黄河灯会等都是各民族或某区域特有的传统节日,而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花儿会、朝山会等则是青海境内六大世居民族,尤其是汉、土、藏、蒙古等民族共享的全国性或区域性节日,这些数目繁多的传统节日共同构成了青海绚丽多彩的多民族节日文化。在青海的节日文化体系中,作为岁首的春节是分布区域最广、传承民族最多、影响最大的多民族共享节日。青海的汉、藏、土和蒙古族群众都将春节作为最重视、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而回族、撒拉族虽不正式过春节,却也参与春节的商业贸易活动和娱乐庆典,并通过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影响着其他世居民族的春节饮食习俗。因此,春节是青海多民族共同传承、共同享有的重大传统节日,它既是三大民俗文化圈多元交融、和美共荣的文化表征,也是加强各民族文化认同、社会和谐的文化桥梁和精神纽带。
春节是青海儒释道民俗文化圈中最具典型性的汉族传统节日文化事象,且随着汉文化在青海地区的广泛传播,春节逐渐成为青海世居少数民族藏、蒙古和土族人民的重大传统节日,这些少数民族群众也跟汉族一样,有吃腊八粥、祭灶、守岁、上坟、拜年、过元宵节等习俗。青海东部农业区的藏族称春节为“嘉洛洛萨尔”(藏语,意为农历新年),他们同汉族一样重视春节,其春节习俗主要有年终诵经、吃腊八粥、掸尘、祭灶、煨桑、上坟、贴对联、拜佛、喝年茶等。土族的春节习俗跟汉族基本一致,有过冬至、腊八、祭灶、上坟、贴对联、接神、到村庙进香祈福、拜年、跳冒火等习俗。蒙古族称春节为“察汗萨日”(蒙古语,意为白节),他们以春节为上节,非常重视,主要习俗有小年除尘供火神、祭天、供佛、煨桑、吹海螺、喝年茶、拜年、祭火神、踏“新踪”等。从节日期间举行的仪式和活动看,青海各少数民族虽然基本上沿袭了汉族春节的传统仪规和习俗,但也根据自己的生产、生活、信仰和审美情趣对其进行了改造,使之成为既具有汉文化传统,又具有本民族文化传统特质的多元共融的共享性节日。可以说,春节原本是汉族的传统节日,但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随着汉文化在青海地区的广泛传播,它深深根植于青海藏、蒙古和土等民族文化之中,成为这些世居少数民族的重大传统节日,这本身就是文化认同的结果。
二、生活习俗和人生礼仪的交融共享
青海儒释道、藏传佛教和伊斯兰三大民俗文化圈内的各世居民族在长期的繁衍生息中毗邻而居,在经济上互相依存、互利共生,文化上互相交流、交融共享,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生活习俗和人生礼仪。以语言为例,都主动积极地学习汉语,尤其是与汉族杂居或交通条件便利的少数民族地区,汉语较为普及。除了回族一直使用汉语外,青海东部地区一些长期与汉族杂居的藏族、蒙古族、土族和撒拉族,很早以前就已经不会说本民族语言,而是说汉语。如清中叶时土族中就因“与民(指汉民)厝杂而居,联姻结社,并有不习土语者。”①赵宗福等:《青海多元民俗文化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页。还有青海东部农业区许多藏族由于与汉族长期杂居,汉化程度很深,他们和汉族一样从事农业生产,住庄廓,主要交流全部使用汉语,只是夹杂个别藏语词组。青海汉语方言中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元素,是汉语中少有的深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的方言,在汉语及汉语诸方言中具有典型性。如“阿拉巴拉”(马马虎虎)、“闪巴”(屠夫)、“拿巴”(残疾人)、“当玛”(过去)、“囊玛”(内部)、“曼巴”(医生)、“卡码”(规范)等都是藏语借词;“胡都”(非常)、“一挂”(全部)等为土语借词;“海纳”(风仙花)、“赛俩目”(穆斯林群众问候语)等为阿拉伯语借词等。汉语方言中借用了少数民族语言,汉语词汇亦大量进入各民族语言中,青海的藏、土、蒙古和撒拉语中借用了大量的汉语借词,而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借用也十分普遍,在语言方面的共享随处可见。由于受儒释道和藏传佛教文化影响都比较深,蒙古族、土族语言中吸收了很多汉语和藏语词汇。需要指出的是,青海河湟各民族在使用其他民族语言借词时,汉语词汇大多跟社会政治、科学技术、现代新名词密切相关,而藏语词汇很大一部分为宗教用语,如“喇嘛”“阿卡”等词。由于同属阿尔泰蒙古语系,土语、撒拉语、保安语和东乡语中同样存在一些共同的词汇。
在青海三大民俗文化圈的语言民俗中,“双语合璧”的现象较为普遍,即在一组词汇中同时出现汉语词汇和其他少数民族词汇的语言现象,有藏汉合璧、土汉合璧、蒙汉合璧、汉撒拉语合璧。双语合璧的词汇有一部分是地名:“巴顔喀拉山”中“巴颜喀拉”是蒙古语(意为“富饶青色的山”),“山”是汉语; “孟达天池”中“孟达”是撒拉族语(意为“就在这里”),“天池”是汉语;等等。民间谚语和歌谣中也存在双语合璧的现象:湟源的顺口溜“铜布、勺子、西纳哈,一口气说了三种话”,对这种双语合璧的现象进行了形象的展现,其中,“铜布”是藏语“勺子”的发音,“西纳哈”是蒙古语中“勺子”的发音;儿歌“阿吾和阿吾是两挑担,什毛家里拌炒面,你一碗来我一碗,把什毛呈个老仰绊”①张成材:《青海汉语方言中的民族语言成分》,《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其中,“阿吾”是藏语“阿哥”的意思,“什毛”是藏语“嫂子”的意思,一首儿歌中融入了藏语、汉语,形象地展现了藏汉两族人民和谐共居的生活场景。在青海的多民族地区,各民族同时会几种语言的现象也较为普遍: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三川地区的回族,基本上都会说土语,与当地土族群众交流没有丝毫障碍;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五屯地区的土族,在家和村内说土语,遇到藏族群众则说藏语,遇到汉族说汉语。
由于地理环境相同,青海河湟地区农业区各民族生产方式和衣食住行基本相近或一致,都是以农耕为基本生产方式。过去,青海河湟农业区普遍采用“二牛抬杠”的耕作方式,以人畜粪便、灶灰、炕灰等农家肥为农作物肥料,以犁、耙、木锨、木杈、连枷、榔头、碌碡为共享生产工具,收割时用镰刀为工具,碾场时让牲畜拉着碌碡碾压,然后用连枷敲打,用木杈扬尘,汉族、土族由此还衍生了祭碌碡的生产习俗。饮食习惯方面,除伊斯兰民俗文化圈内回、撒拉等民族有忌食猪肉、不嗜烟酒外,其他基本一致,都喜欢食用青稞面。儒释道民俗文化圈内的部分汉族还受藏族影响,有喝酥油茶、吃糌粑、手抓羊肉的生活习俗,而以青稞为原料酿制的酩酼酒,更是深受汉、土、藏、蒙古族群众喜欢的传统酒品。衣食住行方面,青海河湟农业区各民族都以庄廓为传统民居,只是叫法不一,汉族称为“庄廓”,土族称为“日麻”“囊托”,撒拉族称为“巴孜尔”。河湟地区各民族的庄廓构造布局与汉族基本相同,但在局部上有民族差异:藏族庄廓一般有佛堂或佛龛,有的房间中有锅头连炕布局;撒拉族庄廓上梁时,红布里除了包粮食外,还要放钱及《古兰经》经文;回族庄廓的上房一般要悬挂阿拉伯书法条幅或麦加“天房图”;蒙古族庄廓内有煨桑台和嘛呢杆;土族庄廓内有中宫,民和土族还有在中宫中埋崩巴(即宝瓶)习俗;等等。
人生礼仪在青海三大民俗文化圈内同样具有共享性,河湟地区的汉、土、藏、蒙古等民族都有基本类似的诞生礼、丧葬礼和婚礼习俗。以婚礼为例,除了回族、撒拉族有一些受宗教限制的仪式外,六大世居民族的婚礼程序基本相似,汉族传统的“六礼”婚姻仪礼为各民族共享。据《西宁府新志》《贵德县志稿》《青海风土调查集》等地方志资料记载,清朝初年,河湟地区的藏族婚礼就已经包括求亲、订婚、送彩礼、选吉日、婚娶等仪式,只是成婚吉日是从佛经中选,新娘不落夫家,等成婚一段时间夫妇关系和睦或生孩子后才去婆家居住。据《西宁县风土调查记》《青海省大通县风土调查录》等记载,清末至民国时期,土民结婚时,先由媒人介绍,允亲后用酒瓶定亲,送聘礼,按经卷择日接娶,送亲,唱婚礼曲,泼水迎亲,等等。虽然各民族婚礼细节上有诸多不同,但其婚礼程序基本相近,都是按照汉族“六礼”的程序进行,一般要由男方家请媒人去女方家说亲,如女家许诺,男方舅舅和媒人等结伴去女方家送礼茶、衣物,称之为“订婚”,并商量好聘礼数额和送达日期,然后送聘礼,最后择吉日由男方家迎亲成婚,迎娶时要摆设上马席和下马席、撒红筷子、跨火盆避邪,摆针线,抬针线,谢媒,官戴新郎,拜天地,入洞房,回门等,这些婚礼仪式和习俗都是各民族共享的。
葬礼习俗方面,河湟地区各民族都以土葬为主要形式,并兼有火葬、水葬等不同形式。河湟地区的汉、土、藏和蒙古族大都实行土葬,虽然在葬法上有一些区别,但其仪式和禁忌都基本相同,如报丧、吊丧、祭奠、念经、哭丧、入葬、服孝、尽七、百天、周年等,甚至回族、撒拉族分三天、头七、二七、三七、四七、百天、周年念“亥亭”的时间都跟汉族尽七、百天、周年时间一致。民和土族的葬礼则已完全汉化,土族老人一般年过60就开始给自己准备寿材、寿衣,葬礼上的主要仪式有收尸、哭丧、吊丧、念经、等外家、出丧、入葬等,入葬后进入悼亡阶段,须念7个“度郎”,即每隔七天要请喇嘛到家念经超亡人,百天和周年也要请喇嘛念经给亡人祈福,称之为“过周年”,其葬礼的隆重程度和纪念仪式甚至比汉族还讲究和繁琐。藏族则跟汉族一样,在家人去世的一年内不过任何节日,不拜访亲友,不办喜事,孝子百日内不理发,百天换孝,等等。
三、口头传统与民间文艺的交融共享
青海是多民族民间文化的宝库,儒释道、藏传佛教和伊斯兰三大民俗文化圈内的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了浩如烟海的口头传统和绚丽多彩的民间文艺,各民族的口头传统和民间文艺不仅是传承和延续其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海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吸收与借鉴,其口头传统和民间文艺既具有各自独特的发展历程和民族特色,又具有多元共生、共融共享的鲜明特征。青海河湟地区是三大民俗文化圈的交融之地,共同生活在这一多元文化场域中的各民族民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传承和享用着一些精彩纷呈的区域性多民族民间文化,河湟花儿、社火和锅庄舞就是其中的经典之作。
花儿是广泛流行于我国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由汉、回、藏、土、撒拉、东乡、保安、裕固和蒙古等9个民族共同用汉语演唱的区域性民歌,是西部民歌乃至中国民歌中属于标志性的口承文艺。根据音乐旋律和歌词格律形式,花儿可分为河湟花儿和洮岷花儿两大系列,而青海花儿是河湟花儿的主体部分。花儿在青海主要流传于东部河湟地区,并间及青海西部各地,其生成和传承地域极其广阔。花儿的传承历史悠久,但关于其起源与传承,文献并无记载,只是在明清时期的古人诗文中有一些诗录。根据目前所见到的资料,花儿最早出现于明代诗人高弘《古鄯行吟》之二,其诗云“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①转引自赵宗福《花儿通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据《河州志》记载,高弘是山西大同府朔州人,举人,于成化庚寅年(1470)任河州卫儒学教授,“在任尊严守正,笃学善吟,人材多有造就。”②[明]吴祯著,黄选平审,马志勇校:《河州志校刊》,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这首诗形象地描写了当时古鄯(今青海省民和县古鄯镇)地区农家男女在劳作时传唱花儿的场景,说明早在明代中期河湟一带花儿已经很流行了。清代乾隆时,狄道诗人吴镇的《我忆临洮好》十首中的第九首云:“我忆临洮好,灵踪足胜游。石船藏水面,玉井泻峰头。多雨山皆潤,长丰岁不愁。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③转引自赵宗福《花儿通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描写了清初洮岷地区藏族女子唱花儿的情形,说明至少在清代,藏族民众已成为花儿的传承者和享用者。
青海花儿既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也是各民族文化和睦共荣的表征。具体来说,花儿的唱词虽主要来源于汉族文学,但其曲调却充分吸收了藏、回族等少数民族音乐的文化元素,而宗教信仰不同又大都有自己本民族语言的各民族用河湟方言共同传唱花儿,热爱花儿,从而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民歌史上的一个奇迹。赵宗福认为,青海的“6个世居民族都在唱花儿,而且基本上都用汉语演唱,其歌词格式、音乐曲令、歌唱程式在适度保持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色的同时,几乎完全一样。”“这些民族中既有信仰儒释道的汉族,又有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土族、蒙古族,又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撒拉族、东乡族……这些民族语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习惯不同,但是他们都共同用汉语演唱花儿,体现出了一种民族亲和、兼容并存的内在精神。”④赵宗福:《西北花儿的文化形态与文化传承——以青海花儿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
青海花儿是各民族共同创造、传承和享用的口头传承艺术,藏族、土族、撒拉族等民族的花儿无论是在用词造句,还是曲令、调式等方面有着显著的民族特色。藏族花儿语词以汉语为主,但造句时却根据自己的语言习惯运用倒装句式,他们还用汉、藏两种语言创造了“风搅雪”花儿:“大石头根里的清泉水,哇里麻曲通果洛(意为黄乳牛吃水着哩);我这里想你着没法儿,却干内曲依果洛(意为你那里做啥着哩)”。土族和撒拉族中也有汉土合璧、汉撒合璧的“风搅雪”花儿,汉语和土语、汉语和撒拉语交叉使用,使得花儿的民族特色极为浓郁。如土汉合璧的花儿,“蚂蚁虫儿两头儿大,介希登你那仁达怀哇(意为你十七来我十八),介达活罗赛你达怀哇(意为我俩儿配对嗬美啊)”。①吉狄马加、赵宗福:《青海花儿大典》,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这些汉语和藏语、汉语和土语交叉使用“风搅雪”花儿,使得青海花儿呈现出了极为浓郁的多民族色彩。从曲调上说,藏族花儿中揉进了“拉伊”等本民族民歌的元素,而土族、撒拉族有自己常用的一些花儿曲令,如“土族令”“撒拉族令”等。
社火是中原汉族传统文化在青海的标志性传承,主要流传于青海东部农业区汉族村落之中,也有部分土族村庄或汉藏杂居的村庄于每年春节期间举行,是深受河湟地区各民族群众喜爱的春节文艺活动。关于社火的起源,民间有“楚庄王突围”“罗成打登州”、明初从南京迁徙的移民带来等传说。由于没有确切文献记载,社火何时传播到青海河湟地区已无从考据。从高适的《九曲词》(二)云:“万骑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骐驎。到处尽逢欢洽事,想看总是太平人”②赵宗福选注:《历代咏青诗选》,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中展现的场景看,当时声势浩大的集体高歌和舞麒麟的场面可能跟社火有一定联系。清末,西宁诗人朱耀南《社火》诗云:“休明鼓吹答升平,街舞衢歌雅颂声。巧制鱼龙看变化,粉墨登场又多名。”而从该诗看,最迟在清末民国时期,社火在河湟地区十分盛行。社火通常由灯官老爷担任首席表演者,其“身子”(即角色)有报子、龙灯、狮子、春牛、船姑娘、艄公、五子夺魁、八大光棍、八仙、胭脂马、火球、竹马子、胖婆娘、拉花姐、哑巴儿、高跷、高台等,还有鼓手、锣手、钹手、管弦手等。除了白天走街串巷的歌舞表演外,还有俗称为“黑社火”的夜场社火,其表演节目有《刘海戏蟾撒金钱》 《大头罗汉戏柳翠》 《五鬼闹判》 《张连卖布》《钉缸》等,剧目丰富多彩,几乎包括所有的小调、民歌、酒曲、秧歌、道情、贤孝、眉户以及民乐曲牌等民间曲艺形式。③朱世奎:《青海风俗简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页。青海河湟地区的社火一般由火神会组织,其主旨为娱神,祈求神灵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正式演出前,各村社火队要先到庙里降香,焚香化表,鸣炮祝祷。正式演出时,喧天的锣鼓、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悠扬的小调、多姿多彩的舞蹈、飞舞的青龙与狮子,胖婆娘、傻公子、买膏药等“身子”的诙谐表演,营造了一种“红红火火过大年”的欢快节日气氛,极大地丰富了河湟地区各民族的文化生活。
河湟社火是各民族共享的民间文化事象,一方面,它蕴含着不同时代的民俗仪礼和民间信仰,保留着许多中原地区已经失传或变化较大的古俗,如上古的巫舞、汉代的百戏、隋唐的歌舞至明清的地方小戏小曲,都可以在河湟社火中找到其影子,堪称是汉族古代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是河湟地区汉族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由于其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河湟社火对周围的少数民族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不仅自身吸收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还传播到少数民族村落,成为土族、藏族、蒙古族等民族群众的传统民间节庆活动。河湟社火中有藏舞、牦牛舞、蒙古摔跤等表演,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色彩。大通县长宁镇新寨村的社火中,至今还保留着牦牛舞表演,其角色有牧人、牦牛、藏族小伙、胖婆娘、傻公子等,其中,牧人和藏族小伙都头戴礼帽、身穿藏袍,表演情节有“走圆场”“挡牛”“挤奶”“惊牛”“牧人打死黑熊”等情节,是当地藏族牧民的生活写照。④赵宗福:《中国节日志·春节》(青海卷),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358页。蒙古摔跤流行于海西蒙汉杂居的农业区,海西都兰县的察汗乌苏镇、香日德镇、乌兰县的希里沟镇等地耍社火时要表演蒙古摔跤节目,由1人表演,演员穿上特制的服装,双手套进一双靴子内,再躬身双手着地,形成两个蒙古少年摔跤的形象。
民和土族称社火为“阳廓”,是“秧歌”两字在土语中的变音,“跳阳廓”是盛行于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三川地区土族村落的社火。过去,官亭镇在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九还要举行“焰火会”,有人也称其为“火神会”。届时,官亭镇吕家、秦家、张家、何家等村以祭祀关公为主旨,举行“阳廓大汇演”和“焰火会”。土族“阳廓”的“身子”有阿海(土语,指灯官)、旗牌手、忠良(指公子或读书人)、拉花姐、交子关(土语,指卖膏药的)、妖婆子(指胖婆娘)、锣鼓手、小阿海(土语,指竹马子)、龙灯、千里马(指胭脂马)、船姑娘等。土族“阳廓”也演黑社火,晚上表演《“牧童放牛》 《张良耍赌》 《彦贵买水》等“阳廓折子”,虽然有些“身子”称呼不一,但其基本仪式和内容与汉族社火大致相似。此外,据关丙胜等人调查,湟中县西纳地区拉沙社火的“参与人群以汉族为主,并有藏、蒙古等民族”①关丙胜、赵郡丹:《文化的演进博弈——河湟西纳地区阳坡人的社火历程》,《青海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其中,阳坡村社火在沿承河湟社火基本套路的同时,还增加了耍牦牛、摸磊②当地人对藏族一种集体舞蹈的称呼。、老秧歌③与汉族民间舞蹈“秧歌舞”不同,为男舞者装扮成放羊人后的集体舞蹈。、哈拉熊④两人表演,一人装扮成黑熊,一人装扮成猎人用铁链拉着黑熊。等具有藏蒙风情的节目。
锅庄是藏族传统舞蹈,藏族人又称之为“卓”,藏语意为“圆圈舞”。锅庄历史悠久,其原型可追溯到马家窑时期青海出土的两件著名的舞蹈纹彩陶盆,其中,大通上孙家寨墓地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内壁绘有3组15人手拉手跳舞的场景,宗日遗址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则绘有2组24人手拉手舞蹈的场景,这两件舞蹈纹彩陶盆上所绘的舞蹈图案是我国最早的成型舞蹈图案,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最古老的舞蹈形象。大通上孙家寨舞蹈纹彩陶盆和同德宗日舞蹈纹彩陶盆所绘制的都是手拉手的舞蹈,这种“联臂踏歌”舞蹈形式与至今流行于藏、彝、羌、纳西、普米族的锅庄舞、左脚舞等形态极为接近,围圈作舞、连臂踏歌、左脚起步的古舞形式,是藏缅语族民间舞蹈的主要特色。大通舞蹈彩陶盆出土于湟水流域,湟水流域是古羌族的发源地之一,彩陶上绘制的连臂舞可能与先羌文化有关,而宗日文化是先羌文化,宗日舞蹈盆上的连臂舞无疑也属于先羌文化,这两个被定格在5000多年前、虽历经数千年的岁月沧桑仍栩栩如生的连臂踏歌的群舞场很可能就是锅庄舞的雏形,它像两组神秘的文化密码,向人们彰显了锅庄舞的悠久历史和动人魅力。
此外,清代的史籍、志书和游记中也有一些关于至今仍盛行于河湟地区的藏族锅庄舞蹈的记述:傅恒、董浩等篡编、乾隆十六年(1751)刊用的《皇清职贡图》中载“男女相悦,携手歌舞,名曰锅庄。”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印的《卫藏图识》载“俗有跳歌粧(即锅庄)之戏,盖以妇女十余人,首戴白布围帽,如箭鹘,著五色彩衣,携手成圈,腾足于空,团圞歌舞。度曲亦靡靡可听。”清人李心横《金川锁记》中记述藏民“俗喜跳锅庄嘉会”,“男女纷沓,连臂踏歌”。从这些记载看,早在清初,锅庄舞就在藏区广泛流行,而早在民国时期就盛行于互助土族地区的安昭舞也是联臂踏歌的舞蹈形式,极有可能是受藏族锅庄舞影响后产生的土族传统舞蹈。现今,锅庄是深受青海各民族人民喜爱的舞蹈,除了藏族外,其他各民族民众也喜欢跳锅庄,闲暇和节庆期间,各民族民众聚集在广场和场院中跳锅庄,气氛极为热烈,锅庄已成为青海各民族共享的文化事象。
从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历史来看,文化交流交融、共存共享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文化纽带和思想根基。正是由于不同历史时期、各地区文化的交流互鉴与共融共享,才最终整合形成了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为核心、具有很强凝聚力和生命力的“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青海儒释道、藏传佛教和伊斯兰三大民俗文化圈交流交融、互动共享、和谐相处的历史与现状,既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多元民俗文化交流互鉴的“活体”与“范本”,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形成与发展的缩影和典型例证,不仅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青海各民族逐步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也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建构多元一体文化共同体的区域民俗实践,是青海各民族群众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和精神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