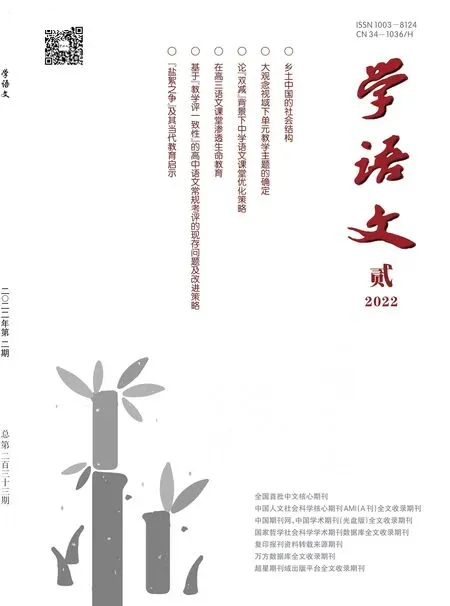意象美的不同表现形态之探析
——以统编人教版教材茹志鹃的《百合花》为例
□ 曹俊敏
《百合花》是一篇战争题材的短篇小说,讲述的是革命军人牺牲的故事。与同题材的作品相比,小说的战争色彩并不浓厚,感情基调也不悲壮沉重,反而显得比较平和素淡。在这种基调下,读者感受更多的是一种明朗和温润。透过简单的情节内容和人物关系,我们可以看到闪烁于战火之中的生命之美:淳朴率真的人性之美,微妙纯洁的人情之美,高尚无私的人格之美。值得一提的是,在故事的推进中,作者颇有意识地创设了一系列美的意象,如“百合花”、“野菊花”、“中秋月”,等等,它们如锦中绣花,既丰富了人物的形象内涵,又为故事平添了几分抒情意味,构成了作品独具特色的艺术之美。
一、文学意象的概念与特点
文学意象是文学作品中赋有某种含义和意味的主观形象。在具体创作中,文学意象是作者传情达意的重要媒介,也是作品思想主旨的艺术外显。从表现形式来看,文学是一种审美艺术,文学的美主要源于意象,当美流动于意象之中并引发了情感共鸣,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便得以真正实现。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意象选取和运用上,一般遵循的都是美学原则。追溯诗歌文化的源头——《诗经》和《楚辞》,不难发现,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等等,不论是草木形象,还是虫鸟形象,都营造出了一种纯美之境,在情感传递中给人以无限美感。
中国现当代小说在创作实践中,自觉继承了这一传统特点,茹志鹃的《百合花》就是凸显意象美学的典范之作。作品在意象构建过程中既运用了符合大众审美心理的常规意象,如“百合花”“野菊花”等;也挑拣了一些蕴含丰富美学内涵的特殊意象,如“干馒头”“破布片”等,从而带给读者多形态、多维度的立体审美体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课标》)指出:“让学生在语言文字运用的学习中受到美的熏陶,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审美感知和创造表现的能力。”显然,这与中国传统文学以美传美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同。
二、文学意象的表现形态
文学意象的基本特征有哲理性、象征性、荒诞性和求解性等。其中,象征性是文学意象的主要表现特征。在通常情况下,文学意象的传情达意是通过形象的象征来完成的,象征的“形象”就是蕴含某种情感或者意义的载体。由此观之,《百合花》中的“百合花棉被”“中秋的满月”“干硬的馒头”“枪筒里的野菊花”等诸多意象,不仅是反映作品内容的审美符号,更是包涵作者情感的象征主体。以下,笔者试从文学意象的象征性角度,探析作品意象美的几种表现形态。
(一)以美衬美
美的意象是通过美的外在形象加以表现,被人的直观所感知,从而成为人的审美对象。茹志鹃的《百合花》是一篇女性视角的作品,在意象选取和情感表现上具有浓郁的女性特点,彰显了鲜明的女性审美心理,例如:百合花的新婚棉被,清丽而芬芳的野菊花,等等。透过舒朗而诗意的笔调,我们可以尽情领略到女性文学所特有的隽逸和含蓄之美。文中关于棉被的描写:“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看似轻描淡写的一笔,却不着痕迹地写出了女性对于美的天生敏感。“百合花棉被”作为新媳妇的随身嫁妆,洋溢着浓厚的喜庆色彩,本身就是美的事物,在特定场合下,这种美又不断地延展和升华,最终成为自然美与人情美的统一体。同时,在借被过程中,作者还细腻地描写了新媳妇的美丽外貌,多次突出她的“笑”。这些描写都是在渲染一种美的氛围,为新媳妇纯洁善良的美好心灵搭建支架。所以,这里的“百合花棉被”既是美的实体,也是美的象征,在棉被的“百合花”中,我们嗅到了人情美与人性美的馨香。
再看“野菊花”意象。在作者精心选构的意象中,“野菊花”着墨最为简洁,文中仅有一处描写:“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虽寥寥一笔,却不能忽略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如果说棉被上的“百合花”传递的是一种圣洁之美,那么枪筒里的“野菊花”则给人一种朴素之美。在“我”的眼中,通讯员俨然成为了美的化身,不论是其高挑厚实的外形,还是其护送途中的局促言行,抑或借棉被时的难为表情,都被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美感。这种美感不是“我”的刻意添加,而是源自通讯员不加修饰的本真性情,正如质朴淡雅的野菊花,默默无闻而沁人心脾。可见,“野菊花”是通讯员在物质贫乏的战火年代最美的生命写照,它充分体现了作品在意象创设上以美衬美的特点。
(二)因缺而美
文学意象的美,可以通过外在形象直接带给读者丰富的审美体验,如《百合花》中的“百合花”“野菊花”“中秋月”,等等,其本身的形象特质,自然为作品平添了诗意之美。不过,美的内涵与外延并不囿于外在形象,它与审美主体的认知层次和价值取向也密切相关。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说:“如果你在自己的心中找不到美,那么你就没有地方可以发现美的踪迹。”在某种意义上,美是情感与意识的产物,情感倾向不同,审美感知也会随之不同。作品中,有些意象的外在特征并不符合固有的审美标准,但经过作者的情感倾注和着力渲染,这些意象也具备了特定的美学功能,比如“干馒头”“破布片”等。普通的馒头和残破的布片,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唤醒人们的审美意识,但在文学创作中则不同,形象的美感与其外观并不完全对等,审美主体(作者和读者)的情感和精神投入才是美感获得的重要因素。
1.“干馒头”中显人格之美。“干馒头”在文中先后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通讯员到包扎所后准备回团部时:“走不几步,他又想起了什么,在自己挂包里掏了一阵,摸出两个馒头,朝我扬了扬,顺手放在路边石头上,说:‘给你开饭啦!’”一般情况下,“干馒头”谈不上美食,更不具有美感,可在物质过度缺乏的战争年代,它却给人以生的召唤和美的期待。“掏了一阵”“摸出”“放”等,表明了馒头在通讯员心中的珍贵地位;而“扬了扬”,则突出了通讯员的热情与可爱,此时“扬”的何止是干硬的馒头,分明是美好的心灵。在一系列简洁、稚拙的动作中,通讯员无私淳朴的鲜亮形象豁然而立。“干馒头”第二次出现在通讯员不幸牺牲后:“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看着静静躺在木板上的通讯员,“我”莫名地产生了一些奇特的念头,“想看见他坐起来”,“想看见他羞涩地笑”,这些念头最后定格在摸到“干馒头”上,不禁让人感佩作者高超绝妙的审美建构:当通讯员年轻的生命随着战争的残酷悄然而逝时,“他给我开的饭”——干硬的馒头竟成了“我”唯一的情感寄托,这是何等地哀伤与悲痛!逝去与留存之间,通讯员舍已救人、无畏生死的人格之美尽显无遗。
2.“破布片”里藏性情之美。“破布片”在文中一共出现过三次。“不想他一步还没有走出去,就听见‘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口子撕得不小”,这是“破布片”的产生原由。在现实生活中,撕破衣服本是一件小事,“破布片”不值得一提;但在艺术构思中,它却体现了作者独到的审美眼光:于细微处见真性情。在“借被子”的特定环境中,通讯员遭遇碰壁,而“我”成功借得。于是,通讯员在新媳妇家抱被子时,“竟扬起脸,装作没看见”,“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导致衣服被划了一个口子。从人物塑造来看,划破衣服时的细节描写正是通讯员率直性格的生动诠释。第二次是典型特写:“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这里,通过“我”的视角再次聚焦“破布片”,烘染通讯员天真稚朴的性情。“一飘一飘”摇曳的“破布片”,在“我”眼中,俨然成为了通讯员可爱性情的最美见证。“破布片”最后一次出现在通讯员遇难时:“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肩头的洞口与安详的面容在感官上并不谐调,甚至有些对立,而这恰恰是作品的可读之处。通讯员因负气而留下“破布片”,但他并没有留下遗憾,“安详的合着眼”是最好地证明。从拿被子到回团部,由护送同志至不幸牺牲,“破布片”时隐时现,看似信手之笔,实则匠心独运,在殆无美感的“破布片”里,包藏的却是通讯员至善至美的真性情。
(三)由悲生美
按审美主体的感受,美可分为优美、崇高、悲剧、喜剧四种形式。文学意象的美在构建与表现上,也形态各异:有秀丽雅致之美,也有雄浑壮阔之美;有温婉和畅之美,也有悲壮凄怆之美,等等。无论何种意象美,都有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都能带给读者丰盈的阅读获得感。《百合花》在意象美的表现方式上不拘一格,呈现出审美需求的多样化特点,而最涤荡人心的莫过于由悲生美。悲与美在形态上是矛盾冲突的,一般性认知很难将它们融为一体,但在文学艺术表现中,悲与美的关系却颇为微妙。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中认为:“悲和美有很深的渊源,悲可以产生美。”从解读层面看,悲会激发读者发现美的灵感,扩展读者在美感上的思维张力,增强其对艺术审美的敏锐性。《百合花》在结尾部分,正是通过“百合花棉被”的功能转移——从新媳妇的婚嫁妆到通讯员的陪葬品,由美到悲,悲中生美,实现唤醒人们追求美好人性与人情的创作初衷。
作者第一次写“百合花棉被”,可谓不惜笔墨,质地、颜色、图案等面面俱到且相当细致,主要意图就是营造浓厚的喜庆气氛,为“借被”情节铺设环境。新婚刚满月,就要借出心爱温馨的唯一嫁妆,搁谁都会有些不舍,通讯员的空手而归情有可原。后来,在“我”的一番陈说下,新媳妇转变态度,爽快答应借被,完成形象升格。此时,美丽、善良的新媳妇,如同作者精心描绘的“百合花棉被”,成为读者心中美的印记。
就此搁笔,未尝不可,但表现力似乎弱了一些。于是,当通讯员牺牲时,“百合花棉被”又出现了:“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美的事物与美的人物再次同框,“百合花棉被”又将新媳妇和通讯员连在了一起。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此时的棉被已由婚嫁妆变成了陪葬品,新媳妇也从美丽的借被者变成了悲伤的送葬者,这无疑给作品抹上了一层悲剧色彩。“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毁给人看”,作品在结构安排上以年轻、可爱生命的逝去收束全文,正符合此意。在未曾预料的结局中,在通讯员静默的葬礼上,虽然“百合花棉被”的原态美被“毁灭”了,但读者却深深地感受到了“毁灭”中所诞生的人性美,并由此衍生了更多的生命遐想与思考,也许这就是悲剧所潜藏的艺术魅力。
结语:文学是想像的艺术,也是审美的艺术。《百合花》通过建构各具形态的意象之美,描绘了一幕幕既温情又纯净的战后场景,唤醒了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人性美与人情美的无尽守望。茹志鹃在创作谈中曾说:“文学创作是一桩有益于人生,有益于人类的事业。对于创作者个人来说,很有趣,也很令人动情。”《百合花》正是一篇有益于人生、有益于人类的动情小说,在朴素、清郁的文字中始终流淌着一股暖人肺腑的真情实感。在新课程背景下,这篇小说入选统编版高中语文新教材,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即立于培育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进而引领学生健康成长。《课标》指出:“通过审美体验、评价等活动形成正确的审美意识、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是涵养语文学科素养的重要途径。”在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渐趋成熟的关键期,《百合花》这样的作品,对于他们的形塑和成长来说,无疑是最美的青春之歌。以意象美濡染人格美,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树立美的向标,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语文教学,我们都殷殷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