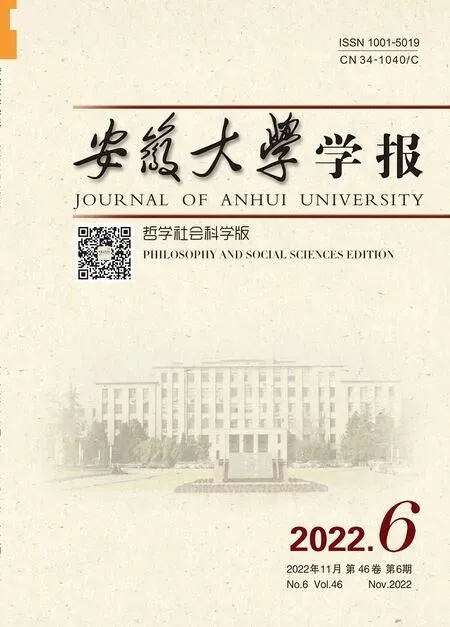命定之下的个体修为:王充“贤者命困”论旨趣探微
王 尔
王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系统、深入地讨论“命”的思想家。在王充《论衡》的开篇位置,有若干篇讨论“命运”问题的文章。如果说《论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那么命运论则构成这一体系演绎、展开的逻辑前提,它是王充整体哲学之能成立的理论出发点。王充谈命,与他对个体实践的认识和建构有关。目前,学界关于王充命论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大多没有联系其个体实践论来探讨。以往认为,王充认同以宿命支配人生一切行为,其实践论是消极而无甚意义的,甚至据此质疑《论衡》有没有价值论(1)如徐复观认为王充“将人生、政治、社会一举而投入于机械而又偶然的不可测度的命运里去,剥夺了人一切的主体性,一听此机械而又偶然的命运的宰割。”参见徐复观《王充考论》,《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4页。龚程鹏讨论王充命论而后说:“甚至于我们可以问《论衡》有价值论吗?所谓价值论,是指讨论人生宇宙间应以何种价值为依归、人生应以何种价值为目标……王充对这些似乎完全没有涉及。”参见龚程鹏《汉代思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18页。周桂钿指出,简单否定王充命论的意义,是目前许多王充研究论著中的普遍现象。参见周桂钿《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4页。其他还可参考杨超《王充命定论思想的剖析》,《文史哲》1956年第11期;周桂钿:《王充性命论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王晓毅:《王充的命理学体系》,《孔子研究》2001年第6期。。我们认为,王充论命对其思想体系的意义恰在于提出了明确的价值论。借助对命的论述,《论衡》为面对不可逃避之命运的个体应该如何履践人生价值的问题确立了指引方向。
与王充对“命运”的讨论相关的,是如何看待人的能力(道德)与命运之关系的问题。以人能否预见和改变命运为标准,学者将中国古代的命运观划分为不同的类型(2)傅斯年将古代的命运观念分为命定论、命正论、命运论、非命论和俟命论。唐君毅则提出宗教义、形上义、预定义、道德义、所遇环境义五方面概括命运论的不同侧面。参考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九龙:人生出版社,1966年。。王充对命运的看法可被归为“命可预知而不可改变”的类型,即人能够预测命运,但人的能力无法左右命运(3)陈宁:《中国古代命运观的现代诠释》,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页。。在这一类别中,王充与许负等汉代善相人者在命运与实践关系问题上有不同看法,而他的观点的独特性及价值论尚未被学者辨明。
实际上,王充并非就命论命,而是将命运放在与个体之生命实践和价值实现之关系中进行阐释。而这种个体的生命实践与价值实现又在贤者那里有最为鲜明的体现,因此“命”与“贤者”被精心地结合在一起,“贤者”成为王充考察命运的重要参照。贤者之命运如何?面待宿命的安排,贤者会抗争还是顺应?个体是否还具备自由意志?要言之,“命”与“贤者”的身份特征、现实遭遇、使命追求、价值安顿等问题紧密关联,构成《论衡》命论的基本内容。本文希望探讨《论衡》中一种有关命定框架下个体修为的学说——“贤者命困”论,揭示其题旨义涵,并从思想史与社会史背景,追寻这一学说之渊源及其影响。
一、命不可改而性可改:命定论下的“善恶之行”与“胸中之志”
王充认为人有“命”,是为一种普遍意义的“有命论”: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论衡·命禄》)
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论衡·命禄》)
凡人禀命有二品,一曰所当触值之命,二曰强弱寿夭之命。(《论衡·气寿》)
人禀元气于天,各受寿夭之命,以立长短之形。(《论衡·无形》)
“有命”即表明,命运是人注定不可摆脱的。对此王充从命运自身的两个特点来加以说明。第一,在人出生时,根据初禀元气之性质,其命就已决定。王充认为命可分为“死生寿夭之命”与“贵贱贫富之命”。前者指寿命,人禀赋元气之或厚或薄,决定了体魄之强弱和寿命之长短。后者指禄命,即生命之遭遇景况,取决于产生元气之星体的尊卑位次。王充相信元气产生自宇宙星体,后者犹如朝廷百官,各有尊卑地位。不同的星体发出的精气各不类同,这决定了命运之贫富贵贱。可见寿命与福命完全是由先天之气决定的,这便是“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论衡·命义》),以及“命,谓初所禀得而生也”(《论衡·初禀》)。王充还引入了“遭、遇、幸、偶”诸词来表示偶然的、不可预知的遭遇,这些遭遇看似随机,实则在禀赋元气、获得命运时已被决定(4)“所当触值之命”的偶然遭遇也由先天之气所定,参见王晓毅《王充的命理学体系》,《孔子研究》2001年第6期。。
第二,一个人的命的好坏厚薄,与他的能力(道德和才能的高低)没有必然关系。即命具有一种德、才无涉的性质,如以下论述:
夫临事知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仕宦贵贱,治产贫富,命与时也。命则不可勉,时则不可力。(《论衡·命禄》)
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论衡·逢遇》)
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祸福之至,幸、不幸也。(《论衡·累害》)
由命之“元气初禀”与“德才无涉”性质推导,王充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人的命运与后天的“操行”无关。“操行”是人的德才在经验世界中的行为表现,它与命运境遇不存在因果关系。王充屡屡提到“命运无关乎操行”之说法:
富贵贫贱皆在初禀之时,不在长大之后,随操行而至也。(《论衡·命义》)
人之死生自有长短,不在操行善恶也。(《论衡·问孔》)
夫贤人有被病而早死,恶人有完强而老寿,人之病死,不在操行为恶也。(《论衡·治期》)
这类说法背后是“操行”取决于人“性”的设定,由此可见王充特殊的性命说。在“性—命”问题上,王充质疑了先秦两汉流行的认为“性”与“命”之间存在强关联性的观点。先秦儒家尤其是思孟学派多将命视为天命(令),认为“性自命出”“天命之谓性”:人性出于天命,被禀赋了天的道德命令,性、命之间关系紧密(5)在先秦两汉的性命观中,“性”来源于“天命”,是“天命”的下落和转化,人物禀受于己身之中。“天命”与“性”虽有位格的不同,其实体并无二致。参见丁四新《作为中国哲学关键词的“性”概念的生成及其早期论域的开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不同的是,王充的“命”主要指人的命运,他对性、命关系的看法颇为复杂。一方面从本原上看,性与命都是人禀受元气时就获得的天赋之物。“禀性受命,同一实也。”(《论衡·本性》)“人生受性,则受命矣。性命俱禀,同时并得。”(《论衡·初禀》)这是就“自然之性”而言的,即天性和性格。这种性的坚强软弱与命之寿夭有关,此乃性与命“同”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性与命又是相异的。当“性”指“道德之性”时,性的善恶与命之吉凶无关:
夫性与命异,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恶而命吉。操行善恶者,性也;祸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祸,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恶而得福,是性恶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恶,命自有吉凶。(《论衡·命义》)
性之善恶与命之吉凶都是自然而然的,其间没有因果关系。“性与命异”是《论衡》的重要讲法。在《本性》《率性》等论性的篇目中,性都指道德之性,表现为“操行”。先天的命运与后天的操行无关,归根结底,性与命有极大的不同。
性与命之间的差异,最明显地体现为性可改而命不可改。首先,性有善有恶,即有人性善,有人性恶,这是由人禀气之薄厚决定的:“禀气有厚泊,故性有善恶也。”(《论衡·率性》)更重要的是,人性可被改变,性恶者可被教化变为善。“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论衡·率性》)人性之不变指其自然而然的天性、“真性”,人性之变指其后天形成的人为之性、“伪性”。王充强调两者价值等同,伪性也是性:“天道有真伪。真者固自与天相应,伪者人加知巧,亦与真者无以异也。”“(性)犹丝也,其有所渐化为善恶,犹蓝丹之染练丝,使之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无异。”(《论衡·率性》)王充承袭荀子的人性可塑的观点,认为“性”是可在后天变化的。
由此,王充提出了“命—性”“命运—操行”“先定—可变”的二分框架结构,演绎出独特的“性命论”。命不可以被人掌握,但性可被掌握。“命定”不意味着命运控制了人生的一切行动,因为命运无法决定人的道德选择和自由意志。个体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可以改变德性:“德不能感天,诚不能变动,君子笃信审己也,安能遏累害于人?”(《论衡·累害》)这就为命定论之下的个体修为提供了可能性与可行性。
王充假设了德福不一致的情况。他反复提到“或行善而得祸,是性善而命凶”“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以及“修身正行,不能来福”,这种说法与善恶有报的报应论相悖,相较之下,报应论对人更有扬善惩恶的效果。如此一来,德福不一致的观念何以保证人的操行?人为何需要修身行善?王充必须论证“命定之下的操行”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可贵”的:人坚持操行,不是为了得到好命,而是为了某种更高的人生追求。人自主行为的价值可以高于命运所规划限定之人生价值。《命义》末尾的重要论断,可视为对整个命论主旨的提炼和总结:
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命,有盛衰之(禄),重以遭遇幸偶之逢,获从生死而卒其善恶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
人的命运有好有坏,还有各种不可测的遭遇,能从生到死保持善恶分明的操行、实现胸中抱负的人,实在太稀罕。王充将命的讨论落脚于“善恶之行”和“胸中之志”的问题上,有其深意。对这两个概念他屡有提及:“清直不容乡党,志洁不交非徒,失众心者,人憎而毁之”(《论衡·定贤》),“清正”和“志洁”之人常遭世俗之毁誉。“内累于胸中之知,外劬于礼义之操,不敢妄进苟取,故有稽留之难”(《论衡·状留》),贤者有知守礼,往往仕途不顺。“清正”“礼义之操”对应“善之行”,“志洁”“胸中之知”对应“胸中之志”。《论衡》的“善之行”指发自道德、遵守礼义的行为,“胸中之志”指高洁不屈的志向,两者都是“性”的外在表现,是后天所形成的,无关乎先天的命。王充将命论与“善恶之行”“胸中之志”紧密联系,蕴含道德判断和价值追求于其中,为的是建立一种面对命运之不公,仍坚持自我价值实现的贤者人格。
遭遇不可抗拒的命运与无法预料的运势,人还能坚守操行和志向,就尤其可贵。比如面对掌握自己前途的君主,不迎合上意(《论衡·逢遇》);身处诽谤谗言而泰然应对,坚守操行(《论衡·累害》);见有人佞幸得宠,违反道义却得主欢心,仍宁可“不侥幸”(《论衡·幸偶》)。这种不苟合、坚守道义的举动,需过人的胆识和坚强的意志。对这类人来说,“志行”而非“好命”是自主人生的最高境界。王充论命之规定性时,会不断渲染这种分辨“善恶之行”并坚守“胸中之志”的人格,构建命运不善而志行高洁的贤者形象:
①以贤事恶君,君不欲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贤圣之臣,遭欲为治之君,而终有不遇,孔子、孟轲是也。孔子绝粮陈、蔡,孟轲困于齐、梁,非时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浅,不能用大才也。……圣贤务高,至言难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论衡·逢遇》)
②累生于乡里,害发于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虽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颜回、曾参不能全身也。(《论衡·累害》)
③古贤美极,无以卫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贤洁之人也!极累害之谤,而贤洁之实见焉。立贤洁之迹,毁谤之尘安得不生? ……动身章智,显光气于世;奋志敖党,立卓异于俗,固常通人所谗嫉也。……君子也,以忠言招患,以高行招耻,何世不然?(《论衡·累害》)
④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虽才智如孔子,犹无成立之功。世俗见人节行高,则曰:“贤哲如此,何不贵?”见人谋虑深,则曰:“辩慧如此,何不富?”贵富有命禄,不在贤哲与辩慧。(《论衡·命禄》)
⑤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则夫顺道而触者,为不幸矣。……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无有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又曰:“君子处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论衡·幸偶》)
“获罪得脱,幸也。无罪见拘,不幸也。”(《论衡·命义》)
从这几段论述中,“贤者”的形象挺立了出来。段①提到贤者以道义事君,遇到不好道义的君主就很难被赏识。即使遇到好道之君,又会因为君主才能太低而不被重用。段②说古今才能优异、德行高尚的人都难免遭到乡里或朝廷的诽谤。段③补充说“贤洁”之人受到世俗的忌惮,声誉被损。段④称才智极高者往往难以施行其智,即使有所施行也难以成功,才智与富贵之间没有必然关系。段⑤借孔子之言指出君子宁可不幸,不求“侥幸”。在这类叙述中,王充总结出古今贤者很难幸免于困厄之命运的规律。这种情况不仅是可能的,更是普遍的。
王充还从“贤者难被世俗辨识”的角度说明其命运多舛。《定贤》篇提出“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贵为贤乎”“以朝庭选举皆归善为贤乎”等二十条世俗辨识贤者的标准,实则是为了否定其有效性,指出真贤不能以地位之高、财富之厚、门生之多等世俗标准来判定。因此真贤很难被觉察,更不易被举荐提拔,无缘于好命是正常的:“贤者还在闾巷之间,贫贱终老,被无验之谤。”(《论衡·定贤》)总之,王充声称贤者因其行为、志向与世俗格格不入而很难获得世俗意义的好命。他暗中高度肯定了身处不可抗拒的逆境中仍然坚守善行和志向的人,称其乃世间稀少之人杰。如此,“贤者命困”构成《论衡》一个隐匿但重要的命题。
二、贤者的价值实现与命运之关系
王充以“贤者命困”为前提,推演出积极主动的个体实践论,构筑其关注个体人格价值的思想体系,而非抱怨贤者无力回天,要其顺从命运(6)龚鹏程说:“倒霉、运气不好,才使得文儒沉沦不偶。王充的思考很快就集中到这儿来了……(命论诸篇)就是这种自叹倒霉、自伤薄命之下的合理化陈述。企图以才禄命定、偶然际会说,来解释才士在那个伟大时代中不幸的遭遇,并宽慰自己心中的愤懑。”似不确。参见龚程鹏《汉代思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06~207页。。“贤者命困”是《论衡》论证的预设而非终点。那么“命”与贤者价值实现是何种关系?
“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命”表现为贫富、贵贱、寿夭等处境状态。王充的命运概念可分“寿命”和“禄命”。他倾向于将命理解为一种寿夭、贵贱的际遇。“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论衡·命禄》)“命”虽然形成自精气,但就其现象而言,“命”具体表现为“遇”和“谤”一类外部境遇之事。“命者,贫富贵贱也。”(《论衡·命义》)“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贵;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贫贱。或时才高行厚,命恶,废而不进……仕宦贵贱,治产贫富,命与时也。”(《论衡·命禄》)王充往往在地位、财富、健康与疾病等范畴下讨论命运。贫富、贵贱、寿夭,都在人出生而禀赋元气时就已决定,是命中注定的,属于命运的表现形式。
王充进一步说,富贵、长寿是一种对肉身意义的生命追求,它主要被世俗所关心,而“贤者”对此并不看重。《论衡》经常提及某类“俗”现象及“俗”观点,如“世俗之议”“俗语”“俗人”“俗儒”,并对之批评。“好命”是按“俗”的标准所定义的被世俗宠爱的东西。所谓“富贵,人情所贪;高官大位,人之所欲”(《论衡·定贤》),而“高士所贵,不与俗均,故其名称不与世同”(《论衡·自纪》)。贤者、高士不很看重富贵、长寿等“好命”,他们有一种高于享受生命的追求。当这种追求与获取好命之间有冲突时,他们的选择与俗人不同。视“富贵”为“俗”,对之有所不齿,是汉代士人阶层的一种风气现象,如西汉之博士严彭祖:
(严彭祖)以高第入为左冯翊,迁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权贵。或说曰:“天时不胜人事,君以不修小礼曲意,亡贵人左右之助,经谊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终。(《汉书·儒林传》)
从严彭祖的话可见“苟求富贵”被视为一种“从俗”的表现。不愿以违背先王之道的方式来获取厚禄,班固称之“廉直不事权贵”。士人视“谋富贵”为“俗”并表示不齿,如屈原所说“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楚辞·卜居》),司马迁也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报任安书》)儒家向来认为追求富贵不应违背礼义。王充暗示“好命”是流俗情欲之所求,并非贤者的至高追求。这不是说贤者不欲求富贵。王充说明的是在道德准则和生命欲望冲突的情形下贤者的选择,如“非好死而恶生也,非恶富贵而乐贫贱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贵及己,士不辞也”(《孝经·立节》)这种理解。
贤者虽然命运不济,其为人处世,安身立命,仍由其自由意志决定,不被命运所限制。他自愿承担这种选择的后果。从现实来看,贤者的行事准则与“好命”往往不兼容。很多情况下,好命的获得需要人违背道德原则。俗人希望得遇,需谄媚君主,成为佞幸(《论衡·逢遇》《论衡·幸偶》),毁伤他人(《论衡·累害》)。这些都不是贤者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从理论来看,贤者人生价值的实现可以不借助现实地位之高和寿命之长。既然“好命”呈现为富贵和长寿,如果贤者能够不依傍于地位和寿命来实现其人生价值,他便挺现出一种超越命运的人生姿态。首先是地位。贤者难有“贵”位,这往往是他选择的结果。王充将贤者不得提拔、不受重用,解释为贤者的品行端正和能力过高所致。人之贤能带来的不是晋升而是滞留:他们往往潜心于钻研圣人之道,为官廉洁正直,不迎合别人,便很难被提拔。贤者对内受到知识的约束,对外恪守礼义操守,这是他们遭到“沉滞之留”的原因(《论衡·状留》)。另外,在位者未必真贤,因为得到地位的手段往往是能力之外的因素。《状留》《定贤》认为政治地位的缺失恰恰标识了贤者的身份。“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论语·里仁》),难以得“遇”是贤者自主的选择。贤者的价值实现不受限于其现实地位之低,他们有别的途径来实现。
“贤者命困”论与王充自己的生命体验相关。他仕途不畅,终生位贱,以著书立说、记录思想安顿自己。在《自纪》篇中,面对“仕途失败者著书立说有何意义”的讥嘲,他回答,圣贤如孔子比我潦倒多了,若以被用与否来衡量人的能力,那些做官吃俸禄的人就都胜过孔子、墨子。自己愿与原宪、伯夷等高士同行,耻于与子贡为伍。“命厚禄善,庸人尊显;命薄禄恶,奇俊落魄”,贤者之命薄乃古今一贯。这段自述与《论衡》对命运、贤者的讨论多有呼应,互为解释。不可简单认为是王充对人生不顺的抱怨牢骚,其实是他心路印记和思想体系的真实表达。
王充也不主张贤者应当归隐,沉浸于与世隔绝的个体生活。隐居不符合“贤”之定义,仕途不顺之贤者仍应肩负社会担当:“(以)恬无欲,志不在于仕,苟欲全身养性为贤乎?是则老聃之徒也。道人与贤殊科者,忧世济民于难。是以孔子栖栖,墨子遑遑。不进与孔、墨合务,而还与黄、老同操,非贤也。”“大贤之在世也,时行则行,时止则止,铨可否之宜,以制清浊之行。”(《论衡·定贤》)王充努力为贤者找到某种不借助社会地位却仍可匡世济民的路径,以及在命运困顿之下仍能实现“胸中之志”的生存之道。
王充还认为贤者的价值实现不拘于有形之躯体。贤者“寿命”景况多不佳。他反问道:为何常常是善人短寿,恶人终老?(《论衡·福虚》)在《命义》篇他举了很多贤者短寿的例子,如果说颜渊和冉伯牛是无故夭折,那么屈平和伍员尽忠事君,反而因之遭害。贤者也会遭遇无妄之灾,“无罪见拘”或“遭逢非常之变”,如成汤囚夏台,文王厄牖里。尽管这些遭遇似乎命中所定,王充仍哀其不幸:为何品行高贵、才华横溢之人,反而屡屡罹难?他意识到贤者会招人陷害,引起君主猜忌,遭受飞来横祸,“君子也,以忠言招患”(《论衡·累害》)。
尽管如此,以下这段话可见王充相信“身体”的损毁并不削减贤者的生命价值:

身体虽如草木般腐朽,名声却能与日月同辉;行迹甘愿与孔子比穷,文采则与扬雄并肩。王充高度赞扬德丰、知博、文彰之徒,尽管他们一生短暂,名声却流传千古,“吾荣之”。反之,身居尊位、生活安逸、文章不遗者,百年以后会像万物一样消逝,“非吾所臧”。贤者借助“文章”来表达和传载其才能。司马迁说过“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7)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王充同样推崇倜傥非常之人,他们以留世的文章超越了有限的生命。这既是王充的自我标榜,也是“贤者命困”论在事实和经验上的成立依据。
王充希望探讨的是,贤者如何不依借命运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超越命运对生命的限制。就贤者的价值实现而言,命运的顺逆并不重要。命运是人所不可把控的,但人不需要把控它。王充反对神仙家追求长生之术:“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体已定,不可减增……形不可变化,命不可减加。”(《论衡·无形》)以祭祀鬼神祈求健康长寿,属无稽之谈(《论衡·祀义》)。“求生”在王充看来不是个重要问题。但另一方面,王充不厌其烦地谈“遇”“幸”“累害”,他潜意识仍看重这些际遇,无法完全超越荣辱得失。这也可见王充并非主张消极避世,他仍有强烈的现世关怀意识,退守姿态之下隐含着进取。
王充将命之好坏解释为寿夭、贵贱、贫富诸境遇。好命以肉体生命的世俗享受为标准,是一种世俗的定义,为俗人所关心。按照这种尺度,他提出:命运之困,反而标识了不与俗同的贤者身份;贤者之独立人格、价值追求、恬淡心态,使其并不很看重所谓好命。命运之困不会减弱贤者的生命价值。在这种意义上,贤者以道德之自主性和人格之独立性,超越了世俗之命,在无位、无财甚至短寿诸情况下仍可能名垂青史。“贤者命困”论最终探讨了贤者在不依傍于政治地位的情况下如何安身立命、实现自身价值等诸问题。徐复观等学者称王充命论:“把生命安放在命运里面的人生,实即把生命安放在偶然里面的人生,也即是一种漂泊无根的人生。”(8)徐复观:《汉代思想史》第二卷,第389页。邓红、龚程鹏的说法类似。徐只看到其一面,没看到另一面。
三、诸子与文章:“贤者”的身份定位及其超越命运之途径
“贤者命困”论构成了《论衡》思想体系的论证前提。《论衡》各篇进一步探讨了当命运不济之时,贤者何为的问题。
贤者没有现实地位,却希望匡世济民,这是通过撰著有补于世的文章来实现的。首先,王充用“素相”“诸子”“文儒”等概念指称一种才能卓异但官途不济的贤者。陆贾、贾谊、董仲舒、刘向、扬雄、桓谭属于此类,他们构成了一个区别于经师的汉代“诸子”谱系。这些人没有很高的地位,但有安世济民之志向和才干,并擅长写作。他们疏离于现实政治,以“素相”(“不在位的丞相”)为己任:“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谭)不相,素丞相之迹,存于《新论》者也。”(《论衡·定贤》)“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诸子之传书,素相之事也。观《春秋》以见王意,读诸子以睹相指。”(《论衡·超奇》)这类人擅长著书立说,将安世济民之道蕴含于其中,以文章传递其经世关怀。王充推崇“素相”“诸子”和“文儒”,这三个概念分别对立于“宰相”“经师”和“世儒”,意指一类不受重用、不被世俗社会所认可的独立知识分子,其是真正之贤者,不拘时势,倜傥卓绝,批判世俗,得以媲美孔孟等先秦诸子。在“贤者命困”论的推演下,“素相”成为无位贤者之身份定位。
其次,贤者将文章当成安身立命的事业。擅长文章者必是人杰,文如其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繁文之人,人之杰也。”(《论衡·超奇》)王充认为文章撰著是无位者表达和传播其思想的唯一途径。贤者得遇时尽忠宣化,失遇时则应该“称论贬说,以觉失俗”(《论衡·对作》),即评论是非,留下论著,纠正世俗不良风气。“作文”被视作古今才高之人的出路,“上自孔墨之党,下至荀孟之徒”,无一不是“教训必作垂文”(《论衡·对作》)。像邹伯奇、袁太伯、周长生等人“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论衡·案书》),是文章而不是现实地位标榜了他们的价值。贤者之文章,其一,应传达礼义,寄寓是非、褒贬之判断于文中。“化民须礼义,礼义须文章”(《论衡·效力》),圣贤作经传,都是为匡济薄俗,褒是抑非,实现对人民的教化(《论衡·对作》)。其二,文章应针砭时弊,摒弃虚妄之说,纠正被曲解的儒学之义,传达真实之道理。圣贤之创作皆有现实针对性,不作无病呻吟、哗众取宠之文,力求引导人民回归内心之实诚。其三,文章应长于论辩和说理,激发个体理性思辨精神。王充推崇一种“论”的体裁,区别于圣人之“作”和“述”。“论”是对作者内心真实而有条理的表达,这种体裁倡导个体心灵的推理、演绎能力。他将归谬法的运用贯穿于《论衡》,正是“论”的一种体现(9)参见徐英瑾《基于汉语土壤的启蒙哲学何以可能——以王充的〈论衡〉为例》,《复旦学报》2021年第4期。。王充相信“文”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是内在才能的直接对应物,并且几乎是这种才能唯一的外在体现(10)参见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37页。。论理的文章著作被认为能够纠正虚妄的社会风气,趋导儒学向常识化、理性化的本义复归。通过贤者的撰文实践,王充希望祛除当时俗儒强加于儒学的神秘内容,恢复早期儒家的人文主义色彩,以此为实施教化之正确途径。
王充将“文”视为贤者的事业,贤者因文章而成就自己。“文”的撰著无须借用官场地位或现实资源即可完成,是贤者突破命运限制、实现个体价值的可行方式。在此背后,王充为草野的思想者构筑了安顿精神的私人空间,探讨了无位贤者的存在方式:追求道德的自主性和才学的独立性,以求实、理性、批判世俗的方式,匡正时弊,间接地教化民众。他将诸子著书立说称为“素相”之事,视其为表达诸子旨意的途径(《论衡·定贤》)。“素相诸子”的贤者论和“以文为事”的实践论拓展了“贤者命困”的内涵,是以命论为前提推演而来的命题。从“命”出发,构建“素相”身份,提出“作文”的实践方式,同时赋予这种实践理性启蒙色彩的教化意涵,《论衡》由此构筑了一个严密、完整的思想体系。
四、“天人有分”与个体意识:“贤者命困”论的思想史脉络及社会背景
“贤者命困”论应被置于《穷达以时》等文献所构成的基于“天人相分”的儒家境遇观及其彰显的道德自主性之思想传统中来看待。儒家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的德才与境遇存在正向联系,即道德定命论(moral determinism)(11)陈宁:《中国古代命运观的现代诠释》,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页。。其中又可分为两种思路。一是“不仕无义”论,将出仕与否视为人的修身立德完成与否的标志,认为德、位一致。人能否充分发展与其能否获得现实地位有关,这是一种用“好命”(出仕)来证实“道德”的思路(12)“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子路批评隐士“不仕无义”(《论语·微子》),刘宝楠《论语正义》解释“不仕无义”:“义者,宜也。君子成己所以成物,故士必宜仕。仕即是义,亦即是道。不仕则无君臣之义,是为乱伦。”对“德位一致”的论证,参考张亦辰《论孔、孟德位观的异同:以亲亲与尊贤的张力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另一种是“大德受命”论。人之生命是天赋予的,有德之人的生命会得到天的眷顾、厚待。这是用“道德”来证实“好命”的思路(13)典型如《礼记·中庸》:“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故大德者必受命。”《韩诗外传》子路言:“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报之以祸。”。这两种思路都认为道德和命运之间存在强因果性。两者皆以天有神性为前提,强调天人之间的感应和同调关系,属于“天人和合”的境遇观。
与上述两种思路不同,王充持道德中性的命运前定论(amoral pre-determinism)。王充的命运论以“天人有分(职分)”的观念为基础(14)关于“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两种儒家天人观,可参考梁涛《竹简〈穷达以时〉与早期儒家天人观》,《哲学研究》2003年第4期。由此推演出的两种命运观、德福观,可参考王中江《〈穷达以时〉与孔子的境遇观和道德自主论》,《伦理学与公共事务》第4卷,李建华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2~114页。,以天人各有职分来解释命运。这种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郭店楚简《穷达以时》。
《穷达以时》认为,命运之“穷达”都由“时”决定。首先,天与人各有职分,应该各司其职:“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辨别天人差异,人才知道怎么行动。其次,贤人能否得遇,要看天能否提供相应的时机:“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郭店简《唐虞之道》提到圣王如尧也须依借时命(15)“圣以遇命,仁以逢时,未尝遇贤……纵仁圣可与,时弗可及矣。”参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最后,尽管“穷达以时”,人在德行上仍需高度自律,时刻反省:“善否,己也。穷达以时,德行一也。”时命是不可控的,但善恶之行可由个体自己掌握。可见在“天人有分”的观念、穷达与时命之关系、面对“誉毁”的处理方式以及对德行一致的追求等问题上,《穷达以时》与王充命论多有相似处。《论衡·祸虚》称“凡人穷达祸福之至,大之则命,小之则时……穷达有时,遭遇有命也”,直接借用了“穷达以时”的概念。
《穷达以时》的“天人有分”思想在其他相关的文献中也有表述,如《荀子·宥坐》《说苑·杂言》《孔子家语·在厄》以及《韩诗外传》卷七第六章等篇,有诸如“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荀子·宥坐》)等说法。此外,《庄子·让王》《吕氏春秋·慎人》《孔子家语·困誓》和《风俗通义·穷通》诸篇也提及“陈蔡之厄”中孔子针对困境的积极言论(16)诸如“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庄子·让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孔子家语·困誓》)之说。。以上文献构成了先秦至两汉“天人有分”的命运论脉络。其基本内容如下:首先,明确将“人”(“材”)与“时”(“世”“命”)对立起来,正视二者之间的张力,以“天人有分”为立场质疑天人和合、德福一致之说(17)在《荀子·宥坐》中,为纠正子路“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报之以祸”的观点,孔子回答:“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其次,关注贤者“不遇时”“不遇世”的普遍遭遇及这种遭遇与德才之关系等问题。以“贤人”“君子”和“学者”为出发点探讨时运,暗含为其德位之差鸣不平之意。这构成了先秦两汉时运论的一个基本范式:个体人格在逆境中愈加彰显(18)儒家往往将厄运升华为忧患意识,以此构成道德实践的动力。参见宋健《君子固穷:比较视域中的运气、幸福与道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最后,为贤者的安身立命指明方向,强调道德之不为命运所动摇的自主性,提出“反求诸己”的内省功夫:“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荀子·宥坐》)。对照之,《论衡》也涉及这三方面内容。王充命运论与《穷达以时》和《荀子》所开创“天人有分”的时运论传统更具亲缘性(19)通常认为“天人相分”是荀子设计政治时的重要思路,参见姚勇《天人之分与职能之异——〈荀子·天论〉“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新诠》,《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而非如过去学者所论,来自一种强调“元气偶适”的道家自然哲学传统。后者过于强调王充之命的自然属性,忽视了其以“贤者命困”为逻辑起点来树立贤者价值标尺的理论目标。
相比于“命”,《穷达以时》等文献更强调“时”,认为由“时”决定了“穷”“难”“通”“达”等人生状态,而对命运问题没有过多直接论述。由此,上述文献多表达“以俟其时”(《荀子·在宥》)的处世观,对汉代士人影响较大,如“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时,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盐铁论·地广》)、“君子修德以俟时,不先时而起,不后时而缩”(20)扬雄撰,司马光集注:《太玄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06页。等说。俟时的观念强调,君子不遇之时的修德、求知是为适当时机的到来做好准备,君子期待“遇其时”,等候时运的逆转。因此君子德才的发挥仍依赖于时机降临。到了王充那里,“命”变成一个主要的概念,发展出命运之遭遇幸偶等具体内涵。命被深入论述,而命运的顺逆与才能的发挥之间被认为没有必然联系。一方面,命是完全不可抗拒的;另一方面,贤者的自行其是则格外可贵。从强调“时”到强调“命”,“天人相分”境遇观被《论衡》演绎出新内容。王充撤除了命运逆转的可能性,他在个体道德自主性上坚持得更彻底,论证了价值实现可以超越命运之拘定:人可以不再寄望于时运,一定程度上能够将命置于考虑之外来行事。
此外,“贤者命困”论的形成还与西汉末年到东汉个体意识浮现的社会思潮有关。这个时代的士人多关注命运问题。以此为主题的文章源源涌现,它们描述一种不拘于命运的独立人格志向,成为东汉时代的一股新气象。两汉之际拒仕新莽朝、入东汉后颇不得志的冯衍,作《扬节赋》云:“废吊问之礼,绝游宦之路,眇然有超物之心,无偶俗之志。”(21)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79页。士人吴良被视作“不希旨偶俗,以徼时誉”(22)范晔:《后汉书》卷二七《吴良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944页。。“偶俗”指迎合世俗。“不偶俗”之风尚,一如王充所论之不求幸偶。冯衍又作《显志赋》,认为贤者不须拘守一时之名节,应以不变之“道德之实”应对万变之时势。冯衍表示自己既能适应各种时势,“与时变化”“因时为业”,又能恪守常道,“正身直行”,做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言下之意,无论是西汉、新莽、更始汉朝还是现在,其都以“德”一以贯之,以不变应对环境之万变。冯衍在东汉不被重用,既贫又贱,“喟然长叹,自伤不遭”。尽管如此,冯衍不拘小节,正直行道,超然物外,并不为福祸所囿。冯衍晚年隐居长安渭陵冯氏墓边,过恬淡无为的生活(23)范晔:《后汉书》卷二八下《冯衍传》,第985页。。他对世俗的讥刺及其“贤者命困”的问题意识,展露了经历两汉之际之动乱的士人心态。
两汉之际的崔篆作《慰志赋》,羡慕古代贤者之得时,哀叹自己辗转于诸政权间,生不逢时,称“绝世俗之进取”(24)范晔:《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第1705~1706页。。班彪作《悼离骚》,感慨圣贤之穷达取决于时命:“夫华植之有零茂,故阴阳之度也。圣哲有穷达,亦命之故也。惟达人进止得时,行以遂伸,否则诎而坼蠖,体龙蛇以幽潜。”(25)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二十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598页。班彪本人则“仕不为禄,所如不合;学不为人,博而不俗”(26)班固:《汉书》卷一○○上《叙传上》,第4213页。。冯衍、崔篆、班彪皆出身累仕西汉的家族,他们哀叹时运,与新莽代汉又速亡、各家势力交替更迭的动荡局势有关。更重要的是,这些士人多次易主,对个体与政权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对政治产生了自觉或不自觉的疏离。甚至他们对新兴的东汉王朝并不完全信任,隐退不仕的姿态,或带有主动选择。这正是个体意识萌生的表现。进入相对稳定的东汉明章时代,文人依然关注“贤者命困”的问题。崔篆之孙崔骃,“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时人或讥其太玄静,将以后名失实”(27)范晔:《后汉书》卷五二《崔骃转》,第1708页。,作《达旨》;班彪之子班固,“或讥以无功,又感东方朔、扬雄自谕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28)班固:《汉书》卷一○○《叙传上》,第4225页。,作《答宾戏》。这两篇虚拟的对话,皆表达了崔骃、班固轻视现世的得遇和富贵,追求道德和学问之“正道”,弘扬君子“所守”(29)崔骃称:“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举;非不欲室也,恶登墙而楼处。叫呼衒鬻,悬旌自表,非随和之宝也。暴智燿世,因以干禄,非仲尼之道也。”“子笑我之沈滞,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则而我弗亏,行有枉径而我弗随。”(《达旨》)班固也称:“若乃夷抗行于首阳,惠降志于辱仕,颜耽乐于箪瓢,孔终篇于西狩,声盈塞于天渊,真吾徒之师表也。”“故夫泥蟠而天飞者,应龙之神也;先贱而后贵者,和、随之珍也;时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答宾戏》)。
明帝、章帝时期是东汉鼎盛的时代,也是政治与儒学通力合作、互相妥协又互为制约的时代(30)参见王尔《光武“受命”与永平制礼》,《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以儒学获得仕进成为当时晋迁之常态,形成一条吸引学子的功名利禄之途。儒士的品格和学识不被世俗重视,仕途得意成为判定士人成功的标志,这种氛围使不遇之士难以自处。出生于建武三年的王充曾师从班彪,与班固、崔骃是同时代人。王充对命运的关注受这一时期风气的影响。王充摆脱了对得遇的渴望,贤者未必需要俟时,不必将人生寄望于富贵:
福至不谓己所得,祸到不谓己所为。故时进意不为丰,时退志不为亏。不嫌亏以求盈,不违险以趋平,不鬻智以干禄,不辞爵以吊名,不贪进以自明,不恶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齐死生,钧吉凶而一败成,遭十羊胜,谓之无伤。动归于天,故不自明。(《论衡·自纪》)
贤者仅仅“忧德之不丰”,而将福祸、进退、安危、盈亏、平险、生死、成败等人生境遇置之度外,纵使遭遇众人诽谤也无妨。超越命运的个体形象在诸如此类的论述中悄然确立。比王充稍晚的王符,提出“仁重而势轻,位蔑而义荣”的“潜夫”身份观,继续论述这种贤者个体化的存在方式(31)王符自居为“不欲章显其名”的“潜夫”,《潜夫论·论荣》表达了与王充相似的境遇观。参见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2页。。《穷达以时》等文献构筑的天人有分、德福相离、注重不因时而变的道德自律之时命论传统,遭遇东汉时代个体疏离于官场的政治文化新局面,使士人皆从各自角度论述命运不济之下个体何为的问题,凸显个体思想与著作的意义,反思、消解现行社会秩序及评价标准,修正德福一致、学优则仕的主流儒家话语。东汉乡里民间舆论重视个人的美德和文化学识,与西汉崇尚富贵的乡里风尚截然不同,这反映出东汉时代对士人的评价尺度从外部仕宦经历转向内在才能(32)参见卜宪群《乡论与秩序:先秦至汉魏乡里舆论与国家关系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清儒赵翼认为东汉士大夫有尚名节、特立独行的现象:“志节之士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33)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07页。。这些人形成士的自觉,不苟合流俗,在桓灵之际政治腐败时刻挺身而出,身体力行匡扶天下,坚守礼法,身陷党锢而怀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之大志(34)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7~400页。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71~577页。。到了“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的魏、晋动乱时代,士人朝不保夕,发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两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典论·论文》)的感慨,用文章超越肉体生命以求不朽的撰著意识最终成熟,其背后仍是王充命论的逻辑延续。真正的个体主义思潮至此以玄学、文学等形式蔚然大观。
五、结 语
本文重新探讨了王充命论的内涵和价值。借助命的“先天禀赋”和“德才无涉”性质,王充首先推演出命运之不可改、性之可改的观点,提出命定论下个体修为的可能性。其次,通过建构命运不济下辨明“善恶之行”并坚守“胸中之志”的贤者形象,王充彰显个体修为的可贵性。命运薄厚表现为贵贱、贫富、寿夭等境遇状态。对“富贵”“长寿”等境遇的追求其实是对肉体生命的享受,是一种世俗人生的喜好。贤者追求高于享受肉体生命的价值实现,也因此可能不得富贵。最终,《论衡》借助“素相”“诸子”“文儒”概念,为不被世俗认可的贤者建立价值路径,提出“文章”是他们匡世济民、名垂后世的方式,以撰著针砭时弊之论说文为贤者毕生之事业。王充的命论是对“天人相分”境遇观的继承和突破,又与东汉时期个体意识萌生、觉醒的社会思潮相呼应。
在现代社会,人的行为同其人生的结果之间同样具有弱关系性和非对称的不确定性。如此,就必须面对决定人境遇的社会环境与个体才能发展之间的种种矛盾。尽管人们都知道不应以人的仕途不济而否定其能力,但却往往回避这样的问题:面对多舛之命途,一个有德才的人还有多大的可能性去实现生命的价值?社会能否给这种人提供容身和发展的空间?传统儒家思想虽强调“独善其身”,却始终未能提供一个社会性的对抗不公命运的合理做法。王充的贤者命论,提出了个体在某种不公的社会机制下仍可以保持自由意志并实现自我发展的问题。意志自由与遭遇之不确定性是相容的,一切可由个体作出选择,当然选择者要承担其选择的结果(35)王中江:《强弱相关性与因果确定性和机遇》,《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同时,这种坚守本身就有其可贵之处。王充为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存在价值及其实现方式提供了多样的思考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