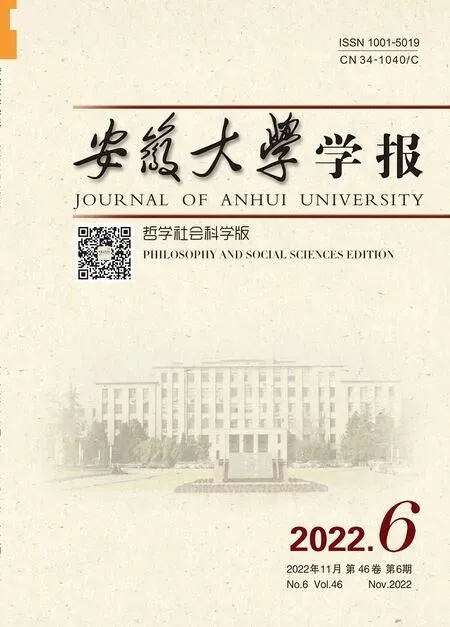安大简《诗经》的异序问题
——兼论先秦文献文本的非稳定性
郝 敬
2019年9月,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下文简称“安大简”)一期研究成果发布。该批竹简于2015年初由安徽大学入藏,经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和国家文物局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分别检测,确认该批竹简年代大致为战国中期(公元前330年)。安大简一期成果为《诗经》,主要内容为文字辨识(1)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安大简《诗经》现存内容为《诗经》的国风部分,各篇依次连续抄写,存诗57篇。与毛诗相比,安大简《诗经》在风部、篇目和章次排列等文本方面出现了较多的差异。本文将在此基础上,从文学文献学的角度对安大简《诗经》异序问题加以考察讨论。
一、安大简《诗经》文本概况
安大简《诗经》现存部分,按竹简原有编号共计117号,其中第18、19、23、24、26、30、56、57、58、60—71、95、96、97号等24支简缺失,残简不等,实际存简93支。存简内容为《诗经》的国风部分,各篇依次连续抄写,存诗57篇。按竹简原有编号顺序,各篇分别为:
《周南》11篇,现存10篇,抄写于第1至17号与20号竹简之上,所存18支简大致完整,第15、16号简简首稍有残缺,依次连续抄写,为《关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苢》《汉广》《汝坟》(缺)和《麟之趾》。其中,《汉广》缺三章末句,《汝坟》全无,《麟之趾》缺首章,当在所缺失的第18、19号简上。各篇文字与毛诗(2)本文涉及的毛诗诸篇目,均引自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下不赘述。小有异同,各篇次序与毛诗《周南》一致。惟《卷耳》《螽斯》篇二、三章均与毛诗章次互异。
《召南》14篇,抄写于第21至41号竹简之上,其中第23、24、26、30号4支简缺失,其余各简完整度不一,依次连续抄写,为《鹊巢》《采蘩》《草虫》《采蘋》《甘棠》《行露》《羔羊》《殷其雷》《摽有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何彼襛矣》和《驺虞》,惟《殷其雷》《江有汜》两篇完整,其余各篇文字残缺不一,此不赘述。各篇文字与毛诗小有异同,惟《驺虞》篇多末一(多)章,毛诗未见。各篇次序与毛诗《召南》一致,惟《羔羊》《江有汜》篇二、三章,《殷其雷》首、三章,均与毛诗章次互异。
《秦》10篇,抄写于第42至60号竹简之上,其中第56、57、58、60号4支简缺失,其余各简完整度不一,依次连续抄写,为《车邻》《驷驖》《小戎》《蒹葭》《终南》《黄鸟》《渭阳》《晨风》《无衣》《权舆》。其中,《渭阳》篇今在毛诗《无衣》后,余者次序皆同。各篇文字小有异同,惟《无衣》篇多末句“赠子以组,明月将逝”,毛诗未见。《车邻》《驷驖》篇二、三章,《小戎》《黄鸟》篇首、二、三章,均与毛诗章次互异。又《小戎》二章四、五、六句,语次亦与毛诗前后互异。又《无衣》篇依前例,二、三章应与毛诗章次互异,详后。
《某》,风部不详,篇数不详,应抄写于第61至70号竹简之上,惜乎十简全失。因全简抄写密度每支简约为38字,又因第72号简为《汾且洳》二章末二字与三章,所缺首章和二章约38字,当在第71号竹简之上。又因第83号竹简标明“侯 六”,风部区分清晰,故第70号简当不属其下《侯》部。依前例,十简约380字篇幅,而国风所余各部,篇幅或长或短,短者如《桧》《曹》不足300字,长者如《邶》《郑》则大大超越380字之限,均无法独立满足十简篇幅之条件。按全简所载各风部,如《甬(鄘)》《魏(唐)》皆有不足毛诗本部篇目之例,故十简不应为二风所加,当为独立风部,且篇目不足毛诗本部。
《侯》6篇,抄写于第71—83号竹简之上,其中第71号简缺失,其余各简完整度不一,依次连续抄写,为《汾且洳》《陟岵》《园有桃》《伐檀》《硕鼠》《十亩之间》。本部各篇,今均属毛诗《魏风》,独缺首篇《葛屦》。各篇次序与毛诗《魏风》有异,《陟岵》今在《园有桃》后,《十亩之间》今在《伐檀》前。各篇文字小有异同,《硕鼠》首、二章与毛诗章次互异。毛诗国风今无《侯》部。
《甬(鄘)》9篇,抄写于第84—99号竹简之上,其中第95、96、97号3支简缺失,其余各简完整度不一,依次连续抄写,为《柏舟》《墙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鹑之奔奔》《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其中,第94号残简为《定之方中》部分,第98号简为《干旄》部分,所缺三支简当为《蝃蝀》《相鼠》篇,因第99号简在《干旄》篇末标记“甬 九”,故此部风诗共9篇,实存7篇,今均属毛诗《鄘风》,独缺末篇《载驰》。各篇次序与《鄘风》一致,各篇文字小有异同,《墙有茨》首、三章,与毛诗章次互异。另,《定之方中》二、三章,当与毛诗章次互异,详后。
《魏》9篇,抄写于第100—117号竹简之上,各简完整度不一,依次连续抄写,为《葛屦》《蟋蟀》《扬之水》《山有枢》《椒聊》《绸缪》《有杕之杜》《羔裘》《无衣》《鸨羽》。第117号竹简篇末标记“魏九 葛屦”,篇数有误,实有10篇。除首篇《葛屦》今属毛诗《魏风》,余九篇全属毛诗《唐风》,缺《杕杜》《葛生》《采苓》三篇。各篇次序与毛诗《唐风》多异,《扬之水》今在毛诗《山有枢》后,《山有枢》今在毛诗《蟋蟀》后,《有杕之杜》今在毛诗《无衣》后,《羔裘》今在毛诗《杕杜》后,《鸨羽》今在毛诗《羔裘》后。各篇文字多有异同,如《葛屦》比毛诗二章多第四句“何以百适”,上下语义较毛诗通顺。《扬之水》比毛诗三章多末两句“如以告人,害于躬身”,上下语义亦较毛诗通顺。《绸缪》比毛诗缺末章末两句,疑为“子兮子兮,如此邢侯何”,因末三句为“见此邢侯”,则上下语义与毛诗大不同,简本更佳。此外,《蟋蟀》首、二章,《绸缪》《鸨羽》二、三章,与毛诗章次互异。《山有枢》首章三、四句和五、六句次序,亦与毛诗前后互异。
二、风部次序差异
安大简《诗经》呈现了与传世文献截然不同的风部次序。为求直观比较,特选取《左传》所记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聘鲁观周乐、毛诗、郑玄《诗谱》之风部次序,与安大简《诗经》比较,按时间顺序制成表1,如下:

表1 《左传》、安大简、毛诗、郑玄《诗谱》所记风部次序异同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二南外,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国风余部并无固定的先后次序,只有大致相似的区域表述。这一点在《左传》和毛诗的记述中特别明显,季札观周乐,在儒家相传的孔子整理《诗经》之前,为公元前544年;毛诗最终形成,在汉惠帝废挟书律之后,约公元前191年后,虽然毛亨所传为子夏之学,与季札所观之周乐有一定的学源关系,但在数百年的流传中,包括口耳相承的非文字传播状态中,只有二南与邶、鄘、卫、王、郑、齐等稳定地居于十五国风的前部,而后部的诸风除魏、唐和陈、桧、曹有相对固定的次序外,几无定序。直至郑玄作《诗谱》,《桧风》前提,《王风》后置,犹未定也。故《诗》在口耳相承与文字并存的传播状态下,最大的可能是并无一个固定表述顺序的母本,包括鲁国在内的各地对《诗》的再表述顺序,其实仍处于一个自由状态。居于战国中期的安大简《诗经》正体现出这样的特点,二南之后,秦风的位置大为提前,其后某风、侯(魏?)风、鄘风、魏(唐?)风的排序,与目前可知的秦火前后的传世文献记载皆不相同。
因此,我们据以为定本的毛诗,也应仅是之前在各地流传的次序不一的《诗经》众多版本中的一种而已,并不是唯一的一种。
三、篇目次序差异与“侯”“魏”所指
除却风部大类排序不同外,安大简还体现出部类内部篇目排序的不同,为求直观比较,特选取安大简和毛诗具体篇目比较,制成表2,如下:

续表2
从上表可以看出,安大简除了缺失的第61至70号十支简所构成的一个风部外,所见六风中,二南的具体篇目次序与毛诗完全一致,文献流传状态最为稳定。其余四风,《秦风》与《甬(鄘)风》的篇目次序较为稳定,前者与毛诗篇目数量相同,仅《渭阳》篇前提至《晨风》前;后者与毛诗次序相同,仅缺少最后一首《载驰》篇。安大简中的《侯风》与《魏风》,与毛诗差异较大。前者在毛诗中并无该部,所录篇目全在毛诗《魏风》,但少首篇《葛屦》,次序又驳杂淆乱;后者所录除首篇《葛屦》外,余篇在毛诗中全属《唐风》,次序亦驳杂淆乱。
可见,简本抄录所据之“底本”,必定处于一个文本正在固定中的文献状态,即篇目大致稳定,而所属风部与次序排列尚未最终确定。同时,各风部的文本固定有先有后,二南的篇目及次序已经固定,其余各风部篇目与次序编排不一。
安大简《诗经》所见六风中,问题最突出的即为“侯”与“魏”的风部命名。侯,《左传》所记季札观周乐时并无对此部名称的记载,毛诗亦无此部。根据其所著录具体篇目,均属今之《魏风》。据全简抄录之错漏情况,亦不能排除此字有讹误之嫌。黄德宽先生以为“侯”即《王风》(3)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前言第2页。,但所录篇目并无今之《王风》,不妥。魏,第117号简云“魏九 葛屦”,而此部实录10篇,故简本抄写讹误明显。此部除首篇《葛屦》属今之《魏风》,其余九首均属《唐风》。如考虑到文献传播中的真实递减、简本抄录出现的讹误,综合联系抄录篇目推断,则极有可能“侯”为《魏风》,“魏”乃《唐风》。学界从字形发展、风部次序、地域所属和诗歌旨义等角度,对此二风名称已有相关讨论,亦可参(4)夏大兆:《安大简〈诗经〉“侯六”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夏大兆:《安大简〈诗经〉“侯六”续考》,《北方论丛》2020年第1期;王化平:《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浅析》,《北方论丛》2020年第1期;陈民镇:《安大简〈国风〉的次序及“侯风”试解》,《北方论丛》2020年第1期。。但限于目前出土文献相关环节的资料缺失,以及与传世文献的不适配,诸说皆不能为定论。“侯”当存疑,以待他证。
四、多篇章次互异
安大简的文本与通行的毛诗相比,出现了一个极为特殊的文献现象,即多篇文本章次互异。为方便讨论,特将相关文本互异现象制成表3,如下:

表3 安大简、毛诗具体篇目章次互异对校表

续表3
从上表可以看出,与通行的毛诗相比,安大简的文本出现了多篇章次互异现象,即现存的57首诗中有17首诗发生了明显的章次互异。在六个风部中,周南2首,召南3首,秦5首,侯(魏?)1首,甬(鄘)2首,魏(唐?)4首,秦、魏(唐?)二风居多。这其中,章次互异又多表现为诗歌的二、三章互异,共计有11首,而首、二章互异与首、三章互异的各2首,首、二、三章交错互异的仅1首,单章语句互异的仅2首。
在不涉及一些助词、虚词的情况下,大部分的章次互异对毛诗的解读并不会产生语义及全篇的理解偏差,符合风诗往复回环、一咏三叹的整体特征,只有少数篇目会影响和修正我们的惯常解读。其中四篇,简本章次为佳,优于毛诗。一为《驷驖》,按简本所录,首章为秦襄公狩猎的准备阶段,二章为进入狩猎场所与狩猎器具的细节描写,三章为狩猎成功时的片段描写。读来脉络清晰,节奏紧凑,刻画有详有略,重点突出,尤以“舍拔则获”结尾,语尽而意不尽,足胜于往昔如“平淡无味”(5)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37页。之评价多矣。一为《小戎》,按简本所录,分写战车、兵器、战马,每章后四句则写思妇之情,末句以“胡然我念之”的思念之情收束三章四言之整齐句式,较毛诗二章中杂五言突兀而出更为妥帖。三为《绸缪》,三章所云“邢侯”,与前“良人”“粲者”文例相类,放置全篇,收束前章,则语义尤佳于“邂逅”生硬之意。简本此篇章次与异文相结合,可据改毛诗。四为《定之方中》,按简本所录,首章叙营建城市宫室,二章叙访察民间劝事农桑,三章叙登高后纵览楚丘,抒发对徙居后美好生活的祝福,并以“终然允臧”收束,较毛诗叙事顺序更为合理。
在上述章次互异的篇目中,有一首较为特殊,即《秦风·无衣》。此篇在安大简中为残篇,仅余“(修我矛)戟。与子偕作!赠子以组,明月将逝!”13字,属第59号竹简。“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句,毛诗在二章,但简本此句后又多“赠子以组,明月将逝”八字,遂接《权舆》篇,无中断,故依简本书写之例,“修我矛戟,与子偕作”章当为三章,《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未标明。而所余“赠子以组,明月将逝”二句,当为是诗终章末句,毛诗未传,当属逸句。《毛诗序》解为“刺用兵”,班固《赵充国辛庆忌传赞》则从正面肯定:“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6)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98~2999页。原诗三章,气势雄浑,排比递推,主旨愈强,如宋词之豪放之歌。然《秦风》亦有婉约之作,如《蒹葭》三章,娓娓道来,情不恣肆。二体合而成篇,正在末句“赠子以组,明月将逝”,虽显家国功业之豪壮,亦存生命有限之感慨。大不掩小,以小见大。此二句之收束,佳于毛诗多矣。
五、先秦《诗经》文本的非稳定性
从文献流传层面看,出现如此多的章次互异现象(约占简本现存风诗的30%),虽结合全简抄录之讹误情况,不能排除此简在抄录时有错简的可能,但更大的可能性是抄录所据诗歌之原貌即如此。这就可以和前文合并讨论,即风诗在早期流传时,各篇章次并非皆有固定之顺序,或风诗会根据流传所在地的实际情况加以演绎,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风诗会根据口耳相承和文字传播的差异发生变化,综合造成同一首诗歌在不同地区或不同时期的文本章次互异现象。
考虑到上文讨论的风部次序,既不与之前的季札所叙相同,亦不与之后的毛诗所叙相同,如果传承的文本是固定的状态,则是非常不合理的现象。所以,只有风诗在毛诗形成之前的传承一直处于非固定的状态,并没有一个稳定的文本,才能满足安大简《诗经》出现的风部次序差异、篇目次序差异和具体章次差异甚至具体语句差异的条件。反观,这也有促于我们理解先秦时期文献的文本传承特点——至少在刻版(包括石经)普及之前——大量抄录的文本依然保存着非固定的文献状态。
如果这个结论可以成立,我们再读《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记录,就会得到不同的认知。《左传》云: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06~2007页。
以往学界对这段文献的解读多集中于对《诗经》风、雅、颂三部的分类划分,尤其关注于十五国风,认为在其时已经有了固定的先后顺序。这种解读甚至又长时间地引发了对于孔子删诗说的相关争论。而安大简《诗经》的风部次序表达,就为我们对季札观周乐的解读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当鲁国依次为季札演奏各类风诗时,除了开始的二南外,季札的经典性评价其实大多带有“其……乎”的判断语气模式。这种语句表达的模式,既可以显示季札虽居于东南夷狄之邦,但自信于知识体系与道德价值的全面掌握,也可以侧面显示出相对于传统中原诸国,在吴地习诗的季札对风诗各部的次序并无固定的确认。因此,除了对二南有稳定的认知,其他的风部评判则多少带有求证的意味。这与安大简《诗经》的记录顺序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而这个事例的判断也符合王国维先生、陈寅恪先生宣扬的“二重证据法”,即以出土文献弥补传世文献之不足。
六、先秦文献文本的非稳定性
通过上文的讨论,我们可以对安大简《诗经》从文学文献学的角度作出一个大致的判断。由于此简本与传世文本在风部次序、篇目次序、风部命名和章次顺序等方面出现了较多的差异,综合众多因素,我们认为安大简《诗经》仅仅是毛诗定本出现之前、在口耳相承传播状态中的流传于世的《诗经》众多文本中的一种。在《诗经》文本依然没有最终固定下来的历史阶段,安大简《诗经》仅仅是《诗经》早期面貌的一个侧面呈现,不能完全判断其为《诗经》的“祖本”,也不能随意据简本改毛诗。
同时,我们也可以借助对安大简《诗经》的文学文献学的考察,对秦火之前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文献的文本流传状态作出一个大致的判断,即在刻版(包括石经)出现之前,无论是口耳相承还是简牍抄录,文本始终处于一个非固定的状态中,差异是在所难免的。而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中的文本的变化,不论是增删改逸,对考察最终定本的祖源的唯一性是无能为力的。因此,若将刘向、刘歆校书之时作为文献考察的分界点,运用不同的文献认知观点和文献考察方法,向前倒推溯源,向后推衍支流,不失为掌握先秦文献的一条通律。
OntheDifferenceinOrderofTheBookofSongsRecordedonBambooSlipsintheWarringStatesPeriodCollectedbyAnhuiUniversity—A Discussion on the Instability of Documents in the Pre-Qin Period
HAOJing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handed-down documents such as Mao’s Poetry,TheBookofSongsrecorded on bamboo slip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ollected by Anhui University has many text differences in the naming of The Ballads(Feng) and the order of titles and chapters within. Though documents inZhou-nanandShao-nanare relatively stable, other parts of The Ballads(Feng) are different in naming and the order of contents. Seventeen poems among the fifty-seven poems in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Anhui University belong to different chapters. These differences can modify our usual interpretation of Mao’s Poetry to a certain exten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 lost sentence Zeng-zi-yi-zu Ming-yue-jiang-shi in the poemWuYiofQinFeng, which can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handed-down literature. Analysis of these differences can not only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eng part ofTheBookofSongs, but also enable a reasonable and appropriate judgment on the philological value ofTheBookofSongsrecorded on bamboo slip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ollected by Anhui University. At the same time, strong evidence can be provided for the instability of documents in the pre-Qin Period.
Keywords: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Anhui University;TheBookofSongs; difference in 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