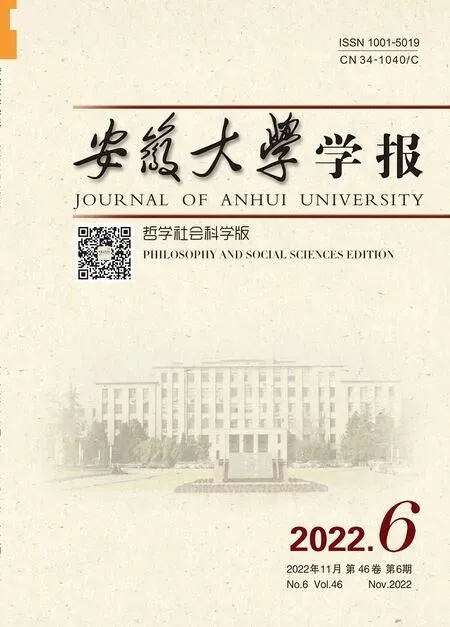姚鼐“镕铸唐宋”新论
潘务正
一、引 言
在给弟子鲍桂星的书信中,姚鼐明确提到其“平生论诗宗旨”是“镕铸唐宋”。此信开首有“今年闻与馆选,极欣慰”之语(1)姚鼐:《惜抱轩尺牍》卷四《与鲍双五》其三,卢坡:《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70~171页。,鲍氏嘉庆四年成进士,馆选庶吉士,据此,提出“镕铸唐宋”的论诗主张时,姚氏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当然,这并非其晚年才形成的主张,而是如他所说,乃“平生”一贯的宗旨。
“镕铸唐宋”昭示着唐宋诗是两种明显不同乃至对立的诗体或风格,二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这些异质因素可以融合在一起,以此解决诗学发展的出路问题。清代诗坛,由于宗唐诗风与宗宋诗风产生的流弊,为改变这种状况,诗论家有意识地调适唐宋诗之间的对立,于是提出“融合唐宋”“不分唐宋”的观点。《御选唐宋诗醇》虽仅选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六家,但考虑到其云江西诗派“变化于韩、杜之间”,故“无庸复见”(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御选唐宋诗醇》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28页。,则此选实亦包括黄庭坚,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弥合唐宋的倾向。其他如吴雷发云“岂唐诗中无宋,宋诗中无唐”(3)吴雷发:《说诗菅蒯》一五,丁福保辑:《清诗话》(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34页。,李重华“折衷”唐宋(4)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论诗答问三则》其三,丁福保辑:《清诗话》(下),第957页。李氏折衷唐宋同时,又反对宋诗,倾向于宗唐。,也是力求打破唐宋诗之间的界限。袁枚的诗学观点有时也被称为“镕铸唐宋”(5)施山:《望云诗话》卷二(蒋寅主编:《清代诗话珍本丛刊》第一辑第十九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第325页)云:“惜抱与随园论诗皆镕铸唐宋,不分疆域。”,不过他虽然明确反对诗分唐宋,实际上亦分唐界宋,欣赏唐诗,不喜诚斋体之外的宋诗(6)王英志主编:《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81~382页。,这种态度,很难做到融合二者。清代中期诗坛,真正做到不轩轾唐宋,又镕铸两体的是姚鼐(7)柳春蕊有《“镕铸唐宋”:姚鼐诗学理论及其实践》(《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一文从两个方面展开,即推崇诗学中的“雅颂”传统,推举儒者之诗,突出创作主体的道德修养;在具体诗法上,学习杜甫和黄庭坚,以文法为诗法,偏重诗歌结构和内在气韵的流转。本文论述思路与柳文有很大不同。。
二、模拟与脱化
“镕铸唐宋”既关涉诗学取向(“唐宋”),也阐明学诗方法(“镕铸”),姚鼐在其言论中常用“镕铸”指示如何学诗。他评价业师刘大櫆的诗文“能包括古人之异体,镕以成其体”(8)姚鼐:《刘海峰先生传》,《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后集》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09页。,显然,“镕铸”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学习对象,广泛向古人学习,甚至“古人之异体”也即相对立的因素都可为我所学;二是学习的目的,形成自己的面貌,也即“成其体”。二者即是明清诗学中一直争辩不休的模拟与脱化问题。姚鼐主张学诗从模拟入手,经过一番艰苦的功夫之后,再求脱化,如此方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教导侄孙姚元之说:
学诗文不模拟,何由得入?须专模拟一家,已得似后,再易一家。如是数番之后,自能镕铸古人,自成一体。若初学未能逼似,先求脱化,必全无成就。(9)姚鼐:《惜抱轩尺牍》卷八《与伯昂从侄孙》其三,《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第331页。
在他看来,学诗的初始阶段是模拟,先模拟一家,达到“似”的程度,再更换另一家;经过多次模拟,掌握多家的路径,自然能将古人之精华熔于一炉,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只有在坚持不懈的模拟基础上,才能脱化;不从模拟入手而急于求脱化,则不可能有所得。因为强调模拟,所以姚鼐对前后七子模拟之风尽管有批评,但亦将其视为正宗:“比拟诚太过,未失诗人葩。”(10)姚鼐:《硕士约过舍久俟不至余将渡江留书与之成六十六韵》,姚永朴:《惜抱轩诗集训纂》卷五,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第252页。钱谦益讥讽七子的学诗方式,姚鼐痛诋之云:“近世人习闻钱受之偏论,轻讥明人之模仿,文不经模仿,亦安能脱化?”(11)姚鼐:《惜抱轩尺牍》卷四《与管异之》其五,《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第192页。正因如此,姚鼐学诗“从明七子入”(12)吴德旋:《姚惜抱先生墓表》,《初月楼文续钞》卷八,《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6册,第171页。。模拟是学诗的基础,脱化是高级阶段,而终极目标是追求“自成一体”的成效。
对于由模拟到脱化的过程,姚鼐有深刻的体会。学诗的第一阶段,是由不似到似。他对方东树说:“大抵学古人必始而迷闷,苦毫无似处,久而能似之,又久而自得,不复似之。若初不知有迷闷难似之境,则其人必终身无望矣。”(13)姚鼐:《惜抱轩尺牍·补编》卷二《与方植之》其三,《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第450页。也就是说学诗的过程是:不似—似—不似。由于各方面的限制,初学者对前人之诗了解不深,故模拟时很难学得像,必然进入一个苦闷的境地。度过此种苦闷的阶段,才能有所心得,达到似古人的地步。所以由不似到似是一个长期而艰辛的过程,又是必经之径。在《今体诗钞》中,姚鼐往往点出某诗学某人,并且指出模拟达到的阶段,如评储光羲《寒夜江口泊舟》、綦毋潜《若耶溪逢孔九》及皎然《寻陆鸿渐不遇》云:“似孟公。”评丘为《题农舍》云:“似右丞。”意思是三人之诗已度过迷闷难似的境地,达到“似”的阶段。又评韦应物《逢郴州使因寄郑协律》“何减右丞”,评其《碧涧别墅喜皇甫侍御相访》为“何减摩诘”(14)姚鼐编选、曹光甫标点:《今体诗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1页、55页、183页、56页、162页、165页。。显然,达到似某人的地步已属不易。
由似到脱化,也要经历艰难的过程,需要“天启”才能实现。姚鼐教导门生陈用光云:“学文之法无他,多读多为,以待其一日之成就,非可以人力速之也。士苟非有天启,必不能尽其神妙。然苟人辍其力,则天亦何自而启之哉?”(15)姚鼐:《惜抱轩尺牍》卷五《与陈硕士》其九,《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第216页。又说:“至其神妙之境,又须于无意中忽然遇之,非可力探;然非功力之深,终身必不遇此境也。”(16)《惜抱轩语》,见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上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404页。功夫是基础,模拟求似的阶段必须“多读多为”。而在由似到脱化的阶段中,功夫的作用虽不如前一阶段,但仍不能脱离,只有功夫加上“天启”即灵感的到来方能臻于“神妙”的极境,也即脱化。对于这个“天启”,姚鼐有时用“禅悟”来解释,他告诫侄孙姚莹云:“凡诗文事与禅家相似,须由悟入,非语言所能传……欲悟亦无他法,熟读精思而已。”(17)姚鼐:《惜抱轩尺牍》卷八《与石甫侄孙》其八,《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第353页。又对陈用光说:“文家之事,大似禅悟;观人评论、圈点,皆是借径。一旦豁然有得,呵佛骂祖,无不可者。”(18)姚鼐:《惜抱轩尺牍》卷五《与陈硕士》其二,《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第208页。熟读精思到一定的程度,即可顿悟,无所不可,形成自己的面貌。他评陈子昂《春夜别友人》云:“从小谢《离夜》一首脱化来。”(19)姚鼐编选、曹光甫标点:《今体诗钞·五言今体诗钞》卷一,第5页。此不用“似小谢”,而是用“脱化”来评,在他看来,此诗已有自己的面貌。
可见,“镕铸”就是从一家家的模拟入手,由不似到似,然后经过顿悟,达到脱化的境界,至此,就能“自成一家”。“镕铸唐宋”即以唐宋两代诗人为模拟对象,姚鼐《今体诗钞》只收唐宋人诗,体现出“镕铸唐宋”的宗旨。这些诗人有的选入一首或数首,有的则选入一二卷的篇幅。就入选规模来看,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李商隐、苏轼、黄庭坚、陆游诸人是他重点模拟的对象。姚氏企图在效法诸家的基础上,进而求变,达到自成一家的化境。他虽主张学诗先学七子,但又告诫门生“勿沿习皮毛,使人生厌”(20)郭麐:《樗园销夏录》卷下,嘉庆刻本。。对于李商隐学杜“但摹其句格,不得其一气喷薄、顿挫精神、纵横变化处”亦深表不满(21)姚鼐编选、曹光甫标点:《今体诗钞·五言今体诗钞》卷九,第206页。。他最倾心黄庭坚学杜的路数,评《题樊侯庙》《徐孺子祠堂》云:
二首从杜公《咏怀古迹》来而变其面貌。凡咏古诗,镕铸事迹,裁对工巧,此西昆纤丽之体,若大家以自吐胸臆,兀傲纵横,岂以俪事为尚哉!(22)姚鼐编选、曹光甫标点:《今体诗钞·七言今体诗钞》卷八,第330~331页。
正如方东树所指出的,后诗颔联“藤萝得意干云日,箫鼓何心进酒樽”即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四“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之意(23)方东树著、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61年,第451页。,但姚鼐认为黄庭坚此二诗虽从杜甫组诗而来,都是借咏古而“自吐胸臆”,甚至效法杜诗之对仗,但黄诗精神面貌与杜诗已完全不同,杜之沉郁顿挫,至黄则是“兀傲纵横”。黄庭坚学杜诗,由模拟而脱化最终“自成一体”,所以被姚鼐树立为学诗的典范。姚氏自作诗也是按照这种路径操作的,鲍桂星说他“镕冶唐宋,自成一家”(24)《比部姚姬传先生》,见鲍桂星《觉生感旧诗钞》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76册,第506页。,绝非门生对恩师的虚誉。
“镕铸唐宋”所包含的模拟与新变的关系,在明清诗坛往往是割裂的,且选取哪种学诗方式,同时也关涉着师法对象的选择。正如叶燮所言,学唐诗者如前后七子、王士禛多着意模拟,故趋于“陈熟”;学宋诗者如公安派、竟陵派及浙派等,多着意变化,故趋于“生新”。二者互相排斥,前后循环:“厌陈熟者,必趋生新;而厌生新者,则又返趋陈熟。”出于此,叶燮强调将两者融合:
陈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济,于陈中见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若主于一而彼此交讥,则二俱有过。(25)叶燮: 《原诗》卷三《外篇上》,丁福保辑:《清诗话》(下),第606页。
从学诗的方法来说,是模拟与新变的融合;从宗法的对象来说,是宗唐与宗宋的融合。很显然,姚鼐的观点与之相近,并且在具体的路径上,比前人有着更为精微的探讨。
姚鼐的时代,以沈德潜为代表的宗唐诗人遵从七子及王士禛遗法,重模拟;而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诗人,崇尚杨万里,且追踪公安派,凸显个性而重变化,极力批评沈德潜宗唐诗风,其《答曾南村论诗》云:“提笔先须问性情,风裁休划宋元明。八音分列宫商韵,一代都存《雅》《颂》声。秋月气清千处好,化工才大百花生。怜予官退诗偏进,虽不能军好论兵。”(26)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三,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9页。他反对诗分唐宋且是唐非宋之论,认为只要具有性情与天赋,无论什么时代都可以写出好诗。姚鼐对沈德潜并无太多评论性话语,毕竟沈氏论诗重模拟,强调有不变之法与至变之法,并通过效法前人,达到“其言自吾而立”的脱化之境(27)沈德潜:《答滑苑祥书》,《归愚文钞》卷一五,潘务正、李言编辑点校:《沈德潜诗文集》(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377页。,不过其诗模拟的成分大于脱化。而袁枚偏重变化,反对模拟,他明确说过“我道古人文,宜读不宜仿”(28)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六《读书二首》其二,《袁枚全集新编》第一册,第103页。之类的话。姚氏汲取两种诗学取向的经验与教训,将模拟与脱化结合,“镕铸”成就最高的唐宋两代之诗,力求形成第三种诗学高峰——清诗。
三、性情与学问
模拟需广泛而深入地学习前人作品,而脱化所达到的“自成一体”强调具有个人的性情面目,因此模拟与脱化分别代表的是知识与性情,而前者指向宋诗传统,后者指向唐诗传统(29)见张健《知识与抒情:宋代诗学研究》之绪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页。。严羽对本朝“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风气极为不满,推崇“吟咏性情”“惟在兴趣”的盛唐诸人之诗,他区分唐宋诗的根据就是性情与学问,唐人以性情为诗,宋人以学问为诗,前者是性情传统,后者是知识传统。王士禛追踪严羽诗学,将诗歌根植于“兴会”与“根柢”二者之上,“兴会”即“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等由性情而生的境界,根柢即“本之风雅,以导其源,溯之楚《骚》、汉魏乐府诗,以达其流,博之九经、三史、诸子,以穷其变”,强调学习前代诗歌审美经验,累积诗材、扩充识见,故他说“根柢原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30)王士禛:《突星阁诗集序》,《渔洋文集》卷三,见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三),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1560页。,根柢相当于宋诗传统,兴会相当于唐诗传统。
同时,严羽同王士禛一定程度上提出镕铸唐宋的审美理想。严羽一方面认为性情与知识二者是对立的,性情排斥学问,故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但另一方面,他意识到作诗需要知识基础,故说:“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31)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26页。调和知识与性情之间的紧张关系。王士禛也是如此,他一方面认为性情与知识“二者率不可得兼”(32)王士禛:《突星阁诗集序》,《渔洋文集》卷三,见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三),第1560页。,另一方面他又说“学力深始能见性情”(33)王士禛:《诗问》,《带经堂诗话》卷二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822页。,性情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从而融合唐宋诗之传统。当有人质疑他学宋时,他辩解道:“吾别裁不敢过隘,然吾自运未尝恣于无范。”(34)陆嘉淑:《渔洋续诗集序》,《渔洋续诗集》卷首,《王士禛全集》(一),第688页。因为恪守唐诗传统,故说“未尝恣于无范”;同时又有意识地取法宋诗,故说“别裁不敢过隘”,这也是一种“镕铸唐宋”,只不过是以唐诗为主而已。姚鼐的诗学主张同于严羽、王士禛,他说:“大抵好文字,亦须待好题目然后发。积学用功,以俟一旦兴会精神之至,虽古名家亦不过如此而已。”(35)《惜抱轩语》,《历代文话续编》上册,第401页。他也用“兴会”与“积学”来论诗,只有在积学的基础上,才能有兴会的产生,知识是性情的基础。由模拟进而脱化,将知识与性情相结合,充分学习前代诗歌的创作经验,具备一定的美学修养之后,方能“自称一家”,从而实现“镕铸唐宋”的美学理想。
清代中期诗坛,知识与性情二者处于对立的状态。宋人“以学问为诗”,将学问作为诗材与典故,知识已经成为抒情的障碍(36)张健:《知识与抒情:宋代诗学研究》之绪论,第11页。;清代乾嘉时期汉学盛行之下的宗宋诗人亦好此风,厉鹗、钱载、翁方纲等甚至以自注的形式炫耀诗中使用的僻典,造成知识淹没性情,引起时人反感,袁枚就有“抄书”之讥(37)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七《仿元遗山论诗》其三十六,《袁枚全集新编》第三册,第647页。。姚鼐并不反对“以学问为诗”,但对宗宋诗风唯见学问不睹性情之弊深表不满,他批评厉鹗以文字为诗造成的“险怪”之风为“诗家之恶派”(38)姚鼐:《惜抱轩尺牍》卷四《与鲍双五》其三:“今日诗家大为榛塞,虽通人不能具正见。吾断谓樊榭、简斋,皆诗家之恶派。此论出必大为世怨怒,然理不可易。”(《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第171页),而对融学问入性情,做到只见性情,不睹学问的诗歌,却大加赞扬。门生谢启昆学问该博,精于考据,为补朱彝尊《经义考》之阙略而撰成《小学考》,所著《西魏书》亦“博综辩论”;但作诗并不炫耀知识,姚氏读后有“空灵骀荡,多具天趣,若初不以学问长者”之感,认为这是“所蕴之深且远”所致,“非如浅学小夫之矜于一得者”(39)姚鼐: 《谢蕴山诗集序》,《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四,第55页。,是学问与性情完美的融合,远胜只讲学问、不见性情的学人之诗。正因如此,他教导弟子郭麐云:
近日为诗当先学七子,得其典雅严重,但勿沿习皮毛,使人生厌;复参以宋人坡、谷诸家,学问宏大,自能别开生面。(40)郭麐:《樗园销夏录》卷下。
前后七子及苏轼、黄庭坚诸家之诗既是作为学习对象的“知识”,同时,七子之“典雅严重”的性情与苏、黄之“宏大”的学问又勾连唐诗传统与宋诗传统,姚鼐主张先学七子所代表的唐诗传统,再揣摩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传统,在性情中融入知识,如此“镕铸唐宋”,达到“别开生面”即“自成一家”的境界。
与宋诗派只见学问不睹性情相反,性灵诗学提倡的性情是以排斥知识为前提,也同样割裂了二者的关系。袁枚反对宗宋诗风卖弄学问的“抄书”之习,而提倡性灵诗学,其理论主张有两个来源,一是杨万里“诚斋体”,袁氏“深爱”的杨万里之言是:“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41)袁枚:《随园诗话》卷一,《袁枚全集新编》第八册,第2页。此论虽主要针对沈德潜格调诗风,但考虑到“诚斋体”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对江西诗派“以学问为诗”之风气的反驳,而力求回归唐诗传统的诗学理路,则可知袁氏推举诚斋体,也是有意识地针砭学人之诗的不良风气,故他讽刺宗宋诗风云:“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42)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七《仿元遗山论诗》其三十六,《袁枚全集新编》第三册,第647页。为反对知识入侵诗歌领域,袁枚又向明代公安派借鉴,这是性灵诗学的第二个来源。公安派以李贽“最初一念之本心”的童心说为理论基础,主张性灵具有不假思索、冲口而出的自然性,因此坚决排斥“闻见道理”即知识对性情的改造(43)李贽:《童心说》,《焚书》卷三,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第98页。。出于此,在《诗经》的国风传统和雅颂传统中,袁枚更推崇前者。他说:“诗言志,劳人思妇,都可以言,《三百篇》不尽学者作也。”(44)袁枚:《与邵厚庵太守论杜茶村文书》,《小仓山房文集》卷一九,《袁枚全集新编》第六册,第358页。《诗经》中除学者所作的《雅》《颂》之外,也有劳人思妇所作之《国风》。后者没有受到“闻见道理”的干扰,因此能保存“本心”,其所言之志为真;前者受“闻见道理”的支配,在性灵诗人看来其所言之志失真。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国风》传统高于《雅》《颂》传统,学者所代表的知识传统在“言志”理论的主导下退居次位。
姚鼐既不满宗宋诗风以学问埋没性情的弊端,也反对性灵诗风为救弊而排斥知识纯任性情的主张。虽然他也意识到人之性情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全乎天者”,一是“因人而造乎天者”,但与袁枚不同,他更为肯定后者。《诗经》中“成于田野闺闼无足称述之人,而语言微妙,后世能文之士,有莫能逮”,此类《国风》之作属于“全乎天者”,其成就固不低,然仅是“言《诗》之一端”;至于“文王、周公之圣,大、小雅之贤,扬乎朝廷,达乎神鬼,反复乎训诫,光昭乎政事,道德修明,而学术该备”,此类《雅》《颂》之作属于“因人而造乎天者”,其成就“非如列国风诗釆于里巷者可并论也”。“全乎天者”为诗,“偶然而言中,虽见录于圣人,然使更益为之,则无可观已”;而“儒者之盛”,则“兼雅颂,备正变,一人之作,屡出而愈美”。两相比照之下,自可看出《雅》《颂》传统高于《国风》传统。在古今诗人中,姚鼐最推崇杜甫,因为“子美之诗,其才天纵,而致学精思,与之并至,故为古今诗人之冠”(45)姚鼐:《敦拙堂诗集序》,《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四,第49页。。天赋之才性加以后天之学问,是其成为最伟大诗人的根本条件。这种观点与袁枚针锋相对,无疑是就性灵诗学而发。
袁枚反对“闻见道理”对性灵的干扰,实际就是排斥理学对人欲的规范,其言“诗由情生”,而“情所最先,莫如男女”(46)袁枚:《答蕺园论诗书》,《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袁枚全集新编》第七册,第595页。,故肯定艳情诗。姚鼐提倡知识对性情的提升作用,以道德修养的高低衡量诗境的高下,故力诋公安派、竟陵派性情之俗,他对陈用光说:“我观士腹中,一俗乃症瘕。束书都不观,恣口如闹蛙。公安及竟陵,齿冷诚非佳。古今一丘貉,讵可为择差。”(47)姚鼐:《硕士约过舍久俟不至余将渡江留书与之成六十六韵》,《惜抱轩诗集训纂》卷五,第252~253页。指斥公安及竟陵二派不读书而造成的鄙俗之病,“古今一丘貉”中,自然包含同时代的袁枚。由于抛弃读书明理的工夫,性灵诗派津津乐道属于人之本性的“饮食男女”之大欲,而抛弃道德理性,这是姚鼐极为反感的,故特别强调读书问学对性情的提升之功,他说:“读书者,欲有益于吾身心也。”(48)姚鼐:《惜抱轩尺牍》卷六《与陈硕士》其二十六,《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第267页。此承宋儒“道问学”之工夫而来(49)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学四·读书法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1页)有云:“学问,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底已是第二义。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来。然圣人教人,须要读这书时,盖为自家虽有这道理,须是经历过,方得。圣人说底,是他曾经历过来。”此即姚鼐所云读书有益身心之意。,正因如此,姚氏对“道德修明”的《雅》《颂》诗篇推崇备至。可见,由于理论基础不同,袁、姚二人对待性情与学问之关系的认识形同水火。
姚鼐编纂《今体诗钞》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要正雅祛邪。在序中他对当下诗坛深表不满:“至今日而为今体者,纷纭歧出,多趋讹谬,风雅之道日衰。”为“存古人之正轨,以正雅祛邪”,他接续王士禛《古诗选》而选唐宋近体诗,尽管王氏此选并不完全惬于其心,但鉴于其“大体雅正,足以维持诗学,启导后进”(50)姚鼐编选、曹光甫标注:《今体诗钞序目》,《今体诗钞》卷首。,故亦推崇之。在与陈用光的信中,他再次阐述编纂此选的用意是“以俗体诗之陋,抄此为学者正路耳”(51)姚鼐:《惜抱轩尺牍》卷六《与陈硕士》其五十二,《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第294~295页。,所云其时为“俗体诗”者,直指袁枚性灵诗学及其拥趸。性灵诗学之“俗”,就情感性质而言,由于割裂性情与学问的联系,其诗歌性情品味不高(52)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二卷以“性情与学问”为标题,紧扣乾隆一朝袁枚的性灵诗学与宗宋诗人以学问为诗的对立与交融立论。本文所论,与之有联系,但亦不尽相同。。《今体诗钞》中,黄庭坚之诗因具有“兀傲磊落之气,足与古今作俗诗者澡濯胸胃,导启性灵”,故与苏轼合选一卷;陆游之诗“激发忠愤,横极才力”(53)姚鼐编选、曹光甫标注:《今体诗钞序目》,《今体诗钞》卷首。,故所收南宋一卷中以他为主。这种处理,显然是有意识地针对性灵诗派。
宗宋诗风“以学问为诗”埋没性情,性灵诗派重性情而轻学问,二者都割裂性情与学问的关系,所以均遭到姚鼐的批评,故他将厉鹗险怪诗风与袁枚浅俗诗风同视为“诗家之恶派”,为救其弊,主张将性情与学问二者融合,镕铸唐诗传统与宋诗传统,为诗学发展找到一条康庄大道。
四、高奇与蕴藉
从艺术表现来看,“从胸臆中流出”的性灵诗风至少有两个弊端,一是诗行一气直下,容易产生“滑俗”之弊;二是语言浅近,缺乏含蓄蕴藉的韵味。对于此两大病,作为旁观者的姚鼐有清楚的认识。姚鼐虽未直接点名批评袁枚,实亦流露出不满。就前者而言,在《近体诗钞》中,他对元白诗风的流弊深存戒心,评白诗云:
香山以流易之体,极富赡之思,非独俗士夺魄,亦使胜流倾心。然滑俗之病,遂至滥恶,后皆以太傅为藉口矣。非慎取之,何以维雅正哉?(54)姚鼐编选、曹光甫标注:《今体诗钞序目》,《今体诗钞》卷首。
袁枚在六十岁生日诗中就有“想为香山作后身”之句(55)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四《六十》其四,《袁枚全集新编》第二册,第538页。,所以姚鼐所指后世“滑俗”之病,无疑是针对性灵诗风的弊端。就后者而言,姚鼐明确指出,“欲作古贤辞,先弃凡俗语”,他批评其时两大诗派“浅易询灶妪,险怪趋虬户”(56)姚鼐: 《与张荷塘论诗》,姚永朴:《惜抱轩诗集训纂》卷四,第201页。,以“浅易”和“险怪”直指袁枚与厉鹗之失。性灵诗派外,王士禛及其追随者追求神韵,然格局狭小,骨力不张,滑落为诗坛边缘性存在;宗宋诗风另一趋势是朝俚俗化方向发展,又暴露出“刻露之病”(57)袁宏道:《冯琢庵师》其二、《叙曾太史诗》,《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二、三五,第781~782页、1106页。,缺少含蓄之韵味。总之,无论是宗唐、宗宋诗风,还是袁枚性灵诗派,都不能令姚鼐满意。
对于诗坛的流弊,如何力挽颓波?也是“镕铸唐宋”。姚门弟子梅曾亮评其师之诗云:“以山谷之高奇,兼唐贤之蕴藉。”桐城后学吴汝纶亦云:“先生诗勿问何体,罔不深古雅健,耐人寻绎。”(58)姚永朴:《惜抱轩诗集训纂序》引,《惜抱轩诗集训纂》卷首。“山谷之高奇”与“深古雅健”是宋诗风格,“蕴藉”与“耐人寻绎”是唐诗含蓄蕴藉的传统,二者的结合,即“镕铸唐宋”:以“山谷之高奇”救神韵诗风之弱;以“唐贤之蕴藉”救性灵诗风及宗宋诗风之浅俗刻露。
先看“山谷之高奇”。姚鼐对于矫正香山“流易”之病的诗人都甚为看重,如选李商隐诗一卷,就是因为其诗“近掩刘白”。尽管“矫敝流易”时“用思太过,而僻晦之敝又生”,但仍谓之为“诗中豪杰士”。苏轼之诗,“用梦得、香山格调,其妙处岂刘白所能望哉”(59)姚鼐编选、曹光甫标注:《今体诗钞序目》,《今体诗钞》卷首。。但因其为“天才”,常人难学,故非理想的典范。相较之下,黄庭坚诗最符合他的标准。受叔父姚范的影响,姚鼐自青年时代就喜学黄诗(60)王文治:《梦楼诗集自序》(《王梦楼诗集》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70册,第643页)云:“甲戌春至京师……与辽东朱子颖、桐城姚姬传论诗……姬传深于古文,以诗为余技,然颇能兼杜少陵、黄山谷之长。”乾隆十九年甲戌姚鼐年方二十三岁。。姚范于黄诗评价极高,他说:“涪翁以惊创为奇,其神兀傲,其气崛奇,玄思瑰句,排斥冥筌,自得意表。玩诵之久,有一切厨馔腥蝼而不可食之意。”(61)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149册,第82页。黄诗的兀傲崛奇,除去精神境界的不俗之外,艺术上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声调拗峭,以窄韵见长;用典造句奇特不凡;断裂的表面与连贯的意脉(62)参见莫砺锋《论黄庭坚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唐宋诗歌论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396~413页。。姚鼐对黄诗的用典方式兴趣不是太大,但于其押韵、对仗及以文为诗却极为用心揣摩。

在对仗方面,姚鼐亦喜学山谷体。唐诗对仗工整,为与之抗衡,黄庭坚试图以“不工”之对化唐诗的“稳顺”为宋诗的“奇特”(66)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80页。。如葛立方所举《上叔父夷仲》中的“万里书来儿女瘦,十月山行冰雪深”句,像律诗中这种“两句意甚远,而中实潜贯者,最为高作”,而“鲁直如此句甚多,不能概举”(67)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第14页。。此联上句言人事,下句言景物,事类毫不相干,意思相去甚远,从而形成远韵。姚鼐亦喜如此对仗,如“空山短日惜余景,野老长甘息机”(《题负薪图》)、“白雾乍开人入市,丹林犹缀鹤归巢”(《郡楼寓目》)、“携手故交皆好事,当头新月最怜春”(《元宵曹习庵中允家燕集》)、“牛羊落落散高垄,车马骎骎谁少年”(《漫兴》)、“浩浩东流浮积气,茫茫后死独伤心”(《临江寺塔》)等,均有意学之,虽奇特不如黄诗,但可以看出姚氏之兴趣所在。
姚鼐最喜效法山谷体以文为诗。首先是以散文句式入诗,黄庭坚尝语王直方云:“作诗使《史》《汉》间全语,为有气骨。”(68)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五“孟浩然”条,第101页。他将散句化入律诗之中,如“且然聊尔耳,得也自知之”(69)《德孺五丈和之字诗韵难而愈工辄复和成可发一笑》,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黄宝华点校:《山谷诗集注》卷一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50页。即是。姚鼐亦好在律诗中用散句,如“欲将北海同尊酒,绕尽西山到卫州”(《清苑望郎山有怀朱克斋》)、“故人揖我燕山前,送我来过清汶川。海右青山不可极,中原落日何茫然”(《漫兴》)、“泥汊绝岸菰芦风,吹逐白云如转蓬。兀兹小舟未可下,杳然叠嶂何当通”(《泥汊阻风》)、“衰年不愿海山居,愿舐淮南药鼎余”(《谢简斋惠天台僧所饷黄精》)等,此数诗姚莹赞为深得“苏、黄妙谛”(70)姚莹:《惜抱轩诗文》,见黄季耕点校《识小录》卷五,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第133页。,以散句入诗当是最主要的表征。宋诗之“雅健”,多得力于此种句法。
其次是以文法为诗。杜甫长律“运掉变化如龙蛇,穿贯往复如一线”(71)姚鼐编选、曹光甫校点:《今体诗钞序目》,《今体诗钞》卷首。,“旁见侧出,无所不包,而首尾一线,寻其脉络,转得清明”(72)姚鼐编选、曹光甫校点:《今体诗钞·五言今体诗钞》卷六,第124页。,姚鼐对此种以文之结构为诗的做法推崇备至。苏、黄从《檀弓》的“或数句书一事,或三句书一事,至有两句而书一事者,语极简而味长,事不相涉而意脉贯穿”(73)费衮撰、金圆校点:《梁溪漫志》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5页。的文法中,体悟出诗法。方东树评黄诗云:“山谷之妙,起无端,接无端,大笔如椽,转折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每每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联属,非寻常意计所及。”(74)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二,第314页。这种精妙的文法,方氏一言以蔽之曰“语不接而意接”(75)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第28页。,被桐城诗派奉为秘笈。姚鼐善于在这种断法中见出“首尾一贯”的联系,唐李从一《送王牧往吉州谒王使君叔》云:“细草绿汀洲,王孙耐薄游。年华初冠带,文体旧弓裘。野渡花争发,春塘水乱流。使君矜小阮,应念倚门愁。”纪昀讥此诗意绪承接不清,姚谓不然:“诗言此细草初绿时,一少年遽堪远游乎?三四紧承此意。五六言春盛正少年在途,其母在家思念之时,而下以‘倚门愁’作结。其意绪颇分明,不至如纪所斥。”(76)姚鼐编选、曹光甫标点:《今体诗钞·五言今体诗钞》卷七,第173~174页。他在表面看去承接不明的诗句中,发现连贯的意脉。以“连山断岭”布局,“最为文之高致”(77)苏辙:《诗病五事》,《栾城三集》卷八,陈宏天、高秀芳校点:《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29页。,姚鼐之诗,曾国藩评之云:“能以古文之法,通之于诗,故劲气盘折。”(78)姚永朴:《惜抱轩诗集训纂序》引曾国藩语,《惜抱轩诗集训纂》卷首。即就此而言。
姚鼐以奇峭的韵脚、不工的对仗、散句入律诗及以语断意连的文法为诗,形成其诗“高奇”之风貌,一改骨力不张的神韵诗风与流易的性灵诗风之弊。
不过对于苏、黄诗的不足,姚鼐亦有清醒的认识。桐城前辈张英曾比较唐宋诗之特征云:“唐诗多浑融而意常含于言外,宋诗多刻露而意必尽于言中。”(79)张英:《南汀诗集序》,《笃素堂文集》卷四,见张英撰,江小角、杨怀志点校《张英全书》(上),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15页。唐诗蕴藉,宋诗刻露。姚氏虽推崇黄庭坚,但亦发现其诗有浅直之病。黄庭坚《送彭南阳》云:“南阳令尹振华镳,三月春风困柳条。携手河梁愁欲别,离魂芳草不胜招。壶觞谈笑平民讼,宾客风流醉舞腰。若见贤如武侯者,为言来仕圣明朝。”姚评云:“结太浅直,不为佳。江西社中诸公多为此等语所误。”(80)姚鼐编选、曹光甫标点:《今体诗钞·七言今体诗钞》卷八,第333~334页。律诗尾联应宕开一笔,令人味之不尽,从而具有蕴藉之美。而此诗尾联说得平浅直白,毫无含蓄之味。救宋诗刻露之弊唯有唐诗之蕴藉,为此,姚鼐推崇初盛唐诗中的神韵之作。他称赞沈佺期《古意赠补阙乔知之》云:“高振唐音,远包古韵,此是神到之作,当取冠一朝。”推其为唐代之冠。又盛称王维七律“能备三十二相而意兴超远,有虽对荣观,燕处超然之意,宜独冠盛唐诸公”(81)姚鼐:《今体诗钞序目》,《今体诗钞》卷首。,推其为盛唐第一人。“神到”“意兴超远”即富有蕴藉含蓄的神韵,可见姚鼐最倾倒此种诗风。他主张将黄庭坚为代表的高奇之宋诗与蕴藉含蓄的唐诗相融合,故而王芑孙之诗“体用宋贤,而咀诵之余,别有韵味”(82)姚鼐:《与王铁夫书》,《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后集》卷三,第290页。,深得其赞赏。秦瀛称王氏之诗“特奇肆”,“瑰玮绝特”,铁保称之为“峥嵘傲岸,无一字寄人篱落下”(83)秦瀛及铁保序,王芑孙《渊雅堂诗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480册,第359~359页。,此是得“山谷之高奇”,是为“体用宋贤”;同时,王诗还具有含蓄不尽的“韵味”,是得唐诗之“蕴藉”,二者兼备,从而将唐诗与宋诗熔于一炉。姚氏欣赏王诗,正在于他自己也是“学玉局而不失唐人格韵”(84)徐世昌《晚晴簃诗话》卷九一评姚鼐诗云:“七古尤晶莹华贵,晚年虽学玉局而不失唐人格韵。”实际姚氏之诗不止七古,也不仅晚年,中年以后之诗,即有意识做到镕铸唐宋。,以此规避宋诗“刻露”之病。同为招贤之诗,姚鼐云:“六艺高论玉麈挥,百家杨秉莫能非。欣登云阁仍簪笔,却送春艎忆钓矶。再应征书丞相老,三为祭酒大夫稀。圣朝举欲留儒者,岂得归田志不违?”(85)姚鼐:《鱼门编修曩以一诗送仆南归今失其稿更向仆抄取因并一诗寄之》,姚永朴:《惜抱轩诗集训纂》卷八,第370页。姚氏七律“功力甚深,兼盛唐、苏公之胜”(86)姚莹:《惜抱轩诗文》,黄季耕点校:《识小录》卷五,第133页。,此诗前三联用典繁密,通首言人事而不及风景,正类苏、黄。然与《送彭南阳》末联相比,黄诗正言遇贤者而动员其出仕;姚氏则反说:朝廷用贤,贤士怎能不违背归田之志呢?黄诗言尽意亦尽,而姚诗言尽意不尽,较黄诗更具蕴藉之味。
姚鼐取黄诗之“高奇”以诊治神韵诗风之苶弱、性灵诗风之俚俗,又以唐诗之“蕴藉”弥补宗宋诗风、性灵诗风“刻露”“浅直”之弊,兼有二者,实现“镕铸唐宋”的诗学理想。
五、宏阔与幽深
姚鼐从谢启昆诗风中发现其“镕铸唐宋”之处,他称谢氏之诗“风格清举,囊括唐宋之菁,备有宏阔幽深之境”(87)姚鼐:《谢蕴山诗集序》,《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四,第55页。,将“唐宋之菁”与“宏阔幽深”并举,显然是将二者同唐宋诗相对应,也就是说,唐诗之精华在于“宏阔”之境,宋诗之精华在于“幽深”之境,谢诗囊括二者,从而兼镕唐宋诗之风格。
唐诗中亦有如孟浩然诗“空逸淡宕”“趣兴奇逸”之风,但最主要的是“雄”“壮”一类,严羽评盛唐诸公“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88)严羽:《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严羽:《沧浪集·沧浪严先生吟卷》卷一,明正德刻本。,这种风貌代表了唐诗的成就。姚鼐品题的杜审言“壮丽精切”、唐玄宗“雄秀”、王维“雄浑”、张道济“雄整”、杜甫“雄警奇变”“喷薄如江河之决”等(89)姚鼐编选、曹光甫标注:《今体诗钞》第9页、16页、29页、18页、129页、130页。,与严羽所言相同,所以“宏阔”所指为唐诗风貌。中唐以降,诗人由外在事功的追求退避为心性道德的修持;理学注重内在人格的修养境界,精神内敛的同时,对人性与物理的洞察更为深刻入微。宋诗中亦有“雅健”之风,但更能代表宋诗特征的是“平淡”之美,此乃心性的平和与淡泊所致(90)宋诗平淡之风的成因,可参见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第333~346页。,由于受不易觉察与难以把握的心性支配,故常与“深”相连,诸如“深远闲淡”“平淡而山高水深”(91)欧阳修《六一诗话》评梅尧臣诗云:“以深远闲淡为意”(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7页);黄庭坚:《与王观复书三首》其二(《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四部丛刊》第990册)。,所以“幽深”主要就宋诗而言。姚氏于此种风貌极其推崇,其评黄庭坚《题落星寺》其三云:“真所谓似不食烟火人语”(92)姚鼐编选、曹光甫标注:《今体诗钞·七言今体诗钞》卷八,第338页。;黄氏评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云:“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93)黄庭坚:《跋东坡乐府》,《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四部丛刊》第992册。是知识与胸襟积淀出苏词“高妙”之境。姚氏借用此语以评黄诗,意在胸襟为诗风之根本所在,落星寺静谧的环境、寺僧恬淡的生活,都是在审视者即诗人清闲的心境主导下才有的景象,三者共同构成“幽”而“深”的境界。好友苏去疾诗亦有此风貌,姚鼐赞叹不已道:
大抵高格清韵,出自胸臆,而远追古人不可到之境于空濛旷邈之区,会古人不易识之情于幽邃杳曲之路。使人初对,或淡然无足赏;再三往复,则为之欣抃恻怆,不能自已。此是诗家第一种怀抱,蓄无穷之义味者也。以言才力雄富,则或不如古;以言神理精到,真与古作者并驱,以存名家正统。(94)姚鼐:《答苏园公书》,《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后集》卷三,第294页。
苏去疾“高格清韵”的诗风是“胸臆”即深厚的理学修养所造就的情怀,为高超人格的美学体现,故姚氏称之为“诗家第一种怀抱”。这种人格投射在诗歌中,形成“空濛旷邈”“幽邃杳曲”的风貌,此即“幽深”。姚氏称此为“名家正统”,推崇之意不言自明。
宏阔与幽深两种境界作为唐宋诗风的典型代表,其间的对立不言而喻,但姚诗有意识地将二者融合,《题唐人〈关山行旅图〉》云:
乱山奔如涛,急水高如山。千山万水不可度,况有倚天绝地之雄关!终南东走洛与宛,剑阁岷嶓天最远。山头日落关前晚,青烟满地黄云返。栈中马足蹑重云,岩底车声行绝坂。后有舆从前建旄,孤骑席帽丝鞭操;负担汗贱且劳,耳边不断风骚骚,猿鸟悲啸兕虎嗥。青枫密竹苦雾塞,仰首始露青天高。林开地阔春陂绿,商舶渔舠牵缆续。嘉陵江水下渝州,愁听巴人竹枝曲。不道曲声悲,且说含辞苦,山头十日九风雨。君王肠断为零铃,行路谁能不酸楚。路草岩花秋复春,关山犹有未归人。丹青写尽关山怨,千古行人行不断。将身涉险岂非愚,不及田间藜藿饭。或言男儿桑弧蓬矢射四方,那得日在妻孥旁。樵夫隐士同一谷,英雄贾客偕征行。士生各有志,未易相评量。亦有进退无不可,出亦非见居非藏。苍生自待命世者,岂必栖栖求异乡。(95)姚永朴:《惜抱轩诗集训纂》卷三,第159~160页。
诗开首极力描摹关山行旅之艰辛,似李白《蜀道难》之雄豪;然“林开地阔”以下四句,景物由迷蒙灰暗突然变得清丽宛转,急促的节奏也舒缓下来。诗的后幅思考如何评价士子出处的问题,以“出亦非见居非藏”的达观稀释这一矛盾,诗人与读者的情绪至此都得到宽解。姚莹说此篇为“东坡得意之作”(96)姚莹:《惜抱轩诗文》,《识小录》卷五,第133页。,主要指后幅通达的议论而言。此诗将宏阔之境、清丽之景及平和的心境前后衔接,很好地处理两种对立风格的融合。
“宏阔”之境属于阳刚之美,“幽深”之境属于阴柔之美,“备有宏阔幽深之境”正与姚鼐憧憬的“阳刚阴柔,并行而不容偏废”的美学理想一致。姚鼐认为刚柔二者如果有其一端而绝无另一端,则“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如此“则必无与于文者”。然而他又认识到,古代最伟大的文学家,也很难做到二者毫无“偏废”,而若必偏于一端,因为天地之道尚阳而下阴,那么“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97)姚鼐:《海愚诗钞序》,《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四,第48页。。按此推理,“宏阔”的唐诗之境必然高于“幽深”的宋诗之境。但实际上,姚鼐更偏爱宋诗的平淡,如称道张五典之诗“清气逸韵,具见胸中之高亮”,汪之顺诗“清韵悠邈……而尘埃浊翳无纤毫可入”,左兰成“孤清远俗,真诗人性情”(98)分别见《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四《荷塘诗集序》、《文集后集》卷一《梅湖诗集序》、卷二《左兰成诗题辞》,第51页、264页、288页。,等等。不过因受苏轼“绚烂之后归于平淡”之论的影响,他所说的幽深,是与宏阔相结合的幽深。他认为高常德之诗“贯合唐宋之体”,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思力所向,搜抉奇异,出以平显”(99)姚鼐:《高常德诗集序》,《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四,第47页。,“搜抉奇异”指向宏阔,而“出以平显”指向幽深,入手起于绚烂,终点归于平淡,正与苏黄之论相合。在与王芑孙的信中,他又说:
古人文章之体非一类,其瑰玮奇丽之振发,亦不可谓其尽出于无意也;然要是才力气势驱使之所必至,非勉力而为之也。后人勉学,觉其累积纸上,有如赘疣。故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语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100)姚鼐:《与王铁夫书》,《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后集》卷三,第289页。
“瑰玮”与“平淡”两种文境中,他更为推崇后者;然这种境界,是历经“搜抉奇异”之后,自然生成的境界,内涵了“瑰玮奇丽”之境。姚鼐的审美理想与真实的审美趣味之间,表面上有偏离,实际有内在的一致性。
袁枚论诗亦重刚柔相济,他说:“诗虽奇伟,而不能揉磨入细,未免粗才。诗虽幽俊,而不能展拓开张,终窘边幅。有作用人,放之则弥六合,收之则敛方寸,巨刃摩天,金针刺绣,一以贯之者也。”(101)袁枚:《随园诗话》卷三,《袁枚全集新编》第八册,第90页。相较之下,他也偏重柔胜,在规劝好友祝德麟时,他一方面说“圣贤之学,刚柔并用”,另一方面又说“然而柔克之功,较胜于刚克”,祝氏之诗的缺点正是“能刚而不能柔”(102)袁枚:《答祝芷塘太史》,《小仓山房尺牍》卷一,《袁枚全集新编》第十五册,第229页。。他肯定蒋士铨诗“气压九州”,又批评其“能大而不能小,能放而不能敛,能刚而不能柔”(103)袁枚:《随园诗话》卷三,《袁枚全集新编》第八册,第90页。,有其一而不能糅合其对立面。重刚柔相济,又偏于阴柔之美,姚、袁二人美学理想极为一致。
袁枚与姚鼐提倡刚柔相济的诗风,是出于对诗学史的反思。前后七子诗学盛唐而至“粗豪”,“无沉着、冲淡意味”(104)李开先:《咏雪诗序》,《李中麓闲居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41册,第12页。;七子后学“浸成格套,以浮响虚声相高”(105)袁中道:《阮集之诗序》,《珂雪斋前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75册,第569~570页。;王士禛救之以神韵,又变而为“虚响”(10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御选唐宋诗醇》提要,第1728页。;沈德潜救之以格调,却显“谨而庸”(107)管世铭:《读雪山房杂著》,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另一方面,清代宗宋诗人学苏、陆者如吴中诗派走上“有队仗无意趣,有覂逸无蕴藉”(108)沈德潜:《王凤喈诗序》,《归愚文钞》卷一四,《沈德潜诗文集》(三),第1359页。之途,学黄庭坚者或流于秀水派朱彝尊之“枯瘠无味”(109)郭麐:《樗园销夏录》卷下。,或遁入浙派如厉鹗之“险怪”。总之,欲救一弊,一弊又生。有鉴于此,袁枚、姚鼐欲以刚柔相济的美学理想了结诗学史上循环往复出现的弊端。
袁枚诗歌创作与理论有很大的偏差。他推尊《国风》传统,阐扬钟嵘《诗品》的性情诗学,宗尚白居易闲适诗风,青睐杨万里的诚斋体诗,又与公安三袁心源遥接,在这些传统的作用下,其诗之得失正如尚镕所评云:“学前人而出以灵活,有纤佻之病。……子才笔巧,故描写得出……然描写而少浑涵。”又云:“子才专尚性灵,而太不讲究格调,所以喜诚斋之镂刻,而近于词曲。……律诗往往不对,盖欲上追唐人高唱也,然失之率意矣。”(110)尚镕:《三家诗话》,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920~1921页、1922页。其性灵诗风“纤佻”“少浑涵”,缺乏唐诗“宏阔”之境;“刻镂”“率意”,又少宋诗“幽深”之境。其本人如此,性灵诗派末流的情况可想而知。姚鼐亲见袁枚及性灵诗派之失,以及诗学史不断上演的流弊,故而力倡阳刚阴柔相济的美学理想,主张兼镕“宏阔”与“幽深”的唐宋诗之境,将诗学史上优良的传统熔于一炉,以形成超越前代,独树一帜的诗学风貌。
六、余 论
前后七子意识到中唐之变在中国诗史上的转折意义,决然发出“诗自天宝以下,俱无足观”的论断,他们排斥中唐以下的诗歌传统,重倡自《诗经》至盛唐意与境谐的审美传统。而公安派有感七子及其后学宗唐诗风的弊端,加之受童心说及市民阶层思潮的影响,转而提倡“宁今宁俗”的诗风,以白居易、苏轼为宗法对象。至此,以宗唐为代表的雅正诗风与宗宋形成的俚俗诗风之间的对垒成为古典诗学解决的重要问题。姚鼐无疑是崇尚唐诗传统的,但他也认识到一味宗唐的弊端,所以有选择地向宋诗传统寻求治病良方,他从苏轼、黄庭坚及陆游等诗中窥见新因素,以精审的学问、高奇的技巧及幽深的风格弥补宗唐诗风的空虚、平熟及浮浅,又以真挚的性情、蕴藉的艺术与宏阔的境界弥补宗宋诗风的险怪、浅直与枯寂,由此实现“镕铸唐宋”的理论祈向。清代不管是宗唐诗人还是宗宋诗人,都不会视对方为绝对的对立面,而是有意识地适当吸取精华,以规避宗法对象自身无法解决的缺陷。
唐诗与宋诗为中国古典诗学树立了两座高峰,自宋代以后,诗人或者宗唐,或者宗宋,而无法找到超越唐宋的第三条诗路。清人较元明两朝诗人有着更为远大的抱负,他们有意构建本朝诗风,在找不到更好出路的前提下,鉴于前代诗史,便镕铸唐宋两朝诗歌精华,取双方之长,补双方之短,力求由此形成来源于唐宋诗而又独立于唐宋诗之外的另一座诗歌高峰。此由王士禛、叶燮始,袁枚、翁方纲、姚鼐等人追踪前贤,亦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尽管清人并未真正实现这一理想,但不能抹杀他们曾经做过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