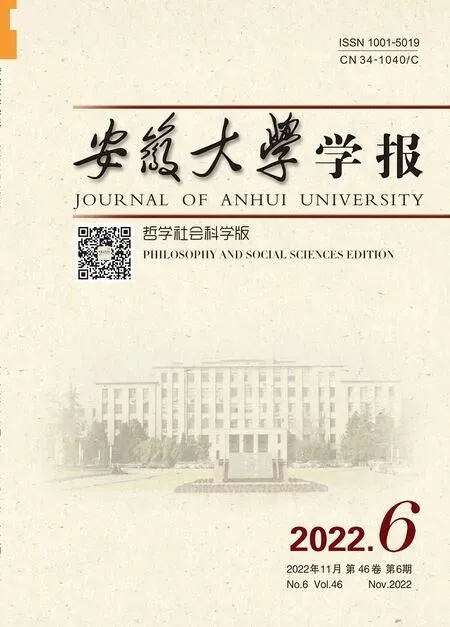安大简《诗经》中的“蟡”字试析
侯乃峰
一、安大简《诗经》中的“蟡”字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公布了一批战国《诗经》竹简(以下简称“安大简《诗经》”)。这是迄今为止可以见到的最早的《诗经》抄本,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安大简《诗经》中,出现了三个原整理者隶定为“蟡”的字,字形列举如下:



三个字所在文句的辞例都是“蟡=它=”,即“蟡它”之重文,皆对应今传本《毛诗》的“委”字,毫无疑问这是同一个字。原整理者于第31简注释说:
蟡=它=:《毛诗》作“委蛇委蛇”。“蟡”“它”二字后有重文符号。“蟡它”,叠韵联绵词。《韩诗》作“逶迤”。“蟡”属匣纽歌部,“委”“逶”属影纽微部,影、匣同属喉音,歌、微二韵亦很近,《诗经》中有大量歌、微合韵的现象,可资佐证。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卷十九“逶迤”注引“逶”又作“蟡”。“它”,“蛇”之初文。古从“它”者多与从“也”通,故“蛇”“迤”可相通(参《古字通假会典》第六七八页)。毛传:“委蛇,行可从迹也。”郑笺:“委蛇,委曲自得之貌。”此句指行步之姿态。(2)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90页。
于第87简注释说:
蟡=它=:《毛诗》作“委委佗佗”。简文此句又见《羔羊》。“蟡”,从“虫”,“为”声,《说文》“逶”之或体。“蟡=它=”,有重文符号,《鲁诗》作“袆袆它它”,《韩诗》作“逶迤”。“蟡它”“委佗”,即“逶迤”,联绵词,行走之貌。简文当从于省吾说,读为“逶迤逶迤”(参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第一二至一三页)。(3)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30页。
也就是说,原整理者将此字隶定为“蟡”,字形分析成从“虫”“为”声。
如果仅从字形出发进行严格隶定,这种处理方式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如果从古文字形体演变的角度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蟡”字当是一个由于形体割裂讹变而产生的分化字,直接隶定为“蟡”其实并不是十分妥当。
《说文》:“逶,逶迤,衺去之皃。从辵、委声。蟡,或从虫、为。”即“蟡”字在《说文》中没有单列字头,而是作为“逶”字之或体出现。清人王筠认为《说文》以“逶”“蟡”为一字不可信,他在《说文释例》中说:

王筠认为见于《说文》的“蟡”字是后人所增,据小徐本《说文》原无“蟡”字来看,《说文》原本并没有这个字;“蟡”字的形体,也是后世因“逶迤”词形有作“蜲蛇”者,故类化添加“虫”旁而成。现在根据安大简《诗经》来看,“蟡”字形在战国简中已经出现,且正好对应今传本《诗经》“逶迤(委蛇)”的“逶(委)”字,可见《说文》以“逶”“蟡”为一字之说自有所本,许慎应当是见到过典籍文献中以“蟡”为“逶”的用字现象,故将“蟡”字作为“逶”之或体。王筠认为“蟡”字是后人所增的看法是不对的。

二、“蟡”字的形体来源蠡测
“蟡”字,又见于传世文献《管子·水地》:“涸川之精者生于蟡。蟡者,一头而两身,其形若虵(蛇),其长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鱼鳖。此涸川水之精也。”(6)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915页。这段文字事涉玄虚,蟡似是随文造字,当与战国古文字材料中所见的“蟡”字关系不大。后世字书如《玉篇》等多引《管子》此文“似蛇”云云以释“蟡”字,很可能只是单纯的因袭旧文,不足采信。我们如此推测,是有较为充分的证据的,具体详见下文。
大徐本《说文》将“蟡”字作为“逶”字的或体,而没有单列字头,是不是许慎由于疏忽而漏收呢?我们认为,实际情况应该不是这样的。具体说来,“蟡”字其实当是大约战国时期由“为”字形体割裂讹变而分化出来的一个古文字形,原本并不存在;“蟡”字形的产生,当是古人出于异体分工的需求,让其分担“为”字部分表义功能的结果。要说明这个问题,需要先从“为”字的古文字形体演变过程谈起。
“为”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写作从又、从象,会以手役象以助劳其事,即作为之意(7)季旭升:《说文新证》,台北:艺文印书馆,2014年,第194页。。甲骨文的“为”字,有一种将大象的尾部特别突出表现写成分叉状的字形,如:



到金文阶段,“为”字的这种写法继续保留下来,如:



















我们知道,楚系简牍中所见的“象”字,有写成省去身体部分的笔画,只保留头部象鼻形和下部尾巴形笔画(多写作二重分叉状)的写法,如:





安大简《诗经》中的“象”字,还有将身体部分的笔画与尾巴形笔画近乎重合在一起的写法,如:



尤其是第44简的字形,如果没有其他的“象”字形作参照,下部的笔画几乎分不清究竟是大象身体部分的笔画还是尾巴部分的笔画。若是古人书写之时稍有草率,省略掉左上部的一撇笔,则就与上引第31简“蟡”字形右部的写法差不多了。

以上列举的字形中所见的繁复写法的“象”字,下部分叉状的尾巴有的写成两重,有的写成一重。可以设想,在战国文字系统中,如果“为”字所从的“象”写成上举楚简中所见的那种省去身体部分的笔画,只保留头部象鼻形和下部的分叉状尾巴形笔画,同时分叉状尾巴形仅写成一重,则就会出现如下字形:





综上可见,在战国楚简文字中,将分叉状尾巴形的笔画割裂出来,写成类似古文字“虫”字旁的现象是很常见的。此种讹变现象正可以与战国文字中将“为”字所从的大象之分叉状尾部的笔画割裂出来隶定成“虫”旁,从而将字释为“蟡”进行类比。
三、《说文》视“蟡”为“逶”字或体原因之推测
根据以上所列举的现象我们可以确信,战国楚系简帛文字中那些所谓的“蟡”字,原本就是“为”字形,下部所谓的“虫”旁其实是表示大象分叉状尾部的笔画,根本就不需要隶定的。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许慎在编纂《说文解字》之时没有将“蟡”字单列字头了。因为到了东汉时期,许慎当时所能见到的典籍文献大都应当属于今文经学系统的文本,其中大概根本就不存在出现于战国古文系统的“蟡”字。追根溯源,战国古文中所见的“蟡”字形,其实都应当是“为”字形割裂讹变而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许慎在《说文》中没有把“蟡”字单独列为字头,显然是有道理的。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安大简《诗经》中所谓的“蟡”字,其实是“为”的后起分化字,其所从的“虫”旁其实是“为”字形中表示大象分叉状尾部的笔画割裂讹变而成的,可以直接隶定成“为”。战国文字材料中,“蟡”字形已经分化出来,分担了其所从出的母字“为”的部分表义功能,如读为“化”、用为“逶”若“委”等。但这种分化进行得并不彻底,最终“蟡”没有成为富有生命力的通行字进入秦汉时期的文字书写系统中去。随着秦朝“书同文”政策的推行,作为战国古文写法的“蟡”字被废弃,只保留在战国古文系统的文本中。许慎在编纂《说文》时,当是根据古文系统的典籍文献里类似安大简《诗经》中用“蟡”为“逶”的现象,将“蟡”字看作“逶”之或体,而没有将“蟡”字单列字头,自有其道理。端赖安大简《诗经》的出土,为我们重新认识“蟡”字的形体来源及其与“逶”字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条件。
ATextualAnalysisoftheAncientCharacter“Gui(蟡)”inTheBookofSongsRecordedonBambooSlipsintheWarringStatesPeriodCollectedbyAnhuiUniversity
HOUNaifeng
Abstract: InTheBookofSongsrecorded on bamboo slip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ollected by Anhui University, there are three characters written as “Gui(蟡)”.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the three characters written as “Gui(蟡)” should be directly assigned to “Wei(为)” as its later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s. In the materials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character “Gui(蟡)” has been differentiated, sharing part of the semantic function of the “mother character” of “Wei(为)”. It is thereby understandable that Xu Shen regarded “Gui(蟡)” as a variant of “Wei(逶)”inOriginofChineseCharacterswithout listing “Gui(蟡)” as a separate Chinese character.
Keywords:TheBookofSongsrecorded on bamboo slip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ollected by Anhui University; Gui(蟡); Wei(为);Wei(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