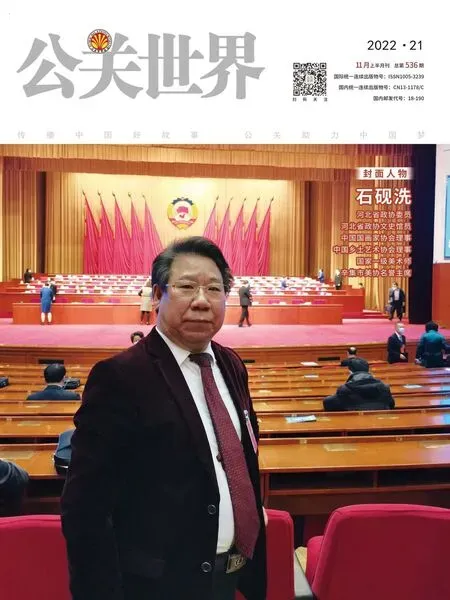媒介事件的集体记忆建构研究
——以“1981女排世界杯夺冠”为例
文/姜楠 王旭宁 赵京阳 周朝霞
一、问题的提出
研究小组作为21世纪的00后的在读大学生,对1981年中国女排世界杯夺冠这一事件关注始于一位研究小组成员所讲述的家中长辈的故事。那位长辈对中国女排有着近乎于狂热的喜爱,虽然年事已高,但是仍坚持学习新媒体知识,只为上网了解女排相关资讯。经过调查研究,研究者发现1981年中国女排世界杯夺冠是中国在世界篮、排、足三大球的比赛中第一次荣获世界冠军的称号,是我国在体育竞技领域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开创了中国女排的新纪元,拥有空前的影响力,振奋了亿万国人。每每提及女排夺冠,人们眼前总是能浮现当时女排姑娘力克对手最终手捧奖杯登上领奖台的画面,心中涌起骄傲的情感。更重要的是,这些体验并不局限于那些坐在收音机或电视机前见证历史者,也扩散到事后才出生的数字时代原住民。换言之,1981年中国女排世界杯夺冠不仅在亲历者脑海中打下深刻的烙印,也进入了公共记忆,塑造着一代又一代国人的民族国家认同,成为一项重大的媒介事件。
本研究试图以1981年中国女排世界杯夺冠此项媒介事件为例,对比个体记忆与实时赛况,来探究电视媒介如何构建集体记忆,并从个体参与中理解媒介与媒介事件在家庭、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影响。其中访问对象的组成:Y(男,77岁,浙江台州人);N(女,80岁,浙江台州人);J(男,79岁,浙江湖州人)。
二、“媒介事件”概念界定
戴扬与卡茨提出:“媒介事件”是指 “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是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可以称这些事件为 “电视仪式”或 “节日电视”,甚至是“文化表演”。[1]在直播与观看的过程,类似于涂尔干所说的 “仪式”。同时戴扬和卡茨还提出了媒介事件的三个“基本脚本”或三种基本类型:竞赛、征服和加冕。媒介事件堪称电子纪念碑,仿佛注定进入集体记忆。在“历史的现场直播”中,大规模的媒体报道和节日般的观看往往会在公众心目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乃至变成个体生命与世代的分水岭。[2]戴扬和卡茨在《媒介事件》中还提出了一个论断:“进入集体记忆的并不是原始事件,而是电视呈现的‘历史性’版本。电视会在根本上改变大多数事件,让它们在亲身参与事件的人们眼中变得面目全非”,而这些重大事件的首要效果,以及它们在集体记忆中的位置,多半系于广播出来的版本,而不是最初搬演的版本”。[3]
三、媒介事件构建集体记忆
1.媒介事件的信息获取与参与
(1)广播、报纸到电视。通过采访发现,两对受访者均通过报纸、广播到电视获取女排赛事信息。84年以前,主要获取信息的渠道是报纸和广播,受访者J提到“报纸我那时候也看的很多。湖州日报之类的,都有登女排夺冠,我都看了”。但据受访者反映,对于这一时期的体育赛事记忆没有购买电视后清晰。当被问及对1981年女排世界杯夺冠的印象时,受访者Y表示“因为81年我们没电视机,也是听广播、以后看报纸、看资料,没有后面看电视的印象深了。”两对受访者家中的电视都是1984年购买的上海金星牌12寸(或14寸)电视,售价为430元,约是一名普通职工十个月的工资。
(2)解说员的影响。据采访得知,受访者Y对五连冠中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夺冠印象最深,一个主要原因是该场比赛的解说员是宋世雄。受访者对其情绪饱满、仿佛身临其境般的解说评价极高,“他确实比其他人好,我们印象当中确实是他最好,他会把观众代入到比赛当中去,随着比赛的输一个,胜一个,他都会讲得清楚,就好像你直接参加比赛,在现场看到一样的”。这样的解说有助于受众对媒介事件的记忆与情感纽带的激活。
(3)主动参与。80年代,由于文娱生活匮乏,体育赛事成为消遣解闷的一种渠道。而除了消遣,看女排“为国争光”也是受众主动参与媒介事件的重要原因。受访者Y表示“自从那个中国女排81年取得冠军以后,第一次取得冠军以后啊,是在日本举办的,对中国女排的喜欢程度啊,马上就上来了”。在体育赛事背后,蕴含着国家之间的竞争。受访者对中国与美国、日本对阵的女排比赛印象格外深刻,情绪也格外激动。而在对女排精神的询问中,受访者J认为“女排精神就是为国争光。打出了国威,为国争光添彩”,受访者Y也认为“女排精神是国家强盛的象征”。另外,作为一名女性劳动者,受访者N觉得女排夺冠是“给妇女同胞争气”的一种象征,这激励了她在日常生活中的生产实践。
(4)家庭场景。两对受访者均在家中观看女排比赛。受访者N提到,那时单位的电视主要用来看电影,家中购买电视后,会有邻居前来看电视剧,但没有人来一起看排球比赛。排球比赛成为夫妻工作、带孩子之余的一种放松方式,也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未来几十年的共同话题与共同兴趣,正如《媒介事件》一书中提到的,“家庭成员一起体验事件,因而加强了群体记忆及代与代之间的关系”。[4]两对受访者均表示五连冠是当时周边热议的社会话题,不仅家庭会对胜利表示兴奋,在单位也是个热门话题,“觉得中国在世界大赛中排球能够拿到冠军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2.电视媒体塑造媒介事件的关键因素
首先电视媒体发布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具有相应的量化标准和要求,在类似的传播过程中或者宣传视频需要产生一定的高潮,并且最大程度上达到触发观众的情感,因而需要突出与强调电视传播的有效性和议程设置。由于在传统媒体时代,收视率和完播率在预测和监测传播效果中处于支配地位,因而这也要求电视从业者一方面在相关媒介事件的节目制作上不仅仅要求收视率的保证,而且另一方面通过对于收视率和完播率的分析观察来调整相关媒介事件的话题塑造和引导。
其次在收集电视媒介事件的舆论反响过程,媒体从业者主要在于通过预判的方式来猜测传播效果,当时舆论和反响的预判主要是通过所谓收视分钟率来预判影响有多大,由可视化的数据可以让有大量经验的工作人员根据收视率去预判和调整相关节目的播放和议程设置。甚至可以预判观众在第几分钟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反映,但具体的舆论情况不得而知,观众一般都通过电话访谈的形式来呈现舆论,因此电视时代也是数据时代,数据就可以让媒介事件更加地达到共鸣的效果。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舆论收集的方式,就是早期的论坛会建立关于媒介事件的话题,类似于今天新媒体环境下类似于微博等社交媒体的话题等。
其次从议程设置的角度来探讨,在以电视等为主导媒体的社会背景下,社会大众与电视媒体会产生共识,首先是社会大众不仅会对媒体产生一种信任感,以及媒体传播的信息,在议程设置上观众会自然而然跟随媒体报道的走向,并且对于重大的媒介事件舆论也不大可能产生舆论撕裂的状况,换而言之,由于当时媒体环境较为单一,媒体场域较不复杂,虽然记者或者编辑对于收视率具有相关的要求,但是从业者们会很严格地按照职业分寸谨慎地去选择他们想传达的信息,因而两方面都决定了舆论是趋向于单一化的。当时的电视人职业操守非常强,并不会像当今新闻生产场域的背景下,部分自媒体从业者为了相应经济利益而毫无下限,博人眼球故意制造舆论风口。正是传统电视时代由于人们所接触的媒介和信息是非常有限的,接受信息的渠道十分单一。因此更好有利于女排夺冠的记忆塑造与传播。
3.受众自我选择对媒介事件的作用
(1)对胜利的夸大。受访者对中国队的胜利记忆存在夸大成分。1981年中国女排世界杯夺冠赛,对手是日本队,比分是三比二,而在受访者J的记忆中,比分是三比零。另外,受访者J对2008年中国女排奥运会的成绩记忆也有夸张,将季军记为冠军。这种记忆的夸张,可能是出于受访者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与对中国女排的信任。
(2)对“牺牲者”角色的喜爱。中国女排的粉丝,受访者N表示,她在五连冠期间最喜欢的女排队员是陈招娣,原因是她很能吃苦,“她多次受伤的,多次受伤都拼命打的。她死了以后,骨灰火化以后,都还有钉子拿出来,好几枚七八枚钉子钉着的。有一次比赛打好之后她上飞机都上不去,人家把她扶上去。这样子的情况下都还在打,特别能坚持”。而受访者N对于女排精神的理解也是“能吃苦”。在80年代,以奋不顾身的姿势投身群体建设中的形象饱受赞扬。
(3)对“本地人”的特殊记忆。受访者J与受访者N均为浙江人,他们喜欢的女排队员周苏红、陈招娣也是浙江人。这或许表明地缘关系上的亲近会影响受众对媒介事件的记忆深度与记忆范围。
结语
1981年中国女排世界杯夺冠作为一项重大的媒介事件,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而且1981年第三届女排世界杯的决赛地点位于日本大阪体育馆,而决赛阵容更是中国队对阵东道主日本队,这场比赛不可避免地被染上家国情怀和政治色彩。而1981年中国女排世界杯夺冠这一媒介事件也可以说是融合了竞赛和加冕这两大 “基本脚本”,有着独特的历史性意义。并且也通过女排夺冠这一媒介事件作为一个较小的切入点,有代表性地由浅入深地探讨了媒介事件从信息生产者的角度,以及观众的角度来分析。媒介事件体现了政治、心理、态度,也反映了媒介的进步和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