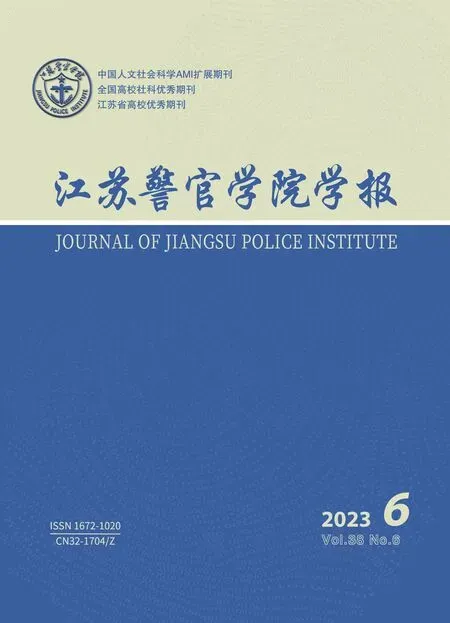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化理据及其条件展开
张健一
一、问题的缘起
泰森在世纪之战中恶意咬伤霍利菲尔德、谭望嵩在奥运会比赛中飞踹波科尼奥利、詹姆斯在抢篮板球卡位时挥肘“招待”斯图尔特……在诸如足球、篮球、拳击等对抗性竞技体育活动中,运动员受伤甚至死亡的事例已屡见不鲜。通常情况下,无论这些行为是否造成重大伤害,惩戒机制都会谨守“行业自洽”原理,以驱逐出场、罚款、禁赛为核心的制裁体系原则上排斥了刑法的介入。不过,虽然恪守最后手段法的基本定位,刑法应谦抑处罚冲动;但秉持整体法秩序保障法的规范品格,刑法也不能无动于衷。揆诸当下,学界虽在刑法有限介入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上达成共识,但在介入的界限上却莫衷一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未能彻底贯彻立足正当化理据建构正当化条件的方法论逻辑,而是从事实出发,经验性地建构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化条件;其二,基于法教义学路径来讨论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正当化理据的书斋式研究较多,结合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具体样态的接地气思考较少;其三,有关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主观正当化条件诉讼证明的研究浅尝辄止,削弱了实体标准的可信度。
以刑事一体化视角审视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立法,迫切需要在价值上奠定根据、技术上厘定标准、证明上构建路径。本文首先检视了实体法上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化理据,追问造成他人伤害乃至死亡的竞技体育行为为何能出罪。进而,立足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型构其正当化条件。最后,结合对抗性竞技体育行为的特质,探讨其主观正当化条件的司法认定问题。
二、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化理据
(一)社会相当性理论
社会相当性理论主张,竞技体育中所包含的伤害风险已被社会一般人的普遍观念、社会伦理秩序所接受,用体育规则处置、排斥刑法介入的方法已被公众认可。①黄佳鑫:《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刑法规避与规制》,《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4 年第2 期。该说初为阻却行为构成要件符合性所创,后因其极强的包容性而发展为行为无价值论正当化事由的通理。然而,将其适用于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时,却难掩论理的粗糙。其一,将作为正当化事由统一原理的社会相当性理论不加剪裁地适用于下位的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既有种属失调之嫌,又无法立足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特征而为型构其正当化条件提供指引。其二,为社会伦理秩序所容许构成了行为相当性的内核。然而,在后工业时代、风险时代、数字时代并存的当下,社会伦理本就迭代更新、变动不居,其在市场化、商业化等外力裹挟下的竞技领域更是日渐模糊。其三,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因其社会相当性而正当化,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也可因具备社会相当性而正当化。既然正当化理据无差异,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正当化条件当无差别,但这又不符合现实情况。
(二)正当业务学说
在正当业务学说看来,对于大力士摔跤、拳击手格斗等造成的伤害,只要行为遵守了相关竞技体育规则即属正当业务的范畴,就应排除行为的故意伤害违法性。日本刑法关于“正当业务行为,不罚”的规定是该说的有力论据;②[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232 页。我国刑法理论通说对此亦持肯定态度。③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版,第128 页。但是,形式上规范的说辞难掩其实质上的困顿:其一,本末倒置。正当业务学说与其说是关于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正当化理据的思考,不如说是对该类行为正当化条件的探索。然而,只有在价值层面释明了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化理据,才能够确定哪些致人伤害的竞技体育行为可以被正当化。其二,由于正当的行为在竞技体育领域即表现为合规行为,因而“遵守了相关竞技体育规则即属正当业务”有同语反复之嫌。
(三)被害人承诺理论
被害人承诺理论主张,规则范畴内的过失运动伤害因参与者同意而合法化,但故意或严重过失违反规则导致的伤害除外。④林亚刚、赵慧:《竞技体育中伤害行为的刑法评价》,《政治与法律》2005 年第2 期。美国《模范刑法典》规定,因身体伤害被指控的犯罪,可将行为发生于危险能够被合理预见的合法竞技运动领域作为抗辩事由。⑤刘仁文:《美国模范刑法典及其评注》,法律出版社2005 年版,第40~41 页。毋庸置疑,被害人承诺理论具有尊重事实的品格,例如,当WWE 运动员走上拳台就意味着对身体伤害的默示承诺。由于尊重事实的理论品格恰好契合公众的常态化认知,被害人承诺理论顺理成章地成为竞技体育正当化根据领域的通说。然而,该说也同样遭受着质疑:其一,挂一漏万。该说只对以攻击对手身体为胜负标准的竞技行为如拳击、相扑有解释力。在足球、篮球等不以攻击对手身体为胜负标准的竞技行为中,运动员只是承诺了竞技运动导致的受伤危险而非实害结果。其二,规范悖论。我国民法典第1176 条规定,自愿参加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致害的,除加害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外,受害者不得向加害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可见,主观过错而非被害人承诺厘定了正当竞技体育行为与侵权行为的界限。其三,学理冲突。基于“有限父权主义”,被害人对重伤、死亡的承诺无效。因此,该说无法解释诸如班古拉事件①在2006 年中超比赛中,沈阳队外援班古拉被青岛队吕刚踢中左眼并导致永久性失明。等严重伤害行为何以不受处罚。
(四)容许风险理论
该理论以交通运输领域为切入点,主张对遵守特定行业规则、具有法益侵害危险性的行为,应根据其对社会发展的有用性,阻却犯罪的成立。有学者认为,“允许性风险理论能够对具体的体育竞技行为提供以保护法益为导向的有限制的解说”。②罗嘉司、王明辉:《竞技致损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及刑罚边界》,《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 年第4 期。不过,虽然该理论嫁接了社会学知识来解释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勇气可嘉,却也面临着质疑:其一,容许风险理论与风险社会研究相伴相生。然而,风险社会理论导源于科技发展、财富生产招致的新型风险,③[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关于人类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等问题的思考》,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 年第3 期。并未涉足竞技体育领域。其二,解释学的任务是为立法容许的风险行为找寻正当化根据。诸如疫苗临床试验、交通运输等活动的确存在侵害法益的危险,立法政策之所以容许是因为其有益于疾病防控或经济发展。然而,倡导将容许风险理论引入竞技体育领域的理论叙说,却未能进一步阐释为什么遵守比赛规则的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应被容许。其三,容许风险理论秉持比较衡量行为危险性与有用性的方法论逻辑,这虽与功利主义哲学的优越利益原理一脉同源,却未能借助功利主义哲学方法论深刻阐释该类行为的有用性及其优先于行为危险性的界限。
(五)综合说
以单一说的理论瑕疵为基点,该说主张综合运用正当业务说、危险接受理论与优越利益原理建构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化理据。其中,正当业务说旨在将竞技体育伤害问题的论域限定于合规行为,危险接受理论与优越利益原理则以运动员接受了伤害危险、存在优越于运动员身体健康的体育利益为由,主张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可以被正当化。④钱叶六:《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及边界》,《法学家》2017 年第3 期。然而,综合说看似兼容并蓄,实则饾饤堆砌。其一,从正当化理据的来源角度看,既然国家认可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是正当业务或追求优越利益的方式,为何还要寻求运动员对危险的接受?反之亦然。其二,从综合说内部的关系角度看,以行为系正当业务为前提,在竞技比赛致人轻伤时,适用危险接受理论;致人重伤时,适用优越利益原理。可见,构成该说的三个要素之间并无基于统一价值、特定逻辑的顺位关系,只是基于不同事由的简单堆砌。其三,从构成要素角度看,危险接受理论与事实相悖。危险接受理论主要为行为无价值论者所倡导。据此,以危险接受理论正当化竞技体育伤害行为,需要运动员在比赛时对身体伤害风险及其关联的实害结果、加害者对受害者的同意均有认知,而这在激烈的对抗性竞技过程中几无可能。
(六)优越利益原理
该说主张,在竞技体育场合,之所以容许重大伤害乃至死亡结果,根本上还是基于存在着“振兴体育”这种优越的利益。⑤[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4 年版,第160 页。该说招致一系列不合理的批评。其一,“竞技体育伤害行为侵犯个人法益,体育事业是超个人法益,二者无法比较”。⑥吴玉萍:《竞技体育行为与体育暴力行为界分的刑法考察》,《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 年第3 期。然而,以超个人法益优越于个人法益为根据的制度设计俯拾皆是。例如,警察依法执行逮捕就意味着公务行为秩序优越于个人人身自由;再如,设置潮汐红绿灯是在顺畅的交通秩序与其他车道个别车辆通行权的对立中选择了前者;又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关于明显超出合法收入部分财产非法性的推定,是以克减国家工作人员个人权利的方式舒缓公诉机关的证明责任,实现打击贪腐犯罪的价值诉求。在竞技体育领域,基于维系对抗性的考量,有限伤害原则被普遍认可,这成为优越利益原理的有力“背书”。其二,“没有取得保护竞技体育的发展与保护运动员个人法益的平衡”。①王桢:《论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刑法规制》,《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4 年第4 期。这种指责有张冠李戴之嫌。优越利益原理致力于回答竞技体育伤害何以被正当化,至于为衡平体育事业与运动员人身法益构建标准,则是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化条件课题。其三,“没有适当考虑社会伦理规范,容易导致为保护较大法益不择手段损害较小法益”。②[日]大塚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141 页。然而,“在传统伦理学中,无伤被许多学者看成是具有核心意义的一个道德准则”。③刘雪丰:《论竞技体育的有限伤害伦理准则》,《文史博览》2007 年第2 期。若考虑社会伦理规范,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将无论如何都不能正当化。但这既不符合事实,又背离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24 条规定,国家促进竞技体育发展,鼓励运动员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在体育竞赛中创造优异成绩。据此,“振兴体育”以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创造优异成绩为核心要义。优异成绩是衡量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外在指标,提升体育运动技术水平是追求优异成绩的内在尺度。笔者以下从三个维度阐释优越利益原理之所以能成为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化理据,并回答为何较之于运动员的身体伤害(风险),“振兴体育”居于价值优位。其一,“暴力性是竞技体育的固有属性”。④曲伶俐、吴玉萍:《竞技体育暴力行为的刑法解读》,《山东社会科学》2010 年第3 期。作为战争的替代物,对抗性竞技体育活动是规范化人类发泄情绪的方式之一。竞技体育运动中,由身体对抗带来的视听体验可以有效舒缓公众在日常压力下不断积聚的攻击冲动,避免其外化为越轨乃至违法行为。同时,既然竞技体育身体对抗并非毫无节制而必须受制于体育规则,而体育规则又以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为价值追求,那么,较之于运动员的身体伤害(风险),“振兴体育”居于价值优位也就不难理解。其二,体育比赛规则容许竞技体育危险行为,恰是基于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优越于竞技体育危险的考量。竞技体育危险行为与超凡的体育技艺往往是相伴相生的。其三,对抗性竞技体育比赛中,机会转瞬即逝,运动员凭直觉行事的情形并不鲜见。例如,足球运动员在遭遇铲抢时的跳起、拳击手在遭遇击打后的出拳、抢篮板球卡位时的抬臂等等。这种直觉高度依赖平时反复训练形成的肌肉记忆,而这也正是体育竞技水平提高的表现。此时,即便给对方造成伤害,也不值得刑法非难。否则,运动员在苛刻的刑事治理体系面前将会裹足不前,对抗性竞技体育运动也将与日常健身活动并无二致。更为重要的是,较之于普通人,运动员对竞技体育伤害风险有更加清晰、准确的认知。既然踏上竞技场的运动员在“振兴体育”与竞技体育致害的博弈中选择了前者,就意味着较之于普通民众,运动员身体的需保护性实现了类型性降低。基于人本主义立场,法规范此时应当为其遮风挡雨,而非横加阻拦。
三、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正当化的条件
(一)相关学说及反思
关于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正当化的条件,理论上聚讼不断。学者们对诸如时空条件(行为发生在正当的对抗性竞技体育活动中)、主体条件(参与比赛的运动员)、因果条件(竞技行为致害)、主观条件(基于比赛目的)达成基本共识(下称四要件说)。⑤吴玉萍:《竞技体育行为与体育暴力行为界分的刑法考察》,《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 年第3 期。⑥钱叶六:《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及边界》,《法学家》2017 年第3 期。有学者效仿正当防卫的条件,指出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正当化还需具备对象条件(针对另一方运动员)与行为限度条件(没有明显超过限度并造成重大损害)(下称六要件说)。⑦徐明、李正新:《竞技体育中伤害行为的立法化》,《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 年第7 期。这些学说遵循行为叙事结构,并未将作为类型化事实的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置于犯罪检验体系考察,也未能在认识论上秉持价值规整事实的方法二元论。
一方面,行为叙事结构重点着眼于存在论视野中的现象形态,关注何人何时何地在何意支配下实施了导致何种结果的何种行为。娓娓道来的平铺直叙的确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既视感,但也不得不直面事实认知侵蚀规范标准的拷问。例如,检讨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是否正当应以行为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为前提,“竞技行为致害”只是行为事实在结果面向的表征。也正是因为这一表征,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是否正当才成为问题。但无论如何,这都不能成为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正当化的规范标准。再如,若行为发生在非对抗性竞技体育场域,就不可能因对抗致人伤害,进而不会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自无必要讨论行为的正当化条件。将行为发生场域作为行为正当化条件,是在将碎片化的经验性、常态性事实认知作为检验行为正当化的标准,忽略了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化条件只是故意伤害罪检验标准中的一个环节。更为根本的是,遵循行为叙事结构,纷繁复杂的事实样态可以衍生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正当化条件。例如,作为主观的正当化条件,为何“基于比赛目的”不能置换为“基于公平比赛目的”,抑或是“基于有序比赛目的”?
另一方面,方法二元论力主以价值性思考规整碎片化的现象世界。①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 年版,第128 页。现有学说混乱的起因在于认识论层面对方法二元论的漠视,亦即没有秉持立足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型构其正当化条件的方法论,使对抗性竞技体育正当化根据与正当化条件的探讨被割裂开来。例如,有学者分别研讨了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正当化根据与正当化条件,却未交代二者的关系。②徐明、李正新:《竞技体育中伤害行为的立法化》,《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3 年第7 期。主张四要件说的部分学者,将社会相当性原理视为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化根据,但正如下文所述,除了“遵守比赛规则”外③“四要件说”关于对抗性竞技体育活动正当性的要求与“遵守比赛规则”的说法并无二致。,该说给出的其他要件均不能作为行为正当化条件。虽然社会相当性原理与正当业务学说关于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化条件完全一致,但却不能像正当业务学说一样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上述条件④这并不意味着本文认可正当业务学说作为对抗性竞技体育致害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在前文对“正当业务学说”的评价中,笔者已指出该说存在一系列疑点。。
(二)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正当化条件及其展开
竞技体育伤害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所欲禁止的致人身体伤害或危险的结果,行为人主观上对此也有认知。为对抗上述主客观不法评价,就需要行为具有客观的正当化事由,行为人主观上对该事由有认知。作为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正当化根据的“振兴体育”,以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创造优异成绩为核心。为防止一味追求胜局而可能出现背离“振兴体育”初衷的行为,如侧方位铲球、打击对手后脑等等,就需要厘定对抗性竞技体育比赛行为的尺度。体育比赛规则是在长期实践中积淀并不断改进的、促进体育运动水平提升的保障和防范运动过当伤害的标尺,遵守比赛规则的体育运动技术动作符合“振兴体育”的初衷。因此,“遵守特定类型的体育比赛规则”在客观阶层对抗因行为导致他人伤害(危险)结果的客观不法,“认识到遵守比赛规则的要求而实施竞技体育行为”在主观阶层抵消了对行为致害的认知所成立的主观不法。
接下来的问题是,竞技体育伤害行为主客观正当化条件的检验顺序应如何安排?基于如下三点,在检验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化事由时,应秉持客观判断优先的基本逻辑。其一,由于主体是通过他人的表情、语言、动作等一系列外化感觉材料,并结合自己的经验推测他人心理状态的,⑤冯亚东、叶睿:《间接故意不明时的过失推定》,《法学》2013 年第4 期。因而遵守比赛规则成为是否有遵守比赛规则意识的判断依据。其二,若优先证成行为人有遵守比赛规则意识则再行客观阶层判断;当客观上行为人存在违规时,还需返回主观阶层判断其对违规有无过失,即认识的可能性。可见,主观条件优先的检验构造可能导致“回头看”现象,反之则不存在上述问题。较之于遵循客观判断优先逻辑形成的“客观-主观”的判断模式,“主观-客观-主观”的判断构造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嫌。其三,认识并不一定是行为人在上意识中心地带的对事物的清楚认识,也可能是由于经验积累形成的在上意识边缘地带的对事物的含糊意识。⑥黄荣坚:《刑法解题——关于不法意识及犯罪结构》,《台大法学论丛》1991 年第2 期。竞技体育行为致人伤害的主体意识中心地带往往是比赛本身,而遵守比赛规则的认识往往居于意识的边缘地带,在诉讼证明中相对困难。遵循先易后难的证明路径,也应该首先检验客观的正当化条件。
多数情况下,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正当化条件呈现为“全有”或“全无”样态。值得关注的是两种例外情况:其一,客观上有遵守比赛规则的行为,主观上没有遵守比赛规则的意思(下称例外一)。例如,著名的基恩事件①曼联球星基恩在自传中称其铲伤哈兰德是为报复后者之前对自己的伤害行为。然而,该铲球行为在客观上并未违规。,或是足球运动员意图抬脚过高伤害对方,因对方跳起而未得逞。其二,客观上没有遵守比赛规则的行为,主观上有遵守比赛规则的意识。例如,在前述“班古拉事件”中,吕刚抬脚过高的确违反了国际足联比赛规则,但其主观上只是想“解围”(下称例外二)。对于例外一,行为虽然因遵守比赛规则而可以抵消实害结果的不法,但创设的对他人健康法益的危险是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行为人创设了导致他人健康法益具体危险的行为并对此有认识时,无论行为是否有实害结果,都符合故意伤害罪(未遂)的构成要件。对于例外二,行为虽然违反了比赛规则,即便主观上认识到可能伤害对方,但因主观上遵守比赛规则的认识足以抵消故意的主观不法,也只能考虑是否成立过失犯罪。在对重伤害结果以及对违反比赛规则有认识的可能时,则行为符合过失致人重伤罪的构成要件。具体判断规则如下表所示。

表1 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刑法评价机制
四、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主观正当化条件的司法认定
对于行为人客观上违反比赛规则造成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由于过失轻伤不具有刑事可罚性,因而主观上有无遵守比赛规则的认识将直接决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既然从事竞技体育行为以专业性知识、针对性训练为必要,故以未能认识到违反比赛规则进行辩解,原则上因与事理逻辑、常识常理相悖而说服力阙如。作为例外,鉴于事实认知是规范认知的前提,认识到行为被评价为违规的事实是行为人有违反比赛规则认识的基础,因而客观上违反了比赛规则却未能认识到这一事实的情形在逻辑上只能有两种类型:一是行为人未能认识到被评价为违反比赛规则的事实(下称类型一);二是虽然认识到被评价为违反比赛规则的事实,但行为人有不违规的充分自信(下称类型二)。
类型一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这是因为,未能认识到被评价为违反比赛规则的事实,就意味着没有认识到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事实。由于违法阻却事由均针对故意行为而设定,没有认识到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也就无须进行故意犯罪违法性阶层的检验。例如,不得击打后脑是拳击比赛的铁律。在拳击手意图击打对方脸颊,却因对方躲避而意外击中后脑并致人重伤的案件中,拳击手无法预知这种结果,也就不存在符合故意伤害罪主观要件的事实,也就没有必要依次进行主观正当化条件的检验。至于行为客观上是否违反了规则,行为人是否因没有认识到上述事态而未能认识到违规,在所不问。在认识到行为被评价为违规的事实后,对抗性竞技体育参与者应当产生不实施行为的反对动机,否则就意味着对法秩序的背反,除非有行为不违规的充分依据。
由于包括比赛规则在内的规则首先是一种命令或禁止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的规范,基于同领域内规范效力的平等性,能够对抗比赛规则、抑制竞技体育参与者反对动机的依据也必然是比赛规则或衍生物。因此,类型二的子类型如下:
一是,对抗性竞技体育参与者错误地信赖已经失效或尚未生效的比赛规则,且无法知晓即时有效的比赛规则。“错误”意味着其并不知晓相关比赛规则已失效或尚未生效。以不知晓并且不可能知晓的比赛规则苛求运动员,有违“法不强人所难”的格言。之所以要求其“无法知晓即时有效的比赛规则”,首先是因为有可能知晓即时有效比赛规则而不去了解的运动员呈现出蔑视比赛规则的人格态度,基于秩序价值,比赛规则无须对其退让;其次,如果存在可能知晓即时有效比赛规则而不去了解的行为人,其可以肆意而为却无须承担责任,就会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再次,如果不处罚此类行为人,就意味着合规主体要承担他人不合规行为的风险,这有违风险分配的法理。
二是,裁判员对与具体竞技体育伤害行为实质相同的行为做出过不违规的判罚,竞技体育参与者因信赖该判罚而行为。裁判员一个个鲜活的判罚赋予抽象的比赛规则以实践生命力。运动员往往通过裁判员的判罚来把握比赛规则的精神、价值和内涵。裁判员对比赛规则的不同理解深刻影响着运动员的技术动作、行为选择。信赖既往判罚而行为的运动员,即便事后被评价为违反了比赛规则,也应被视为具备主观的正当化条件,否则就会使运动员缺失行为指引,背离“振兴体育”的初衷。
五、结语
不少学者主张,刑法在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领域应恪守谦抑。毋庸置疑,较之斗殴伤害等典型的故意伤害现象,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确有其特殊性。基于促进体育事业的考量,刑法应当对必要限度内的伤害行为保持容忍,并可立足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特质,有针对性地设计诸如缓刑、替代性处罚等刑罚退出机制。然而,尊重诸如促进体育事业等于法有据的吁求是恪守谦抑,但若包容有违体育价值的对抗性竞技体育伤害行为则是渎职。体育法、刑法等各个法律部门应在坚持既有范式基础上合理回应治理诉求,切实做到既不越位,又不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