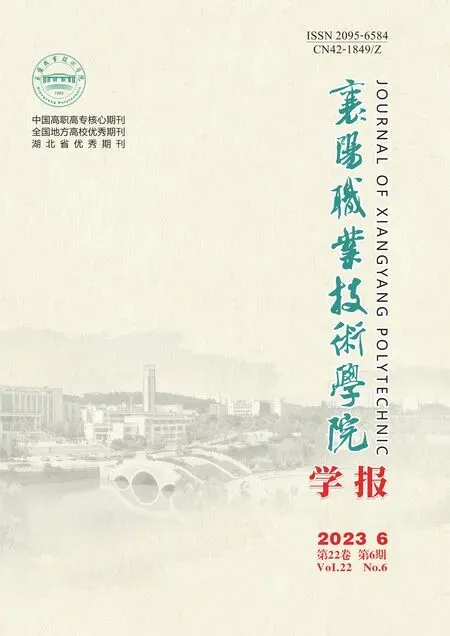质朴与丰赡:《白气球》叙事的美学追求
余海林
(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襄阳 441021)
美国著名剧作家罗伯特·麦基曾说过:“一个讲故事的人即是一个生活诗人,一个艺术家,将日常生活、内心生活和外在生活、梦想和现实转化为一首诗,一首以事件而不是以语言为韵律的诗——一个长达两小时的比喻,告诉观众:生活就像这样!”[1]伊朗新电影的导演们就是这样一群特别的“诗人”,这些富含诗人气质的叙述者,将诗意倾注在质朴、平凡的小事上,创作出一大批纯真动人的儿童电影。贾法·帕纳西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获奖处女作《白气球》就是一部以质朴与丰赡为美学追求的诗意性电影。
一、叙事的质朴性
(一)简约的叙事结构
《白气球》讲述了一个为实现新年愿望不断“寻找”的故事——新年将至,7岁的小女孩娜西亚想要买一条四条鳍的漂亮金鱼,妈妈不肯答应,在哥哥的帮助下,妈妈将家里唯一的500元钞票给了她。买鱼途中,耍蛇人骗取了娜西亚的钞票,可她伤心的泪水又使耍蛇人把钞票还给了她。赶到金鱼店,娜西亚却发现手里的钞票丢了。一个好心的老妇人陪娜西亚一起寻找,发现那张钞票被摩托车刮进罩着铁丝网的下水道里。娜西亚求隔壁裁缝店的老板把钞票取出来,可裁缝店老板没时间帮她,娜西亚无助地守在那里。哥哥阿里跑来找她,也没办法把钞票取上来。阿里试着请周围的大人们帮忙,可大人们都忙着回家过年,谁也没有耐心帮助他们。直到卖气球的阿富汗男孩出现,在他无私的帮助下,终于用口香糖将钞票粘了出来。娜西亚和哥哥拿着钞票欢快地跑开,买回了想要的金鱼,然后又高兴地回家去,只剩下那个孤独的阿富汗男孩举着木杆上的一只白气球,怅然若失地待在那里。这时,新年的钟声响了起来。
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日常生活故事。故事的时间有限——新年来临前的一个多小时。新年是一个时限,广播里不断地传出报时声,不断强调着时间;故事的场景有限——娜西亚家的院子、耍蛇场、金鱼店、钞票掉进下水道的马路边;故事叙事的线索单一——就是那买金鱼的500元钞票,整个故事就围绕小女孩“要钱——买金鱼——丢钱——找钱”展开,这是以线性时间进行的顺时序叙事,采用“产生希望——希望破灭——产生希望——希望破灭……”这一循环的叙事结构来搭起影片的叙事框架。
另一方面,因为故事发生在马路边,路自然而然就成为电影的主要场景,路将众多人物、事件贯穿起来,展现真实的社会图景,给人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化的感觉。这样来看,路在《白气球》中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叙事线索的作用。
(二)平缓的叙事节奏
电影故事如果很简单,且又是按照顺时序平铺直叙的话,很容易造成平淡无奇的效果,难以吸引观众的持久兴趣。为此,电影通常会设置悬念,以推动电影情节进展、牵动人物关系变化、调动观众参与,由此控制叙事节奏,抓住观众的心理,《白气球》即是如此。我们知道,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经典叙事型电影习惯以戏剧式冲突来建构悬念,这种冲突具有一定的巧合性、夸张性,始终表现出清晰的因果关系。《白气球》与此显然不同,它严格按照事件变化的物理时间来顺时序展开,采用的是一种非戏剧式的悬念——这是一种更生活化、真实化的悬念设置。
《白气球》一开始,妈妈不同意买金鱼,娜西亚伤心——拿着妈妈给的钞票去买金鱼,她开心——耍蛇人骗取娜西亚的钞票,她伤心——娜西亚委屈流泪,耍蛇人把钞票还回来,她开心——在金鱼店里,发现钞票丢了,娜西亚伤心——在下水道里发现了丢掉的钞票,娜西亚开心——多次请大人帮忙而不能取出钞票,娜西亚伤心——阿富汗男孩帮忙取出钞票,买到气球,娜西亚开心。《白气球》利用“伤心——开心”的不断转换,成功抓住人们的心理,制造出悬念,由此形成了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
另一方面,电影在叙事时,娜西亚遇到的各类人物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想不到”——想不到那两个看起来狡猾的耍蛇人仅仅因为眼泪就把钞票还给了娜西亚;想不到那个偶遇的老妇人居然耐心地陪娜西亚找钞票;想不到那个怪怪的大兵,竟然是因为思念妹妹才和娜西亚搭讪;想不到那个贫穷的卖气球的阿富汗男孩竟然那样无私地帮忙把钞票粘出来……这诸多“想不到”也是电影故意设计的心理悬念。
《白气球》没有大开合的故事,更没有传奇,它不着意于戏剧情节的展现,只以散文风格将注意力集中于孩子的心理世界和精神视野,把孩子单纯、干净、纯粹而执着的追求作为影片的叙事中心所在。同时,在这种平缓的叙事中,又多方展现伊朗的社会图景,使该片具有了自然、宁静、朴实、散淡之美。因而,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不是戏剧的逻辑而是生活的逻辑在决定了《白气球》的叙事。
(三)朴实的叙事风格
在叙事风格上,《白气球》与好莱坞式的精心设计的虚构故事、节奏紧张、强烈戏剧冲突和奇观化的视觉效果的影片有着截然相反的艺术追求,它是质朴电影的典范,运用朴实的电影叙事、极简化的电影语言来表达生活中最基本的命题,它没有英雄主义,没有正反人物对立,没有复杂离奇的故事,没有戏剧性的对话,没有人为强化的戏剧动作,只有朴素淳厚的生活细节,天性简单的人物、脉络简单的故事和简约的结构,这使得《白气球》看起来似乎是对现实的复制。
在电影语言上,《白气球》使用实景拍摄,采用自然光源,大量使用长镜头,为追求真实而使影像枯燥化,也没有娱乐性,这就使影片形成了鲜明的纪实风格。
在对白上,《白气球》的对白质朴简单,那都是一些絮絮叨叨、不断重复的话语,娜西亚、老太太、裁缝店老板的话都是如此,唯有那个大兵与娜西亚的对话最具情趣与意味。
在音效上,《白气球》仅在电影最后才使用了有限的音乐;为追求生活本色、实况效果,《白气球》采用了同期录音,直接把街头原生态的声音作为电影的背景声音,虽嘈杂,但却真实、自然。
《白气球》通过构图、光影和色调等视听语言形式使整部电影体现出一种诗意的美学特征,呈现出一种清新、自然、简约、质朴的风格,这正是《白气球》这种类型的伊朗新电影被称为“简约主义电影”的原因所在。
二、意蕴的丰赡性
(一)逼真的社会图景
《白气球》虽则是一部儿童电影,但其叙事视角却是纯客观的成人视角,我们不能仅仅将其视为一部简单的儿童电影。影片讲述的重心是一对小兄妹的小悲欢、小确幸,但与此同时,影片也以“在路上”的叙事模式,展示了实景的街道和来自生活中的丰富多义的影像,以此含蓄地反映伊朗社会的种种问题。
譬如,小女孩娜西亚的父亲全程只有声音出现,但却时时刻刻都有强大的存在感,这一设置无形之中就反映了伊朗男人的地位;还有那个叫莱萨的邻居男孩到娜西亚家捞金鱼做新年装饰品,可他实际上却高价卖给了金鱼店。又譬如,虽然许多人在忙碌着过年,但路边的空地上,一群穿着破旧、目光麻木的男人却无所事事地看着耍蛇表演,令人想起鲁迅反映国民性“看与被看”的经典话题。再譬如,那个有假也不能回家乡探望家人的大兵,苦衷却是没有钱买车票;电影里,街道是土路,房子老旧不堪,人们的衣着十分寒酸。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伊朗社会的封闭与贫穷。虽然电影解说这是1937年的伊朗,但我们更相信这应该是反映当今伊朗社会、经济现状的曲笔。
阿巴斯认为:“社会的主体是由普通人构成的,好莱坞式的奇观化的生活离现实很遥远,电影要通过对现实的客观描写来反映社会现实,深入普通人生活。”[2]从创作意图来讲,《白气球》把主要场景放在路上,实景拍摄,固然是为了回避家庭的敏感内容,躲避严厉的审查,但客观上也是希望通过“路”引出广阔的社会现实,观照芸芸众生的生活,反映真实的社会图景,让观众发现来自生活的深刻质感。至于电影借此表达的意图在哪里,这完全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二)深切的人文关怀
《白气球》通过丰富多义的影像还表达了深切的人文关怀,这主要表现在对儿童生命的关怀、对人性与伊朗民族个性的赞美上。
《白气球》洋溢着纯真而又欢快的气息,整个故事围绕娜西亚这个小女孩展开,她的每一颦一笑都让人觉得可爱,她对新年的愿望真诚、执着,这是伊朗儿童生命的真实写照。他们虽然物质贫穷,但却保持了纯真、乐观、坚韧、执着的美好天性,这是伊朗民族的骄傲和生命力所在。伊朗著名导演马基德·马基迪说:“我对儿童世界特别感兴趣,我的童年也是我思路的源泉。我也经历过‘天堂的孩子’的童年,拍摄儿童电影你不用墨守成规,可以挥洒自如。纯真是儿童世界中最令人折服的。”[3]
另一方面,《白气球》还通过娜西亚一路“寻钱”的故事,状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审视了人性的冷漠与热心,可以视为伊朗社会的一个小小缩影。这部电影一系列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恰恰是电影所要表达的赞美之处。譬如,耍蛇人因为娜西亚伤心流泪就把钞票还给了她;一位陌生的妈妈听说娜西亚的钱丢了,主动要为她买一条金鱼;陌生的老妇人一路带娜西亚寻钞票,一路教诲她不要到不该去的地方去;搭讪的大兵因为思念妹妹,默默关注、安慰娜西亚;金鱼店的老板友好善良,让娜西亚先拿走鱼,再回来送钱;还有那个无私的阿富汗男孩,他自己掏钱买口香糖,帮小兄妹粘出钞票,这些都是美好人性的闪光。影片用缄默的镜头语言表达了对人性之美的褒扬和对伊朗民族于艰苦和困顿中坚守宁静、乐观、坚韧、执着个性的赞美。另外,在影片结尾,电影还含蓄地传递出对阿富汗难民问题的忧戚与同情,流露出深深的悲悯情怀。
(三)象征的意味深长
电影拍摄离不开道具的使用,道具也是电影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求“写实性”的《白气球》所使用的道具并不多,主要有三个——“金鱼”“杆”“白气球”,它们都有深深的隐喻与象征意味。
这其中,“金鱼”的隐喻与象征意味最为明显,它代表小女孩的新年愿望,从电影反映的情况看,“金鱼”就像中国人过年的鲜花、福字贴一样,是伊朗人普遍喜欢的新年装饰品,是人们对新年美好期盼与向往的寄托物。
“杆”的隐喻与象征意味则最容易被忽视,一杆连两头,杆可视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连接器。《白气球》使用道具“杆”一共有三次——第一次,小哥哥向一对过路的年轻情侣借他们新买的长杆,但被拒绝了,那长杆虽然漂亮,对孩子而言却是冷漠、无用的,它走不进孩子们的心中,不能给孩子带来快乐;第二次,是借用裁缝店老板的铁顶杆,裁缝店老板刻板不耐烦,他并不情愿帮助孩子们,那铁顶杆粗笨、实沉,接通不了孩子们的心,也帮不了孩子们;第三次,是一截被阿富汗男孩用来拴气球的简简单单的木杆,孩子们一起想办法,成功地用木杆、口香糖将钞票粘取出来,只有孩子懂得孩子,他们靠自己找到了快乐。
“白气球”的隐喻与象征意味最为复杂、多义。影片结尾,那个无私帮助小兄妹取出钞票的阿富汗男孩,很快被小兄妹忘记了,他举着那截只剩下一只白气球的木杆,默默呆坐在原地,影片于此定格,新年的钟声、银幕外不详的爆炸声响起。这一幕可谓旁逸斜出,令人百味杂陈。“白气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只为了表达对阿富汗难民问题的关心,传递深深的悲悯与救赎情怀?还是另有深意?有论者认为:“从任何意义上说,阿富汗男孩都处于叙事的‘边缘’——当然,这是重点。他和他的白气球几乎没在电影中出现过。而且,有人可能会补充说,电影中也没有出现伊朗的政治局势和伊朗国内的阿富汗难民问题。然而,白气球是电影的标题,也是最后的影像:这个非常出人意料的长时间的定格影像,展示着自己是电影的关键,是一个观众有必要花时间来‘解读’的停滞画面。人们对拉齐耶(现在已经没有同情心了)的追求的认同受到质疑:影片言外之意是阿富汗难民不会回家庆祝新年——他们没有家。但这个影像太语焉不详,又太强有力,不能简化为单个层面的解读。阿富汗男孩和他的白气球的定格画面回应并修改了电影之前所有的‘迷人’的叙述,即整条影像链。”[4]
是故,有人称《白气球》的结尾为“豹尾”,这确有道理,它是关切,也是质疑、反转,是别有深意。马基德·马基迪认为:“电影的结尾可以说是电影的总结部分,观众们从最后一个画面中可以感受到整个电影的灵魂。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结尾处的设计可以给观众留下想象的空间,也让这个画面在他们的脑海中一直保存下来。画面设计是十分重要的,极具美感的画面可以在观众的脑海中留存很久……电影的结尾是整部电影的灵魂。”[3]伊朗新电影往往具有开放性结局,《白气球》的象征性结尾即是其中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