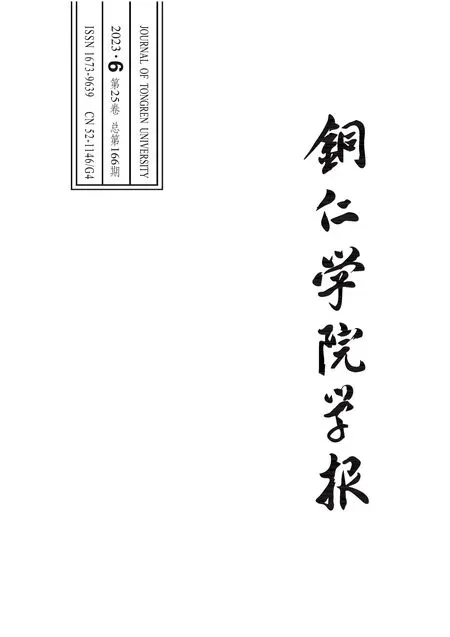赋与诗用典异同论
辛 梓
赋与诗用典异同论
辛 梓1,2
(1.桂林医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广西 桂林 541199;2.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用典作为文学重要写作方法之一,在赋与诗中呈现出不同面貌。早期用典是从辞令论说的语言艺术到文学写作手法的迁移。文人用典在赋与诗中的差异,主要体现为赋始举事、诗好化言两方面。南北朝赋与诗的用典之异,是用典方法和文体需求带来的不同。前者体现为赋繁与诗简的不同典面,后者体现为赋典多类义体物、诗典多代言写志。及至庾信用典集前代之大成,从典故本身替代和证言的功能出发,重新诠释典故在赋与诗中的运用,从而使其赋与诗之用典,都呈现出叙理与抒情统一的特征。
赋; 诗; 典故; 引言; 引事
何为用典?萧子显《南齐书》称之“缉事”,萧绎《内典碑铭集林序》谈“引事”,刘勰《文心雕龙》定名为“事类”,钟嵘《诗品序》唤为“用事”,萧统《文选序》曰“事”,颜之推《颜氏家训》称“事义”。典故具体是如何使用的,刘勰在《事类》篇进行了说明:“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1]1407典故就是使用精炼的语言,援引前人的成辞或事迹,浓缩凝炼在作品中,表达复杂的情感内容。钟嵘《诗品序》谈宋末以来文人诗用典,说“何贵于用事”[2]174,表达了对适时诗坛“文章殆同书抄”[2]180风气的批评,并指出胜语“皆由直寻”[2]174。受钟嵘品评诗歌用典的影响,历来对诗歌用典的研究较多。然刘勰《事类》篇中讨论用典时所举之例,乃以赋为主,兼有它体,说明当时文人创作代表性的用典,多集中体现在赋作之中。用典实际上是以赋为寄托,进而得到广泛使用和发展的写作手法。
近年来的典故研究,大多将研究视角放在典故本体的研究上,或论语典,或论事典,多从作品本身出发,论用典方式、典面及典源等,对赋与诗用典之异却少加区分。需知本同末异,针对不同文体,作者在使典入赋、诗时,也会因体制宜,将之改易成不同面貌。笔者主要讨论赋的用典方式,从赋与诗用典异同的角度,考察赋典与诗典的差异发展和不同文体需求,兼考量赋之用典对诗之用典有什么影响。
一、赋始举事,诗好化言
早期文人在赋与诗方面对典故的选择,主要表现出“赋始举事,诗好化言”的特点。这是由文体与语典、事典的不同适应性所决定的。用典最早并非用于文学创作,而是用来说明卦爻辞或训诫,刘勰在《事类》篇中云:
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1]1407-1408
在涉及语言文字的活动中用前人古事古辞,这些是最早使用典故的例子。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大夫、纵横策士在外交问答和辞令论说中,也喜用《诗经》中的句子表达意志,或是借用前代例子来说明态度。这种赋诗言志、赋事叙理的方式,从“引成辞”和“举人事”的概念上来说,同样属于刘勰界定的用典范畴。在战国末年到秦汉之际,典故运用逐渐进入文学创作。刘勰《事类》篇谈及文人用典,云:“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1]1413屈原和宋玉的楚辞,化用了很多《诗经》中的句子,这与战国以来论说好引诗、引事的观念有关。“莫取旧辞”则是通过艺术手法的加工,使典故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是用典的方法之一。又:“唯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1]1413可见,及至汉初,文人用典的情况虽不多,但几位代表作家的用典已初现端倪,引诗、引事逐渐从辞令论说转为文学创作的手法进入赋与诗,开始为文学创作服务。
西汉时期总体用典数量不多,可以用来对比的材料也不多,但仍存在一些差异,尤其表现在赋的创作开始主动引事。贾谊赋、相如赋虽已有较多语典和成段排比的事典,但引事只是开始进入赋这种题材,总体使用情况不多,并没有成为一种固定的习惯和共识。如司马相如《长门赋》几不引事,宋玉《风赋》也仅用言。至东汉时期,班彪作《北征赋》多写见闻,却又不离典故。事典、语典已在赋中频繁交替出现,基本均匀地分布在篇幅中。如:
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3]142-143
六句之中,语典、事典间杂交叠,借前人语慨古人事,几乎每句都涉及典故。事典也不仅集中在一处,而是多处分布。如:“忿戎王之淫狡,秽宣后之失贞。嘉秦昭之讨贼,赫斯怒以北征。”[3]143班彪以历史观照现实,怒戎王和宣后失道,赞秦昭王的能为。甚至末尾处“乱曰”也用圣贤书辞为己证,说明“君子履信无不居兮,虽之蛮貊何忧惧兮”[3]144的道理。相较于西汉赋的用典,东汉赋用典已经呈现出比较成熟的面貌,典故开始大量入赋。在西汉赋中初现端倪的事典,也从个性化的写作手法渐趋成为一种共识。
西汉存诗较少,多以辞、歌为名,难以窥其用典面貌。及至东汉,则可以看到较多的引诗化句的用典。《古诗十九首》的抒情多化用《诗经》《楚辞》语典,如《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馀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3]409
其中“生别离”出自屈原《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3]467句,表达作者离别之悲,“道路阻且长”出自《秦风·蒹葭》“溯洄从之,道阻且长”[3]422句,指路远难能相见。“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句,李善注:“《韩诗外传》曰:‘《诗》曰:代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皆不忘本之谓也。”原诗题名为何已不可考,但研读该句之意,可知其为旧辞翻新语,化用而成。古诗中少见事典,仅《西北有高楼》中“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3]410句一例,引用了春秋时齐国大夫杞梁之妻,在丧夫后无依无靠,以代抒悲情。除此之外,并无他用。《古诗十九首》的语典既有化成辞的,也有化意境的,且在化用时联系前后,在原有典意的基础上作情感延伸。事典的使用则少之又少。可见在两汉时期,诗中引事还是一个比较少见的现象。
章太炎《国故论衡》说:“武帝以后,宗室削弱,藩臣无邦交之礼,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时有解散。”[4]用典既上承前代的辞令论说而来,纵横家入汉后一变为赋家,则用典更多出现在赋中,也是一种语言艺术从口语到文学的迁移。引事是纵横家在论说中枚举事例的做法,赋家最初在赋体作品中使用事典,也是得益于赋的篇幅巨大,能够更好地安排内容丰富的材料。而诗歌篇幅有限,并且多直接抒情达意,相较于间接委婉的事典,语典更适合诗歌的需要,因此,诗歌多用语典。
两汉时期,文人用典渐成为创作趋势,赋和诗为典故的使用提供了文学载体。文人对典故如何入赋、入诗有自己的选择标准,将这个时期的赋与诗的用典面貌,简单概括为“赋始举事,诗好化言”。
二、典面的赋繁与诗简
曹丕在《典论·论文》谈“诗赋欲丽”[3]720,提出了重视文采的追求,而典故能使赋和诗在踵事增华上更进一步。自建安、太康以来追求语言雅丽,至元嘉文学雕琢山水,再到永明文学刻镂声律,用典的适用性被不断提升。“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1]208的唯美文学观点被发扬光大。典故为赋和诗的创作提供原材料,赋和诗同为文学创作的载体,都追求文采和行文用韵的和谐,呈现的面貌却不尽相同。赋繁与诗简的差异也体现在用典中,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
(一)赋典言事合一,诗典言事分离
赋的句式更自由,虽有对仗要求,但在形式上更能灵活安排典面,因此多为引言兼引事。罗积勇《用典研究》中将这种情况分成四类:(1)引言而带出其事属引事;(2)引语不带出其事而带进当初语境属引言;(3)引语而涉及事情属引言;(4)引述事之语属引事。这四种用法在各类赋作中都很常见,如具有代表性的江淹《恨赋》众事:
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
至如秦帝按剑,诸侯西驰。
若乃赵王既虏,迁於房陵。薄暮心动,昧旦神兴。别艳姬与美女,丧金舆及玉乘。置酒欲饮,悲来填膺。千秋万岁,为怨难胜。
至乃敬通见抵,罢归田里。闭关却扫,塞门不仕。左对孺人,顾弄稚子。脱略公卿,跌宕文史。赍志没地,长怀无已。[3]235-236
“拱木敛魂”出自《左传》,李善注:“秦伯谓蹇叔曰:‘中寿,尔墓之木拱矣。’”江淹引语并非要引原事用来骂人指摘,只是借用当时秦穆公的口吻,指出一种死后沉寂的现象。“秦帝按剑”,李善注:“秦始皇太后不谨,幸郎嫪毐,始皇按剑而坐。”此处用《说苑》载事,引述事之语兼引嫪毐乱政之事,指出适时秦始皇对嫪毐的怒与恨来呼应主题,下文接“诸侯西驰”指秦统一而六国合纵抗秦之事,两句衔接又形成新的典面。“千秋万岁,为怨难胜。”用语《战国策》,李善注:“楚王谓安陵君:‘寡人万岁千秋之后,谁与为乐也!’”引语而涉及楚王感慨死生的情形,切合《恨赋》所表达的主题。“赍志没地,长怀无已。”用冯衍《显志赋》“赍此恨而入冥”[5]989句,《与阴就书》曰:“衍年老被病,恐一旦无禄,命先犬马,怀抱不报,赍恨入冥。”[5]978此化用冯衍语,同时也引冯衍不受任用之事,表达恐死有余恨的仕途叹恨。通过截取语言而带出文字所包含的事件,引言和引事同时进行,这种用典方法的叙事性也更强,对所引对象的语言描述较诗更为细致,涉及场景、语言、事件等多个方面,使赋典呈现出言事合一的效果。
南朝文人诗以五言诗为主,兼有杂言。受到文体结构和字数、句式的影响,典面不宜过长,需精准凝炼,以语言浓缩精华又能传递情感为佳。典面所表达的含义,需要结合全诗的抒情核心进行解读,多在单句内完成用典,所以诗典一般单引言或引事。此处同样以江淹为例,如《侍始安王石头》:
绪官承盛世,逢恩侍英王。结剑从深景,抚袖逐曾光。暮情郁无已,流望在川阳。平原忽超远,参差见南湘。何如塞北阴,云鸿尽来翔。揽镜照愁色,徒坐引忧方。山中如未夕,无使桂叶伤。[6]99
“平原忽超远”用屈原《国殇》“平原忽兮路超远”[7]47句,“从坐引忧方”用曹丕《善哉行》“忧来无方,人莫知之”[3]391二句糅合为一句,都是以小句为单位的精炼引语。亦有以联为单位的用典,这种方式多化用他人句义,如“何如塞北阴,云鸿尽来翔”联,《吕氏春秋·仲秋》:“仲秋之月,候雁来。”高诱注:“是月候时之雁从北漠中来。”[8]此用其义。又“山中如未夕,无使桂叶殇”联,化用《招隐士》首尾二句之意,皆将原本的典面,拆解后重新组合成适合诗歌的句式。即使是错综复杂的事件,也尽量以简单的名词进行替代,“参差见南湘”句“南湘”用舜葬苍梧之野事,代指宋孝武帝薨,七月葬丹阳秣陵县事。可以看出,诗典并未过多花费笔墨在概括事件上,仅以地名、人名或某些特定事物作为替代引事。由于五言字数和诗歌篇幅的诸多限制,诗典用词含蓄,且单引语或引事,言事往往分离。一般不会在典面后再追加论断,言不尽意,点到为止,典故只作辅佐性质以助益诗歌的情感表达。
(二)赋典铺排造势,诗典点缀修饰
为支撑论点,说明道理,赋中举例常通过排比方式引事,为论证增加说服力。这种大面积铺排成段的引事方法,给人以文采斐然,气势磅礴的扑面之感。这种排比引事自汉赋已有,至魏晋已成为赋体常见的句式之一。魏晋时期文人赋用典,力求罗列众事,甚至交错反复描写、使用同个典故,以事套事、层叠出现,且所占篇幅也越来越大。如郭璞《江赋》:
若乃岷精垂曜於东井,阳侯遯形乎大波。奇相得道而宅神,乃协灵爽於湘娥。骇黄龙之负舟,识伯禹之仰嗟。壮荆飞之擒蛟,终成气乎太阿。悍要离之图庆,在中流而推戈。悲灵均之任石,叹渔父之櫂歌。想周穆之济师,驱八骏於鼋鼍。感交甫之丧珮,慜神使之婴罗。[3]189-190
郭璞举众事说明长江的自然之道与永世不衰的活力,几乎一句一事。这种赋典的铺排效果,提升了赋的风格气势,使语言表现力更强,说理气势更足。这也使赋典中集合了大量的历史人物意象,具有远超诗典的意象群。
诗典作为点缀和修饰,使用得当可使抒情的韵味更悠长,具有曲折委婉、隐晦朦胧的效果。如阮籍《咏怀》其六:
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冈岑,飞鸟鸣相过。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3]323
第四联引人名、地名概指李斯、苏秦事,二人皆因贪求功名遭祸身死,其经历让人反思。第五联“求仁得仁”是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评价。这两联一前一后作比较,从而传达出了阮籍避世远祸以藏身的态度,这是他处在魏晋之交的切身体验。阮籍藉由两种不同的事迹比较,传达内敛克制的情感。
赋繁与诗简概括了不同文体典面的不同面貌特征。赋的用典是面,多典论证一事理。诗的用典是点,围绕一点抒情。赋典引辞举事并不深入,作者以旁观者视角进行罗列,受篇幅限制较少,叙事性较强。诗典传递作者情感而深入其事,典面更为凝练,意象群趋向小范围的精准典故,更有针对性。
三、文体的客观与主观
文体本身的差异决定了赋和诗在用典上的差异。赋和诗是两种独立的文体,但两者从出身上来说又血脉相连,故在讨论时不可完全将二者割裂。
(一)敷陈与抒情的文体需求
班固《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3]21萧统《文选序》谈赋体,也说道:“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3]1-2既说是古诗之流,但又另称之为赋,这是为什么呢?自汉以来的赋篇,都冠以赋名,实际上是将赋从“古诗之流”的范畴剥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古来文体独立,首先就体现在作品的命名中。如颂体,自《诗经》中就有《商颂》《鲁颂》,到后来又有屈原作《橘颂》等。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分“八体”,这些文体在创作命名时都会有特定称呼的“尾巴”。如论体,有贾谊《过秦论》、孔融《孝廉论》、陆机《辩亡论》;书体有李斯《谏逐客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等等。赋之名的独立出现,说明赋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固定的标准。再到后来刘勰《文心雕龙》第六篇至第二十篇,对文体进行了更详细的分类,其中都有“选文以定篇”的具体例作。《诠赋》篇刘勰将之置于文体论的第三篇,一方面是考虑到赋和诗的关系,故置于《明诗》《乐府》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刘勰对赋体独立地位的肯定。
挚虞《文章流别论》写赋从诗中的分离,有这样一段内容:“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9]819古代作诗以抒发情感,不超越道德礼仪的界限,其内容是克制的,因此,诗需要“发乎情、止乎礼义”。而为了满足表达和敷陈的需求,从诗歌中分化出来的文体,就是后来的赋。赋与古诗不同,能使人极貌写物,尽言尽意,通过铺排其辞,承担了列举事例,进而阐明道理和志向的功能。这两种不同的创作需求,赋予了典故不同的功能。挚虞其后评诗、赋差异又云:“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9]819强调了诗歌的抒“情”核心,指出典故作为写作手法,在诗歌中所承担的辅佐功能。作者为了抒情言志而写诗,诗歌即是个人情感寄托的对象。典故的使用是为了更好地助益情义的抒发,而并不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作者经由典故串联起情感脉络,使诗歌前后圆融,最终回归己身,抒发个性。对于后来的赋体,虽挚虞对其评价不高,但也明确了铺排在赋体中的比重,即事物铺叙的篇幅一般远超过情义的抒发。
既然明确了赋与诗在文体需求上存在差异,那这种差异之于用典又有哪些影响?笔者认为从功能上可以简单概括为:赋典类义体物,诗典代言写志。
(二)赋典类义体物
荀卿作《赋篇》第二十六以下五篇赋,每篇的结尾处用“请归之礼”[10]310“夫是之谓君子之知”[10]311“请归之云”[10]312“夫是之谓蚕理”[10]313“夫是之谓箴理”[10]315作为结语,分别对礼、知、云、蚕、箴五个内容进行理论性阐述。宋玉《高唐赋序》载楚襄王令宋玉作赋时言:“王曰:‘试为寡人赋之。’”[3]265《神女赋》也载:“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3]267《登徒子好色赋》中让宋玉为己辩白时也说:“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3]269楚襄王对宋玉提出要求,用现代汉语简单概括,即“你来解释一下其中的道理”或“你把知道的事情说出来听听”。可知宋玉作赋的缘故,乃是进行道理的陈说。贾谊《鵩鸟赋》也说:“乃为赋以自广也。”[3]198就是用道理来说服自己。
陆机谈“赋体物而浏亮”[3]241,阐明了赋体铺排陈事的特性。刘勰说赋“铺采摛文”,因而赋之用典也受到这种特性的影响,成为说明的手段之一,更重体察物事和叙理。一篇赋中,往往通过铺排事例支撑论点,反复讨论说明观点。内容上先说什么、再说什么,都经过了精妙的编排,逻辑上循序渐进。如江淹《水上神女赋》开篇:
江上丈人,游宦荆吴。首卫国,望燕途;历秦关,出宋都。遍览下蔡之女,具悦泣上之殊,未有粉白黛黑,鬼神之所无也。[6]24
首段为神女的出场作铺垫,所写四地,皆古时美女所出之处。随后反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鄘风·桑中》中写美女事的典故,称这些美女都不足美。之后写与神女相遇时,曰:
窈窕暂见,偃蹇还没。冶异绝俗,奇丽不常。青琴羞艳,素女惭光。笑李后於汉主,耻西施於越王。[6]25
青琴、素女、李后、西施四人,相较开篇事典,所蕴含的故事内容变得更为具体和丰富了。末段用“嫔杨不足闻知,夔牙焉能委悉”[6]27。典面复又变得紧凑。这种典故的先后顺序经过精心安排,循序渐进。文体需求也使赋在体物时务求写尽,举例引事时力求面广。江淹使史上众美女逐一与神女相比而失色,进而说明神女之美。江淹赋在引事时,其视角往往游离在事例之外,作为一个旁观者去引用和描述,陈述客观事实,所写皆体物声色。典故几乎完全没有涉及创作时的内心情感状态,也没有个人志向的直接抒发。这一点与诗体的抒情性有很大差异。总而概之,赋重体物,通过铺排引事以尽描摹之态,进一步明晰概念,进行说明,阐述观点。
(三)诗典代言写志
自《诗经》以来,诗歌的抒情传统被不断发扬,陆机谈“诗缘情而绮靡”[3]241着重于“情”之一字,诗歌作为最具有抒情内涵的文体,其抒情性需要藉由文字传达。情之所至,辞之所发,这种特点也表现在典故上。诗歌重叙个人感情,作者更藉由典故背后所蕴藏的情感和故事,进行强烈的自我抒情。虽六朝文学重整饬精雕,或有为救对仗而生硬用典的情况。但总体而言,诗典由自内发,具有强烈的个性化特点,以典传情,为自我代言,起到奠定诗歌感情基调之用。
由于不同作者的作品各有其风格,故仍以江淹的赋与诗为例分析。在江淹的诗典中,无论引事或引语,皆起到对作品的核心情感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感春冰遥和谢中书二首》其二:
暮意歌《上春》,怅哉望佳人。揽洲之宿莽,命为瑶桂因。观书术不变,学古道恒真。若作商山客,寄谢丹水滨。[6]112
此诗三处用典,屈原《离骚》有“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4句,江淹诗首句用其意。“佳人”用屈原香草美人的意象指建平王,暮春之时同草木零落之时,表达时机错失之意。又原句原引“夕揽洲之宿莽”[7]4句,宿莽遇冬不枯,江淹以此喻馋人虽欲困己,己心性坚定不可改易。诗名所寄的时节乃春天,江淹见春感发,所写内容却是秋暮至寒冬的时节变化。加之美人与宿莽的楚辞意象构成,皆传达出适时境遇与心境的不顺。建平王时任荆州刺史,有求仙隐逸之志,作为幕僚的江淹则借遥和之诗的口吻,传递出对建平王不思乘时进取、建功立业的失望心情。句末用商山四皓的典故明志,暗藏隐而未发的感慨——若为隐士,或反能得建平王之青睐。无论是句中语典的情感抒发,或末句事典的寄托向往,都围绕江淹怀才不遇的个人情感,传递、诉说心境,典故是他抒情时的暂时寄托,并非抒情的重点。
江淹的赋典重在写视觉听觉的所见所闻,然后进行比较,对内心的体察较少。而诗典则围绕着言志核心去抒发感情,借此达到一种为作者代言的功能。诗典起到间接传情、含蓄写志的效果,能让情感的表达更加委婉曲折。
(四)工具性与功能性的阅读体验
前文从创作者的角度去讨论文体需求不同带来的差异,与之相对,文体不同,读者在读诗典和读赋典时的切入角度也会不同。读赋典时,读者多会循着典面铺陈的思路,思考用典精当与否。读者一般能较直观地阅读到赋典的铺排,感受到这种铺排带来的气势,但并不会去深究典故背后的含义。如江淹《别赋》:
傥有华阴上士,服食还山。术既妙而犹学,道已寂而未传。守丹灶而不顾,炼金鼎而方坚。驾鹤上汉,骖鸾腾天。暂游万里,少别千年。惟世间兮重别,谢主人兮依然。[3]238
排比中的每个事典都只是众事之一。读者能感受到江淹这段内容所引,皆为服药求仙之事,用来说明仙家之别情。这些是读者整体而直观的感受。因此,赋典一般是工具性的,作为说明道理的一部分引入赋篇。
读诗典时,读者通过解读诗典背后的含义,探究作者想要传递的情感。哪怕只是一二字的典故,读者都会去思考诗典所传达的信号,探究作者有什么隐而未发的思绪。如江淹《从冠军建平王登香炉峰》:“此山具鸾鹤,往来尽仙灵。”[3]319此句“鸾鹤”同样用洪崖先生和王子乔的典故。与读赋不同,读者在读诗时就会从典故隐藏的含义切入,思考为何会在写景时使用该典,是否为借景抒情,而江淹又是否借此传递出他对仙人的向往,表达修仙隐逸的志向等。诗典一般是功能性的,作为点缀和修饰出现在诗作中,使情感不过于直露。从接受的角度来说,赋与诗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
赋之重说理,与诗之求抒情的不同文体需求,使相同典故在不同文体作品中起到不同作用,使原本独立于历史的典故,同源不同体,展现出不同的面貌。作者对典故的再创作,丰富了典故的功能。概而言之,文体需求不同造成了典故的功能差异。赋典作用于前后逻辑的串联和举例,以达到体物说明的效果。因此,赋典的叙事性强,但用典多只停留于陈述其事、就事论事,并不会在事后传递什么隐而未发的情感,故重在体物和阐述。赋典客观,替代作者陈事体物,所叙所论大都无关作者的个性心灵,更多的是一种共性价值取向或观点的陈述讨论。诗典主观,重叙个人情感,借典故进行强烈的自我抒情。无论引语或引事,诗典最终都会回归创作者本身。其功能主要是为作者代言,为写志的核心服务。
四、赋与诗用典的集大成
前文已从时代发展的角度论赋与诗用典之异,本段则论赋与诗用典之同。刘勰《事类》评司马相如《上林赋》时说:
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唱和千万人,乃相如推之。然而滥侈葛天,推三成万者,信赋妄书,致斯谬也。[1]1436
可见前人成辞故实出入文学创作,虽大都可归为用典,但用典也有合适与不合适的分别。刘勰《事类》篇云:“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1]1432这说明用典恰当则助益,失当则减色。从评价优劣的角度来看,用典的手法在变,对用典的评价标准也在变。
魏晋时期的文人用典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但同样也存在一些问题。萧子显谈用典说:“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11]可以看出当时对用典的理解,就是要求对仗与博学。这种追求直观体现在典故数量上。这个时期的用典受到文体观念发展的影响,在诗和赋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文人们的持续探索和尝试中,典故的功能也不断发生改变。这也是笔者主要选择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作品考察赋与诗用典之异同的原因。诗典以抒情为先,赋典以叙事为主。但到后来,这种以文体作为区分的方式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批评。
无论是“胤征羲和”“盘庚诰民”或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辞令论说,引言引事的本质是为了替代和证言,这是典故最根本的功能。典故在进入文学创作后,诗典以引言为主、引事为辅,大部分能很好地围绕着诗的抒情主题得到应用。而赋典却在引事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势走偏锋。刘勰《事类》篇谈用典,多举赋为例,证明了赋中的用典更为当时所看重,又曰:“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1]1427。
刘勰对用典提出了积累学问、用典简约、选取精确和切合要理的四方面要求。但南朝以来对典故的审美需求,却只取第一点,不加节制,在求“博”路上渐行渐远,文人都好用典故以示自身博学。钟嵘《诗品序》对此提出批评,曰:“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2]174这种现象实为当时文人创作之通病,赋和诗都大量堆砌典故,甚至为了使典故陌生化,“必易一二字,不欲有同抄袭”[12]。这种单一的追求趋势,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平衡,使典故繁杂、选取失当、无法切中要理与核心,实际上损害了典故的功能。赋的核心是“铺采摛文”以说理,当作赋变成卖弄学识的方式,就会出现“文章殆同书抄”的情况。无限制扩张的赋典,引事过多,导致作品感情缺失,不加选择的典故喧宾夺主。赋之不像赋,反成纯粹的咏史之流,这是错误的用典方式给作品带来的伤害。
庾信是用典的集大成者,其赋典与诗典,相对而言受到文体的影响较小。庾信用典把握住了典故本身替代和证言的功能,这样一来就使赋典和诗典在功能上趋近了。故进以庾信为例,略论赋与诗用典之同。
庾信赋典打破了之前客体角度的叙理用典方式,除了之前固有的引事叙理外,还大量引事说自己的事情,加入了个人抒情。《哀江南赋》中所引事迹,很多都能映照史实,或对应庾信自身经历。如:
拒神亭而亡戟,临横江而弃马。崩於钜鹿之沙,碎於长平之瓦。[13]130
此以孙策丢戟弃马代指柳仲礼勇武却难挽颓势,以巨鹿、长平两战落败之军代指梁军惨败。又:
若乃阴陵失路,钓台斜趣。望赤壁而沾衣,舣乌江而不渡。[13]139
这句实是庾信言己同项羽一样找不到可走之路,为躲避战事,在江岸边迷茫。又:
信生世等於龙门,辞亲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遗训,受成书之顾托。[13]141
庾信此言己经历同司马迁,在江陵受父临终遗训。可以看出庾信所用赋典,或能与自身的经历相呼应,或能与时代进程相对照,抒写强烈的个人忧虑。
江淹也有遭逢人生不如意时的赋作,他贬谪吴兴期间作《去故乡赋》:“切赵瑟以横涕,金燕笳而坐悲。”[6]11写悲伤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但并没有与自身经历联系起来。又江淹《待罪江南思北归赋》:“夫以雄才不世之主,犹储精於沛乡;奇略独出之君,尚婉恋於樊阳。潘去洛而掩涕,陆出吴而增伤。”[6]33所写皆为背井离乡之事,但和他个人具体经历并没有重合。江淹是遭贬离乡,而典源中的人物离乡原因各异。江淹的引事偏向于发散性思维的延伸,相较之下,庾信赋典则牢牢把握了个人情感、个人经历这个核心。通俗一点说,江淹对典故的选择,即当他因思念故乡感到伤心时,选择一个表达伤心的典故,寻求情感中共性的部分。庾信则不然,庾信引事经过了精心挑选,即当他发现历史上某个人、某件事与他的个人经历相近,他便会以此为说,追求典故与己身经历的映照。
庾信的诗典相较前人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和赋相同,其诗也是叙理和抒情的统一。如《拟咏怀》其四:
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离宫延子产,羁旅接陈完。寓卫非所寓,安齐独未安。雪泣悲去鲁,凄然忆相韩。惟彼穷途恸,知余行路难。[13]231
这首诗几乎每句都在用典,“离宫延子产”指“子产使尽坏其馆之垣”[14]1127事;陈完奔齐,自称“羁旅之臣”[14]267等。庾信的引事,可以从字句间联系到事典对象的具体经历。这种叙事性源于对典面的铺排,以往多见于赋中,甚至向赋典“言事合一”的方向趋近。在庾信之前,诗体的抒情性较强,而叙事性相对较弱。江淹诗中也有排比引事的情况,但与庾信有所不同。如《游黄蘗山》的四句:“秦皇慕隐沦,汉武愿长年。皆负雄豪威,弃剑为名山”[6]117表达一种因不得志而求仙的心境。“慕隐沦”“愿长年”去修饰秦皇汉武,缺少对事件的描述,可见江淹只是借秦皇汉武的名字,作为求仙心境的寄托对象。江淹诗中事典的核心,仍是为了自我抒情。反观庾信诗作在“言事合一”的同时,又不落抒情。其诗末句“惟彼穷途恸,知余行路难”,对前文所引子产、陈完、黎侯、重耳、孔子、张良等人事反向用之,突出了“余”的存在。并且他认为只有遭逢绝路恸哭的阮籍,能懂他的感受。前面部分几乎都是叙事用典,却在最终回归了抒情。
在庾信之前的许多文人,对典故替代和证言的功能把握失当,大都受赋与诗的题材限制,多用赋说理、用诗抒情,这使得前人的赋典和诗典也都呈现出与文体需求相结合的特色。庾信的用典统一性,使他的赋与诗,都呈现出叙理与抒情统一的特征。
历来认为江淹《恨赋》用语使事视角独特,能使古今共情而格外动人。但严格评价其用典之优劣,这些历史故事,并没有起到作为典故所应有的替代和证言功能。《恨赋》多段式排比的引事,除首段和末段简单抒发对恨这种古今共情的感慨外,中间六段皆为具体事件的铺排,另有两段是引言的铺排。这种方式使“恨”的主题如排山倒海般反复呈现,令人感受到“恨”之多与无奈,也增强了全赋的叙事性。但考察几个事例作为典故的功能时就会发现,虽然这些人物的经历,都表达了“恨”这种情感,但秦皇霸业遭断、赵王被掳失位、李陵投降失节、昭君和亲远嫁、冯衍罢官故里以及嵇康受诬入狱,这些事件的具体情形,都很难与江淹的个人经历相对照,即找不到这些典故所替代的对象。这些事所欲证之言,也没有落实到具体的语句之中,使人找不到作为叙事者的“我”的主体,更遑论个人观点的表达。虽然典故使《恨赋》呈现出独特的气势和面貌而为人称颂,但其用典并不能算标准而成熟的用典。过多的叙述历史故事,反而使典故失去了替代和证言的功能,淡化了主体表达,使引事像咏史之流,《恨赋》更似“恨史”之类。
与之相较,庾信的《哀江南赋》,即使篇幅庞大乃至一段述引一事,却能做到古今对照,引古事用申今情,这是因为庾信有选择地使用典故。陈寅恪评价说:“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於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15]“古典以述今事”实现了今事以古事证言,“古事今情”说明古事为今事替代抒情。而此情此景既是古今共有,最终就引起了共鸣,既实现了赋典铺叙体物的功能,又达到了抒情代言的目的,是用典的集大成者。庾信的诗典也具备这样的特征,并不局限于赋或诗的文体限制,而是将典故的替代和证言功能发挥到极致,使之走向体物写志、抒情叙理的统一,可谓用典之正宗。
五、余论
自秦汉以来,文人开始使典故入赋、入诗,初步表现为“赋始举事、诗好化言”的面貌。在这之后,对典故的理解和追求也在不断更新、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尤重典故,赋典和诗典也呈现出赋繁诗简的面貌,主要体现在“赋典言事合一,诗典言事分离”和“赋典铺排造势,诗典点缀修饰”两个方面。赋与诗的文体追求不同,赋体追求敷陈而诗体追求抒情,这也反映在典故使用上,同时带来不同的阅读体验。赋典是工具性的支撑材料,因此多类义体物;诗典是功能性的寄托材料,为代言写志服务。这个时期文人用典虽多,但还没有从典故本身的功能去用典,并且过多引事反成时代通病,伤害甚至限制了典故的发展。历经魏晋南北朝剑走偏锋的追求,文人对用典功能的探索终于回归了典故本体功能。庾信的作品是用典的集大成者,准确把握了典故替代和证言的功能,用典精恰,使无论赋或诗,都做到了抒情和叙理的统一。
诚然,赋与诗之用典,有同有异,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典故本身有历史沉淀的价值和含义,端看作者需求为何。需求不同,使用方式也不尽相同。赋和诗对典故有不同的文体需求,故赋典和诗典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南北朝时期,文人创作通过用典以示博学,同样符合当时的需求。因此,在对比和评价时,并不能一概而论地评其好坏,端看从什么角度去进行讨论。
[1] 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 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3]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 章太炎.国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110.
[5]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 胡之骥,注.江文通集汇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 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 高诱,注.吕氏春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51.
[9] 严可均,辑.全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0] 杨倞,注.荀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1]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908.
[12] 孙德谦.孙德谦著作集:九[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160.
[13] 倪璠,注.庾子山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4] 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5]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234.
Differences Between Fu’s Quotation and Poetry’s Quotation
XIN Zi1,2
( 1.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Guilin Medical University, Guilin 541199, Guangxi, China; 2.School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Guangxi, China )
Quotation,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thods of Fu and poetry creation, presents different features in Fu and poetry. In the early period, quotation is the transfer from the language art of rhetoric to the technique of literary writ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u and poetry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Fu likes to quote things, while poetry likes to quote language. Later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u and poetry is the method of quotation and the need of literary style. The former is embodied in the complexity of Fu and the simplicity of poetry. The latter is embodied in Fu’s use of quotation to describe the appearance of objects, and poetry’s use of quotation to express one’s ambition. When it comes to Yu Xin’s quotations, it is the culmination of a previous era. Starting from the substitution of quotation itself, and the function definition of testimony. His paper reinterprets the application of quotation in Fu and poetry, and both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ty of narrative theory and lyric.
fu, poetry, quotation, quotation of things, quotation of language
I206.2
A
1673-9639 (2023) 06-0026-10
2023-10-11
辛 梓(1992- ),女,广西桂林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汉魏六朝文学。
(责任编辑 郭玲珍)(责任校对 肖 峰)(英文编辑 田兴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