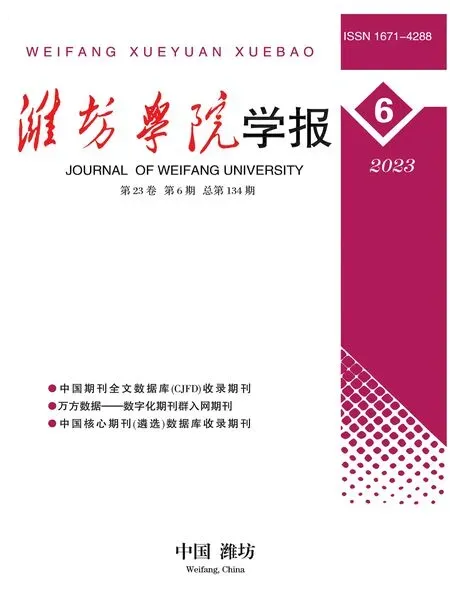《左传分国集注》对桐城义法的接受考论
吴敬堂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韩广櫡(1885-1969),字席筹,江苏徐州人,著有《左传分国集注》《徐州古代建筑史》《万寿祺诗注释》《阎尔梅诗注释》等。[1]《左传分国集注·序》云其取邹平马骕《左传事纬》及桐城吴闿生《左传微》所编篇目而略加变易以成书。尤值得注意的是,《分国集注》成书所据之《左传微》,“继承了桐城派从《左传》中阐释‘义法’的传统,并赋予其新的内涵。”[2]显示了《左传微》对桐城传统“义法”理论的新认识与新阐释。
一、从方苞“文道合一”论到吴闿生以“文法解义理”
自方苞提出古文“义法”说,即成为桐城派之共同理论基石。方苞在《又书货殖传后》中提出: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3]P59
就方苞对于“义法”之定义来源看,其源自《春秋》义法;就“义法”之阐释方式说,其依托《周易》以敷衍。故而方苞行之于文的审美规范,实际上是“宗经”观念下的产物。进一步说,就是将六经作为文章写作的取法对象。
郭绍虞先生谓:“盖望溪所谓义法,可视为两个分立的单词,也可作为一个连缀的骈词。由分立的单词言,则义是义,而法是法,义法之说,即所以谋道与文的融合。由连缀的骈词言,则义法又是学古之途径,只成为学文方式而已。”[4]P375则方苞之古文义法,重视义与法的独立与争鸣,亦强调道与文的交融。方苞依据《周易》将其古文义法之“义”表述为“言有物”,此之“物”自有其限定范畴。如方苞曾对归有光之文提出批评,并认为归氏之文“袭常缀琐,虽欲大远于俗言,其道无由”,[3]P117故“震川之文于所谓有序者,盖庶几矣,而有物者,则寡焉”。[3]P117也就是说,在方苞义法理论的判断下,归氏之文论“法”则尚可,但其文所表现的生活日常之琐事则不在“物”的范围。所以论“物”,归氏文“则寡焉”。而方苞所提倡的“物”,即“道”。《答申谦居书》中有言:
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为伪。[3]P165
“本经术”是指桐城派文学家们所强调的“文本于经”的审美观念及思想准则,“依于事物之理”则是要以世间万物所体现的事理作为依托。所以方苞所强调的“物”,或者说文章之“道”,便是将经学的思想准则应用到世间万物之事理的解读之上。故而方苞之“义法”论,即强调文章中“文道合一”的审美规范。
桐城大家吴汝纶之子吴闿生(1877-1950),曾留学东洋,在传统文化受西学冲击而普遍受到质疑的大背景下,受到传统与新式教育的吴闿生跳出了传统视野的拘囿,重新审视《左传》与桐城义法理论。《左传微》书前曾克端序言曰:“《左氏》一书,传孔门微言,为百世文章宗祖;其晦乱否塞,于诸书为尤甚。”[5]P1所以吴闿生作《左传微》,专以“发明《左氏》微言为主”[5]P1。这说明,相对于方苞在《左传》中求文章之根坻,吴闿生则以成熟、完善的桐城文法系统反在《左传》中求其“微言”,继而借“微言”寻《春秋》“大义”,创制了以“文法解义理”的独特路径。
如,方苞在《左传义法举要·城濮之战》的义法分析中,多次涉及对晋文公形象的评陟。例如:
晋侯惟有德,故能上德也。[6]P15
亦见晋侯有德有礼而保施,又与避三舍以报楚相映。[6]P15
晋侯有德有礼而勤民,具见于此。[6]P17方苞认为“此篇言晋侯有德有礼而能勤民,所以胜”[6]P19,此为“义”;而“与避三舍以报楚相映”“具见于此”等为文章之“法”,实际上是在《左传》如何融合“义”“法”角度作文章学的提示。而在《左传微》的阐释系统中,则讲求通过研求文句深意,突破传统上的晋文形象,重新将晋文建构为一个“表里不一”的负面人物。如斥责晋文之“假仁义”: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文之教也)此段铺张晋文之重信义,然实写其信义皆临时措办耳。“于是乎”字凡三见,所谓假仁义也。[5]P115-116
揭露晋文“狐疑虚怯”:
晋侯患之,公疑焉,是以惧,皆叙晋侯之狐疑虚怯,即以为文字章法。[5]P116
吴闿生凭借对《左传》的文法分析,揭露了晋文公性格的缺陷,显示了晋文之霸的背后,更多的是战事、国事中的算计和力量的角逐。我们有理由相信,吴闿生对于《左传微》之“微”的解读方式,其实是在《左传》文字的深曲委婉处寻绎其幽微意旨,即以“文法解义理”。
在“文法解义理”方法的指导下,吴闿生亦极其注重咀嚼文字背后的褒贬意味,注意解析文章结构中的义理涵义,并强调前后文的联系。如《晋文之霸》篇的叙事中虽充斥着对晋文公德行的称许,但吴闿生通过文法分析得出了与传统完全相反的结论。在温地会盟中,晋文公以诸侯的身份而召天王,故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8]吴闿生评价说:
德者,明晋侯之不德也,前路铺张策命,极其堂皇,忽于此处揭出不臣之实,一字之诛严于斧钺矣。[5]P121
孔子当然是为君子讳,但当吴闿生尝试解码孔子所谓“明德”的对象时,并没有拘囿于传统的经师观点,而是通过比对前后叙事文字中的缝隙——例如“于是乎”“患”等——重新搭建晋文的形象框架。
植根于经学的桐城派义法说,从方苞“文道合一”的文章学理论到吴闿生以“文法解义理”阐释学方式,体现了渐趋成熟的文论对经学根坻的反哺,亦影响了《左传分国集注》的义理阐释方式。
二、《左传分国集注》对《左传微》“文法解义理”的接受与适用
吴闿生在《与李右周进士论〈左传〉书》中提出《左传》“文法之奇,总其大要,约有数端”,包括“逆摄”“横接”“旁溢”及“反射”四端。这四种方式是吴闿生以文法解读《左传》义理的重要手段,而韩席筹在编纂《左传分国集注》时亦注重此四法的继承与运用。
第一,对于“逆摄”文法的接受与运用。吴闿生解释“逆摄”为“吉凶未至,辄先见败征”[5]P1,对于此种叙事,韩席筹不仅集引吴评,而且注意在吴氏的观点上阐述己论。例如《楚昭厉之争》篇首传文:
郑公子忽在王所,故陈侯请妻之,郑伯许之,乃成昏。八年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辛亥,以妫氏归。甲寅,入于郑。陈针子送女。先配而后祖。针子曰:“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5]P25-26
对此,吴评曰:
《左氏》此等处最多,皆逆摄后文成败,用笔特为惊矫。[5]P26
对于公子忽失礼之描述,吴闿生借文法点拨,视其为见逐见弑的预示。据上述,“逆摄”指的是失礼失德而导致严重后果的叙述模式,包括征兆、预言等内含因果关系的叙事。韩席筹亦言公子忽的失礼行为,曰:
忽奉父命逆妇,本未失礼,惟忽在王所,宜反郑告祖,而后如陈,不当先逆而后告祖也。昏姻为人伦之始,稍一失礼,即开成败,可惧哉![8]P497
正因为公子忽逆妇时的失礼之举,导致了其悲惨结局。《左传》传文很少直接表明因果的逻辑,而是通过叙事的过程表现出来,所以吴、韩二人对于事件发展过程极其关注,并不断挖掘叙事过程中的隐微。
第二,对“横接”的接受。吴闿生解释“横接”为“必然之势无可避免,而语意所趋未尝径落……必有所借而后入,必有所附而后申”[5]P1。例如《左传分国集注·臧孙纥出奔》传文:
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孙曰:“无辞。”将盟臧氏,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而问盟首焉。对曰:“盟东门氏也,曰:‘毋或如东门遂不听公命,杀嫡立庶。’盟叔孙氏也,曰:‘毋或如叔孙侨如欲废国常,荡覆公室。’”季孙曰:“臧孙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门斩关?”季孙用之,乃盟臧氏,曰:“无或如臧孙纥干国之纪,犯门斩关!”臧孙闻之,曰:“国有人焉,谁居?其孟椒乎!”[8]P94
《左传分国集注》引吴氏评曰:
横接处,飘逸而入。[8]P94
传文前以“臧孙纥致防而奔齐”结臧氏立后一事,突以盟誓“横接”而入,借季武子废长立幼及斩关以出事插入,亦借出奔之事而延伸。臧孙纥的真正罪证应该是帮助季武子立幼子为储君,但在盟誓时,季武子及孟椒却巧妙地利用破坏门禁的罪行来掩盖。看似出奔之事已结,《左氏》又补叙季武子因臧孙纥出奔而盟誓一事,虽属余波,但在商讨盟会之罪行时,亦点出“不听公命,杀嫡立庶”“欲废国常,荡覆公室”的事实真相以收束全篇。
第三,对“旁溢”的接受与阐发。吴闿生解释“旁溢”为“假轶事小文肆为异采,则其横溢而四出者也”[5]P2。如“蹇叔哭师”例:
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8]P703-704
《左传分国集注》引吴评曰:
此精神旁溢处,俶傥诙丽,极文章能事,后人无能及之者。太史公所以不如左氏,止争此等,他更无论矣。[8]P704
蹇叔言谏不被采取,故先哭师,后哭子,事极自然,顺承而下。且取事风趣,文情四溢,紧张的战事在此稍得缓和的空隙。所谓太史公不及之处,指荆轲《易水歌》之文,吴氏以为在“蹇叔哭师”这种轶事的刻画,是对传文义理的情感性表达,是《左氏》胜《史记》之处。然韩席筹评曰:
此言秦穆违蹇叔而以贪勤民,且逆摄下文素服郊次哭祭,而追悔靡及也。读者宜善体会传文精神,毋以辞害意也。王引之驳杜解而申证其说,且谓与邲之战逢大夫指木尸子相类,实则似是而非,其不合传意与杜相若也。谓蹇叔能逆料晋必邀击秦师匹马只轮不返则可,若谓预戒其子必死二陵间,以备收骨,则拘泥。……执此以读《左氏》,则精神尽失矣。[8]P703-704
韩席筹以为“蹇叔哭师”事,不仅逆摄后文素服郊次哭祭,亦是表现人物情感、体现《左传》传文义理之处。所以在解读“蹇叔哭师”时,不能拘泥于字面的文辞,而是要体会《左传》传文背后的隐微,与《左传微》强调对隐微的挖掘一脉相承。
第四,对于“反射”的接受与应用。吴闿生解释“反射”为“言出于此,意涉于彼,如汤沃雪,如镜鉴幽。若此者,皆其相反而益著者也”[5]P2,与方苞所说的“反对”相类。如《左传分国集注·晋灵之弑》篇郤成子言曰:“贾季乱,且罪大,不如随会,能贱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无罪。”[8]P295《左传分国集注》下引吴注曰:
“贱而有耻,柔而不犯”,皆阿曲从谀之谓,非真以此誉士会也。乃反射诸人得罪于赵氏者,皆不肯阿附之者耳,此为微曲深至。[8]P295
吴闿生从文法角度提出,“贱而有耻,柔而不犯”是阿曲之词,并非郤成子之识人,而着意在反射得罪赵氏者。相对于吴氏揪郤成子言语之文法大发议论,韩氏则从句读角度切入,解释潜藏在郤成子语中的反射文法。韩席筹评曰:
仍宜读会字句绝,能贱者,能处卑贱也,贾季惟不能贱,故一易中军而遂作乱,随会能贱而有耻,故后日执政,急流勇退,以已晋乱,且此能字与上能外事能字相映为章法。[8]P295
韩氏借郤成子口出之以反衬,将贾季之不安贫贱而作乱与随会之安于贫贱而于邲战急流勇退“反射”,以示士会才能对于晋国的必要性。是以两者相对就像热汤浇雪,效果极其明显。
总言之,受到《左传微》以文法解读义理的影响,《左传分国集注》非常注重对于《左传》文法的阐释,不仅注意吸纳《左传微》的合理评注,亦注意以文法解读义法手段对《左传》传文加以阐释。而在逐渐的接受过程中,《左传分国集注》亦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义理阐释方式。
三、《左传分国集注》与《左传微》义理阐释进路之比对
《左传微》阐释义理以评注的方式随文见义,而《左传分国集注》以集注体综合运用了文法、尾评、考据等方式进行义理阐释,且所引注文常与作者观念不同,体现出百家争鸣的特色。
例如在《左传微·隐公之难》中,在“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5]P2传文下,吴闿生引其父吴汝纶之语评曰:“此等迂曲之说决非左氏之手。”又加按语曰:“凡《左传》中解释经文者,大率皆后之经师之所附益,读者不可不知也。”[5]P2当吴氏改编《左传》为纪事本末体后,以为这条传文在《左传》的文本系统中显得极其突兀,即方盛良先生所讲的“解释经义的句子与文法不合”[2],并将之归罪于后世经师所改。解读《左传》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判断哪些部分体现了春秋时代的意识形态,哪些部分含有后世的修辞方式。韩席筹在爬疏此条传文时,肯定了吴氏父子之说,但态度更加审慎。韩氏首先引用《谷梁传》文:“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又加按语谓:“此说是也,妇人无外行,于礼当系夫之谥,妾不得体君,不得已而系之子,仲子系惠公,而不得系于孝公,亦犹成风系僖公而不系庄公耳。左氏于文公九年秦人归赗事记之甚明,而此乃以桓公之母未薨而赗何也。”[8]P40韩氏将《左传微》中解释模糊的“经师窜入说”转化为义理的考据上,解释更加圆融。显然,《左传微》及《左传分国集注》两书不仅在义理观点上存有分歧,在揭示义理之进路上亦有差别。
继以郑庄公的案例加以详述。《郑共叔段之乱》篇主要记述了“郑伯克段于鄢”事,吴、韩二人对此事的看法略同。吴氏在篇题按语下言:
此篇以诛庄公之不孝为主。[5]P6
韩氏尾评曰:
然吾谓庄公不友之罪小,不孝之罪大。[8]P494由上可知,两者都强调了郑庄公的不孝之罪。当我们选择遵从文本表层的指向去审视郑庄公的行为,会发现庄公实际上并未有太多逾越之举。而“君子曰”的评断,便是庄公过失的总结。但竹添光鸿认为:“考叔固非孝子,庄公亦非孝感之人,君臣机诈相投,以欺一世。而君子之论如此何也。古人宽于责恶,而急于劝善,故一有改恶迁善之举,则录其见行,而略其隐衷,忠厚待人之道然也。”[9]包括竹添氏在内大多数读者都倾向怀疑这段叙事的表层涵义,他们都相信文本背后隐藏了庄公的真实形象。所以《左传微》评注将批评的言论几乎集中在了郑庄公身上,例如说他狡狯阴狠:
必欲杀弟,偏作爱之之言,狡甚。[5]P6
前数层状写郑庄之阴狠险诈,穷形极态。至“可矣”二字,始为揭破。[5]P7
讥讽其不孝不悌:
词气中便已不知有母。[5]P6
不知有弟,而已有死之之意矣。[5]P6
可见吴闿生利用文本表层下的缝隙,将这种隐晦的叙述转为直接的判断与评价。而对于庄公的负面评价以及对共叔段性格评价的忽略,与《左传》中的表层训诫背道而驰。但吴闿生这种得之于“以文法解义理”的阐释方式,即单一地通过发掘文本间“寄意于幽微,托趣于绵邈”以解读《左传》义理的方式,总归是一家之言。相对之下,《左传分国集注》的综合体例似乎更能吸收百家之长,如吴曾祺《左传菁华录》对庄公的正面评价,韩氏亦一并收入。体例上的优势,给予了《左传分国集注》更多解释的空间。《郑共叔段之乱》尾评曰:
叔段之乱,胡康侯专罪郑伯,冯氏《解春集》驳之,二说皆有所偏,而冯氏尤甚。夫段以庄元年就封于京,日以田猎骑射为事,多材好勇,渐蓄异志,完聚缮兵,欲为桓叔之病翼,蔡公之入郢,不臣不弟,信有罪矣。庄公逐之,似不为过。……然则胡传专罪郑伯,固不能无偏,冯氏之专罪叔段,称郑伯仁厚,其偏不尤甚乎![8]P493-494
在韩氏看来,郑庄公虽是祸首,但像胡康侯专罪郑伯的观点亦不可取。共叔段田猎骑射,练兵买马,暗结姜氏,也是不臣不悌之行,所以只批评一端的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总言之,相对吴闿生着眼于文本表层下细微处的解读,韩席筹更强调对文本所体现的人物形象进行整体概括与归纳,综合运用文法、尾评、考据等手段进行体会传文的主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