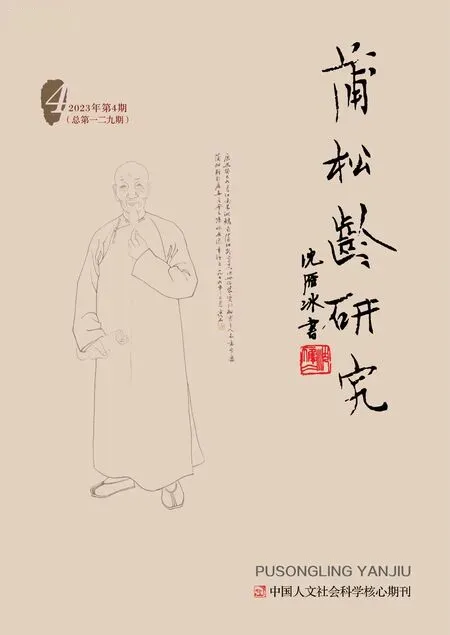《牡丹亭》与《香玉》中的“至情”之比较
党月异
(德州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德州 253023)
从晚明到清初,汤显祖和蒲松龄两位大作家分别在《牡丹亭》和《香玉》中发出同样的呼声,汤显祖在《牡丹亭还魂记题辞》中说:“如丽娘者,乃可谓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①本文所引《牡丹亭》原文,均出自汤显祖著《牡丹亭》,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以下不再一一注明。蒲松龄在《香玉》中三次提及“至情”,“妾以年少书生,什九薄幸;不知君固至情人也”“报君喜信:花神感君至情,俾香玉复降宫中”“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花以鬼从,而人以魂寄,非其结于情者深耶?”②本文所引《聊斋志异》原文,均出自蒲松龄著、朱其铠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年版。以下不再一一注明。二人都提出“情之至”的至情言论。追根溯源,可以说,《香玉》是对《牡丹亭》至情论的遥相呼应和进一步的情感书写,是对明晚情感话语的自觉延伸与有意回响,其中有继承也有发展和突破。《聊斋志异》中关于至情的故事貌似很多,如《阿宝》《连城》《瑞云》《莲香》等,但是只有《香玉》一篇明确提出“情之至”概念,与汤显祖《牡丹亭》形成明确的对应关系,是作者有意视之为“至情”代表作还是偶然留痕,值得深思。有学者也注意到《香玉》的特殊性:“《连城》之外,能达到汤显祖所谓‘情之至’高度的还有《莲香》《香玉》《陈锡九》等篇,其中,以《香玉》最为突出。”[1]152可以说,清初《香玉》和晚明《牡丹亭》建立了一种明确的对话关系。蒲松龄与汤显祖可谓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梳理从《牡丹亭》到《香玉》中至情文化谱系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汤显祖的至情思想及对蒲松龄的影响
中国文学史的情感书写由来已久。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2]278晋以后,言情文学有进一步表现,但没有相关理论内容表述。明代哲学开始转向人的内心追寻与探索,阳明心学盛行一时。由“心”及“情”,在文学领域掀起一股重视情感本位的思潮。明人关于“情”的阐释非常具体丰富。汤显祖的授业老师罗汝芳有“赤子之心”说:“天初生我,只是个赤子。赤子之心,浑然天理。”[3]764李贽说:“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情者,天地万物之真机也,非感,其何以见之哉!”[4]171随后袁宏道则曰:“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5]188汤显祖深受其老师罗汝芳及李贽影响,他说:“如明德先生(罗汝芳)者,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紫柏)之雄,听以李百泉(李蛰)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6]1229在时代思潮的裹挟之下,“情”成为汤显祖的毕生追求和理想。他认为情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天性:“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7]275重情,是晚明文学家共同的思想特点,而汤显祖则将这个“情”,强调发挥至极点。《牡丹亭》是其“至情”说的代表作,杜丽娘因情成梦,为情而死,死而复生的情节体现了“至情”感天动地的神奇力量。考察汤显祖的生活和时代背景,他的“情”字,是与宋明之“理”相对抗的,是站在阳明心学的立场来反对程朱理学的。其《牡丹亭还魂记题辞》说得很明确:“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显然,汤显祖的“至情”思想是在情与理的冲突中形成,呼唤的是精神的自由和个性解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关于汤显祖对蒲松龄的影响,显然有很多证据可以支撑。康熙九年(1670),蒲松龄应同乡宝应知县孙蕙邀请去宝应县为其做幕僚。此次远行,蒲松龄邂逅了孙蕙的小妾、扬州才女顾青霞,并为顾青霞赋诗多首。《伤顾青霞》是蒲松龄哀悼顾青霞的病逝:“吟音仿佛耳中存,无复笙歌望墓门。燕子楼中遗剩粉,牡丹亭下吊香魂。”[8]676这首诗提及“牡丹亭”,显然是借用汤显祖《牡丹亭》的旨意,意谓渴望顾青霞的香魂能像杜丽娘因情而生。此外,《聊斋志异》中有很多婚恋故事包含离魂和死而复生的情节,与《牡丹亭》叙述结构非常相似,如《连城》《阿宝》。很多学者也注意到《牡丹亭》与《聊斋志异》的关联,王士禛评论《连城》道:“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9]533直接点出了汤显祖对蒲松龄的影响。《阿宝》写孙子楚为了追求阿宝不惜切断枝指、离魂化鸟,各种非常人之状。冯镇峦评:“此一情痴与杜丽娘之于柳梦梅,一女悦男,一男悦女,皆以梦感,俱千古一对情痴。”[9]1717也指出蒲松龄与汤显祖心灵相通的不谋而合。
从以上可见,汤显祖《牡丹亭》的至情思想对蒲松龄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具体到《牡丹亭》和《香玉》的关系,可说是有千丝万缕的意脉相连。在《游园惊梦》中,保护杜丽娘和柳梦梅云雨欢幸的是掌管南安府后花园的花神,此花神“专掌惜玉怜香”。杜丽娘游赏的后花园牡丹亭中有诸多牡丹花,而《香玉》中主人公偏巧是牡丹花仙,名字偏巧叫香玉,是巧合还是蒲松龄对《牡丹亭》的有意借而为之?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说《牡丹亭》构成蒲松龄创作《香玉》的前文本,也成为他对话的潜在对象。
二、《香玉》和《牡丹亭》至情思想的异曲同工
《香玉》和《牡丹亭》在至情思想的表达上可谓异曲同工,两部作品的叙事逻辑、情感生成特点、奇幻之笔及诗化色彩等方面都遥相呼应,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一)叙事逻辑都是“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因爱重生
两部作品的至情思想都是通过非常态的形式表现出来,主人公杜丽娘和香玉都经历了由生到死,死后成鬼,因爱而复生的奇幻过程,表达了真爱可以战胜一切的至情思想。至情观念强烈影响着叙事逻辑、叙事走向。至情是两部作品叙事走向共同的推进力,使得“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死而复生这类叙事结构的出现和中国的生命哲学密切相关,中国生命哲学的特点之一在于强调生生不息的往复循环,大到天地自然,可以五百年沧海桑田轮转,小到个人生死,也可以有“三生石上旧精魂”的来生期待。《牡丹亭》和《香玉》把“死而复生”这一蕴涵着传统哲学密码的命题提升到一个至高的境界,通过“死而复生”来获得爱情的圆满,复活的不只是生命,更是在无望生活中的美好爱情。
杜丽娘因为《关雎》开启了青春觉醒的大门,因为游园赏春倍感青春的寂寞孤独,有了向爱之心。在梦境中与柳梦梅共享云雨之欢是杜丽娘青春意识和本能觉醒的表现,这种觉醒在杜丽娘的精神世界掀起狂风巨浪,最终寻爱不得而撒手人寰,体现了“生者可以死”的至情力量。杜丽娘由生到死的经历,是对“至情”理想的追求,死亡不是感情的终结,而是一场凤凰涅槃,是向爱而生的前奏,是主人公摆脱现实束缚、实现自己理想的起点。《魂游》《幽媾》描写杜丽娘的鬼魂追寻梦中情人并大胆与之幽会。与柳梦梅双向奔赴的至情重新点燃了杜丽娘的生命之光,她得以重返人世间,体现了“死可以生”的至情特点。杜丽娘是作者理想中“情”的代表人物,围绕她因情而死,死而复生,展现了作者的“至情”理想。
《香玉》中,黄生无意中窥见香玉,心生爱慕,追寻无果后在树下题诗。香玉感于黄生的风雅与深情,自荐枕席。其后香玉被移而枯,黄生作哭花诗五十首,日日临穴涕泣。绛雪有感于黄生对香玉的至情,愿意以朋友的身份陪伴黄生。花神终于被黄生一往情深的至情感动,香玉得以以花鬼之形出现在黄生面前,并嘱咐黄生,须经一年的用心培植养护,她才可以从花鬼变为花仙。在黄生精心呵护下,香玉终于重返花仙之席,这就是和《牡丹亭》如出一辙的“死可以生”的至情力量。黄生死后,寄魂于牡丹花下,是一棵长有五片嫩叶的红芽,与香玉、绛雪为邻。不想数年后被小道士砍去,牡丹、耐冬也随后憔悴而死。这也是《牡丹亭》所讴歌的“生者可以死”的至情境界。黄生、香玉、绛雪从相遇相知到相守相依、不离不弃,都是至情至义之人。香玉为了爱可以大费周章地重生,香玉、绛雪为了爱与友谊可以义无反顾地选择死亡,黄生也因为爱可以淡泊从容地面对死亡。至情至爱面前,生和死都不是问题,再次验证了汤显祖《牡丹亭》所说的“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的至情理想。
(二)情感生成特点都是由欲到爱的人性升华,肯定“欲”和“色”
至情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渐升华、逐步发展的。杜丽娘在春梦中对柳梦梅只是青春的欲望和冲动,无多少感情可言。三年后她的鬼魂回到人间,找到柳梦梅,此时他们的关系仍然停留在欲望和本能的满足上。杜丽娘是抱着“趁此良宵,完其前梦”的愿望与之幽会,满足于肌肤之亲:“每夜得共枕席,平生之愿足矣。”而柳梦梅自拾得她的画像后,所想的也不外乎是希望“梦里相亲,春风一夜”。随着情节的发展,二人的爱情逐渐升华到情爱之爱,杜丽娘逐渐了解到柳梦梅为人处世的魅力,感受到被爱、被尊重的温暖和呵护。比如,为了杜丽娘他敢冒被斩首的危险开棺,使杜丽娘重返人间;为了杜丽娘的心愿,他在战乱中替她打探父母的下落;也为爱忍受了杜宝的奚落和责打。因而,杜丽娘再三赞赏柳梦梅的诚信、担当和能力:“有我那信行的人儿,他穴地通天,打听的远。”这些美好的人性光辉都使杜丽娘的爱情更加稳固并得到升华,也进一步激发了杜丽娘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在她刚刚生还后,还说“必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鬼可虚情,人须实礼”。随着情爱的深厚,杜丽娘对封建理学教条进行了激烈地抗争。当父亲问她:“保亲的是谁?……送亲的是谁?”她针锋相对,理直气壮:“保亲的是母丧门……送亲的是母夜叉。”至此,她的情爱达到了极致,他们的情爱之路显然是逐渐升华的。
《香玉》中的主人公也是经历了由欲到情的过程,交往由重色向重情发展。黄生在下清宫看到两位艳丽女郎后情不自禁地追逐,吓得两位女郎慌忙逃走,显得举止轻薄有失斯文。在见到黄生的题诗后,香玉觉得是同道中人,于是二人幽会。此时,他们的关系还是停留在简单的男欢女爱的浅层次的满足。后来香玉死去,黄生体会到了失去的痛苦,依香玉之言,每日浇灌,用心培植,耗时一年,香玉终于复生。而香玉做了花鬼后也惦记黄生,怕他孤单寂寞,嘱托绛雪“陪侍郎君”。二人的感情成长是彼此奔赴的,他们的感情经过时间的考验愈加坚固,从而超越了最初的乍见之欢,感情得以升华。
值得注意的是,《香玉》和《牡丹亭》两部作品都在很大程度上对“欲”和“色”进行了肯定描写,都是在“欲”的引导下才发展为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明至清初的时代思潮———肯定人的情欲。传统的儒家思想对人欲向来持否定态度,尤其宋代理学家更是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明中叶以后,在阳明心学、李贽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一股个性解放的潮流,文学作品开始突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对性爱有了大胆的肯定描写。《牡丹亭·游园惊梦》中把性爱场景写得唯美自然,《香玉》对性爱也是持自然肯定的心态。爱情是基于身体的情感,当然离不开身体的吸引力,植根身体的情感是自然也是人道,这是爱情的特质。弗洛伊德说:“爱情是建筑在直接的性冲动和其目的受抑制的性冲动同时存在的基础之上的,而对象则将主体的一部分自恋性自我力比多引向它自身。这是一个只能容纳自我和对象的情况。”[10]154《香玉》和《牡丹亭》对人本身欲望的肯定描写,显示了明清以来思想的发展趋向。
(三)都以奇幻之笔写至情之美、至情之深
中国的爱情故事总离不开鬼神气息,反映出爱情在现实中难以企及于是转而追求在幻境中达成。以奇幻之笔写极致之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惯常手法。两位作家都通过悖于常规的物象和悖于常情的行为来表现至情的极致之美,两部作品恋情的发展都置于非现实的情况下,前者是通过入梦以及死后变鬼来实现,而后者是人与花仙、花鬼的爱情,鬼神成为解决现实矛盾的工具或方式。以奇幻笔法写情,有助于增强至情的艺术感染力。
《牡丹亭》中,一对陌生男女在梦中相会交合,一奇也。“转过这芍药栏前,紧靠着湖山石边。……两情和合,真个是千般爱惜,万种温存”,这一场云雨欢会,景美、人美、情美,浪漫唯美,以极幻世界写极致之情的极致之美。杜丽娘因梦而亡,慕色而亡,又一奇也,说明有情而不得、直教人生生死死的巨大能量。冥府之内,丽娘现身,判官感念杜宝功勋,放杜丽娘出枉死城,又一奇。柳梦梅卧病梅花观中,捡到杜丽娘的自画像,竟然动了心,又一奇。杜丽娘鬼魂主动找到柳梦梅,人鬼同枕,又一奇。柳梦梅开棺使杜丽娘复活,又一奇。二人情缘竟然惊动皇上,最终由皇帝裁决“敕赐团圆”,又一奇。在作者精心布局的重重奇幻中,展现了至情的情之深、情之美、情之感天动地的惊人力量。
“蒲松龄常通过幻化人物的神异性表现至情,奇幻人物具有世间常人所不具备的神异性,使现实中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最大限度地表现极致之情。”[11]12《香玉》中的牡丹花仙幻化为人,与黄生遇合,其后罹难又变为花鬼,花鬼又变成花仙,重新幻化为人,黄生死后竟然也变为牡丹赤芽,这一切都以极幻之笔写极致之情。《香玉》也以幻笔写出了至情之美,香玉从绽放的牡丹花蕊中“飘然欲下”复活重生的场景,是如此唯美:“次年四月至宫,则花一朵,含苞未放;方流连间,花摇摇欲拆;少时已开,花大如盘,俨然有小美人坐蕊中,裁三四指许;转瞬飘然欲下,则香玉也。”幻化场景中花美、人美、情更美,更是幻中见至情。正如但明伦所评:“种则情种,根则情根,苞则情苞,蕊则情蕊……无限深情,一时全绽。”[12]1554用力绽放的不只是牡丹花朵,还有黄生与香玉的无限深情。
(四)至情思想都有诗化的色彩
《香玉》和《牡丹亭》两部作品的男女主人公都用诗句传情达意,倾诉衷肠,使得至情思想充满诗化色彩。
杜丽娘临死前在自画像上题诗一首:“近睹分明似俨然,远观自在若飞仙。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后来此诗成为杜、柳二人遇合的重要依托和媒介,既是杜丽娘对来世姻缘的希冀,又开启了柳梦梅接纳杜丽娘的契机。柳梦梅在捡到画像看到题诗后,心神摇荡,和诗一首:“丹青妙处欲天然,不是天仙即地仙。欲傍蟾宫人近远,恰如春在柳梅边。”这样的唱和之诗,不但是情节上的呼应,也使得他们的至情充满诗意美感。
《香玉》中,连接黄生和香玉与绛雪关系、推动他们关系发展的也是彼此的诗词唱和引发的心意相通。黄生偶遇香玉,题诗:“无限相思苦,含情对短缸。恐归沙吒利,何处觅无双?”香玉本不想与之结交,看见黄生的题诗,觉其是风雅之士,因而主动前来就之,并和诗一首:“良夜更易尽,朝暾已上窗。愿如梁上燕,栖处自成双。”在香玉被移走后,黄生写诗怀念:“山院黄昏雨,垂帘坐小窗。相思人不见,中夜泪双双。”绛雪感动之下和诗一首:“连袂人何处?孤灯照晚窗。空山人一个,对影自成双。”唱和之中,引发了友情的增长和递进。香玉死后,黄生做哭花诗五十首,也赋予了他们的情爱诗化色彩。《香玉》中的诗是连接爱情和友情的纽带,与《牡丹亭》如出一辙,使得至情世界充满诗意。
另外,两部作品中都用了情景交融的笔法,创造出一种诗的氛围和意境。《牡丹亭》中杜丽娘在游园中的一段心声历来被人认为是诗情画意、情景交融之笔:“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此一段虽是言说青春的觉醒与苦闷、春色的繁华与凄凉,却也赋予杜丽娘的至情一种诗化的美感。《香玉》中一开篇,香玉和绛雪的出场如同一幅动态的美人美景图画:“素衣掩映花间……袖裙飘拂,香风洋溢,追过短墙,寂然已杳。”可谓人去留香,美不胜收。黄生死后,“次年,果有肥芽突出,叶如其数。道士以为异,益灌溉之。三年,高数尺,大拱把,但不花”,黄生变为花,与香玉相依,显然是一种诗化的处理,充满了艺术的美感。
三、《香玉》和《牡丹亭》至情思想的同中有异
虽然《香玉》和《牡丹亭》在至情思想上有继承也有一致性,但由于时代不同、作家经历不同、审美理想不同,两部作品在创作初衷、至情内涵、至情主体、创作视角、价格指向等方面显示出诸多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蒲松龄对至情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
(一)创作初衷不同
《牡丹亭》体现了反抗程朱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呼声,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追求至情更自觉。产生于宋代的程朱理学真正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始于明初最高统治者把它定为官方哲学,极大强化了礼教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尤其是对女性的束缚更加严苛,明代节妇烈女数量之多远超前朝。但是随着明代后期资本主义的初步萌芽,新的思想意识和新观念也在不断形成,如王阳明的阳明心学,罗汝芳的人欲合理性的论调,李贽的童心说等观点,都肯定了人的正常欲望,与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程朱理学针锋相对。汤显祖的“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的观念,正是在这种情与理正面交锋的时代思潮中产生的。《牡丹亭》的创作主旨是以情反理,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礼赞像杜丽娘这样的有情之人,肯定了至情的美好与崇高,给明代女性以极大的心理鼓舞。所以《牡丹亭》一经问世,立刻得到当时很多青年女性的共鸣和认同。
《香玉》更多是蒲松龄困顿孤单生活中的梦幻之笔,是蒲松龄落寞失意人生的精神补偿与自我慰藉。《聊斋志异》很大程度上是蒲松龄借谈鬼说狐表现自我情怀,《葛巾》《小谢》《绿衣女》《连琐》等,都是写一位书生寂寞读书之时有少女来就,彼此吟诵或嬉戏,令清冷的书斋充满欢乐和生机,几番相会后方知其为狐鬼花妖。联系蒲松龄的生活经历和婚姻状况,这些创作可以视作是蒲松龄在寂寞苦闷的生活境遇中而生发的幻想世界。蒲松龄有几十年在家乡缙绅毕际有家坐馆,返家时间有限,夫妻聚少离多,难免孤单寂寞丛生。他在《家居》写道:“久以鹤梅当妻子,且将家舍作邮亭。”[8]563即便家有贤妻,也难免滋生红颜知己、红袖添香的憧憬,从而营造出快意人生的文学场景。反映在《聊斋志异》创作中,便是书生与各类女子的奇幻际遇,《香玉》中的香玉和绛雪形象便是如此。
简而言之,《牡丹亭》重在鞭挞社会现实,《香玉》重在憧憬个人理想。
(二)至情的内涵不同
《牡丹亭》的主旨是以情反理,其中的“情”是一个同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规范相对立的范畴,是作为“理”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它一方面指男女爱情,一方面指人本能的欲望,包含有个性解放的思想。杜丽娘的形象显现出思想解放与生命自由的人文主义光辉,面对爱情的萌生,她勇敢去寻梦,为此她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面对梦中情人柳梦梅,她热情主动;面对以父亲为代表的封建伦理规范体系的打压,她强硬发声。在杜丽娘全力追寻爱情的过程中,她所受到的封建礼教的熏陶,随着欲和情的增长不断瓦解,在追求个性解放道路上越走越远。因此,《牡丹亭》的至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理学的桎梏与牢笼,包含了个性解放、生命自由的人文主义思想内涵。
《香玉》中的“情”除了爱情和欲望之外,还有友情、知己之情、道义之情等,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双美”模式,描绘了一种男女关系的新境界,体现出作者对于爱情与友情两种至情的渴望和追求。《牡丹亭》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的至情实现是一条线索,而在《香玉》中除了香玉与黄生二人这一条线索之外,还有绛雪和黄生这条至情线索。香玉和黄生相爱后,香玉不幸罹难,此为第一条线索;痛失香玉的黄生要求绛雪陪伴,两人产生了友情,此为第二条线索。对于友情,绛雪对黄生的友谊更多是道义之情。作者通过塑造“一妻一友”的双美形象,来表现香玉与黄生之间的爱情和绛雪对香玉、对黄生的友情。蒲松龄认为男女之间除了爱情关系之外,还可以建立朋友关系。他在《娇娜》篇中就表达了对于男女友情的羡慕与追求,“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这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显然是一种与封建礼教对立的思想意识。
清代但明伦准确点评了这种爱情友情并举的写法:“爱妻良友,两两并写,各具性情,各肖口吻。”[13]171美好的爱情与真挚的友情并行而来,可谓是文学作品中的一股清流,令人耳目一新。“这种一妻一友的双美模式,不仅在《聊斋志异》中仅此一例,在古代文学创作史上也是少见的。”[14]103
总之,《牡丹亭》重在至情之深,《香玉》重在至情之广。
(三)至情的主体不同
《牡丹亭》主要是写人类之间、人鬼之间的男女至情,《香玉》主要是写花妖与人类之间的至情,是跨越物种的至情。杜丽娘是人间女子,受封建礼教束缚深重,她生活的天地只有闺房和书房,逛后花园也只能背着父母偶尔为之,她代表着明代女性被禁锢的生活状态——女子整体上完全被动,没有主动社交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她在追爱的路上只能被动等待,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蒲松龄有意打破生物物种的界限,因为“至情”,所以即便是非人类的花妖狐魅都可以和人在一起。香玉是花妖,没有礼教的桎梏,她的生活范围相对于杜丽娘而言是较为广阔的,她有社交的自由,可以主动找到黄生表达爱意,她和黄生爱情的初始远比杜丽娘的爱情来得简单、轻易。杜丽娘为了爱丧失了生命,香玉虽然也丧失了生命,却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外力的搬移。《香玉》中的另一至情主体黄生,也非常规意义上的人类,他不仅能接受与异类花仙相爱,更能为了至情而变为牡丹,化身异类,从而以世俗生命的消亡,转换为爱情生命的延续。
杜丽娘作为人间女子,其功名利禄之心还是很明显的。死前自画像题诗曰:“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希望自己嫁给一个进士及第的书生。在重生后仍然挂怀此事,对柳梦梅说:“鬼魂求出世,贫落望登科。夫荣妻贵显,凝盼事如何?”柳梦梅也表达了对功名富贵的向往:“夫贵妻荣八字安排,敢你七香车稳情载,六宫宣有你朝拜。”
而香玉作为花神,自然是没有功名之心,她更注重琴瑟相和、灵肉交合的境界。黄生虽是人间男子,却借住在远离人间烟火的崂山下清宫,名义上借此读书,但通篇不见黄生刻苦攻读、穷首皓经,反而是恣意追欢,纵情享受世间美色。十几年来他一直和香玉、绛雪厮守山上,不知人间烟火为何物,从没见其参加科举,也无传统知识分子的仕宦宏图,显然下清宫是介于人世与仙界的理想国。某种意义上,黄生是蒲松龄乌托邦意义上的人间理想,没有任何世俗的牵绊与桎梏。“蒲松龄不仅在物质层面表现情,表现人欲,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为情张本,写人或异类对于真善美的自由心灵的强烈追求”“情在精神层面最值得赞美的,就是对于真善美、特别是对于所有世俗羁绊的自由的追求”。[15]3这是蒲松龄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之处。
(四)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的不同观照
《牡丹亭》是汤显祖为女性代言,从女性视角来创作此剧,关注的是明代女性面临的共性问题。明代宋明理学的桎梏与压抑使广大女性苦不堪言,杜丽娘的生存环境、贫瘠的精神世界和抑郁苦闷的心理是整个时代的投影。她艰难的追爱过程是汤显祖对于时代的控诉。
正因为从女性视角出发,自觉关注明代女性的生存境遇,所以汤显祖在《牡丹亭》的写作构思上有意利用多重空间的转换,显示人物不同的心理需求和性格成长史。具体来说就是《牡丹亭》主要设置了四重空间:闺阁空间、后花园空间、梦空间、冥空间。闺阁空间的杜丽娘畏手畏脚、谨言慎行,对父母老师毕恭毕敬,内心的欲望只能无声无息。后花园空间的杜丽娘在明媚的春光中,将心声大胆倾诉于断墙颓垣:“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梦空间的杜丽娘彻底放飞自我,和一个陌生男子共赴春梦。冥空间的杜丽娘执着于追寻爱情,主动找到柳梦梅,共结连理。四重空间的人物都以杜丽娘为主导,以她的需求推进情节的进展,以女性视角切入,更能引发明代女性的强烈共鸣,对于思想解放的推波助澜也更有效。
《香玉》显然是男性视角下对女性的意淫和幻想,蒲松龄虽然很多作品肯定女性的才华与智慧,对女性有足够的重视,但是也有把女性当做附属工具的倾向,他仍然是站在男性文化中心的立场描写女性。女人是男人的附属,是从远古采摘狩猎时代延绵至今的社会潜在意识。“人类是男性的,男人不是从女人本身,而是从相对男人而言来界定女人,女人不被看作一个自主的存在。……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16]124蒲松龄笔下的女子并不具备真正的主体存在,而是作为书生寂寞生活的解药或工具而存在。“作者按照男性的意愿愿对女性进行重塑、改造,从而写出能满足他们心理的完美的女性形象,进而企图把理想变为现实,最大程度地满足男性在现实社会中的需要。”[14]104她们往往总是在书生需要的时候为他们带来红袖添香的快乐,同时对书生别无所求。《香玉》的空间叙事比较单一,仅限于黄生的书斋,也是基于男性视角的优越立场,在这种男权观照下的空间里,香玉与绛雪纷至沓来。蒲松龄并没有把这些女性置于与男性平等的位置上,多次从男性视角写黄生的愁绪孤苦,但从未站在香玉与绛雪的角度去关注她们的心理轨迹和情感需求,“从这个角度看《香玉》中爱妻良友的‘双美’模式与传统的‘双美一夫’殊途同归,都是封建文人们在男权社会中开出的一副解救男性寂寞的迷幻药罢了”。[14]110
(五)至情实现的价值指向与结局不同
《牡丹亭》中杜、柳二人更注重追求世俗爱情的价值实现,最终结局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柳梦梅状元及第,授编修院学士,妻杜丽娘,封阳和县君。汤显祖的思想除了至情论之外,还有贵生思想,他当年在被贬徐闻后,发现此地是蛮荒烟瘴之地,这里的人“轻生好斗,教育落后,不知礼仪”。汤显祖决心改变这里的状况,于1591 年修成贵生书院,并著《贵生说》。其中有言:“大人之学,起于知生,知生则知自贵,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重也。”[6]1163贵生,就是以人为本,敬畏生命、珍惜生命,无区别地看待众生,呵护众生。汤显祖“贵生”思想,使得他的至情观更注重现世的圆满与世俗幸福。虽然汤显祖的至情观是其进步思想的体现,但也不乏其局限性,《牡丹亭》没有彻底实现汤显祖以情代理的哲学宣言,未从根本上逃脱封建礼教的传统轨道,爱情大团圆的结局依旧离不开状元及第、夫贵妻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最高封建统治者的裁决,仍然是在封建伦常的秩序里获得至情的实现。
《香玉》中至情实现的价值指向,无关人间烟火和仕宦功名,他们的追求更多在精神层面,是始于欲望而达于精神契合的至情境界。虽然香玉和黄生的至情最终得到了花神的恩赐,使香玉复活,但结局却是黄生、香玉相继死去,是悲剧性的结局。在迥异于《牡丹亭》的结局中,显示了蒲松龄对汤显祖至情思想的进一步超越,不同于汤显祖的“贵生”思想,蒲松龄的生死观耐人寻味,具有超脱死亡的淡然。黄生病后,其子伤感,黄生不以为然,笑曰:“此我生期,非死期也,何哀为!”在《章阿端》中,蒲松龄曾说:“情之所钟,本愿长死,不乐生也。”同样表达了作者对于至情与生死的看法。黄生不惧死亡,认为死亡是生期,非死期,因为可以永远伴随相爱的人左右,是一件幸事。但最后黄生所谓的“生期”愿景并没有持续多久,三株花先后被斫去、憔悴死,“一去而两殉之,即非坚贞,亦为情死矣”。白牡丹和耐冬殉情而死,是“至情”的表现,同时也是对现实的无奈和清醒认识。从“至情”到“情死”,是蒲松龄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回归。但三人的同时消亡,又何尝不是情死之后的一次永生,正所谓“此我生期,非死期也”,又何尝不是基于现实之后的另一种浪漫主义的至情,在人与自然天地的合一中,体现了蒲松龄对至情的终极关怀。因而《香玉》虽然是悲剧结局,却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悲剧,周先慎《说〈香玉〉》:“对于他们的死,读者感受到的……不是恐惧,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欣慰,一种哀艳的美感,甚至是一种愉悦。”[17]96
《牡丹亭》在现实与虚幻之中完成对至情的讴歌,《香玉》在乌托邦的空间中完成对至情的追求。《牡丹亭》中的至情表现主要是杜丽娘重生,而《香玉》中的至情表现除了香玉的重生,还有黄生、香玉、绛雪的从容赴死。
(六)至情路上的写实与规避
出于作家的社会使命感,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对杜丽娘寻爱之路上面对的困难是写实的,没有回避家庭、社会、时代带给她的重重枷锁,她和柳梦梅追求爱情的路上遇到了封建势力的重重阻碍,其阻力主要是来自以杜宝为代表的封建家长阵营。杜丽娘和柳梦梅追求以婚姻为目的的长相厮守非常明确,“妾千金之躯,一旦付与郎矣,勿负奴心”“姐姐嫁了小生罢”“秀才有此心,何不请媒相聘?也省的奴家为你担慌受怕”“明早敬造尊庭,拜见令尊令堂,方好问亲于姐姐”“你要小生发愿,定为正妻,便与姐姐拈香去”。历经种种磨难与挫折,二人终于缔结美满姻缘。
《香玉》的叙述采用了去背景化的方法,通过各种方式尽量淡化、消解现实矛盾冲突,以此逃避世间伦常与秩序规范,从而使得人物能够自由舒展心性、张扬个体生命。故事地点有意设置在远离人间烟火的崂山下清宫,又有意安排香玉、绛雪是不受人间礼法限制的花仙,她们可以自由接近男子,随心所欲。在黄生与香玉追求爱情的路上作者有意回避了很多的世俗性问题,比如黄生的妻子,比如黄生的科举功名,比如黄生香玉的婚姻问题等等。香玉可谓是黄生书斋生活的一道白月光。黄生明明是有妻室之人,却又任情发展,深爱香玉,直至生死相随,显然是不被世间伦理所允许。在这近乎世外桃源、自动回避很多尘世问题的环境中,黄生自由任性,与香玉、绛雪自在交往,萌生真挚的爱情和深厚的友谊。三人行是作者心目中田园牧歌一般的存在,逃离了人间伦常秩序的繁杂枷锁和羁绊,他们的相处和交往模式完全屏蔽了封建礼教的重重樊篱。香玉与黄生的爱情,毫无世俗的功利性,他们从没谈及婚嫁问题,不以婚姻为旨归,从没要求长相厮守,也从未谈及“傍蟾宫”这些沉重功利的话题,只是任性自然,随遇而安,在规避现实近似“真空”的世界中,获得自由、自然、洒脱的人生体验。文学一方面要反映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另一方面也有责任提供理想。《牡丹亭》的夫贵妻荣是一种世俗的价值追求,《香玉》中跨越物种、超脱名利与生死的自然洒脱又何尝不是一种人间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