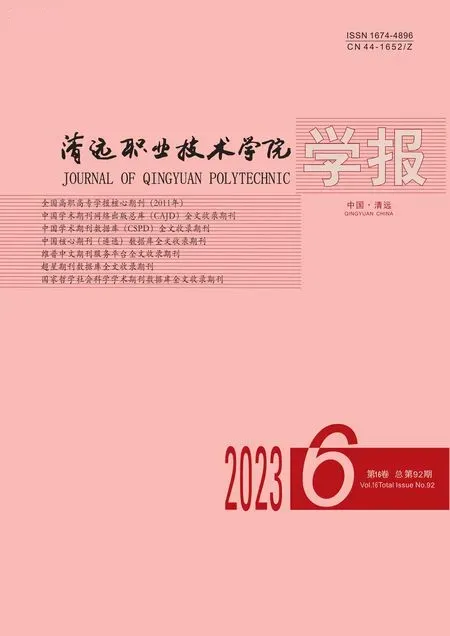薛宝钗诗观及其实践价值
钱志富,毛佳怡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浙江绍兴 312030)
笔者近日重读《红楼梦》,发现《红楼梦》中塑造的典型人物薛宝钗不仅在貌上“艳冠群芳”,不输林黛玉,而且诗才上更是与林黛玉不相上下,堪称卓绝,尤其令人惊异的是,薛宝钗较之林黛玉还有相对完整的诗歌观念,这就不得不令人要重新审视薛宝钗这个重要人物了。
1 诗歌“寄兴寓情”观及其实践
薛宝钗诗歌观的核心是,诗歌不过都是“寄兴寓情”,不“要见了做”[1]253。故事是这样的,贾府三小姐探春突发妙想,想邀请大观园诸诗人雅集秋爽斋,正巧当日贾芸正要给怡红院送来白海棠,一时成为大观园新闻,于是就将诗社临时命名为海棠社,而且择日不如撞日,各位诗翁便要做起诗来。这时候,二小姐迎春突然说,连海棠都没有观赏过,这诗怎么做呢?大观园诸诗人中,迎春不仅性格懦弱且诗才平平,对诗歌的理解是典型的“题材决定论”或者叫素材决定论,一定要亲自见过才能进行创作,所以有此一问。值得注意的是,“题材决定论”曾经占据中国现代诗歌思想的主流。诗歌“要见了做”,这是迎春的诗歌观,也是许多当代中国诗人的诗歌观念。自然,古人也有所谓“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身之所历是铁门限”的诗学命题。当迎春说完“都还未赏,先倒做诗”之后,宝钗立马回应道:“不过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见了才做”。宝钗可能害怕别人误解她轻视亲身体验对诗歌创作的决定性作用,立即补充说:“古人的诗赋也不过都是寄兴寓情,要等见了做,如今也没有这些诗了”[1]253。从诗歌创作的原理上说,题材对于诗歌创作具有一定的规定作用,而且作者一定要有相对丰富的人生阅历,诗歌本身具有某种情境特征,“见了做”也是常见的诗歌创作现象。金圣叹评杜诗,每每赞赏他在“见了做”上下的功夫。可是,“见了做”只是诗歌创作的一般性原理,诗歌的创作还有特殊性原理,就是不一定要等到见了才去做。文学理论里面有一种现实主义的理论,强调题材对于文学创作的制约作用,认为文学的创作必须来源于生活,没有生活,就没有创作。俄罗斯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更是从美学高度肯定了生活对于写作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生活是创作的美学源泉这样的著名命题。依此原理,创作者需要深入生活,细心地体察全面的社会生活。所以,“见了做”差不多就是文学或者诗歌创作原理上的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薛宝钗的这种诗歌观念是突破性的一种创见,具有某种原创性。
今天审视薛宝钗的这种诗歌观念,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一是,薛宝钗的这种诗歌观念是她对整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历史的理性总结。在她看来,诗歌创作的重点是“寄兴寓情”,而不是对客观现实冷漠地模拟和描写,诗人要抒发自己的主观情感,发表对于社会人生的主观认知,这个才是诗歌创作的重中之重。她的这种观念直接承接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诗可以兴”“诗可以怨”,诗人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主观情感,这是诗人至高无上的特权。二是,诗歌创作中由于抒发主观的情志必然引发一种想象力爆发的神思,这种神思能够突破现实世界的物理时空,进入一种灵性的心理时空,诗人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刹那间缤纷的意象纷至沓来。薛宝钗当然没有对她自己的诗歌观念进行理论性阐发,可是她一提出这样的见解,愚钝如迎春这样的人也立马响应,马上就启动诗社的组织工作,让各位诗翁进入诗歌创作的准备状态了。探春和林黛玉及薛宝钗等各骋诗才,启动神思,在没有见到白海棠的情况下提交了满意的诗歌答卷。探春写出了“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林黛玉写出了“偷来梨蕊三分白,借来梅花一缕魂”,而薛宝钗写出了“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这样的妙句。果然,诗歌是可以在不见原物的情景之下创作出来的,而且可以是杰出的作品。三是见了才能做,容易束缚思想,诗歌创作不能回避“见”,诗人的诗歌创作不能闭门造车,诗人要奔向广阔的社会人生,可是诗人要处理好“见”和发挥想象力的关系,不能被“所见”限制住。大诗人艾青曾经谈到他诗歌创作中的成败得失,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国统区写出了《向太阳》《火把》和《他死在第二次》这样的成功的作品,可是到达延安之后,却写出了像《吴满有》这样比较失败的作品;到了五十年代,艾青写的失败的作品还包括《藏枪记》等。他后来总结说,凡是自由地发挥想象力的时候创作出来的就是成功的作品,可是一切按现实来的没有发挥出想象力的却是失败的作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价值在于强调题材对于创作的激发作用,可是如果没有想象力的参与,现实主义只能是一种“伪现实主义”。艾青强调联想与想象对于诗歌创作的作用,尽力回避客观地、冷漠地描摹现实,这是其成为中国现当代最伟大的诗人的原动力。艾青的创作经验对薛宝钗的诗歌观念是一个重要的验证。
自然薛宝钗的诗歌观念透射出的是作为诗人和诗歌理论家及诗歌批评家的曹雪芹的诗学思想,曹雪芹替他笔下的人物作诗,坚持诗歌创作的第一原则就是“寄兴寓情”,不“要见了做”。当然,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灵魂,他们也能够“活在”我们的生命进程之中。因此像薛宝钗这样的典型人物是可以挣脱他的创造者的主观束缚而具有独立自主的思想的。
2 “诗题不宜过于新巧及不限韵”诗观及其实践
薛宝钗诗歌观念的第二条是,“诗题不宜过于新巧”。故事是这样的,大观园举办海棠社大获成功之后,史湘云艳羡不已。史湘云诗才卓绝,不让林薛。史湘云不但一下子补了两首令人赞叹的海棠诗,还要亲自起社,邀众人题写菊花诗。当史湘云到蘅芜苑跟薛宝钗一起讨论拟定菊花诗题的时候,薛宝钗给她提出了一条中肯而且有可操作性的建议,那就是诗题不宜过于新巧。古人作诗,有某种竞赛的性质,常常拟定一定的题目,而且限韵。定题且限韵,是为了增加作诗的难度,以测定做诗人的诗才。有的诗歌组织者常常为了增加作诗的难度,出一些刁钻古怪的诗题且用险韵。薛宝钗明确反对刁钻古怪的诗题和险韵,说:“诗题也别过于新巧了,你看古人中哪里有那些刁钻古怪的题目和那极险的韵呢?”应该说,薛宝钗的这条诗歌观,紧扣她的诗歌要“寄兴寓情”的诗歌命题,只要作者能够抒发他的主观的情思和深刻的思想,就够了。孔子所谓“辞达而已矣”就是这个意思。为了说服史湘云,薛宝钗道出了诗题过于新巧和韵过险所带来的弊端,“若题目过于新巧,韵过于险,再不得好诗,倒小家子气”[1]259。薛宝钗主张诗歌创作要大气,所谓大气,就是要抓住诗歌创作的核心,不要过于在细枝末节上用功夫。在薛宝钗看来,诗歌的正途只在抒发诗人的主观情思,诗的技巧只是为表达诗人的主观情思服务的,因此诗要质朴大气,诗歌离不开普通受众,只有普通受众能够接受的东西才是好东西。一切刁钻古怪的东西,都不会为普通受众所喜爱。薛宝钗的这种为普通受众着想的诗歌观念,咋看起来有点“普罗”意味呢?其实,薛宝钗的这种诗观跟中国新诗史上的诗歌大众化运动所提倡的还是有区别的。刻意大众化而降低诗歌的审美标准这件事在薛宝钗那里肯定不会得到同意的。
薛宝钗秉承孔子推广的儒家诗教,认定作诗需温柔敦厚,她的诗歌风貌跟林黛玉的纤巧风流是两个路数,一直深受大观园众诗家推崇。大观园诗观评论家李纨对薛诗的评价是“含蓄浑厚”。的确,薛宝钗的诗是写得浑厚、质朴而大气,读来滋味盎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薛宝钗回避诗题上的过于新巧,可是她并不反对诗歌艺术在创新维度上的追求。的确,跟别的艺术形式比较,诗歌是最具有某种先锋性的艺术。一部诗歌史,就是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的历史。薛宝钗说:“诗固然怕说熟话”,薛宝钗是承认诗“怕说熟话”的。所谓熟话就是说话时不够巧妙,就是平面化和庸常化,就是失去了审美新鲜感的令人生厌的套话和空话。诗歌应该抛弃平面化和庸常化,诗歌需要一些必要的陌生化。俄罗斯著名诗歌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说,诗歌需要去除熟悉化,要使石头成为石头,借助陌生化技巧,诗歌可以获得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红楼梦》曾经借香菱之口表达了对王维诗歌“无理而妙”神奇效果的礼赞。中国新诗史是一部借鉴西方诗歌艺术史经验的历史,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诗歌界常常出现恶意先锋化和陌生化的现象,诗歌里面的话,常常是让人看不懂的黑话,谜语一般,大家都看不懂。薛宝钗说:“诗固然怕说熟话,然也不可过于求生;头一件,只要主意清新,措词就不俗了”[1]259。“不可过于求生”,的确是一种诗歌创作上的忠告。所谓“过于求生”,不正是一种恶意先锋化和陌生化的体现吗?当然在薛宝钗那个时代,也就是曹雪芹生活的那个时代,这些西方的概念还没有出现,可是道理是一样的。
经过商讨,史湘云与薛宝钗确定了拟定菊花诗题目的原则,即新鲜大方。“新鲜”就是追求某种程度上的创新和先锋性,有意避开俗套;“大方”就是给选取题目的诗歌作者留下“寄兴寓情”的空间,避开小家子气。她们一共拟定十二个菊花题,从《忆菊》开始,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包含《访菊》《种菊》《对菊》《供菊》《咏菊》《画菊》《问菊》《簪菊》《菊影》《菊梦》,最后是《残菊》,展现在诸人面前的完全是一个多样开放的系统。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诗情萌发状况选适合自己的题目来做,史薛林探等大观园诗翁涉及的诗社题目最后连韵也不限,放得开得很。谈到诗的韵,薛宝钗说:“我平生最不喜限韵,分明有好诗,何苦为韵所缚?咱们别学那小家派”[1]259。薛宝钗又一次拿诗歌创作的小家子气开刀。实践证明,这种放开,大大地激发并解放了诗歌创作的生产力。等诗社开启时,每一题都有人认领,每一题都有好诗和警句产生。连常常落第的怡红公子贾宝玉也一下子认领了《访菊》和《种菊》两题,虽然他的诗没有林黛玉、史湘云、探春和薛宝钗写的诗那么寄兴高远、寓情醇厚,但批评家李纨也认可了他,说:“你的也好,只不及这几句新雅就是了”[1]266。贾宝玉自己也觉得他的“霜前月下谁家种,槛外篱边何处秋?”“昨夜不期经雨活,今朝犹喜带霜开”等是得意之句,只是不及林黛玉的“口角噙香对月吟”和史湘云的“清冷香中抱膝吟”等诗句新巧有韵致。
《红楼梦》中多次描写大观园中诸翁结社吟诗的盛况,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即兴式的现场感的创作要出好诗的确不易。诗当然可以即兴创作,曹植七步成诗,他敏捷的诗才的确令人惊叹。可是,诗歌的精品也需要苦吟。李白诗才敏捷,即兴创作而精彩纷呈是可以的,可是杜甫的好多诗歌作品却是苦吟的结果,所谓杜甫“诗律老更细”强调的正是苦吟。更有像孟郊、贾岛那样的诗人,不苦吟是出不了好诗的。永和九年的兰亭雅集被千古传诵,可是当年的那些诸多杰作现在谁还知道呢?好在王羲之的书法名篇《兰亭集序》流传下来了。《红楼梦》作者自己在诗歌创作上天才卓绝,给他作品中那么多人物以集体即兴创作的机会,而且涌现那么多精品,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太容易找到的。
薛宝钗的“诗题不宜过于新巧”以及“不喜限韵”的诗歌观念反映出曹雪芹某种前卫的诗学思想,曹雪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离他那个时代二百多年后会是一个自由诗的时代,而且产生出那么多杰出的甚至堪称伟大的诗人。
曹雪芹诗学思想在核心观念上体现了某种对孔子所主张的诗学思想的承接性,他借薛宝钗之口对孔子的“兴观群怨”思想进行了通俗化,使得孔子诗学具有某种可操作性,而在放开限韵和不可过于新巧方面具有某种前卫性和先锋性。
3 薛宝钗诗歌观念对中国诗歌当下创作的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中的天才诗人林黛玉也是有自己的诗歌观念的。她曾经指导香菱写诗,跟薛宝钗一样,她的诗歌观念也比较开放,她看轻诗的一切所谓的规矩,什么对仗,什么平仄,在真正的诗面前,都可以让位的。当然,无论是薛宝钗或者是林黛玉,不过都是曹雪芹笔下的人物,她们的诗歌观念都是曹雪芹本人的诗学思想的反映。正如前面所说,薛宝钗和林黛玉等的诗歌观念在曹雪芹那个时代是比较前卫和先锋的。在那个时代,连散文也是韵律化的,何况诗?诗律和韵是无论怎样也不能抛弃的。只是,今天回过头来看,却真正有意思的是,那样严苛的诗律到了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居然受到彻底颠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学运动,更直接地说,就是白话文运动。文废骈,诗废律,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提出的“作诗如作文”竟然成了新诗创作的金科玉律。《红楼梦》里面只认“寄兴寓情”,宽待平仄和韵,在今天看来,的确是非常前卫和先锋的。胡适尝试白话诗,只要白话不要诗,连必要的凝练也不要,的确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可是,胡适引领的这场诗歌革命在某种意义上的确解放了诗的生产力。新诗百年,自由诗的创作取得了辉煌的实际的成绩,产生了不少大家名家及其影响深远的诗歌作品,成为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产。胡适对《红楼梦》这部古典白话文学经典的推崇,在新文化运动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引发了一场新的文学和文化的革命运动。
如今新诗已历经百年,其中经历过由铁腕人物推动的大众化运动,也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先锋化运动。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轰轰烈烈地发动了一场新民歌运动,就是诗歌大众化运动的一种极端化模式。历史证明,极端大众化伤害到了诗歌最起码的审美标准,也使得诗歌丧失了自己强劲的生产力。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一些中国诗人推动了中国诗歌全盘西化甚至恶性先锋化的运动,他们甚至否认诗歌抒发个人的主观情思,借用西方理论家所谓的“情感谬误”学说以及“思想谬误”学说,颠覆诗歌原有的情感和意义的表达,结果产生了一大批晦涩难懂的所谓诗歌作品。在笔者看来,无论是极端大众化抑或是恶性先锋化,都是在走极端,都是在牺牲诗的生产力。
薛宝钗的诗歌观念对我们当下诗歌创作的重要启示是,诗歌首先还是要坚守“寄兴寓情”的本位立场,诗歌当然要创新,可是在创新上要避免小家子气。薛宝钗在诗歌创作上反对“见了才能做”的题材决定论,可是她并没有反对阻断现实,从她协助史湘云拟定菊花诗题的具体操作来看,“及物性”仍然是她诗歌观念的核心内容。因此,笔者在此梳理出薛宝钗的两条重要的诗歌观念,希望能够对当下的诗歌创作有一点启示,能够把诗歌创作在态度上端正到“寄兴寓情”上来,既要保留诗歌创作上一定的先锋性、创新性,提升诗歌的艺术性,也要避开诗歌创作上的小家子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中国诗歌界逐渐接受了西方形式主义诗学思想,认为诗歌的艺术元素只在形式表达,跟内容无关,所谓“情感谬误”,只要诗歌“寄兴寓情”就在艺术上错了。有的诗人对情感的表达深恶痛绝,甚至叫嚣说在创作的时候要让情感死得很难堪。这不仅是小家子气的问题了,是彻底否定诗歌的正途和大道。薛宝钗的“寄兴寓情”观,对纠正形式主义的诗歌之弊应该是一剂良药。
当然,在言说西方的时候,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西方的诗学思想并非全是形式主义或者先锋的东西,“寄兴寓情”在大多数西方诗人那里仍然是他们诗歌创作上的正途和大道,就是西方形式主义和先锋性的东西也仍然有借鉴的价值和意义。台湾诗人洛夫和余光中都对西方有所借鉴和继承,自然也对伟大的中国诗艺传统有所继承和借鉴。当然,他们各自的诗路历程的确不一样。诗人洛夫曾经穿着厚厚的西方先锋主义诗艺之靴写出了诸如《石室之死亡》这样让人读不太懂的作品,可是他很多时候回顾传统,抛弃恶性先锋主义的诗艺之靴,写出了如《长恨歌》《湖南大雪》等脍炙人口的好诗。
由上可见,薛宝钗的诗歌观念对中国当下的诗歌创作具有相当多的启示,中国诗歌如果要回归正途,必须要坚持薛宝钗所倡导的“寄兴寓情”创作原则。如前所说,薛宝钗的诗歌观反映的自然是曹雪芹的诗学思想,曹雪芹的诗学思想对当今中国诗坛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希望诗坛能够回归正途,避免诗歌创作上的小家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