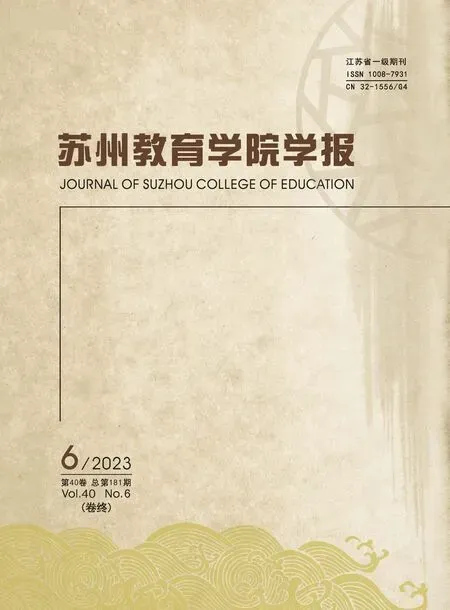母爱话语中的规训
——《晚安,妈妈》的母女关系论析
徐丛辉
(哈尔滨师范大学 西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美国当代女剧作家玛莎·诺曼的《晚安,妈妈》(’Night, Mother)[1]是一部深入探讨母女关系的经典剧作,1979 年在百老汇首演大获成功,1983 年获得普利策戏剧奖,随后剧本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上演。该剧作于20 世纪90 年代引入我国,先后进入北京、成都、广州等地的大小剧场,观众反响强烈。《晚安,妈妈》这部只有母、女两个人物出场的独幕剧,沉重而发人深省地表现了普通家庭中母女间敏感、复杂的情感关系。母亲塞尔玛对女儿杰茜的爱无微不至,却让女儿失去了对个人生活的掌控,加速了女儿个人悲剧的发生。母爱是高尚而伟大的,母亲拥有天然的权力去呵护子女,这份权力区别于微观权力关系中的其他社会关系,它承载着母女间与生俱来的爱与亲情。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权力理论中,权力与规训并驾齐驱,规训往往发生在军队、监狱、学校、精神病院这些场所,通过权力作用于主客体关系得以实现。[2]158在当代社会中,这种权力运用也适用于分析家庭内部关系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对抗,而且,在家庭内部关系中,权力发挥着不容忽视的规训作用。《晚安,妈妈》中,人物对话是整部剧的灵魂,看似平淡琐碎的日常对话却抽丝剥茧般把疏离的母女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杰茜最后开枪自杀,母亲绝望地哭喊着:杰茜,原谅我,我曾以为你是我的。[1]58作为全剧的点睛之笔,这句话道出了这段扭曲关系的症结,母爱失去了本该有的治愈力量,取而代之的是无处不在的规训。在塞尔玛和杰茜的母女关系中,这种规训主要发生在空间、身体和话语三个层面。
一、“被看”的空间
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中,疯癫是理性的对立面,理性为了维护自己的主体地位,把“疯癫”禁锢起来加以规训。[3]塞尔玛和患有癫痫病的女儿杰茜生活在美国南部乡下的一栋房子里,对杰茜而言,这栋房子远离外界纷扰,父亲已经离世,丈夫与别的女人出走,儿子在外游手好闲且许久不归,只剩她与母亲相依为命。她们所处的空间和外界是疏离的,塞尔玛对杰茜说:咱们的东西是别人不想要的。[1]12在这个远离人群、相对封闭的空间内,她们的相处模式形成了“看”与“被看”的权力秩序,母女之间的关系也是疏离的。
《晚安,妈妈》中唯一的舞台布景就是母女二人居住的房子,这本是母亲的居所,杰茜离婚后,母亲让她搬来与自己同住,同时把日常生活统统交给杰茜打理,杰茜每日在家里忙碌,在母亲“看”的视线范围内活动。家中的起居室和厨房相连,其他的小房间都通向起居室。在这个公共的开放空间里凌乱地堆放着杂志、编织物花样手册及随处可见的针线用品,这些都是与母亲有关的东西,她拥有对这个可见空间及附属物的所有支配权,其中也包括女儿杰茜。在母亲眼中,杰茜一直是她的附属物,杰茜遗传了父亲的癫痫病,儿时几次病发后,塞尔玛再没让杰茜离开过她的视线,杰茜在母亲密不透风的庇护下长大。成年后,在母亲的安排下,杰茜结婚生子,但最终与丈夫感情破裂。离婚后,塞尔玛再次将女儿召唤回家,继续让她生活在自己的“规训”下。杰茜随时可能犯病,没有工作,她能做的事情寥寥无几,母亲的住所仿佛是禁闭室,这里远离外界生活,远离来自各种敌意的排斥,只有母亲对女儿的规训。
一方面,塞尔玛给女儿不停地安排家务,让她有事可做,而无法惹是生非。杰茜整天忙于家务琐事,她的行为在母亲的日常规训下变得得体而规范。在内部敞开式的空间中,塞尔玛可以时刻了解女儿的情况,久而久之,这种随时的关注对身为中年人的杰茜来说,已不再是出于母爱的保护,更像是一种持续的、无所不在的监视。在空间的支配关系下,杰茜在厨房和客厅这些公共空间里打理着没完没了的家务,她随时都处于“被看”的状态,听话地按照母亲的意志去完成日程表上的每个任务;而一直在“看”的母亲又随时安排、修正杰茜的行为,使其遵照指令,把家里的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对母亲而言,她在这个行使规训权力的空间里,实现了最大限度的、最有效的母爱。
另一方面,“被看”的杰茜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在母亲这里,她自始至终过着主体感荡然无存的生活。日常生活中,塞尔玛总是把自己的需要投射到女儿身上,杰茜必须对她言听计从,除了感受来自母亲时时刻刻的“看”,还要忍受哥哥道森一家时常前来“打扰”。对于杰茜而言,道森虽然没有与她们共同生活,却对她的生活了如指掌,并且对她表现出了极度的关心,“他老纳闷整天我在干什么,有些事情你还没来得及说想不想让他们知道,他们已经知道了,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在场,你的事跟他们不相干,他们却知道了”[1]19。哥哥道森的时常“在场”让杰茜觉得自己完全没有独立空间和个人隐私,没有人顾及自己的感受,她的生活被“看”得一清二楚。杂货店里母女二人的购物开支一直记在道森的账户里;每次杰茜犯病,母亲总是第一时间通知道森,让他赶来帮忙处理。尽管母亲强调会避免让道森看到杰茜的窘态,但杰茜还是感到活得没有任何尊严可言,她觉得自己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但这里是母亲的家,她清楚自己没有权力禁止别人进入,以致后来只要哥哥嫂子一来,杰茜就会躲起来以保护仅有的自尊。
二、被“驯服”的身体
在福柯的权力观中,身体的驯服是权力主体作用于对象的结果,在封闭的空间里,人在其中的活动被精心设计,从而促成规训造就个人。[2]156塞尔玛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着女儿,母爱名义下的规训将杰茜孤立在母亲眼皮底下的保护区。杰茜的生存状态一如剧本开头对她的描述:杰茜·凯茨,四十岁上下,面色苍白,看上去有点手足无措,也说不清楚她为什么感到控制不住自己的躯体—事实也确实如此。[1]4在这部90 分钟的独幕戏中,杰茜不停地忙碌于琐碎的事情,有条不紊地安排着她自杀后母亲的生活—杰茜认为自己难得如此清醒和克制,庆幸自己这次能够掌握生命的主动权。一直以来,杰茜生活在母亲的安排下,她无法自如地掌控身体,不清楚什么时候癫痫病会突然发作。丧失身体支配权的杰茜从小到大都听从母亲的安排,丈夫和儿子相继离家后,杰茜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成为她相依为命的人,她在家里对母亲更是唯命是从,按照“日程表”完成每天的家务:做饭、洗衣服、收拾房间、订药、洗糖罐……母亲说她干活麻利,但在杰茜看来,这不过是母亲日复一日的刻意规训罢了。这种规训塑造了杰茜的生活日常,她那被驯服的身体像机器一样循规蹈矩,日复一日地按照设定好的程序运转。
对杰茜而言,她希望身体得到驯服,因为癫痫病,不受控制的身体常常让她不知所措。如她所言,即使有机会出去工作,也显得格格不入,连笑容都被别人认为是怪怪的。因此,杰茜渴望身体得到驯服,这样至少她可以应付家里的琐事,让她有存在的价值,不再一无是处。但不幸的是,这个驯服身体的力量并非来源于她自己,而是来自母女关系中强大的规训力量。这种占有性的规训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剥夺了杰茜掌控身体的权力。即使随着年龄的增长,杰茜癫痫病发作的次数在逐渐减少,可是在她心里,真正的自己从没有出现过,而且也永远不会出现。[1]50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今的母女关系对于杰茜来说是消极的,逐渐失去了天然的救赎意义,阻隔了杰茜与外界的联系,她没有朋友和社交活动,没有可支配的生活。长期的规训导致杰茜的主体性被剥夺,造就了她的奴性人格,只剩下“训练有素”的躯体。杰茜已经对生活和人生完全失去了自主期望,她绝望地把自己的生活比喻为乘坐长途汽车,并给过去的人生下了结论:我就是坐上五十年再下车,到达的还是原来的地方。[1]24
在母女关系的另一端,塞尔玛与离婚后的女儿一起生活,并在母女关系中一直扮演着支配者的角色,杰茜遗传了父亲的癫痫病,母亲塞尔玛严守秘密,没有向任何人透露,直到婚后杰茜和丈夫去骑马时不幸犯病,这才去医院接受了全面治疗。在杰茜自杀前,她对自己患癫痫病的事实毫不知情,她一直不明真相地在母亲的安排下生活,随着病情的好转,杰茜越来越渴望能够拥有正常人的生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支配身体,但是,她始终没能找到逃出规训束缚的出口。在这个意义上,剧终时杰茜的自杀与其说是出于对未来生活的绝望,不如说是她决意要夺回身体控制权的终极选择。杰茜一直在等待一个宣告生命主权的时刻,尽管这是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但对杰茜而言,此时生命的意义在于这个决定本身,因为她从未按照自己真实的意愿活过,也从未真正掌握过自己的话语权。
三、话语的“牢笼”
福柯认为,在人类社会关系中,权力无处不在,“任何教育制度都是维持或修改话语占有以及其所传递的知识和权力的政治方式”[4]。家庭具有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作为《晚安,妈妈》中母女间主要的沟通手段,话语无疑是最直接的规训方式。在她们的生活空间中,杰茜沉默寡言,塞尔玛则牢牢掌握着话语权,看似平淡琐碎的日常语言通过权力和意志的干预被秩序化。母女二人的谈话内容仅限于家庭生活,对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有昏了过去,手脚冰凉,躺在担架上才能看见车道”[1]37的杰茜来说,日常话语构建了一个无形的牢笼,将她束缚其中,不得解脱。
塞尔玛用话语时刻支配着杰茜的日常行为,塞尔玛在心理上总是缺乏明晰的“自我边界”,她指导和控制杰茜的生活,一直希望与女儿“共生”在一起,她日常的语言是强势的、具有进攻性的,她的话语充斥着各种提问、质问和训斥:你为什么看报纸?你为什么不穿我给你织的毛衣?你还记得我以前是什么样?……你犯病时看到了星星还是什么?你到底是怎么从马上摔下来的?赛希尔为什么离开你?你把我的旧眼镜放在哪儿啦?……[1]38面对这些日常唠叨和抱怨,杰茜都是顺从地回应。在塞尔玛眼中,儿时的杰茜是她的附属品,离婚后的杰茜虽已步入中年,但在她眼里仍旧是需要被规训的,她对杰茜的规训从未停止,“我说了,别翻个乱七八糟”[1]10,“杰茜,你得注意礼貌,先问问家里的什么东西你可以拿。反正我死了,也都归你”[1]13。这种扭曲的母女关系使杰茜无处可逃,只能畏缩在话语的牢笼里。
面对母亲的话语控制,被剥夺了话语权的杰茜直言自己“这辈子从来不跟人打交道,除了去医院”[1]26,她无法控制身体,不能清楚地去思考,也不擅长表达,经常忘事,杰茜衣服的口袋很深,里面时常放着纸条,身上总是带着一支笔。杰茜认为写字是一种可靠的与外界交流的途径,她总是用写纸条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这是她与自己交流的方式,也是她反控制的话语方式。甚至在自杀前,她把家里所有人的生日都记在一张单子上留给母亲,用文字向哥哥道别。随着剧情的发展,母亲得知杰茜想要自杀后,试图劝杰茜放弃这个念头,此时母女二人的对话愈发激烈。杰茜渴望能够拥有自主、自决的权力,成为真正自由的人,她不想在任何事情上都身不由己,结束生命也许是她摆脱当前处境的唯一途径。相比之下,母亲迟来的承诺显得那样的牵强,“我要多注意你的要求,多听你的话,表现得好些。不再为自己抱怨。你问我什么,我就讲真话,让你有发言权”[1]49。在人命关天的时刻,母亲一语中的地道出了杰茜一直以来的可悲处境,在这段相依为命的母女关系中,杰茜没有话语权,面对母亲强势的话语,杰茜从来没有招架之力,她更怀念小时候享受母爱时的温馨,现在中年的她仍旧热爱生活,可又无能为力,在本该承载无限亲情的家中,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最终,杰茜选择不再继续等待,走向“命运之门”,她对母亲道出了那句“晚安啦,妈妈”后开枪自杀,为这段母女关系永远画上了句号。
四、结语
作为美国女性主义戏剧的杰出代表,《晚安,妈妈》聚焦当代家庭中的母女关系,在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对母女之间情感的刻画中,塞尔玛和杰茜的母女关系显然已经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情感依托和治愈力量,对母爱话语种种内涵的颠覆和质疑,凸显了其规训的意涵和实质。在日常生活空间中“被看”,身体一直在被“驯服”,又囿于“话语”的牢笼,由此,杰茜彻底丧失了属于自己的主体性,母亲无处不在的陪伴与监管对她来说已经是不能承受之重。杰茜生命的结束是母女关系的终结,这段母女关系之于杰茜来说不再具有母爱的救赎意义,而是蒙上了规训的悲情色彩。杰茜在最后的抗争中,用生命换来捍卫自身主体性的权力,是她为实现生命意义的悲怆之举,给观众留下了关于母女关系的无尽思考。就此而言,这部剧的警示意义跨越时代,注定成为世界戏剧舞台上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