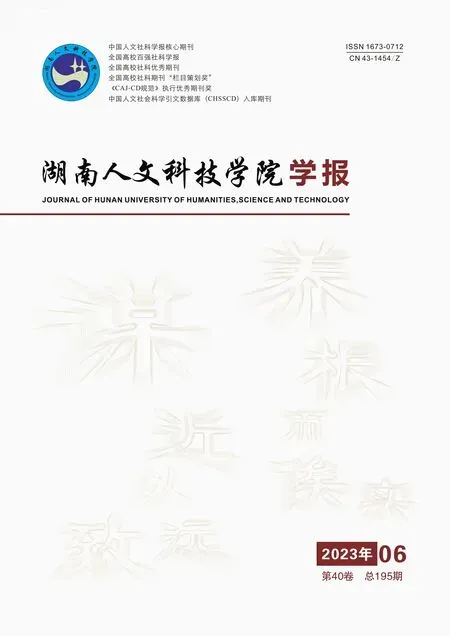习近平关于文艺铸魂育人论述的传统文化根基探赜
彭 玲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文学院,湖南 娄底 417000)
习近平围绕文艺工作发表了系列讲话,提出“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责”[1]17这一重要论述。 “文艺铸魂育人”的论述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育人思想,总结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文艺育人经验。 “文艺铸魂育人”涉及主体、载体、方式等几个主要维度,这几个主要维度都赓续了传统文化的血脉和精神。 首先,文艺工作者承担着铸魂育人的主体责任,必须追求德艺双馨,这和崇德尚艺的传统一脉相承。 其次,好的作品是文艺铸魂育人的重要载体,好的作品是紧扣时代脉搏、以人民为中心、以中国精神为灵魂的作品,这与传统现实主义、民本思想及文以载道思想息息相关。 再次,文艺铸魂育人的方式是通过润物无声的艺术熏陶启迪人的心灵,这继承了传统人文化成的思想。
一、文艺工作者:崇德尚艺
文艺工作者是文艺铸魂育人的主体,承担着铸魂育人的使命,必须具备相应的素养。 习近平指出:“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2]23作为灵魂的工程师,在塑造人心之前,首先要“塑造自己”[1]18,“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1]18。 同时,必须“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3]14。 习近平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对我国崇德尚艺传统的赓续。
早在先秦时期,先民们就有崇德尚艺的传统,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能创作出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 《论语·泰伯》记载了孔子对尧的一段评价:“大哉尧之为君也! 巍巍乎! 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4]孔子以“大”来称颂尧,是因为尧德行广远,能与天相准,故其制定的礼乐典章制度光芒四射。 尽管此时的“文章”主要指礼乐典章制度,其内涵不同于后来的“文”或“艺”,但包含了“文”和“艺”,尧深厚的德行是支撑其创作灿烂礼乐典章制度的内核。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观点,进一步阐明了德正文正的道理。 《孟子》记载,公孙丑向孟子请教分辨他人言辞的策略,孟子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5]67在孟子看来,偏颇的言辞、过激的言辞、偏离正道的言辞、躲闪的言辞均与人的思想德行有关,思想德行的偏激、极端、不守正道及不坦荡才会产生以上言辞,因此,只有“正人心”,才能“息邪说”“放淫辞”[5]168。 除孔孟外,荀子也认为道德操守是言辞表达的基础,君子要“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6]328,这样才能言语流利而不胡说八道。 受先秦重德传统的影响,汉代德充文昌的观念更加突出。 王充指出:“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7]在王充看来,文是德的外在表现形式,作家的品德高下影响文艺作品的优劣。 关于德与艺的关系,徐干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艺者,德之枝叶也;德者,人之根本也。 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独立。”[8]徐干将德行比喻成人之根本,艺为德行的枝叶,二者统一,不可偏废。 树木没有枝叶其根干就不能壮大,人缺少艺就不能成就德行,变成粗鄙之人。
南北朝时期,刘勰认为理想的作家应该是德才兼备的梓材之士,应该“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9]567唐宋以降,古文家延续德艺并重的传统,强调全面加强作家的内在修养。韩愈指出,“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10]“有诸其中”说明了文艺作品内容渗透了作家的德行、思想、情感、学识、气魄等。 欧阳修的观点与韩愈的观点颇为相类,认为作家只有具备了高尚的品德与丰富的学识等,才能写出永恒不朽的文章。 欧阳修之后,周敦颐、朱熹等理学家重德轻艺,但是,这种倾向持续时间不长,发展到明清,宋濂、姚鼐、袁枚等人重新回到了德艺兼顾的传统。
从上面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崇德尚艺一直是我国文艺思想史上的一个宝贵传统,强调作家道德修养对其创作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在新时代背景下,针对文艺工作者失德及文艺创作失序等问题,赓续我国崇德尚艺的传统,呼吁文艺工作者加强道德修养,提升精神境界,创作符合时代及人民需要的文艺作品。
那么,文艺工作者如何才能创作符合时代及人民需要的作品呢? 习近平给出了几个方面的具体意见。 其一,立志高远,心系民族复兴伟业。 古今中外优秀的文艺家,都志存高远,胸怀天下。 比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陆游,等等。 都有匡时济世的情怀。 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3]6其二,坚守人民立场,创作人民满意的作品。 人民是文艺的丰沛源泉,也是文学的生命力所在,文学史上优秀的作家心中始终装着人民,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于谦的“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深林”等都是心系人民、情系民生的佳句。 新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3]7-8其三,坚持守正创新,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 一方面,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要从中华文明与文学传统中汲取营养,又要大胆探索,推动文艺内容与形式的创新;另一方面,要立足中国大地,聚焦中国人民,折射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3]12其四,弘扬正道,坚守艺术理想。 在市场经济浪潮中,文艺工作者要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不走捷径,不求速成,不逐虚名,不贪小利,要“下真功夫、练真本事、求真名声”[3]15。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赓续了我国崇德尚艺的传统,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做到德艺双馨,为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承担铸魂育人的责任奠定了主体条件。
二、文艺作品:现实主义、民本思想与文以载道
文艺工作者承担铸魂育人的主体责任,优秀文艺作品则是铸魂育人的重要载体,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理想社会形态的建构、引领健康精神风尚的形成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就像习近平所说,“举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2]6,“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坚韧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1]5
那么,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才能振奋人心? 才能铸魂育人呢? 首先,文艺作品必须贴近生活,引领时代。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谈及文艺与社会生活、时代的关系时,直接引用了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刘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洪应明“登高使人心旷,临流使人意远”等观点,强调文艺作品应该贴近生活,引领时代。 习近平对文艺与生活、时代关系的论述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国古代的现实主义诗学传统。 现实主义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中国古代文学,从《诗经》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到汉乐府的“缘事而发”,从曹操的“借古题写时事”到杜甫的“即事名篇”,从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到元杂剧及明清小说,都彰显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 《诗经·国风》中的很多诗篇、汉魏六朝的《木兰辞》、杜甫“三吏”“三别”、陆游的《示儿》、关汉卿的《窦娥冤》、冯梦龙及凌蒙初的“三言”“二拍”、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是各个时代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现实感。 新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续接现实主义传统,书写新时代、新现实与新变革,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生活,回答时代课题,从而促进社会变革,引领时代发展。
其次,文艺作品必须以人民为中心。 文艺来源于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2]15因此,文艺要把人民作为表现的主体,要反映人民的生活,要刻画人民的形象,表现人民的喜怒哀乐,从而让文学起到感染人民、陶冶人民的作用。 尽管“人民”一词古已有之,但是,其内涵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含义并不一致。 比如,《诗经·大雅·抑》“质尔人民,谨尔侯度”[11]句的“人民”指百姓;《周礼》“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举之……”[12]中的“人民”指逃亡的奴隶;《管子·侈靡》“牛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13]中的“人民”指平民。 我们今天所讲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根植于民本文化,民本文化是我国古代文艺及文化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尚书》。 《尚书·五子之歌》载:“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4]发展到孔孟,民本思想已比较完善,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反对不教而杀;孟子认为民贵君轻,主张保民、养民与教民。受民本思想的影响,古代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都纪录了百姓田猎、采集、祭祀、求偶、战争、徭役等方面的生活,抒发了百姓思乡怀人、忧国伤时、匡贫济困、建功报国等方面的情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习近平继承与发扬了传统民本思想,主张文艺作品要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表现人民生活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从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再次,文艺作品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习近平指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2]21这和文以载道的传统一脉相承,文以载道思想虽到北宋的周敦颐才正式提出,但是,在周敦颐之前,很多思想家有过关于艺与道、文与道的相关论述。 比如,荀子将乐与道结合起来讨论,指出“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6]295。 刘勰认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9]10。 韩愈的弟子李汉在给韩愈文集作序时,直接提出“文者贯道之器也”[15]的观点,柳宗元则坚持“文者以明道”[16]。要而言之,文道关系一直备受思想家们关注。 尽管思想家们对“道”的阐释各有不同,但是,用文来承载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进步观念与美好理想的愿望是相同的。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习近平将“道”具体化为中国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精神内涵丰富,其中,最重要的内涵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爱国主义是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激发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精神是最能激励中华儿女开拓进取、励精图治、推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力量源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因此,在当今社会文艺还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领域商业化倾向严重,有的作品三观不正、格调低俗、内容肤浅、形式粗糙,对人们的身心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发扬中国文艺追求向上向善的优良传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3]9-10从而发挥文艺作品感染人、打动人、塑造人、引领人的作用。
三、文艺育人方式:人文化成
文艺铸魂育人的方式不是说教式的、灌输式的,而是在审美体验中潜移默化地完成的,人在审美体验过程中能够获得情感的享受、心灵的净化与灵魂的洗礼。 就像习近平所言,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2]23,能够“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2]-24
习近平对文艺铸魂育人方式的总结既基于文艺本身的审美特点,又是对人文化成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人文化成”最早见于《周易》,《周易·贲卦》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疏解“人文”为“《诗》、《书》、《礼》、《乐》之谓……”[17]也就是说,人们通过观察自然现象来把握其发展规律,通过把握《诗》《书》《礼》《乐》等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来化成天下。 《诗》《书》《礼》《乐》有什么特点呢? 《诗》《书》《礼》《乐》除了政教性特征外,其情感性、形象性等审美特征比较突出。 正是基于《诗》《书》《礼》《乐》的形象性、情感性特征,孔子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命题。 “兴”,历代学者都将其释为“起”,学界少有参差之言,其中,朱熹的注解至今仍具有典范性,“兴,起也。 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覆,其感人又易入。 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18]100。 诗源于真性情,因此,能兴发人之好善恶恶之心,涤除不美好的情感。 换句话说,诗可以让人净化心灵,提高觉悟,提升境界。 通过学诗回归性情之正,便能立于礼,“所谓立,乃是自作决定,自有信心,发乎内心的当然,而自然能适乎外物的合理趋向,亦即是自己能把握自己而又能涵融群体的生活”[19]。 立于礼,不是被动地遵守外在的规范,而是主动地调整自己的身心状态,自觉约束粗野卑劣的品质,巩固人性中素朴纯真的因子,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个体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精神的愉悦与享受。 诗与礼使个体性与社会性、本真性与文饰性达到了统一,进而进入成于乐的阶段。 成于乐是指乐“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查滓。 故学者之终,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18]100-101。 也就是说,乐可以怡情养性,涤污除秽,消融人心之偏狭、浮躁、浅薄等。 人通过乐之熏染,最终可达和通圆融之境。 可见,诗礼乐之教,是文艺与人格的有机融合。 一方面,人格培养以文艺审美为中介,在审美体验中人格得以提升,整个过程自然而然,不勉不强;另一方面,文艺以人格培养为旨归,通过感动人心化育天下。
习近平继承了传统“人文化成”思想,提倡文艺“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 文艺如何才能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呢?
首先,要塑造典型的形象感染人。 文艺铸魂育人不是通过理论灌输与道德说教来实现的,而是要塑造典型的形象来感染人,“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1]12。典型人物既来源于现实生活,又渗透了作者的情感态度、艺术趣味与审美理想等等。 文艺工作者只有高度凝练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并将自己的艺术理想与审美追求等融入其中,才能创作出有感染力与生命力的作品,从而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因为“道德的人只能从审美的人发展而来,不能由自然状态中产生。”[20]人们接受文艺作品,首先感知到的就是其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然后调动自己的审美体验与这些人物形象产生情感共鸣。 在这个过程中,接受者的价值观、人生观与世界观便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 比如,李大钊、江姐、刘胡兰、狼牙山五壮士、焦裕禄、孔繁森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让接受者在情感上与他们同频共振,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进而受到鼓舞与启迪,就像苏联美学家莫·卡冈所说:“艺术使人们进行自我体验,这正是它的教育力量之所在。”[21]新时代条件下,习近平要求文艺工作者“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1]17,于是,产生了《功勋》中的于敏、申纪兰、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等共和国勋章人物,《中国医生》中的张竞予、吴晨光、文婷等舍“小家为大家”的白衣天使,《长津湖》中的雷公、于从戎、伍千里、伍万里、梅生等保家卫国的勇士,《夺冠》中的郎平、陈忠和、袁伟民、孙晋芳、张蓉芳等坚韧执着的女排教练及队员,他们都是“最美人物”。 这些人物有血有肉、鲜明生动,让人们能够感知甚至效仿,具有巨大的引领作用。
其次,要用真挚的情感打动人。 文艺铸魂育人不是生硬地将某种价值观念传递给受众,而是在润物无声的情感体验过程中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品格,因此,文艺作品要有温度,要让人动心、动情。习近平强调,文艺工作者“把崇高的价值、美好的情感融入自己的作品”[1]17,“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3]9一部作品之所以动人,主要在于作者饱含深情地去创作,通过作品抒发人民的真实情感,并且能让受众产生情感的共鸣。 恰如黑格尔所言,“人们常说,艺术总要能感动人;……一般地说,感动就是在情感上的共鸣”[22]。 比如,梁晓声的《人世间》展示了相濡以沫的夫妻情、血浓于水的亲子情、患难与共的兄弟姊妹情、互帮互衬的邻里情、志同道合的友情、忠贞不渝的爱情,这些情感彰显了真善美的力量,照亮了普通人的生活,引导人向上向善,带给人温暖、希望、勇气与力量。
再次,要用精湛的艺术吸引人。 文艺铸魂育人需要通过美的创造、传播与欣赏才能实现,作品首先要有审美感染力,才能吸引受众交流与对话,进而对受众产生精神影响。 如果作品粗制滥造,便不能吸引人,不能给人以审美享受,更不能陶冶人、引领人。 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主要是因为韶乐思想纯正、艺术精湛,富有感染力,孔子在欣赏的过程中获得了心灵愉悦与美的享受。 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诗经、楚辞、汉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的优秀篇章,都是通过精炼的语言、生动的形象、整齐的韵律、优美的意象、曲折的情节等吸引读者的参与,激发读者的想象与情感,从而达到化人育人的目的。 当下,“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文艺创作生产的格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2]28,因此,文艺工作者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内容,创新形式,探索技巧,用精湛的艺术进行情感的传递与思想的浸润。比如,《流浪地球2》在硬核科技与浪漫想象构织的艺术空间中,设置了勇担使命、无私奉献、和衷共济、砥砺前行等主题,渗透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等理念,太空电梯、MOSS 系统、行星发动机等硬科技元素很容易激发青少年的兴趣,让青少年在异彩纷呈的视觉盛宴中感受到文化自信、科技自信与工业自信。
总之,文艺铸魂育人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实践历史与深厚的文化根基,从孔子的诗教到康有为的礼乐教化,都突出了文艺在培养理想人格、净化社会风气、稳定家国秩序等方面的作用。 当前,尽管我国文艺创作繁荣发展、文艺作品百花齐放,但是,文艺界浮躁之风盛行,有的作家胡编乱写,有的作品粗制滥造,有的艺人失德失范,给大众尤其是青少年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另外,西方流行文化强势入侵,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 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坚定文化自信,继承和发展了崇德尚艺、文以载道、人文化成等传统,借鉴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文艺育人理论,总结与弘扬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文艺育人的经验,形成了文艺铸魂育人的论述。 这一论述的形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对文艺工作者的主体素养的提升、文艺作品的健康发展、文艺真善美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河北省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巡演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