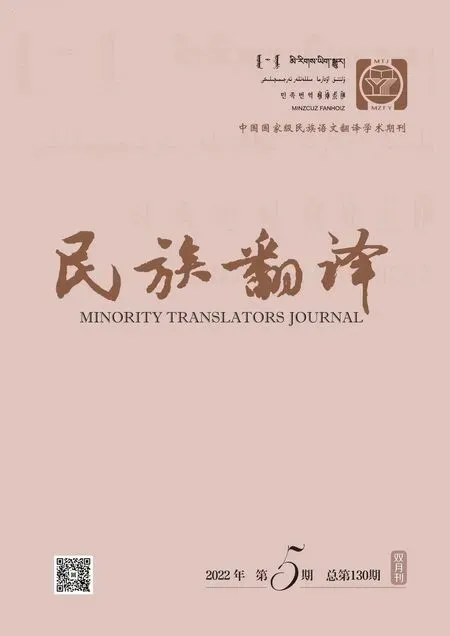中国传统译论的阐释模式*
⊙ 卜超群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从东汉至唐宋佛经翻译的第一次翻译高潮到改革开放以前,出现了不少在中国传统言意观影响之下的翻译论述,譬如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玄奘“五不翻”、赞宁“六例”、彦琮“八备”等。但在改革开放之前,对这些翻译论说的研究一般都停留在引证推崇或举例说明阶段,很少对这些理论的意义进行发掘阐释[1]。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第四次翻译高潮的到来,传统译论的研究开始呈现复苏之势[2],出现了大批从资料汇编、译论史和理论视角来研究中国传统译论的著作。这些著作的研究路径集中在“史”“论”“释”三大类上,“史”的路径主要是从历时维度,运用史学方法对传统译论的发展进行挖掘、爬梳和整理,如罗新璋《翻译论集》、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等;“论”的路径重在从传统译论内在发展逻辑、层次维度和整体结构上构建具有现代特征的理论体系,如张思洁《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吴志杰《中国传统译论专题研究》、王平《中国传统译论的美学特色研究》等;最后,“释”的路径主要是以注解的方式对传统译论进行解读和阐释,致力于在当代译学主体与传统译论言说者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对话关系,如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朱志瑜和朱晓龙《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张佩瑶《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赵巍《中国传统译论的社会文化阐释》等。不管是“史”还是“论”的路径,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传统译论的文本意义,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夹杂着“释”的痕迹,譬如对译论文本中的晦涩生词、核心句子的解释。因此,本文着重梳理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阐释模式,以期从多元的阐释路径中找到共性,为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阐释方法提供参考。
一、基本概念界定
早在先秦诸子论道辩名时,中国的阐释理论和方法就已经开始。“阐释”是“阐释学”(hermeneutics)的实践过程,后者得名于希腊神话中传达大神宙斯意旨的神行太保赫尔墨斯(Hermes)[3]。“hermeneutics”一词又被译为“诠释学”或“解释学”。其中,“解释”一词意义太过宽泛,可用于对一个文本、一个行为,抑或是一个物理现象的解释[4],而“诠释”和“阐释”最大的意义区别,在于“诠”偏重文本字句的考证,是以历史文献为对象之训诂,对文献“本义”的寻找和证明,是为求经典原始认知为传承所用;而“阐”则以历史文献为中介,衍生文献少有甚至所无之“意义”,侧重于文本思想意义的推演,意在创制和传播新的思想和价值[5]。训诂注重语义考证,讲究字词的“元义”,信奉孔子的“述而不作”,建构的是“我注六经”的释义模式;而阐释在于意义假设,推崇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讲求微言大义,构建的是“六经注我”的释义模式。正如张江教授所言:“义理不可无训诂,阐释不可无诠释”[5]152。二者是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
中国传统译论,即中国传统的有关翻译的论说,既包括从汉末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翻译家和学者提出的有关翻译理论与方法的论述,也涵盖近年来发表的一些在理论上沿袭和发展古代、近代翻译思想的文章和专著[6]。它不以时间为划分依据,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罗新璋提出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等学说,尽管在时间上属于现当代范畴,但其仍然属于传统译论;它亦不以地缘国别为区分标准,如美国夏威夷大学东方学者安乐哲(Roger T. Ames)和郝大为(David L. Hall)的研究,虽然地缘上不属于中国,但其在学理上也属于“中国传统译论”的范畴[7]。因此,甄别中国传统译论,不以时间、地缘为基准,而是以学理上是否继承中国传统译论特色为标准,即在翻译论题上、研究方法上、表述方式上,以及在理论特质和精神旨趣上是否表现出浓厚传统国学味道的译论[8]。因此,本文所涉及的“中国传统译论的阐释”,就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翻译的理论论述的阐释,是关于其文本思想意义的推演,是立足历史文献,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话语的训诂而阐发义理。
学者王宏印指出:“对于传统译论文本意义的阐释,除了从语源考察或文本结构分析来推演作者的意图,还可以从理论话语的文化渊源进行阐释,来说明该理论的文化资源状况或作者所受的直接影响。”[8]267因此,从阐释的对象来看,可以是对传统译论文本字、词、句、篇的意义阐释,也可以是从社会、历史或文化渊源等文本外视角进行阐释。学者张江表示:“阐释以文本为归宿,只有能够帮助其他读者理解文本的,才是阐释。”[9]而为了阐释文本的意义,除了译论文本内部的阐释,文本外部的社会、历史或文化渊源的解读也必不可少。只有在一定社会、历史或文化语境中,文本的意义才有确定的可能性。综上,对于中国传统译论的阐释既包含基于文本的字、词、句、篇的解读,亦涵盖从文本外剖析其社会、历史或文化渊源,以期获得文本意义确定性的阐释。
二、中国传统译论的主要阐释模式
在阐释的路径中,注释是疏通文本意义注解的一种常见体例。《周礼·天官冢宰》贾公彦疏:“注者,于经之下自注己意,使经义可申,故云注也。”[10]汪耀楠先生在《注释学纲要》一书中明确指出,注释应当有明确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以今释古,以浅释深,以普通话释方言,以具体明确的内容解释含义广泛的概念[11]。《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一书中,对佛教用语“三达”、典故“白马驮经”、佛经史上的重要人物支谦,以及重要地名也进行了标注,原则是一般大学文科生能够读懂[12]。《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则采用西方哲学家Appiach深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的方法,借助注释、评注等方法,将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13]。其注释多达三百多条,提供了详尽的解释、背景及研究材料。
除了注释这种常见的体例,从阐释的时间维度来看,阐释的模式主要涵盖“以古释古”和“以今释古”两种,“以古释古”即沿用古人的意思来阐释传统译论文本意义,而“以今释古”则用现代的译学理论或观点来阐释传统译论文本意义;从阐释的地缘维度来看,阐释模式主要有“以西释中”和“以中释中”两种,“以西释中”即用西方的翻译理论或致思方式来阐释中国传统译论文本意义,“以中释中”则是从中国社会、文化、历史角度来阐释中国传统译论文本意义。由于划分的维度不同,这几种模式有交叉重叠的部分,譬如“五四运动”以来,文化先锋们为了建立新文化而引进了西方的学术规范和术语,对传统进行了彻底“改造”,“今”之现当代译论早早就打上了西方译论的烙印,因此,“今”“西”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区分。
“以古释古”不同于注释,注释是通过考据训诂,注重还原重难点字词的字音、原义与出处,而“以古释古”只是对传统译论的关键词语进行现代汉语翻译,即沿用古人的意思来阐释译论,讲求述而不作,这种阐释模式多出现在资料汇编的“史”的路径上。以《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和《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为例,二者均重视从史论的角度来阐释中国的翻译历史,以论述译论家的生平事迹及其译论贡献为主,穿插涵盖译论家思想的关键译论话语意义的阐释。譬如,马祖毅对“三不易”的阐释:“圣人是以当时的习俗来谈话的,古今时俗不同,要使古俗适应今时,很不容易,此其一;把古圣先贤的微言大义传达给后世的浅识者,很不容易,此其二;释迦牟尼死后,弟子阿难造经时尚且非常慎重,现在却由平凡人来传译,也很不容易,此其三。”[14]在讲到马建忠的善译理论时,陈福康指出:“马氏指出要达到‘善译’,必须平时就对译与所译两种语言都深有研究,甚至对各自文字的字源即其异同也深入考察。在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原文的音调,文句的繁简,文体的变化,以及义理精微之所在等,反复斟酌,随后还要摹仿原文的神情与语义。”[15]由于二者是从历史的维度来挖掘和整理传统译论,坚持以“立片言以居要”,将中国传统译论忠实地翻译为现代汉语,不敢有过多发挥。虽忠实原义,“但不利于发掘深层理论意义,使传统停留于传统,很难真正融入现当代译论。”[16]10
“以今释古”即用现代译学的观点来阐释中国传统译论,以《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和《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为例,二者都讲究从现代译学的观点来阐释中国传统译论。在讲到“五失本,三不易”时,朱志瑜指出,道安在处理《阿毗昙序》和《比丘大戒序》两种不同译本中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与现代译学中所说的文本类型相似[12]。张佩瑶在论及《大云经》是否为赞宁所说的“重译”时,引用当代学者孔慧怡的研究,打破了对“重译”的固有概念,认为对于赞宁而言,“即使只是对译本加上一个新疏,而让读者有了不同于无疏译本的阐释,或许就可以被看作为重译。”[13]197除此之外,在《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中,王宏印也多次采用现代译学的观点对传统译论文本进行阐释,譬如把“五不翻”的内容转换成“一词多义”“文化局限词”“约定俗成的通行译法”等现代术语的内容;在论述严复的翻译实践时,将严复译作为“达旨”所做的变通处理转换成增减法、换例法、注释法、比较法等现代翻译术语[8]。
“以西释中”,借用西方翻译理论或致思方式来阐释中国传统译论。譬如谈到道安“五失本”时,朱志瑜从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目的论出发,认为翻译是有目的的交际活动。为了达到向大众进行佛经“宣道”的目的,“五失本”中的“失本”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必须的[12]。张佩瑶论及道安时期佛经翻译盛况时,借用多元系统翻译理论来解释在译入语(社会政治)系统出现危机时,(宗教)文学的翻译将会从边缘向中心[13],论及中国佛经翻译及佛经翻译僧侣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是在于无法确定佛经源语时,提到这与西方解构主义观点中的传播与差异相吻合[13]。除了直接引用西方翻译思想或观点来进行传统译论文本阐释以外,运用西方哲学的致思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逻辑思辨也是“以西释中”另一种形式。譬如王宏印通过挖掘整理和逻辑思辨,将质派文派、音译意译、直译重译、译意译味、形似神似、翻译标准、可译性、境界、语言、译者等译论范畴,归纳为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标准或原则、主体性、可译性等问题[8]。张思洁从本体论、认识论和过程论来对传统译论进行范畴和体系构建,确立中国传统译论的十四对哲学范畴[7]。吴志杰围绕中国传统文化中“意”“诚”“心”“神”“适”五个核心词汇进行哲学思辨,从翻译本体论、伦理学、认识论、审美及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系统阐释,并构建了一个以“意”为核心的闭环的中国传统译论话语体系[17]。
“以中释中”,是从古典美学、文论、传统哲学话语或中国社会文化的角度去阐释中国传统译论文本的渊源。如,张思洁筛选了传统哲学中的十四对范畴,确立了道、诚、有无、意象、心物、虚静、言意(中介)、形神动静、虚实、言意(审美)、本、信、神似、化境、意合、文质的传统译论范畴[7]。《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和《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则在注释中多次从传统文化角度对核心词句进行阐释。譬如对僧祐论梵、汉文字起源时所说的“故字为言蹄,言为理荃,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朱志瑜指出,(荃蹄之喻)出自《庄子·外物篇》,全句意为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文字是用来转写语言的[12]。在辨析“文”与“质”的关系时,张佩瑶用孔子《论语》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来进行文化渊源的阐释[13]。除了传统哲学和古代文论以外,古典美学也是阐释中国传统译论的一大视角。如,王平在《中国传统译论的美学特色研究》中从比较美学的角度,通过对文学文本的鉴赏和分析,从文化诗学的层面进行中西文化比较[18]。另外,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从社会文化历史语境来对文本阐释也是“以中释中”的另一维度。如,《中国传统译论的社会文化阐释》聚焦中国传统译论的文本之外,从社会文化角度切入中国传统译论翻译的三次高潮,即佛经翻译时期的“重质”与“格义”,明清之际的“西学中源”以及清末民初的“中体西用”,意在阐释体现儒家民族中心主义的“华夷之辨”对翻译实践的影响,旨在展示传统译论的历史文化渊源与继承性。譬如: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由于受“名从主人,物从中国”的华夷观念影响,佛教为了传播,常常通过比附中国文化固有道家儒家观念来阐释佛教名词,即“格义”;支谶译介的《道行般若经》中借用“本无、自然”等道家概念来表示佛教的“缘起性空”[16]。《中国传统译论的社会文化阐释》将中国传统译论置于宏观历史文化背景中,探讨其发展的脉络、创新与继承的关系,为中国传统译论的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不足及启示
(一)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不足
在阐释的过程中,文本阐释的局限性和阐释的方法论问题是中国传统译论现代阐释中的两个主要问题。首先,文本阐释的视角较为局限,大部分中国传统译论的研究都聚焦译论话语中的关键词或句,缺少对译论语篇的整体把握,掐头去尾忽略整个语篇的意义,只注意序文主干部分的几个关键字,而忽略整个句子的意义,导致“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如,黄小芃通过对《法句经序》的序头和序尾现代汉语阐释,发现了被过去译学研究者忽视的重要译论,其内容涵盖《法句经序》的性质、形成过程、版本和编者的情况。随后,将序干部分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放在整个句子层面进行现代汉语阐释,追本溯源,发现这并非支谦的主张,而是支谦翻译实践中不得已而为之的对策和做法[19]。这也颠覆了传统译论研究中的“文”“质”之争的基本认知。除此以外,由于古代译论晦涩难懂,部分研究者在前人文本意义的阐释基础上转释,不对译论原文本进行考证分析,可能会导致文本意义经过多轮阐释,逐渐“失真”,如在《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中,王宏印发现梁启超把道安“五失本”第二条“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中的“文”理解为“谓好用文言”,实为大相径庭,道安此处的“文”出自孔子《论语》“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应是“文采”的“文”,而不是“文言”的“文”。[8]
其次,上述几种阐释模式中都存在方法论不足的问题。其中,“以古释古”,从历史的维度,用传统的名言、术语、概念、范畴,言说传统话语,把传统的概念、思想置于传统语境中理解[20],但却未将其进行现代转化,很难让传统译论走进当代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焕发新机。譬如,对“五失本,三不易”“五不翻”“六例”等话语的阐释,不少阐释研究停留在对传统译论字字对译的现代汉语阐释上,未能在理论或研究方法上做进一步的阐发。因此,客体阐释不足成了主要问题。阐释学认为,只有当个体处在“前理解—理解—后理解”的本体运动过程中,他才是完全的存在。如果一个学者拥有完善的“前理解”和“理解”能力,但却述而不作,解而不释,不通过“后理解”即阐释,来显示自己的价值和目的,那他也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学者[20]。因此,对文本意义的阐释不能只停留在语义还原与内部发展研究的阶段,还应该对其概念、论题和形态进行现代化转换,挖掘它与当代中国译论和西方译论对话的空间,思考它可以为当前中国翻译理论建设提供哪些新的材料、视角、观点和方法[21]。而不管是“以今释古”或是“以西释中”,受西学东渐的影响,西方逻辑论证推理和表述的方式已经渗透到现代译论的方方面面,西方译论也常常被用作阐释“他者”(中国传统译论)的工具,以西方译论为参照来阐释中国传统译论,是重构中国传统译论的有效途径。但在阐释的过程中,要把握好使用的方式,使之成为认识“自我”的“镜子”,而不是以其为标杆的“尺子”,用西方译论去丈量剪裁中国传统译论,只会让中国传统译论失去自我,成为阐释“他者”的产物。部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中以表面上的相似性掩盖了实质上的差异性,结果蒙蔽、消解、扭曲了中国译论的特质性[22]。这些都可能会破坏中国传统译论特有的理论性质和理论形态,不利于再现中国传统译论自身的完整性和内在系统性。“以中释中”,从外部和宏观的社会文化角度切入中国传统译论,却未对中国传统译论内部发展脉络和文本本身进行阐释。譬如《中国传统译论的社会文化阐释》在阐释佛经翻译时期重要译论时只选取了“五不翻”来阐释其文化观,但对其他观点,如“五失本、三不易”等重要译论话语的社会文化因素则未有涉及。
(二)中国传统译论研究方法的思考
1.训诂而阐发义理
对中国传统译论的阐释始终要立足于译论文本,一旦脱离了文本或者其所在的社会、历史或文化背景,意义的阐释则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阐释的对象应该始终围绕中国传统译论文本,是基于文本的意义推演。通过训诂而阐发义理,考据字证,还原传统译论的“本义”。而对传统译论的“本义”的考据,不应只考察其关键字句而忽略语篇整体的互文性,只有将译论文本置于整体语境中,才能挖掘出传统译论中的真正价值。如黄小芃聚焦彦琮《辩证论》的现代汉语和跨语阐释,从“法”“志愿益人”“践觉场”“牢戒足”“不染讥恶”等阐释关键点和难点,对比分析了历史学家、哲学家、译论家和香港学者的不同阐释版本,发现各家分歧所在,并根据字词训诂、具体语境的考察给出了自己的双语阐释版本[23]。通过这样的正本溯源,确保阐释对象意义的确定性。
2.古今、中西双向阐释
关于中国传统译论的阐释方法,不管是“以古释古”“以今释古”,还是“以西释中”“以中释中”,单向的阐释都可能会出现“厚古薄今”“厚今薄古”或是“以西律中”的情况,因此,古今、中西双向阐释,互相阐发,融合创新也许可以解决阐释过程中的跑偏或是极端化问题。通过中西译论思想体系之间的范畴比较和对照,发现彼此的异同,从而更好地凸显自身的特性和存在价值,这也被诸多学者视为中国传统译论现代阐释和转化的有效途径。张佩瑶表示,既从西方当代翻译理论的视角,观照所选条目的内容,又从传统译论的视角反观当代译论的相关思想,以捕捉中西译论相互阐释、互相诘问、互动融合的可能[13]。张思洁认为,只有当中国传统译论与西方理论互为“他者”,并且在比照中互相阐释时,他们才显现出各自的特性和自身存在的价值[7]。吴志杰坚持在中西比较中创获新见[17]。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即对传统译论进行现代阐释,使其内在精神价值进入现代译学理论系统。这种转化应从传统哲学范畴和译学元范畴入手,运用中外比较以及阐释与考据相结合的方法[24]。
四、结语
不论是何种阐释模式,“以古释古”“以今释古”“以西释中”或是“以中释中”,其基本方法论原则应是训诂而阐释义理,只有通过字义考证,还原译论话语的真义,才能把握中国传统译论中的理论资源,知道中国传统译论中有什么;古今、中西双向阐释,应该成为具体阐释的方法路径,以“他者”为参照,相互阐发,才能了解中国传统译论在当今该如何说,对构建现代翻译理论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黄忠廉教授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