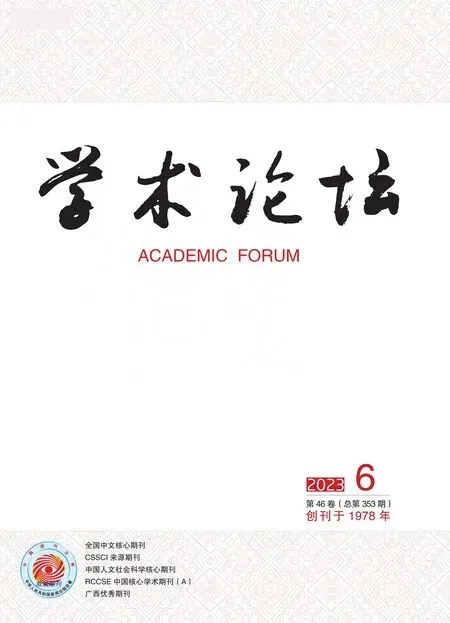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研究
刘家国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1).,这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国的必然路径,又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然而,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重创了传统闭环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导致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变革出现了许多新的影响因素,这不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大大提升了全球供应链治理的难度。此外,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特别是信奉单边主义的美国企图通过“关税战”“技术战”等手段对我国明星企业(如华为、中兴、科大讯飞等)进行出口限制和技术打压②李巍,李玙译.解析美国对华为的“战争”——跨国供应链的政治经济学[J].当代亚太,2021(1):4-45,159.,以图实现“去中国化”的目的,这对我国产业安全带来了巨大隐患。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冲突恶化导致全球供应链出现了治理体系松动、治理多边合作机制弱化、治理评估体系缺位等问题,使得现有的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已无法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大大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全面复苏与长远发展。因此,构建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与治理新格局,成了亟待解决的现实议题。
全球供应链是在全球范围内由研发设计、采购、制造、运输及服务等各个环节所构成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跨国分工不断演化的产物①林梦,路红艳,孙继勇.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趋势及我国应对策略[J].国际贸易,2020(10):19-25.。作为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全球供应链贸易额约占全球贸易总额的50%②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trading for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s[R]. Washington:World Bank Publications,2020:16.。毫不夸张地说,全球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决定着全球经济的命脉。2022 年9 月,习近平主席向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致贺信时强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③新华社.习近平向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致贺信[N].人民日报,2022-09-20(01).。全球供应链作为推动全球经济健康长远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全球供应链的运作效率是学术界最早关注的话题,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贸易理论,还是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比例学说,均强调通过特定的方式参与跨国分工或自由贸易是各国的最佳选择。21世纪之后的新贸易理论也旨在表明,无条件地参与全球分工是帕累托最优的④苏庆义.全球供应链安全与效率关系分析[J].国际政治科学,2021(2):1-32.。然而,自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学者开始意识到,通过禀赋优势参与全球供应链虽能给参与者带来最佳效用,但同样也可能带来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例如,自然环境、国际政治、文化差异、科技变革、企业内部管理以及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均可能对供应链的全球运作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⑤丁伟东,刘凯,贺国先.供应链风险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3(4):67-69.。因此,为了保障全球供应链的安全稳定运行,不少学者关注如何降低全球供应链的风险,并尝试开发一套集风险识别⑥徐绪松,曾学工,郑小京.供应链风险管理研究综述——风险识别[J].技术经济,2013(5):78-86,120.、风险评估⑦ABDEL-BASSET M, GUNASEKARAN M, MOHAMED M, et al. A framework for risk assessment,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economic tool for quantifying risks in supply chain[J]. 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2019,90:489-502.、风险预测⑧BOGATAJ D, BOGATAJ M. Measuring the supply chain risk and vulnerability in frequency spa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2007(1/2):291-301.和风险管控⑨郑小京,郑湛,徐绪松.供应链风险管理研究综述——风险控制[J].技术经济,2013(8):118-124.为一体的全球供应链风险应对方案,这为全球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提供了理论指导。
整理相关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外关于全球供应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缺少从社会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角度对全球供应链进行探讨,且很少关注全球供应链的治理问题。2023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指出,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人类社会需要更加公正合理、更趋平衡、更具韧性、更为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EB/OL].(2023-10-10)[2023-10-16]. 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202310/t20231010_11158751.shtml.。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文尝试构建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旨在为全球供应链治理提供决策参考。第一,回顾全球治理的发展史,在其基础上提出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内涵,以回答“全球供应链治理是什么”的问题;第二,基于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动因和现存困境,系统阐述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原因,以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全球供应链治理”的问题;第三,从政治、安全、经济、文明交流和生态五大维度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全球供应链治理的新变化,以回答“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什么可以治理全球供应链”的问题;第四,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基础,提出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的推进路径,以回答“如何实现全球供应链治理”的问题。
二、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内涵与动因
(一)全球治理的历史沿革
“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为控制、引导和操纵①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J].南京社会科学,2001(9):40-44.。在治理理论发展的前期,“治理”和“统治”两词通常是相互交织,其使用范围涉及国家的行政和政治活动。1992年,罗西瑙开创性地将治理和统治进行了辨别,认为治理的主体可以不是政府,治理也可以不需要通过国家的强制手段来实现,并将治理定义为存在于规则与制度空隙之间的某些制度设计,或是用于化解规制矛盾和协调利益竞争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范式②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张胜军,刘小林,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4-8.。罗茲(Rhodes)、斯托克(Stoker)、戈丹(Gaudin)等人从治理的定义、主体和目标等方面进一步丰富了治理的内涵③RHODES R A W. The new governance: 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J]. Political studies,1996(4):652-667.④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J].华夏风,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1):19-30.⑤戈丹.现代的治理,昨天和今天:借重法国政府政策得以明确的几点认识[J].陈思,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1):49-58.。作为治理理论的重要开拓者,罗西瑙(Rosenau)率先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将全球治理界定为涵盖各个层次的人类活动,从家庭到国际社会的制度系统,这些制度系统通过控制行动来实现不同的目的,进而对不同层面的人类活动产生跨国影响⑥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张胜军,刘小林,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56-159.。正是因为罗西瑙从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将全球治理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全球治理才成为家喻户晓的术语。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对全球治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定义,认为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各种策略集合⑦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rhood: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R/OL].(2022-11-24)[2023-04-04]. http://www.gdrc.org/u-gov/global-neighbourhood/chap1.htm.。在此之后,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对全球治理开展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囊括了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海洋治理、全球教育治理、全球网络安全治理等诸多领域,特别是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多边合作机制失灵、公共产品赤字的时代,全球治理再度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话题。
(二)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内涵
通过梳理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全球供应链和全球治理的研究体系较为完备,但尚未发现有学者就全球供应链的治理问题开展系统研究,且目前学术界对全球供应链治理的概念尚未作出清晰的界定。在全球供应链和全球治理概念的基础上,可将全球供应链治理定义为多元参与主体通过协商、合作、关系与规则等方式,围绕全球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包括产品的研发设计、原材料的采购、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以及资金流、物流、商流和信息流的流动等),形成具有共同价值、平等、权力去中心化等特征的一系列规范和制度,以期实现全球供应链高效、安全、绿色运行的共同目的。由此引申,全球供应链治理具有以下基本内涵。
第一,全球供应链治理需要“共商”。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共商”是指供应链参与主体对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基本理念、重点领域、体系机制和最终目标等方面的共同认识、辨析与判断,强调供应链参与主体的治理权力、机会和规则的平等。共商是进行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基础,体现了全球供应链治理的民主化,是现代社会全球供应链治理的重要方法,也是广大供应链参与主体的价值共识。全球供应链参与主体应该通过对话协商来共同设计全球供应链治理规制,使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愈发反映大多数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
第二,全球供应链治理需要“共建”。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共建”是指供应链参与主体在全球供应链治理方面的共同建设与创新,强调供应链参与主体的治理责任和义务平等。共建是进行全球供应链治理的根本路径,体现了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合作性,是汇聚供应链参与主体多重优势的重要平台,也是广大供应链参与主体的行动导向。全球供应链参与主体应该采取实际行动来构建全球供应链共同体,使全球供应链更加高效、安全和绿色,愈发满足大多数参与主体的发展需要。
第三,全球供应链治理需要“共享”。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共享”是指供应链参与主体共同享受全球供应链治理成果,强调供应链参与主体享受全球供应链治理成果的平等。共享是进行全球供应链治理的最终目的,体现了全球供应链治理的普惠性,是供应链参与主体合作的关键纽带,也是广大供应链参与主体的共同诉求。全球供应链参与主体应该通过提升自身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力和话语权,使得全球供应链的利益分配更加公平公正,愈发符合各参与主体开展全球供应链建设的初衷。
(三)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动因
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形成是由全球供应链的基本特征与参与主体的有限理性两方面因素决定。从整体来看,全球供应链是由不同国家、地区和企业等参与主体共同组成以满足全球消费者需求的全球供应网络,供应链参与主体通过比较成本优势,实现全球供应链运营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从个体来看,全球供应链是一个差异化、开放型的组织,每个参与主体都是相互分离、独立决策的个体,拥有自主决策权和控制权,且都是基于个体理性的角度去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导致全球供应链在行为和目标上可能存在矛盾。就国家而言,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差异导致国家之间的既得利益不一致,进而导致全球供应链在行为和目标上出现矛盾。供应链全球化不仅受到“无形之手”的操控,而且其背后有着“有形之手”的掌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势不可挡、一往无前之时,供应链的安全关切和权力逻辑销声匿迹,而在地缘政治博弈剑拔弩张之际,供应链的安全需求和权力锋芒便随之毕露。一方面,部分强国凭借其在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将全球供应链政治化、武器化,以此来服务自身的战略需求;另一方面,面对强国的市场和技术霸凌,小国同样试图借助政策调整来管控国内至关重要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以此来捍卫国家经济和产业安全。就企业而言,地域差异和组织独立性导致供应链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导致全球供应链在行为和目标上产生矛盾。在商业交易中,绝大部分企业往往会保留某些私有信息(如市场需求、价格策略、企业产能等),以便在谈判中取得主动权,此种行为造成了全球供应链中存在并非所有谈判者都知道的私有信息,且某些私有信息通常无法被证实,或者获取及证实的费用太高,从而无法签署有效的契约来监督和管控全球供应链的所有参与者,导致因为“隐藏行动”或投机行为带来的风险。因此,就全球供应链的基本特征和参与决策者的有限理性而言,对全球供应链进行系统治理势在必行。
三、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存在的困境
(一)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发展要求
第一,全球供应链治理理念落后。当前,全球供应链治理规范缺失,不能有效维持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和通畅运行,致使全球性问题不断产生并持续积累。一方面,作为全球供应链治理的主导者,西方国家向全世界强行推销符合自身利益的“普世价值”,大大加剧了全球供应链参与主体的国家安全冲突,削弱了全球供应链参与主体的治理合作共识;另一方面,西方国家长期奉行政治联盟和冷战思维,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供应链治理的理念冲突。
第二,全球供应链治理效率下降。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在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中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及地位严重缺失。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的强势兴起,新兴国家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出现新的变化,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已无法适应现有国家关系发展的需要。此外,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多变、国际冲突持续升温和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等因素造成全球供应链“断链”“脱钩”等一系列问题,打破了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的供需关系,治理规则已落后于日益复杂的治理议题。全球供应链治理体制的碎片化加剧,导致机制规则的模糊及其效应的降低,影响了供应链全球治理的实效性。
第三,全球供应链治理协调困难。全球供应链治理是一个协商、合作和共同管理的过程,需要多元化和多层次行为主体的共同参与。全球供应链治理涉及全球不同行为主体,但不同行为主体的利益观念存在分歧。在当今的全球供应链治理机制下,各个国家和企业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来参与全球供应链的管理。因此,在国际利益格局的分化和冲突中,全球供应链治理很难摆脱“猎鹿困境”①程同顺,邢西敬.从政治系统论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J].行政论坛,2017(3):18-24.,合作意愿不强,联合行动困难重重。全球供应链治理迫切需要各方加强统筹协调,而协调难点在于如何实现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的衔接。
第四,全球供应链治理权力垄断。全球供应链治理涵盖不同国家和企业,平等对话协商是进行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前提。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不能随意挥舞“市场”和“技术”的大棒来支配小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管理。大量事实证明,尽管大国的综合实力强劲,但其仍无法单独应对供应链的全球性问题。众多中小国家在全球供应链治理中的代表性,决定着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合法性和民主性。然而,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以及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仍由发达国家掌控的情形下,制度设计更偏向于发达国家,遏制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获取正当权利和合法利益的机会,导致严重缺乏公平性和公正性。
(二)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缺乏共生理性
国家既有个体理性,也有共生理性。个体理性以无视他国安全及全球安全的个体利益为决策依据,造成的结果是混乱、动荡和冲突。共生理性要求各国超越个体理性,在追求本国安全的同时兼顾别国的合理安全关切,从而避免个体理性压倒共生理性所带来的失序状态。当今世界,“冷战思维”与“热战冲突”并行,原有国际秩序出现松动和失效,新的国际规则在短时间内难以确立且被认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威胁上升,为了寻求自身的绝对安全,一些西方国家沉迷于拉帮结派,搞排他性的“小山头”和“小圈子”,严重破坏国际安全秩序,加剧全球治理的赤字。就全球供应链治理而言,西方国家在“零和博弈”思维的驱动下,操纵其拥有的能够破坏和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手段与能力,企图通过技术断供、贸易脱钩、区域排挤等手段,遏制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科技水平提升,以此来稳固其作为全球发展利益的主导者和分配者的地位②张杰,陈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风险研判与维护策略[J].改革,2022(4):12-20.。
(三)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出现失衡
第一,国际权力格局重塑,致使国际秩序涣散。世界格局的多极化与均衡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其变化的未知性所带来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必须承认,在国际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势必会出现国与国间不同势力的竞争和对抗,这也是未来进行全球供应链治理的主要背景和关键影响因素。虽然“斗而不破”仍是当前大国竞争的主流基调,但新兴国家综合实力的变化与现存国际权力结构之间的失衡,势必会加剧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态势。就其对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影响而言,主要表现为权力结构变化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竞合的影响。
第二,地缘经济秩序强化,加速“去中国化”。免疫屏障的形成缓解了全球疫情,全球商务贸易也逐步恢复,但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是全方位且长期存在。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日本等国家深刻认识到“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潜在风险,开始注重供应链效率和安全的平衡,进而提出了“中国+1”和供应链“去中国化”的战略,将地处中国的部分产业转移至本国或其他区域,从而分散供应链风险。例如,为了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减少对进口的依赖,日本投入20亿美元用于推进“供应链改革”项目,试图将产业链供应链转移出中国。据东京商事研究公司对2600家日资企业开展的调查数据,在日本官方宣布进行“供应链改革”之后,有37%的企业有意向将部分生产线撤出中国①芯智讯.日本政府出资2435 亿日元,鼓励日资企业将生产撤出中国[EB/OL].(2020-04-10)[2023-03-20].https://mp.weixin.qq.com/s/yxLMVaWdxCXoMvIsoLfYKg.。
第三,治理体系区域化凸显,致使治理机制乏力。供应链区域化是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演进过程中出现的新趋势。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在局部地区进行资源配置的优势逐渐大于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配置的优势,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不断缩短,区域化、本土化逐渐成为供应链发展的新形态。此外,参与主体多样化、安全需求迫切性和利益诉求多元化使供应链的区域治理需求进一步衍生。因此,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区域化所显露的“竞争性多边主义”特性②MORSE J C, KEOHANE R O. 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J].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2014(4):385-412.,与分散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多元的利益诉求一拍即合,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治理体系的安全性,扩大了各类主体参与全球供应链治理的途径,致使现行的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宛如“空中楼阁”。
第四,治理理念碰撞,加速共同价值瓦解。全球供应链参与主体的价值理念是影响其决策偏好的关键因素,而各参与主体对利益的共同诉求则是建立和保持供应链稳定合作的基本条件。无论是认知全球性问题,还是选择全球供应链治理原则及其实现机制,都要求全球供应链各参与主体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在特定议题达成初步共识后,再在策略和实施上作出抉择。在后疫情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所引发的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强化国际社会的利己主义思想,使得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倾向于追捧切实利益,同时推卸自身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导致进一步削弱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信任③阙天舒,张纪腾.后疫情时代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面临的挑战及中国选择——基于实验主义治理视角的分析[J].国际观察,2021(4):125-156.。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全球供应链治理的五大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议题,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囊括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大方面内涵,是应对全球治理难题的重要理念。全球供应链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其治理可行性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一)政治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塑全球供应链治理的价值共识
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以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等方式破坏、遏制他国民族发展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大肆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霸权优势,通过学术形态、影视作品、文学艺术和外事交往等方式向全世界散播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思想的价值观④沈贺.美国文化霸权与“普世价值”在我国的传播[J].思想教育研究,2017(1):37-42.。这一套看似完美无缺的价值理念成为许多国家早期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思想武器。就“普世”而言,“价值”的标准应是地位平等、内外统一、不分远近、不论亲疏、统一执行的,但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行动却一直奉行双重价值标准,即大国之间的自由以侵犯小国的自由为条件,强国之间的民主以剥削弱国的价值为基础,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人权以引发不同种族间的敌对为行为导向⑤黄陈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全球治理内涵及方法论展现[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0-22.。由于民族、种族、阶级和国家的存在,人们在价值认知上存在差异,导致“价值”的“普世”在理论上无法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核心思想的“共同价值”。不同于“普世”的普遍性,“共同”讲究相对性,其不排除世界各国人民对“价值”有不同的看法,客观地承认了人在价值认知上的差异性。当今世界,引发地缘政治危机、国际冲突、全球供应链“断链”“脱钩”等全球治理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国家之间的价值理念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价值”的提出,有效化解地区分歧,凝聚人类共识,增强国家互信,为推进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价值导向。
(二)安全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全球供应链治理的新型国际关系
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全球化进程中独占经济、科技和军事发展的鳌头,掌控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具体而言,在全球供应链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控制产业链供应链的高端核心技术,同时通过“市场机制”和“技术限制”等手段打压第三方国家的发展,以维护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霸主地位。从微观上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这种不平衡的全球供应链利益分配模式使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沟壑越来越大。财富正在加速向世界上1%的精英群体集中,而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则成了被剥削对象,他们不仅没有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而且生存愈发困难。从宏观上来看,畸形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放大了“马太效应”,全球的经济稳定面临潜在威胁(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全球供应链治理中的国际关系新的论断,即传统国际关系背后所体现的权力分配格局可以通过和平、协作、共赢的方式予以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建立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而构建普遍安全世界的主要内容是保障全球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各国应该摒弃暴力、冷战的手段,通过平等协商、深化合作的方式来维护全球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供应链治理中的新型国际关系描绘了宏伟蓝图。
(三)经济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明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前进方向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数据,从1969 年开始,在短短11 年的时间里,全球大宗商品贸易总额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从18%快速上升至42%,特别是在2007年,全球大宗商品贸易总额占全球GDP 的比重一度接近50%①UNCTAD.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22: development prospects in a fractured world: global disorder and regional responses[R/OL].(2022-10-03)[2023-04-06]. 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s.。换而言之,国家之间的商贸活动成了全球GDP 增长的主要动力源。然而,自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商品贸易额逐渐收缩,2022 年全球商品贸易总额占全球GDP 的比重缩至31.8%,这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出现倒退现象。其中,始作俑者是西方发达国家所倡导的贸易保护主义,其以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为由,制定了一系列逆全球化措施,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公然挑衅国际统一市场和跨国分工网络,违背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根据熵增理论,一个封闭区域的熵值会持续增加,直至死亡,要想避免死亡,必须开放,与外界交换能量、信息、人才②胡奇英.人类命运共同体供应链的内涵、使命及框架体系[J].供应链管理,2022(1):7-16.。自我封闭是导致自身毁灭的开始,“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③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34.。全球供应链的本质是开放,在开放中重组,在动态中调整,以谋求更广阔的发展。加速推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开放,增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互利协作,引领国际分工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协调与共赢的方向演进,具有更加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供应链治理明确了发展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
(四)文明交流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完善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参与机制
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参与主体包括国家和第三方管理机构等,各参与主体之间理应形成地位平等、互帮互助、发展成果共享的合作伙伴关系。然而,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掌控着全球供应链治理的领导权。在以主观意识为主导的治理机制下,当国与国之间发生产业链供应链冲突时,西方发达国家都是站在自身角度提出问题解决方案,发展中国家很难通过现有的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来维护自身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正当权益。最终,看似“多边”的全球供应链治理机制,实质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单边”供应链治理平台,导致部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供应链治理的能动性不强,降低了全球供应链治理的效率。近年来,随着全球供应链治理机制的不断完善,G20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等平台使部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供应链治理的梦想如愿以偿。但对于全球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现有的全球供应链治理机制仍存在许多不足,全球供应链“断供”的现象仍在全球各地频繁发生。特别是新冠疫情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以保护自身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为由,大肆在全球制造供应链“断链”“脱钩”事件,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和通畅运营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为了满足对全球供应链治理的需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框架内,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建设始终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注重通过双边合作、三方合作、多边合作等多样化合作方式,使得共建国家各骋所长,充分激发自身发展优势和潜能。“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不具有排他性,不同文明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可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完善了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参与机制。
(五)生态维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贡献全球供应链绿色治理的中国智慧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天堂,也是人类唯一的家园,呵护好地球家园事关人类福祉。自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力获得空前发展,但也加剧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严重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平衡,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近年来,全球气候急剧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荒漠化加剧、臭氧层漏洞扩大等生态危机深刻验证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矛盾,人类的生存发展面临巨大的威胁。为了维护生态平衡,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和资源安全,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大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新变局、新形势下的生命力,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就全球供应链而言,坚持把绿色作为底色,推进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制造、绿色投资和绿色金融,进一步倡导建设更为紧密的全球供应链绿色发展伙伴关系。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供应链的绿色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五、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推进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商”“共建”和“共享”,该理念为全球供应链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具体而言,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基础,以凝聚合作共识、深化战略合作、完善体制机制和共享治理成果为行动导向,以承认多元参与主体的差异性、寻求多元参与主体的一致性、拓宽“一带一路”合作领域、创新多边双边合作模式、建立国际治理组织、建立双边和小多边治理组织、打造国际公共产品、建立共享机制为关键抓手,以实现全球供应链的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共同期望。
(一)凝聚合作共识
第一,承认多元参与主体的差异性。在自然和社会中,差异是一种最为普遍的现象,是世界运行最为原始、最为永恒的动力。如同树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一样,多元主体的跨地区参与导致全球供应链出现许多差异性(如目标差异、文化差异、地理差异、政治制度差异等)。参与主体之间的差异性是导致全球供应链脆弱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对待全球供应链参与主体之间的差异成为全球供应链治理的一大难题①马俊峰,马乔恩.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内在逻辑和时代价值[J].学术论坛,2018(2):70-7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参与。”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35.对于全球供应链而言,承认、尊重、包容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差异性是实现各参与主体平等交流的前提,是凝聚合作共识与理念的必经之路。只有敢于承认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差异,才能更好汇集各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和意见建议,以便从中寻求共同利益,进而实现多元参与主体的亲密合作,提高全球供应链的运作效率和韧性。
第二,寻求多元参与主体的一致性。差异性中往往蕴藏着一致性,承认差异性的最终目的是寻求一致性。从全球供应链角度来看,全球供应链参与主体之间的矛盾与共识并不是始终不变的,在加强对话与协作中需要用系统性、动态性和发展性的眼光看待参与主体的异同及竞合关系,搁置小异,寻求大同。较为简单、实际且机智的方式可以先从特定的实际合作入手,由浅入深逐步探寻、扩大并构建各参与主体在理念上的相互共情或认同,在同一观念下扩大对特定场景差异性的认知力与接受度,以实现参与主体的“求同存异”。此外,观念具有根深蒂固的属性,但往往也具有流动性的特征,各参与主体通过学习借鉴,以实现择善而从、举一反三。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各参与主体在政治、安全、经济、文明交流和生态方面所面对的共同挑战和共同利益诉求日益增多,可以通过对现行的全球供应链治理机制进行变革,创建能够振兴国际领导力、实现利益捆绑、加强协作基础的新型国际机构,以此来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二)深化战略合作
第一,拓宽“一带一路”合作领域。“一带一路”倡议惠及沿线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广泛辐射和普惠效果③李文锋.我国参与全球供应链治理的主要方向[J].开放导报,2020(2):28-35.,已经成为共建国家为了实现互利共赢的战略目标而构建的具有全球性和区域性特征的现代新型供应链体系创举,是参与各方一致诉求的生动表达。“一带一路”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搭建、重塑和变革是一种全新的、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具有起点高、辐射范围广、要素自由流动等特点,既有需求端的大力驱动,也有政府的鼎力支持。高效运用云计算、大数据、5G 和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推动与共建国家构建数智化、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化的新型供应链体系。注重“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以参与者生态环境利益为主要建设目标之一,扩大绿色发展的溢出效应,推动建设绿色供应链体系。抓住全球供应链重塑、传统行业迁移的契机,努力挖掘“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产能合作潜力,引导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向共建国家和地区迁移落地,推动共建全球供应链体系。此外,依托“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中心城市和港口资源,孵化一批具有国际或区域影响力的供应链协作平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集设计研发、采购、制造、物流运输和销售等环节于一体的综合性供应链服务网络。
第二,创新多边双边合作模式。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和气候环境变化等因素对全球供应链供给、运输和需求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新冠疫情引起的物流瘫痪、地缘政治博弈下的供应链本土化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海运运输停滞等。提升全球供应链韧性,促进世界经济复苏,需要各参与主体共同探索全球供应链合作的新模式。将中国的“世界工厂”优势、欧美的核心技术优势以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诉求进行有机整合,借助多边交流平台(如G20 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等)和多边合作平台(如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创新产能合作方式,推动构建国际供应链合作平台,保障全球与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高效运行。推进与部分国家就关心的重要领域(如半导体、电池、集成电路、精密仪器等)进行沟通交流,签署贸易、劳务、土地、科技合作和经济援助等协议,有目的性地开展双边多边合作,实现各方利益的深度融合。大力推动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的互通互联,畅通劳动力、资本要素的跨国跨区域流动,打通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动脉,保障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三)完善体制机制
第一,探索建立全球供应链国际治理组织。治理系统性思维是解决治理碎片化的重要思路,建立多元化、多层次行为主体共同参与的全球供应链治理组织,可以提高区域性国际治理组织的协调和整合能力,从而优化全球供应链治理结构,提升全球供应链治理效能。建立全球性的供应链治理机构,快速有效地应对全球供应链的效率与安全问题,改善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以全球供应链治理各类高端论坛常态化、制度化为契机,构建涵盖发展和治理两大职能的全球性供应链治理机构,提高各参与主体的协调能力,协助各参与主体作出科学决策,为治理集体的联合行动指明方向。以应对某一长期存在的全球供应链共同问题(如供给不足、运输中断、气候变化等)为导向,构建全球供应链国际治理组织,率先实现某一供应链环节的有效治理,进而逐渐将治理拓展覆盖整个全球供应链网络。基于不同参与主体面临的全球供应链共性问题,更易建立全球供应链专业性治理组织,从而实现治理效能的最大化。
第二,加快建立全球供应链双边和小多边治理组织。当前,全球供应链治理权力、机会和规则并不平等,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供应链治理体制机制,迫使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平等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这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供应链治理的能动性。若得不到供应链大部分参与方的配合和支持,构建多元化、多层次行为主体共同参与的全球供应链治理组织就会极其困难,且构建成本也不可估算,即便可以建成,其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有待商榷。从政治关系、地域差异、供应链治理需求与治理能力等方面出发,建立全球供应链双边和小双边治理组织更加切实与紧迫。优先与关系友好的邻近国家和地区建立深层次、多样化的双边供应链治理组织,就共同关注的供应链问题交流看法,深化治理合作领域,增强跨境治理效能。优先与邻近的多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小多边供应链治理组织,共同应对跨境跨区域的供应链挑战,保障各方的共同利益。探索与供应链治理能力和治理环境较差的国家和地区共同构建针对性强、职能明确的供应链治理组织,在优化这类国家和地区供应链治理能力和治理环境的同时,有效防止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外溢,共同维护相关国家和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四)共享治理成果
第一,打造包容普惠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是进行供应链治理成果全球共享的前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具有强大优势,积极参与并领导全球治理,而设计并提供具有霸权主义性质的国际公共产品是美国引领全球治理、维护其国际地位的重要方式(如建立联合国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进入21 世纪后,财政赤字、军事过度扩张、金融危机等因素导致美国的支付能力一落千丈,进而使其在提供公共产品、稳定市场、促进合作等功能性服务方面的核心作用下降①IKENBERRY G J.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3.0: America and the dilemmas of liberal world order[J].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2009(1):71-87.。当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所获得的利益回报无法弥补其供给支出时,美国毫不犹豫地选择断供国际公共产品,并试图亲手终结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特别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在“美国优先”战略的引导下,美国随意退出外交、国际安全、环境、卫生等领域的一系列全球合作组织,多次摒绝承担国际义务,导致现有的国际公共产品供需严重失衡。因此,亟须打造不具有霸权性质且更加包容普惠的国际公共产品。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应在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提升自身话语权和国际地位,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努力探索符合全球人民共同利益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①周波,张强,寇铁军.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历史演进、发展趋势及中国的策略选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2(10):10-21.。
第二,建立公平公正的共享机制。“共享”就是通过灵活性的制度安排,使得全球供应链治理更加公正合理。共享是社会发展的美好憧憬,规则、机制和制度等是实现这一憧憬的重要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规则制定、权力分配、技术优势等方式对全球供应链治理加以控制,并坐拥管理全球供应链的绝对权力,随时转嫁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危机,而发展中国家仅依靠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输出的方式,苟且于全球供应链之中,并被迫承受全球供应链高速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这一现状对全球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带来巨大威胁,暴露出现有全球供应链共享体系机制的弊端,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供应链共享体系机制亟待建立。一方面,世界各国要矢志不渝地坚持国际法治,坚决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全球供应链治理理应遵循各国的共同原则与一致意见,不能搞一家独大和“一言堂”。另一方面,世界各国要通过自身实力与智慧,增加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力,提高在全球供应链治理中的话语权,以实现全球供应链治理成果共享的民主化、公平化和公正化。
六、结 语
国际权力结构的调整给全球安全稳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也使得全球供应链从原本的纯商业问题转变成了重大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与此同时,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也为各国在全球供应链治理中弘扬新理念、新价值创造了新机遇。面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逆流,中国号召各国应始终坚持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基本定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构想,为全球供应链变革治理体系、摆脱“断链”“脱钩”和提升治理效能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供应链的治理开辟了新的思路和路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治理目标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新治理思路和路径的落实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挑战。一方面,地缘政治博弈仍会阻挠治理进程。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地缘政治博弈始终贯穿人类的发展史,是全球供应链治理进程中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地缘政治博弈会对世界的经济、文化、环境等带来危害,甚至导致国家之间针锋相对,乃至兵戎相见。另一方面,突发事件时常干扰治理进程。从全球供应链的发展历程来看,突发事件与全球供应链的通畅运行休戚相关,其突发性、不可预测性和破坏性等特点更是为全球供应链的良好运行埋下了不定时炸弹。因此,结合当前实际和未来变化,有效地提出并落实全球供应链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模式,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