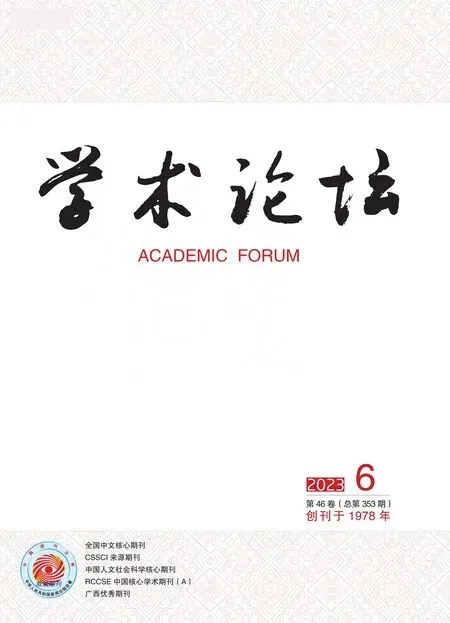双边领事条约在领事保护实践中的价值
谢海霞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1).。《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以下简称《对外关系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了我国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我国公民和组织在海外的安全和正当权益。2023年9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以下简称《领事条例》)是专门规定领事保护与协助的行政法规,其明确我国领事保护与协助的主体、内容、方式和措施,明晰了各相关机构的职责,构建了领事保护与协助的国内统筹机制,为维护我国在海外的公民、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正当权益提供国内法依据。针对在海外的我国公民被拘留、逮捕、监禁或者以其他方式被驻在国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领事条例》第九条明确规定我国驻外外交机构应按照驻在国法律和我国与驻在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开展领事保护与协助。准确理解和适用《领事条例》中所指的国际条约内容,既是我国对外关系法治化的要求,体现对我国《对外关系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和第三十一条规定的“采取适当措施实施和适用条约和协定”的遵守,也符合保护我国公民正当权益的需要。我国是《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缔约国,同时我国与多个国家之间也适用双边领事条约或者双边领事协定(以下统称为双边领事条约),根据《领事条例》第九条所规定的特殊情形,在为我国国民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时,需要厘清多边领事公约和双边领事条约的关系,尤其要厘清双边领事条约规定的具体化的操作范式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双边领事条约为领事保护与协助提供了程序规则,这些程序规则的惯行也推动了领事保护走向法治化进程。
一、双边领事条约适用上的有限性
我国《领事条例》第九条的内容源于1963 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①《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对“与派遣国国民通讯及联络”进行了规定:“一、为便于领馆执行其对派遣国国民之职务计:(一)领事官员得自由与派遣国国民通讯及会见。派遣国国民与派遣国领事官员通讯及会见应有同样自由。(二)遇有领馆辖区内有派遣国国民受逮捕或监禁或羁押候审、或受任何其他方式之拘禁之情事,经其本人请求时,接受国主管当局应迅即通知派遣国领馆。受逮捕、监禁、羁押或拘禁之人致领馆之信件亦应由该当局迅予递交。该当局应将本款规定之权利迅即告知当事人。(三)领事官员有权探访受监禁、羁押或拘禁之派遣国国民,与之交谈或通讯,并代聘其法律代表。领事官员并有权探访其辖区内依判决而受监禁、羁押或拘禁之派遣国国民。但如受监禁、羁押或拘禁之国民明示反对为其采取行动时,领事官员应避免采取此种行动。二、本条第一项所称各项权利应遵照接受国法律规章行使之,但此项法律规章务须使本条所规定之权利之目的得以充分实现。”的规定。我国于1979 年加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作为公约缔约国,我国驻外外交机构依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开展领事保护与协助。有学者在对我国签订的双边领事条约进行分析之后,认为我国双边领事条约规定范围过窄②颜梅林.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中的“领事通知权”研究——以中外双边领事条约(协定)相关条款之比较及完善为视角[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58-68.,该判断是否准确需要结合领事法的发展实践展开分析,厘清双边领事条约的适用条件。
(一)双边领事条约的内容被统一化
现代领事法是对双边领事条约实践的总结和发展。作为一部全球普遍适用的国际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是对双边领事实践和习惯国际法的编纂,为领事保护本国国民和利益构建了一套规则体系。双边领事实践历史悠久,领事机构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领事制度是基于国际贸易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是为了维护国家海外利益需要而逐步形成的规则,国家间通过习惯做法和双边领事条约调整双边领事关系。双边领事条约实践可追溯到1769年3月13日法国和西班牙缔结的《帕尔多条约》,该条约被认为是第一个现代的领事条约③戈尔-布思.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M].杨立义,曾寄萍,曾浩,等译.5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305.,有关领事保护的职能在双边领事条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授权领事在领区内保护派遣国国民和法人的权利和利益的条款体现在多个国家的双边领事条约中。为保护在海外的本国国民,领事需要与国民保持联系和沟通,提供领事服务和领事协助,“对领事履行保护职务至关重要的是,他必须有权在派遣国国民被逮捕后立即得到通知,并可到狱中探视和为其提供法律及相关协助”④李宗周.领事法和领事实践[M].梁宝山,黄屏,潘维煌,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127.。因此,针对特定情形下限制一国国民人身自由的事项应迅即通知派遣国领事被逐步写入双边领事条约。领事保护本国国民的实践以双边领事条约为前提,强调对等原则的适用,如果两国之间没有双边领事条约,则很难实现对本国国民的保护。双边领事条约对领事通知条款的纳入有着阶段性发展过程,并且各个双边领事条约中对领事通知的规定也不尽相同,直到领事法逐步被成文化、法典化,统一的领事通知和领事会见条款最终被写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制定模式和内容深受1961年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影响,是“以普遍接受的规则为基础,实现了现行习惯与法律渐进发展的完美结合”①法斯本德,彼得斯.牛津国际法史手册:下册[M].李明倩,刘俊,王伟臣,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823.。目前,《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有182个缔约国②Vienna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Z/OL].(2023-04-12)[2023-09-05].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III-6&chapter=3.,其所确立的规则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成为了联合国制定的最重要的多边条约之一,推动了领事立法的标准化和现代化。
针对一国国民在海外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情形,《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构建了领事保护与协助的基本规则,其中,公约第五条明确了领事有权在接受国内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的利益,公约第三十六条赋予派遣国领事官员享有与本国国民通讯及联络的权利,以确保派遣国领事官员和本国国民之间能自由通讯及会见。一旦领区内的派遣国国民被逮捕、监禁或羁押候审、拘禁或者被采取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时,经本人请求,接受国主管当局应“迅即通知”派遣国领馆。尽管历史上双边领事实践中通知领事的做法已经非常普遍,各国也都认为领事与本国国民通讯及联络的权利对执行领事职务至关重要,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草案文本在多次被修正情况下,才最终将领事通知的内容写入。随着《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生效,公约第三十六条得以普遍适用。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被认为建构了一套领事保护与协助机制。根据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如果一国国民在他国被逮捕、监禁、羁押候审或者以其他方式被限制人身自由,则(1)被拘禁的派遣国国民享有领事通知权,这是一项个人权利;(2)接受国负有双重义务,包括迅即告知派遣国国民享有通知领事官员的权利和迅即通知派遣国领事官员的义务;(3)派遣国领事官员享有会见本国国民的权利,并有权提供领事协助;(4)如果个人权利或者派遣国的权利被损害,依据国际法,派遣国领事官员有权与接受国进行交涉、抗议,必要时可以采取外交保护措施;(5)如果接受国违反义务,个人可以在接受国国内法律框架内寻求法律救济;(6)针对接受国的违反条约义务行为,派遣国有权寻求国际救济,包括但不限于在国际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接受国承担国家责任。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制定影响了各缔约国的嗣后双边领事条约实践,其规定成为双边领事条约的缔约范本。为了便利本国领事官员履行职责,各缔约国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相关规定写入双边领事条约,尤其是涉及领事保护的条款,这“在1964 年《美国和苏联领事条约》中或许得到了最充分的证明”③李宗周.领事法和领事实践[M].梁宝山,黄屏,潘维煌,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136.,其第十二条重申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的内容。不仅如此,一些国家间的双边领事条约还将特定情形下的通知领事官员的义务视为一项绝对义务,而不是取决于被逮捕或者被拘禁的国民的意愿。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领事协定》第二十条中专门规定了此项内容,明确了中澳之间适用《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并同意本协定未明确规定的事项”以及协定中的用语都按《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处理。此外,我国缔结的其他双边领事条约也有类似的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领事协议论》第十二条的规定。
(二)双边领事条约的适用要合“规”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缔结对双边领事条约的适用产生了深远影响,双边领事条约的适用不得违反公约的规定,减损公约的效力。相较《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双边领事条约是特别法,理论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是一项广为接受的释法准则,也是一种解决规范性冲突的手段,尽管在国际法上,关于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的实践考察仍然缺乏清晰的适用标准,如果说“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指的是一个标准的法律推理手段,国际法以及其他被视为体系的法律领域都采用这个手段④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EB/OL].[2023-09-22]. https://legal.un.org/ilc/documentation/english/a_cn4_l682.pdf.。在领事法的实践中,也存在着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实践,表现为双边领事条约与《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在适用上是否存在潜在冲突问题。就《领事条例》第九条所涉事项而言,如果我国公民在海外被拘留、逮捕、监禁或者以其他方式被驻在国限制人身自由的,领事在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时,不仅要适用《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和习惯国际法,如果接受国与我国缔结了双边领事条约,还涉及同时适用的情形。
第一,对于同一内容,如果双边领事条约与《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规定相同,则优先适用《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在双边领事实践中,即使规定一致、用语相同,依然存在着对同一规定的不同解释问题。例如,《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规定了接受国负有“迅即通知”义务,这种义务是接受国对派遣国所负之义务,还是包括对被逮捕或拘禁的外国国民也负有通知义务,在实践中就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在德国诉美国的“拉格兰德案”①见LaGrand(Germany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Judgement,I. C.J.Reports 2001,p.466.中,美国和德国争议的焦点就涉及《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是否也涉及个人权利,德国认为无论从该条款用语的通常含义,还是综合考虑公约条款上下文,都可以看出第三十六条也“为个人赋权”,但是美国否认这是一项个人权利。在印度诉巴基斯坦的“贾达夫案”②见Jadhav(India v. Pakistan),Judgment,I.C.J.Reports 2019,p.418.中,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同意“迅即通知”是一项义务,但是何谓“迅即”,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双方诉到国际法院,国际法院认为,巴基斯坦是在逮捕贾达夫后三周才通知,这构成了对“迅即通知”义务的违反。我国驻外外交机构在依据《领事条例》履行职责时,需要密切关注《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最新发展实践,重新认识和解释双边领事条约下的义务,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我国国民的正当权益。
第二,就同一事项,如果《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与双边领事条约规定不同的,双边领事条约的规定是否有效以及能否适用,需要结合《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考察。这就存在两种不同的适用情形。一种情形是,如果双边领事条约的规定没有减损《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效力的,则双边领事条约可以继续适用。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领事条约》第十三条规定,如果缔约一方的国民在领区内被拘留、逮捕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被剥夺自由时,接受国主管机关应在三个工作日内通知领馆,除非该国民书面明示反对通知领事。此处关于通知期限的约定以及当事人拒绝领事通知和拒绝领事会见的规定,都是《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所没有规定的,如果这些约定不减损《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效力,则中俄之间可以适用双边领事条约的特别规定。另一种情形是,如果双边领事条约的规定实质上构成对《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背离,尤其是对《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的背离,则双边领事条约的特别约定不一定具有法律效力,二者之间存在适用上的潜在冲突。具体到我国《领事条例》第九条所针对的特殊情形,我国驻外外交机构在适用双边领事条约时,应首先考察双边领事条约的规定是否合“规”,只有在相关条款不违反《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前提下,双边领事条约才能予以适用。
二、双边领事条约适用应符合最低标准
我国驻外外交机构依据《领事条例》第九条,在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时,如果需要适用双边领事条约,应符合《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要求的最低标准。国际法院在“贾达夫案”中明确指出,《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被认为是确立了领事保护的最低标准,任何双边领事条约的内容都不得减损公约的内容,尤其在涉及有关个人权利保护方面。
(一)为“个人赋权”是标准确立的重要前提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缔结的目的是确保领馆能代表本国有效执行领事职务,公约本身并不创设个人权利。随着国际法日益“人本化”,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愈加重视,尤其是自20 世纪初以来,现代性转换了叙事范式,学界对传统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并主张将个人“视作法律秩序的最终和真正的主体”①法斯本德,彼得斯.牛津国际法史手册:上册[M].李明倩,刘俊,王伟臣,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319.,个人最终成为国际法律秩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构建了现代国际法中个人权利保护的框架和基础,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在是非判断的价值取向上出现了强调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倾向,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趋于提高……在涉及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时,国际舆论和道义判断的天平往往向弱势的一方倾斜”②黄惠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107.。这种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从国际社会的发展以及国际法的特性来看,可以依靠国际法主体的自觉行动,也可以通过国际法机制和体制的革新来推动。无论动因如何表现,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势对领事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被赋予了新的含义,“领事在为被逮捕的派遣国国民提供领事保护被证明是《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③QUIGLEY J B .Vienna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 in retrospect and into the future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J].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2013,38:1-26.。随着领事通知条款被纳入三个核心人权条约④三个核心人权条约是指《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和《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自成一体的外交领事法⑤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EB/OL].[2023-10-22]. https://legal.un.org/ilc/documentation/english/a_cn4_l682.pdf.和人权法规则体系之间的互动推动了领事通知规则的发展,领事会见开始逐步被“人权化”。2019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领事会见是一项人权”⑥联合国大会文件A/74/318[EB/OL].(2019-08-20)[2023-10-22].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9/257/90/PDF/N1925790.pdf?OpenElement.,指出向在海外面临死刑的国民提供某种标准的领事保护已经成为一般惯例,这将推动领事会见成为一项人权。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规定了领事保护的核心内容。当一国国民在海外被逮捕、拘禁或者被采取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时,领事通知是触发领事保护与协助的机制。然而,问题在于领事通知是谁的权利,是国民的权利还是国家的权利?在1979 年美国诉伊朗案⑦见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Staff in Tehran (U.S. v. Iran),1980 I.C.J.3(May 24).中,美国提出伊朗作为接受国,有义务保障美国驻伊朗领事官员会见其本国国民,由于伊朗扣押了美国驻伊朗的领事,导致其无法对有需要的美国国民提供保护,因此不仅侵害了在伊朗的美国国民领事会见的权利,而且也侵害了美国作为派遣国保护其国民的权利。也就是说,就领事保护的实质而言,美国主张⑧见Memorial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Staffin Tehran (U.S. v. Iran),1980 I.C.J Pleadings 174(Nov. 29,1979).其不仅包括保护国家的权利,而且也包括保护个人的权利。如果《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调整的是缔约国之间的关系,那么该外国国民的国籍国当前有权利得到通知,问题是该外国国民是否也享有被告知有权通知本国领事的权利,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种被告知的权利可以被归入“米兰达规则”的第四规则⑨SAMSON E.Revisiting Miranda after Avena: the implications of Mexico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J].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2005(5):1068-1127.。如果这种个人权利存在的话,则当外国国民被逮捕拘禁时,采取措施的国家就负有告知义务和通知义务,即告知外国国民享有通知其本国领事官员的权利,并尽到通知该国民国籍国的义务。在实践中,对《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解释和适用存在争议,因此该条款也被认为是“一条有争议的条款”⑩SHAW M N. International law[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1146.,围绕该条款的解释和适用引发了多起国际争端,国际法院审理了多个与此相关的案件,包括1998年的“巴拉圭诉美国案”①见Vienna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Paraguay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Order of 9 April 1998,I. C. J. Reports 1998,p.266.、2001年的“拉格兰德案”(德国诉美国)、2004年的“阿韦纳案”(墨西哥诉美国)②见Avena and Other Mexican Nationals(Mexico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Judgment,I. C. J. Reports 2004, p.12.、2009 年墨西哥诉美国执行判决案③见Request for Interpretation of the Judgment of 31 March 2004 in the Case concerning Avena and Other Mexican Nationals(Mexico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Judgment,I.C.J. Reports 2009,p.3.、2019 年的“贾达夫案”(印度诉巴基斯坦)。此外,1998 年的“迪亚洛案”④见Ahmadou Sadio Diallo(Republic of Guinea v.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Preliminary Objections,Judgment,I.C.J.Reports 2007,p.582.(几内亚诉刚果)中也涉及对《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解读。
在“拉格兰德案”中,国际法院指出《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第一款(b)项为个人创设了权利,因此,接受国负有双重义务,即“迅即告知”义务和“迅即通知”义务,以便利领事官员开展领事协助。也就是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规定的领事通知义务,为便利领事官员开展领事保护构建了一个相互关联的机制。在“阿韦纳案”中,多名墨西哥人在美国多个州被判处死刑。墨西哥认为美国有关当局在审理这些涉及墨西哥国民的案件时,未告知墨西哥国民享有通知墨西哥驻美国领事的权利,美国的做法构成对《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义务的违反。美国则认为《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的内容属于国家权利,是为了便利领事官员履行职务而规定的,尽管个人可以从国家行为中获益,所谓的个人权利也是依附于国家权利而存在的,不能构成一项单独的个人权利,更不属于基本人权。国际法院在“阿韦纳案”的判决中肯定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是为“个人赋权”,这种权利是可以在美国国内法律体系中主张的权利。国际法院还进一步阐述了领事通知中个人权利与派遣国权利的相互关系,指出接受国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也构成对国家权利的侵犯。
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规定,国际法院的判决对当事国具有约束力。上述所涉案件当事国(美国、德国、墨西哥等)承诺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履行国际法院判决。国际法院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审理,不仅澄清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的含义,同时也发展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的内容。国际法院对《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的解释和适用内容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接受国负有“迅即告知”外国国民享有领事通知的义务被逐步纳入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关于《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的实践还在发展中,例如,近年来有关被逮捕或者拘禁的外国人提起的领事通知权的诉讼在美国呈现爆炸式增长,在最近的10年中,已经差不多有400多起涉及《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案件在联邦法院提起⑤BUYS C G,POLLOCK S D,PELLICER I N.Do unto others:the importance of better compliance with consular notification rights[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1(3):461-502.。美国于2011年曾经推出《领事通知执行法案》草案,以“实现从中央立法到地方执法的一体执行模式”⑥QUIGLEY J B.Vienna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in retrospect and into the future(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J].2013,38:1-26.,但是该草案并未获得通过。围绕《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的解释和适用并不是个案问题,个人权利仍未得到充分保护,公约缔约国相关国内立法和措施不够完善是其主要原因之一。虽然公约缔约国实践与国际法院的司法解决争议实践之间存在差别,这种隔阂的弥补和填充仍需要后续的条约实践予以完善(包括被纳入多个人权条约的实践),但是在多个核心人权条约中都规定了领事通知的内容,人权组织也在加强该领域的研究,持续推动领事会见内容人权化,以确保个人获得领事通知和获得领事协助的权利。
(二)最低标准的含义
领事保护中最低标准的确立与双边领事实践的多样性紧密相关。由于领事法的模糊性,双边领事条约的广泛存在,条约内容具有多样化特点,这也造成各国在讨论缔结《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时,担心公约内容被碎片化。一方面,外交领事法发展的基础是国家的外交领事实践,《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都是源于对习惯国际法的编纂,两个公约中也都写明“凡未经本公约明文规定之问题应继续适用国际习惯法之规例”,外交领事实践受习惯国际法的约束。在双边领事实践中,为了凸显对本国利益的维护,尤其是保护本国国民利益的具体需要,国家之间还不断通过缔结双边领事条约方式来细化领事保护与协助的具体规则,正如我国作为《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缔约国,还与50 多个国家之间适用双边领事条约的规定。尽管有学者担心双边领事条约内容的广泛性可能会妨碍外交领事实践中新的习惯做法的形成,事实上,这种对于模糊性与碎片化的担心最终被国际法院在国际争议解决的实践予以澄清。在“贾达夫案”中,国际法院阐明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在领事法中具有基石地位,任何双边领事条约的内容和实践都不能动摇公约的地位,也不能克减公约规定的权利。
在“贾达夫案”中,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争议焦点之一是领事通知中能否适用国家安全例外。也就是说,印度和巴基斯坦于2008 年签订的《领事准入协定》能否排除《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的适用,双边领事条约作为特别法,或者作为后来订立的法律,能否背离《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双边领事条约中的特别约定能否优先于《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一般条款适用。在该案中,2017 年印度向国际法院起诉巴基斯坦,称巴基斯坦以印度国民贾达夫(Kulbhushan Sudhir Jadhav)在巴基斯坦境内开展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了贾达夫并判处其死刑。在此期间,巴基斯坦没有将逮捕贾达夫的事件“迅即通知”印度领事,这构成对《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违反;巴基斯坦未尽到“迅即告知”义务,未能告知贾达夫享有《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规定的通知印度领事的权利,导致印度领事官员无法开展领事探视;巴基斯坦还拒绝印度领事官员会见贾达夫等。巴基斯坦以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后法优于先法为由,认为在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应适用两国的《领事准入协定》,而非《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巴基斯坦与印度的《领事准入协定》规定有领事会见条款,其中明确了当缔约一方的国民被逮捕、拘押或监禁时,另一方主管当局应“迅即通知”其国籍国代表;一方应许可缔约另一方代表在三个月内探视被逮捕、拘押或监禁的本国国民;双方约定,一旦确认外国国民身份,在刑满后一个月内释放并遣返该外国国民;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双方将个案处理①见Jadhav case(India v. Pakistan),ICJ,17 July 2019 Judgment,para 91.。据此,巴基斯坦主张本案属于个案处理情形,两国的《领事准入协定》是对《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相关条款的补充和引申。印度认为,本案不能适用两国的《领事准入协定》,因为双边领事条约不能修改《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中已经确定的权利和义务,《领事准入协定》的缔约双方无意减损《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的适用效果。印度还提出巴基斯坦的解释与《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七十三条的规定相悖,从条约文本的文义解释来看,《领事准入协定》规定的个案处理是指释放和驱逐出境的个案处理安排,而不是国家安全例外的适用。
围绕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讼争焦点,国际法院首先分析了嗣后订立的《领事准入协定》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关系。国际法院考察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缔约实践,指出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于1977 年、1969 年加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两国在加入该公约时都未对公约条款提出保留,故应适用《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同时还应受《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七十三条的约束。《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七十三条明确了公约不是排他的,签署和批准公约并“不影响当事国间现行有效之其他国际协定”,因此各国有权继续履行之前缔结并生效的国际条约;同时公约“并不禁止各国间另订国际协定以确认、或补充、或推广、或引申本公约之各项规定”。也就是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是开放、包容的,允许多边条约和双边条约之间并行,因此印度和巴基斯坦于2008年缔结的《领事准入协定》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是并行适用关系。国际法院继续讨论了嗣后订立的《领事准入协定》能否背离《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基于《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无论已有的还是新订的双边领事条约,只能“确认、或补充、或推广、或引申”公约内容,提高公约的保护标准,而不能减损公约的效力。从《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的约文来看,该条款并未排除任何适用对象(包括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因此,国际法院认为外国国民的行为性质和内容不影响其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享有的通知领事权利,也就是说,在领事保护中不存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特别约定。
“贾达夫案”的价值在于克服领事法的模糊性,确定《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构成领事保护的最低标准。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公约,由于其成文法的特性以及外交领事实践的多样性,国际法中条约的建设性模糊是条约的特性决定的①韩逸畴.国际法中的“建设性模糊”研究[J].法商研究,2015(6):171-179.,因此公约条款自带开放性和模糊性的特点。无论是由于外交领事法自带模糊性,还是公约内容是为了达成一致而故意在某些事项上的定性模糊,抑或是外交领事工作特性决定的程序模糊,国际法院通过解释公约内容,鼓励缔约国之间开展更高水平的领事保护实践。但在国家的领事立法和领事保护实践中,无论是制定新的双边领事条约,还是解释事先或者嗣后的双边领事条约,只要涉及个人权利保护事项,都不得低于《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确定的标准。针对《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规定中模糊的内容,双边领事条约在履行最低标准的基础上,强化了领事通知具有程序规则性质,为领事保护提供可以运用的程序工作,这使领事保护被赋予新的内容,领事法也逐步“现代化”。
三、双边领事条约深化领事保护的实现
在不减损《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前提下,双边领事条约通过特别约定内容,进一步深化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发展了双边领事保护实践的程序规则,强化了领事通知义务的惯行化,使推定领事会见逐渐成为一项习惯性国际规则。
(一)对实体规则的深化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是对习惯国际法的编纂,反映了双边领事关系实践,但是历史上双边领事条约的差异较大,《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并不能涵盖所有双边领事条约,实践的差异也使得习惯国际法在建立和维护领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②Malcolm D Evans.International law[M]. 4th e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388.。与《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实践不同,双边领事实践并未完全写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实践中形成了包括《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双边领事条约、习惯国际法等共同构成的领事法。为了更有效地便利领事履行其职责,很多国家通过双边领事条约的方式,逐步细化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框架下的领事保护内容。
第一,双边领事条约从内容上补充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譬如,美国和阿尔及利亚于1989 年签订了《美利坚合众国与阿尔及利亚民主共和国领事公约》,双方认为双边领事条约应当就一些具体事项明确具体义务,如有关逮捕和拘留一国国民应通知领事官员的义务以保护本国国民的权利和利益。该条约被认为补充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将促进两国领事以多种方式协助其国民的能力,并推动两国之间的人员和贸易往来。
第二,双边领事条约增加了领事通知事项,丰富了保障个人权利实现的手段。《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的规定非常概要,为了更好地开展领事保护,一些国家之间的双边领事条约还细化了通知领事的细节措施,包括在领事通知中要求接受国明确告知采取逮捕、拘禁等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理由等。《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仅要求通知相关事项,并未规定当事国应告知采取强制措施的理由。为了防止一国滥用强制措施,国家之间通过双边领事条约规定告知采取措施的理由,就可以把《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原则性的规定深化为可操作的步骤,为领事会见和领事协助提供便利性和指向性。在具体的规定中,还存在应请求告知和强制告知理由的不同做法。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领事条约》第三十五条规定:“应领事官员要求,应告知该国民被逮捕或受到何种形式拘禁的理由。”其他如保加利亚、捷克、波兰、斯洛伐克等国家和美国的双边领事协定中也有类似条款规定。有些国家的双边领事协定则采取“强制通知原因”做法,如美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双边领事协定明确规定接受国应将派遣国国民被逮捕拘禁原因告知派遣国领事,即便派遣国领事官员未提出此类要求。
第三,细化领事职责,为领事保护和领事协助提供实现基础。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五条规定的领事职能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领事条约》在一般性地列举领事职务的基础上,又在第二十四条到第三十九条具体规定了领事官员的职责。这种立法体例是一种普遍的双边领事条约实践,许多国家的双边领事条约中都有类似规定,如细化领事与派遣国国民通讯及联系的做法、规定领事协助具体内容等,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迅即通知”义务具体化为“接受国主管当局应于三日内通知领馆”①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领事协定》第十一条。,这种对规则内容的细致描述,有效避免了缔约双方因为规定模糊而引发的争议。例如,我国和意大利的双边领事条约中就对“逮捕、拘留或驱逐通知和探视”作出了多项引申和发展,明确了“七天内通知领馆,并说明原因”,“领事官员……用派遣国或接受国语言同其交谈或通讯,并为其提供法律协助。接受国主管当局对领事官员的探视请求应在第一款的通知后两日内作出安排,以后每月应提供不少于两次的探视机会。领事官员可旁听任何法律诉讼的公开部分”,还引申出“强迫离境或驱逐时”的通知,包括“事先通知”和“因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的重大理由需要驱逐和离境时,通知可在采取措施的同时进行”。
(二)推动程序规则惯行化
国际法院在解释《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的适用时,将之与程序规则紧密相关。尽管国际法院的相关裁决并未得到有效执行,这些裁决中提出了与《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适用相关的程序正义问题。任何对《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规定的个人权利的损害都可能引发后续的程序和实体救济问题。这既是“拉格兰德案”“阿韦纳案”“贾达夫案”的争议焦点,也是在这些案例中不断被清晰化的内容。有关程序正义的讨论对《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国内适用产生了重要影响,围绕该公约国内适用的程序规则还在构建中。
第一,从应请求通知到强制通知、自动通知义务,领事通知的程序价值日益彰显。《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规定应当事人请求而通知其本国领事,如果当事人不知道其享有通知领事的权利,则无法提出请求,接受国主管当局可能就不通知其本国领事,领事会见就可能被架空,领事保护与协助就无法开展。为了保障本国国民的权利实现,许多国家的双边领事条约中纳入了“强制通知条款”,即当派遣国国民被逮捕、拘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时,无需当事人请求,接受国负有“迅即通知”义务。从应当事人请求通知到强制通知派遣国领事,目的在于强化缔约双方履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义务,保障个人权利实现,这种对公约规则细化的做法符合领事法发展趋势。就强制通知义务价值而言,这种义务最大程度地保障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中个人权利的实现,防止因当事人不知道权利存在而导致通知领事并获得领事协助权利的缺失。同时,强制通知义务并不减损当事人个人的权利,如果当事人不同意,其可以拒绝接受领事协助,拒绝领事会见。此外,一些国家还在双边领事条约中明确缔约各方互负强制通知义务,如美国和50 多个国家之间的双边领事条约都规定了自动通知义务,我国与40多个国家缔结的双边领事条约也纳入了强制通知条款,例如我国与美国之间就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领事条约》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强制通知义务,而不再适用《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规定的应当事人请求通知。
强制通知作为一项条约义务,如果接受国未尽到通知义务,可能造成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因为领事通知权是保障派遣国领事与被限制自由的本国国民会见及通讯权利。接受国对于该义务的违反,将构成对《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违反。当《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被赋予新的含义后,围绕该条款的实践将出现新发展。为了尽到强制通知义务,一些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陆续对国内立法进行了修改,将告知被逮捕拘禁的外国人享有通知本国领事的内容写入国内立法。虽然强制通知义务并未获得美国联邦立法通过,但是包括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几个州陆续修改了立法,明确了强制通知的内容。此外,针对违反《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规定的领事通知案例,德国则明确了将案件发回重审的救济途径①见Abstract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s Order of 19 September 2006,2 BvR 2115/01,2 BvR 2132/01, 2 BvR 348/03[CODICES].。
我国始终在强化履行公约义务,从目前的实践来看,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全面的领事通知和领事探视制度,既有刑事诉讼法、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也有相关规定和相关部门的执法程序规则,还制定了清晰的时间表,明确了具体的执法和司法程序,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021 年3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专门对涉外刑事案件的审理和刑事司法协助涉及的领事通知和领事探视作出了明确规定,同时我国多个部门也明确了保障领事通知的程序步骤。2022 年,我国法院审理美国籍被告人沙迪德·阿布杜梅亭故意杀人案中,在一审②孙航.美国籍被告人沙迪德·阿布杜梅亭故意杀人案一审宣判[N].人民法院报,2022-04-22(01).和二审③孙航.浙江高院二审公开庭审理被告人沙迪德·阿布杜梅亭故意杀人上诉案[N].人民法院报,2022-07-30(04).审理期间,两审法院都依法充分保障了被告人沙迪德·阿布杜梅亭的辩护、获得翻译、领事探视等各项诉讼权利,开庭、宣判前均依法通知了美国驻华使领馆。法院为被告人沙迪德·阿布杜梅亭指派了两名辩护律师和聘请了翻译人员,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官员旁听了庭审。
第二,细化程序规则内容,通知义务成为可执行的程序规则。国际法院在“拉格兰德案”“贾达夫案”中都确认接受国的“迅即通知”义务和派遣国领事会见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如果接受国未告知被逮捕、被拘禁的外国国民享有该项权利,则该外国国民不可能知道其有权要求将其被逮捕、被拘禁的情况通知其本国驻接受国的领事官员。针对《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的模糊性术语,一些国家在双边领事条约中细化可操作的程序规则,其中包括明确通知时间,如规定“七天”通知、“三日”通知、“四天”通知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西兰领事协定》第十一条规定了“拘留、逮捕通知和探视权”,明确了“三日内通知”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领事条约》第十二条专门规定了“关于拘留、逮捕的通知和探视”的时间要求,明确了缔约应在“四天内通知领馆”,而且应在“通知后三日内”安排领事会见。其他的一些双边领事条约也都强化了时间要求④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领事条约》等其他双边领事条约也有类似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意大利共和国领事条约》还明确通知领事的具体内容、步骤和安排。此外,双边领事实践的程序要求对我国国内立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通过在相关立法规定领事通知要求,以保障当事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权利;通过制定部门规章等方式,明确在具体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涉及对外国籍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依法保障领事通知和领事探视权利。我国行政机关还制定了内部程序规则,明确了具体的工作程序,形成了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内部规则等共同构成的保障机制。
领事法的特点在于对等性,缔约双方都遵照统一内容和标准执行,有利于双方领事履行领事职务。同时,双边的实践不断被复制推广,领事的职能不断被具体化、程序化、清晰化和透明化,尽管各种具体的细节有所区别,但其中的一些做法已经逐步被固定下来并成为习惯做法,甚至逐渐发展成为习惯国际法,如实践中确立的接受国告知义务、通知时限限制、强制通知义务已经成为普遍的国际实践。《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强调对等适用,一国为在海外的本国国民提供的领事协助和领事保护措施,也对等适用于该国对另一国承担的义务。对等原则的适用是平衡双方利益的结果,当然也为双方领事履行职责划定了行为边界,领事保护与协助得以在理性和平衡中稳步推进。
(三)供给的有限性
双边领事条约提供的是个性化的实践,双边领事条约规定各不相同,这也是国际社会始终担心领事法被碎片化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双边领事条约确实为领事保护与协助确立了程序规则,但是双边领事条约的作用是有限性。
我国《对外关系法》第三十一条中明确了我国采取“适当措施”适用条约和协定,其中关于“适当措施”的理解应采取开放态度,不仅包括条约在国内适用,也包括我国在域外运用条约。当我国驻外外交机构在海外保护我国公民时,尤其涉及我国公民被采取强制措施时,我国驻外外交机构需要综合运用多边条约和双边领事条约,此时不同的双边领事条约提供了不同的方案,不同的方案可能都是符合“适当措施”要求。用“适当”来解释我国需要同时适用多边条约和双边条约的情形,无疑体现了科学立法的要求,也为我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指明了法治化方向。
从目前的阶段来看,双边领事条约实践还在不断发展中,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情形:一方面,按照《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将该公约中未定事宜纳入双边领事条约中,可能面临新条款与公约的衔接甚至冲突难题;另一方面,通过双边领事条约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进一步细化成为发展趋势,包括双边领事条约中约定强制通知义务、强制告知理由、约定通知的时限等,这些内容如果能被反复地实践,就能推动形成新的习惯性国际规则,为《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发展提供实践素材。至于如何履行强制通知,如何告知被逮捕、被拘禁的外国人,何时通知,其实还涉及接受国国内法立法和执法的问题以及派遣国领事职责内容,这也是领事通知被视为领事保护的关键环节的原因之一。
此外,双边领事条约要与其他国际法规则协同发展,这体现了领事法深受一般国际法发展的影响。对于海外领事保护权利救济,还要结合一般国际法进行分析。个人权利能否得到救济最终需要依据国内法的救济规则解决,这也是国际法院在“拉格兰德案”“阿韦纳案”“贾达夫案”中所明确的。在实践中,国际法院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才会施加国家责任。如果一国对《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所规定的领事通知的性质认识不一致,在其国内立法中也未规定侵害领事通知权案件的救济规则,在该国的外国人事实上是无法在该国主张个人权利救济的。即便外国人的国籍国为其开展领事保护,但是并不必然得到有效的救济。在这种情形下,即便有双边领事条约,也很难通过双边领事条约率先解决权利救济问题。也就是说,双边领事条约的理想范本的达成是要落实到《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发展实践,需要基于国家已有或者可操作的实践。
外交领事关系是自成一体的规则体系,并深受政治关系的影响,外交领事法充满着模糊性以及与之相伴的灵活性,因此,与其他类型的条约协定相比,勾勒出一个细致入微的双边领事条约范本是很困难的。就我国的双边领事实践而言,有学者提出,相较于《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我国双边领事条约在主体内容上没有明显的突破;缺乏对重要名词的明确界定,缺乏对“领事保护”的概括式或列举式规定;“有必要在对43个中外双边领事条约(协定)中与领事保护相关的条款进行分类比较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当前领事保护实践之需,扬长避短地拟定中外双边领事条约(协定)范本,并以此作为旧约修订的参考以及新约签订的谈判文本,或以换文的形式达成关于具体问题的约定”①丁丽柏.《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革新与中国的应对——以海外国民领事保护为视角[J].政法论坛,2019(3):125-133.。对于我国双边领事条约的实践而言,应将之放到《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框架下进行讨论,结合公约缔约目的以及公约的具体规定与当前实践,从整体协调论出发,对照《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七十三条的规定,重新审视我国与外国缔结的双边领事条约的内容,在推动我国《领事条例》第九条的实践进程中逐步评估已有双边领事条约的价值,以便利领事保护与协助的开展。至于目前是否需要制定新的双边领事条约范本,考虑到历史上双边领事条约并无统一的模板和范本,双边领事条约的一些内容也被其他公约吸收,结合《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相关条约的最新实践以及我国领事保护与协助的实践予以综合考量。
四、结 语
在领事保护与协助中,双边领事条约的适用和发展呈现出独特性,双边领事实践与普遍适用的国际公约共同作用,不断提升领事保护的水平,完善领事保护与协助的机制。一方面,双边领事条约实践推动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形成,领事法的法典化也统一了双边领事条约的内容,规范了双边领事条约的适用标准,从而构建出全球性的领事法规则和适用准则,双边领事条约的立法和实践被提升到新的发展高度;另一方面,双边领事条约具有灵活性的特点,国家通过升级双边领事条约的内容和履行,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发展了多边规则,为《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三十六条的实现贡献了可操作的标准。随着强制通知义务、强制告知理由、约定通知时限等内容被写入双边领事条约、被引入双边领事实践和被纳入国内法实践,领事通知和领事会见的新做法开始呈现出惯行化趋势,这将推动新的习惯性国际规则形成。就我国的实践而言,我国《对外关系法》完善了条约实施和适用制度,为我国实施和适用已加入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等外交类公约以及相关双边条约提供了基本法律遵循②黄惠康.中国对外关系立法的里程碑——论中国首部《对外关系法》应运而生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系统集成和守正创新[J].武大国际法评论,2023(4):1-27.。按照我国《对外关系法》的要求,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运用好“适当措施”,最大限度地保护我国公民的正当权益。我国驻外外交机构在依据《领事条例》第九条开展领事保护与协助时,既要研究和运用《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等多边公约的最新实践和最新发展成果,也要结合具体案例,综合解释和适用案例所涉的双边领事条约的具体规定。考虑到我国缔结的双边领事条约内容具有多样性,我国开展的领事保护与协助的措施也将呈现稳定性和灵活性兼而有之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