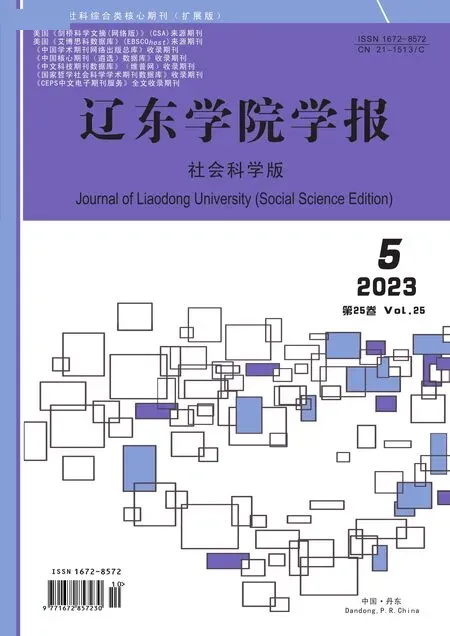诗史互文:史传与史诗功能的侧重与互补
孟曙光 ,艾春明
(1.丹东市教师进修学校 培训部,辽宁 丹东 118001,2.渤海大学 文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一、史诗是游牧民族的专利
叶舒宪在《英雄与太阳》中提到,大量的英雄史诗产生的背景都与游牧民族的文化有关,但他把史诗产生的动力归结为游牧文明与城市文明、农业文明之间的冲击震荡,进而认为“在单一的生态环境中和平发展起来的孤立的、封闭的文化群落,是极不利于产生英雄史诗的。即使是流动性的游牧生活方式本身也不足以为英雄史诗的诞生提供必然条件”[1]24。此一观点的有力证据是“因为欧亚大陆的绿色草原文化带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而那时却没有产生出一部史诗”[1]24。叶舒宪此处忽视了一个概念的含义差别,即“产生”和“流传”的差别。准确地说,是上古(公元前4世纪至前2世纪)欧亚内陆草原的游牧民族没能直接流传下来自己的史诗,却不能断定说他们从没有产生过英雄史诗。究其原因,首先是草原游牧民族常常是来去无踪影,特别在古代,其文化历史都是借周边定居民族的史书才得以保存一鳞半爪,考古学文化因为干旱沙漠草原的自然条件,也难以留存和被发现,更不要说口传状态的英雄史诗,即使借助其他相邻文化流传的机会都很少,这是因为在公元2世纪之前,这广袤的草原周围几乎还没有掌握便捷的文字书写技术的民族。其次是个别早期史诗类叙事作品如《吉尔伽美什》未必没有上古草原民族流传下来的故事或生活经历的原型。就史诗与游牧文化关系来看,叶著更多注意到的是中古以后属于印欧语系各民族的史诗,如日耳曼民族的《希尔德布兰特之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贝奥武甫》、哥特人的《旧埃达》及再晚些的英国的《熙德之哥》、德国的《尼贝龙根之歌》、法国的《罗兰之歌》和俄国的《伊戈尔远征记》,这些史诗都以民族大迁徙或征伐为题材背景,征战对象是亚洲游牧民族。
其实,最早出现的几部原生史诗也都与游牧民族、游牧文化有血肉联系,这里不妨略陈史实: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来自叙利亚草原的阿摩里特人或称闪米特人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约在公元前2000年初,他们建立了以巴比伦城为中心的古巴比伦王国,古巴比伦文学最高成就的史诗《吉尔佳美什》最初约完成于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大抵与闪米特人同时,欧亚内大陆西南部的印欧人,也先后朝三个方向迁徙:东至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的西北边境;西至多瑙河流域、巴尔干半岛、希腊半岛、亚平宁半岛,直至大西洋边;南至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在其迁徙过程中,印欧人不断与当地人融合,先后建立了印度吠陀文明、安息帝国、波斯帝国、迈锡尼文明、古希腊文明、罗马帝国等。酝酿创造了荷马史诗的迈锡尼人或多里安人,都是外来的入侵者。一拨一拨的越来越富于冒险和好战精神的古希腊人本身就有游牧民族的血统。之所以有保留地使用这样的说法,是因为史学家认为克里特人和迈锡尼(阿卡亚)人、希腊人不是同一种族,同时又有明显迹象表明克里特人的主要经济形态是海洋贸易,但是荷马时代和整个前希腊文明时代,却在周围强大而持久的游牧人群进攻背景下形成了史诗文化。很难想象单凭原始的海洋渔猎就能造就那样强悍的气质。太平洋岛国的漂流民族,至今还没有走出蒙昧多远。同样,公元前1500年左右,来自中亚草原的雅利安人的部落联盟侵入了印度,并且永久定居下来,近千年后的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印度的两大史诗核心故事完成。也就是说,上古时代的几大史诗,都是定居下来的游牧民族后裔创造的(1)以上描述主要依据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和韦尔斯《世界史纲》、江林昌《中国上古文明考论》等书。下文同。。
几大史诗虽然产生在相距遥远的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环境,却具有并保持着惊人相似的血脉联系。这种联系的表征十分鲜明:强健体魄与智慧合一的英雄主人公、以杀戮乃至嗜血为壮美的英雄主义、对女人的强烈占有欲、对物质财富的真率追逐等,都是草原游牧民族才有的精神品格。特别是以民族迁徙或征伐为表象的游历、漂泊,为寻找对手的长途跋涉、冒险的经历沉淀为深层结构,一再出现于欧洲文学的叙事传统里。一会儿是骑士,一会儿是流浪汉,一会儿是游吟诗人,最初的游荡是谋生手段、追求事功,到后来甚至漫无目的,游荡漂泊本身成了生命的固有含义。《吉尔伽美什》里海岸女巫西杜利劝英雄放弃辛苦的无尽旅行,过享乐生活,英雄不为所动,执意寻找永生之谜。《奥德修纪》中奥德修斯海上冒险旅行,女神卡吕普索劝他留下共享太平长生,英雄却执意离去。史诗作品中英雄的品格,似乎与留居一地的平安生活存在着天然的冲突,只有在不断的游荡漂泊进程中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不能不说这是马背民族古老生活习惯内化的结果。史诗是游牧民族的专利。
二、草原游牧文化与史诗生成
认为史诗是游牧民族的专利,当然不是指这些史诗的故事内容都直接描写游牧生活和经历,而是说草原游牧民族通过殖民扩散,为后起的城市文明、农业文明圈植入了促使史诗发育的基因,为他们留下了骠悍的精神血脉。
(一)草原游牧文化与马背民族性格特征的形成
以欧亚内陆干旱的草原沙地为舞台的诸民族,因为植被简单、土地平旷、人与被驯服的马的合作,其主客条件共同促成了一种独特而富有活力的生存方式--能快速行动,以征战掠夺、经商冒险为日常形态。即使同样从事畜牧业,这些草原游牧民族与植被丰富的湿热地域的放牧业和中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存在明显的不同,和美洲古代土著及非洲沙漠没有驯马的原始游猎民族如布须曼人也同样有明显的区别。他们横跨几千里大范围的游猎、冲撞、兼并,必然养成对不同部族文化的兼容吸纳和整合的习惯,并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这种动力和能量。考古界差不多公认,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之间,东欧南部居民已经掌握了牛、小牲畜甚至马匹的驯养;至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之交,欧洲草原某些地区(特别是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已经出现畜牧业超过农业的迹象,南俄草原马匹的使用也不会晚于公元前4世纪。虽然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公元前4世纪的南俄草原的人群已经掌握骑马术,但即使是马车的速度和连续行进能力也大大超出了人的两条腿。由此,草原游牧文化及马背民族的性格特征几乎与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同时形成。游牧文化对古代几大文化圈的影响力不可小视。荷马史诗虽然描写的是已经建立了城邦文明的民族征战的故事,但其中精神趣味特别是对叙事的爱好、较强叙事能力很可能是游牧祖先遗传给他们的。只不过后来他们已蜕变为“海上骑马民族”,如果说“创造爱琴海文明的那些英雄们,个个都是集商人、强盗和殖民者于一身的开拓者”[2],则要给他们这顶桂冠加上“第二代”的称号,来自亚欧草原的游牧人群才是第一代殖民者。
(二)草原游牧文化促成史诗的生成发育
综合来看,草原游牧文化为史诗的生成发育提供了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经常游移的生活要求尽最大可能减少必须携带的财产或生产生活资料,因而部族历史、神话、英雄故事只能更多依靠口头流传,不能书之竹帛,客观上推动了口头文学的发展。原生的几大史诗都是口头说唱文学的成果。
第二,游牧的人群每人都是生于甲地,长于乙地,终老于丙地,生活行迹很难考其具体的地点,即使有某一地点的记忆,这个地点的方位、四至也会十分宽泛,因而游牧民族个人的生命经历,会自然脱掉具体时空背景,从而轻易地获得人生故事的传奇性和虚构化。真实的生活历史当其失去具体的时空联系时,就转而成为西方文学观念以虚构为正统的纯粹文学作品。
第三,游牧民族在更大地域范围展开的部族冲突、兼并,可以将各个部族分散发展的神话、故事及英雄传说收集起来。同时由于游牧民族不像农耕民族那样氏族血缘关系在新国家或他种高级社会组织结构中得以保留,其新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建立就会少些阻力,信仰及神话、故事传说会更容易整合丰富起来,个人叙事也容易上升为宏大叙事,发育出更高级形态。
第四,游移的生活习惯,还养成了游牧民族以移动的视角观察景物,以移动的线路为序记忆事件的思维定式和叙事惯用手段,这是叙事文学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
第五,广阔的游历、频繁的征战冒险,为游牧民族神话、史诗提供了足够多的生活素材和英雄主义气质,不仅有事可叙,更有叙事的需求。
通过对比,我们看到中国古代汉族与欧洲及其他史诗发达民族的文学传统(指以语言为载体的精神文化共同体)是在原始神话之后走上不同发展路径的。以游牧文化精神为基础的印欧语诸民族,原始神话与口传的部族历史相结合,发展成发达的叙事文学--史诗;以农耕文化精神为基础的中国,神话与书写的历史脱节并受到书写历史的压制而不得整合发展,想象、创造的欲望在以抒情为目的的隐语、象征(中国传统的概念为“比兴”)文学传统里得到释放、满足。
三、史诗的纪史功能与史传的文学功能
(一)史传叙事是中国农业文明下的代表性叙事形式
《诗经》所奠定的中国文学基础是抒情性的,虽然《诗经》也有叙事成分,但它的叙事是为抒情而设。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3]《左传》更是先秦散文“叙事之最”,这是我国学界的普遍认识,因此以《左传》等史传为样本与西方史诗对照研究,取样标准才能对称,剖析的意义也更典型。
《左传》《国语》虽然还不是纪传体,但以人为核心的叙史记事形式,与《史记》没有本质区别,可以“史传”统称之。中国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所记事即人物行动轨迹、事件,与西方史诗的记事概念是一致的。记言史书史料也不是纯粹记言,如《论语》那种语录体之记言,也多伴有说话的人物、情境等信息。记言史官早就明白这个道理:脱离具体情境,某些语言的准确含义就会不知所云,而加上了说话人物、情境就构成了简单叙事,因此中国的历史著作,无论记言记事,都离不开叙事,只是侧重点不同。史传叙事于是成为中国农业文明下的代表性叙事形式。
(二)史传的诗之用和史诗的史之用
这里的“用”指潜在的文化承载功能,也指历史上实际发生过的对史或诗文本的读解结果。中国史传本是历史著作,主要发挥历史的资治借鉴作用,各种史的体裁尤以史传为最,又是历代读书人当文学来欣赏玩味的对象。西方的历史著作提供的只是事件概要,揭示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足矣,中国的史传不以概要和揭示联系为满足,还兼以和文学描写相比也不逊色的细节展示,可满足读者好奇探微的审美需求。对比之下,西方的史诗主要满足一般民众娱乐需求,算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史学家要了解古希腊社会,找不到比荷马史诗提供的社会生活图景更加详细的史籍,西方史学也时常玩以诗证史的把戏。汤普森说,“在希腊时代以前,根本就没有既能表现事件又能说明文体的历史”[4]7,希腊时代的历史则是散文说书家(logographoi)们的印象追忆。大名鼎鼎的塔西陀《编年史》,以中国史学的眼光看,根本就不叫编年史,因为我们记述历史事件要求精确的时空条件,时间维度不仅要有准确年份,甚至要有月日干支。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认为:“了解希腊早期的历史和文化的线索……其中较重要的是希腊人自己留下的宝贵遗产--四大史诗,即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赫希奥德的《工作与时日》和《神谱》。”[5]对后两部书多部文学史都不以史诗看待,而认为是史料文献,可见西方严肃的史学家也不太在意文学与历史、史诗与史传的文体界限。汤普森说:“叙事史是最古老的一种历史。虽然历史科学已经提出更高的问题,但这种叙事史永远不会被废弃,永远不会死亡。”[4]30黑格尔说:“我们看到荷马用最优美的诗歌和丰富多彩的人物性格把这种英雄时代的世界情况描绘出来了。”[6]118黑格尔还说,如果把各民族史诗部结集在一起,那就成了一部世界史[6]122。从语源看,西方的历史(History)是故事(Story),即别人的(His)或(Her)的故事而已。克罗齐曾言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西方人没有精确的历史,只好拿史诗当历史来看。现代某些中国人因为没有史诗,把自己的历史不当回事,好像觉得无地自容。
(三)诗史何以互文:史传与史诗功能的侧重与互补
事实上,中西方都存在诗、史不分,史、诗互通互用的倾向,有人称文学与历史有互文的性质[7]。这种倾向不是巧合而是有其原因。通常认为文学和历史最大的区别是纪实与虚构的差别,然而这虚与实又是相对的,只是在多大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衡量的问题。不必发生但是可能发生、应该发生的文学真实是对历史事件的抽象,是在较大时间尺度上观察得到的历史,或者如有所称的是“历史的虚化”[8]。诸多叙事文学的创作实践证明,文学之所以比生活(第一历史)更集中、更典型,不过是将生活中的事件、人、地、场景等做了时空的挪移。从生活到文学与从“第一历史”到“第二历史”的原理没有什么大区别。如果以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叙事精度看西方早期历史著作,那已经就是虚化了的。抛开文学或历史在具体的赖以产生、流传、消费的文化共同体(国家、民族)中会回应、应激出怎样的读解效果不谈,它们在上层建筑序列里却扮演着相似乃至相同的角色,完成相同的文化功能,那就是它们都是在为一定的社会族群提供相适应的价值趋向。因为哲学、道德说教即使已经产生了,它也无法面向族群大众,而史诗、史传的受众相仿佛,且最大限度涵盖数量。无论是史诗叙事还是史传叙事,形式略有不同,骨子里都是族群最好、最易普及流行的关于人生经验的教材,对维系一定族群、社会起到其他任何上层建筑形式难以企及的作用。反过来说,为社会输入基础软件--叙事的任务,在古希腊等民族交给了史诗,在中国交给了历史。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英雄主义、积极进取、勇于探索、冒险等精神,通过荷马史诗世代传承,正如马克思所说,史诗与希腊神话一起不仅是欧洲文学的源头,还成为欧洲文学的土壤;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忠肝义胆、诚实正直、修齐治平等,主要也是通过史传影响一代一代的读书人,史传中的明君贤相、能臣侠士、忠奸斗争,又不断被改编创作,以更通俗的形式教育民众,更兼以中国汉族人还有正史和稗史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共同完成对全民的教化功能。
四、结语
汉族为什么没有史诗?这是中国文学界睁眼看西方之后引出的至今萦绕于心的疑惑。但是如果把眼光扩展到中国的少数民族,扩展到全世界,就会看到:中国汉族的史诗只是没有产生西方或印欧语民族古代那种经典的样式而已。分散的农耕定居生活更多记录了生命个体的精彩,而游牧征战的集团生活更多留下的是英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