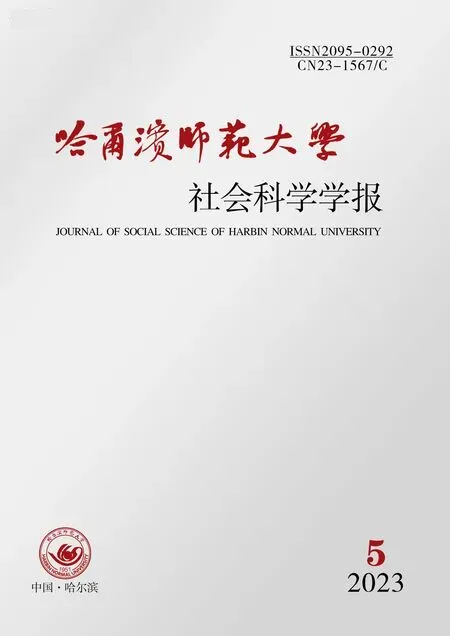《论语》中以“人”为目标域的概念隐喻研究
洪 敏
(安徽外国语学院 英语语言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将隐喻研究带入了一个新时代。该书从认知角度首次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他们将隐喻定义为“跨概念域的映射”。他们认为隐喻的本质是通过某一事物来理解、体验另一事物,隐喻是从源域向目标域的本体映射过程,即概念隐喻可视为以一个具体、熟悉的概念去理解和构建另一个抽象、模糊的概念。根据该理论,隐喻直接参与人类认知过程,是人类思维的重要手段,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这一研究带来了与传统隐喻观不同的研究思路,这种新的认知方法拓宽了人们对隐喻本质的理解。
《论语》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载体,主要以语录和对话文体的形式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的言行,其中富含隐喻,他们在日常对话交流中经常选取和自然相关或偏生活化的事物作为源域来表达儒家的思想观念。Lakoff 与 Johnson 认为日常的对话是“朴实平常的语言”,正是在朴实平常的语言中潜藏着概念隐喻[1](P4)。其中有些隐喻性的表达成为常用语和成语,人们代代相传,深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和思维中。
2000多年来,对于《论语》这部典籍著作的研究层出不穷,以往的学者多限于文本注释、哲学价值、翻译等方面的研究。即使涉及《论语》的语言探讨,研究重点主要限于语言的修辞层面。即使目前的一些研究涉及到了隐喻认知层面的知识,如王银娜[2](P59-63)和许群爱、刘宇红[3](P54-56)从认知视角来探讨《论语》的奥秘,但他们的研究更侧重于文化、哲学方面的解读,其中对隐喻的总结不全面、不深入。对以“人”为目标域的隐喻的具体分析较少,特别是从认知角度的解读比较简单粗浅。这种研究的弊端在于很难揭示隐喻背后的认知机制,反映隐喻的认知过程,无法揭示《论语》隐喻所反映的内部概念结构和创作机制。
二、《论语》中以“人”为目标域的概念隐喻
本文以《论语》中关于“人”的概念隐喻为切入点,将“人”作为目标域进行分类,归纳出人是植物、人是动物和人是无生命物体三类隐喻。《论语》言简意赅,微言大义,古往今来不同学者的解读不尽相同。其中多数富含隐喻文段的目标域并没有明确表明,而且有些例句中包含不只一组隐喻映射,本文主要侧重从“人”为目标域这一角度进行认知解读。有些论语原文较长,笔者只引用了包含隐喻的部分内容。
(一)人是植物
(1)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论语·子罕》)
源域:庄稼 目标域:颜回或一般人
苗(拔苗)→ 树立志向却没有行动
秀(开花)→ 修行却半途而废
实(结果)→ 立志并坚持不懈
孔子运用结构隐喻,将抽象的人的发展历程隐喻成具体的植物生命周期。地里的庄稼从“苗”到“秀”再到“实”,即经历拔苗、开花再到结果整个生命历程。但是,并非所有的庄稼都能经历这个完整的过程。在此期间,有的只长苗而没有开花;有的开了花长了穗却没有结果。如同有的人树立了志向,却没有行动;有的人立了志也进行了修行,但半途而废。只有那些既树立远大志向,积极行动,并能够坚持到底的人才会有所成就。
(2)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论语·子罕》)
源域:松柏 目标域:人
生长的环境 → 成长的环境
经历严寒,四季常青 → 战胜困难,成就自我
松柏能四季常青是因为经受住了严寒等艰苦环境的考验,一个人要想成才就要不怕困难,矢志不移,经得住各种考验。后人遂以“松柏之志”代指坚贞不移的志节。这一章以自然现象喻人,说明要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和考验一个人的品格[4](P443)。
(3)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论语·阳货》)
源域:石头 目标域:孔子自己
源域:匏瓜 目标域:孔子自己
变老时中看而不能吃 → 变老时无法被重用
这一句包含两个隐喻,这里以“匏瓜”为源域进行分类。匏瓜是葫芦,嫩的时候可以炒菜吃,等变老后就不能吃了,一般只能挂着当装饰。孔子认为自己现在年轻力壮,斗志昂扬,可以大有作为。通过隐喻和反问委婉地表达志向,他因自己长期得不到重用而感到怀才不遇、寂寞孤独,如匏瓜中看而不可吃。
(二)人是动物
(1)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
源域:犁牛之子 目标域:仲弓
出身低贱 → 冉伯牛的儿子,出身卑微
不能用于祭祀 → 得不到重用
这里从源域建立到目标域的映射主要基于两点。首先,仲弓的父亲叫冉耕,字伯牛。所以从名字来看,仲弓是名副其实的“犁牛之子”。其次,据记载,冉雍(仲弓)的父亲出身卑微且品行不端,可见仲弓也是出身低贱。一般来说,犁牛之子长得再好,也不能用来祭祀。就像仲弓一样,他虽然有高尚的道德和突出的才干,却由于出身不好得不到重用。但是,孔子对寄予很高的期望,相信他的才能一定会有用武之地。孔子这里鼓励仲弓站在更高的格局上,不要因为一时囿于现实而放弃自己。由此可见,孔子“有教无类”,不以出身贵贱论英雄[5](P158)。
(2)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论语·泰伯》)
源域:鸟 → 目标域:人
将死时鸣哀 → 将死时言善
朱熹解释说:“鸟畏死,故鸣哀;人穷反本,故言善。”[6](P159)也就是说,鸟因为怕死而发出凄厉悲哀的叫声。人因为到了生命的尽头,反省自己的一生,回归生命的本质,所以说出善良的话来。
曾子与孟敬子在政治立场上是对立的。曾子在临死以前还在试图改变孟敬子的态度,所以他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曾子用鸟将死而鸣哀来隐喻人将死而言善的道理,可谓是用心良苦,临死也不忘弘道。他主要强调的是君子要管理好自己的姿态、表情和语言,保持端庄和威仪。这些看似是细枝末节,却是君子修身之本,而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起点。正因如此,曾子在给三点建议之前用了这个隐喻,希望孟敬子能够特别重视他最后的遗言。
(3)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论语〈季氏将伐颛臾〉》)
源域:龟玉 目标域:颛臾
破碎、被毁 → 被占领
源域:虎兕 目标域:季氏
跑出笼子伤人 → 侵犯颛臾
源域:虎兕、龟玉的看守者 目标域:冉有、季路
保护虎兕、龟玉 → 保护颛臾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双重隐喻:一是将季氏比作虎兕(老虎和犀牛),将颛臾比作龟玉(龟甲和玉石)。季氏攻打颛臾,好比虎兕跑出笼子伤人;颛臾如被攻灭,好比龟甲、玉石毁于椟中。二是将冉有、季路比作虎兕、龟玉的看守者,虎兕出柙伤人,龟玉毁于椟中,是看守者的失职。冉有、季路作为季氏家臣若不能劝谏季氏放弃武力,致使颛臾被灭,也是他们的失职。
这里根据第一个隐喻的源域、目标域特点将它归类成“人是动物”。这一隐喻批评了季氏兼并颛臾的企图,并阐发了孔子以礼治国、为政以德的主张。孔子不主张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而希望采用礼、义、仁、乐的方式影响、教化人们,从而构建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国家。
(4)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论语·微子》)
源域:凤鸟 目标域:孔子
祥瑞之鸟 → 圣人,高洁之士
只在政治清明时出现 → 等待圣明的君主任用
凤鸟是传说中的祥瑞之鸟,只在政治清明时才会出现。过去人们认为“凤鸟待圣君乃见”。如果圣君在位,凤鸟才会出现。楚狂这个人是有名的隐士,他用“凤”来比孔子,可见孔子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楚狂对孔子说你老是想把这个时代挽救过来,还是挽救不了的啊!算了吧!算了吧!这个时候想出来从政,挽救这个时代危险极了。
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以天下为己任,虽然知道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施行仁政、推行礼乐很难,但是一直坚持寻找圣明的君主。
(5)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
源域:鸟与兽 目标域:孔子和隐士
分别在天空中飞,陆地上走 → 入世与辟世
鸟海阔天空地飞,兽在陆地上行走,这两类动物没有什么交集,也就是说人各有志,各走各的路,远走的就去远走,高飞的就去高飞[7](P750)。孔子和隐士不同之处在于天下无道,隐士选择“辟世”,而孔子选择迎难而上,周游列国。其中的隐喻鲜明地反映了孔子和隐者面对衰势乱象所表现的不同态度,隐者认为孔子是愚,而这恰恰是体现了他弘道救世的担当精神[4](P415)。
(6)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论语·颜渊》)
源域:虎豹与犬羊 目标域:君子与一般人
两者皮毛不同,物种不同 → 两者外在不一样,不可相提并论
“鞟”指的是去毛的兽皮。假如去掉虎豹和犬羊的毛,那就无法区别这两种动物了。动物的皮毛如同一个人的“文”,即外在表现,如他的谈吐举止,衣着礼仪、文采等。子贡认为“文”和“质”并不是矛盾和对立的,他们互为表里,和谐统一。外在的表现是一个人内在的反映,内在的品质需要外在来体现。虎豹和犬羊他们的皮毛价值不同,代表的动物也有本质的区别,人们分辨他们的方式就是看皮毛,看外在的斑纹。子贡的这一观点和孔子一致,孔子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只有具备“仁”的内在品格,同时又能合乎“礼”地表现出来,方能成为“君子”。
(7)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
源域:鸡 目标域:小人(小地方的普通百姓)
体型小 → 见识短、境界低
源域:牛刀 目标域:礼乐
刀具较大 → 教化的内容层次较高
这里用“鸡”来隐喻武城这类小地方的普通百姓,意在说明不论大国和小国,也不论在位的君子和普通百姓,都需要接受礼乐教化,学为人之道。正如《论语·为政》中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说明礼乐在孔子治国思想中的地位和意义。
(8)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问》)
源域:骥 目标域:人
贵在有德 → 以德为先
人们称赞千里马不是因为它力量大、跑得快,而是因为它有德行。千里马的德行是什么呢?能辨方向、识路线、有毅力、配合主人等。这里孔子表面上说“马”,其实强调的是“人”。德才兼备的人才当然是最佳选择,但如果两者不能得兼,“德”一定是最重要的衡量人才的标准。
(三)人是无生命物体
1.人是容器
(1)子曰:“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
源域:器物,工具 目标域:君子
用途固定、单一 → 兼备各种才能
器物的特点是用途固定、单一。“君子不器”可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从人生境界来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君子应“上学而下达”,不应舍上而取下,舍道而就器,不为“小人儒”,当为“君子儒”。从君子自身标准方面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君子不应仅具备某种技能,并以此为谋生手段的工具化人才,而应该兼备各种才能。孔子自己就是一个“不器”的例子。如孔子说自己“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吾不试,故艺。”别人眼中的孔子:“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没有充分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是他的一生完成了两件大事,就是创立儒学和开办私学,他一方面总结继承古代文化成果,形成儒学思想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办学传授给学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儒家学派[4](P82)。从管理者用人的角度来说,是指选拔人才不能只看其一面或只看到其一长处[8](P186-188)。人要全方位发展,将自身的潜能挖掘出来。同时,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君子不器”这一观念可以增强自己应对风险的能力,让自己拥有反脆弱的特性[9](P88)。
(2)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论语·公冶长》)
源域:瑚琏 目标域:子贡
贵重而华美的祭器 → 具有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才能
算不上“国之重器” → 没有达到君子的理想境界
瑚琏是古代宗庙中祭祀用的一种的玉制祭器,不那么光彩夺目,但还比较珍贵。子贡在孔子学生中是个通才,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皆较擅长且很有成就。此处孔子把子贡比作瑚琏,说明他才智出众,堪当重任。而正如前面提到,孔子主张“君子不器”,这里说子贡是像瑚琏一样的器物,说明孔子认为子贡具有局限性,还没有达到君子的要求和理想的境界。孔子觉得子贡很会做生意,将太多的精力投入在赚钱上,而孔子的观点是“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所以孔子认为子贡的人生境界和“瑚琏”类似,只是祭祀用的器皿,虽然精美洁净而庄严,但算不上“国之重器”。这个隐喻对于后人学习、工作中的自我培养和塑造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指导作用。
(3)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
源域:觚(古代一种酒器)目标域:孔子自己
沽(卖)→ 施展才华,实现理想
这句话很简短,也没有上下文,古今学者理解不尽相同。这里从隐喻角度来解读。“觚”和“沽”同音,可看成语音隐喻。孔子看到一个觚,联想起“沽”这个字。于是就说:做不做事呢?我还是要做事的,等人来请我吧。孔子不想在家闲着,所以说“看谁出价高、谁重视我,我就去为谁做事”[9](P309)。孔子周游列国,想要推行儒家思想,实现“平天下”的理想,但是一直怀才不遇,“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
(4)子曰:“噫!斗宵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
源域:斗筲 目标域:当时的为政者
量器,容量小 → 气量狭小,境界不高
朱熹注:“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细也。算,数也。”[6](P219-220)杨伯峻先生对这句话的译文:“咳,这班器识狭小的人算得什么?”[10](P199)
这句话出现的情境是:学生子贡问孔子成为“士”的标准。在孔子回答了三类不同境界的“士”之后,子贡联系实际,问:“今天这些党政的人,属于哪个级别?”孔子这才回复上面这句话。斗筲是量器,容量小而且能让人一眼看清里面装的东西。孔子隐喻那些为政者气量狭小,见识短浅,追求蝇头小利、追求名声和面子。总之就是境界不高,格局不大。
2.人是自然风景
(1)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源域:风 目标域:君子之德
动力和影响力大 → 感召力大
无处不在 → 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源域:草 目标域:小人之德
随风摆动 → 飘忽不定,易受影响
君子的德行像风一样,小人的德行像草一样。风刮过来,草自然会随着风的方向倒过去。风的力量越大,草倾向的力量就越大。因此,一个大政治家的领导,应该造成一种风气[7](P525)。这体现了孔子的为政理念,他一向主张以道德感化人民,就像“风”吹动“草”一样。这个隐喻强调君子、管理者的道德感染力和影响力广泛而深远,且是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正如《论语·为政》中提到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2)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平?多见其不知量也。”(《论语·子张》)
源域:日月 目标域:孔子
高不可攀 → 境界高远,可望不可及
源域:丘陵 目标域:贤者
比平地略高 → 比常人境界稍高
丘陵比平地高一点,但日月和平地、丘陵不在一个高度,更不在一个维度,常人只可仰望却无法超越。一般贤者如同丘陵,虽有一定的高度,常人努力一点还可以超越。而孔子在子贡心目中如同日月一样的存在,高不可攀且和一般贤者不在一个维度。日月不仅高远,还一直散发光芒,照亮人间、温暖人心。子贡的这一隐喻说明孔子的伟大和神圣。对于别人的诋毁,不过是自逃光明、自居黑暗,根本改变不了日月即孔子的影响力。另一处“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子贡用“天”来比喻孔子,也表达了一样的情怀。
3.人是交通工具
(1)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
源域:大车、小车 目标域:人
行路 → 生存、与人合作
輗、軏 → 人的信用
“大车”是牛车,“小车”是驴车、马车。“輗”和“軏”都是插在车上的销子,是车的连接器,虽然看着不起眼,却是车子运行时非常重要的关键点。车子行走靠的就是“輗”和“軏”,一旦把他们拔掉,车子就无法前进。在这里孔子把“信” 对于人看得与“輗﹑軏”对于 “车” 一样重要。“信” 是个人提高道德修养水平、成就事业、安身立命的基础和条件,一个人不论拥有什么样的身份和地位,和别人交往都需要有“信用”这个连接器。如果不讲信用,言而无信,那他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无法与人合作、共事。
4.人是朽木、粪土之墙
(1)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
源域:朽木、粪土之墙 目标域:宰予
不可雕、不可圬 → 不可教、不可信
孔子因为宰予白天睡懒觉,认为他像腐烂的木头不可以雕刻,像脏土垒砌的墙面不堪涂抹。孔子认为宰予是“朽木”、“粪土”,这一隐喻似乎和孔子“温良恭俭让”的形象不太符合,这需要结合当时的情境和上下文分析。宰予位列“言语”之科,《史记》称其“利口辩辞”,可见他善于辩论。从后半句也可以推测,宰予平时可能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珍惜时间、废寝忘食之类,孔子就“听其言而信其行”了。而“昼寝”这件事很可能发生还不止一次,所以孔子特别气愤,改变了以前的观念,认为考察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
三、隐喻反映的儒家认知方式和价值观念
“隐喻思维及其概念体系来自于生活体验,它不能脱离社会文化环境而自发形成。”[1]束定芳与汤本庆认为每个文化中都有一些关键词往往是隐喻,它们就像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通过它们我们可以发现隐藏在下面的该文化整个概念系统[11](P1-6)。基于概念隐喻理论和以上三类隐喻的分析,可以总结儒家文化中蕴含的认知方式和价值观念。
(一)治国理念
孔子强调为政以德的思想。“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说明孔子认为社会的管理,根本在人,不在物,不在神;对人的管理,根本在为政者应“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的目标是治国平天下,而他把社会安定天下太平,建立在人们道德自觉的基础上。
(二)为人之道
孔子提出了理想的人格要求,即君子人格。前面分析的隐喻从侧面反映了一些儒家的君子标准。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说明君子应有志向、有毅力、有恒心,经得起苦难和时间考验。“君子不器”说明君子是全面发展、博学多能的人。“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可见君子之“德”的重要性。“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鞹犹犬羊之鞹。”说明君子需要“文“质”兼备,内外兼修。这既体现了孔子所竭力推崇的“君子”的理想人格,也反映了其一以贯之的中庸思想。“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干事业,都要有始有终,不能半途而废、功亏一篑。坚持到生命最后,才能算真正成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可见信用是孔子人生准则中很重要的一条,但是孔子强调“义之与比”,而不是“言必信行必果”。
(三)人才观念
孔子认为仲弓是“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这种人才观启示和激励着我们后人:不能因为卑微的出身而否定自己,更不要因为他人的歧视而变得消沉,相信只要肯动脑筋、勇于探索、不断追求上进,耐心等待最佳时机的到来,普通人也能成为英雄。这也提醒当政者选拔人才不能只看出身而抛弃贤才,不能任人唯亲。他将子贡隐喻成瑚琏。认为宰予是朽木、粪土之墙。可见孔子对学生评价是全面、中肯也是直接的,体现了他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思想。孔子的教育是成人、立人、达人、爱人的教育,而不是知识灌输、专业技能的培养。孔子认为当时的为政者是“斗筲之人”,他眼中合格乃至优秀的为政者是什么样的呢?通过前面分析的隐喻已经看得出来,为政以德,以礼治国,讲仁义,重百姓。
(四)孔子的人生定位
学生眼中的孔子像日月,像山、天一样高深莫测。楚狂接舆认为孔子是“凤”,是心怀大德之人。他认为这只“凤”是需要有盛世和明君来彰显的,只适合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出现,乱世和昏君只能玷污“凤”的高尚德操,不如等到天下太平的时候再出来大展身手。这里和“鸟兽不可与同群”表达得意思一样,孔子和隐士是“鸟”和“兽”,人生的选择不同。
孔子将自己看成是“觚”、“匏瓜”,他积极入世,希望将自己的仁道、礼乐等思想付诸实践,造福于民。但他经常有一种时不我与和时运不济的遗憾。
五、结语
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对《论语》中以“人”为目标域的概念隐喻进行探究,总结出儒家的治国理念、人才观念、为人之道、孔子的人生定位和使命等儒家认知方式和价值观念。通过深入解读这些以“人”为目标域的概念隐喻内涵和运作机制,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思想,它摆脱了天命的羁绊,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是独立于天的,自主的自由的人文思想体系。也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中华文化的发展转到了以人为本的轨道上来[4](P40)。这一研究验证了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一种思维习惯和重要的认知方式,为中国传统典籍的解读提供一个更微观的视角,有利于提高认知水平,提升思维能力,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从而探索了一条西方学术中国化的路径。基于这些基本的思维习惯和认知方式,外国读者可以更生动形象地理解孔子、《论语》和儒家思想,从而更深入地感悟中国文化经典,领悟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及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