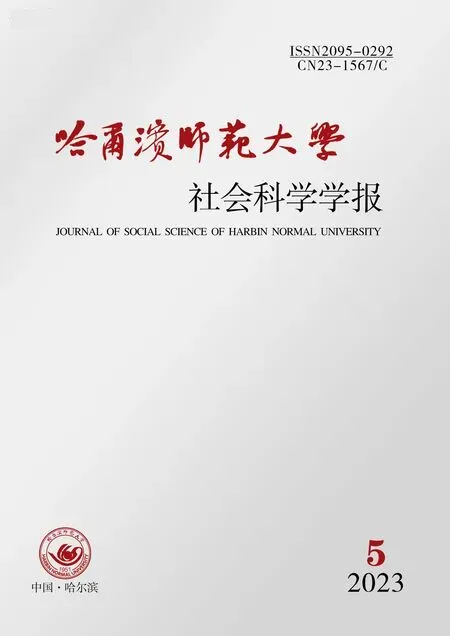经验复活、身份认同、历史重构和话语诉求
——评冉正宝散文集《荒二代的麦浪》
廖冬梅
(嘉应学院 文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荒二代的麦浪》作为一种非虚构写作,其创作动机也许在于私享,但是其文本实践却自觉不自觉地抵达了深刻的思想高地,暗合了某些先锋性的前沿理论观念,具有了包含多个公共话题的阐释空间。作家对特定的北中国的空间经验和特殊历史时代的时间经验的整合和复活,不仅表征着他对一代人的执着的身份认同,同时具有提示社会问题、发现历史真相以及达成主体话语诉求的价值和意义。
一、特定时空经验的复活
《荒二代的麦浪》的创作基于出生于中国特定地理环境和特殊历史时代的一代人特有的生活经验,本质上是一种非虚构写作。“荒二代”虽然没有“红二代”“官二代”拥有被主流话语认可的政治资源,也没有“富二代”坐拥豪车别墅的经济底气,甚至也没有“星二代”可以招摇过市的颜值和演技。但比起当今社会更大多数更无从命名的“工二代”“农二代”或“兵二代”“知二代”来说,“荒二代”毕竟跟“荒一代”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也就和过去国家的边垦政策、开发黑土地的经济建设、以及几十年刻在北大荒土地上的红色基因这些宏大叙事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这一代人还是有比其他同龄人更值得骄傲的历史经验(以时间经验为主)可以追溯的。同时,“千里雪飘,万里冰封”的极地式的地理环境,虽然难有江南的春江水暖和杨柳岸晓风残月,也自有其天苍野茫以及森林之王,有浪漫如梦的北国风光以及和黑土地共生的深厚的东北人文底蕴。因而,“荒二代”还有一个值得回望和思念的故乡生活经验(以空间经验为主)可以叙写。
从上述两个维度出发,作家首先在文本的第一辑《“荒二代”的乐土》部分,通过第一人称“我”的叙事,主要复活了作为“荒二代”代表的个体在东北黑土地上历历在目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故乡生活经验,这些主要跟自然地理环境有关的经验,我们姑且称之为空间经验。文本中有关北国广袤空间经验书写的文字,虽然抹不去“荒一代”开拓期北方偏远蛮荒之地理环境的恶劣,也能见证“荒一代”人开发初期所经历的艰难和苦涩,但因为作家用了由南向北由今向往这种具有时空间离效果的回望式笔调,因而,文本中所复活的只能是作为“荒二代”代表的“我”的个体经验,因而,文本中所呈现的人事物景,实质上都是饱含作家经验的艺术化而非技术性的情感表达。
因而,作家之笔,一方面生动了故乡北中国的自然风物,另一方面激活了荒二代赖以成长和发展的充满生机和能量的人文底蕴,为读者留存了“荒二代”真实的生活图景和一幅神奇北中国的壮美画卷。这其中不仅包括视觉、听觉和味觉在内的多种感性经验,并由丰富的感性经验生发出复杂多元的情感体验。《荒二代的麦浪》中的情感不是单向度的:有“回不去了”的现代性感伤,有对父母辈“荒一代”乐于开拓、敢于牺牲和奉献精神的景仰,有对孩提时代作为懵懂顽童流连于嬉戏玩乐和口腹之欲的儿时趣事的不舍和流连,有对亲邻和师长教诲的默念和感恩。虽然几乎每一篇都不避苦痛和酸涩,但同时每一篇落笔都在肯定生命的欢悦和生存的智慧,能让读者发现一种将生活诗意化审美化的态度,并能在对负面情感的过滤之后融入理性的思考和认识的提升。
因而,作家笔下所有的苦都不再酸涩,所有的痛也不再揪心,所有的死亡都联系着新生。作家神笔一般在尖山后面加了一个日式的昵称“子”,虽也提及跟山有关的战争、墓地和死亡,却少了靠山吃山的落后与无奈,字里行间反而多了一种对“只此青绿”的钟爱和自豪,同时油然生出另一种享用大山恩赐的满足感和有了敬畏自然去除贪欲的主体间性意识;房檐下那排表征严寒的“冰溜子”之前被用了“诱人的”来修饰,少了令人望而生畏的“苦寒”成分,成了少年心中“万象更新,希望复活的象征”[1](P11)之物;《走,采黑天天去》的标题更是满含着“一起同乐”的欢悦和享受;位于分场场部中央的摇把儿辘轳井,也远离了劳作的艰辛和危险,钻进了作家的心里;于是,“我”为每年冬天逐渐少见的肆无忌惮,飞扬跋扈的“大烟炮”天气心生感叹,觉得“少了肆虐带来的痛感,可也少了一种美感。”[2](P14)“我”对故乡儿时生活环境,童年游戏,大众的普遍记忆——白酒以及物质匮乏年代舌尖上的美食、春节以及还没有登上大雅之堂的冰雪运动无不给予单向度的“月是故乡明”式的厚爱,但这种厚爱又不流于偏爱,而建立在对当代科技理性和市场经济的弊端进行反思的前提之上。因而,艺术想象中的童年记忆因为时空的遥远不复拥有而自然变得“物以稀为贵”了:童年小伙伴一起玩耍的游戏嘎拉哈要远胜于当今电脑和手机上的电子模拟游戏,北大荒白酒因为成了两代北大荒人的深刻记忆而价值远远胜过茅台酒和五粮液。
再看作家笔下呈现的“‘荒二代’的影像”。所谓“影像”其实就是“荒二代”时代经验的集成:国营体制保障下既有农场生活的安宁和满足,同时也带来个体意识和潜能发展的局限;出走的“荒二代”个体心灵状态也复杂多样,有人茫然和无措,有人痛苦和悲伤,有人携带着韧性和任性,也有人憧憬着诗和远方,更有“我”,享受着根正苗红的优厚待遇,记忆里想找也找不到悲伤;“我”有时陶醉于一个人的音乐会,有时也追逐时尚的喇叭裤;“我”的记忆中,高音喇叭传出的不全是震耳欲聋的权力话语和时代高调,广播历史人物故事时也听起来韵味十足;“荒二代”的爱情很难脱离特定的时代背景,大多具有被约定被指派的被动性质,因而少自由,多悲剧;国营农场在20世纪末期改制成了农垦集团,“我”也成了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永远的旅人……
如果说作者有关“‘荒二代’的乐土”的书写是个体成长有关上述空间经验的复活,主要着眼于建构一种原生态的人与自然,人与感性,人与原初之间的天人合一的和谐生存状态的话,那么,“‘荒二代’的影像”部分则是基于“荒二代”以及他们承传的父母辈在黑土地上奋斗和创造的时间或曰时代经验的复活,主要提取的是人和时代历史、人和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共生关系。《荒二代的麦浪》作为非虚构写作,源于经验也超越了经验。时间和空间经验经作家之手得以从遥远的记忆中浮出,复活成为切近的触手可感、勃勃生机的天地自然、成为温热浓郁的家国情怀、成为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精神通道,既是生活,是艺术和诗,同时也是哲学。
二、鲜明的“身份认同”意识
《荒二代的麦浪》还表现出强烈而鲜明的身份认同意识。身份认同在作家笔下有三个方面的起因:首先,对“荒二代”一代人身份认同的书写起源于现实中被历史放逐的一代人“失乐园”之后寻找精神寄托和心理归属的需要。作者在文本最后一篇中写道:“我失去了一个个根脉,成了一朵蒲公英的花絮,飘飘荡荡随风而去,扎根结果,然后变成成熟的花絮再度流浪。”[3](P304)“流浪者期盼归乡”的心理状态正是《荒二代的麦浪》内在的创作动力。正如刘瑜所言:“身份认同是‘人性的处境’。”[4](P8)个体一出生,不仅打上了鲜明的家族血缘印记,同时带上了非个人的社会时代,历史和文化印记,这些社会身份网络构成每个个体后天自我成长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基础。而“现代化和全球化则进一步强化这种‘人性的处境’。现代化意味着传统、稳定的社区纽带被打破,现代人的生活成为一场漫长的‘流浪’,人们不断被抛入陌生的地点、陌生的群体、陌生的关系,‘独自承受’一切挑战。这种原子化状态驱动着弗洛姆所说的‘逃避自由’心理——人们试图在不断分崩离析的世界中抓住一点什么,哪怕抓住的仅仅是‘想象的共同体’。”[4](P8-9)
因此,流浪者的寻根书写贯穿了《荒二代的麦浪》的始终。正是因为有失去的感性焦虑,才有身份认同的必要。
其次,身份认同还源于个体对自我和群体生存状态的超越性形而上理性思考的需要。人到中年的作家,对“荒二代”这群被历史遗忘的人进行生存的叩问:
我们虽然不能被写入历史,但我们同样需要认清楚我们是一群怎样的人——我们现在都在哪里?……我们是谁?……其实这些问题也是哲学史上的永恒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我迫切想知道,但哪本书里都没有答案。[5](P163-164)
对这些问题,作家在文本中通过边叙述边议论的方式进行了一一回答:“我们是伟大的垦荒时代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却不是这个时代的开创者”。我们是“荒一代”的孩子,同时确证了“荒二代”群体共同的特质:“本分,简单,高贵和快乐”[6](P133),当然还有野性、智慧和信仰。
第三,身份认同还源于社会现实背景中个体所遭遇的他者或“想象他者”的压抑而导致的权利或自由失落后要求重新获得的诉求。“荒二代”的他者不仅包括官二代,富二代和星二代以及“院二代”。所谓“二代”的命名,指涉的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的社会分层,在改革开放中,不同的人们根据其先天性的家庭背景和后天的政策带来的红利多少而形成不同的阶层。
对于身份认同的这个现实背景,《荒二代的麦浪》虽然只在《自序:我是“荒二代”》中蜻蜓点水,一笔带过,但是,正因为这一“点”让我们读到了身份认同的现实背景或曰原因。基于这种现实背景而对“荒二代”的身份认同,就具有构建多元共存的民众生存状态的话语内涵。作家的写作让我们一方面相信,“荒二代”是个既拥有着自己的乐土,影像和麦浪的一群,同时是有追求、涵养,能包容、敢奋斗和有成就的一群,他们既没必要因为不能入史而自暴自弃,也没必要羡慕或攀比或者被其他“二代”同化。“荒二代”大可以在作者建构的文字世界和现实生活中自美其美,他们大可以和社会上流行的“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和“星二代”以及“院二代”以及更多的无名的“穷二代”“农二代”“工二代”或“知二代”,构成多元共存的更大的集体。多元共存才能百花齐放,多元发展才是国家和社会生机勃勃的力量之源。但多元共存得以成立需要一个前提:多元平等而不是二元对立。而现实生活中的“荒二代”作为一个群体却处于失语状态,比“荒二代”更不济的众多的“二代”们无疑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而存在,都是不争的事实。而社会上的弱势或失语群体又会因为事实上和较强势的“二代”们存在的各方面的巨大差距而自觉没有值得炫耀的资本和底气。他们会产生失落、怅惘或不甘等复杂情绪。因此,要维持现实中真正多元个体并存的稳定结构,就需要建构一个可以保障任意“二代”中的个体都可以自由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平等和自由空间。才可以打破阶层固化,贫富分化,避免阶层对立、紧张和撕裂。但是目前,社会上已经出现“二代”之类的命名,其实就说明阶层固化的苗头已经出现。而且,不同“二代”所指涉的不仅是地位的高低,实力的强弱和占有优势资源的多寡之别,同时,更重要的是“彼二代”和“此二代”群体之间的心理和情绪状态也不一样。如何缩小“二代”之间的现实差距和平衡他们之间的心理以及情绪差异,就成为一个值得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同时,作为个体,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到,自我不仅需要自我的身份认同,需要主体确认,尊严的获得和自由的发展,同时,在各种“二代”组成的“我们”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我们’,由人之为人的理性与同情心融合为一个一望无际的整体。”[4](P14)因此,“我”和“他者”“我们”以及“他们”“公民”以及“个人”的关系是否能够调节和建构成一种平衡和谐、相辅相成的关系,就关系到社会结构是否能够维持长期稳定此等重大的社会课题。但是,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这些由宏大话语支持的身份认同,往往惯于外在地把不同个体拉到一个平等的心理位置,另一方面,国家/民族认同的公民身份认同不可避免地遮蔽了个体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资源配置不均所造成的阶层固化带来的个体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结果不平等的真实体验。
因此,如何正视和认同众多“二代”之间的差异,并积极调动每个群体的积极性,并尽可能最大程度地消除“二代”和“二代”之间结构性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就变得不容忽视。这也许是《荒二代的麦浪》中身份认同书写留给我们的深度思考吧。
关于文本中涉及的身份认同书写,我们还可以作更进一步思考:到底应该通过什么来获得自我价值的“认同”?每个个体固然都与生俱来携带着特定的身份,这些身份决定了个体成长和发展之前的类似基因密码一样的“初始设置的情感圈层结构和意义诠释系统”。[4](P11)
但是,人之为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决定了个体不可能在这些初始设置的共同性特征面前毫无作为,他会修改这些初始密码,他会自我发展和自我创造。因此,过分强调我是“荒二代”难免进入画地为牢的心理误区。但是,读完《荒二代的麦浪》,我们发现作家对“我是荒二代”的强调的“度”把握得很精准,没有“过度”之嫌。他一方面不断地强调“荒二代”与生俱来的激情、梦想、精神印记和文化承传,另一方面,字里行间也不断强调和肯定作为“荒二代”的个体后天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重要性,诚然,个体无法完全跳出先天身份去完成一种没有根基的“空中飞行”式的自我成长,但是,个体可以自觉在既定的身份属性之间进行主体选择和重组、并从中寻求突破或僭越,同时注意吸收和融入“他者”身份的积极因素。这样,向外追求公平和正义,向内追求自我创造和自我完善,如此才是可以保证个体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发展的有效身份认同。
三、对有关边垦故事的历史重构
对 “荒二代”的书写不仅指涉东北故土风物的描摹、血缘亲情的家族代际承传以及一代人的身份认同,同时指向我国20世纪50、60年代那段特殊的历史。这段历史不缺主流话语的宏大叙事,同时也不断进入新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作家乃至先锋文学作家的关注视野,那么,出版于2022年的《荒二代的麦浪》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哪些重构呢?下面笔者将围绕这个问题进行集中分析。
首先,文本中贯穿着鲜明的自觉的历史书写的个人意识:
个人的历史回忆有时比宏大叙事的历史记录来得更加真实,……我的记忆里的东西不一定完全是当时的真实风貌,但我会真实地把存在脑海中的记忆和感受写出来,让一段岁月复活在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身上。[7](P109)
在《父亲的修配所》的结尾,作家再次表达了自己对个人化历史的喜好:
“我喜欢这种个人化的叙述,因为历史是个什么样子,没有那个人能说得清楚,历史应该是每个人叙事的总和,包括我这篇回忆。”[8](P172)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自觉意识,《荒二代的麦浪》中历史的重构不仅表现在对个体对历史的选择性回忆和想象,同时包含一种基于对传统历史书写反思而产生的新历史主义式地对另一种历史真相的发现和评价。作家笔下,对边垦历史和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图景,都进行了个人化的选择和捕捉。主要从人情、人性以及文化的视点,而很少从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宏观层面或以阶级/阶层的视点去重现那段历史。对比一下前人有关北大荒的历史书写,以及跟“荒一代”相关的边垦历史、知青运动以及“文革”历史的书写,就能够感觉到《荒二代的麦浪》中鲜明的新历史主义的重写策略。重写不仅体现在对历史人物形象的重塑,也体现在对历史做出新的阐释和评价。比如对于“文革”那段历史的记忆,作者没有像刘心武、卢新华等伤痕文学作家那样激烈地控诉“文革”给国家和人们所带来的外伤和内伤,而是真实地坚持说“我的记忆里没有悲伤”[9](P117),同时又强调:“我的记忆里没有悲伤,不代表那个时代没有悲伤。”[9](P117)
于是,作家不以一个特殊历史的冷漠见证者的局外人态度去记录历史,也不运用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手法美化历史,不从一个受害者的立场出发去控诉或反思历史,而是遵循着自己作为一个“荒二代”人的真实体验重构历史,在文本中发出了诸如“知青该不该忏悔”的历史诘问,同时也表达出与张抗抗以及梁晓声等著名知青作家不同的回答:不能因知青中的少数人的作恶或有罪而提出让整个知青群体自省或忏悔的要求,忏悔不忏悔,本质上属于当事人个人内心或灵魂层面的认知或体悟,外人强求呼吁也无济于事。而对于“知青该不该返城”的问题,更有自己的看法:从对“荒二代”教育的角度以及开发和建设北大荒的角度看,知青都不该返城。
再看《荒二代的麦浪》对历史中人的重写。之前的作家由于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倾向于选择那种被权力话语激荡起来的毫不利己、专门为国的先进人物进行理想化书写。比如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规约之下由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编选的短篇小说集《边疆的主人》系列小说,就惯于塑造那种像丁小红(梁晓声的短篇小说《边疆的主人》里的主人公)、余永斗(陈可雄的短篇小说《新松挺拔》中的主人公)耿长炯(张抗抗的早期长篇《分界线》中的人物),还有杜晚香(丁玲散文《杜晚香》中的主人公)之类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是那种阶级性远大于人性,满脑子里都是国家财产、斗争或思想改造的“硬汉”或“铁娘子”式的英雄形象。
作家试图从普遍人性出发寻求对历史人物新的理解,站在人作为主体的立场上重新审视人的生存境遇。在作家笔下,有的只是一群在“荒二代”眼中神一样存在的热爱和传递着知识和文化的知青,或者如“我”的母亲那样的支边青年,他们的支边动机中除了国家召唤之外也不无个人对当时官方话语承诺的物质待遇和经济状况改善的心动和渴盼,也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和小私心。但是在发现承诺根本无法兑现、现实与官宣之言有天壤之别的情况下,他们心中也会有失落,有牢骚,他们也会动摇之前心中的信念,也想逃离“北大荒”那个苦寒之地,他们算不上意识形态话语认可的先进典型,他们甚至也不被历史公正地对待,但是他们和先进典型一样为实现特定时代伟大的国家梦而无悔地付出了自己的一生,他们除了被时代裹挟成为被侮辱和被损坏的受害者之外,还有自己坚守的底线、也不缺主体性的精神追求。可以说,他们比起那些虚张声势的英雄或者受害者形象更立体更丰满,在他们身上,可以感受更多人性的真和善,更多的主体性以及灵魂和精神世界的自由。相比那些名见史传的复转官兵和广大知青,他们也许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了那段历史中活生生的主体。
需要强调的是,《荒二代的麦浪》对历史的重构,跟当代文学史上众多新历史小说家的价值倾向和情感态度又不相同。作者试图在宏大历史叙事和个人化叙事之间找到了一个较为理性的情感支点,避免陷入全盘认同主流历史书写或者极端主观性和个人化的荒诞游戏或历史虚无主义式的非理性书写(如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等文本)两个极端。对边垦历史的书写,作者既尊重历史真实,提供了大量有据可查的数字化史料,重现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垦边人将几千里荒原建成富庶粮仓的人间奇迹,又弘扬了边垦历史留下的最大的精神财富,歌颂了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主体力量,肯定了“荒一代”人秉持的政治觉悟、精神境界、道德情操和意志品质,同时字里行间又补充了诸多主流历史话语自觉不自觉省略的历史和人性真相,也不避对这段历史进行辩证的主观认识和评价。
四、主体性的话语诉求
《荒二代的麦浪》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创作动力不来源于任何利益集团的授意,这种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现实功利性的写作,能够达成作家主体性的话语诉求。其主体性话语诉求主要表现在对“麦浪”意象的创意书写和对传统/权威话语和流行话语的双重反控制,以及拒绝附和和沉默,大胆地发出真声。
首先,来看麦浪意象的创意书写。
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写过有关麦子的意象:诸如麦田、麦地、麦子、麦粒、麦穗、麦秸垛等。西方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要算梵高笔下的“麦田”意象了。梵高创作了许多有关“麦田”的油画,前期《孤鸟翔空的麦田》中的“麦田”满溢着强劲的生命伟力,晚期《圣保罗医院后的麦田和收割者》《黄色的麦田》《暴风雨似的天空和麦田》以及《群鸦乱飞的麦田》等等,特别是《群鸦乱飞的麦田》则基本都是梵高自杀离世之前内心真实的映射,由激情到迷惘的反复和孤独无助。
1951年,塞林格创作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小说中“麦田”作为主人公青年霍尔顿的精神家园之所在。文中霍尔顿渴望成为一个麦田守护者,守护着儿童世界的纯真与美好,防止他们受到成人世界的污染。“麦田”意象象征着疏离了虚伪和贪婪的纯真美好的儿童世界。同时也象征了美国“垮掉的一代”青年的迷惘和对美好的回望以及对未来的追求。
在中国还有当代诗人海子,他的抒情短诗中也经常使用“麦地”意象。他的《麦地》《五月的麦地》《麦地或遥远》《麦地与诗人》等篇中多次出现“麦地”意象群:麦地、麦子、麦粒、麦田、麦秸等。最著名的《五月的麦地》中有“全世界的兄弟们/要在麦地里拥抱”[10](P353)的诗句,其中的“麦地”意象象征人类安宁富足、“诗意栖居”的生存状态。在《麦地与诗人·答复》中他又写下“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11](P355-356),此篇中的麦地则转向了诗人对离开麦地之后自觉无力偿还麦地的养育之恩的深沉愧疚、孤独无助的抒写。深深眷恋着农业文明同时又热切追随着西方先哲的海子,一方面竭力讴歌麦地的慷慨给予和无言大爱,另一方面,又因觉得自己无力回报麦地的养育之恩而倍感困惑和痛苦。
当代先锋诗人雨田的长诗《麦地》则继续践行着海子的大诗理想,他笔下的“麦地”则幻化成承载人类生命和生存的重要图景,见证着人性的挣扎和扭曲、生和死的轮回,象征着先锋诗人对理性中心、偶像崇拜等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的后现代性反思,表征着诗人对人类历史难以挣脱的循环宿命以及人性之恶的深刻的悲剧性体验和洞察。
新时期女作家张洁有一篇散文《拣麦穗》,文中的“麦穗”,承载着女性笔下单纯而懵懂的小女孩通过“拣麦穗,备嫁妆”这种农村女孩最素朴简单的方式在物质匮乏的特殊年代对自己未来的打算和谋划。“麦穗”意象象征着女人待嫁的物质基础。
铁凝《麦秸垛》中的“麦秸垛”,形似女性乳房,因此象征女性如大地般哺育万物的创造和奉献。同样书写过北大荒岁月的现代作家聂绀弩也有一首《麦垛》,其中有这样的诗句:“麦垛千堆又万堆,长城迤逦复迂回。散兵线上黄金满,金字塔边赤日辉。”[12](P37)“麦垛”成了“长城”和“金字塔”,表征的是诗人虽身处逆境却仍然坚强挺立的强者或硬汉情怀。
而《荒二代的麦浪》里也出现了一个跟中外作家笔下的“麦地”意象群相关但不等同的“麦浪”意象.作家不仅以“荒二代的麦浪”命名全书,“麦浪”成为文本的核心意象,在第一辑里的最后一篇,还单独书写了“麦浪”意象:
在近处看麦苗田和站在尖山子上看就不一样了,没过膝盖的麦苗在北方爽快的劲风吹拂下,前赴后继,形成了绿色的麦浪。麦浪不仅仅是李健《风吹麦浪》中涌动着的金色,在它还是绿色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兴风作浪”了。只是春天的麦浪里不会裹挟丰收的喜悦,但会推送希望,让一个正在拼命成长的少年浑身充满力量。[13](P59)
这里的“麦浪”意象,不同于如前所述众多作家书写的最大特点:首先,在于它不是一个个体意象,而是一个群像。众多接近成熟的麦穗或麦株聚合在一起才能形成阵阵麦浪,用来指称“荒二代”这个群体非常贴切。其次,“麦浪”还意味着一种充满希望和期盼的生命状态。幼小的麦苗无法形成麦浪。渐渐长高或抽穗之后变成金色充盈着饱满麦粒的麦株才有一种沉甸甸的力量,这既是心中充满着希望的少年之心的表征,同时也是渐入中年的作家理性看取历史和时代现象的人生智慧的外化。第三,“麦浪”意象在文本中舍弃了张洁、铁凝等作家主要取其指涉物质丰足或女性孕育给予等写实层面的内涵,也不执着于海子或雨田等诗人追求超越性形而上的对于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等现代或后现代主义内涵。麦浪意象在作家笔下更多地疏离了苦痛和迷惘,而象征着希望和喜悦,鲜明地体现出作为现实生活中体验过酸楚和苦涩的“荒二代”作家不流连于揭示伤痕不沉迷于咀嚼苦痛,而竭力将生活审美化的浪漫主义文人情怀。第四,“麦浪”还是一个典型的动感意象。青黄相接,前赴后继,恣意翻滚,是一个自由自在具有行动力的主体意象。作者用如此的麦浪意象更多地突出和象征着“荒二代”人前赴后继、乘风破浪的行动能力,因而,“麦浪”意象可能还更深刻地隐喻着作家对荒二代作为“历史中间代”所应该具有的敢于继承先辈,也勇于接受现实以及开拓和思考未来的历史承担者的希冀和期盼。因此,这个动感意象背后的话语内涵就既包含了作者对自由快乐、浪漫高贵、美以及优雅等生命状态的追求,最重要的还具有了承传,承担和创造的主体性话语诉求:我是荒二代,我们进不了历史,但我们有自己的麦浪,在天地间无所顾忌,自由翻滚,我们自己生长自己成熟,我们自己书写自己的历史!
再看《荒二代的麦浪》对权威/传统话语和大众流行话语的双重反控制。
面对“荒二代”没有历史的现状,作家不仅有自我撰写历史话语的勇气和实践,还时时警惕着自己的文字落入主流传统话语的窠臼。正如福柯所强调的,话语背后是权力,话语的传达实质上具有权力统辖和控制的功能。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体,要避免成为被权力话语或流行的大众话语控制的客体,就要设法说出自己的话,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话语主体。权力者可以“凭仗刀笔行事”[14](P8),按照权力意志组织话语,那么,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则可以在象征性的文本世界中,竭力行使着自己的话语权力。
《荒二代的麦浪》的作者无疑有着清醒的话语主体意识。不仅在文本的《自序:我是“荒二代”》中为“荒二代”的概念命名,在后文中还提炼出“荒二代”一代人的集体性格。他还僭越了红/黑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无所顾忌地盛赞那源于“黑土地”的黑色思想,并且认为越接近底层思维的“黑色”思想,才越是求真深邃的敏锐洞见;文本中,北大荒精神不是刻在墙上喊在口中写在教科书里,而是“藏在望不到尽头的垄沟里”[15](P263);神一般存在于作家笔下的,不是领导或偶像,也不是时代标兵或先进楷模,而是哈师大中文系的老师们;对权威话语讳莫如深的有关“逃离北大荒”的故事,没有省略,反而单独开题书写以示强调。
作家进行主体性反控制书写所指向的,不仅有上述的权威/传统话语,还有某些流行的大众话语。《看不到寺庙的北大荒》里的文字,反驳了“没有寺庙就等于没有信仰”的流行话语。指出有关地域性格的说法也值得怀疑。此外,对当今社会上流行的全民娱乐现象,作家也大胆放言:
现在的社会大有“娱乐至死”的趋势,无论是严肃的与不严肃的,无论是科学的和非科学的,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大家似乎都喜欢用非常娱乐化的形式呈现出来,虽然轻松了,但却混淆了一切,尤其是扭曲了娱乐应有的功能。[16](P291)
最后来看作家在文本中发出的真声。在分析当年复转军人和支边青年和知青为何逃离北大荒时,作家直言不讳地指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领导们的规划太离谱以及不公平的待遇和不够人性化的管理方式。作家毫不掩饰自己对特定年代重大社会事件的主体认知和观点:历史话语缺乏对支边青年贡献的肯定,这是不公平的。边垦时代的宣传话语,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付出所谓“无悔青春”的“荒一代”,在很大程度上,沦为“集体情怀”道德话语捆绑的无奈的廉价劳动力或者工具。成为权力话语“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予取予求的支配对象;那些仅靠口号宣讲或刻板教条式的支配和控制,或者局限于对少数时代英雄的夸赞,而不能物化和落实于时代中每一个人的现实承担中的所谓“时代精神”,是不靠谱的。
这些真声的发出,具有“改造国民性”的话语诉求。1927年鲁迅在香港曾经做过一次名为《无声的中国》的讲演,感叹于中国历代压迫过严,更兼汉字的学用两难,传统思想的因循守旧,致使中国多数人变成沉默的大多数,“不能说话”。希望“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17](P15)希望之余,鲁迅又马上意识到这种希望的虚妄,于是感叹中国仍然是一个“无声的中国”,并指出人如果没有声音,就等于“死了”或“哑了”,鲁迅虽然看到了发出声音的难度,他依旧主张迎难而上发出真声。
《荒二代的麦浪》无疑发出了鲁迅所希望的真声。这样的真声也许不如洪钟大吕,也能悠远绵长地敲击着人们的耳鼓。这样的真声,有如福柯所说的“诊断器”[18](P228),具有诊断时代病症和思想病症的功能。敢于不计利害发出真声的知识分子,也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正如福柯所强调的:“不仅使别人的思想得到改塑,也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改塑,改变自己的意识,也改变别人的意识,才是知识分子的天职。”[19](P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