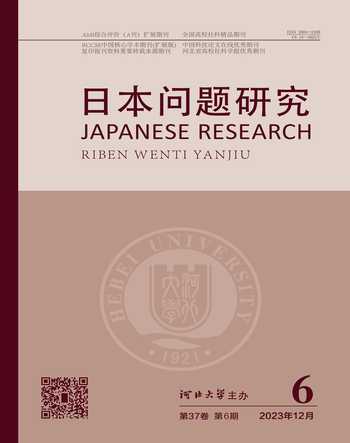日本家庭寄养制度探析
江新兴 常梦斐

摘 要:日本家庭寄养制度始于1948年,随着二战后保护战争受害儿童事业的结束逐渐走向衰退。20世纪90年代后,受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儿童权利以及日本国内虐待儿童成为社会问题的双重影响,政府在对需要保护的儿童实施社会养育时,确立了家庭寄养优先的原则。现行寄养家庭包括四个类型,其实施体制则由都道府县、儿童咨询所与各支援机构组成。近年来,日本的家庭寄养委托率虽然稳步提升,但进展依旧缓慢,存在着知名度不高、与“领养”混淆、民众成为寄养家庭的意向不高以及寄养家庭数量不足等问题。对此,日本政府从制度改革、扩大宣传、完善支援体系等方面提出了解决之策。
关键词:家庭寄养制度;寄养家庭;需保护儿童;儿童福利;社会养育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23)06-0041-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3.06.005
日本的家庭寄养制度,始于1948年实施的《儿童福利法》,与儿童养育机构共同承担了保护儿童的功能。家庭寄养制度确立后,出现了短暂的隆盛期,在制度上经历了发展衰退期、重新评估期和加速发展期。在现实中,与儿童养育机构相比,无论接收儿童的数量还是寄养家庭的数量都没有较大的提高。与欧美国家以家庭寄养为主不同,日本更偏重于通过福利机构养育需要保护的儿童①。究其原因,既有社会认识上的问题,也有推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探究日本家庭寄养制度实施现状,剖析其面临的困境成因以及日本政府为破解困局所做的努力,有利于加深对日本推动保护儿童问题的理解,也可以为正在探索家庭寄养模式的其他国家提供借鉴。
一、日本的家庭寄养制度
家庭寄养制度指委托寄养家庭养育18岁以下的、没有监护人或被认为不适合让监护人监护的儿童(以下称“需要保护的儿童”)的制度,换言之,指对因各种原因无法在父母身边生活的儿童提供替代的养育场所,为他们提供一个温暖、有爱的家庭成长环境的制度。虽由寄养家庭代替亲生父母养育儿童,但养父母和需要保护的儿童间并不建立法律上的亲子关系,亲生父母仍为儿童的监护人。自古以来,日本社会一直存在家庭寄养的习俗。
在日本的法律体系中,对需要保护的儿童,由国家和地方政府代替家庭养育即社会养育,包括家庭养育和儿童养育机构养育两种安置方式。家庭寄养制度在家庭养育中担负着核心角色。另一种安置方式的儿童养育机构,包括乳儿院、儿童福利院、儿童心理治疗机构等。与采用集体养育方式的养育机构不同,家庭寄养采取个别养育方式。养育家庭和养育机构共同承担了保护儿童的功能。
(一)家庭寄养制度建立的背景
首先,日本需要保护的儿童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就已经凸显,战争末期,战争孤儿、流浪儿童充斥街头,保护这些儿童成为当时日本政府的紧急课题,因此制定了《战灾遗孤保护对策纲要方案》。以此方案为基础,1945年9月出台了《战争孤儿等保护对策纲要》,规定了保护和培养儿童的三种主要方式,即委托个人家庭养育、介绍被收养为养子、集体保护培养。其中“集体保护培养”指的是收容到机构设施养育[在最初的《战灾遗孤保护对策纲要方案》中,三种方法排在第一位的是“介绍被收养为养子”,后面正式出台的《纲要》中排位发生了变化,但“集体保护培养”一直都排在第三位。参见貴田美鈴.里親制度の史的展開と課題[M].東京:勁草書房,2019:70.]。旧厚生省儿童局实施的《全国孤儿总调查结果》显示,1948年日本全国孤儿总数高达123 511人,其中包含战争孤儿28 248人,从原殖民地、占领地等归国孤儿11 351人,普通孤儿81 266人,以及弃儿2 647人[1]348-350。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需要保护的流浪儿、孤儿,1947年发布的《儿童福利法案概要》指出,“现如今我国虽然有儿童保护设施,但尽早发现需要保护儿童并采取保护措施的设施数量依然不足,(省略)儿童保护设施仍有诸多需改进之处”[1]763-765。由于儿童机构设施建设和管理滞后,仍然有许多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有些人甚至成为实施盗窃、抢劫的失足少年,给日本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治安隐患[在1947年《儿童福利法》制定实施之前,日本实施了保护儿童的措施,按时间顺序,1945年9月15日文部省发布了「戦災孤児等集団合宿教育に関スル件」的通知,要求以战争孤儿等为对象作为教育对策实施团体集训教育;5天后的9月20日又发布了「戦災孤児等保護対策要綱」的通知,实施对象为战争孤儿,主要保护方法有委托家庭保护、介绍养子家庭、集体保护。1946年4月15日厚生省发布通知「浮浪児其の他児童保護等の応急措置実施に関する件」,要求对在停车场和公园流浪的战争孤儿进一步采取保护措施。1947年12月6日,厚生省出于为保护战争孤儿对策而制作资料的需要,通知在全国实施「全国孤児一斉調査」。]。儿童保护机构和设施数量的不足,让家庭承担了更多的保护和培养儿童的任务。这也是家庭寄养制度建立后最初一段时间得到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其次,明治维新后,日本随着经济的发展重视社会救济和福利制度的完善,在政府和民间积极推进儿童保护工作。政府相继发布实施了救济儿童的政策[如《关于弃儿养育的大米配置法》(1871年)、《针对生育三个孩子贫困家庭的抚养费发放法》(1873年)、《救恤规则》(1874年)等法律。],民间社会慈善家设立以孤儿、弃儿为对象的设施,以及以收容“不良少年”为对象的感化院等,承担了保护儿童的主要工作。进入昭和时代后,与儿童问题有关的《救护法》(1929年)、《少年教护法》(1933年)、《母子保护法》(1937年)等法律相继制定。同一时期,为了防止对儿童放置不管以及儿童劳工化(童工)等虐待现象频发,1933年又制定了《防止虐待儿童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新宪法保障国民生存权的背景下,《儿童福利法》指出:所有儿童有成长权利,其生活须得到保障,安全应受到保護。事实上,在战后日本社会除面临保护孤儿、弃儿、贫困儿童、流浪儿童等紧急课题外,还存在童工、贩卖人口、虐待儿童等现实问题。为了应对儿童受侵害问题,1947年制定了《儿童福利法》,该法既体现了福利国家的理念,也是对明治以来保护儿童政策的继承。
家庭寄养制度作为保护儿童的措施,私人之间进行的委托难免缺乏专业指导与公正监督,由此使得需要保护的儿童陷入危险与不幸境地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2]。因此,将家庭寄养置于法律框架内形成制度,既能减轻儿童养育机构的压力,同时又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与特定值得信赖的大人之间形成依恋关系,让更多的孩子在与家庭类似的环境中生活,促其形成健全的人格。
(二)家庭寄养制度的变迁
日本自古就有家庭寄养的习俗,从公卿贵族到普通百姓,为了让孩子健康成长,都有让他人(拟制父母)代养孩子的习俗[被寄养的儿童称为“里子”,寄养家庭在民俗中有拟制父母的习俗,即通过为儿童起名字、授乳等形成持续终生的亲子关系。参见竹内利美.里子[M]//日本民族学協会.日本社会民俗辞典2.誠文堂新光社,1952:1533-1541.]。明治时代中期,基于比起在设施中的集体养育由家庭进行个别养育更理想的理念,通过孤儿院、保育院等机构设施中介,把需要保护的儿童寄养到私人家庭(院外委托)。这种“院外委托”被学者视为现代家庭寄养制度的原型[3]。由此可见,家庭寄养在日本有着悠久的传统。
日本的家庭寄养制度在公法上明确定位始于1948年实施的《儿童福利法》。次年10月,又发布实施了落实家庭寄养制度的基本方针《寄养家庭养育运用纲要》,该《纲要》指出:“……与在设施的集体养育相比,家庭养育儿童会得到更好保护的情况较多。”尽管肯定了家庭环境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但家庭寄养与收养等形式的区别不明确,选择家庭养育的优越性并不突出,所以,对需要保护的儿童进行保护时出现了偏重利用养育机构的倾向。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出现了有关“设施症”的争论,但最终还是停留在改善机构养育质量上,没有以此为契机实现重视家庭养育的政策转向[4]。在20世纪50年代末以前,因儿童福利设施建设滞后,家庭寄养制度在保护战争孤儿、弃婴、流浪儿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加之联合国派遣的儿童福利专家对家庭寄养制度运用的指导,家庭寄养的儿童数量在1958年达到最高值[1958年委托到寄养家庭的儿童数为9 489人,登记在册的寄养家庭数达到18 500人~19 000人左右(全国里親会:「里親制度関連予算·統計平成19年度」)。。
20世纪50年代末,儿童保护机构和寄养家庭接受的儿童的数量都开始减少,此前不断扩大的机构设施出现了缺员情况,政府的压缩调整措施使机构反而努力维持定员在一定水平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家庭寄养制度基本上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联动,在经济高速增长及建设福利国家的背景下,政府实施了针对寄养家庭的优惠税法,强调将儿童与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多地成立了推进家庭养育的民间团体,家庭养育受到更多的期待。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高速增长结束后,社会福利方面的财政投入被压缩,寄养家庭被定位于志愿者等民间活力的运用上。尽管1974年厚生省公布了《短期家庭寄养制度》[指由于母亲分娩、生病、住院、拘禁等原因,短期(1个月至1年以内)或者利用长期休假、周末等接受委托养育需要保护的儿童。],对家庭寄养制度实施了最早的改革,在政策上通过扩大需要保护的儿童范围,扩充家庭寄养的方式,谋求家庭寄养事业的发展。但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70年代与寄养家庭制度相关问题的表述逐渐减少,政府的公共责任越来越收缩[5]。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因应社会形势的变化,经过修改的民法,强调實施特别领养制度[指领养人将需保护儿童加入同一户籍,在法律上建立亲子关系。领养制度分为“普通领养”和“特殊领养”,前者领养的儿童没有年龄限制,与亲生父母不断绝法律上的关系;后者领养的儿童应不满6岁,与亲生父母断绝法律上的关系,儿童的亲生父母为死亡、失踪、幼年产子等情况,儿童不可能再重新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受其影响,1987年将《寄养家庭养育运用纲要》修改为《寄养家庭等养育家庭运用纲要》,重点是改变了只有特殊的慈善家和有产者才能成为寄养家庭的传统理念,扩大了寻求寄养的家庭的范围;儿童咨询所开始特别领养制度的运用;有效利用民间力量;导入每年一次寄养家庭研修制度等。但从实际效果看,寄养家庭的数量和委托寄养的儿童数量都没有改变继续减少的趋势。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迎来了重新评价家庭寄养制度的时期。一方面,受20世纪80年代欧美更加重视儿童权利意识的影响,日本批准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1994年)。公约规定:在有家庭氛围的环境中成长是儿童的权利,国家有义务安排家庭寄养、领养以及养育设施,为缺少家庭环境的儿童提供养育的替代方式;同时还规定了保障需要保护的儿童在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原则,即通过援助尽量使儿童留在家庭,必须将儿童转到家庭外养育时,要采取短期的家庭寄养措施,努力修复其家庭生活。在此背景下,日本国内对家庭寄养制度的研究很活跃,相关团体纷纷建议对家庭寄养制度实行改革,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实现儿童的最大利益、满足孩子需求的多种形式的家庭寄养上。另一方面,修改儿童福利设施的最低标准,规定儿童养育设施必须发挥与家庭环境协调的作用,对机构设施里希望到寄养家庭生活的儿童,要积极推进并对其进行帮助。而且,在寄养家庭因故白天不能照顾儿童时,应允许其像通常上下学一样“通所”。同时,随着虐待儿童事件的增加,养育机构设施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作为社会福利结构改革的一部分,调整以往的优先养育机构的政策势在必行。
2002年,日本对家庭寄养制度做了较大改革。厚生劳动省以省令的形式发布了《关于认定寄养家庭等的省令》和《关于家庭寄养的最低标准》,将家庭寄养定位为社会养育并对其进行重构。在原有养育寄养家庭和短期寄养家庭的基础上,增加了专业寄养家庭(养育有被虐待经历的儿童)与亲属寄养家庭(养育亲属的孩子),形成了现有家庭寄养类型的雏形。2008年,日本政府再次对家庭寄养制度进行修改,具体包括:从制度上区分了寄养家庭养育和领养寄养家庭;为寄养家庭的养父母提供义务培训;家庭寄养类型调整为养育寄养家庭(将短期家庭寄养并入其中)、专业寄养家庭、领养寄养家庭和亲属寄养家庭;实施家庭寄养支援机构项目以及寄养家庭补贴翻倍等措施。
2011年,日本政府出台《家庭寄养委托指导方针》,规定对需要保护的儿童实施社会养育时,改变此前重视机构设施养育的做法,原则上转向优先家庭寄养。首次,通过政策的形式将家庭养育理念置于“优先”地位。接着,在2017年修改了《儿童福利法》,明确了家庭养育优先的理念,指出“儿童是权利的主体”,儿童应该由亲生父母在家庭养育,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应该在与家庭同样的环境中养育,在前述要求均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在良好的、接近家庭的环境中养育。受此修改法的影响,为了将法律理念具体化,“关于新的社会养育应有状态的研讨会”公布了《社会养育新愿景》[6]。该文件强调构建市町村对有儿童家庭的支援体制,强化对寄养家庭的全面支援体制(支援培训机构)和对家庭寄养制度改革,彻底贯彻婴幼儿家庭养育原则,明确了养育年限等措施目标[对需要保护的儿童,不满3岁的在5年以内、其他学龄前儿童在7年以内,由寄养家庭养育比率提高到75%以上;儿童期以后的大概10年以内,由寄养家庭养育的比率提高到50%以上。]。2018年7月,厚生劳动省儿童家庭局公布了“寄养家庭养育综合支援机构及其业务指针”[7],为实现高质量的寄养家庭养育,提出了都道府县推进培训业务的具体方式。
(三)现行家庭寄养的分类
现行《儿童福利法》根据需要保护的儿童的属性不同,将家庭寄养分为4类,分别是养育寄养家庭、专业寄养家庭、领养寄养家庭和亲属寄养家庭,见表1。
表1中的4类型分法是2008年对《儿童福利法》进行修改后的结果。修改后分类上主要的变化如下。其一,将原来的“养育寄养家庭”和“短期寄养家庭”合并为“养育寄养家庭”。其二,将原来包含在“养育寄养家庭”中的“领养寄养家庭”[领养寄养家庭又分为普通领养寄养家庭和特殊领养寄养家庭。],在法律上明确分开。前者对儿童没有条件设定,单纯为了儿童的幸福成为寄养家庭,以养育儿童为目的。后者则以领养养子为目的,期待选择的儿童尽可能如己所愿,是为了养父母或者家庭才养育儿童。这样,根据所养育的儿童的属性不同,分为“养育寄养家庭”和“专业寄养家庭”,再加上“领养寄养家庭”和“亲属寄养家庭”,共计4类。
除以上法律制度规定的4类家庭寄养方式外,儿童福利院等机构还设立了“周末寄养家庭”和“假期寄养家庭”等灵活便利的形式,即利用周末或寒暑假的时间,将希望体验家庭生活的儿童委托给寄养家庭养育,通过将缺少家庭生活经验的儿童置身于温暖有爱的家庭环境中的方式,期待这些儿童可以形成正确的家庭观、世界观,并拥有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
(四)家庭寄养制度的实施体制和寄养家庭的支持体系
第一,家庭寄养的实施体制。在家庭寄养制度实施过程中,厚生劳动省设立的雇用均等·儿童家庭局负责对家庭寄养制度的实施进行指导和监督,责任主体为各都道府县的知事,具体落实由下设的儿童咨询所负责[8]46。按照法律规定,都道府县知事授权地方政府所属的儿童咨询所,具体业务由配属在儿童咨询所的“儿童福祉司”承担。流程为希望养育需保护儿童的家庭,在居住地的儿童咨询所提出申请,儿童咨询所经过资格审查的相关调查后,由都道府县知事认定,经儿童福利审议会审定并登记为寄养家庭,再经过与委托儿童沟通,儿童正式进入寄养家庭。
儿童咨询所在儿童福利制度实施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业务主要包括:①就儿童保护及其他与儿童福利相关的事项接受大众的咨询,并提供专业的指导;②寄养家庭的认定、登记事务;③寄养委托事务;④寄养指导与联络协调;⑤解除寄养委托关系等。儿童咨询所的所长负责寄养家庭的认定和指导监察,具体工作由配属在儿童咨询所的专职“儿童福祉司”落实。儿童福祉司经过特殊的训练和培训,同寄养委托调度员、寄养援助专业咨询员等组成小组,在相关支援机构的协助下,共同推动家庭寄养的开展。其主要工作有:授权对寄养家庭的认定;对需要保護的儿童安排家庭寄养;对儿童实施临时监护或安排家庭状况较差的儿童入住福利养育机构;对寄养过程进行指导、监察。
第二,家庭寄养的支持体系。与普通家庭以父母与孩子为核心的养育方式不同,在法律上,寄养家庭不是“私人”,在地位上属于“公共制度”的一部分。家庭寄养是国家、地方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基础上实施的养育,以儿童咨询所为中心,涉及到市町村、寄养家庭会、儿童家庭援助中心、社会养育机构、公益法人及非营利组织(NPO)以及需要保护的儿童对策协议会等形成的地区网络。官方的公益法人全国寄养家庭会(1971年厚生省设立),在全国都道府县及政令城市有分支机构66个,开展寄养家庭制度的调查研究、寄养家庭的开拓、针对寄养家庭以及被委托儿童的咨询指导等活动。2012年设置的“全国家庭寄养等推进委员会”,“为家庭寄养提供信息,提高养育知识和技术,也为儿童咨询所和寄养家庭支持机构提供信息,相互交换意见,共同支持寄养家庭”[8]47。另外,2008年家庭寄养支持机构被制度化,儿童咨询所业务中有关支援和招聘等内容允许委托外部机构,在支持寄养家庭方面,正在探索公共机关和地区进一步合作的模式。儿童福利机构中设“家庭寄养支持专业咨询员”,负责沟通和协调寄养家庭与机构设施之间的关系。家庭寄养支持机构设“家庭寄养推进员”。这些组织形成了对家庭寄养制度的支持网络体系。
除了儿童咨询所以及各种与家庭寄养有关联的组织支持外,在经济上,在将需要保护的儿童委托给寄养家庭时,政府会支付寄养补贴(仅限养育寄养家庭与专业寄养家庭)、养育儿童所需的一般生活费和其他费用。养育寄养家庭补贴为每名儿童每月9万日元;专业寄养家庭补贴为每名儿童每月14.1万日元。一般生活费包括伙食费、服装费等,对未满1岁的婴儿每月补贴60 390日元;对1岁以上的儿童每月补贴52 370日元[9]。另外,还有教育、就业、医疗以及通讯等其他补贴费用,根据实际情况由各地政府与国家承担。
二、日本家庭寄养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日本家庭寄养制度的现状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虐待儿童事件持续增加、儿童权利受到重视的背景下,日本积极推进家庭养育环境中的养育寄养家庭制度。特别是近年来在政策和法律中强调优先家庭养育的重要性,大力推进家庭寄养制度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从家庭寄养制度运用整体情况看,截止2021年3月,日本共有14 401户寄养家庭登记在册(同一家庭可重复登记分类项目),其中包括养育寄养家庭11 853户,专业寄养家庭715户,领养寄养家庭5 619户,亲属寄养家庭610户;利用家庭寄养制度的4 759户(同一家庭可寄养多名孩子),其中有3 774户选择将孩子委托给养育寄养家庭,171户将孩子委托给专业寄养家庭,353户将孩子委托给领养寄养家庭,还有565户将孩子委托给亲属寄养家庭,共计6 019名儿童入住寄养家庭[10]。
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07年的40多年间,需要保护的儿童数量稳定在3.5万人左右,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约九成的儿童在机构设施、一成的儿童在寄养家庭接受养育[11]。近年来,尽管受环境和政策的影响这种状况有所变化,家庭寄养委托率[家庭寄养委托率包括入住家庭屋的儿童,计算公式为:家庭寄养委托率=(家庭寄养+家庭屋)儿童数/(家庭寄养+家庭屋+乳儿院+儿童福利院)儿童数×100%。]从2010年的12%提高到2020年底的22.8%。入住乳儿院、儿童福利院的儿童数量虽有所减少,但其占比在社会抚养中仍在70%以上。目前,日本约有4.6万名需要保护的儿童,实际上接受儿童的寄养家庭约有4千个[公益財団法人全国里親会ホームページ,2023年4月26日,https://www.zensato.or.jp。],这表明由机构养育需要保护的儿童仍然是当前日本社会养育的主流方式,提高家庭寄养的占比是日本今后的重要课题。
日本各都道府县在家庭寄养运用上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2020年度福利行政报告显示,日本平均家庭寄养委托率为22.8%,其中20个都道府县的委托率在平均委托率之上,27个都道府县在平均委托率以下。新潟县新潟市的委托率最高,达58.3%,新潟全县平均委托率为40.6%;委托率最低的是宫崎县,仅为10.6%,新潟县的平均委托率约为宫崎县的4倍[6]。
从寄养家庭的属性看,综合复数调查结果显示,寄养家庭养父母的年龄都在50岁~60岁,半数都有亲生孩子,登记后到接受第一个儿童的时间约为1年半,约七成为核心家庭,八成住房为独立住宅[12]。
(二)日本推行家庭寄养制度存在的问题
纵观日本家庭寄养制度70多年的发展史,既有鼎盛期也有低落期,目前家庭寄养率有了一定增长,但需保护儿童接受机构设施养育仍占主要地位。这种状况与制度运行存在的问题分不开,也与社会对家庭寄养制度认识上存在不足有关。
1.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日本家庭寄养制度创建之初,对寄养父母的资格设定为有产者和有经济实力的慈善家,而将普通人排除在寄养家庭之外。直到1987年才在《寄养家庭等养育家庭运用纲要》中改变了这样的理念,扩大了寻求寄养家庭的范围,培养普通人成为优秀的寄养家庭父母。然而,对寄养家庭的固有观念使得人们对成为寄养家庭望而却步,进而影响了其登记数量的增加。
其次,在经济高速增长结束、追求福利国家的政策面临重新评价、压缩福利方面财政支出的背景下,“日本式福利社会论”甚嚣尘上,提倡有效利用民间力量参与福利服务,遂将家庭寄养的承担者定位为志愿者,将促进家庭寄养事业委托给全国寄养家庭会,以此来缩小公共部门的责任和负担,导致家庭寄养制度应用处于被放置的状态。
最后,无论在《儿童福利法》还是《寄养家庭养育运营纲要》中,都没有明确机构设施、家庭寄养、领养等儿童福利中社会福利应有的方向。特别是日本虽然也强调家庭养育的重要性,但在机构设施养育还是家庭养育上态度暧昧。这既是儿童福利发展方向的问题,同时也忽视了家庭养育有利于培养儿童在体验正常的家庭生活过程中增加对家庭的理解,为其将来组建家庭奠定良好基础,这是在机构养育中难以达到的。
2.社会认知度低,存在“不解”甚至“误解”
家庭寄养制度在日本民众中的认知度低于预期。人们对家庭寄养大多停留在仅听说过或部分了解的程度上。对1万名调查对象的调查结果显示,有20.6%的人表示完全不了解家庭寄养,41.2%的人表示只听说过这个词,31.6%的人了解部分内容,非常了解的人仅占6.6%。超六成以上的人对家庭寄养处于“不了解”的状态[13]。较低的知名度无疑阻碍了家庭寄养制度的广泛推行。
日本民众对家庭寄养存在相当程度的“误解”。第一,因没有正确认识家庭寄养,产生了与“领养”[日文原文为“養子縁組をする”,即建立法律上的亲子关系,与本论文讨论的“家庭寄养”不同。]制度的混同。领养养子是传统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的习俗,以维持家业经营和保障家系延续为目的,养父母与养子需要建立法律上的亲子关系,人们通常会从同姓近亲中收养养子以保证家业永续[14]。家庭寄养制度中的“领养寄养家庭”与民法修改法案的相关内容保持了统一,同时也是为了应对现实中通过寄养实现领养需求的增加。除此之外,家庭寄养中养父母与需要保护的儿童在法律上并不构成亲子关系,而且儿童在寄养家庭中生活一段时间后,经过儿童咨询所等机构的研判,可能会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或进入相关机构养育,即家庭寄养中的养育关系是暂时性的,而非永久性的。然而,上面的同一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将“家庭寄养”视为收养养子的占30.4%。第二,在民俗中,将表示寄养儿童含义的“里子”与表示抱养含义的“貰い子”混同。“貰い子”与“里子”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但“貰い子”一直有榨取儿童、保障劳动力的负面印象,这种负面印象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认知,也成为家庭寄养不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里子”指委托他人代养的孩子,目的是为了让孩子不变的柔弱而健康成长。“貰い子”更多是为了“家”的延續保障劳动力。如一些地方作为农村家庭被迫减少抚养人口的手段,让孩子作为劳动力到渔村家庭建立拟制亲子关系。参见坂井摂子.近代日本の里親慣習[J].現代社会文化研究,2009(44):55-72.]。第三,不少人将需要保护的儿童与有各种问题的儿童划等号,在上述调查中如此认为者占27.9%。事实上,接受社会抚养的需要保护的儿童中,45.2%的儿童是受亲生父母的虐待、亲生父母拒不履行抚养义务或被抛弃的受虐待儿童,15.6%的儿童是由于亲生父母患有精神疾病无法履行抚养义务,12.7%的儿童则是因为父母一方或双方处于死亡、行踪不明、监禁或卧床状态[10]。
3.普通民众对成为寄养家庭的愿望不高
从民众角度看,日本民众对于成为寄养家庭的意向普遍不高。他们对养育没有血缘关系的儿童在认识上与推进社会养育的目的存在差距[对于家庭寄养制度发展业绩不佳,许多研究成果认为其障碍在于日本重视血缘关系的国民性,即国民对养育没有血缘关系的儿童有抵触情绪,以及对没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和子女存在偏见与歧视。参见庄司順一.フォスターケア里親制度と里親養育[M].明石書店,2003:68; 網野智,など.里親制度及びその運用に関する研究[G].日本子ども家庭総合研究所紀要35,181-208.],而且对需要保护的儿童实施社会养育在儿童健康成长和人生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了解甚少。另一方面,欧美国家基于实现儿童福利的理念养育非血缘儿童的情况较多,但日本在传统血缘文化因素的影响下,阻碍了民众成为寄养家庭的意愿。调查显示,愿意成为养育寄养家庭的人不足一成,不愿意的约占七成,还有二成人表示无法回答[13]。因为缺乏家庭养育对儿童成长重要性的理解,人们将对家庭养育的关注聚焦到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上。据调查,阻碍人们成为寄养家庭的因素主要有“出于经济上的担心(47.6%)”“因为会左右孩子的人生,感觉责任重大(42.3%)”等[13]。人们更多地考虑对个人利益的影响,较少从儿童成长角度认识家庭寄养制度。
2021年,在5 785.5万户日本家庭中仅有14 401户登记成为寄养家庭。同年,日本有需要保护的儿童约4.2万人,实际接受寄养家庭养育的儿童数量为6 019人。于是许多登记在册的寄养家庭,一直没有被委托的儿童入住,处于等待委托的状态。但根据《社会养育新愿景》报告书中提出的“未满3岁儿童在5年内、学龄前儿童在7年内其家庭寄养率达到75%以上,学龄后儿童在约10年内家庭寄养率达到50%以上”[6]的目标以及需要保护儿童总数来看,日本現有的寄养家庭数量远远不够。在开拓新的寄养家庭的同时,需要制定解决等待委托问题的对策,寻求寄养家庭供给和需求的有机结合。
三、日本政府推进家庭寄养制度发展的措施
制度运行存在漏洞、社会认知度偏低、寄养家庭数量不足等现实表象下折射出的其实是理想与现实、国家与国民、政策与实施之间存在的差距。然而,日本政府对于上述问题绝非无知无觉。厚生劳动省曾对日本家庭寄养制度的利用状况指出:“就目前而言,全国平均家庭寄养委托率仍不到二成;其增长进度缓慢,每年只有1%左右;各自治体之间差距巨大。”[15]为此,日本政府在不断完善儿童福利相关法律的同时,从制度改革、扩大宣传、完善支援体系等方面入手,为破解困局做出了诸多努力。
1.扩大寄养父母的招募范围,落实家庭寄养优先原则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改变只有慈善家和有产者才能成为寄养父母的理念,这意味着在保障需要保护的儿童健康成长的前提下,更多普通人被纳入寄养父母的后备军。但因选择成为寄养家庭的动机[希望成为寄养家庭的动机可归纳为几种,分别为:宗教信仰;帮助受虐待儿童等社会责任意识;自身有同样的经历;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没有亲生子女,想抚养孩子。参见貴田美鈴.里親制度の史的展開と課題:社会的養護における位置づけと養育実態[M].東京:勁草書房,2019:288.]不同,在寻求扩大寄养家庭过程中,根据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做法, 避免“一刀切”。为增加寄养父母的数量和提高养育质量,加强儿童咨询所的寄养家庭养育综合支援业务[指制度的宣传、寄养父母的招聘及考察、寄养家庭登记前后的培训及委托后寄养父母的研修、寄养父母与儿童间的协调、对接受儿童的养父母的帮助、结束寄养后的支援等一系列支援家庭寄养的工作。]能力,探讨将该综合支援业务委托给社会福利法人和NPO法人等民间机构,并通过登记体验性的周末、季节寄养家庭,增设临时保护寄养家庭、专职寄养家庭等新类型寄养家庭。
日本政府在《儿童福利法》修改法案(2016年)中确立了家庭养育优先的理念,明确将家庭寄养放在社会养育的首位。在落实上,政府进一步对家庭寄养制度进行了改革完善,例如:规定儿童咨询所的职员须接受各种培训来提高职业素养,以为民众提供更高质量的专业化服务;优化业务办理流程,有计划地推进调查、保护、采取措施与支援管理工作的职能分离,消除寄养工作举措的协调不到位问题;为进一步落实家庭寄养优先原则,原则上不再安排新认定的需要保护的学龄前儿童入住养育机构等[6]。在向家庭寄养渐进过渡的同时,充实儿童咨询所等支援家庭养育的各种社会资源,构建将设施从业人员纳入到帮助寄养家庭的支援体制。
2.加大宣传力度
除了利用地方报纸、政府网站、电视广告等常见的宣传方式外,还在街头或活动现场分发宣传手册,举办说明会或寄养家庭体验发表会,与本地企业、大学、社区等合作,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16],提高人们对于家庭寄养的认知度,重视通过宣传改变人们对家庭寄养的错误认知与刻板印象,消除对该制度的担忧与戒备,让人们认识到,家庭寄养是应社会要求对不能在家庭成长的孩子采取的代替养育措施;重视民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减少人们对成为寄养家庭后在经济、生活、工作等方面的担忧;更重要的是,让人们了解家庭环境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认识到营造整个社会帮助儿童成长的环境、构建齐心协力互相帮助的社会支援体系,对应对少子化问题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3.提高经济补贴,完善支援体系
经济原因是阻碍人们成为寄养家庭的首要因素。因此,减轻人们对寄送费用的担忧是推进家庭寄养制度的必行之策。对此,日本政府曾多次提高寄养补贴金额。例如,2009年之前养育寄养家庭补贴为每名儿童每月3.4万日元,专业寄养家庭为9.02万日元;2009年4月起养育寄养家庭补贴倍增至7.2万日元,专业寄养家庭补贴也大幅增长到12.3万日元;随后补贴金额又在2018年、2022年两度上调。此外,日本儿童支援协会与多数地方政府还会为寄养家庭提供免费保险,以防因意外产生额外的经济损失。
与此同时,解决家庭寄养问题绝不能仅局限于制度本身,相关支援体系的完善、其他养育方式的跟进与政府的支持同样不可或缺。因此,应建立以市町村为单位的儿童家庭支援体系,如《社会养育的新愿景》强调推进被委托儿童和被领养的养子能自然地融入地區社会的措施,指出在地区社会中,要树立接受家庭形式的多样化意识、把别人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作为地区整体的孩子培育的意识,有必要开展教育和启发活动;尽快成立集招募、培训、支援等职能于一身的寄养(Fostering)支援机构;优化领养相关法规,推进领养事业的加速展开;5年内创设由专家组成的、对社会抚养机构进行评估的专业评估机构;10年内实现养育机构的小规模化(最多6人)与地区分散化,且机构中常驻2人及2人以上职工;同时,国家将为上述计划的实现确保最大程度的预算支持[6]。
结 语
日本的家庭寄养与机构养育共同承担了对需要保护的儿童的社会养育任务。家庭寄养经过二战后保护战争受害儿童的需要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在1958年达到最高值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直处于低落状态,20世纪90年代日本虐待儿童问题日益深刻,重视儿童权利压力增大,以此为背景,实现了由以机构养育为主向家庭寄养养育优先的政策转向,落实以儿童的健康成长为出发点,以将其培养成个性丰富、人格独立的成人为中心思想的养育理念,为需要保护的儿童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然而,普通民众对该制度的不解甚至误解所导致的,如对成为寄养家庭敬而远之、对利用寄养家庭制度瞻前虑后、现有寄养家庭数量不足等问题,也是日本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真切现实。为此,日本政府采取了加强宣传力度、改革现有制度、完善支援机构、保障预算支持等诸多策略以摆脱当前困境。
需要认识到,即便日本《儿童福利法》确立了家庭养育优先原则,也并不意味着家庭寄养是所有需要保护儿童的最优解。家庭寄养作为社会养育方式的一种,与机构养育并非二择其一的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取长补短的合作关系[17]。因此,在涉及需要保护的儿童的问题上,应始终以儿童福祉为出发点,秉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既要避免陷入寄养、机构还是领养的机械排序之中,又要警惕对家庭寄养委托率的盲目追求。
[参考文献]
[1]児童福祉法研究会.児童福祉法成立資料集成:上巻[M].東京:ドメス出版,1978.
[2]網野智.里親制度の運営について 2 [J].社会事業,1948, 31 (11/12):30-36.
[3]櫻井奈津子.施設養護と里親制度[M]//北川清一.新·児童福祉施設と実践方法養護原理のパラダイム.東京:中央法規出版,2000:179-192.
[4]貴田美鈴.里親制度の史的展開と課題[M].東京:勁草書房,2019:280-281.
[5]貴田美鈴.里親制度における政策主体の意図:1960年代から1980年代の社会福祉の政策展開に着目して[J].人間文化研究,2007(8):83-97.
[6]厚生労働省.新しい社会的養育ビジョン[EB/OL].[2022-10-20].
https://www.mhlw.go.jp/file/04-Houdouhappyou-11905000-Koyoukintoujidoukateikyoku-Kateifukushika/0000173865.pdf.
[7]厚生労働省子ども家庭局.里親養育包括支援機関(フォスタリング機関)及びその業務に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EB/OL].[2023-01-20].https://www.mhlw.go.jo/content/000477823.pdf.
[8]金洁.日本家庭寄养制度[J].社会福利,2016(4):46-47.
[9]厚生労働省.里親制度(資料集)[EB/OL].[2022-10-10].
https://www.mhlw.go.jp/content/000998011.pdf.
[10]厚生労働省.社会的養育の推進に向けて(令和4年3月31日)[EB/OL].[2022-10-10].https://www.mhlw.go.jp/content/000833294.pdf.
[11]園井ゆり.里親養育の必要性と新しい家族としての養育家族[J].活水論文集,2010(53):19-40.
[12]厚生労働省雇用均等·児童家庭局.児童養護施設入所児童等調査結果の概要[EB/OL].(2009)[2022-11-10]. https://foster-family.jp/data-room/stock-file/200907korosho-nyushojido-chosa-H2002.pdf.
[13]日本財団.「里親」に関する意識·実態調査報告書[EB/OL].[2022-10-15].
https://nf-kodomokatei.jp/wp-content/uploads/2020/12/satooya2019.pdf.
[14]聂友军.收养养子习俗与传统日本伦理观[J].日本研究,2017(1):67-73.
[15]厚生労働省.都道府県社会的養育推進計画の策定要領[EB/OL].[2022-10-20].https://www.mhlw.go.jp/content/000477822.pdf.
[16]厚生労働省.都道府県等における里親等委託推進に向けた個別項目ごとの取組事例[EB/OL].[2022-11-02].https://www.mhlw.go.jp/content/000763042.pdf.
[17]全国児童養護問題研究会.「新しい社会的養育ビジョン」に対する意見[EB/OL].[2022-11-10].http://youmonken.org/vision.pdf.
[責任编辑 孙 丽]
An Analysis of Japanese Foster Care
JIANG Xinxing, CHANG Mengfei
(School of Japanese Language,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The foster care system in Japan has began since 1948. After World War II, with the end of the project of protecting war-victimized children, it went into recession. After 1990s, influenced by the double pressures of international emphasis on childrens rights and children abuse becoming a social problem in Japa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the priority principle of foster care when implementing social care for children who are in need of protection.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foster families. The main body of its implementation is composed of prefectures, childrens welfare centers and various support institutions. In recent years, although the foster care entrustment rate in Japan has increased steadily, the progress is still slow. In the process of actual implementation,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low popularity, confusion with “adoption”, low intention to become foster families and insufficient foster families. Therefor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proposed solu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reforming the system, expanding publicity and improving support.
Key words: foster care system; foster families; aid-requiring children; childrens welfare; social nurtu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