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遂平妖传》到《天书奇谭》:古典小说重构与现代情理呈现
庄亮亮 彭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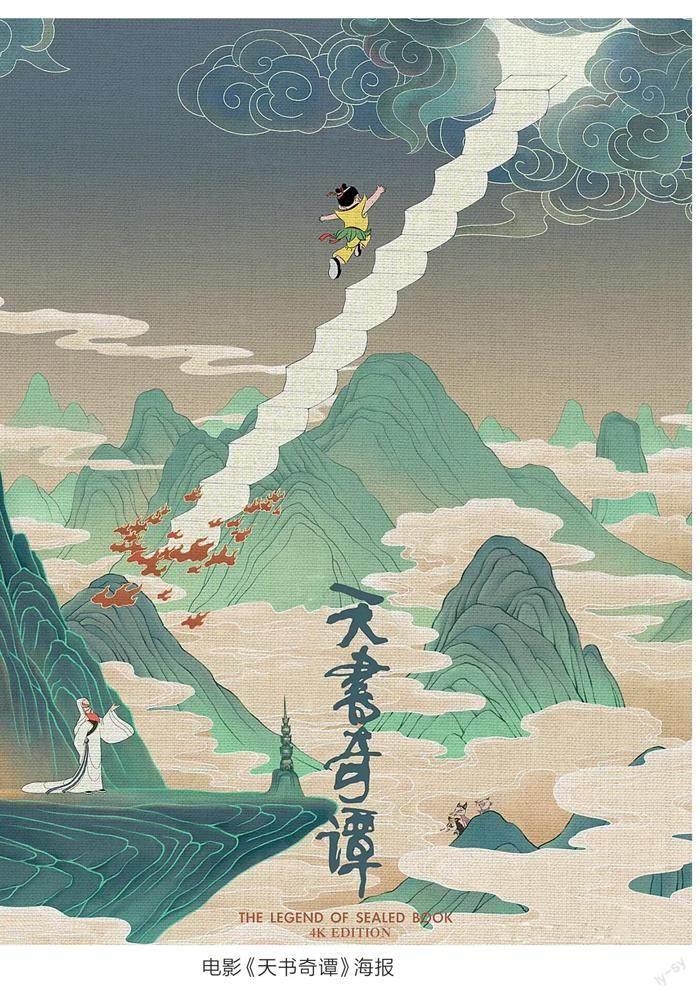
由王树忱、钱运达导演,包蕾、王树忱编剧,柯明担任造型设计,中国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83年出品的动画电影《天书奇谭》取材于罗贯中编次、冯梦龙增补的《三遂平妖传》。2021年11月5日为让观众重温经典,经高清修复而成的《天书奇谭4K纪念版》如期重映。该电影的成功源于对古典小说深厚文化内核进行了吸收与表现,并对小说的人物、情节进行了大胆的重构。不仅如此,基于现代价值观念的传输与给予受众群体的正确导向的要求,电影对小说的道德价值取向作出了新阐释,即美丑认知、自我与社会、情感与道义的引导与思考,最后电影打破题材的局限性对现代人类的困境作出了深刻揭示。
一、人物形象与情节的重构
电影《天书奇谭》以因袁公偷阅载有108条法术的天書,为造福世人将其刻在人间石壁,由此而触犯天条受到责罚为开端。其故事情节主要是狐精偷食仙丹幻化人身,并以妖术蛊惑人心为害生民,之后袁公指导蛋生习得天书法术与狐妖争斗并获得成功。从情节与人物关系上看,《天书奇谭》中的人物群体主要划分为三类:妖精、仙人、凡人。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主要遵循反权威与扁平化处理。不仅如此,电影为了文本化到视觉化的成功呈现,别出心裁地选用中国古典的戏剧脸谱来展现鲜明的人物性格,而这样的处理就必须对《三遂平妖传》中原本的人物行动与语言进行重构。
(一)人物的重构与性格表现
《天书奇谭》中对于仙人的刻画,以玉帝、袁公、习得仙法的蛋生为主要代表。首先《天书奇谭》将玉帝的形象从《三遂平妖传》的理智正义重构为昏聩享乐的特权阶级形象。如玉帝在《三遂平妖传》中对袁公私带天书下凡的做法进行评价时说:“这如意册乃九天秘法,不许泄漏人间,只因世上人心不正,得了此书必然生事害民,那畜生兽心未改,有犯天条,不可恕也!”[1]体现出玉帝作为三界之主对于生民生存的怜悯与担忧。但在《天书奇谭》中,玉帝边吃果子边说:“你偷取天书下凡,私刻于石壁,泄露天机,该当何罪?”在得到北斗星君求情之后,仍旧边吐果核边罚袁公,成了不问事由、缺乏决断且举止轻浮的上位者形象。因此,玉帝在《天书奇谭》中呈现出的脸谱由灰与白的两色组合而成。白色具有粉白与油白之分,具有奸诈多疑或年长的特征,另外再有灰色的加入塑造出玉帝年老昏聩的戏剧形象。
《天书奇谭》中袁公的形象也得到较大的改变。《三遂平妖传》中的袁公由白猿得道升仙而成,性情虽有改变,但仍存有猴性。小说中他不但觊觎仙桃,而且是为了见识箧中妙物而私阅天书。得到天书后心下大喜:“只此一书,够我老袁受用矣!”[2]可见其盗取天书多受顽皮天性与私欲的影响。而电影《天书奇谭》中的袁公虽亦是受好奇驱使而私阅天书,但如意册上书“天道无私,流传后世”,让袁公意识到将如意册流传到人间具有正义性。而往后指导蛋生习得天书也是出于对狐妖打击以及天书流传正义性的考虑。因此《天书奇谭》中的袁公是绝对正义仙人的化身。电影在视觉呈现上袁公形象的描绘采用了“武净”关羽的脸谱:红色的络腮胡须,一双细长的丹凤眼,两道红眉斜插入鬓,脑门上则勾画了一个“文净”包公式的、象征着刚正不阿的“月牙”。红色的脸庞和白色的衣物,象征“忠义”和“清白”。[3]
电影对蛋生的形象进行了更大的颠覆与重构。在《三遂平妖传》中的蛋生是从蛋里出生,因养在寺里而成了蛋子和尚。蛋子和尚多次盗取天书,最终如愿以偿,并在狐妖圣姑姑的帮助下修炼天书法术。在此过程中竟稀里糊涂地与狐妖为王则的造反提供了一定的助力。虽然最终化身诸葛智遂帮助文彦博赢得了战争,但与电影《天书奇谭》中的人物形象差异较大。《天书奇谭》中的蛋生以一个小孩的形象出现,自始至终天性良善、心怀百姓。同时,蛋生始终站在狐精的对立面。唯一有较大关联的是狐精的天书确实取自于蛋生,不同的是在小说中叙述成主动共享,电影中改编为被动偷抢而来。蛋生形象重构成小孩,这是受到观众群体的影响,只有主角以观众群体接受的年龄形象出现才能更加贴近受众。该片主角蛋生继承了袁公的意志,敢于和邪恶作斗争,因此在蛋生的戏剧脸谱的额头上同样出现了“月牙”标志来作为蛋生具有正义基因的标志。除此之外,蛋生圆脸与红晕的设计也让蛋生增添了一份可爱与活泼。
三个狐妖的形象取自《三遂平妖传》中的圣姑姑、胡黜(左黜)、胡媚儿(胡永儿)。对于狐妖的形象,《天书奇谭》之中将其直接化为恶妖与绝对反派,并用奸、丑、旦三绝的京剧脸谱来勾画三妖奸邪、滑稽、魅惑的妖精形象。但在《三遂平妖传》的狐妖形象塑造过程中,并没有绝对恶化狐妖,只是在故事情节中不断地推进狐妖形象的转化。如圣姑姑在狐儿胡黜因中箭瘸了之后,听取子女会有祸端,应当修道的建议,开始带着胡黜与胡媚儿求神问道,并且还训斥了胡黜报复的想法。另外,圣姑姑还因为欣赏永儿的善良心性(实是圣姑姑之女)私授其天书,以帮助员外一家渡过生活上的难关。被圣姑姑授予天书的胡永儿对老实的卜吉有眷顾之心。这些都体现出狐妖一族虽为妖物却怀有人性与道义之心。这与电影中绝对奸诈的角色演绎有所出入。
凡人的形象在电影和小说中都有比较丰富的展示。从百姓、僧侣、道士一直到官员都有涉及。不过电影中对小说中的凡人形象做了打散、重装处理,如小说中发现蛋生、埋蛋生、养蛋生慈长老全都参与了,而在电影中做这些事情的分别是和尚、狐精圣姑姑和老妇人;电影中两个针锋相对、互争钱财以至斗殴的和尚在小说中的原型有二,一是好色的贾道人师徒,二是矛盾丛生的慈长老和他的弟子们。此外,电影中的任性、昏庸且行动像陀螺的小皇帝形象表面上是虚构的,因为小说《三遂平妖传》中的时间定位是宋仁宗年间,彼时仁宗是成年且被认为是圣明的君主。但细细考察这个昏庸滑稽的小皇帝,其原型很可能是起兵造反的王则,他无勇无谋全赖妖法且小胜之后纵欲无度、为政不仁。从小说与电影的人物的对比中看到,不论是小说中的凡人胡员外、贾道士师徒、贪污县官、错判冤案的郑州知州,还是电影中的财迷奴才样的县令、像个不倒翁滴溜转着眼珠的府尹大人、像陀螺般的小皇帝,都流露出人性的贪婪、狡诈、自私、愚昧等品行。在凡人形象的戏剧化中,《天书奇谭》中的“县官”是典型的丑角,其脸型设计采用了京剧中的文丑脸谱。为了达到“尖嘴猴腮”的吝啬低劣面相,县官的脸型被夸张成倒三角形,眼部的设计采用欧洲马戏小丑的“十”字形眼妆,把“县官”的愚蠢可笑刻画得入木三分。为讽刺县官的贪财如命,其帽子左右的乌纱翅也被夸张成两枚铜钱形状。[4]
(二)情节的重设
电影《天书奇谭》取材于古典神魔小说《三遂平妖传》,也正是因为神魔小说的受众大多是有一定阅读能力且心智较为成熟的成年人,所以小说情节以及用语设计都较为大胆。如第十回的石头陀夜闹罗家畈时杀人取胎血,第二十回时员外杀胡永儿等都刻画出较为血腥的场面。这些场面不适宜出现在主要以少年儿童为主要受众的动画电影里。因此,电影需要对《三遂平妖传》中的情节进行一定的借鉴与改造。
首先,对主线尽可能地保留。小说中以圣姑姑、胡黜、胡媚儿三只狐精的活动为主线。在这个主线下又主要突出圣姑姑的修法与胡媚儿的魅惑之事,以及转生成长。同样,在电影里狐精们以大反派的形象出现,故事脉络也是主要围绕着这三只狐精修法、起祸,最后被剿灭的线索推进。不过,小说篇幅毕竟达到四十回,如若在电影中全部体现是完全不可能的。对于《天书奇谭》来说,即使只对《三遂平妖传》中一个完整主线进行介绍都很困难,因此在保留主线的基础上,需要对主线中的三只狐妖的各条线索进行剪除。如胡媚儿转生胡永儿,以及胡永儿的成长结局这些全部剪除;关于胡黜个人在小说中的全部戏码也做了删除。不过,《天书奇谭》为了刻画胡黜贪吃的丑角滑稽形象,特意安排了其偷吃鸡被店小二与厨师追赶的桥段。总的来说,电影主线在尽可能地保留小说脉络的要求下,将狐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叙述,并剪除了不太必要的个人事件。
其次,对副线进行修改和删除。小说中副线也有主、次之分。主要的副线是以蛋子和尚的成长、修道、助战为脉络,另外还杂以当时朝廷官员之间的忠奸斗争,白猴袁公、道士张鸾等较为独立的线索。但不管如何,这些线索如若在电影中加以体现的话就没有必要。因此,电影当中事件社会背景的展示直接被抹去,袁公的升仙也不需要交代,并且直接删掉道士张鸾这个角色。对于主要的副线蛋子和尚的成长及其过程也直接进行修改,将由人抚养长大直接变为蛋中生出,吃了仁慈老妇人的饼之后立马长大成人。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蛋子和尚与狐妖存在关系上的“暧昧”,配合圣姑姑的谎言,默认做了其转世的弟弟。蛋子和尚击杀石头陀等也做了删除。这样处理的目的是为了主线与副线之间能够较快地产生关联,从而推动电影情节的快速发展,即完成矛盾的迅速激化。
最后,情节修改与套用来突出矛盾。在小说之中,蛋子和尚与狐妖的矛盾实际上被弱化了,甚至在蛋子和尚化身诸葛智遂之前,他与狐精并没有实质上的矛盾。蛋子和尚的主要矛盾,可能来自于包拯。电影中对于蛋子和尚的矛盾彰显做出了必要的修改。从对包拯的不满转嫁到狐精身上,且这种不满主要是出于正邪对立而言。电影中狐妖灭蝗求雨哄骗百姓,被蛋生揭露且施法灭蝗,最终求雨成功。其实这是借鉴并修改了小说中第十七回博平县张鸾祈雨五龙坛左黜斗法的事件。这样做只是为了突出蛋生与狐精的矛盾,让电影在冲突中更好地发展开来。
电影对于小说情节的修改与创新,其目的是更为清晰地将主线与副线在电影中铺设开来,并且在较短的电影时间中让故事叙述达到冲突的高潮,以推动故事的进一步发展。除了电影本身的需要,也应当关注到较为简单的故事叙述,即更加有利于受众察觉到电影情节背后所要传达出来的情理与道德价值观。
二、价值观的引导与生存隐喻
四十回本的《三遂平妖传》成书过程较为崎岖,其大致成书时间是在明代时期,且神魔小说的直接受众大多为成年人。在这样的定位下如果以力求复原《三遂平妖传》中原本故事的原则来拍摄《天书奇谭》,那么所显示出来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与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自然会产生较大出入。如蛋子和尚多次偷盗天书的行为,以及小说中较为明显的忠君价值观念等。因此,《天书奇谭》通过对人物与情节上重新取舍与构造,以传递出更加适合现代价值观的影视作品,对青少年儿童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除此之外,该电影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更是在其故事性、趣味性背后所传递出的对人类生存困境的隐喻。
(一)现代价值观
美丑的思考。动画电影需要利用丰富的色彩、精美的动画人物设计来满足受众对画面审美的需求。电影《天书奇谭》同样如此,江南市井与山水的描画、京剧脸谱等的运用都增加了美感。除此之外,人物形象还传递出强烈的美丑对照。电影中的基本做法就是丑化反派角色、美化正义形象以达到强烈的美丑之分,以外在形象来标识内心好坏。不过,电影中为了给予观众更多的思考空间,也同样做了美丑对照的深刻呈现。如美丽缺祸害百姓的小狐妖与老而善良的老婆婆之间的强烈对比,其目的就是让受众去思考何为真美。
自我与社会。这是电影中主要的思考点,也是电影价值观输出的主要意义。在《平妖传》中盛行个人利益为主的观念,袁公与蛋生两人在小说中的各种行为都是受制于个人的私利。电影中抛弃了游离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摇摆人物形象,直接取用社会价值取向来作为正义的一方,突出在自我私欲与社会利益之间,社会利益的重要性。如电影中的袁公盗天书是为了帮助世人,蛋生盗学天书也是为了帮助老百姓,因而被划为正义的一方。相反,狐精三人所学道法全是为了满足他人私欲的同时,实现自己私欲,全然不顾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同时,贪玩任性的小皇帝、贪婪精明的府尹、欲望不断的县官都是因为过度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成为电影中的反面角色。因此对观众所传达出来的形象就是舍己为人、不顾个人安危的正义英雄,而这也是电影对受众价值的主要输出。
情感与道义。除了自我与社会的价值取向外,电影《天书奇谭》还有一处点睛之笔。那就是作为师傅的袁公被天神用铁索绑走、弟子蛋生含泪呼唤的场景。这个场景让很多观众产生情感共鸣,也成功地令观众代入到电影中去。而这里,电影传达出来的是对道义较为“悲剧”结局的痛惜,以及师徒真挚情感的感动。师徒之情的真挚在小说之中也有所体现,不过是蛋子和尚对慈长老的感情,但這份感情远没有电影中刻画得那么动人。电影中对于师徒情感,以及道义的“悲剧”结局的刻画,是用悲剧的情感氛围来烘托道义的伟大,让观众对于这样的道义坚持更加钦佩,从而影响观众的价值认知与道德取向。
(二)人类困境的隐喻与救赎
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汉语又译为“解围之神”“机械送神”等,拉丁语字面含义为从机械而来的神。在古希腊喜剧舞台上,当剧情发展陷入僵局时,就会用机械装置降下一个神祗来改变事态或解决问题。这种通过外在手段推动剧情发展的方式,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遭到相当大的诟病。电影《天书奇谭》中最后也是袁公的出现完成了对狐妖的收服。袁公就成为该电影显而易见的“降神”。那么,袁公的降神是否只是为了解决情节冲突中无法纾解的矛盾,而以牵强的情节推动着存在呢?其意义自然远不止于此,基于小说《平妖传》基础上的改编,电影在人性立体刻画上不如小说来得真切,但在作品中却传达出了较小说更为深刻且宏大的主题,即机械降神的终结后的人类的生存困境。
许多的观影者将电影中的袁公称为现代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或是“西西弗斯”。而袁公所带下凡间的就是人类所需要的“火种”——天书,借以解决人类生存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但袁公私授天书于蛋生并没有得到其预想的结果,反而被狐妖一类滥用,成为他们牟利的工具。
电影《天书奇谭》中人类的生存困境主要是两个层面,即人类基本生存需求的困境与人类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冲突所造成的困境。人类困境的哲学探讨是复杂的,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指出的是人类在当代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人口剧增、环境冲突尖锐、资源减少、社会分裂、区域对抗等。另外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唯意志论、存在主义的生存理论、弗洛伊德学说、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美国未来学说的极限理论等,也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揭示了现代的“人类困境”。电影题材的选取自然无法涵盖如此多的人类生存困境问题,不过电影同样指出了人类生存与社会内在矛盾问题的基本本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其一,人与自然冲突。电影中的人类在遭遇严重蝗灾时,面临了粮食危机。另外,人类与狐的沖突也是人与自然冲突的另外一面。虽然狐妖依靠人类不断获得更好的待遇,但狐妖待遇的获得是依靠牺牲部分人类的利益,归根到底是生存权、生存资源的争夺。《人类处在转折点上》一书指出“人类好象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量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料危机等等……这场全球性危机程度之深、克服之难,对迄今为止指引人类社会进步的若干基本观念提出挑战。”[5]而袁公盗取天书的一大目的就是希望天书能够最大程度改变人类生存环境,减少自然对人类生存空间的挤压。蛋生也确实使用天书上的法术对抗了自然灾害,完成袁公的最初设想。但天神对人类的赋能影响并非如此美好。
其二,人类社会分裂。电影在很大程度上比小说更具讽刺意味,并且将讽刺对象直指统治阶层。统治阶层与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行为品德的强烈对比,恰恰反映出社会分裂的基本状态。电影中人类社会所给予人类的生存困境远比自然带来的更为严重,蛋生所学的法术足以应付人类的温饱问题,不过更多的作用是为了对抗满足人类贪欲而使用的狐妖法术。不难看出,袁公的天书造福人类的设想的最大障碍恰恰就是人类自身。
另外,电影最终揭示出的是机械降神终结后的人类困境。以上所说的人与自然冲突、人性的两面以及社会阶层的划分等问题,是电影机械降神时就已经存在的问题。但电影在机械降神的事件(袁公回到天庭)终结后,使得这样的人类生存困境更加复杂多样。究其根本就是神对人的赋能,而这种赋能只能被少数人所掌握。少数运用手头的天神赋能,完成对人类社会大部资源的占有,也因此造成阶级变化以及阶级矛盾的不断加深。天神赋能又在某一程度上提升人类社会运用客观规律的能力,与自然矛盾也开始加重。征服自然成为人类验证自我能力的重要方式,而自然的范畴有时候也包括人自己造就的“神”。弗朗西斯·培根用“知识的力量”这一“伟大的工具”取代了上帝的神性和权威,人类无需以上帝的权威来维持人类对自然界的统治,人类只需凭借知识和理性力量就足以征服自然界。但正如玉皇大帝对于天书禁止下凡危害的预见一样,近代哲学对于人本身的抬高并没有让人类完全凌驾于自然,相反还遭受了自然的反噬,把人类推进更深的困境。因此,在电影结尾,袁公虽然以机械降神的方式扭转了剧情发展,但天神的特殊赋能仍旧留在人间。这不得不引起思考,随着人类的发展,这样的赋能是拯救人类摆脱困境还是让人类进入另一种由人类社会自身矛盾所带来的更深的困境呢?
结语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评介:“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6]鲁迅对于《聊斋志异》的评价同样适用于《三遂平妖传》及其改编而来的《天书奇谭》。所有的狐鬼精魅其实都是人,或者说人性幻化,欲壑难填的凡人终会受到妖心的影响。当然,这样的人妖关系非一部电影可以传达给青少年的,因此电影通过对《三遂平妖传》中的人物与情节的借鉴与重构,影响着青少年观众对于正义、权威、美、丑、情感的正确认识。假使当年观影的小孩长大后读到《三遂平妖传》,将会更加明白电影中那些滑稽与奇特对话传递出来更深的价值批判,即人类生存困境的揭示。
参考文献:
[1][2][明]罗贯中,冯梦龙.平妖传[M].南昌:豫章书社,1981:7,8.
[3][4]田建伟.中国戏曲脸谱对民族动画造型设计的影响[ J ].艺术评论,2011(02):74-77.
[5][美]米哈依罗·米萨诺维克,[德]爱德华·帕斯托尔.人类处在转折点上[M].刘长毅,李永平,孙晓光,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9.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47.
【作者简介】 庄亮亮,男,福建福清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诗赋理论研究;
彭 健,男,贵州大方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唐宋元文献与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