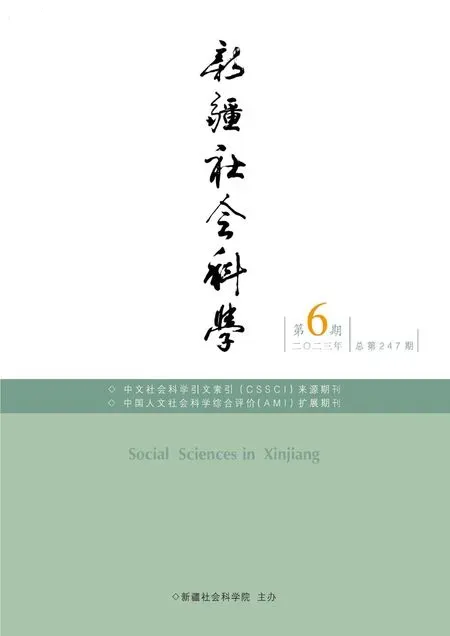数字经济下的共同富裕:机遇、挑战与应对*
谢宜泽
内容提要: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同向而行。一方面,数字经济扩大了经济增量和就业空间,通过增效赋能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优化了经济存量,为共同富裕奠定了更充裕的物质基础,提供了更多元的收入分配渠道;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受到数字技术和数字治理水平的制约,而且数字经济的发展仍不平衡不充分,同时它也在创造新的收入不平等,使广大低技能劳动者遭遇结构性失业风险。为加速数字经济时代的共同富裕历史进程,应集中力量攻克核心数字技术,全面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规范数字经济发展,按照共同富裕的实践要求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全方位强化数字教育,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加速弥合数字技能鸿沟,全面释放数字红利。
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快速发展,人类社会正在朝着数字经济的方向加速演进。面对这一不可逆转的时代大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6,22、30页。。与此同时,在顺利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面对后全面小康时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郑重地作出了“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的重要论断,(2)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为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再次重申:“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并要求到2035年“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6,22、30页。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本质要求,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接点,二者历史性地交汇在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中国,形成一股同向而行的聚合之势。那么,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将带来何种机遇,又将形成哪些挑战,以及面对这些机遇与挑战,我们应当如何做出积极有为的主动应对?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针对上述时代之问,本文试图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讨论。
一、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一个分析框架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均属于复合型概念。数字经济一词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由美国学者唐·泰普斯科特首次提出。(4)Don Tapscott,The Digital Economy: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New York:McGraw-Hill,1996,pp.12-60.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如今数字经济普遍被认为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5)G20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itiative,September 5,2016.它通常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种典型形态,主要呈现信息化引领、开放化融合、泛在化普惠三个方面的显著特征。(6)梅宏:《大数据与数字经济》,《求是》2022年第2期。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数字经济起步较晚,1996年的规模为430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63、日本的1/23、英国的1/6。(7)马化腾等:《数字经济:中国创新增长新动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4页。进入21世纪后,我国数字经济开始加速发展,后发先至,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2016—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从22.6万亿元增长至45.5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从30.3%提升至39.8%。(8)数字经济数据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2022年7月;GDP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如果横向比较,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为7.1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相当于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主要国家的总和。(9)数据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2022年12月。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格局中,当前中国、美国、欧盟已成三足鼎立之势。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初心与使命。它可被视为“富裕”这一前置要素和“共同”这一价值取向的有机融合,故而天然包含了经济持续增长和分配更加公平两个维度,(10)谢宜泽、胡鞍钢:《基于诊断法的共同富裕之路——以示范区浙江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11期。反映了共同富裕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要求。在过去一百年,党带领全国人民先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改革开放中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消灭绝对贫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已经为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制度基础、物质基础和实践基础。经过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数十余载赶超式发展,2021年我国GDP达到114.4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的18.5%,人均GDP达到12 551美元,即将步入世界银行所界定的高收入国家行列;(11)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新理念引领新发展,新时代开创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2022年9月13日。在收入分配方面,虽然当前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仍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但相较于2008年的峰值(0.491),已经有所下降,2021年这一系数为0.466。(12)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据测算,以模拟的2035年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为基准,2019年我国共同富裕综合实现程度达到67%,比2011年提高了9.8个百分点。(13)吕光明、陈欣悦:《2035年共同富裕阶段目标实现指数监测研究》,《统计研究》2022年第4期。从全球范围来看,在所考察的162个经济体中,2020年中国的共同富裕程度接近世界平均水平。(14)万海远、陈基平:《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量化方法》,《财贸经济》2021年第12期。
立足于数字经济的两种形态和共同富裕的两个维度,本文构造了关于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在这一框架当中,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可以归结为四条路径:一是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产业化影响经济增长;二是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产业化影响分配公平;三是数字经济通过产业数字化影响经济增长;四是数字经济通过产业数字化影响分配公平。其中,第一和第三条路径主要是通过影响共同富裕的富裕之维进而影响共同富裕的整体实现;第二和第四条路径则主要是通过影响共同富裕的共同之维进而影响共同富裕的整体实现。当然,无论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它们对共同富裕的富裕之维或共同之维的影响都存在正反两个方面。

图1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15)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数字产业化下共同富裕的机遇与挑战
数字产业化即信息通信产业,它属于数字经济的基础部分,是数字经济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业、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业以及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业态。2021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8.35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总量比重的18.3%,占GDP比重的7.3%,(16)数据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2022年7月。与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大致相当,是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主导产业之一。
(一)数字产业化影响共同富裕的经济增长路径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每一次科技革命不仅会带领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也会催生一些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兴产业。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创了人类的蒸汽时代,同时诞生了运用机器生产机器的机器制造业;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创了人类的电气时代,同时也诞生了作为能源生产的电力工业。肇始于20世纪下半叶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亦是如此,它不仅开创了人类的信息时代,而且催生了作为信息时代基石的信息产业。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人类正在迅速从信息(Information Technology,IT)时代迈向数字(Digital Technology,DT)时代,信息产业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充。这些产业一方面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经济结构当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直接推动着经济增长。比如,1990—2020年我国电信业务总量从109.6亿元增长至13.7万亿元,三十年间增长了上千倍,其占GDP的比重也由原来的0.6%提升至13.5%;与此同时,2010—2020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也从1.4万亿元增长至8.2万亿元,占GDP比重由3.3%提升至8%。另一方面,数字产业化所形成的网络基础设施,正在产生着不可估量的正外部效应。2012—2021年我国网民规模从5.4亿增长至10.3亿,互联网普及率从39.7%提升至72.9%,移动电话普及率由82.5部/百人增长至116.3部/百人,电子商务销售额则由2013年的5.7万亿元增长至22.8万亿元,(17)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整整翻了两番。这些均有效改善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信息不对称局面,降低了人们信息获取和交易的成本,激活了社会闲置资产,拓宽了人们的生活半径,极大地促进了信息、资金以及商品的流通,间接拉动了经济增长。所以,无论是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还是间接作用,数字产业化都扩大了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数字产业化极大地拓展了经济增长的空间,而且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催生的机器制造业和电力工业相比,数字产业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绿色低碳环保等优良属性,更契合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要求。不过,即便如此,数字产业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存在现实条件的制约。
一方面是数字技术水平的制约。数字技术是数字产业化的源动力,因此,数字技术的进步程度决定了数字产业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限度。而数字技术与任何技术一样,它的进步方式无非通过两条路径,即内源式的自主创新和外源式的引进吸收。按照技术扩散的一般性规律,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通常先是向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然后进行技术模仿,再进行自主创新。如今我国数字技术正处于吸收引进向自主创新路径转换的关键过渡期,此时如果内部的自主创新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而又遭逢外部的技术封锁或技术压制,那么,这将引发潜在的数字经济安全风险,扩大数字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竞争已经成为国家间竞争最核心的部分。在科技竞争当中,信息技术竞争又几乎是最为关键和激烈的领域。近年来,美国以泛化的国家安全为由,率先挑起对华贸易战并向科技战延伸,不但将我国部分科技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列入所谓的“实体清单”(Entity List),阻碍正常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而且实施“小院高墙”策略,推出《芯片与科学法案》,对我国半导体产业进行出口管制、技术脱钩和极限施压,试图迟滞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在这一国际背景下,通信网络、集成电路、基础软件、核心电子元器件等的前沿技术成为影响我国数字产业安全的“卡脖子”技术。更主要的是,这些关键共性技术是整个制造业体系的基石,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极强的溢出效应。因此,美国的数字霸权主义行径不仅阻碍了全球的互联互通,而且它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的破坏将制约着我国数字产业的迭代升级,对我国未来一段时期数字经济的继续发展壮大造成一定冲击,进而成为影响我国共同富裕历史进程的最大外部变量。
另一方面是数字治理水平的制约。英国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指出:“技术革命在财富创造潜力上的充分展开起先产生出相当混乱而矛盾的社会后果,此后则需要一次重大的制度重组。”(18)〔英〕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田方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30页。换言之,技术创新对社会秩序而言不啻为一次震荡,为了实现技术与社会的再度耦合,技术变革与制度变革或治理变革需要相伴而行。这意味着数字治理的制度构建和能力提升速度也必须契合数字技术的发展速度,否则,数字产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将无法得到有效预防和及时纠正,从而演变为妨碍经济增长的“异己”力量。
以数字产业化重要表现形式的平台经济为例,互联网平台作为一种中介组织,它本身不从事生产也不进行消费,而是依靠规模优势和信息优势进行线上撮合,从而缩短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推动商品价值的实现,加快商品周转和货币流通的速度。(19)谢富胜、吴越、王生升:《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因此,平台经济存在着推动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面。与此同时,互联网平台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它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但依然无法摆脱资本逐利的属性。为了竞争流量抢夺用户,避免陷入只有少量用户加入的小规模网络均衡,互联网平台往往运用“先予后取”的赢利策略。在初创期,在风险投资的资金支持下采取“烧钱”模式快速扩张,让利于商家与消费者,获取稀缺的注意力资源;等到用户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在行业领域获得一家独大垄断优势后,互联网平台则逐渐暴露资本的本性,通过各种方式将流量变现,攫取超额的垄断租金。比如,在供给端,大型平台运用其与商家、劳动者的不对称依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逼迫商家对接入平台排他性地“二选一”或者压榨平台劳动者。有的对中小平台企业进行“降维打击”和“猎杀式并购”,以构筑难以逾越的市场壁垒;(20)王天晓、吴宏政:《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战略抉择》,《新疆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在需求端,则运用强大的算力和不断优化的算法根据年龄、职业、习惯、收入、偏好等信息对消费者进行数字“画像”,进行精准的广告投送和商品推介,营造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和加剧圈层文化,运用大数据“杀熟”,形成差异化的价格歧视。这些既挤压了生产端利润又侵蚀了消费者剩余,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阻碍了社会总福利水平的提升,甚至推动着数字产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走向反面,当然也与共同富裕的实践要求背道而驰。
(二)数字产业化影响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路径
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就业是参与收入分配的前提条件。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收入分配之维的主要渠道在于就业。既有研究表明,技术变革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效应,即破坏效应、转移效应和创造效应。(21)Brucker Matthias,Marcelo LaFleurand Ingo Pitterle,The Impact of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on Labor Market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Social Affairs Frontier Issues,July 31,2017.数字经济作为数字技术衍生的经济形态,从理论上而言,它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亦无外乎表现为以上三种效应。
数字产业化对就业市场既存在转移效应也存在创造效应。转移效应主要表现为消费互联网的兴起将商品零售、社会服务等部分工作由线下转移到线上。这更多影响的是就业的方式,而对就业的总量或结构影响较小。数字产业化作为完全因科学技术发展而产生的新兴产业,它对原有经济活动而言,属于扩大活动边界的增量调整,将有效带动就业总量的扩张,所以,数字产业化影响就业更主要的是创造效应。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提供的就业岗位已经达到1.91亿个,占全年总就业人数的24.6%,其中,数字产业化部分的就业岗位达到1220万个。(22)数据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2019年4月。如果单纯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来看,2003—2021年,已经从117万人增加至519万人,(23)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在过去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增长了4.4倍,成为所有分类行业当中就业增长最为迅速的领域。此外,依托数字技术的平台经济也催生了许多新的就业形态,各式各样的灵活就业模式为广大劳动者提供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外卖骑手、网络客服、直播带货、网约车司机等成为新生代劳动者重要的职业选择。当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左右,一些平台的外卖骑手达到400多万人;在平台上从事主播以及相关从业人员达到160多万。(24)数据源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2022年1月17日。这些新兴职业的技能门槛较低、工作时间宽松,工资也高于农民工的平均值,(25)李力行、周广肃:《平台经济下的劳动就业和收入分配:变化趋势与政策应对》,《国际经济评论》2022年第2期。扩大和提高了低收入者的收入来源和收入水平。“云客服”等职业打破了传统职业对工作的时空限制,更是为广大行动不便的残障人士提供了就业以及创收的可能。所以,借由就业创造这一渠道,数字产业化可以有效激发人们的潜能,吸纳闲散劳动力,从而提升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善收入分配局面,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社会的形成。
数字产业化扩大了就业空间,为许多劳动者创造和增加了收入,但由于其巨大的规模效应和高人力资本特征,数字产业化也显示出极强的“造富”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不同行业以及行业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信息产业或数字产业一直属于社会高薪行业。从平均工资来看,2021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均工资达到20.2万元,是所有行业当中最高的,为全体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1.9倍。(26)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而且数字产业的某些特殊人群,比如一些互联网巨头的领导层和明星员工,他们的收入或财富更是高到普通人永远无法企及的地步。据《福布斯》发布的排名,2022年中国内地富豪榜的前10名中,一半为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创始人,平均财富高达261.6亿美元;(27)数据源于《2022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2022年11月10日。既有研究表明,为了争夺具有高创新潜力的明星员工或保证老员工的忠诚度,相比于其他市场结构相对稳定的行业,软件行业通常许诺以高工资和股票期权等资本收入作为绩效奖励。(28)Andersson Fredrik,et al.,Reaching for the Stars:Who Pays for Talent in Innovative Industries?The Economic Journal,2009(119),pp.308-332.除此之外,数字产业化过程中的一些新兴行业逐渐呈现两极分化、“赢者通吃”的趋势。比如,网络直播等的流量和收入开始往头部主播加速集中,使之获取了与其社会贡献完全不成比例的高额收入,造成行业内部收入严重的苦乐不均。
三、产业数字化下共同富裕的机遇与挑战
产业数字化指的是传统产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数量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它的实质是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马克思曾经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2页。产业数字化虽然没有改变人类“推磨”的方式,但它在加入了数据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后,基于海量数据所产生的信息与知识,优化了人类“推磨”的决策和流程,提高了人类“推磨”的效率,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具有了等同于生产工具变革的重要意义。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产业数字化已经成为我国数字经济的主要形态以及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据测算,2021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37.2万亿元,约为2016年的2.1倍,占数字经济比重的81.7%,占GDP比重的32.5%。(30)数据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2022年7月。
(一)产业数字化影响共同富裕的经济增长路径
根据索洛模型的分解,经济增长的源泉可以归结为劳动投入的增加、资本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三个方面。(31)Solow Robert,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1),pp.65-94.产业数字化是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改造以创造条件让数据这一要素参与生产的过程,因此,它不涉及劳动要素或资本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主要是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影响共同富裕的经济增长之维。进一步地,产业数字化之所以可以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关键在于它对生产工具的增效赋能。
生产工具是衡量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以往历次科技革命首先改变的都是人类从事社会生产所必需的生产工具,通过改变生产工具提高劳动效率,进而推动经济总量加速增长和社会财富加速积累。不过,在工业时代,无论是蒸汽机还是内燃机,生产工具变革本质上改变的都是能量转换的方式。与之不同的是,数字时代的生产工具变革主要是对已有生产工具的智能化改造,使之在数据、算法和网络的共同作用下自动地进行更及时的、更精准的决策和操作,从而全方位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财务成本,提升企业的劳动生产效率、资本使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有效对冲因老龄化和少子化引发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负面影响。既有研究表明,相比于非数字化企业,数字化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平均利润率更高,成本费用率更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2)赵宸宇、王文春、李雪松:《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财贸经济》2021年第7期。除此之外,还有研究指出,经济的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服务分工、提升产业协同、创造数字孪生三个并存又继起的步骤,推动着全社会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源泉。(33)江小涓、靳景:《数字技术提升经济效率:服务分工、产业协同和数实孪生》,《管理世界》2022年第12期。
作为数字时代降本增效的重要手段,产业数字化对经济增长的挑战不在于它本身存在何种弊端,而在于当前它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不充分与不平衡的格局,这严重制约着其潜能的整体释放。首先,产业数字化发展不充分主要表现为我国数字技术的产业渗透率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一定差距。近年来,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后,在“无接触”式经济的倒逼之下,我国不同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不断提速,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数字经济渗透率均有了明显提升。2016—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从6.2%、16.8%和29.6%提升至8.9%、21%和40.7%。(34)数据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年4月。然而,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全球代表性国家相比,除第一产业渗透率略高于8.6%的平均水平之外,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渗透率均低于24.3%和45.3%的平均水平。如果与世界先进国家比较,则其中的差距更为明显。比如,在第一产业,英国的数字经济渗透率已经超过30%;在第二产业,德国、韩国的数字经济渗透率已经达到40%以上;而在第三产业,英国、德国、美国的数字经济渗透率已经高于60%。(35)全球层面以及各个国家的数据为2021年。数据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2022年12月。在上述对比中可以瞥见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巨大空间。
其次,产业数字化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存在较大差异。随着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不同地方政府都敏锐地察觉到产业数字化势不可挡,也都纷纷有意识地出台政策进行提前布局,但不同地区的数字化转型结果却不尽相同,东部地区的发展程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从产业数字化占GDP比重来看,2020年东部地区绝大部分省份均超过30%,上海更是高达45.1%;而在中西部地区,除了湖北和重庆之外,其余省份基本处于20%—30%之间。(36)数据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年4月。如果从城市空间观察,产业数字化已经形成“两超八极”格局,它们全部位于一线和二线城市,(37)“两超”指的是北京和上海两个产业数字化的超级牵引城市;“八极”指的是福州、大连、广州、重庆、西安、深圳、南京、苏州。详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2022年7月。而且在这一格局当中,除了重庆和西安两座西部城市属于增长极之外,北京和上海两个超级核心以及其余六个增长极均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它们成为全国产业数字化技术、方案和人才的输出地,牵引着周边地区的数字化转型。此外,值得警惕的是,在摩尔定律的主导下,数字时代的技术迭代呈几何级态势,其速率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迅捷,因此,东部地区数字化转型的先发优势与中西部地区的后发劣势随着时间推移可能进一步拉大,甚至固化为产业数字化的区域鸿沟,从而扩大区域间产业数字化本已存在的不平衡局面,进而影响不同地区共建共同富裕社会的整体步伐。
(二)产业数字化影响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路径
与数字产业化类似,产业数字化和收入分配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主要也是以就业为中介。不过,与数字产业化不同,产业数字化对就业的影响主要是创造效应和破坏效应,而且二者的力量均不容忽视。
首先,在产业数字化转型大潮的带动下,许多新型职业应运而生。比如,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农业数字化技术员、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物联网安装调试员,这些都已明确列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新职业目录。当前以数字化新职业为代表的就业市场需求旺盛、就业前景广阔,短时间内仍处于严重的供不应求状态。据测算,2018年我国产业数字化就业岗位达到1.78亿个,占全年就业人数的23.5%。(38)数据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2019年4月。即便如此,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缺口仍然超过500万,预计2025年缺口将突破1000万,届时物联网行业的人才需求缺口总量也将超过1600万,大数据行业的人才需求规模将在2000万左右,数字化管理师的市场需求量和从业数量将呈现井喷式增长,将覆盖全部一级行业和全部96个二级行业。(39)数据源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阿里钉钉:《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2020年7月。产业数字化新职业的诞生及其海量需求不仅将改变未来职业版图,也将成为广大劳动者参与社会财富创造和分配的重要渠道。
其次,产业数字化在创造就业的同时,也将引发就业毁灭。其原因主要在于产业数字化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单位生产效率的跃升,这使得在生产和提供同等数量商品和服务的前提下,所需要的劳动投入和劳动时间趋于下降。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机器换人”产生的替代效应发生作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机器设备不仅极大地解放了从事简单劳动的体力劳动者,也极大地解放了一部分从事复杂劳动的脑力劳动者。在数字化的生产场景之中,劳动者的角色恰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劳动表现为不再象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8页。这一方面推动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让人们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更富有创造性的活动,彰显了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将广大劳动者暴露在失业风险之中。研究表明,1990—2007年每千名美国工人中每增加1个机器人,全美就业人口比例就会降低0.2个百分点。(41)Acemoglu Daron and Restrepo Pascual,Robots and Jobs: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20(6),pp.2188-2244.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报告预计,到2025年,新技术的引进和人机之间劳动分工的转变将导致全球85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而且相对于2020年,几乎所有生产任务都倾向于更多地使用机器,只不过在信息检索、数据处理、传统劳动等方面替代地多一些,在人类依旧保持相对优势的管理、推理、决策、沟通等方面替代地少一些。(42)World Economic Forum,The 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0,October 2020.如今我国正处于数字化转型期,经济结构新老业态的快速交替将加剧产业数字化对就业市场的创造效应和破坏效应,形成暂时的结构性失业风险,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这种态势将更为严峻。
四、数字经济时代加速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应对
数字经济乃大势所趋。无论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它们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当然,也必将深刻影响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根据前文的分析,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既是不可多得的机遇,也是无法回避的挑战,而且机遇与挑战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因此,若要最大限度地运用数字经济加速推动共同富裕,关键在于更好地发挥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从技术、产业、治理和社会等层面多管齐下,采取适当的公共政策因势利导,让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正面效应最大化、负面效应最小化,努力促成挑战向机遇的有效转化。
(一)在技术层面,集中力量攻克核心技术,实现数字技术高水平自立自强
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的技术基石,是驱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这一数字经济双螺旋交替攀升的原始动力。它不仅决定了数字经济的发展高度,也影响着数字经济的产业安全。在时间维度层面,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沿着同一方向展开,故而数字技术也构成了共同富裕的技术基石,决定着共同富裕的行动进程与质量成色。面对部分关键核心数字技术受制于人的境况以及美国等国家的极限施压和技术脱钩,必须放弃以市场换技术的幻想,改变长期以来“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拿来主义”思维惯性,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43)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年第2期。更加自觉地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内源式的原始创新能力,加快自主创新步伐。一方面,尽快补齐技术短板,集中力量攻克数字时代软件和硬件方面的“卡脖子”技术,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和国产替代;另一方面,做长技术长板,换道超车,掌握一批数字时代的杀手锏、颠覆性、非对称技术,不断增强对抗甚至反制西方数字霸权主义技术霸凌的底气和实力。依托强大的科技实力加速推动数字产业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牢牢把握数字经济的发展主动权,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扎实的技术支撑。
(二)在产业层面,全面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扩大数字时代共同富裕的社会财富
产业数字化是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以及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抓手,也是数字时代做优做大共同富裕“蛋糕”的倍增器。在日趋激烈的全球产业数字化竞争中,应当充分发挥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市场失灵领域的不可替代作用,从环境、意愿、能力三位一体的视角全面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尤其是针对第一和第二产业以及中西部地区和三四线城市,更需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和“东数西算”等区域政策的调节作用,弥合产业间和区域间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差距,推动数字化红利向不同产业和不同区域全面渗透。首先,需要统筹推进5G基站、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网络和算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道路、建筑、电网、物流等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加快数字中国建设,为产业数字化全面转型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扫除企业“不能转”的各类制约因素;其次,针对企业数字化改造的前期投入,设计激励相容的税收抵免和贴息贷款等支持政策,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和成本,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充足的内生动力,逐步引导企业在生产、营销、管理等各个环节形成数字化思维,消除企业“不敢转”的畏难情绪,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意愿;最后,立足企业数字化转型痛点和难点,培育一批既懂技术知识又懂行业知识的专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供应商,推广一批面向不同类型企业的数字化应用典型方案,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自建或与互联网科技公司共建数字平台,形成数字化转型的示范效应,多管齐下破解企业“不会转”的现实困境,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能力。
(三)在治理层面,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健全完善适应共同富裕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为了确保数字经济始终前进在共同富裕的轨道,应当运用共同富裕的价值理性引导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扭转数字经济治理落后于数字经济实践的“治理赤字”局面,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形成现代化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积极引导科技向善。在宏观的顶层设计层面,结合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和目标安排优化数字经济的战略规划和评价体系,赋予数字技术正确的价值观,扩大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契合面;在中观的法律制度层面,明确数字经济时代劳资双方以及生产者、互联网平台和消费者之间的权利边界,运用法治手段规范遏制算法乱象,推动算法黑箱透明化,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为王、野蛮生长的草莽阶段向有序竞争、多元共治的规范阶段平稳过渡,重点保护作为共同富裕主体的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将数字经济新就业群体纳入社会保障范围之内,塑造平等公正的数字化生产关系;在微观的监管执行层面,主动破解长期以来的行业监管和属地监管的思维定势,按照数字经济客观运行规律重塑监管理念、监管主体、监管责任和监管手段,强化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协同监管,积极预防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共同打击不正当竞争,动态把握鼓励数字技术应用创新和反对数字平台恶意垄断的平衡点。
(四)在社会层面,全方位强化数字教育,面向共同富裕不断提升全体人民数字素养
数字鸿沟一般表现为数字接入、数字技能和数字福利三个不同层面的不平等。随着宽带中国等战略规划的深入实施,如今我国数字接入不平等的鸿沟已经基本弥合。数字技能不平等成为当前数字鸿沟最集中的表现形式,这也是数字经济时代结构性失业产生的根本原因。而数字技能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数字教育的滞后与失衡。数字教育是数字时代的基础性工程,是数字时代实现数字化生存避免沦为“数字穷人”的治本之策,也是缩小数字鸿沟、共享数字红利的重要途径。因此,破解数字时代的共富难题终极突破口在于将数字教育全方位融入国民教育体系。这不仅需要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阶段开设数字专业,规模化培养数字技术专门人才,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人才支撑,也需要在义务教育阶段进阶式地有机融入数字教育的内容,提高全民的数字素养和数字学习能力;不仅需要在学校教育阶段重视数字教育,也需要立足于数字时代的知识结构,针对下岗失业特定人群,面向再就业提供灵活的数字技能公共培训,通过教育培训改变人力资本结构以适应变化的就业结构;不仅需要通过规范化的渠道提供数字教育,也需要面向全体人民开展新时代数字扫盲运动,完成全体人民尤其是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等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启蒙,加速推动数字技能的扩散,提升全民共建数字时代共同富裕社会的参与感和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