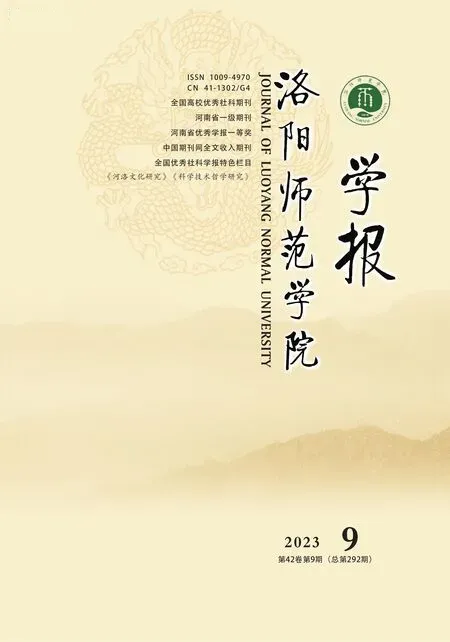奥斯汀的语言哲学思想研究
吕焱莘
(1.陕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2.西安邮电大学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1)
英国哲学家约翰·朗肖·奥斯汀是日常语言哲学牛津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分析哲学的领军人物。他的哲学理念对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创见性地提出了以言语行为理论为代表的一系列语言哲学思想,在整个语言哲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位置并影响了后来一批哲学家和语言学家。
奥斯汀及其理论正式进入中国始于许国璋先生于1979年引入并翻译了《如何以言行事》(Howtodothingswithwords)一书。实际上,国内可查到的最早关于奥斯汀的文献是1963年发表于《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的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教授麦克斯·布腊克撰写的《奥斯汀论行事语》和由英国牛津大学圣体学院院长撰写的《奥斯汀论知觉》。60年来,国内对奥斯汀哲学思想的研究受到了诸多来自哲学、语言学、翻译学、语用学等各个学科学者们的关注。学者们最关心的研究重点首先是言语行为理论及其应用,其次是奥斯汀和其他哲学家,如塞尔和维特根斯坦等的比较研究,还有一些研究者关注奥斯汀的其他哲学思想。学界对奥斯汀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绝大部分聚焦在言语行为理论上,对其整体的语言哲学思想关注很少,鲜有文章勾勒奥斯汀语言哲学思想的全景。
奥斯汀的语言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如何以言行事》《感觉与可感物》与《哲学论文集》三本著作中,这三本著作都是由他的学生在其去世后才整理出版的。《如何以言行事》是奥斯汀的代表作,是其流传最广、最为系统,也最被学界接受和认可的作品,书中详细地论述并阐释了言语行为理论。在《感觉与可感物》中,奥斯汀以艾耶尔的《经验知识的基础》为讨论对象,运用概念分析法分析感觉材料理论。《哲学论文集》由奥斯汀的学生汇编其七篇论文而成,其中包括了他对诸多传统哲学和语言哲学问题的思考。在众多对奥斯汀哲学思想的研究中,杨玉成所做的工作最为全面,他不仅在2013年翻译了《如何以言行事》,更针对奥斯汀的知识观、语言现象学、感觉材料理论等分别撰写了相应的文章,对学者们全面了解奥斯汀的语言哲学思想有很大帮助。
一、语言哲学
哲学是一门探求宇宙和世界本原的学科,从古希腊时期人们在自然的支配下不断追问存在实在性的毕因论,到近代开始思索人的知识从何而来,如何获得真知的认识论,再到20世纪试图用语言来解决哲学问题,语言哲学由此诞生,哲学研究的方向也一直在不断调整变化。学界一般认为语言哲学有指称理论和意义理论两大理论支柱。
奥斯汀的语言哲学思想的核心在于通过对日常语言做各种细微的分析从而了解它们真实的含义和实在的世界。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的指称观、意义观、言语行为理论、知觉观和语言现象学才能有机地融为一体,形成一整套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且内部环环相扣,相互说明,互相印证。
二、奥斯汀的语言哲学思想
(一)奥斯汀的指称观
实际上,奥斯汀从未正面明确且清晰地回答或解决过传统哲学问题,例如是什么决定了指称关系,这也是他一直被许多批评者诟病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从《哲学论文集》中,我们仍然能窥见一些他对于指称的观点。
奥斯汀的指称观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或者说承认弗雷格的含义与指称理论。认为现实实在和意义的联系需要一个中介。在《如何言说》(How to talk)一文中,奥斯汀提出了一种理想的语言情况:言语情景S0(Speech-situation S0)[1]134。S0语言的词汇由受某些约定支配的符号或声音组成。如果不考虑支配它们的约定,这些声音或记号被称为词壳(vocables)[2]52。他将词分为两类:一类是I词(事项词),即按照指称约定形成的词壳,与世界中的事项相关联,概念与专名相似;另一类是T词(类型词),则是按照含义的约定而形成的词壳,与世界中的类型相关联,类似于通名。奥斯汀认为,在S0中无论何时我说出一个断言,我即因此在进行指称又在进行命名,即我在运用I词指称世界中的个项并且用T词命名世界中的类型[2]58。无论是指称还是命名,都需要遵守一定的、共同的约定。但这个约定并不是直接、简单、唯一将意义与实在联系起来的,而是需要放置到具体的使用场景中才能加以判断。这个约定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奥斯汀认为的是什么决定了指称关系的问题。
奥斯汀认为指称关系具有任意性和不确定性。在《一个词语的意义》(The meaning of a word)一文中,奥斯汀提出了“X的意义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试图通过回答这一问题来说明指称关系不是一锤定音的。在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奥斯汀认为只有句子有意义,想要知道单词或短语的意义就要知道它所存在的句子的意义[1]56。他解释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在于人们普遍相信所有单词都是指称,并且是专名,因而代表了某物。但是认为通名像专名一样具有指称意义,或者专名像通名一样具有内涵意义的看法却通常会导致错误[1]61。第二在于一旦分析某一个句子中“X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往往还会继续追问“X在这句话中到底是什么?”从而又引来更多的问题,而单词在每一个句子中的意义又不是完全一致的。此外,奥斯汀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还提出一个长久以来被哲学家们忽视的问题:为什么用同一个名称来指称不同事物?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实际的日常语言中,而不能使用理想语言。唯名论者认为这是因为这些事物都是相似的。奥斯汀批判了这种观点,他认为这不仅与事实不相符,对“相似”一词如何定义也成了问题,因而不能简单地用“相似”来解决。指称关系应当回到切实的事实当中。
在语言的使用中,误名和误指是很常见的情况,但少有语言哲学家探讨这一问题,奥斯汀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首先,误名和误指来自对约定的违反。误名指引用或赋予了错误的名称,误指则是指引用或赋予了错误的含义。无论是误名还是误指都会误导听者,并且都是对言说的意义而非对事实的误导。其次,误名和误指可能是违反常规的,或是异质的。违反常规的误名、误指意为违反了共同被接受的语言规定,异质的误名、误指意为共同被接受的语言规定中出现了错误。
除了误名和误指之外,奥斯汀指出还存在误识。误识需要跟误名明确区分开。误识是指尽管名称确实匹配事项的类别,但名称和含义都是错误的,或者含义是正确的,但名称却不匹配事项的类别。在日常语言中,言说行为的名称数量众多,更为专门化,更模糊,也更重要。我们的言语与所谈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存在各种各样的情况,误名、误指等问题在日常使用中是难以避免的,但识别和区分这些错误却非常重要,不仅能够使言语更加适当,并且能更进一步理解指称和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奥斯汀的意义观
从古至今,对于意义究竟是什么,哲学家们的观点不一而足。从古希腊的本质论,到近代洛克的观念论,再到摩尔的命题论,对意义的看法存在着各种派别。与对指称的观点相似,奥斯汀虽没有明确、清楚地表述过自己的意义观,但他同样在演讲和讲义中表露了对意义的看法。
奥斯汀的意义观不以真假为标准。他推翻了认为逻辑-语义的真值条件是语言理解的中心这个观点,便直接进入了言语行为的描写[3]。奥斯汀认为语言意义与言语行为是关联的,行为话语的得体与其陈述的事实是否为真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4]。日常语言中,并非所有的语句都有真假之分,许多语句既不为真也不为假,因此用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来判断意义是不恰当的。基于他对语言的观察,奥斯汀将语句分成不同的类别,在规避将“真假”作为唯一意义标准的同时,补充了人们对日常语言的认识,并提出以“说话就是做事”为核心观点的言语行为理论。与前人不同,他从行为的角度来研究意义,意义存在于语言行为之中,完成言语行为意义也就得到了表述,甚至可以说研究言语行为就是研究语词的意义。不仅如此,奥斯汀还提出了“适切”的概念,作为对语句意义的补充。尽管不是所有的语句都有真假,但在特定的语境中说某句话是否得体,是否适切是相对确定的。
奥斯汀对“真”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看法。在《哲学论文集》中的多篇文章中,包括《真理》(Truth)、《对事实的不公》(Unfair to facts),《一个词语的意义》(The meaning of a word)等,他都细致地分析了“真”“真理”“事实”等传统哲学概念。首先,他没有对什么是真理以及真理的本质是什么多加讨论。实际上,奥斯汀对大部分传统哲学概念的本质,即它们究竟是什么,抱有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这些概念取决于如何解释这些词语。因而,奥斯汀认为“真理”取决于人们把什么东西看作真的或者人们对什么东西使用“是真的”这一表达[1]118。那么,什么是“真”就没有一个确定的回答。尽管上文提到奥斯汀推翻了逻辑实证主义将真值条件作为意义的中心这一观点,但他并不是全然拒绝“真”这一概念。他主张约定真理符合论,即一个陈述在符合事实的情况下为真,言词与实在之间约定的符合。其次,奥斯汀将“真”视为一个评价的维度。因为陈述在不同的语境中由于不同的目的以不同的方式符合事实,而非简单、全然、绝对符合事实,也就不能轻易断言真假,而是从某一角度、某一情况、某一场景考察语言的意义。
奥斯汀的意义观还与语境密不可分。弗雷格最早提出上下文理论(Contextualism,也有学者译为语境论),主要关注词语之间的关系,认为一个词语只有在一个命题中才有意义[5]。维特根斯坦的意义使用论与其内核一致,他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奥斯汀继承了前面两位学者的看法,他同样认为语境与意义密不可分。他强调不存在脱离语境的单纯意向性的言语行为。我们必须注意现实语境的情况。注意我们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以及究竟为什么[6]。这就与“适切”联系起来。一个语词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变迁是自然概念的本质而不是偶然具有的一个缺陷[7]8。对语境的强调是一种动态的意义观,这意味着哲学家发现并承认意义并非一成不变、静态固定的,而会随着语境等因素不断变化,这为如何认识意义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结合了真、适切、语境和言语行为等多个评价维度的意义观也成为了奥斯汀提出言语行为理论的哲学基础。
(三)言语行为理论
奥斯汀语言哲学思想的核心是言语行为理论,其撰写的《如何以言行事》一书完整地阐释了这一理论。奥斯汀并不认同哲学家们对陈述的任务只能是描述某种事态或陈述某个事实,且这种描述和陈述必有真假之分的观点,并对如何区分问句、命令句、陈述句提出了疑问。他认为“说出句子显然并不是要描述我在做我说这句话时我应做的事情,也不是要陈述我正在做它:说出句子本身就是做我应做或在做的事情”[8]9。他建议将这种类型的句子称为施行句,而将能够用传统语言哲学中的真假加以判断的句子称为记述句。他还提出了施行句的判断标准:恰当。“我们把有关在说施行式的场合可能是错的或者可能出错的事情的学说,称作是有关不恰当的学说。”[8]17并指出共有六种类型的不恰当。然而,他发现有些句子既不能用恰当也不能用真假进行判断,因而在后期对施行和记述的二分法做了补充,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分别是话语行为“在说某些事情时我们所做的一组事情”;话语施事行为“实施例诸如告知、命令、警告、承诺等话语施事行为,即具有一定(约定俗成)力量的话语行为”;话语施效行为“通过说某些事情我们实现或取得某些效果,如使人信服、说服、阻止甚至是使人吃惊或使人误导”[8]103。在此基础上,他将话语施事力分为五个类型:裁决式、运用式、承诺式、表态式和表明式。
言语行为理论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奥斯汀深受这两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影响。首先,奥斯汀接受了弗雷格对于指称和含义的理论,这一点在他的指称观中已有体现。他将一种话语行为的意义(含义与所指)作为施行话语和记述话语的区分维度之一,表明了对言语应有含义和所指两个层面的意义的认同。其次,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学说与奥斯汀的哲学思想密不可分。奥斯汀最受公认的成就是言语行为理论,而维特根斯坦的 “语言游戏”可以被视作这一理论的先声。语言游戏的根本在于一种实践方式 (行动方式) 。话语即行为[9]。他们对语言哲学的研究都出自使用的视角,强调研究使用中的语言和语言应该如何被使用。语言哲学研究至此从传统的静态论证发展到全新的动态探索,语言与行为之间的辩证关系得到深刻阐释,这不但是对逻辑实证主义观点的重新思考,也是对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的发展和继承。奥斯汀“说话即行事”的思想从会话层面探索语言的种种意义,它深度揭示了人类日常语言的真实状况[10]。言语行为理论打破了传统语言哲学中只关注语言和世界的静态二元论,引入了第三元,即人类,还将目光投射到语言除指称和意义之外的第三个研究维度:功能。这对一直纠结于语言的逻辑和真假的传统语言哲学研究无疑是一大创新性的突破。但必须承认的是言语行为理论还存在着种种不足和局限性:一是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仍不完全且缺乏普适的标准,许多维度之间存在重叠、混乱和繁杂的情况;二是缺乏对听话者的关注,只注重说话者及其话语,忽视了言语的交流和意义的传达是一个说话与听话的双向过程;三是无论是言语行为二分说还是三分说,都只注重对施行话语的分析,对记述话语和话语行为的探讨极少,因而整个理论体系不够完善。
言语行为理论甫一提出,对许多哲学家产生了影响,也对语用学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奥斯汀的学生、美国哲学家塞尔在老师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并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语言哲学观点。他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更具有系统性、逻辑性和规约性。他将奥斯汀提出的各类言语和行为更为细致地做了重新划分,还将人类语言和行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并引入了“意向性”的概念,极大地拓宽了语言哲学的研究范畴。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为语用学注入了生命力并成为了学科的重要的理论支柱,使语用学摆脱了与语义学纠缠不清的研究方向,拥有了独立的学科理论和内容。此外,言语行为理论也不断和新学科、新技术和新方向相结合,间接刺激了社会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新兴学科的发展。
(四)奥斯汀的知觉观和语言现象学
知觉观和语言现象学也是奥斯汀语言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他的指称观、意义观和言语行为理论一脉相连,密不可分,是共享一致的思想内核。但很少有学者聚焦这两部分内容,从而完整地描绘奥斯汀哲学思想体系,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知觉”尽管在语言哲学领域中被讨论得较少,但本身却是一个很古老的哲学问题,其关键在于人们是感知物质实在还是感知感觉材料。奥斯汀的知觉观在《感觉与可感物》一书中得到了全面而集中的表述。他以逻辑语言学家艾耶尔的《经验知识的基础》为讨论对象,借助概念分析的方法批判建立在“依据错觉的论证”的基础上的感觉材料理论,并提出了自己对感觉和可感物的看法:“我们从来不曾看到或以其他方式感知(或‘感觉’)到物质对象(或‘物质事物’),无论如何,至少我们从来不曾感知或感觉到它们,而是只感知到感觉材料(或我们自己的观念、印象、感觉项、感官感知、感知项,等等)。”[7]2他对感觉材料的批驳主要在于:我们确实会在各种反常的条件下感知各种各样的事物,但我们没有理由引进非实在的或非物质的“感觉材料”作为错觉中的觉知的直接对象,因为我们在各种情况中所知觉到的事物都是实在的[11]。与奥斯汀对其他传统哲学问题的看法类似,他首先对感觉、感知等词语的用法和意义提出了疑问,认为它们是哲学用语,而非日常用语。其次,他认为关于感官感知的问题被过于简单化和格式化了。感知的实际情况比哲学家们通常认可的更为多样和复杂,因而要抛弃对一体化的积习和对二分法的膜拜。
奥斯汀将自己对语言的探究和分析称为语言现象学,主要研究人在什么时候会说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用什么词,通过对特定术语的使用做细致的研究来处理或消解某些传统哲学问题[12]。这就将上述对奥斯汀语言哲学思想的讨论全部涵盖了进去,因此甚至可以说奥斯汀的语言哲学思想就是语言现象学。这一名称的提出一是为了克服传统语言哲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揭示传统哲学中对术语的滥用和对日常词语的混淆,将语言与现实连接在一起,将语言面向事情本身。二是为新的语言科学,即语用学的诞生铺设了道路。从新的视角出发解救处于混乱中的语言哲学问题,并使其成为一门新的独立学科。有学者认为,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其实就是关于语言的现象学,语用哲学和语言现象学有着内在的一致性[13]。奥斯汀还为自己的语言现象学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步骤:一是选定研究领域;二是尽可能完整地收集所有与研究领域相关的语言资源;三是以语言现象学的通常方式研究词语可以在什么情况下被使用;四是系统表述第三步所取得的成果;五是依据上一阶段的成果检验传统哲学的论证。与其他语言哲学理论相比,奥斯汀的语言现象学不仅视角独树一帜,而且更清楚地阐释了理论原则和具体的实践方法,对语言哲学的发展意义深远。
三、结语
奥斯汀的语言哲学思想是语言哲学史上一颗光芒璀璨的明珠,他对指称、意义、知觉的观点共同组成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哲学基础,经由对哲学术语和日常语言进行微小细致的分析进而发展为一套系统的语言现象学学说。这不仅是一条学习哲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必经之路,更能启发后人沿着他的思想路径继续探索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不但如此,他的语言分析方法和对传统哲学问题的思考与突破也为中国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对中国哲学和语言学的发展有所裨益。